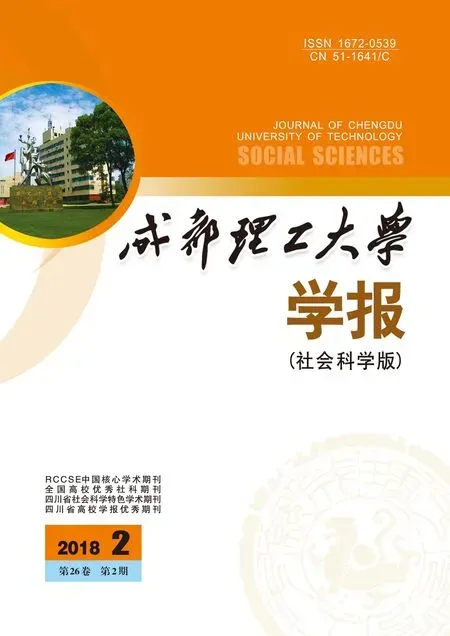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秘密条款解读
2018-03-20郭宇航
郭宇航
(德国明斯特大学 哲学学院,德国 明斯特 48149)
1795年,康德模仿相关外交文件,按照条约的形式写出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基于反思欧洲各国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与灾难,康德渴望能制定出社会生活的规则,巩固道德,实现永久和平,进而把人类从一些人的肆意妄为中解救出来,表达了哲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永久和平论》 共分为五部分:引言,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系论以及附录。其中,康德对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的描述较多,在最后一部分,康德反对实践政治家“鬼鬼祟祟的政治”, 因为其自身的“表里不一”[1]386f和旨在诡辩,实践政治家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以欺骗他人为目的(详见康德的论文《雄辩术》)。在《雄辩术》里,康德以“启蒙者”的口吻论述这样的欺骗是如何称不上道德的,从而对一般人民群众进行启蒙。从1794年10月到1797年期间康德发表的论文里不难看出,康德对文字修辞运用得淋漓尽致,康德引出秘密条款带有非常明显的启蒙者的意味:“哲学家们关于公共和平可能性条件的准则,应当被为战争而武装起来的国家引为忠告。”[1]374。康德表述“秘密”条款含有一种内在矛盾,“即探讨公共法权时的一项秘密条款在客观上,亦即在内容上看是一个矛盾;但在主观上说,就提出这种条款的人格资质来评判,其中却完全可能有一个秘密。”[1]374即个人“主观”上的考虑,如何在“客观”上达成对秘密条款的一致同意,且最终成为对公众行之有效的条款。康德不仅讽刺地提出“秘密”条款,同时也强调,实践政治家不应一味指责理论政治家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危害当前政府的地位。如在前言康德所描述的保留条款(拉丁语Clausula Salvatoria),即“老于世故的政治家与理论的政治家发生争执时,也必须行事始终如一,不要在他贸然提出并且公开发表的意见背后嗅到对国家的危险”[1]368。对于如何确立和平准则,康德表示,国家将“悄无声息地”要求公民“公开自由地谈论关于发动战争和确立和平的普遍准则”[1]369。康德稍后补充到,在确立和平普遍的准则上,“不需要特殊的安排”[1]370,因为“普遍人类理性”提供了这样清晰的要求。
秘密条款出现在《永久和平》的最后并且只占一页篇幅,相比其他条款,康德对秘密条款的表述显得极其精炼,但是解读秘密条款就发现,它实际上贯穿了康德后期之于政治和哲学的见解,因此解读秘密条款对于理清康德对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对秘密条款进行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对秘密条款进行四个部分的解读: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哲学家王”的政府,实践知识何以可能,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分配。四个部分的解读所依据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中的思想脉络,康德首先从否定哲学家从事政治首脑工作,然后反对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模式,再到阐述哲学能够指导实践因为人具有实践理性,最后解释哲学和政治的分工是历史文化的进程,哲学绝不会从政治领域撤出。
一、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
首先,康德批评古罗马预言式的战争决定论,在古罗马,虔诚的祭司通过预言等仪式来决定战争或者和平。在任何正式的战争来临之前规定有三十天的时间对战争进行准备,在此期间,公众向祭司咨询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种种未来情形,从而最后决定是否发起战争或者缔结和平条约。古罗马共和国思想家西塞罗(Cicero)提到,在古罗马院制下,祭司的预言是国王利益的体现,例如,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通过祭司对战争的声明,创造了法律(拉丁语Ius),即通过虔诚者的法则以达到最大正义(拉丁语Iustissimae),任何战争不应该攻击和反对这种神圣法则,即,我们获取权力是为了人民。”[2]
祭司的预言往往考虑国王利益而成为某种形式的口号,忽视了真正民众的诉求。康德指出,不同于祭司协商式的预言,哲学家的协商不应只关注于形式方面,而应真正地提出政治见解。不同于祭祀预言者,康德提出,广义上的哲学家没有特殊政治权利,只是提供咨询工作。康德谈到的哲学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哲学家是指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狭义的哲学家指仅从事哲学专业的人,康德实则更加推崇广义的哲学家,后者代表了人类理性。在论文最后,康德指出,一个公众辩论的王国是必要的,所有人都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发出理性之声,而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权利不能被限制在任何特定专业的群体[1]374。康德对秘密条款批判是积极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公众和其内在理性,在康德语境下,哲学家就是公众。在最后总结中,康德指出,普遍理性不局限在特定的专业群体,人们相信,通过公共讨论,理性能够被检验。因此,普遍理性能够达到事实理性。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去审问或否决他人观点,康德反对的是一种狭隘自由观,即,自由只是每个人有能力公开地谈论自己。
其次,哲学家为了自身去行动。康德认为哲学家们不作为从事政治的特殊角色,哲学家也没有特殊义务讨论政治问题以达到某种共有标准,因为哲学家“不管被禁止与否,都将这样去做”[1]241。哲学家的责任是“自由地”积极保卫“人们的一般权利”[1]304,哲学家始终如一地保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既不需要被鼓励,也不需要被审查依据某种政治制度,因为对哲学家来说,主观上对他们最苛刻的控制即是对真理的控制。通常对政治制度、道德、哲学还有科学的讨论都是浅谈辄止,哲学家应该在深层意义上去捍卫和做出对事实的声明,也就是做出道德或者法律有效性的声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常常使用“公正”作为这种有效性声明的隐喻。康德前提预设一个“理性法庭”,即使没有外部的公正条例,理性内在依然能够提出改变。理性思考是为了理性本身,没有人能够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反对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哲学家的意见代表每个人持有的共有立场。
广义上的哲学家代表每个人的立场或者普遍理性,但康德并不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如此。按照康德的秘密条款,哲学家代表了普遍理性,他们的职责是追求真理。在《永久和平》附录1中,康德提到“道德政治家”拥有“政治智慧”(德语Staatsweisheit),并不表明康德认为哲学家拥有特殊政治智慧或者“世界智慧”(德语Weltweisheit)[1]306。政治智慧在广义来说就是普遍理性,但是普遍理性有时候会被束缚。康德举出了法官和律师的例子,法官和律师往往被现实因素束缚而不能完全发挥实践理性。法官在办公室里只是从事“制定国家政策”的工作,而不是“自由的”判断。法官的工作“总是仅仅意图去掌控”国家,其本身是遵从官方的意志,制定政治政策并且依据执行。加入某种利益政党的律师必然首先应对政党忠诚,当试图去攫取政治力量时,律师或许被腐蚀。相比之下,哲学家不期望有这样的政治特权,在《学科之争》的总结中,康德再一次阐明,哲学家的职责是去引导人们考虑自己的权利和对国家负有的责任,哲学家是“人们普遍权利宣告者和解释者”[3]89(《学科之争》)。法官和律师被外部因素束缚,没有审视自己,但康德没有对法官和律师做过多的贬低,因为律师和法官作为实践者,并不怀有赞同他人立场的冲动,而是积累足够多的论据,在这方面他们尊重自己行使了“国家力量”[1]369(《面向永久和平》)。康德提出,在罗马,公正(拉丁语Justia)的象征为蒙住了眼睛的女神,右手边握着剑,左手边也握着相同的剑,康德怀疑律师对权力的渴望比对自己理性的审视相比更大。这里,在公正的象征下,无论哪一边的剑不“向对方做出退让”,“结果就是准备刀兵相见”[1]369。相较于法官和律师被特权束缚,哲学家尚能够审视自身。康德提出法律学者们不能回答什么是“内在权利”(德语Recht);而只能回答什么是法律上“正确的”(德语Rechtens),称为“法则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哲学家必须完成法官们未进行的尝试,哲学家应该提供“普遍标准,即,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正确和错误(拉丁语Lustum et iniustum)”[4]353(《法权论》)。
综上,康德对哲学家没有政治特权的阐述,目的在于揭示通过自身审视权利的重要性。哲学家如果一味对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读过他著作的人进行指责,那么哲学家也就变成了追求某种利益的代言者,即为了满足某种利益,他们将不再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某种特定既定利益的客户代表。哲学家唯有希望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被听到,作为“自由的法则老师”(拉丁语Freier Rechtslehrer)[4]89,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成为“人们权利的守卫者”,通过发现理性自身和限制自身去解释属于人类的根本权利。
二、“哲学家王”的政府
康德没有设定哲学家拥有特定政治权利,哲学家对理性的批判是连贯的,不是尊重自身为了权利,而是尊重权利为了自身。康德批评律师和法官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审视自己而委曲求全。相比之下,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如果哲学家直接占有权力或者间接地操纵最后权力者,他们将无法做出自己真正的判断。哲学家的工作是对人们进行启蒙,其必须自身简单如一地对普遍(道德合法性)人类理性求索。这种活动不需要特殊监管和审查,因为在科学和哲学辩论的一般语境下,他们提出的观点将被中立地指正,理性形容自身,做出自由而非被迫的判断。
但是,普遍理性究竟是什么?康德的《永久和平》旨在为永久和平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普遍理性就是康德开出的良药,那么问题在于普遍理性能否带来和平。康德的解释是,哲学家们寻找发出理性之声,他们不是通过持有任何政治特权,而是通过自身理性去守卫和平。对于某种政治观点,哲学家能够做出解释并且接受别人的意见。哲学家没有特权立场也没有外延权力,对于国家来说,考虑到哲学家自身和他的专业,哲学家的声明是微弱的。但即便微弱,哲学家也应对国家“承担责任”[1]375。哲学是对根本原则的考察,如果哲学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讽刺,而没有进行彻底批判,那么哲学自身难免遭受败坏,仅仅是一个声明,不能产生任何有效的争论。正是在秘密条款里,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充当神学婢女的例子,“例如关于哲学,据说他是神学的婢女(对于另两门学科,法律和医学来说也是这样说),但人们并未正确地看到,这个婢女究竟是在她的仁慈的夫人们前面举着火炬,还是在她们后面拖着脱裙”[1]375。
批评康德的人会反对康德以上的解释,即理性的求索未必比实践有用。即使哲学家发出理性之声,却未必有用。这种批评片面地理解了康德对哲学的定位,其提出对特殊学科的划分,或者是以历史可靠性来划分,或者以学科的社会实践功能来划分。哲学作为一门反思的学问,研究的主体就是人,人身上不但具有纯粹理性,同样具有纯粹的实践理性,哲学能够在实践上应用也就是说人有实践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理解能够加深对法律、医学甚至神学的理解。哲学学科的特征即为了所有重要争论被合适地检验。哲学象征理性的火炬,并参与到对其他学科的评价。哲学家们不应仅提供这些学科所感兴趣问题的咨询工作,而应成为指导其他学科研究的精神指南。
然而,哲学的这种实践能动性往往被人们忽视或者遮蔽。因此,为了对人们进行启蒙,哲学家必须承担责任。康德提出了哲学学科的意义在于,从历史上看,或许哲学落后于其他学科所取得的荣誉和成就。但只要哲学家或者人类理性不满足于简单重复某种空虚价值,而是去怀疑,那么哲学就有它立足之处。哲学能够与不同学科发生联系,例如,在政治领域,当怀疑或者违背政治学的既定原则时,哲学的追问往往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但哲学是不能被弃之不顾的,因为它是为了根本权利原则所做出的阐述,哲学家做出的批判不能被限制或者被忽视。
康德在秘密条款中反复强调,哲学家不拥有任何政治特权,但在最后的段落,康德提到,由某种哲学家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康德在这里实际上贬低的是一种哲学政治家,后者未经审视地去接受他人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因而搁置了作为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哲学政治家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出自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念,即哲学家在掌握权力控制国家后,能够依靠理性原则成功塑造政治王国。在柏拉图提出“哲学家王”之后的2000年里,哲学家似乎对从事政治有种诉求,按照康德来说,这种诉求是难以置信和内在地不可取的:“哲学家成为国王,这是无法指望的,也是不能期望的,因为权力的占有不可避免地破坏理性的自由判断。”[1]375虽然很多思想家拒绝柏拉图“哲学家王”的理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以及伏尔泰,但没有哲学家能够像康德那样明确地反对“哲学家王”的理念:哲学家并不怀有任何希望去谋取政治意义上的职位和立场。
柏拉图提出政治和哲学没有明显区分(《理想国》)[5],在柏拉图《对话篇》里,他首要关心的是政治自身,而不是关于哲学家管理国家方面。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学说,他在谈及“哲学家王”的观念时重点解释国家公民和法则,而少部分谈到了对哲学家从事管理国家工作的担心[6]。按照Cavallar的说法,康德追随亚里士多德“哲学家的角色是作为建议者而不是作为直接从事政治的演员”[7],Cavallar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多在于政治条例和哲学的一般相关性,“通过哲学式的思维制定政治条例”[8]。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和政治联系的如此紧密,从而限制了后来人们在柏拉图的政治条例和哲学之间做出区分和批判。
三、实践知识
哲学是否有政治实践性?康德预设哲学家没有政治特权,哲学家也不期望有政治特权,那么哲学还能不能在政治中起到作用? 哲学和政治之间的问题就是,哲学是否有政治实践性。从历史上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之后,受斯多葛派影响,思想家们转向关注哲学的政治实践性。康德对于哲学政治实践性的贡献在于:首先,康德是第一个批判政治实践性的理论基础和反对整个柏拉图式概念的哲学家。早期的哲学家很少讨论哲学的政治实践性,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哲学最早关注政治实践性,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但是以往哲学家们对哲学政治实践性的支持或者反对都仅仅停留在怀疑上,缺乏清晰性。康德提出,实践行为的原则基础就是先验纯粹道德,后者存在于人类自身。倘若人们想要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考虑,就必须引入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虑必须深思熟虑然后判断,政治应该作为“在实践中的权力学说”[9]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理论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联系较为紧密,但却比以往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们深刻得多。
其次,康德相比之前哲学先驱最大的不同在于,康德严格定义政治知识的概念。在康德哲学里,真实的政治知识必须含有有效内容,不只是陈述事实上的国家关系,而是作为初始义务。主体的责任意志产生实践意识,直接与经验发生联系。哲学家不应该以某种理论的时下局部应用实现来评价实践,不应该简单通过逻辑解释行为。主体的意志作为一个初始的合法基础,已经包含了实践理性对自身的立法。
再者,相比之前哲学先驱,康德的贡献还在于区分实践职能和理论理性。人拥有理性力量,严格审视本身内在并总结判断,理性的实践应用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即自由的个人意识。康德是第一个对实践意识特征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意识如何被实践?这个问题如果模棱两可,道德实践就难以产生任何知识。我们不应满足于对道德实践的自然形容,也不应满足于规范术语里孤零零的概念。规范术语中的概念仅通过逻辑推断而排除了任何从理论知识到实践内在的思考,但是,理论的获取必须考虑到所处环境,政治和道德行为包含个人意志。“完全满意的个人实践行为需要联系到理性,从而仅仅在自身而不靠着任何动机感觉,除此之外根本理性的行为是不可能的。”[10]
康德在反对古代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理念后,重点描述实践知识概念。康德强调纯粹自由,自由实践扎根在个人意识里。在康德看来,对“权力的追求”腐蚀了“理性自由判断”[1]374。哲学家在政治上自由独立的前提是理性内在,劝服任何人通过他本身“自由判断”运用。如果哲学家与外部利益,或者外部利益与哲学家最初主观动机发生冲突,哲学家应不改变自己初衷,坚持寻求真正知识。在这里,康德暗示自由独立和真理的必要联系,理性声明被预设在所有的争论之前。人拥有内在自由,所以可以对政治和国家概念做出理性评价和解释,而非刻意期待真理到来。在理论哲学语境下,一般的初始兴趣在发现真理进程中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必须经过“中立地争论和反复检测”[11]B780(《纯粹理性批判》)。唯有在自由之下,我们能看清楚“冲突的层次”[11]B88I(《纯粹理性批判》)。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下,人们去发现寻找真理,这是一部“纯粹理性的历史”[11]B80f(《纯粹理性批判》),继而产生兴趣,形成“人类理性的文化”知识[11]B878f(《纯粹理性批判》)。
那么归根结底,如何理解自由?康德区分独立哲学家和受政治力量影响之下的人,唯有前者提升了“实践理性可靠性”[12]5:119(《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区分政客和哲学家是看主体行为是否受现实情况影响。在论文补充部分,康德再次提到,“政治深思熟虑”(Staatsklugheit)、 “政治智慧”(Staatsweisheit)就是内在的理性原则。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解释了实践理性就是人有内在自由。然而,假设人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提出义务,自由观点的表达如果总是趋附在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便难以说明一个人是否真正自由。按照康德的观点,哲学家会拒绝考虑这些特定情景和社会因素,因此,批评康德的人把康德视为道德严苛主义者,这种指责对康德是有失公允的。康德的批判之所以有效在于强调实践原则,个人独立地考虑,以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行为,但不能简单地无视政治行为所处的背景。哲学理论学者只解释政治家注意到某种问题,提醒政客做出政治行为的前因和结果,在论文的附录里,康德称这类学者为“政治道德学家”[1]374f(《面向永久和平》)。康德认识到政治家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去做出“自由判断”,就像康德没有对法官和律师做出持续的贬低一样,康德也不是简单地批评政治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主观上平等,在根本上都是“理性的存在”[13]。
四、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划分
按照实践理性相同的原则划分独立行为的领域,在实践政治和哲学批判的领域,存在一个职能区分的问题。对政治和哲学的职能有种简单划分,即只要政治和哲学相互尊敬,并且不损害对方,就能共存下去。康德对这种观点做出了评判,他强调政治和哲学不应只是以不损害对方为基础,而应能够促进对方,哲学的引入有助于发展多元化政治,而政治不管作为实例还是理论都使得哲学家丰富自己的知识。康德的这种政治和哲学的批判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哲学发展的基石。
康德从未希望去限制哲学家从事政治,他反对的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模型。但无论是谁从事这些事情,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政客,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因为相较政客哲学家,真正哲学家需要考虑形形色色的条件而不失自由。个人逼近到政治的力量将阻碍纯粹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家成为国王,他将不再代表平等,而是代表了政治力量。
康德坚持哲学的批判作用,其在《纯粹理性批判》结尾里,谈到“那种批评路径仍旧是敞开的。它用于吸收批判的尝试,那种自由判断的运用比起哲学理论来更加急切地需要。哲学必须独立于所有的特殊的应许,如同它是去检验和评价每一个人在理性自身方面的兴趣。”[11]B884康德坚持哲学的批判作用,因为人类理性最终为了获取知识。康德指出,在文化的进程中,人类“不仅仅”划分他们的劳力,更重要的是,发展不同的专业机能(《普遍历史的理想》[4] 7:21f,《推测的人类历史的开端》[1]8:115ff)。“不仅仅”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下是另有深意的,更多的是强调后者,例如在康德的绝对律令里,即“为了所有理性的存在,存在那种法则,即每个人对待他自身还有所有其他理性存在,不仅仅作为一种方式,而且总是在同一时刻作为他们自身目的”[14]。
在自然状态里,每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会成为对于其他存在的对象,人类社会也处于相同法则之下。作为母亲,因为有了孩子使之成为了母亲;反过来因为母亲,孩子成为了孩子。个人有意识地塑造和发展形成人类社会,于是形成了“文化”。同样,在经济、技术和科学的领域有各种职能的划分,各领域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反而各种职能的划分有益于社会之间的联结。从这方面看,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从事国家管理[5]368b,374b(《理想国》),相比之下,康德提出的世界历史主义者的解释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对各种专业职能的区分是为了构建最终政治秩序,其基础就是人类能够自由地认识到他们自身。哲学家不必一心成为“哲学家王”,这样职能的区分也会给政治带来好处,使得每个人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事情,有的人从事哲学,有的人从事政治,这也是一种民主[1]384f。康德并不希望把政治和哲学隔离开来,在《反对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也明确反对这种分割,马克思指出,虽然实践上的指导不能直接从理论中得到,但是人类内在可以积极地确保人们从事实践活动。
康德的评论者们在文献里指出,由于历史因素,康德严格区分政治和哲学,然而这些因素不能更令人信服[15]。但如果对康德的判断区分仔细审视,其基于的是他对哲学理论和行为领域的不同理解,康德对政治和哲学的区分是思辨的,强调人的内在实践能动性,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柏拉图的模式 (拉丁语Paradeigma)。康德基于哲学的批判职能的模式取代了柏拉图的模式。哲学家作为中立公正的角色有信心施展在政治领域,而不必拥有特权。哲学家能够公开互动发表建议,而本身的独立自由不被限制。康德所说的“人类理性的文化”就是理性进程在理论上成功实现,而如果理性进程在实践上成功实现,那么人们就不再需要国王。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将自主地希望成为“忠诚的人民”[1]376。同柏拉图相比,康德将政治特权寄希望于人类本身,而不是哲学家成为国王。
最后,在附录x里康德再次强调了政治和哲学的区分,“道德和政治的不统一”[1]376。虽然在附录x第一部分,康德没有对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相互联系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并不表明康德认为对政治和哲学不存在联系。康德在最后的总结里指出,我们必须去认识到自身的道德存在,之后发表独立的政治意见,这样的政治意见是有力量的,政治领域就不能简单同道德领域分割开来。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谈论用一个单一主题可以称为“人类文化的共有职能”,基于此,政治和哲学两者自由地发生联系。因此,不用怀疑,不管康德对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念做出何种修改,哲学绝不会从政治世界里撤出。
参考文献:
[1][德] 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M]. 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J. E. G. Zetzel. Cicero: De Re Publica[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17.
[3][德] 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七卷)[M]. 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德] 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M]. 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Paul Shorey. Plato:Republic[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69:509b.
[6]A. Peck Aristotle,M. Hamburger. Morals and Law. The Growth of Aristotle’s Legal Theory [J].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5,(16):170.
[7]Georg Cavallar. Neuere nordamerikanische Arbeiten über Kants Rechts und politische Philosophi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M]. Berlin:De Gruyter,1992,46(2):338.
[8]Fritz Wehrli. Die Schule des Aristoteles Texte Und Kommentar[M].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44:29:18.
[9]Volker Gerhardt. In Otfried H?ffe, Immanuel Kant: Zum Ewigen Frieden[M]. Berlin:De Gruyter.1995:171
[10]Volker Gerhardt. Philosophy and History[M].New York: McGraw-Hill,1988,21(1):17.
[11]P. Guye, A. Wood.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2 M. J. Gregor.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3]Volker Gerhardt.Verifiche: Rivista Trimestrale di Scienze Umane[M]. Berlin: De Gruyter,1990,19(3):247.
[14][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
[15]Georg Cavallar M. J. Gregor: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M].Berlin: De Gruyter,1992,46(2):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