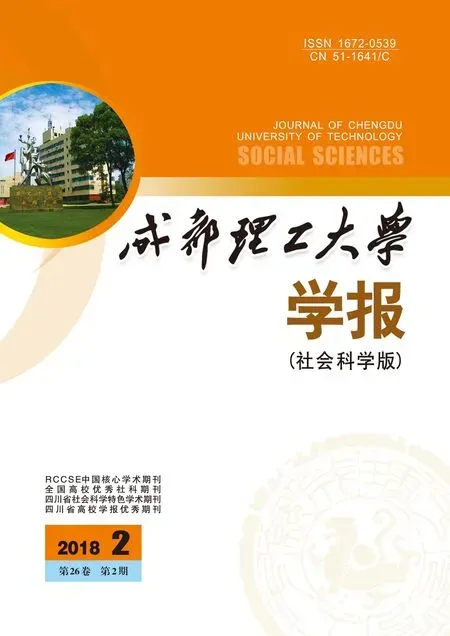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科学发现探究
2018-03-20常红,易显飞
常 红 ,易 显 飞
(1.广东医科大学 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东莞 523808; 2.长沙理工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 410114)
科学发现是科学认识的重要内容,它受制于认识本质的规则或标准。我们理性的、客观的科学认识本身是否负载有性别偏见?女性主义以别样的视角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么在科学发现中情况也是如此吗?科学发现与性别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联系,本文将从科学发现的方法论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的优越性之间的联系出发,来探讨科学发现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一、科学发现方法论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逻辑实证主义:刻意回避科学发现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发现的刻意回避的根本原因在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存在。自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常常困扰于诸如“人的意识是如何可能认识与其完全不同质的外部世界”之类的问题。为了避免再次跳入上述的怪圈中,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发现和辩护分离,把发现问题归入经验心理学,认为发现问题是心理学和历史关心的问题,从而将发现从认识论中清除出去。至此,科学哲学研究便局限于“辩护的语境”,成功地回避了科学发现的研究。
(二)历史主义:科学发现是人为建构的产物
随着汉森《发现的模式》的出版,长期遭到忽视的科学发现问题重新引起了科学哲学家们的关注。但此时的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热衷于构建某一种或几种科学发现的逻辑方法或科学发现的逻辑模式。他们认为,科学发现不是瞬间的灵感而是构建的过程,也绝不是非理性的,并且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发现逻辑或方法并不存在,因为科学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找到像万能的逻辑那样能够解释所有研究领域的成功模式,能做到的只是给出一种充分的建构性解释。
(三)人工智能论:科学发现是一种信息选择
新的转向是纽厄尔和赫本·西蒙,他们已经把关于问题求解的人工智能和科学发现明确地联系起来。这种方法不包括任何诉诸理性的具体定义,人们根据科学的特殊目标和方法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理性形式来辨别科学,但接受科学研究的认知进路的人认为不可能有某种归纳逻辑可以从互相竞争的假说中唯一地挑选出理性的选择。萨伽德认为,有可能构造一种运行于计算机的算法,它将表明两个理论中哪个理论是最好的。至此,科学发现成为一种信息的选择,创造力则成为一种信息的选择能力,一种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发明的能力。“科学发现成为模式识别与选择性搜索的协作过程,而那些直觉、顿悟、灵感等创造性思维,都不过是以储存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认知活动。”[1]
从以上科学发现方法的研究进路中,我们发现科学哲学家们过多地专注于理性方法而忽视了非理性的视角,从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发现归为心理学,只强调理性的证明与辩护,到历史主义学派对建构的呐喊而对非理性的贬斥,再到人工智能企图用计算的逻辑选择最好的理论,不难看出,科学哲学家们试图通过逻辑的方法找到科学发现的逻辑模式。科学发现的研究过分地专注于理性,却压缩排挤了非理性的成分,从而回避了科学发现的非理性视角和研究。科学发现逻辑研究方法中这种执着于理性规避非理性的局限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丢失了的视角——女性视角。科学发现的女性视角更加重视科学发现方法中非理性的因素,强调理性和非理性两者在科学发现中具有的同等地位,反对思维方式上的主客两分的传统二元思维模式,提倡思维的主客统一。
二、科学发现方法中缺失女性视角的成因
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心理性别引起对女性的歧视进而导致对女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忽视。我们将在对性别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社会心理层次中的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探寻女性思维方式的独特之处,并找到女性思维方式被忽略的社会心理学根源,进而解释科学发现方法中固守主客两分思维模式、忽视非理性因素及缺失女性视角的成因。
(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社会性别(gender)不同于生理性别(sex),是人类建构的产物,两者不存在必然的本质联系。生理性别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从生物学意义上定义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社会文化形塑与“性别期望”建构的产物。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丽特认为,一个人从初步懂事起,就被界定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并进行有区别地接受教育与训练,两性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及角色内化为个体的行为规范[2]。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并不是生理差异所能决定的,即使生理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现实中的“差异”有所“贡献”,也不是不可以通过社会因素改变的。社会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形构”中创造的,每个人都“不经意”地在塑造着性别。
(二)男性视角与传统科学的结盟
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产物就是科学研究中的不同性别的气质思维。凯勒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男性气质的形成,认为“客观性”是“心理自治的认知对应物”,而这种自治又与“自我和他人边界的焦虑”相关联。而这种“自我和他人分离的焦虑”就被界定为“男性气质”,分离就是一种控制形式[3]。在《对性别与科学的反思》一书中,凯勒将男性气质形成的原因解释为小男孩通过与母亲“日益明显”的分离建立差异,在他自己与母亲“渐行渐远”的过程中逐渐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并日益明晰与母亲截然不同的性别身份,即恰当的男性身份,“因而才发展出那种与知识的主导科学形式相互关联的认知类型,即超然性、客观性、对于干预和控制认知对象的全神贯注等具有典型意义的‘男性’品质或气质。”[4]这种男性品质的思维方式贯穿了整个传统科学。在传统的科学观中,科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主客二分”,强调科学认识的理性与抽象性,主张不受观察者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影响,来达到描述的“客观性”,以此获得不受“污染”的知识。他们将自己看作独立的主体,自然界成为他们探索的客体,同时与其性别相异的女性也被看作客体。失去了主动性、主体性的女性被看作被动的有时甚至是自然界的隐喻。在这种两分思维中,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割最终将近代科学气质定义为理性、客观性、男性气质的,并将非理性、主观性,划定为女性气质思维方式。
凯勒在动态客观性概念中阐述了女性气质思维。她认为,动态的客观性是一种知识形式,它承认周围世界是客观的、完整的与独立的,但这种客观性并没有阻止我们认为人类与这个“外在”世界是相关性的,知识的形成与保留都依赖于这种相互联系。动态的客观性是一种他人的知识形式,来源于情感与经验的共同主体,以便按照他和她的认识,丰富对他人的理解[5]。这种动态的客观性强调情感、认知经验在知识中的地位与作用,反对男性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绝对“二元对立”,认为主观经验的充分运用,能够促使产生一种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的状态或感觉[6]。这种主体客体合二为一的感觉便是女性主客融合的思维方式,在这种主客融合的思维中,女性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被分离的主客体,被分割的理性非理性在这里合二为一,那种被贬低的“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主观的非理性因素与客观的抽象理性因素共同作用于科学研究中。
(三)性别集体意识导致女性视角与科学的割裂
女性气质思维之所以被忽略,之所以还有观点认为女性不适合学习我们通常所说的“硬科学”,就在于它们与传统文化中的性别集体意识有关。凯勒认为,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科学客观性与男性化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这种约定俗成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信念,并在男性话语霸权的强制引导下形成一股无形的文化力量,制约着对应性别的人的言语系统、思维系统与实践系统[7]。而这种性别偏见的集体意识与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共同作用使得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等符合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最终导致传统科学与男性的联盟——“如果说某一流行的科学观成为理性和客观标准的依据,科学也同样为新的男性化观念提供了依据”[8]。在科学与男性化循环论证相互加强的过程中,“称为科学的东西从被称为男性化的文化偏好中获取了额外的效力与支持;成为女性化的东西,由于脱离了建立在已经男性化的科学所提供的模式之上特殊的社会和智力价值而愈加降低价值”[9]。所以女性与科学的分离,不能归罪于女性本身,性别构建中的男性中心文化与性别歧视集体意识才是两者分离的社会心理学根源。
三、女性视角的优势与新视角下的科学发现
哈丁认为,现代科学所做的各种界定、解释与预见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性别亚文本(sub-text)[10]。女性视角或女性主义实质上是要通过“性别”这一维度 ,打破科学发现中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界限从而寻求一种辩证的统一,打开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黑箱”,解构曾经被认为“合理”的科学知识,解构传统元科学话语的男性主义霸权地位,解构传统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的神话。
女性视角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于它消减主客二分法的分离和对立,更强调整体性,更关心与客体的关系。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科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彼此分离的。女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占据主流的男性科学家的方法不同,在她的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观察主体与观察客体不是截然分开,而是融为一体。麦克林托克曾这样描述她发现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转座”的过程:她每天泡在玉米地中和玉米有进行主观情感上的交流,有时她甚至能感觉进入到玉米的染色体内部。她将自己的成功发现看作是“对生物体的感受”与客体交流的结果。她的发现过程是主观直觉、情感与自然交融的过程。当然,麦克林托克并不否认现有的标准科学方法的有用性和正确性,但这些方法并不是通向真理世界的唯一路径。她相信还有其他正确甚至是“更正确”的方法可以用于认识自然[11]。与主客两分的男性研究方式相异,女性选择了与自然更加温柔而非对立的方式同样达到研究发现的目的。
其次,它恢复了非理性在科学发现中的合法地位。女性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是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抽象、还原。在这种互动联系中强调人要更带感情色彩的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界,而不只是用所谓冷冰冰的理性支配自然。人的直觉、灵感和顿悟等非理性不仅仅是一种女性气质更是科学发现的本质特征,“它们是人类独有的、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活动形成的一种不走正常程序就能够将现象和本质、特殊和一般、部分和整体等认知素材相互统一起来的创造力。它们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知识和能力的直接统一和瞬间结合”[12]。它们甚至是科学发现的关键环节。当科学研究陷入困境,理性逻辑无能为力无法选择时,非理性思维的运用可以突破原有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的局限,为科学开创新境界,为科学发现开辟新道路。在科学发现中,非理性思维甚至比理性思维更关键。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13]在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非理性为理性开辟道路并启动、诱导理性共同作用于科学发现。科学史上的“每一种发现都含有在柏格森意义上的一种非理性因素或一种创造性直觉”[14]。科学发现的过程正如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理性思维是语法规则,非理性思维才是创作的火花。也如法国数学家彭加勒在几何学中所强调的,“没有直觉,几何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他只是按语法写诗,但却毫无思想”[15]。传统科学发现研究中对非理性的忽视不仅是视角的局限,也与科学史事实相背,女性主义在尊重科学史的前提下试图揭示科学发现本身固有的非理性因素,进而恢复非理性在科学发现中的合法地位。
再者,它实现了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女性视角对非理性的强调绝不是试图削弱科学事业的理性的根基。因为女性视角反对的不是科学事业本身,而是对科学的唯理性的哲学理解。而这种哲学理解恰恰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源。事实上,女性视角并不有损科学的客观性,因为女性视角所倡导的非理性乃是以承认科学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女性的“经验性”“情感性”与以追求真理为主旨的科学精神并不相违背,只是希冀补充非理性元素来消除理性的过度张扬,也达到彰显科学发现的人文价值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视角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纽带与桥梁。
通过女性主义的解释,新视角下的科学发现方法论应该是更多元、更丰富、更复杂的,需要我们在思维方式上打破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在方法论上打破逻辑中心论,运用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重新树立一种理性和非理性、逻辑和非逻辑是辩证统一的科学观。
这种辩证的科学观认为:首先,在科学发现中非理性以理性为前提而发生作用。科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严谨最有效的生产知识的体系。科学的根基在于客观性、普适性,而客观性的根基则在于逻辑与经验。如果科学发现仅仅诉诸于非理性,如灵感、直觉等因素的话,那么它势必会完全丧失其客观性特征,进而滑向神秘主义。换言之,许多科学发现在出现之初都带有神秘的色彩——科学家意外的灵感或是天才的直觉把握。但这种神秘的光环在经过理性的审视之后则蜕变为了一种历史必然中的偶然。故就科学而言,非理性只有在理性的指引下才能真正发挥对科学的促进作用。
其次,非理性为科学发现提供契机。非理性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科学事业,特别是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创新特征最为明显的环节之一。如果说科学家长期的理性的思考是干燥的气候的话,那么非理性则是真正点燃柴堆的火花。唯有如此,作为“现实的人”的科学家的价值才能得以尊重;唯有如此,科学事业体现的独创性才变得可理解;唯有如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天生联系才不会被生生割裂。
简而言之,科学发现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两者的辩证关系实质上反映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缺少理性的科学无异于宗教,缺少非理性的科学则退化成了数理逻辑。实现理性与非理性两者的辩证统一不但是科学事业本身的要求,而且是对科学事业进行哲学理解的要求。
参考文献:
[1]Simon H. A. Scientific Discovery as Problem Solving[J].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2,6(01):7-8.
[2]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2.
[3]洪晓楠,姜慧智.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思想评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1-6.
[4]欧阳康.当代英美哲学地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30.
[5]洪晓楠,郭丽丽.女性主义经验论科学哲学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1):38-42.
[6]Ke1ler E. F. Ref1ections 0n Gender and science[M]. New Haven:YaIe Universitv Press,1985:l16.
[7]李银河.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81.
[8]欧阳康.当代英美哲学地图[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30.
[9]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2.
[10]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M].Ithaca and London: 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86:8-9.
[11]Angela Calabrese Barton.Feminist Science Education[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1998:101.
[12]张之沧.当代科技创新中的非理性思维和方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0):98-102.
[1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徐良英,范岱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4.
[14]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M]. London:Hutchinson Press,1959:31.
[15]J. H. Poincare.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M].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1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