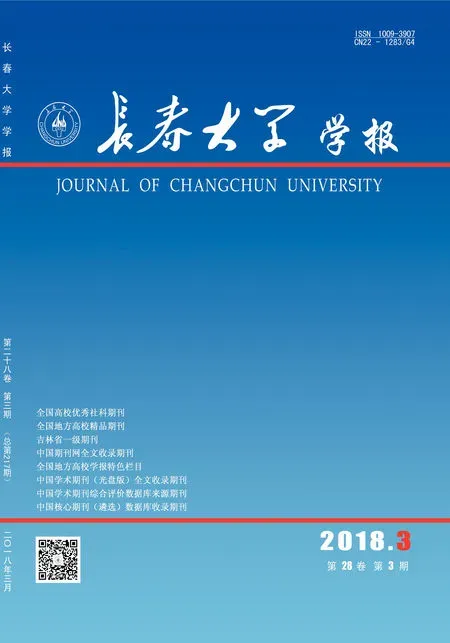论苏轼的游处思想
2018-03-19柳志立
柳志立
(江西服装学院 公共教学部,南昌 330201)
苏轼可谓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人格典范和行为风范方面的典型,一生可谓才难相妨,但进取、有为的大方向却从没因仕途的顺逆而改变,始终如一。在外向建功与内向适心这一士大夫文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二元对立的矛盾中,苏轼之所以能保持平衡的状态和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轼“游处”的思想、生活态度和方式在起作用。即此,本文尝试对苏轼的游处思想作一探究。
关于“游处”之说,古人早有会心之论。对学习之游,《礼记·学记》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1]孔子也说:“游于艺。”[2]对社会与人生,道家的庄子主张要“游”于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3]90,“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3]213,“乘物以游心”(《人间世》)[3]136,以疏离于社会与世俗的“游”的方式来生存。对于心性修养,佛家无念无住而不执著的思想,在观念层次上也大有与世推移(即“游处”)的意味。可见,三家思想皆有“游处”之方。苏轼思想驳杂,其“游处”思想主要源于其现实的仕途生涯的影响,当然也与儒道佛思想的潜在影响有关。
1 大全之道与整体观念
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天与人即物与我,物质和意识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思想与学说。因此,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就自然成为哲学的基本与核心的问题了。宋代是中国古代哲学发达和成熟的时期,天道观(或自然观)和人性论(或心性论、性情论),也是宋代哲学的两大核心问题。苏轼之道作为蜀学的一个方面,可谓内容丰富,也包括天道观和人性论两方面内容,而此处则主要涉及其自然观即关于宇宙万物的创生、存现、发展方面的问题。他在其《上曾丞相书》一文中说:“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4]1379他还说要“通万物之理”(同上),识尽物理,如此方能具有无私之心,方能体道正道、随顺物理物性,可见其自然观的基本内涵乃在“自然之理”,而其以“道”观物的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则是合理性的原则,这也正与老子“道法自然”[5]169和庄子“以人合天”*《庄子今注今译·秋水》云“无以人灭天”[3]461,《庄子今注今译·达生》云“以天合天”[3]525,前者之“天”即指去除后天因困惑于“物”和“利”而生的社会机心而可回归到的人之本性本心的天生而自然的状态,后者之“天”即指世间万物所存现出的天然状态。此处“以人合天”之“天”即指符合物理的人之本性本心的天然状态。的遵循万物之理并随顺物性的自然理势的道论一致,也具有自然的特性。由此可知,其自然观乃“自然”之道。就哲学本体意义上关于宇宙万物本原的预设、建构、阐释的原理与方式与思路而言,其自然之道承老子之道而来,而又与庄子之道相接引,老子从整体的“道”来看待万物的思想和角度、庄子的“大全”*老子以“道”为万物的本原,“道”生万物而又存现于万物之中并通过万物的属性和特征表现出来。在老子看来,“道”具有“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5]169的属性和特征,是一个先验式的没有消长变化的完全的即具有大全的属性和特征的整体。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发展了老子对“道”的整体特性的观点的理解,进而更明确地肯认“道”的大全的属性和特征——“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3]577。思想,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苏轼自然之道的整体性、大全特征与其观照万物整体出发的角度和全体的心理倾向。正如其在《东坡易传》卷八中所云:
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实开之,赋之以名。以名为不足,而取诸物以寓其意,以物为不足,而正言之。[6]
可见,苏轼的自然之道具有“大全”的特征。其自然之道实际在于要穷究万物之理,道理是大全的,可以通晓万物,所以其自然之道也可谓“大全”之道,即整体观照下的万物之理,甚至可谓“自然全体的总名”[7]180及其所对应的现象及现象之间关系存现与发展的原理和根据。
自然之道是万物之理的全体,它可以说是苏轼整体观念与全体性思维的总根源。而从整体着眼来观照万物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倾向,又可谓其游处思想、生活态度和方式得以生成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整体观念与全体性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其生成之首要是源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中“时间-生命”限度的悲感体验。亲故继去的现实使青年时期的苏轼不断地生发出深重浓厚的人生虚无感、空漠感和沧桑感、无奈感,从对“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都山鹿》)[8]21的时光流逝的感叹,到“世间生死如朝暮”(《留题仙都观》)[8]20的生命短暂的悲叹,再到“古今换易如秋草”(同上)、“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荆州十首(其四)》〕[8]57的社会历史兴亡的慨叹,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浓厚深广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会促发从时间限度的整体去思考和看待外物和人生。当然,也与道家思想有关。道家强烈而浓厚的生命意识,全性保真的修持方式,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3]452、“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3]80、“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3]601的人生态度和生存哲学,也多为作者所汲取,用于安顿生命。将人生百态放置于物之性理和万物关系的整体中来观照,既可以方便化解现实的苦难,也有利于作者“时间-生命”的整体意识乃至其观照万象的整体观念的形成。
其次,与作者的江海意识和道家的空间观念的影响有关。众知,儒家诗教观念中有“物感”一说,其意为自然外物会触发和影响人的主体情感和心理。承上可知,如同节序和物候多会直接感发人生短暂、流年不息的生命意识一样,时间意识与生命限度可以说最容易触发对人生苦短的整体感知的心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4]6这不仅使主体生发出时间上整体着眼的观念和观物方式,而且还会引发人与自然对比中所产生的对空间差距的感受——“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同上),进而引发出作者空间上的整体观念——“青鸾歌舞,铢衣摇曳,壶中天地”〔《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9]422。如果说仕途上江海迁转的生涯会直接隐现出作者空间上的整体观念的话,那么道家老子“大方无隅、大象无形”[5]229的言说、庄子关于鲲鹏举翼万里形象的想象(《逍遥游》)[3]3的无限开阔的空间世界,将自然而不自觉地会让人催生一种整体观照外物的思想和意识:“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壶中九华诗并引》)[8]1936。也正由此,“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9]174的无限想象和美好愿望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而道家关于“壶天”世界的信仰和想象则又拓宽了作者的整体观念和全体性的思维方式。壶天世界的说法源于一个文化典故。根据《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记载,方士费长房“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10]83“此后,这一故事又被葛洪记入《神仙传》中,成了道家仙境的代称。有的书还由此繁衍出新的故事,说一个叫施存的人学大丹之道,后为官治理一方,身上常悬一壶,壶大能容五升,可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情景一般。他夜宿其内,自号‘壶天’”[10]83。即此,苏轼常有观照自身和外物的整体观念。仕途上的迁转使其常有江海人生之叹:“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许州西湖》)[8]81命运的不可捉摸使其常有人生“雪泥鸿爪”的偶然流落之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8]90人生在时间上的短暂和江海迁转的劳苦使作者不禁生发出“人生如梦”、“吾生如寄”的沧桑心态和空幻虚无的整体感受:“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入峡》)[8]17;“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屈原塔》)[8]26;“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8]65。这些感受无形中又反向强化了其整体意识,使其整体观照的方式不自觉地带上了生命体验和艺术审美的特点。
当然,苏轼内足无待的人生态度和生存哲学也有助于其整体观念和全体性的思维方式的建构。现实仕途的坎坷使作者“富贵良非愿”〔《归去来集字十首(其六)》〕[8]2205的人生目标得以正向的强化,使其由“外王”理想渐趋向“内圣”目标转向——“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8]2068,内在自足即可。苏轼受庄子思想影响很大:“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11]。庄子逍遥而无依无待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苏轼的“内圣”意识和诉求:“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谁羡人间琢玉郎)》〕[9]579)而道家的壶天世界则一方面打开了他心灵的无限空间,一方面又涵化了他内足无待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境界,利其超越物和欲的界限困惑而能达于艺术的审美。佛家的内在心性修持活动也与此相类,佛家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参见《大正藏·坛经》第48册,第352页。佛家思想更益于贯通物理和物性以便修持强大的内心世界,这也是自由审美活动的基础。正因其能安和自足于内心,内外皆无所求,所以,心灵心源才能不为物和欲所遮蔽,诗意的审美观照活动也才有了出现和实现的可能,对虚实的万象才能更好地进行整体审视。正因有整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所以具有审美性的天地游处的观念、生活态度和方式,才有了生成和实行的可能。
2 无念无住的思想与因缘意识
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八大主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以倡导自明心性以成佛而得名。为排除外界的干扰,其创始人慧能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12]的修持要求,力主“顿悟”。其无念、无住而不执著的思想和修持方式,在佛教义理世俗化的过程中对文人士大夫影响深远。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家佛教思想的生活化、世俗化现象日益加深,文人与佛教徒的交往日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也开始心游物外,自觉地参悟佛理并广结方外之缘,无念无住的佛家义理使苏轼早年“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8]274的人生理想和执著有为的人生态度开始转向,而开始专注于自我内在的心性修为了。其在自觉参禅和与僧人的佛理论辩中,似若有所悟:“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8]2261。佛家思想使作者在现象上逐步地看破成空,思想上日益地超凡脱俗。
在修行方式和义理方面,儒道佛三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相互冲突与相互吸收、融合的状况,宋代很多士大夫文人都是儒道佛思想相生并存,苏轼尤为典型。苏轼晚年从海南儋州北归途中特意到都峤山拜望了他的昔日同窗邵彦肃道士,云:“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疎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书赠邵道士》)[4]2083可见,苏轼已参悟佛家义理很深,且其思想已有佛道相融共生的影子。同为生存哲学和修心之道,儒道佛的义理在本质上的相互贯通也实属正常,尤其是佛道二家。相比之下,佛家比道家更注重内在心性的修持。佛家的无念无住、不执著的观念与庄子逍遥无待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而且一致的,也主张内在自足而不外慕的心性修持的义理,这将使作者能更好地贯通其自然物理为基础和主体的大全之道,也将更便于其游处式的审美活动的展开。
同时,无念无住的思想观念,便于作者现实中随遇而安、随缘自适和心灵中对人生顺逆的偶然状况的淡化和超越,从而能以“游处”的态度和方式来超然地对待自身和外在的状况。而佛家的因缘意识*方立天教授在著作《佛教哲学》第七章中说:“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缘起’也就是一切事物所赖以生起的因缘。”据此而言,佛教的因缘可谓客观中性的内外条件。苏轼受其影响,却将其转化为了文化和风俗意义上的具有褒义情感色彩的友善心理和认同模式,即情感之“缘”和命定之“分”,我们通常所言的因缘或缘分即指此意。参见文献[12],依次为第151、150页。将一切顺逆的偶然和必然的经历都视为因果缘分,以诗意的情怀和宽仁的精神化解苦难和困惑。这种思想在苏轼的诗文中也有所体现:“相逢一醉是前缘”〔《浣溪沙(一梦江湖费五年)》〕[9]539;“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8]627。其处世态度、心理和方式上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游处”的属性与特征,可以说,无念无住的思想观念与因缘意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当苏轼以无念无住、不执著的思想来面对人生与仕途上的困境的时候,“游处”方式就势必成为其生存方式的必然选择,此时的游处思想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和协调性。苏轼当以随缘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与仕途上的困境时,便以浪漫诗意的缘分视角来看待系列沉重的苦难:“宿缘在江海,世网如予何。”(《次韵范淳父送秦少章》)[8]1791以苦为乐,则能内胜超然。
总之,作为游处思想前提的观念形态的无念无住的思想和作为游处的原则、方式、内助力的因缘意识,在本质上都是游处之意的另一种诠释,它们必将能化解作者的游处困累,势必会增加其与世推移、尘世游处的和谐度与安适感,而使其能有可能、尽可能地游处得更刚毅执著和超然洒脱。
3 中隐思想与现实游处的方式
古往今来,儒家士人在人格自由的存持和人生价值的选择方面,几乎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需要适度地依偎皇权以便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要适度维护士人必要的人格独立,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所以要两方面兼顾,就需要在建功的理想和适心的诉求,外在形制的规范和内在心灵的自由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于是,游处于内心的中隐即吏隐、心隐的平衡方式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从理论和逻辑关系上来说,当思想先行,苏轼的游处思想与其现实的中隐方式之间,虽非派生关系,但至少也有因果联带的关系。而实际上是现实中的中隐态度和方式回护和印证着其游处的思想,并与其取得了本质上的相通和一致,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相生助长的关系。
但从理论上来说,往圣先贤们中隐的思想、方式、行为,也有助于作者游处思想和现实官场中中隐方式的建构与成型。苏轼仰慕白居易,中年之后对白居易非常崇奉,白居易的人格与处世态度对苏轼的影响很大,而近乎相同年岁的贬谪生涯,更加深了苏轼对白居易处世态度与行为风范的自觉认同与学习。在初贬黄州时,苏轼就自称“东坡”居士,显然有效法白居易之意。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府,在离开杭州时他曾作诗一首:“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老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二)》〕[8]1675在仕途谪居生涯之中,苏轼时常和白居易相比拟:“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8]1621;“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8]1604。可见苏轼慕白之深。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屡屡为后人所称道,南宋罗大经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13]诚如所言。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要在现实中平衡各种名利关系和矛盾,其处世态度和方式对苏轼很有吸引力:“大隐本来无境界”(《夜直秘阁呈王敏甫》)[8]212;“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8]319;“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8]123。中隐的态度与方式本是很多文人仕途上无奈的选择,但有时却能体现个人主体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境界。白居易的中隐态度和方式在于内心境界的修持,这种处世方式对苏轼诗意审美的游处思想、态度、方式的选择和现实官场中中隐思想与方式的建构,当有深远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现实中隐的生活方式也反向强化着作者的游处思想和态度的建构和成型。
4 艺游活动与对游处的心理补偿
古代有所谓“游学”、“游(于)艺”之说。“游(处)”可谓既不完全随顺,也不真正抗争的态度和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有原则的生存方式和策略,但又不能等同于随意游戏的混世主义或无原则的滑头行径。仕途困顿,游于艺途是很多失意文人的选择,甚至是必然的选择。对苏轼而言,儒家艺游的观念和方式,既是其游处思想的合理延伸——疏世“立言”,更是其游处方式能得以实行的心理前提和基础——人生价值转向以文艺存身和立言不朽的心理补偿方面。艺游活动、文艺化的生活方式、文人意识,一方面,可有助于化解作者仕途的骚怨和无奈之感,以便平和其内心,如“不妨尊酒寄平生”(《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8]1496式的畅饮活动,“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8]240式的吟诵或咏怀,“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送千乘千能两姪还乡》)[8]1519式的超然乐道的生活方式,诸如此类,艺术活动中性的特性可便于疗心消愁。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作者文人文艺化的生活方式充满审美性和艺术特征,使其人生理想化、艺术化、诗意化,而这种人生状态和生活方式在本质意义上正好与其游处思想和方式相互契合、相互生成:“独栖高阁多辞客,为著新书未绝麟;长歌自誷真堪笑,底处人间是所欣?”〔《次韵子由三首(其二)·东楼》〕[8]2134-2135再者,艺游可谓文人正常而为主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乌台诗案后,苏轼以艺游为主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可以说还是对其仕途理想和沧桑心态的反向补偿或代偿的意志行为。反映在其诗中,比如:“惟将翰墨留染濡,绝胜醉倒蛾眉扶。”(《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8]165-166“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次韵答子由》)[8]1027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艺游越顺意,作者尘世游处的态度越积极和坚决,纵然“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4]1904,也绝不更改其傲然挺立之态。可以说,艺游活动不仅是作者游处思想、态度、方式能得以实行的心理前提和基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其游处和中隐方式的辅助和补充。
5 游处的内涵与特征
论及苏轼游处的内涵与特征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苏轼的寄寓、观化思想及其与游处的关系。以整体观念和全体性思维为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思考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时空意识与对生命存现方式的审美观照所引发的个体浓厚深广的悲剧人生观和生命的悲感意识,苏轼生发出浓郁深广的“人生如寄”的“寄寓”[7]491思想:“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8]1881;“吾生一尘,寓形空中”〔《和陶答庞参军(其六)》〕[8]2101。以作为个体的人生思想、态度和生命存现方式的“寄寓”观念为源头,又自然地引发了作者的“观化”意识和“游处”方式。对于“观化”意识,从上古时期圣贤们“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14]520、“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198的观物取象活动,到秦汉时以“采诗”的方式“观风俗”即以诗观化民风的现象,到庄子以“道”观物、“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至乐》)[3]486的观化与思悟的态度和方式,再到苏轼“凡物皆有可观”(《超然台记》)[4]351的观物意识,乃至其“其身与竹化”〔《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8]1433、“俯仰了此世”(《迁居》)[8]2068、“阅世观盛衰”(《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8]2156的观化意识与方式,可谓都是类似而切于概念内涵本质的说法。概略而言,“观化”可谓哲学式或艺术化的观照,或者说,它是以直觉式的宏观观照为前提和基础的心灵体验与思悟的方式与活动,简称“观照”。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寄寓与观化之间,可以说寄寓以整体观照为前提,且其本身也是一种静态整体的观照,而观化则可谓其自然的引申和发展;寄寓与游处之间,它们本质一致,且寄寓思想是游处观念的宏观前提和基础,而游处观念则可谓寄寓思想的自然发展和现实状态。三者之间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本质意义上的一致相通性。如果说寄寓思想是宏观层次和观念状态中生命的阶段性的存现方式与状态的话,像苏轼常寄寓式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和生命,比如“人生百年寄鬓须”(《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8]165,那么游处态度和方式则可谓,微观的现实层面和实际生活中,人的一生以行者或过客的身份于尘世存现的一个阶段和过程。
在整体观念和全体性思维方式之下,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和载体,苏轼游处的思想得以初步形成,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成型。下面,我们来看苏轼游处思想的内涵与特征:
其一,“形”游,即作者现实生活中的江海迁转和飘荡的感受,可谓现实中的游处。有时作者直接申言江海迁转的行者与过客意识和飘荡的感受:“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送曹辅赴闽漕》)[8]1505;“漂零竟何适?浩荡寄此身”(《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8]1923;“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郁孤台》)[8]2269;“大哉天地间,此生得浮游”(《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8]503;“我自飘零足羁旅,更堪秋晚送行人”(《送惠州押监》)[8]2039;“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8]2218。这种游主要是现实仕途上的迁转和流徙的官场现象。有时以象喻性的载体来比拟现实中的游处,暗喻自己行者与过客的身份。比如,他以水波比拟:“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三)》〕[8]455以浮萍比拟:“一身萍挂海中央”〔《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一)》〕[8]2256;“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8]316;“赤子视万类,流萍阅人寰”(《送程七表弟知泗州》)[8]1504。以舟比拟:“生涯到处似樯乌”〔《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三首(其三)》〕[8]382;“忆昔江湖一钓舟”(《次前韵送程六表弟》)[8]1497;“此身随造物,一叶舞澎湃”(《韩子华石淙庄》)[8]440;“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8]2273-2274;“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9]467。以飞蓬比拟:“离合既循环;我生如飞蓬”〔《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二)》〕[8]252。以鸿雁比拟:“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谢运使仲适坐上送王敏仲北使》)[8]1881;“松风梦与故人遇,自驾飞鸿跨九州”(《睡起》)[8]2386。以传舍比拟:“此生如传舍”〔《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9]22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具有流动性和时间、空间变化跨度的象喻性载体,可以使作者现实中虚浮的飘荡感受得以真切地再现出来,其生存方式也因此而充满了审美的诗意特征。
其二,“象”游,基于对一定的现象要素的审美观照所感受到的游处、流转、变迁的文化心理与现实心境,可谓壶天式的镜像游观。“象”游是审美主体以生命情怀或审美精神为动力,以审美心理为基础,以审美的超功利眼光所展开的对外在物象、人类生命活动的虚化的图景、心灵深处的观念影像类“象”的观照活动。苏轼信奉自然之道,常认为,生命所处的外在环境是个整体,即壶天世界,而自我则游处其中:“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8]92。这是相对比较实在的“象”游。还有富有诗意的尘世之游,个体只是尘世的行者和过客而已:“散策尘外游”(《尘外亭》)[8]1944;“此身江海寄天游,一落红尘不易收”(《次韵王定国倅扬州》)[8]1446。此类虚化的社会和人生之“象”,虚空而阔远。还有作者观化、观省世情百态的游,即文化心象、心灵影像之游:“世事徐观真梦寐”(《送蔡冠卿知饶州》)[8]299-300;“荣华坐销歇,阅世如邮传”(《自净土步至功臣寺》)[8]326;“谁言此弱质?阅世观盛衰”(《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8]2156。这是一种心灵的审美活动,也带有哲理思辨的意味,是对人间万象与世事盛衰变化影像的心灵观照和游观活动。
其三,神游,思想上执理寻道和与道合一的追寻、体悟和心灵自我放飞的哲理观化活动,可谓直觉式的合道的心灵体悟与哲理观化式的思想游处。现实不顺意,但苏轼能在体道和审美的神游中自乐。一边在积极地执理问道寻道,神游于方外,如“赤松共游也不恶”(《陪欧阳公燕西湖》)[8]254,“敢问老聃所游;且到南华一游”(《仆所至未尝出游过长芦闻复禅师病甚不可不一问既见则有间矣明日阻风复留见之作三绝句呈闻复并请转呈参廖子各赋数首》)[8]1928,独立的参禅悟道活动可获得内在心性的安适,如“道存目击岂非温”(《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称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笔奇妙而字不可识云天篆也与予言有所会者复作一篇仍用前韵》)[8]1075,还可以与方外之士执道共赏,如“犹喜大江同一味,故应千里共清甘”(《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8]1078;一边体道悟道、追寻与道合一的心、道契合的愉悦安适与心境的超然,神游于心灵,如“眼前勃蹊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戏子由》)[8]296,“心无天游室不空,六凿相攘妇争席”(《送蹇道士归庐山》)[8]1510,“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次韵阳行先》)[8]2273。苏轼喜好哲理思辨,在悲剧人生观的指引下,在自然之理的观化之下,常有看破成空而悲感色彩浓厚的至言:“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吉祥寺僧求阁名》)[8]306-307这类体道的神游之论虽空幻虚无,但毕竟能消解形名之困累,而有助于悲感体验中解除现实的烦恼和困惑。当然,心灵自我放飞的神游,往往充满了哲理观化与诗意审美的味道:“振翮游霄汉”(《入峡》)[8]17;“人间俛仰三千秋,骑鹤归来与子游”(《送蹇道士归庐山》)[8]1511;“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8]244。这种神游与哲理观化(“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迁居》)[8]2068;“嗟汝独何为?闭门观物变”(《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其一)》)[8]179;“谁见槛上人,无言观物泛”(《次韵子由岐下诗》)[8]97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观化万物和物理,而等同一切于内心(“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不烦计荣辱,此丧彼有获;愿君付一笑,造物亦戏剧”(《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8]1506-1507),最终会发现个体只是世间的行者与过客而已。最终,在以“道”御心和对生命的审美体验活动中,作者以气存性,达到了内胜超然的境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独觉》)[8]2140
苏轼天地游处的观念、生活态度和方式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其“形”游、“象”游、“神”游的方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情感、生命体验的特征,可谓其诗性精神与文化情怀的体现。
6 结语
苏轼以儒立身、力主有为,乌台诗案后,其人生理想也渐趋由早年“外王”的仕途建功向人生中后期“内圣”的性情修持、“立言”自适方面转化了,其人生态度虽不够积极,但进取有为的大方向始终没变;同时,士人公心济世的责任感和臣子感恩报国*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论给田募役状》中云:“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伏惟哀怜裁幸。”类似奏章很多。可见,苏轼对北宋君主的感恩报国之心。参见文献[4]卷26之《论给田募役状》,第771页。的使命感也使其不可能真正地退隐田园。于是,外向建功与内向适心之间“游处”的平衡策略和方式就出现了。
苏轼的游处思想、态度、方式生成的前提,是其整体观念与全面观照对象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和方式,而其整体观念和全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主要得力于其自然之道即作为万物之理的大全之道,而源于现实生活和仕途经历而来的对生命的时空体验和整体感观,则成为其整体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核心。当然,以老庄为主的道家的生命体验、时空观念和对壶天的信仰,以及作者对人生的现实体验、道家内足安命的修持方法、佛家内向心性修养的义理所共同促成的苏轼内足无待的人生态度和生存哲学,也是其整体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
从整体着眼来观照万物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倾向,是其游处思想、生活态度和方式得以生成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苏轼的游处思想的形成还与佛家无念无住的思想与因缘意识有关,无念无住的思想和因缘意识分别构成了游处的思想前提,观念形态,行动的原则、方式和内助力量;还与作者的中隐思想有关,可以说,现实中隐的生活方式也反向强化着作者的游处思想和态度的建构和成型;还与作为作者中后期人生价值转向的方向与载体的艺游活动有关,艺游活动可以说既是作者游处思想、态度、方式得以形成、实行的心理前提和基础,又是其游处方式和现实中隐方式的辅助和补充。即此,最终,其游处思想和方式得以建构与成型。而苏轼的游处思想、态度、方式,也为处于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目标的矛盾状态和生存困境中的士大夫文人,指出了适宜可行的方向与出路。
参考文献:
[1] 礼记今注今译[M].王梦鸥,注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318.
[2] 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94.
[3] 庄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重排本[M].陈鼓应,注译.2版. 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茅维.苏轼文集:全六册[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M].陈鼓应,注译.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苏轼.东坡易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0.
[7]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苏轼诗集合注[M].冯应榴,辑注. 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 苏轼词编年校注[M].邹同庆,王宗堂,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 尚永亮.“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2).
[11]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第18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223.
[12] 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76.
[13]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 卷3[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87.
[14]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修订本[M].吕绍纲,修订.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