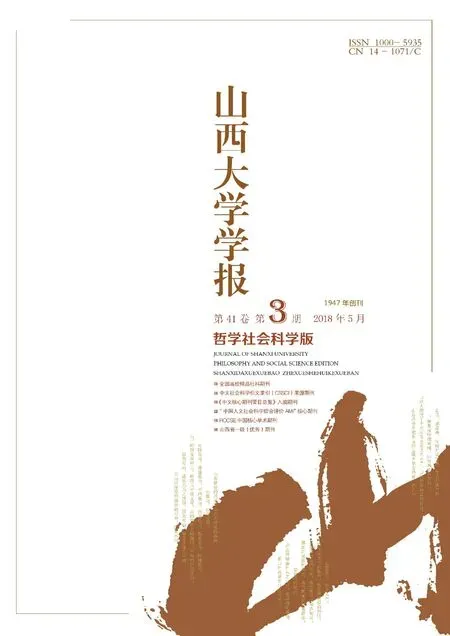乱世情缘中的自我书写
——对张爱玲《少帅》的一种尝试性解读
2018-03-17王春林
王春林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或许与曾经出版过一部名为“传奇”的小说集有关,或许真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也的确称得上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当然了,虽然她早在1995年便已凄然弃世,但此后却仍然不断地会有“新作”出版问世,也同样是一种传奇。这里的所谓“新作”,是指作家生前并未能正式出版,但却遗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手稿,经她所信任的朋友授权后方才与读者见面的那些文学作品。比如散文《异乡记》,比如长篇小说《雷峰塔》《小团圆》《易经》,再比如我们这里将要展开讨论的《少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其情形都是如此。从这种出版方式来看,张爱玲的情形多多少少差堪比拟于先知作家卡夫卡。卡夫卡本来要求朋友把他自己遗留的手稿销毁,没想到的是,朋友却违背了他的遗嘱。不违背不要紧,一违背,就“违背”出了一位世界级的具有强烈先知色彩的大作家。但面对《少帅》,首先让我们感到困惑的,却是文体究竟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一方面,不仅大陆出版此作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版权页上明确标注是“长篇小说”,而且根据张爱玲的若干书信以及相关知情人的回忆,张爱玲在当年也是把这部作品当作“长篇小说”来写作的。但在另一方面,以研究者冯晞乾在《<少帅>考证与评析》中的说法“现存打字稿有八十一页,共七章,约二万三千英文字,是未完稿”[1]23,如果按现存的中文译稿来计算,字数大约不足六万字。六万字是什么概念呢?按照茅盾文学奖的规定,只有满十三万字以上的作品才能够申报。同时,按照当下时代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解,如同《少帅》这样不足六万字的小说文本,只能够被看作是一部中篇小说。那么,《少帅》的文体究竟该如何定位——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在做出这种判定之前,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西之间小说文体观念上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年来翻译介绍进来的一些具体作品,就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比如,阿契贝的《瓦解》《神箭》《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再比如,菲利浦·罗斯的《乳房》《情欲教授》等,这些作品的中译本字数大约都在十万字左右,有的干脆还不足十万字,但版权页上的标注却都是“长篇小说”。如果考虑到当时身在美国的张爱玲所接受的西方相关观念的影响,倘若《少帅》最终能够如愿完稿,那么其字数大约也会接近十万字左右。这样看来,作家本人或者出版社把《少帅》标注为“长篇小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唯其因为在文体的定位上颇费踌躇,一时难以决断,所以到最后也就只能含糊其辞地笼统称之为小说。
只要是熟悉张爱玲的朋友就都知道,与她本人那样一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她小说创作过程中几乎一以贯之的日常叙事特质。日常叙事,是一种与国家叙事相对应的叙事范式。按照学者的研究,所谓国家叙事,是一种“大叙事范畴,说它‘大’并不一定指其题材之大,而是其旨趣、题旨、根本目的之大。”[2]而所谓日常叙事,则指“平民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种族、环境、时代’均退居背景。人的基本生存,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爱情、婚姻、家庭的日常琐事,突现在人生屏幕之上。每个个体(不论身份‘重要’不‘重要’)悲欢离合的命运,精神追求与企望,人品高尚或卑琐,在作家博大的观照之下,都可获得同情的描写。”[2]“日常叙事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每位日常叙事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致力表现‘人生安稳’、拒绝表现‘人生飞扬’的倾向上,日常叙事的作家有着同一性。拒绝强烈对照的悲剧效果,追求‘有更深长的回味’,在‘参差的对照’中,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是日常叙事一族的共同点”。[2]从如此一种角度出发来考察张爱玲的小说,日常叙事特点的具备,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且,敏感者还应该注意到,论者谈论界定日常叙事特质的过程中所专门引述的“人生安稳”“人生飞扬”“有更深长的回味”“参差的对照”乃至于“苍凉”这些语词,都独属于张爱玲,语出作家的一篇名作《自己的文章》。
然而,如果说张爱玲的包括《雷峰塔》《小团圆》《易经》(这些均在作家辞世后方始出版)在内的所有小说都具有鲜明的日常叙事特质,那么,这部《少帅》显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异数。“少帅”,原型乃张学良者是也。张学良,毫无疑问是20世纪中国一位不可或缺的历史风云人物,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他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以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张爱玲的《少帅》就很可能会走向国家叙事,而事实上,它也是一部包含有明显的国家叙事艺术因素的小说。就这样,破天荒地,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看到了中国现代史一众乱世枭雄的形象。比如首任大总统(袁世凯)、老帅陈祖望(张作霖)、基督将军冯以祥(冯玉祥)、吴蟠湖(吴佩乎)、殷锡三(阎锡山),甚至还有那位曾经游走于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的外国人罗纳(其实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等,都是那段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一众乱世枭雄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直系、奉系以及皖系几派军阀之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混战,比如,对中国政局影响巨大的所谓蒋冯阎“中原大战”,再比如,老帅(张作霖)在皇姑屯的被炸身亡,等等,也同样都在《少帅》中得到了相应的艺术表现。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簇拥在一部小说文本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回顾中国本土小说传统,国家叙事与日常叙事可以说是两大艺术范式,《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国家叙事,《红楼梦》《金瓶梅》是日常叙事,两者均获得了极高的思想艺术成就。如此看来,张爱玲的《少帅》显然接续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传统。尽管说作家更多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把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推至远景而加以表现,以至于这些人物和事件都会给读者造成不够清晰的模糊混沌之感(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讲过的一句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但毕竟,张爱玲是在首次进行着她的国家叙事。我们之所以认定《少帅》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种异数,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虽然《少帅》初涉国家叙事,但究其根本,张爱玲还是接受《红楼梦》的充分滋养成长起来的作家,也因此,一旦进入写作状态,骨子里的那种日常叙事根底就会暴露无遗。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开头处一张意外的纸条所引起的府里一众女孩子的嘈杂,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纸条上写着:“小姐,明日此时等我。”府内女孩子众多,那么,这张纸条到底是写给谁的?更进一步,写这张纸条的人又究竟是谁?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张纸条,便引发了府内女孩子们的种种猜想与叽叽喳喳。大家一边纷纷猜想这纸条是给自己的还是给别人的,一边耐心等待到次日的此时揭开谜底:“她们躲在一个窗户后面张望,撅着臀部,圆鼓鼓的仿佛要胀破提花绸袴,粗辫子顺着乳沟垂下来。年纪小的打两根辫子,不过多数人是十八九岁,已经定了亲等过门。她们对这事兴冲冲的,可见从来没爱过。那种痴痴守望一个下午的情态,令四小姐有点替她们难为情。那男人始终没有来。”尽管说纸条的谜底始终是个谜,但作家关于那些女孩子隐隐约约有所期待的纠结心态的展示,却是情态毕现。实际上,如此一张无来历也无去处的纸条的作用,不过是要借此引出周府的四小姐而已。由此即不难见出,只要笔涉日常生活情景,张爱玲的笔触马上就如有神灵附体一般鲜活生动起来。这一点,也集中表现在关于周四小姐婚姻大事的描写上:“她自己为此而死也愿意,但是洪姨娘和老妈子怎么办?她们是她的地狱。只是她对地狱没有执念。眼前她不必言语,低着头就是了。洪姨娘的反应已是极度温和。尽管如此,他与她的事旁人一提就是亵渎,令她不由得绷紧了脸退缩。旁人看上一眼已是误解。”家里人之所以会对周四小姐与少帅的事情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乃因少帅已是有家室的人。这样,她和少帅的情缘事实上就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状态之中。周四小姐自己倒是心甘情愿,所以,才会是“为此而死也愿意”,但家人们的想法就很不相同了。因此,叙述者才会强调洪姨娘与老妈子“是她的地狱”。也正是因为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之中,才会致使“他与她的事旁人一提就是亵渎”。虽然是简短的一段叙述话语,但周四小姐婚事所引发的矛盾纠葛却已跃然纸上。由此可见,虽然张爱玲在《少帅》中的确初涉国家叙事,但归根到底仍是一位日常叙事的高手。倘若我们要在张爱玲的小说写作谱系中给出《少帅》一个基本的评价定位,恐怕只有“国家叙事中的日常叙事”最为合理了。
细细捡拾张爱玲弃世后相继由她的友人陆续推出的长篇小说《雷峰塔》《易经》以及《小团圆》,正如研究者早已指出的,其中自传性因素的存在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故被研究者合称为她的“自传三部曲”。与这三部长篇小说相比较,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少帅》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作是自传性的作品。但请注意,《少帅》虽然取材于张学良的故事,但作家所真正感兴趣的,却并非他那些金戈铁马打打杀杀的疆场故事。说实在话,那些“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兴衰故事,很可能从来就不曾走入过张爱玲的内心世界。她之所以打小就特别喜欢并认同《红楼梦》,极有可能与她的天性有关。因此,当她意欲讲述张学良的故事的时候,聚焦点自然就会落在张学良的爱情故事上。只不过到了小说文本之中,张学良变成了陈叔覃,赵四小姐变成了周四小姐。据研究者考证,张爱玲在《少帅》中并没有完全照搬历史上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比如,关于周四小姐的老父:“首章说他跟老帅陈祖望(现实中的张作霖)‘关系特殊’,第二章说他曾以‘东北总督’身分(份)提携过老帅,而老帅亦曾助他解困,都完全跟历史中的赵四小姐父亲无关。真正的赵父叫赵庆华,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曾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长,又当过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属直系官员,谈不上有恩于老帅。”[1]47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小说写作而言,这种虚构是必要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看到,就其大的历史关节而言,作家还是尽可能恪守了历史的真实。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既要恪守真实,又不能不有所虚构,历史小说的写作,正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然而,谈到张爱玲对陈叔覃与周四小姐之间爱情故事的描写,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作家果真是在如实呈现作为人物原型存在的“张赵”爱情故事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这固然在于对于“张赵”的情感私生活情形,张爱玲更多只能够依凭于自己的艺术想象,但退一步讲,即使作家完全有能力搞明白“张赵”情感私生活的全部真相,她也不会在写作过程中亦步亦趋地去完成一种他人的情感纪实。又或者,一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想象性书写表达“张赵”情感私生活的同时,作家其实自觉不自觉地把自我的情感体验移植了进来。此所谓“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在一篇关于老舍《月牙儿》的研究文章中,笔者曾经指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可以说,作家一辈子都在写着自传或精神自传。’假若我们承认精神分析学说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把老舍的所有作品都视为作家的某种变异了的‘精神自传’,虽然作家本人与作品的叙述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但从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却仍可把《月牙儿》归入作家的‘精神自传’之列。”[3]如果说以上的观点适用于老舍的《月牙儿》,那么,毫无疑问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的这部《少帅》。说到张爱玲自己始终难以释怀的情感块垒,就是她与胡兰成之间那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纠葛。虽然作家的生命中后来还出现过第二任丈夫美国人赖雅,但那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生存的需求而已,最起码在张爱玲自己,情感的投入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或许与当时年龄与地位的不同有关,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段情缘始终存在着某种突出的不对等性。张爱玲的一腔深情与胡兰成的蜻蜓点水始乱终弃,至今想来都让人感喟不已。尽管张爱玲并没有就自己与胡兰成之间的情缘纠葛直截了当地说过什么,但在她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中,我们却还是不难感觉到会有很多旁涉自我的弦外之音。这一点,最集中不过地体现在《少帅》中关于陈叔覃与周四小姐性事的描写上。“他探身掸了掸烟灰,别过头来吻她,一只鹿在潭边漫不经心啜了口水。额前垂着一绺子头发,头向她俯过来,像乌云蔽天,又像山间直罩下来的夜色。她晕眩地坠入黑暗中。”一般人笔下,初吻既是惊慌的,但又是甜蜜的。然而,到了张爱玲的笔下,这一切却都不复存在。无论是“乌云蔽天”,还是“直罩下来的夜色”,抑或“坠入黑暗中”,所有这些比喻性描写,带给读者的都是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与所谓的幸福、甜蜜无关。关键的问题是,如此一种只能够让人联想到“不堪”“苟且”(小说中所用)语词的性事描写,在《少帅》中居然成为一种笼罩性的存在,比比皆是……恕我孤陋寡闻,此前也曾经在很多小说作品中看到过关于男女性事的描写,但与那样一些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语词联系在一起的,却真的是闻所未闻。性事描写一旦与这些贬义语词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就无论如何都美好不了。这哪里是在描写陈叔覃与周四小姐的性事,这简直就是在直接呈示张爱玲理解中的一种不堪性事。又或者,陈叔覃与周四小姐之间的性事,在张爱玲这里只是承担一种突出的镜像功能,借此而折射映照出的,其实是作家对性事的别一种理解与想象。
由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其他作家笔下一般都美妙异常的性事描写,何以到了张爱玲的《少帅》中却会变得如此“不堪”,会带有如此突出的“苟且”色彩?答案恐怕只能从张爱玲自己的情感体验中去寻找。按照研究者的考证,《少帅》的写作念头初始生成于一九五六年,等到真正着笔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三年左右了。这个时候,距张胡之间的情感纠葛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时间的流逝,既可能淡化一般性的人生记忆,却也可能强化某些特别的人生记忆。对于已经去国多年且生存境况并不尽如人意的张爱玲来说,很多人生往事都已淡忘,然而,一些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反倒会进一步强化。这其中,首当其冲者,恐怕就是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又或者,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发酵过程之后,张胡的情感纠葛业已沉淀入张爱玲的个人无意识深处,变成了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释怀的精神情结。唯其因为无法释怀,所以她才会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反复地书写表达这种精神情结。《少帅》中陈叔覃与周四小姐的情感故事,表面上看是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但其内在却毫无疑问是张爱玲自己与那位始乱终弃的风流才子胡兰成。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对于这段情缘,张爱玲在理解认识上伴随着时间推进的一种必然变化的发生。倘若说当年置身于情感发生情景中的张爱玲曾经会感觉到幸福甜蜜的话,那么,时过境迁差不多十年之后,当作家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重新面对这段情感的时候,却更多地意识到其中丑陋不堪的一面。由此可见,写作《少帅》时候的张爱玲,实际上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一方面,她与胡兰成之间的情缘对她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来说,可以说是唯一一次倾心投入的感情过程,因此这段情缘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被忘却。她之所以后来在“自传三部曲”、在《少帅》中要一再书写表现这段情缘,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另一方面,虽然她自己倾心投入,但这场情缘却最终因为胡兰成的背叛而以悲剧的结局草草收场,以至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后来者叹惋不已的悲剧情缘之一。反复追问思考,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正是胡兰成。因内心一种难以释怀的对于胡兰成的怨憎情结强烈作祟的缘故,《少帅》中一旦笔涉“陈周”的性事场景描写,才会那样“不堪”入目,那样充满“苟且”色彩。归根到底,小说中这种种“不堪”与“苟且”的性事描写,所曲折传达出的,正是张爱玲潜意识深处那种无法释怀的精神情结。
但请注意,如果只是停留在自我精神情结一种折射书写的意义上来理解《少帅》中关于陈叔覃与周四小姐的情感故事叙述,还并没有穷尽小说的深邃思想内涵。更进一步,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张爱玲同时也表达着对于女性悲剧命运一种人类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就在开篇不久的第二章结尾处,首先是由周四小姐一位异母的姐姐引发出一句议论:“盲婚如同博彩,获胜的机会尽管渺茫,究竟是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尤其在婚姻尚且遥远的时候。”由这句议论,叙述者接着讲述周四小姐在私塾里曾经念过的一首古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首古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杜牧。引述了杜牧全诗之后,这一章结尾的文字是:“从前扬州的一个妓女,压倒群芳的美人与她竟然同龄,简直不能想象。十三岁,照现代的算法不计生年那一岁的虚龄,其实只有十二。她觉得自己隔着一千年时间的深渊,遥望着彼端另一个十三岁的人。”远在一千年前扬州的一个妓女,与周四小姐之间,很显然是一种彼此遥相呼应映照的关系。具而言之,作家是要借此而写出悠久历史长河中女性的一种共同悲剧命运。所以,请一定不要忽视引述杜牧全诗前的那一句议论,尤其是“盲婚如同博彩”六字。归根到底,周四小姐也罢,她的那位异母姐姐也罢,抑或还是一千年前的那位扬州妓女也罢,都存在着一个“盲婚如同博彩”的问题。所谓“盲婚如同博彩”,意谓女性的婚姻其实带有突出的赌博性质,正如同博彩下注一般。下对了,有可能赢得万贯,下错了,自然是满盘皆输。如此一种感慨性描写的背后,显然有张爱玲真切的人生经验在做支撑。张爱玲与胡兰成情感纠葛的悲剧性结局,所证明的正是张爱玲的所托非人。这就难怪《少帅》第二章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作结。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如此一种人生思考,在《少帅》中并非只此孤例。比如,与陈叔覃首次发生性事前:“她正因为不惯有这种不受干涉的自由,反觉得家里人在监视。不是她俨然不可犯的父亲,在这种环境根本不能想象;是其他人,总在伺机说人坏话的家中女眷,还有负责照顾她的洪姨娘与老妈子。她们化作朴拙的、未上漆的木雕鸟,在椽子与门框上歇着。她没有抬头,但是也大约知道是圆目勾喙的雌雉,一尺来高,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她自己也在上面,透过双圈的木眼睛俯视。”如同此前关于扬州妓女的穿插一样,这里很明显也属于一种想象性描写。问题在于,陈周的第一场性事何以会让作家产生如此一种其他女性皆在“俯视”围观的想象性场景?更何况其中居然还包括有周四小姐自己。而且,这些女性的化身皆是“朴拙的、未上漆的木雕鸟”。在我看来,这种想象性书写,一方面意在表明周四小姐性事过程中的那些“不堪”感受,其实也是这些女性共同的感受,另一方面更在强调这些女性生命力的凝滞与匮乏,简直到了“呆若木鸡”的程度。所谓“木雕鸟”者,其内在意涵或正在此。类似的描写还出现在第四章结尾处:“他拉着她的手往沙发走去。仿佛是长程,两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线,让她落后了几步。她发现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他妻子以及别的人?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分(份)。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们就是人类。”这是一次性事结束后陈叔覃牵手周四小姐时,周四小姐产生的一种幻觉。此种幻觉中,周四小姐竟然与陈妻一起加入到“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而且“她们就是人类”。“人类”一词极为关键,有了这个词,作家在更大范围内透视表现女性共同悲剧命运的思想意旨也就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
阅读《少帅》,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段叙述话语的突兀存在:“虽然这故事早于他的时代,她不知怎么并不愿意告诉他。那一定是吴蟠湖的时候。现在做法肯定不一样了吧?可是一说起其实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就难免恼火。”陈叔覃是着眼于社会改造的政治活动家,看到现实社会多年来的毫无起色,心中自然会感觉“恼火”。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张爱玲这里写出的,一方面固然是民国初年所谓“北洋军阀”时期中国一种“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却是“换汤不换药”根本就没有什么改变的严酷社会现实,但另一方面却非常明确地传达出了作家一种只能够以“绝望、虚无”称之的世界观。关于《少帅》的深刻思想内涵,曾有论者指出:“质疑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的意义,拆穿‘五四’后的所谓进步,我认为是《少帅》小说的第二层宗旨。这种略带悲观的怀疑态度(未至于是主义)其实是一种所罗门王式智慧。早在四〇年代,张爱玲已被《旧约·传道书》的厌世文辞所震动,而《少帅》的第二层宗旨,仅一句‘太阳之下无新事’似乎已足够概括。正因为‘太阳之下无新事’,所以一千年前的扬州妓女跟周四小姐才会承受共同的命运。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不同年代的人无意识地扮演着相同的角色,没完没了地搬演着同一出戏,其实一切没变。不单是现代和古代的界线模糊了,文明和野蛮、进步和守旧也统统不再泾渭分明。”[1]65当“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守旧”也都不再泾渭分明的时候,作家一种只能够被看作是“绝望、虚无”的精神底色,自然也就凸显无遗了。更进一步,一种“绝望、虚无”的世界观,所最终通向的,就是现代层面上人类生存的荒诞与无意义。海明威的渔翁身陷凶险的大海大功尽弃(《老人与海》),卡夫卡的大甲虫脑袋指挥不动细足纷扰的硬壳(《变形记》),萨特的囚犯竟连自身的生理机能也屡屡失禁(《墙》)。“现代派笔下的人物,史诗般的豪气越来越薄,猥琐的散文味却越来越厚,不是走向尊严,而是流为卑微。”[4]原型为张学良的陈叔覃,本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但到了张爱玲的《少帅》中,却变得越来越猥琐和卑微了。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小说关于陈周性事描写的“不堪”与“苟且”,也就有了突出的象征色彩。很大程度上,它所象征说明的,正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日益猥琐与卑微。这种猥琐与卑微,再加上作家世界观的绝望与虚无,确证着现代中国作家张爱玲与世界现代文学一种深层次上的息息相通。
前此一个阶段,阅读当代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野狐岭》,我一方面注意到了其中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明显流露,另一方面却也注意到了作家对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真切爱情的超越性倾情书写。并由雪漠对于爱情的超越性倾情书写,而进一步联想到了李泽厚关于“情本体”*关于李泽厚的“情本体”哲学,请参阅他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与《中国哲学何时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等相关著作。的相关论述。我的结论是,凭借着如此一种“情本体”,雪漠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精神超越。但是,到了张爱玲的《少帅》中,我们却不无震惊地发现,就连本来有指望拯救历史虚无主义的情感世界本身,也已经大有问题,已经处于“不堪”和“苟且”的状态了。这样一来,张爱玲的“绝望”与“虚无”也就只能够更加彻底地“绝望”与“虚无”了。
参考文献:
[1]冯晞乾.《少帅》考证与评析:《少帅》别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2]郑波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J].厦门大学学报,2003(4):56-62.
[3]王春林,王晓俞.《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J].文艺理论研究,1996(3):60-66.
[4]夏中义.接受的合形式性与文化时差[J].上海文学,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