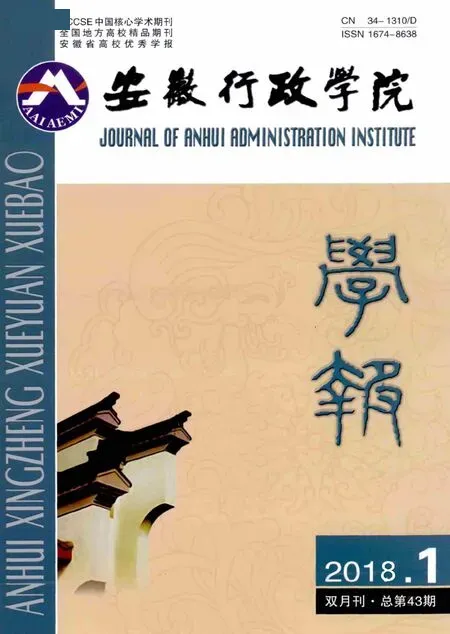国家与市场:论政府在产业培育中的基本角色
2018-03-16赵亭亭封凯栋李君然
赵亭亭,封凯栋,李君然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一)自由市场和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国家与市场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是经济学家最关心也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1];二战以来,政府与市场何者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持续引起广泛的论战①。辩论双方的主要观点在于: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国家在市场中的角色,推崇最小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只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另外一种看法则赋予国家在知识经济中更多的功能和职责,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系统性缺陷。这两种对国家在知识经济中的定位,分别对应着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自由市场和凯恩斯主义,主要理论根据和经验证据见图1所示。

图1 政府与市场:支持和反对的根据[2]
这两种政策思维在理解国家与市场关系中存在共性:市场的先决存在性。都将市场的存在视为给定条件,将国家视为市场系统之外但以不同程度介入市场的一个特殊行为者;国家并不或很少从事市场性生产和交换活动,更多是作为制度框架和特殊商品(货币、知识、人力)的提供者而存在。这两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思维的共性见图2。例如,市场创新中,流行的政策观点认为只要给予私人部门足够的激励,就会促进私人部门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商业化创新自然随之产生。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政策实践就是税收激励。但是以这种政策思维指导实践想要发挥其预期的政策目的必须依赖于两个重要但是又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第一,市场已然存在,其含义是市场上存在能够在该产业进行研发的企业主体;第二,资金(税收)激励足以克服私人部门(企业)对风险的厌恶和规避,愿意投入密集的资金和人员进行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

图2 市场关系的共性:已经存在的市场
(二)国家:市场缔造者
本文认为,市场不是给定的存在,特定产品或产业市场是被人为建构和发展出来的;而它的创造者就是国家。库兹涅茨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工业产品或产业[3]。基于新的产品或新的工业产业,资源配置及配置效率将发生改变;如果将市场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那么新的工业(产品或产业)被创造出就等同于新的市场被创造出来。作为产生新工业领域的基础——全新的、突破性技术革新,它所需要的新知识以及新知识的商业化应用机会,往往是国家直接行为或在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获得。从这一意义上讲,本文认为国家开创了市场。具体而言,国家通过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形式开发了知识和生产技术,又通过直接购买前沿创新产品(例如国防订单)的形式确保这些知识被应用于生产;“不完美的”创新得以获得持续改进的机会,并最终可以实现商业化盈利。在这个过程中,新产品被创造、从事新产品生产的一批企业被培育出来,新的市场也就随之产生。因此,本文认为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它并非市场不足的弥补者,或特殊市场资源(人力资源、制度等)的外部供应者;而是根本意义上的缔造者。
本文进一步认为,在新市场建构的过程中,知识的产生与知识的商业化这两个环节都高度依赖国家的参与才可以完成。就知识本身的生产而言,绝大多数理论都承认它带有公共品属性,被生产出来之后也将产生较强的正外部性;因此一直面临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
二、经济史上的证据: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与市场
这种国家对市场的缔造作用早在一战时期就普遍存在。无线电产品在一战中成为美国海军通讯的支柱,战后美国政府认识到这一产业的战略性意义,所以命令通用电气买下了马可尼公司,并协助新公司买下了无线电专利技术。这样,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成立,无线电产业被塑造出来。但是,二战之前政府的直接介入很少,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工程大学等方式,实现对产业的影响。
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发展实践中,政府以更直接、更积极的方式介入市场塑造,其主要方式包括:①研发投入,包括政府投资企业进行研发,政府下设的研究机构进行研发,政府资助大学的研究;②新产品的购买者;③行业标准和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通过各种政策法规促使知识在公私部门之间的流动和传播;④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风险资助。
(一)战争期间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战争期间政企关系的主要特点:首先,国家的全方面介入获得了合法性,而这一做法奠定了二战后至今国家介入科研和生产的政企互动基础;其次,在具体的知识和生产领域,美国开创了二战后最重要的制度性创新之一,即政府直接雇佣或委托大学对科学项目进行管理和开发,并发展为延续至今的产学研系统;第三,美国通过直接管理、利润丰厚的国防订单、战后优惠赎买政策等培植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如前文所提及,二战之前美国政府直接参与或管理研发和工业生产的情况并不多见,除了RCA的建立。尽管联邦政府一直支持科研活动,美国也有一些科研机构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斯密森学会和美国地理学会。但是政府直接支配和指挥科学研究项目是被抵制的,这种直接作为被认为会使科学失去“自主性”[4]。二战期间,出于战争的需要,政府大量收购先进技术并雇佣科学家、工程师进行有关军事科技的研发,同时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产业也被纳入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的范围内。这样做产生了两个相关联的结果:首先,大量科学家的介入产生了先进的技术成果;其次,战前已经被发明出来但只限于小众业余爱好的技术因其具备战略性,得到迅速的推广和扩散。政府的直接管理和扶植产生了一个繁荣的国内市场,通过战争期间丰厚的利润和战后条件优惠的售卖,这些企业成为拥有很强自主开发能力的大公司,为战后美国科技和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直接管理科学方面,有两个主要的标志性事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ffice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和曼哈顿项目的建立。它们共同确立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有关知识的生产和知识转化的制度安排。
二战之前,美国的军事技术研发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使用军方自己的军事实验室和通过国防承包合同委托私人承包商开发。二战期间主要通过OSRD的全国性协调职能,美国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和模式:直接给高校拨款并干预高校的研究方向。例如,1942年美国政府直接任命伯克利教授奥本海默负责的曼哈顿计划(最初设立在伯克利校园里,后来迁往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此外,美国政府指派了弗雷德特曼成立并领导哈佛大学无线电研究实验室,主要负责电子战中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战争期间的另一重要制度创新在于技术可以快速直接在国家参与下转化为产品。例如,马克米兰和西伯格在伯克利辐射实验室发现了钚元素,在维持爆炸的连锁反应时,这种新元素的威力优于铀235。美国政府立刻在汉福德设立了工厂,生产这种元素。这种做法为高校介入国家工业和创新系统,构建政府—高校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二战期间最重要的技术成果之一就是计算机,而计算机所涉及的主要技术基本来自政府实验室或军方资助的研发项目。1943年,美国陆军弹道研究实验室主持了新的研发项目——PX项目,来取代老的布什差分分析仪,满足计算弹道轨迹的需要。哈佛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Howard Aiken设计了哈佛马克I样机,并于1944年2月完成。1946年在军方的资助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ohn Mauchly和Presper Eckert最终研制成了ENIAC,也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尽管ENIAC占地160平方米,重达30吨,完全不可能实现大规模商业和民用化,但是随着晶体管和存储介质等的发展,这一技术成为未来计算机、信息和互联网产业的基础。
除了这类还需要辅助系统和技术进一步发展才能够实现商业化的先进技术之外,战争期间,政府出于战争目的直接介入和扶植了一些战略性产业,本文以化工制药产业为例,说明政府对产业的直接塑造和培育作用。
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大约4 500项德国专利,政府对这批知识资产的处理办法是向国内领先企业开放。对美国企业来说,专利的获得并不意味着研发能力的获得,但是,专利壁垒的解除促使企业做出内部研发的决策[5]。更重要的是,由于有机化学品之间更紧密的关联性,美国公司在合成染料方面的研发投入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内部吸收和创新能力,为二战期间重要的合成聚合体产品尤其是合成橡胶的研发和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战期间,美国将主要橡胶企业、标准石油公司和国内主要化工公司组织在一起,进行一个合作研发计划。政府选择了丁纳橡胶-S为研发和生产目标,并由联邦政府累计投资约7亿美元建造生产工厂,战后这些工厂大部分以优惠条件售卖给战争期间的合作企业。合成橡胶市场通过战争期间的合作计划和战后的联邦资产售卖而被培育和建立起来,就市场份额来看,1941年橡胶产量为80万吨,1945年为90万吨,其中合成橡胶在1941年占橡胶消费市场总量的0.5%以下,194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4]。
这一阶段知识的产生和扩散的主要特点和机制是:公共部门,尤其是军方是知识创造的主要投资者和重要参与者;私人部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反垄断法)等因素也参与到知识的产生中来;政府出于战争的目的将大学纳入这一知识创造系统,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学的研究方向。这一多重主体的知识产生系统,事实上为战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组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期间重大科技发现或产品研发都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许多战前就发明出来的先进技术因此得到实际应用和扩散(尽管不都是大规模商业化的),更多的先进产品和技术在这一阶段被制造和发明出来,为战后的美国保持先进的科技和商业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更多的合作在政府—大学或政府—企业之间展开,私人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以依托政府项目和组织为主,例如美国政府组织的聚合橡胶研发合作项目、IBM和哈佛大学联合为美国政府研制哈佛马克I号计算机。此外,这一时期的军工合作也为二战后饱受争议的军工复合体的诞生和战后初期大型企业集团占据优势的市场结构奠定了基础,战后军事研发和制造订单倾向于与那些战争期间就有合作的企业签订,例如IBM,这些承包商也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一级国防承包商。
(二)冷战期间的政企关系
尽管二战暂时搁置了关于科学研究与公共部门之间关系的争议,但是这种争议和怀疑远没有消失。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关于科学独立性的讨论重新激烈起来。1957年,随着苏卫一号事件的发生,美国军政各界和公众进入了国家安全压倒其他目标并获得了极大的政策优先排序的背景[6]。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武器开发的方向是追求更先进的尖端武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研项目以追求更高新、更先进的科技为目标。这种性能导向型的知识产出系统,决定了这一阶段公共部门主持和资助的项目所产出的知识以更先进、更优越和追求更大的创新为特征。冷战尤其是在没有战争的年份里持续高昂的军费开支使得一个庞大的武器研发、生产和采购网络正式形成;冷战期间,除去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安全开支占GNP比例的均值达到6.9%,部分财年的联邦军事支出见表1。国防开支对工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赞助和购买昂贵而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上,还体现在庞大的数量上。后者尽管对科技的促进作用可能不如前者显著,但事实上,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生产给国民经济会带来同样深刻的结构性影响。和平期间高昂的国家安全开支和军队扩张迅速增大了经济容量,美国本土工业部门,特别是新技术部门通过这一渠道积累了资本、技术和经验。

表1 冷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7]
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行为形成了主承包商庞大的规模和集中的机构,这一体系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国防合同(含采购和研发)的巨大金额和丰厚利润,与国防部之间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未来的合作,以及国防部一些鼓励科研的制度安排(例如独立科研)等都意味着:大型国防承包商可以超越眼前利益,关注国防部所需要的长远需要。换言之,大型国防承包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短期商业竞争、短期利润回报的压力,持续研发更长远、更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在科研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在政府规划中选择开发哪些技术,这种独立科研活动可以弥补国防部自己制定的计划中的方向性不足(例如遗漏或赶时髦)[8]。但是,有限的国防一级承包商也意味着竞争的不充分,尤其是有限数量的参与者很可能相互之间达成共谋。这些军工承包商在处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与扩散方面,例如军转民副产品、技术共享、新技术开发等,更倾向于在公司(集团)内部进行[8]。
半导体市场是被美国军事需求所培育出来的,冷战是该产业初期的主要促进力量。尽管晶体管可以用于制造便携的收听和无线设备,但是美国早期民用商业市场已经被固定设备所垄断,可移动收听和无线设备在价格上并不具备优势,因为缺乏挑战固定设备的市场竞争力。由于晶体管在军事领域展示了它的技术潜力,因而得到了公共科研和采购订单的支持。公共部门在技术开发和改建方面的投入见表2所列。政府采购确保了生产企业可以获得利润,技术得以产品化并获得进一步改进的机会。在半导体产业,大公司的研发产生了新的发现或技术,而商业利润则大部分由技术发明者通过孵化(spin-off)新公司获得。新公司得以生存,更多是依靠公共部门的订单。以1959年为例,新进入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半导体销量的63%,其中的69%卖给了军队。据统计,1955-1958年,政府采购占了半导体产量的36%~39%。1959-196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5%~48%。Mowery认为“如果没有这些间接的研究经费资助,美国企业有可能以与日本和欧洲公司相同的速度来开发晶体管技术”。

表2 美国政府1955-1961年用于半导体产品研发及产品改善方面的直接开支(估计)[5] 百万美元
(三)冷战后期至今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在这一时期,冷战带来的国家直接介入科学和国防开支的合法性消退;来自西欧和日本的国际竞争压力显著,高昂的国防相关开支在持续的赤字政策之后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导致美国政府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的具体策略产生了进一步调整。更具体地说,国家依然是知识的重要生产者之一,并且从知识的生产阶段就着力于未来的应用;同时,国家重点调整了促进知识产业化应用的政策和制度,包括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以及技术商业化的金融支持计划。
私人部门是这一时期研发投入的主体,政府依然在知识产出上发挥重要作用。国防部先进技术研究局(DARPA)和国家卫生研究院(HIS)依然是新产品的主要技术来源;例如75%新分子聚合物(NMEs)药物技术来源是NIH[9],而被视为主要创新产品的苹果公司iphone移动电话,其硬盘、集成电路、多点触屏等技术都可以追溯政府资助性起源[9]。DARPA的主要制度特征在这一阶段日趋成熟,并成为公共部门仿效的对象。它延续了冷战时期对分散的、更先进的技术和spin-off孵化小型企业进行支持传统,通过任务导向型的平行技术路线[10]设计充分调动了多主体(个人、大学、科研机构、科研团队)加入知识创造。Mazzucato认为DARPA的制度设计有效规避了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由于数量限制而达成的对不确定性的集体逃避机制[9]。
美国在这一阶段对商业化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不同于战争期间的直接管理和组织,也不同于冷战期间对国防铁三角的重视;国家促进技术商业化应用的重点转为促进对已有知识存量的商业化应用;致力于在知识生产与商业化应用之间建立中间连接制度。以拜杜法案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是这一时期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变迁的政策反应,主要政策包括Stevenson-Wydler技术创新法案(1980)、Bayh-Dole大学与中小企业专利法案(1980)、国家合作研究法(1984,1993)、联邦技术转移法(1986)等。20世纪80年代主要促进商业化应用和知识存量扩张的联邦层面立法见表3。

表3 美国政府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的主要立法
在政府支持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本文以DARPA和SBIR为例论述美国政府是如何促进技术的商业化应用。DARPA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对科研团队的支持超越了研发支持的范畴,因为机构的根本目的就是产生可用性技术,所以将资助扩张到可进行商业化阶段[11]。SBIR是美国政府开始于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SBI),该计划规定联邦政府将年度科研预算的1.25%用于小型营利性企业。该项目对初创期风险较大的中小型科研创新企业的资助超过风险资本。尽管风险资本在美国高科技市场的建立方面被认为成效显著,但是风险资本事实上很少出现在商业计划的开始阶段,因为早期的技术和经济风险都更高[12]。此外,风险资本倾向于投资增长潜力、技术复杂度和资本密集度都更低的领域,例如零售业;虽然从制度设计上,风险资本的投资期为十年,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大多集中于3~5年期商业计划。
三、结 论
随着政策和理论界对国家、市场及其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市场双失灵理论发展日臻成熟,政府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应该介入市场引发了越来越深刻的讨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是,当政府与市场投入并非完全替代效应时,且竞争性、外部性和固定高成本存在时;政府的介入一般被认为是必须的。引入非完全替代效应后,政府投入(G)与私人投入(P)可能存在技术溢出,即社会总生产函数被改写为Y=f(P(G),G)。这一公式的变形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宏观经济模型,其经济和政策含义在于:如果公共投资(G)有正外部性,即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正溢出效应,那么公共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影响包括两部分:第一,公共投资导致的经济直接增长部分;第二,公共投资导致私人投资的回报上升,即其溢出部分。这就意味着,政府投入并非是简单的私人投入的补充或修正失灵,而是有从本质上改变私人投资生产函数的可能性。本文所分析的正是这种溢出效应的一个典型可能性,更具体地讲,本文从知识创造和知识商业化应用两个维度分析了国家是如何从无到有缔造一个全新的产业市场的。国家通过投入科研导致了新知识的产生,从而增加了这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同时,国家又直接或间接促进这种知识的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创造了可以被商业化推广的产品。库兹涅茨在经济长周期分析中,认为这种新产品及其所代表的产业市场开创了“工业新时代(new era)”,国家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个开创新产业市场的角色。
注 释
①例如20世纪70年代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于市场和政府作为两种基本经济选择的分歧:加尔布雷斯认为,为了应对经济体的根本不确定性,制造经济稳定,政府政策干预是必须的;弗里德曼则以理想化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认为微观经济个体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将达到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随着东亚新兴工业体经济尤其是日本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关于政府知否直接应用政策工具(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介入经济增长成为讨论的焦点,例如Kruger与Westphal的讨论。
[1]BARDHAN P.Symposium o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0(4):3-7.
[2]WOLF C.Markets or govern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
[3] KUZNETS S.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their nature and their bearing upon cyclical fluctuations[M].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30.
[4]STOKES D E.Pasteur's quadrant: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
[5]MOWERY D C,NELSON R R.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studies of seven industr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6] WANG Z.In Sputnik's Shadow: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8.
[7]恩格尔曼 ,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20世纪[M].蔡挺,张林,李雅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亚历克.美国21世纪科技政策[M].华宏勋,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
[9]MAZZUCATO M.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private sector myths[M].London:Anthem Press,2013.
[10]贝尔菲奥尔.疯狂科学家大本营:世界顶尖科研机构的创新秘密[M].本书翻译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1]BLOCK F.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J].Politics&Society,2008,36:169-206.
[12]PIERRAKIS Y.Venture Capital:Now and after the Dotcom Crash[R].NESTA research report,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