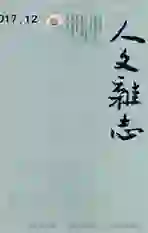中国文化中的“工具理性”
2018-03-13张再林
张再林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发端于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工具理性”的观点,一直不失为中国文化解读中的主导性观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长于“价值理性”,而且在“工具理性”方面亦不逊于西人。这一点,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哲学思想之中,从《周易》的“利用安身”到荀子的“善假于物”,再到王夫之的“天下唯器”即其显证;另一方面它还在中国历史中得以生动地运用,无论是汉唐高度的科技器物文明,还是汉唐发达的思想文化文明都无一不是其说明。认识到这种中国传统的“工具理性”精神,既是对中国文化面貌的真实还原,又可借助于我们自身的思想资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提供明确的路引。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 工具理性 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07—11
一、缘起:中国文化中之“工具理性缺乏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祛魅”合理化的历史。进而,当他对这种合理化的“理性”进行深入思考时,从中又为我们分梳出最主要的两种“理性”类型,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于这两种“理性”,他是这样定义的:
其一,就“工具理性”而言,“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
其二,就“价值理性”而言,“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
易言之,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一种把我们的目标、手段和与之相伴的后果一起合理性地加以考虑和估量的理性。而所谓“价值理性”,就是一种只重视我们行为本身内在的价值意义,而对其能否兑现和成败得失不予考虑的理性。
虽然韦伯认为这两种理性各有利弊、互有所补,但两相比较,韦伯心目中更为重视的却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他认为就合理性程度而言,前者在位阶上更优越于后者。这不仅由于“工具理性”以其目标和手段的双重性、以其对手段的可计算性、以其后果的可预测性、以其价值的中立性,而与人类理性之为理性的性质更为相符,代表了一种更为精致和更高层次的人类理性精神;而且还由于“工具理性”上述种种意蕴同时又与高标实证科学、工业技术、资本增殖的“现代化”精神深深相契,而体现了人类合理化运动的最新的历史趋势。相反,“价值理性”虽对行为的价值意义给予反思,却未能彻底摆脱激情、信仰等非理性的孑遗,而只能在理性化的程度上退处其次。
其实,在韦伯的学说里,他的这种理性观中的“工具理性优先论”与其文明观中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二者是携手而行、并行不悖的。因此,当他从理性比较转向文明比较考查时,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工具理性缺乏论”就成为韦伯学说的应有之论。
在韦伯看来,这种工具理性的缺乏是如此的明显,以致于它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韦伯研究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作——《儒教与道教》一书里,他就为我们揭示出了这种缺乏的种种面相,如,“自然科学思维之欠缺”“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礼的中心概念”“对专家的排斥”“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没有理性的技艺训练”“摆脱了所有竞争”。再如,中国古人虽并不反对对财富的追求,但是“在中国的经济里,未出现理性的客观化倾向”,“(司马迁)把经商看做营利的手段并加以推荐,却让儒教徒感到有失体统”,“在中国,真正的‘社团并不存在(尤其是在城市里),因为没有纯粹以经营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化形式与经济企业形式”。凡此种种,使中西的历史发展呈现出迥然异趣的格局:当西方基于“理性地变革与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及工具人”,为自己推出了资本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之际,“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对于韦伯来说,究其故端,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缺乏实际上源于其文化中“价值理性”的唯一、至上。故韦伯写道,在中国,“名声就是一切,美德是‘目的本身”。并且,他认为,正是这种旨在价值性的“目的本身”的美德的追求,才导致了儒家所谓的“君子不器”的人生理想:“‘君子不器这个根本原理告诉我们,君子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作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这种建立在全才基础上的‘美德,即自我完善,比起通过片面化知识(Vereinseitigung)所获得的财富要来的崇高。即使是处于最有影响地位的人,若不具备来源于教育的这种美德,在世上便会一事无成。因此,‘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这种美德而非营利”。这样,在韦伯看来,作为工具理性必然产物的西方的“专家至上”思想就理所当然地在儒家眼里失去了市场:“在儒教徒看来,专家尽管具有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但是无法具有真正正面的尊严。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有教养的人(君子),而不是‘工具,也就是说,在适应现世的自我完善之中,君子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实现某种客观目的的手段。儒教伦理的这一核心原则,拒斥了行业的专门化、现代的专家官僚体制与专业的训练,尤其是拒斥了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
因此,尽管韦伯在其论著中并没有明确从两种理性出发对比中西文化,尽管韦伯在其论著中似乎并没有对中国文化断然给出“工具理性缺乏”的结论,但如上所述,在韦伯的观点里,其显然把中国文化完全纳入“价值理性”的类型,并且中国文化以其扬此而抑彼,显然被韦伯逐出了“工具理性”的文化阵营,乃至可以說,它与其说是“工具理性”的缺失,不如说是与“工具理性”格格不入,而不啻成为“工具理性”的对立面的典型,以一种难得的“反例”,为我们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工具理性”何以是一种更为优越的人类合理性。
耐人寻思的是,无独有偶,这种对中国文化中的“工具理性”的无视,不仅体现在西人韦伯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解读里,也在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解读中难以幸免地得以反映,尽管较之韦伯,后者更多地是立足于对中国文化维护和讴歌的立场之上。endprint
为此,就不能不涉及到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的阐释和解读,一种被很多人视为是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的最具专业性、也最为权威性的阐释和解读。在笔者看来,该阐释和解读所体现的对中国文化之“工具理性”的无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宗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的阐释和解读,实际上仅仅是从力宗“易简工夫”的陆王心学出发的,是以这种陆王心学为中国哲学代表的。而陆王心学就其对“直指本心”“自性圆满”“当下顿悟”“只好恶就尽了是非”等等的强调,显然其学说实质是非工具理性的、反工具理性的,并且显然区别于强调“格致工夫”的工具主义的程朱理学。而对于宗三先生而言,如果说这种非工具理性的陆王心学乃中国哲学的正统、正宗的话,那么,工具理性的程朱理学则由于被其冠之以“别子为宗”,作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歧出”“异数”而被其彻底打人中国哲学的冷宫。
2.经由宗三先生阐释和解读的产物的“新儒学”,其最核心性的概念是所谓的“智的直觉”。直觉者,直接把握者也,不假中介者也。显然,这种“智的直觉”不仅与张载的“德性之知”、阳明的“致良知”、熊十力的“性智”这些直悟型的概念可谓同趣,也从中再次凸显了宗三先生“新儒学”的非工具主义的特色。故正是从这种“智的直觉”出发,他视中西哲学判然有别,体用殊绝。也即他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代表的康德哲学最根本的区别恰恰在于,人是否有这种“智的直觉”,更确切地说,是否有一种对道德本体的直觉。由此就导致了其认为正是以其有才使中国哲学最终走向了“道德形上学”,而正是以其无则使康德哲学仅仅流于“道德的神学”。“道德形上学”对道德本体的把握是“逆觉体证”,是“明觉活动之自知自证”,与之不同,“道德神学”对道德本体的把握则是借助于“神”“上帝”的預设而假道而成。
3.宗三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完全是将之泛道德化、泛价值化。这不仅表现为其将“心体”“性体”视为天或宇宙的实体,还表现为其继阳明思想的余绪,坚持所谓的“意之所在便是物”,甚至完全否认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主张“物自体”不过是一个“有价值意味的概念”而已,并随之也使“物交而知”的“见闻之知”淡出了其哲学的视域。这一切,正应了牟氏所谓的“以道德为人路,渗透至宇宙论,来适应道德形上学”的思路和思理。
4.固然,在其学说中,宗三先生亦积极强调和隆重祭出了德福相即的“圆善”概念,似乎想藉此在他的哲学中为祸福得失留有一席之地,并试图最终为消解康德哲学中冥顽不化的德性与功利二者之间背反的二律。但同时他又称:“同一世间一切事,概括之亦可说同一心意知物之事,若念念执着,即是人欲……。若能通化自在,以其情应万物而无情,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则即是天理。……顺理而迹本圆即是天地之化……不顺理,则人欲横流,迹本交丧,人间便成地狱。顺理不顺理只在转手间耳”。正如这一表述所示,这种德福相即的“圆善”,只是“一心开二门”所致,只是心意态度的“一念之差”所致,以其突出的“境界论”而非“实践论”“实行论”,使其自身依然打上了鲜明的唯心主义、唯价值主义的印记。
5.这种唯心主义、唯价值主义与牟氏所谓的“内圣外王”的哲学理想不无抵牾。于是,如何从道德形而上的“心体”开出现代科技制度文明的“物理”,就成为牟氏将儒学现代化而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所谓的“良知坎陷说”就在其学说中不可避免地被推出了。此处的“坎陷”取自《易传》,宗三先生对之给出的英文是self-negation,它不过是黑格尔“自我否定”概念的中国版。牟氏认为那种天人合一的“天心”惟有经过“自我坎陷”才能成为与物相对而二的“了别心”,从而与道德“良知”迥异的“知识”“技术”之维也才能在中国哲学中得以确立。然而,同时他又讲:“坎陷其自己而为别以从物,从物始能知物,知物始能宰物。及其可以宰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不难看出,这里所表述的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通过“否定之否定”而最终依然回归自身的逻辑可谓异曲而同工。这无疑表明,牟氏的“良知自我坎陷”之说与其说旨在使自己的“新儒学”学说中先天缺乏的“工具理性”得以开显,不如说就其最终归宿而言,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化与回归走着同一条道路那样,牟氏的这种开显充其量不过是为至尊的“价值理性”作嫁衣裳,充其量不过是以一种貌合神离的“中体西用”的方式,仅仅是使更加本位的“价值理性”得以真正付诸实现的一种手段,并且也是继韦伯之后,为中国文化的“工具理性缺乏论”再次作出了一种中国式的理论论证和思想申辩。
因此,从马克斯·韦伯到牟宗三,在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解读里,都有一种思想一以贯之地贯彻其中,那就是,他们都坚持如果说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工具理性”出发的文化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以“价值理性”为本为宗,并且顾此失彼地使自身患有一种“工具理性”的“先天缺乏症”。我们看到,这种观点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致于它不仅众口铄金地几乎成为学界一致的共识,而且还令学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中衍生出形形色色、不胜枚举的各种现代新儒家理论论著。然而,上世纪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这些以“君子不器”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地区、国度在器物文明上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巨大进步,不能不使这种不无风靡的“工具理性缺乏论”的观点备受质疑,也不能不使人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工具理性”精神的发掘列入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议题。下面,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的、深入的探索将使我们发现,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文化不惟不缺乏“工具理性”,而且正是这种“工具理性”为我们支撑着悠久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
二、中国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思想
就“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方式的关系,韦伯曾写道:“仅仅以这些方式中的其中之一作为取向,这样的具体行动,尤其是社会行动,恐怕是极为罕见的”,例如,“完全为了理性地达到目的而与基本的价值观无涉,这样的行动取向实际上也并不多见”。在这里,韦伯为我们指出,虽然我们可以在思想上抽绎出两种截然异趣的理性,但在现实中,这两种理性却是互相依存的、缺一不可的。他所力推的西方“新教伦理”恰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新教伦理”既以其强调特定工具的实践而为“工具理性”,又以其崇尚普适价值的信仰而为“价值理性”。西方文化是如此,中国文化也不例外。正如西方文化对“工具理性”的崇尚并不意味着其完全无视“价值理性”一样,中国文化对“价值理性”的青睐亦并不意味着其在“工具理性”上留有空白。endprint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不妨从中国文化中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即中国哲学思想谈起。而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周易》思想(尤其对“经”作出解读的《易传》思想),无疑可视之为中国古代“工具理性”得以滥觞的真正的发祥之地。
一旦进入《周易》的思想领地,我们就会发现,与那种奢谈“尽心知天”的后儒不同,《周易》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利用安身”。所谓“利用安身”,是指用什么方式趋利避害,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故和耻于言利的后世儒学形成鲜明对比,《周易》是这样的“唯利是图”,以致于其提出“利见大人”“利涉大川”“变动以利言”“利用为大作”“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把对“利”的诉诸无疑推向了极致。又,关于“利”,《说文解字》日:“利,锸也,从刀”。“利”即作为农具的锯。故段玉裁注:“铦者,臿属。引申为锸利字,锸利引申为凡利害之利”。
既然“利”的原型乃“锯”这一工具,那么,这必然使《周易》从“利用安身”走向了“尚象制器”。故《周易》不仅明确提出“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也即认为人类一切制作工具的活动实际上都取法于《周易》的卦象,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一一列举了何器取法于何象,如“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取法“涣”,“服牛乘马,利重致远”取法“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取法“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取法“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取法“睽”,如此等等(以上见《系辞下》)。更有甚者,除此之外,《周易》还明确地把这种“尚象制器”的创举归功于诸如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古之圣人与后世圣人,如包牺氏取法“离”而为我们制造了以佃以渔的网罟,神农氏取法“益”而为我们制造了耜和耒,黄帝、尧、舜取法“乾”“坤”而为我们制造了上衣下裳。在这些无稽可考的传说里,如果说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新工具的发明如何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则更多看到的是《周易》的“圣人观”乃如何迥异于后人。也就是说,在这里,圣人之为圣人,已不在于他们是垂范千古的道德楷模、至高无上的道德象征,而在于他们恰恰是人们借以利用安身的生产、生活工具的伟大的创造者和发明人。
值得一提的是,《周易》的这种“工具理性”思想并非孤明独发,而是在先秦之际以其此起彼应,而形成多家合鸣之势。其中,墨子就其提出“本、原、用”的三表法(《墨子·非命上》),提出“合其志功”(《墨子·鲁问》),提出“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提出“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墨子·小取》),而为我们推出了中国古代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韩非子就其提出“世无自善之民”,提出“参伍以验”“审合刑名”以及“抱法处势”,而为我们推出了中国古代的工具主义的政治学。庄子则就其提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而为我们推出了中国古代的工具主义的语言学。在此,庄子的这种工具主义的语言学尤其值得人们关注。因为它不仅使后来的王弼“尽扫象数”,反对“任名以号物”,而实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的崇尚人格自由、独立之风,还使后世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不涉言诠”“不执义解”,把一切经典学说都“方便为究竟”地视作为我所需、拿来主义的“方便法门”,并标志着一种“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的中国古代解释学的真正奠定。
其实,在先秦诸子中,使《周易》的“工具理性”精神最能得以理论阐发和发明光大的,则首推荀子。正是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这种天人二分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是如此的重要,它使得中国古人告别了“天人合一”的原始的冥契主义,从而使一种“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在而异己的自然世界真正得以确立。这样,对于荀子来说,要使该异己的自然世界成为为我的自然世界,一种人为的“制之”“用之”“使之”“化之”的活动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也即荀子认为,与其“慕其在天者”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尽其在己”而利用天为人服务。这样,在荀子学说中,就把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问题正式地提到议事日程。
在荀子那里,一方面,这种手段是我们认识自然世界的手段。它不仅包括“缘天官”地借助我们感觉器官产生感性的认识,还包括通过“天君”的“心”对各种“不相能”的感觉材料的综合、分析、选择、权衡,使我们的认识逐渐由直觉的感性过渡到思维的知性,最终上升为“名”“辞”“辨说”等等知识形式。另一方面,对于荀子来说这种手段又是指我们支配自然世界的手段。也即在认识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以实现人自身的目的。故荀子雄论涛涛地写道:“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通过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荀子毋宁说为我们发布了中国“工具主义”思想的最早宣言,它比起那种西人所谓的“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之说的推出,时间上几乎提前了两千多年!
人们看到,正是从这种自觉而明确的“工具主义”思想出发,才使荀子不同于鼓倡“生而知之”“良知良能”的儒学,积极强调后天“学习”的不可或缺,而实开儒家的“工夫论”思想之先河;正是从这种自觉而明确的“工具主义”思想出发,才使荀子告别了儒家沉迷于“血缘化”“氏族化”的社会情结,走上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明分使群”的社会组织学说,而与韦伯所力推的社会分工思想不谋而合;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自觉而明确的“工具主义”思想出发,才使荀子虽置身于儒家的“道之以德”的喧哗声中,却不无清醒地认识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实现了儒家从“内圣”向“外王”的历史性转折,并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所谓“制度儒学”的奠基者。endprint
不无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为荀子在理论上所集大成的这种“工具理性”思想,不仅长期以来未受人们重视,反而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呈被边缘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后古的宋明新儒学的异军突起被推向了极致。也就是说,尽管宋明新儒学中的“理学”以其“格物致知”“涵养省察”的工夫强调,为我们体现了一定的“工具理性”的取向,但就总体上而言,无论是该新儒学的“心学”也罢,还是“理学”也罢,其都旨在服务于、归宿于一种价值性的“德性之知”。这种“德性之知”也即王阳明的“致良知”的“良知”,在王阳明那里,这种“良知”乃取自孟子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它是自性圆满、本自具足和不假他求的,他使我們“见父自然知孝,见弟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于井必然知恻隐”。故“良知”的祭出,不仅意味着宋明新儒学之“抑孟而抑荀”,同时也标志着为荀子所高扬的“工具理性”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最终退隐。
然而,物极必返,在中国思想史上,随后的一种“后理学”思潮的出现,作为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却使这种业已隐而不彰的“工具理性”得以再度的彰显和弘扬。
就“后理学”思潮对“工具理性”的提撕而言,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无疑为我们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为了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从与《周易》的“利用安身”可以互发的王艮的“明哲保身”的命题谈起。也就是说,与宋明新儒学不同,不是“心性”的“心”而是“身体”的“身”被移步换景为王艮的“后理学”学说的中心。故王艮宣称“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宣称“身与道原是一体。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而一旦“身”被提升到本体的“道”的高度,那么,这意味着人类的最高使命已不再是致力于“心思”的发明,而是致力于身体生命的爱护、保存。故王艮提出“爱身如宝”,提出“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随之一道的是,为宋明新儒学所无视的人生理的欲望、需要、利益等等东西被泰州学派再一次得以肯定。从颜钧的“制欲非体仁”到何心隐的“心不能以无欲”,从罗汝芳的“嗜欲岂出天机外”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都无一不是其佐证。
这样,王艮的一种“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就顺理成章并大张旗鼓地被推出了。乃至他宣称“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宣称“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这里的“百姓日用”,即诸如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这些满足人的日常生理需求的活动。对于王艮来说,这些活动不惟不像“理欲之辨”的道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实现“道”的羁绊,反而恰恰是“道”自身的直接体现。于是,这不仅意味着至尊的“道”从天上降尊纡贵地世俗化至人间,而且使“道”从理想的“体”转为实际的“用”,从而使发端于《周易》中的沉睡千年的中国实用性的“工具理性”精神再次得以觉振和唤醒,并且是富含新的历史因子的觉振和唤醒。以致于可以说,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既是明清之际破土而出的社会工商阶层利益的代言者,又可视为是中国近代涛声阵阵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先声之鸣。
此外,谈到“后理学”的“工具理性”,明清之季著名思想家方以智的理论贡献值得一提。如果说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的伦理上的话,那么,方以智的“工具理性”则主要见之于中国文化的认知领域。而他的与培根的归纳法相媲美的“质测之学”的推出即其显例。关于“质测”,方以智谓“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会元,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这里所谓的“物有其故,实考究之”,是指对物的所以然“以实事征实理”。而这里“以实事征实理”的第一步“类其性情”即将众多的事物归类排比,以找出相通一致之处。其与培根归纳的“三表法”第一表的“具有法”(把具有所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列在一起)极其相吻;这里“以实事征实理”的第二步的“征其好恶”即将类比得出的结论再从好坏两个方面加以比照验证,其与培根归纳的“三表法”的第二表的“差异表”(列举出与上表中的例证情形近似,却没有出现所要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不无类似;这里“以实事征实理”的第三步的“推其常变”即将比照所得结论再次类推,以窥其在不同条件下的适应程度,其与培根的归纳的“三表法”第三表的“程度表”(列举出按不同程度出现的所要考察的某些性质的一些例证)庶几近之。
因此,不难看出,虽然中西天各一方,但方以智与培根这两位生活在历史几乎同时期的人的思想却可以心有灵犀地遥相呼应。他们都从传统的“空空穷理”走向了“物性确证”,他们的“实证类比”与“经验归纳”不仅根本精神相契,而且实际步骤亦不可思议地所见略同。无怪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列“方以智”为首出,并对其学术论著给予极高的评述。故当人们把培根目为人类知识“新工具”的奠基者之际,请不要忘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还有方以智以同样贡献可与之并肩而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西方人从培根的“新工具”思想出发,在科学的道路上扬鞭策马、一日千里,而不无遗憾的,方以智的“新工具”思想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在清人之于“理学”的固步自封和乐此不疲中夭折于摇篮里。
谈方以智就不能不谈到王夫之。这不仅由于王夫之是对方氏的“质测之学”给予高度认可的同时代之人,更由于王夫之以其“惟器主义”思想的推出,和方以智一样,使“后理学”的“工具理性”思想得以更为有力的揭示。
众所周知,以其与宋明理学的“心性”学说迥异,王夫之的学说被人视为是一种“唯物主义”。但是,王夫之心目中的“物”并非“自在之物”意义上的“物”,而是如他“以我为人乃有物”所说的,乃是“为我之物”意义上的“物”,也即在人的身行实践中不仅“与其事”且“亲用之”的“用具”之物。这种“用具”之物,按中国古人的说法,也即所谓的“器”。在《说文》中,“器”者“皿”也,而“皿”作为象形字,取象于“饭食之用器也”。其“用具”之义已表露无遗。不难看出,王夫之的这种“物”即“器”的思想完全可以与海德格尔的“物”的理解互为发明,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他亦把“物”目为一种“应手”(ready-at-hand)中的“傢伙”,也即一种缘人而在并呈现出一定合目的性的“用具”,以致于森林乃是一片林场,山是采石场,河流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endprint
因此,正是从这种以“器”训“物”的唯器主义思想出发,才使王夫之把“物”的世界完全等同于“器”的世界,故他提出“天下唯器而已矣”,提出“盈天地之间皆器矣”,而这“物世界”向“器世界”的转移,虽是一字之易,却对中国哲学变革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版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用具形而上学”的真正开启。正是从这种以“器”训“物”的唯器主义思想出发,才使王夫之一反“理学”的“道本器末”的观点,而坚持“道以器丽”“器体道用”的一种全新的主张,故他宣称“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宣称“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乐而无礼乐之道”,在王夫之的笔下,君临万物、至高无上的“道”不过是君子不屑为之的“器”的功能功用、“器”的人所鄙之的“奇技淫巧”。同时,也正是从这种以“器”训“物”的唯器主义思想出发,才使王夫之面对后儒的“一先生之言”“六经之绪说”的道的株守,强调“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而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也即强调“道因时而万殊”,从中不仅使一种中国式的“进步”的理念得以开显,也破天荒地在中国思想与工具进步决定历史进步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
显而易见,这种对“器”的前所未有的推举,既是对宋明新儒的“轻器”思想的奋起矫之,又是对《周易》的“重器”思想的再次重启。中国哲学的“工具理性”思想经此否定之否定,在王夫之的学说中已被趋至登峰造极,并由是也标志着它与中国哲学的“价值理性”一起,而真正成为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乃至即使在现代中国,它也由于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使自身始终葆有着勃勃的生机。从民国时期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问题意识,到改革开放时期“白猫黑猫论”的实验、实用取向,不正是我们民族为这种“工具理性”所谱写出的时代新曲,不正可视为是这种“工具理性”绵永不绝的传统的重继和再续吗?
三、“工具理性”在中国历史中的体现
如果说“价值理性”以其“纯思”而使自身往往流于坐而论道的话,那么,“工具理性”则以其“实践”而使自身与我们实际的生活相勾连。这使我们对“工具理性”的考查必然从思想史落实到人类生活的现实史。换言之,唯有从实际的历史出发,才能使“工具理性”的存在得到真正的检验。
一旦步入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不仅以其精神文明为人所称颂,同时亦以其“工具文明”而著称于世。在这方面,除了产生了举世公认的“四大科技发明”外,还有诸如万里长城、秦直道、丝绸之路、大运河、都江堰等令人叹为观止的工程一个个在中华大地接踵而出。它们作为一座座巍峨而无字的历史丰碑,不仅象征着中华民族征服自然的豐功伟业,也从中使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工具理性”精神得以直接生动并不言而喻的注解,并且亦是征诸史实地对所谓中国文化“工具理性缺乏论”的当头棒喝!
同时,一旦步入中国的历史,我们还会发现,但凡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都与“工具理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都使“工具理性”在自己的时代中得以空前地彰显。而中国历史中“辉煌的汉唐”恰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以汉代为例,汉之所以享国四百余年,之所以与同时期罗马帝国并列为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强大帝国,正是得益于“工具理性”之助。正是基于这种“工具理性”,才使汉人无论是在器物文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巨大进步。
首先,在器物文明上,汉人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除了蔡伦的造纸术被列入世界“四大发明”外,我们还看到了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测知地震的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的《太初历》,《九章算术》的推出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显著标注,张仲景的《伤寒论》、华佗的麻醉术使中国医学迈向新的黄金时期,铁、铜的冶炼技术不断提升已今非昔比,水能机械的发明代表着水能利用取得了根本性进步。与此同时,陶瓷开始出现,水利工程业已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汉人已懂得利用凸透镜来聚光取火,用各种仪器以“观乎天文”,食盐的生产和运输日趋繁荣,铸币业开始步入了鼎盛,农耕技术的不断改善有力地推进了农业文明,丝绸纺织技术亦愈来愈精益求精,由此才有了马王堆汉墓里的“薄如蚕翼”的纱衣的出土,以及丝绸业已作为中华高度的物质文明象征,和向世界输出这种物质文明的“丝绸之路”的在汉代的开通。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汉代发达的器物文明的显证。而这种令人目不暇接的器物文明,不正告诉我们,在经历了“天下苦秦久矣”之后的汉人,如何如梦初醒地使自身重新皈依于中国“利用厚生”的传统,并为自己时代打下了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烙印吗?
其实,这种“工具理性”精神同样也体现在汉代的思想文化上,也就是说,虽然汉代以好古尊经著称于世,虽然中国思想文化的“大一统”格局恰恰在汉代正式确立,但实际情况却是,汉人并没有由此走向不无教条的原教旨主义,而是以无比清醒的实事求是、因时制宜的意识,使自己成为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的思想文化的先驱,而让自己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
本被排除在“六经”之外的黄老思想在汉初的大放异彩、备受礼遇适足以为例。针对秦代的“政苛刑惨”“赋敛重数”的历史教训,并直面多年战争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历史境遇,汉高祖刘邦登基后,任萧何为丞相,采取旨在与民消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惠帝二年,萧何死,曹参为汉相国,萧规曹随,继续沿用刘邦所推行的“黄老之术”,其“治道贵清静,而民自立”,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推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于房户,天下晏然”“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人们看到,正是基于这种汉初大力推行的“黄老之术”,才有了旨在“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的《淮南鸿烈》这一“新道家”的鸿篇巨著在汉初的正式推出,也才有了作为其现实对应者的汉代的“文景之治”的流芳千古。endprint
即使在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的汉武帝期间,这种汉人所长于的一反教条的“拿来主义”亦未停下自己的步履,反而被日益自觉地臻至运用自如。其表现为,名义上是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左右其手的“王霸杂之”和“儒法互用”。由此就有了《汉书》所谓的董仲舒、公孙弘、兒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的记载,而其中的公孙弘尤得这种“儒法互用”之三昧,以致于深合武帝圣意官至相位。此外,汉人的这种“王霸杂之”和“儒法互用”还可见之于史书的汉元帝纪。纪书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却正色诫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在这些事例中,汉人的思想文化观可谓一览无余,他们与其说更为看重的是思想文化中的所谓“终极价值”,不如说是对思想文化能否“通于世务”、能否“达于时宜”尤为独钟。惟其如此,才使汉人虽“独尊儒术”却未步人“执一而贼道”的误区,虽力纠秦人的“严刑峻法”却仍可“汉承秦制”;惟其如此,才使汉人在看似迥异的儒、法两大思想体系中看到其互补之处,从而在两者的各取所需中使自己成为不无实用的“工具理性”的忠实信徒。
汉唐并称,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乃比汉朝更为强盛,以致于可以说,中国历史惟有步入有唐之际,才为自己迎来了最为灿烂辉煌的黄金期。正如汉代的强盛离不开中国的“工具理性”一样,同理,这种“工具理性”亦可视为唐代走向鼎盛的通衢大道之一。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不妨先从唐代“工具理性”最为直接也最为集中的社会表现形式,即唐代的科技文明谈起。
众所周知,尽管学界一些人对唐代科技文明的水平评价有失公允,乃至出现诸如所谓的“唐代的科技文明与人文文化相形见绌”,所谓的“唐代文学的繁荣是以其科技文明的相对滞后为牺牲”等等议论,但实际情况却是,唐代不仅在人文文化上在中国历史中是独领风骚的,而且在科技文明上在中国历史中亦是一骑绝尘的。这一点表现为,一方面,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推出了堪称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千金方》,中国《金刚经》的印制乃目前世界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另一方面,在其他科技门类,亦取得了令人刮目相视的非凡的成就。如在制瓷业上实现了第二次高温技术的突破,开创了白瓷、彩瓷的生产技术;如在造纸业上新创动物胶施胶与明矾沉淀剂技术;如在水果业上取得嫁接理论的突破性认识及其广泛应用;如在纺织业上设计出人工程序控制的小、大花楼提花机;如在冶炼业上形成钢铁生产技术体系并成为定式而被后世长期沿用;如在农业上创造曲辕犁、制作各种形式的龙骨水车,如此等等。也正是这些不胜枚举的科技创新,为唐代各个行业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宋代的科技文明新的飞跃提供了平台。另外,论及到唐代的科技文明,其科学技术的“建制化”发展亦值得一提。它包括唐代科技启蒙教育、科技实科学校、科技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等等。这既是唐人对于中国科技文明发展的重要创举,也是唐人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科技文明遗产,借以才能使中國古代的科技文明代代相继、薪火相传。也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体现了唐人对于中国科技文明的最为实质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一如汉代,唐代的“工具理性”精神同样也体现在思想文化上。一种为汉人所长于的思想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同样为唐人所拥有,并且较之汉人,其在这方面更胜一筹,显得更运用自如,气象也更为雍容大度。
如果说汉人的“拿来主义”主要直面的是本土思想文化的种种选择的话,那么,随着唐代国门的大开,唐人的“拿来主义”则主要直面的是外来思想文化的应对。对蜂拥而至的外来思想文化,是拒之以千里之外呢,还是择其善者而用之?当置身于这一问题时,唐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职是之故,才有了唐太宗李世民所谓的古今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一气魄博大的话语。职是之故,才使不仅诸如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得以传人中国,而且还有印度天文思想与中国天文思想的结合,而一行和尚的《大衍历》即是这一结合的产物。同时,职是之故,才使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唐都长安城时,触目可见的是一个胡骑、胡服、胡乐、胡舞、胡食、胡姬的世界,从中产生了中国民族器乐中著名的“二胡”“京胡”,还有唐玄宗将中国音乐与印度、波斯的音律合成的《霓裳羽衣曲》这一美不胜收的艺术之作。
佛教的中国化更是这种“拿来主义”的杰出之作。众所周知,自唐以降,源于印度的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被推向鼎盛阶段。唐代不仅“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天下僧民,不可胜数”,而且“传衣钵者其于庾岭,谈法界、阐名相者盛于长安”,佛教已由先前的“格义”即简单介绍解释发展为自觉地创立判教体系、教门林立的阶段。佛的论旨已由“教”正式上升为“学”,思想理论界也由“独尊儒术”的一统局面让位于“儒、释、道”三足鼎立。佛学已取得了几乎执中国思想界之牛耳的地位。这最终导致了中唐儒、佛之间的火并,以及以韩愈为代表的“排佛”运动的诞生。
应该承认,这种“排佛”运动的出现并非偶然。本来,佛学与儒学分属两种格格不入的思想体系。二者不仅思理迥异,而且趣旨殊绝。一为“实学”,一为“空学”;一主“在家”,一主“出家”;一倡“人世”,一倡“出世”;一重“人伦”,一轻“人伦”;一尊“血缘”,一贬“血缘”;一崇“生生”,一崇“寂灭”;一为“主动”,一为“主静”;一宗“乐道”,一宗“苦谛”;一隆“忧患”,一破“烦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归根到底,二者的歧出则可一言以蔽之地归结为“尊身”与“尊心”之分。
与儒学的“尊身”不同,佛学的“尊心”乃勿庸置疑的事实。佛学所谓的“一念三千”“万法唯识”“直指人心”“自心是佛”“一心开二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我们谈论的是“心”;佛学的“觉”是“心”的觉,佛学的“识”是“心”的识,佛学的“慧”是“心”的慧,佛学的“解脱”是“心”的解脱,佛学的“烦恼”是“心”的烦恼,佛学的“寂静”是“心”的寂静,佛学的“圆满”是“心”的圆满;无论是佛学的“观”的“中观”,还是佛学的“行”的“戒定慧”,其都是以“心”为不二法门:“中观”是藉“心”的“唯识观”来扫除偏执和贯通一切,“戒慧定”是我心固有、不假他力的戒慧定,用慧能的表述即“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因此,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一种真正的佛学乃人类最自觉也最彻底的心的学说,而这种“唯心主义”之所以在佛学中成为可能,不仅在于佛土印度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纯思辨性”,还在于当人类试图借助于客观环境的“外缘”改变人生苦难而难以实现之时,不得不使自己的努力重心转向“心”的“内因”。endprint
一旦我们把佛学定位于一种重心、尊心的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这种学说一进入中国就突然成为热门货,就不难理解何以举国上下对这种“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的异端学说表现得是如此的如饥似渴。原因恰恰在于,虽然儒道两家都有关于“心”的表述,实际上原先本土化的我们的文化不过是一种“无心的文化”,原先本土化的我们的民族恰恰是一种“无心的民族”。正是这种“心”的空场,才使我们的民族虽立足于一种“以身体之”的不无世俗化的现实世界,却使一种“心领神会”的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付之阙如。正是这种“心”的空场,才使我们民族虽在“肉身的富有”上作足了功夫,却在灵魂的永恒不朽上三缄其口。同时,也正是这种“心”的空场,才使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虽在形而下实学方面引以为荣,却由于缺乏思想概念的支撑,而在形而上哲学方面远逊于西人。
唐人的伟大,恰恰在于面对这一佛风东渐的千古难逢的历史机遇,非但不将佛学拒之于千里之外,反而是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佛为中用地对其接纳之、吸收之并批判地借鉴之。故有唐一代,对佛学取经者有之,译经者有之,释经者有之,判经者有之,发明者有之,并在此基础上将强调“心”的佛学与强调“身”的儒学最终熔为一炉。其结果就是中国化的佛学的“禅宗”破土而出,还有与这种禅宗并行的,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宋明“心性”新儒学的正式出炉。而这种宋明“心性”新儒学的诞生,以其寓心于身、寓形上于形下、寓超越于内在的从容中道的高明,既标志着儒佛抗衡中的儒学的决定性胜利,又宣告了有别于“外在超越”型的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型的中国哲学的正式奠定,中国哲学正式跻身于世界哲学之林。而思及这一切,我们从中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唐人无比博大的胸襟,与其说是唐人无人能及的“文化自信”,不如说是唐人的那种更为自觉也更为成熟的“拿来主义”式的“工具理性”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为我们所带来的极其丰硕的中国文明。
鉴往而知今,今天的现代中国虽然去唐已远,却也同样面临着唐人所置身的种种思想文化境遇、唐人所直面的种种思想文化课题,甚至是更为严峻的思想文化境遇与课题。例如,今天势如潮涌的新科技主义思潮,尤其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思潮的冲击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智能的迅疾发展乃至高智灵机器人在智慧上战胜人的事实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类已开始对自己可能被一种新的类人的物种取而代之而忧心忡忡,还有中国古老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的人本主义传统也将随之一道地寿终正寝。如果说人工智能思潮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威胁以其猜想尚属杞人忧天的话,那么生物技术思潮则使这种威胁变得更为直接、更为真切。生物技术中的器官移植作为身体组织的欠缺的改良,在向儒家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的“全体”思想挑战的同时,乃是对中国传统的身体生命“自足性”信念的威胁。生物技术中基因改造以其对身体遗传基因重新编码,除了可为新种族主义、新“超人”理论鸣锣开道外,也必然在我们今人与坚持我们身体是父母的“遗体”、坚持重血缘重遗传的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作出了切割。生物技术中的体外生殖,意味着胎儿可以在机房中制造出来,它既是对自然主义上的父母生殖观的无情的推翻,又是之于“乾称父,坤称母”(《西铭》)、“天亲合一”的中国传统的大哉孝道观念的彻底的了断。生物技术中的人类寿命急速延长,表面上看它似乎与中国传统“天地之大德日生”的“重生”“唯生”的思想不无吻合,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老年社会”的诸多麻烦,不仅是随着生命延长人的预期、欲望、情感、能力这些“人性”的恶性膨胀,不仅是家庭结构的突然改变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难以预测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源自“天人合一”观念的“生命之时”思想将面对的巨大的挑战。这种“生命之时”思想决定了,“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丰·彖传》),“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系辞上传》),正如自然事物有消有长、有始有终那样,人类的生命也有生亦有死,故古人谓“大哉死乎”(《荀子·大略》),谓“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从而显而易见的是,现代生物技术那种一味的求生拒死不啻與中国传统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切似乎使中国文化传统正在面临着灭顶之灾。但是,值此之时,我们为什么不想想中国历史的唐代,不想想唐人在面对一种全新而又异己的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姿态。故我们相信,正如唐人在应对传统的挑战时使自己走向一种“工具理性”的拿来主义那样,对这种“工具理性”的重拾也将是我们今人的必然之举。这意味着,如果说,当时的唐人通过“工具理性”的运用,将佛学的挑战变成发展自己的机遇,并借此“援佛于儒”地为中国思想最终迎来宋明新儒学这一新的黄金期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人,也将通过“工具理性”的运用使新生命科技思潮的挑战转化为自身成长的千载难逢之机,并借此“援科于玄”地为自己的“重身”“重生”的古老而深刻的哲思之道再谱历史的新曲。
责任编辑:王晓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