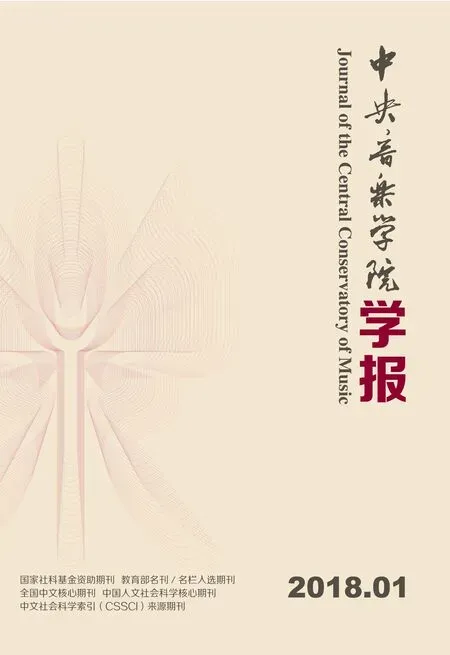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新音乐
2018-03-12塔尔诺波尔斯基
〔俄〕弗·格·塔尔诺波尔斯基 著
彭 程 译
一、先锋派的创伤与历史的讽刺
艺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个美学课题,而且是重大的社会政治学课题之一。对这个话题的任何一种探讨都足以占用几次讲座的时间。我们的意图及其实际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区别,甚至现实本身与我们对它的一些具体呈现之间也会形成差异。首先我们通过这些差异与悖论来看一下艺术与当代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曾将人的努力目标与现实结果之间的不吻合称为“历史的讽刺”。以此为基础去探究经典先锋派时期*作者认为“经典先锋派”的边界并不清晰,但主要指勋伯格、韦伯恩、贝尔格,瓦雷兹、莫索洛夫、罗斯拉维茨及早期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在较大程度上探索音乐语言的作曲家,可以包括诺诺与拉亨曼,但卡赫尔与贝里奥则基本属于后现代主义作曲家;“经典先锋派”作为一个时期也没有与后现代主义更替的准确时间点,但1968年与欧美的“新左派”运动可以看作两者宽泛的“交接”节点——译者根据作者阐述整理。和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在理解自己社会使命时有何等的不同,而社会在建立自身与新艺术之间的关系时又有怎样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
1.在经典先锋派多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各种美学纲领中,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俄罗斯艺术家或者欧洲达达主义者的思想,到德国战后先锋派的观念,将美学现象与政治上的成就直接关联的艺术-政治学评论,无疑在艺术中占据绝对优势。
也可以这样说:从美学效果的角度来评价政治上的决定。经典先锋派不仅关注与自己同时代的观众与听众,也关注某些未来的理想受众。20世纪初甚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流派以这样一个纲领性的词语为自己命名:“未来主义”,即未来的艺术。
所有适宜的先锋派美学都包括对当代社会的批评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经典音乐先锋派类似三段论的美学-政治先锋性纲领可以以阿多诺(Adorno)*本文中俄罗斯人名、苏联人名后保留俄文原文,其他人名后的拉丁字母拼写为译者添加。、诺诺(Nono)及其他杰出代表人物的观点为基础来表述:新音乐培养新的听觉,新的听觉本身又培育新的听众,通过听众(新的个体、新的公民)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公平与人道的社会。
2.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先锋派如此深入地参与社会发展,却遭遇了来自当时社会的极度冷遇。各种难堪始终相伴,从完全不认可到流放艺术家。还有更悲惨的情况,比如在德国与俄罗斯,20世纪第二个25年间先锋派甚至可能会受到肉体上的伤害。
3.今天的情况是何等的不同!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将经典先锋派的遗产根据自己的市场需求成功改写,而且顺利吸收了其革命激情。如今先锋派的观念不仅被正统化了,而且已经走出了博物馆与技术性而深深渗入了我们的生活,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
昨天受迫害的抽象主义者的观念已成为今天窗帘布料设计者想象力的源泉;曾被认为不切实际的建筑设计方案现在躺在声名显赫的商业工作室中;不久前我在莫斯科街头还听到手机铃声发出了路易吉·诺诺《中断的歌曲》中的音高序列。如今先锋派的观念已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实用性的工艺设计,成为一种有效的美丽装饰。
4.今天的艺术经常比经典先锋派更公开地宣告自身的社会-政治学趋向,更激进的艺术家甚至总是把政治的部分放在首位,而根本不顾什么艺术的尊严。
5.后现代社会急切地从现实问题与真实历史中挣脱而进入假象的世界,建立了“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的独特概念。这在俄罗斯甚至得了个专门的名称——“现实性艺术”(акту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使用这个翻译,现在一般统一称为“当代艺术(Современноеискусство)”——译者注。。这一名称本身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传统派”与“经典”先锋派的对立面。这种艺术调整(咀嚼、吸收、改善)了经典先锋派的观念,“卸载”其革命激情,变其为日常生活的商品。在成功地将艺术转化为设计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经典先锋派的思想与原则变为市场的项目。
去掉了那些激进-先锋的、乖谬的因素,“现实性艺术”其实是规矩与“无害”的,因为它只关注自己本身。这种艺术把先锋派的革命能量升华到游戏方式与角色扮演方式的“安全状态”,把早期先锋派的创造力转化为游戏与精美“化妆品”般的轻松形式。
这在具体的方案中得以展现:比如杰出先锋派艺术家的出色创新被当作某种形式的表面点缀、装饰(make up)、化妆品使用在后现代派中。在曾经长期处于某种与世隔绝状态的俄罗斯,有些年轻的作曲家很晚才接触到拉亨曼(Lachenmann)的形态学词典,在完全抛开其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把杰出作曲家的原创发明变成了“公式化的”声音背景,用乐器的噪音音响成功“吓倒”了“俄罗斯村”那些毫无准备的听众。他们在那里扮演了先锋派的开路先锋。
6.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为了照顾这些“角色扮演”*指“现实性艺术”创作并非真正的激进,只是扮演了激进的角色——译者。,建立了专门的“社会文化机器”:一切能够建立的新艺术活动组织(各种双年展、三年展、柏林国际电影节等)。这些活动又建立新的、“被圈起来的”虚拟革命抗议环境,直接渗透到现代文化生活的整个结构中。如今那些高智商的画家与作曲家们如果不去这些活动中例行一下公事是不体面的,就像有时候不去教堂做周日的弥撒。新艺术活动及其组织的各种事件在政府财政预算的有力支持下整体构建了日常文化生活的日程表。它们事实上彻底固化了“现状”并加强了资本的影响力,预先把任何“体系外”的社会观念“翻译”成有市场价值的“复制品”,以此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如何让进行了总体革命并保存了自身资本主义条件的“现实性艺术”进入社会并与社会和平共处呢?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把一切变成商品。艺术在这里毫无例外,今天它被认为是市场的一部分,就像石油或者空运一样。
正如其他任何一种售卖象征性商品*“售卖象征性商品”指利用“象征性消费”(市场营销学术语,与“物质性消费”相对)盈利,如利用消费者风格认同、流行认同等消费心理盈利——译者注。的行业一样,“现实性艺术”的最佳典范是售卖最离奇的、最具丑闻价值的商品,它们吸引眼球的激进的外部特征“自带广告功能”。
在这种特别的市场化环境中,各种各样的新艺术活动自然不仅仅鼓励有激进的外表,还同时直接促进创作。它们是商品的买主和卖主,没有商品,它们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了。艺术活动组织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的一部分,具有社会积极性与人文自由性。
因此,今天西方左派艺术的革命形式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对那些为了新社会的建立与个性化的形成而进行的斗争毫无帮助。与真正有效形成个性的手段相比,这不过是一种假装的革命。
7.宽容对抗偏狭(Intolleranza,诺诺有作品以“偏狭”命名)。今天在西方整个社会与一部分的艺术世界里,借助艺术来完善人、完善社会的思想显然早就失效了。现在时兴的是给任何参与社会的热情打上“早已过时的唐吉珂德精神”的标签。
今天任何一种与通过对人的改造创建“光明未来”的未来主义方案相关的艺术思想,都会被当作隐藏的意识形态问题,被当成一种宣传。有过痛苦历史经验教训的现代人对此长期保有敏感反应。诺诺的偏狭时代过去了,总体包容的时代已经来到。现代社会中建立了自身新的“社会契约”[如果使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术语],其基础是自由价值的绝对优先和对元叙事*后现代主义术语,也称“大叙事”——译者注。总体范围内一切尝试的怀疑:比如科学、宗教、心理学,甚至是历史。
8.自由主义艺术与“革命主义”艺术——“致命的探戈”。自由主义允许任何思想进入自己的圈子,但真正的社会革命观念除外,因为这会消灭自由主义本身。在这一历史语境中,经典先锋派真正革命的社会激情是不合时宜、不需要的。因此,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对抗强大的保守主义时才明确需要先锋-激进主义翅膀的存在,才把它当作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悖论。因为激进先锋派出现本身就是为了破坏传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活动(从权力机构到传统生活方式)。这样的先锋派只能存在于需要它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条件下。俄罗斯与德国20世纪30年代推翻了传统资产阶级的活动组织,似乎实现了先锋派的计划,但历史经验证明了激进-先锋派计划实现的第一个祭品就是先锋派本身。
因此,尽管表面上毫不妥协地对立,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社会与激进先锋派无法失去彼此而独立存在。它们之间达成了秘密的和平共处协议。而在新的社会契约中预先声明了这一共存的独特方式:先锋派把自己的革命火炬替换成烟雾生成器[不要说新维也纳乐派或者瓦雷兹(Varèse),仅将诺诺、拉亨曼、斯帕林格(Spahlinger)与他们在今天的一些中生代继承人相比较就足够了],而自由主义社会将先锋派的革命激情变为纯美学的范畴,为此建立了并在物质上支持新艺术的专业活动组织——新音乐艺术节、现代艺术博物馆、新音乐室内乐团等。
甚至社会赋予了现代艺术真正的王室特权:它把先锋派带出市场的藩篱而直接给予资助。要知道,波普文化或者说是中产阶级文化,与左派政治艺术在西方的区别实际上只存在于政府的资金、不同的基金与赞助计划等方面。有些国家(顺便说一句,指那些不错的国家*作者指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等——译者注。)拥有完整的“激进左派艺术节”产业,用来给先锋派提供对社会保守派作战的错觉。这种情况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斗争的产业完全由这个最保守的社会来直接支持。
当代先锋派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与自身的创伤之一有关。当代先锋派,这一自由主义时代的恐怖小子(infant terrible),就像是莎士比亚的丑角——它既是一个批评家,同时又是这个社会“包养的小三儿”。当代先锋派不仅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革命需求,也更加体会到个体或社会缺失某种实质性变革的外部愿望与机会。
9.对禁忌的美学化。如今先锋派可能已经玩腻了改造社会的思想,但它革新的热情仅在美学领域具有优势。而这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学的”概念正在经历一个严重的变形。
先锋派诸多演进线条中有这样一条非常醒目:之前居于艺术的视野之外的、甚至是那些原则上被排斥的艺术明显成了现实存在的新层面而被美学化。在相近的艺术门类中,杜尚(Duchamp)的“现成”(ready made)项目可以作为明确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送到博物馆的小便池;还有马列维奇(Малевич)与他的《黑色正方形》以及达达主义者的拼贴画(在此列举的是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
在音乐上,这一线条中比较明显的是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与俄罗斯未来主义者们的噪音乐队的思想,瓦雷兹的《电离》与电子乐,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的具体音乐或者拉亨曼的器乐具体音乐,同样还有卡赫尔(Kagel)、凯奇(Cage)、卢西尔(Lucier)等运用大量音响设施与类似体裁的现代作者。所有这些互不相同的作曲家一起测试“艺术”概念本身的强度。如果现在任何客体,甚至任何完全不存在的客体(比如说凯奇的《4′33″》)都可以得到一个艺术作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艺术?艺术的边界在哪里?
10.去找找作者!在现代环境中,艺术活动机构(比如音乐厅、博物馆等)的文化惯性非常强。它们不需要任何艺术家或者阐释者,自己成了艺术的生产者,成了把“废料”再加工为“艺术”的机器。今天所有进入到博物馆、音乐厅的一切都会自动成为“艺术”,甚至即使该事物完全是偶然投入了博物馆或者音乐厅的怀抱(一位流浪汉偶尔信步进入俄罗斯一家展厅,被作为创作者的行为艺术而接受)。
我把这种效果称为“迈达斯国王效应”。如我们所知,迈达斯国王把自己碰到的一切都变成了黄金。现代艺术的博物馆与一些“激进的”新音乐艺术节以此原则为基础构建了一种机制:所有在博物馆里出现的、所有在音乐厅里奏响的甚至没奏响的——都是艺术。以前博物馆与音乐厅扮演着谦虚的角色:艺术的“转播者”,现在作曲家那些依赖音响设备的作品及相近的新体裁使它们成了艺术的生产者。在电子媒体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转换是具有总体性特征的。
11.在大众化与职业化之间。正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Greenberg)在自己的研究中谈到的那样,当代社会不期待作者有独特个性化的原创工作。而且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熟练工与工艺师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艺术家的需求越来越低。对艺术家与作家的实质性需求是让他们干得比自身水平差一点儿。原因很清楚:在只为消费者服务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要拓展消费市场,而不是制造新的艺术。格林伯格这样认识先锋派:这是现代艺术家对美学要求的整体化降低进行抗议。因为之前的时代对艺术家的要求非常高。
非常有趣的是,艺术标准体系本身也随之变化。我想首先关注一个重大的、对我们的时代而言非常典型的矛盾现象: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上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艺术本体固有等级化标准之间的矛盾。只有杰作才能决定艺术本质的发展,而不是那些泛泛之作。艺术上总是有高有低,有大师巨擘,也有平庸之辈。在这个矛盾中又隐藏着另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创伤——艺术的本质(比如先天的独特现象本身就造成等级差别)与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不相适应。
前面谈到的“迈达斯国王效应”可以帮助社会消除这一矛盾。在这里,用自由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看待艺术的思想体系。任何一个客体、任何一个声音现象都可以成为艺术,在这种情况下“好坏”“高低”的准则不存在了。艺术家技能与手艺的问题被忽略并替换为某种实验性“艺术行为”的实际执行本身。艺术家自身似乎也拒绝了作者身份,并将其转让给了冰冷的媒体设备,自己变成那些个人创作容器中的一个。
12.后先锋主义的创伤。后现代主义时代先锋派思想体系、语言、形式的变化中有很多极有意思的观点,这里仅涉及其中几点。可以认为,整个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受到创伤的产物。正如利奥塔指出,这里原则性的变化是社会不仅把当前的一种思想语汇体系变成另外一种,也把一套世界观的观点总和改成另外一种(像我们说的:把神话的改为实验-科学的)。
而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原则性的变化是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对任何整体性人类精神形式都失去了信任。在这一上下文中,后现代主义的实质表现为对已经被丢弃的元叙事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思,不论是齐默尔曼(Zimmermann)、贝里奥(Berio)、施尼特凯(Шнитке)、里姆(Rihm)的风格模拟与引用历史的消亡,还是卡赫尔与戈培尔(Goebbels)的器乐滑稽剧中对情节本身的去除,不论是里盖蒂(Ligeti)、格里塞(Grisey)、米哈伊(Murail)对我们肉体感知能力极限的探究与在这个临界点上进行的游戏,还是在凯奇及其继承者那里“死去”的作者。这种虚幻的丧失感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后现代主义创伤。
二、欧洲音乐先锋派中是否存在“民族的”概念
几年前,歌德学院请我去柏林参加一个与现代艺术中民族性相关的研讨会。邀请函是英文的,我也通过邮箱用英文回了信,表示这个话题我非常感兴趣并且很高兴按计划去参加讨论。研讨会主题是“民族性与新观点——音乐民族性的程度”。当我跟俄罗斯同行说起此事,他们问我:你准备谈论哪个“民族”?要知道在俄罗斯有一百多个民族。我应该谈俄罗斯族、鞑靼族、乌克兰族、高加索民族还是一些欧洲的民族?到柏林参加这个研讨会时发现,研讨会的准确主题是“音乐民族性的程度”。这话用英文来说完全是中性的,可我的德国同行们却产生了关于德国20世纪30年代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负面联想。“民族性”一词在英文、俄文、德文中被填充了不同的意义。这证明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给国际化术语赋予了不同的民族历史负载。这是第一个悖论。
第二个悖论:尽管我们世界的全球化无法被阻止,但今天欧洲各个国家新音乐之间的差异却远比“古老善良的岁月”*《古老善良的岁月》是门泽尔导演的电影,1981年上映。作者在这里借用为一种幽默的表达方式(原文中常见幽默且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大意是指19世纪末之前欧洲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译者。还要大。将今天的情况与正歌剧世界性繁荣的时代相比就很清楚了,甚至与19世纪末浪漫主义顶峰时期相比也很明显:不同国家的作曲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点瓦格纳味道”,因此他们确立的那些创新型音乐语言使得欧洲不同国家的音乐风格比我们现在更加近似。
尽管目前德国内部拥有形形色色的音乐,但它们在整体上与意大利音乐有极大的不同;而现代法国音乐与荷兰音乐也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这里比较的是一些近邻的音乐)。在英国音乐中显现出数量如此众多的不同风格与对立方向,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了它的标志特征。现在不同国家之间音乐的区别比作曲家个人风格之间的区别更大。这是不同文化历史决定的音乐话语(дискурс)的差别。根据我在各种作曲比赛中做评委的经验可以证实,内行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根据匿名总谱的第一页辨别作品的“国籍出身”。当然,这种差别在音乐的实际音响中会更加明显。
我们如此迅速辨别文化地理空间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用什么判断这些使用某“民族学派”(广义)的新语言写成的陌生作品?显然,我们是将新作品与可测定的民族文化话语及其本质特征进行关联。举例来说,不需要成为功力深厚的专家就可以推测出一部最为戏剧性的美国电影也应该会有个喜剧结尾,而即使平静的俄罗斯生活片也难以避免悲剧的净化。对于音乐的内行专家来说就不仅是整体作品了,甚至声音材料本身、音的感受本身、音的处理方法本身都是可以判定这种或那种音乐“出身”的试纸。即使在音乐最初级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根据音乐的构词形态来断定一部作品的文化类型起源。
在此背景下有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先锋派音乐与波普音乐。我们以波普音乐领域最大的欧洲项目“欧洲电视组织的歌曲比赛”为例,这个活动展现了欧洲大陆所有民族文化的极度繁荣与新的多文化景观。比赛以最为民主的原则为基础来组织,接受所有欧洲国家的歌手来参赛,而评委也来自每一个国家,用电话为某一歌曲、歌手与国家投票。但与建立一种新的多文化状态的初衷相反,这一节目的风格与主题事实上单调得令人沮丧。赫赫有名的“多文化自由主义”事业变成了某种(音乐的)“准通用语言”(像语言学中“有条件的英语化”)的绝对霸权,成为理解的“最小公分母”。就是说,成为赤道居民和南极居民都买得起的平等。有时这些民族因素的加入承担的纯粹是粉饰性功能,所有的这些“化妆品”都与任何一种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群众文化的主要标志。
而音乐先锋派要么因为“没有高贵血统的世界主义”而被声讨(我们想想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与俄罗斯),要么自己宣称“高于、后于、出离于”民族艺术。但恰恰是这样的先锋派在自己的个性语言探索中以离奇的方式几乎成了文化中少量残余的民族精神代表者。先锋派用语言宣告自己的原则性创新,宣告自己同民族与历史传统决裂,今天却成为民族与历史传统的主要体现者。我们比较拉莫的和声学著作与格里塞关于音色结构形成的论述就明白,这两个相距两个半世纪的文献是同一种“民族文化话语”的扩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种“话语”可以由格里塞的一部套曲名称来表明:《印象空间》。对我而言,德国音乐中也同样存在一条“贝多芬—拉亨曼”直线,可以用拉亨曼本人的书名《作为生存体验的音乐》来表明。这种例子并不鲜见。
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论述“民族的”这么敏感又危险的玩意必然要小心一点,就像运用核技术一样。今天的民族性并不是从“昨天”来看我们当代,而是从明天来审视我们的整个历史。在当今世界中“民族的”已经不能仅仅理解为与“人种”相关。这种观点或者被新的多文化环境融解,或者进入自我封闭的原教旨主义。“民族的”是天然人种与文化历史在现代层面上的交叉点,是精神特质与新的文化、社会、政治与科技语境的总和。这一认识正好表现出我们文明的主要价值——在全球化多文化的世界上每一个独立个体的个性化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民族性”是“个性”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音乐中的民族独特性如何具体体现呢?在艺术中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并不是用描绘一种地方风光特征或者引用一些民间动机等表面方式来展示。也许民族性首先表现在艺术家如何感受空间与如何表达时间。
我想起一段与此相关的小故事。一位瑞士作家决定写一部真正的列夫·托尔斯泰式俄罗斯风格大部头长篇小说。为此他像俄罗斯作家那样坐上火车出发上路,长时间地看着车窗外一幕一幕流转的风光,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无意义。作家慢慢从旅行箱中取出厚厚的笔记本,写出了自己长篇小说的第一句,然后他再次向窗外望去……等他又拿起笔准备继续写的时候,列车已经停在瑞士边境的终点站了。
这个寓言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地理空间本身可以对文化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庞大的俄罗斯小说也许只能在俄罗斯的极端辽阔中产生,而韦伯恩的小品杰作或许正是受到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鼓舞。
不仅空间的大小范围,一种文化空间内部的组织状况也会对此产生影响。举个例子,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始终没怎么组织好,到现在也是如此,甚至连行政上的边界也只有个大概的轮廓并且经常“游移”;俄罗斯还没建成足够发达的高速公路网,当局在不同区域建立的管理也是不同的;在俄罗斯还有大面积尚未开垦的国土。从这里来看,俄罗斯文化中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空间感受。你永远都可以朝某个方向甚至漫无方向地从世界逃离,可以消失在辽阔的大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广袤的西伯利亚。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空间自己就在那里独立存在着。它不是由物体组建或构成的,而是在高处以形而上的姿态统治着万物,“侵蚀”着万物。空间在俄罗斯文化中与“无限”这一概念对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无底洞。这个不可思议的“黑洞”把一切有形的与明确的东西吸到里面去。甚至时间这样一个与之平等的范畴也常常被无尽的空间吞没,好像转入其中一样[我们想想塔尔科夫斯基(Тарковский)和索库罗夫(Сокуров)的电影]。
作曲家的学派与方向千姿百态。对欧洲整体作曲思维来说最典型的是音乐时间上的清晰观念,作品带有可划分的句法单位。而对俄罗斯音乐来说更典型的时间概念也许是阶梯状不同片段的平等对照*指时间因素(速度、节拍等)在俄罗斯作品中的丰富变化——译者注。(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或者某种类似波浪式的感受。甚至在俄罗斯作曲家的序列主义作品中也极少表现出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尽管对这种技法来说是很典型的特征),而是更多地与其他的思想领域相联系,比如施尼特凯[《很弱》(Pianissimo)中的]不间断的响音性(Сонористически)或者(杰尼索夫《印加的太阳》中的)准偶然主义。
可以以我本人作曲家的工作实践作为补充。尽管我在里曼(Riemann)的格律体系与对新维也纳乐派作品的分析中受到了严格培养,但我认为音乐的时间如同呼吸的过程,像波浪的循环,像日升月落的更替,测量的单位不是一些独立的点或者严格划分的结构学组织(小节),而是一些整体化的曲线。这从我的一些作品名中可以清晰展现:《耗尽时间的呼吸》《他来不及说出的那些话的风》《红移》等等。
我们在时间感受上的区别不仅受到空间感受差异的制约,也来自对历史感受的不同。从我们自身的曲折经历来看,欧洲的历史远比无法预料、杂乱无章的俄罗斯更有秩序性与目的性。俄罗斯不仅常常改变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改变对自身久远历史的看法。俄罗斯人有一个非常棒的笑话:俄罗斯这个国家拥有不可预知的过去。这个过去无论如何也变不成真实的“过去”,它总是带着“今天”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有时候甚至比今天实际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加现实。因此,在俄罗斯艺术中的“历史主义”因素扮演极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传统主义者那里,也体现在俄罗斯先锋主义者那里——从赫列布尼科夫(Хлебников)到索罗金(Сорокин),从斯特拉文斯基到施尼特凯。
我认为,即使在创作行为的本质概念上,也可以从俄罗斯与欧洲的艺术里面找出重要的差别。在欧洲的理解中,创作首先是创立新的构造,创立某种自主的秩序,创立新的宇宙。而俄罗斯作品几乎可以说是以某种“力”的方式,通过神经与被开启的情绪来征服混乱的过程;这是在自然力的浪尖上游戏,充满戏剧性的尝试永远维持在临界状态中。最新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术语“混沌宙(хаосмос)”*后现代主义哲学术语,由混沌(хаос)、宇宙(космос)与渗透(осмос)3个词语错合而成——译者注。对俄罗斯来说早就不新了,可以说是传统的!我想,西方文化不了解这种混沌的整体性挑战。
俄罗斯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对艺术中“约定性”的态度全然不同。一方面,俄罗斯拥有海量传统风格艺术成果,这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得到。所以西方文艺批评界认为当代俄罗斯艺术是约定性非常强的。而另一方面,德国人“未约定的”概念在俄罗斯常被领会为“新约定的”,被教条主义地理解为德国典型形式。看这个例子:如今德国的年轻作曲家使用噪音与乐器的噪音奏法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有趣的是,在德国批评界这些技法自动被归类为“未约定”*意为德国批评界不认为年轻作曲家在创作中使用噪音是必然的、约定俗成的;指批评家会在评论中把这类技法的每一次使用都当成作曲家的创新来看待——译者注。。但德国现代作曲家的新作品出现在俄罗斯的演出海报上时会引来讥讽问句:“什么,又要‘嗤嗤’吗?”这表明对俄罗斯听众来说,如今德国人的“未约定”被当作非常明显的约定形式之一了*意为俄罗斯听众会默认德国当代作曲家必然使用噪音,已经约定俗成;前文的“嗤嗤”指口语中模仿噪音——译者注。。
在俄罗斯,关于约定的界限是非常彻底并且不可妥协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场景可以作为例子。罗斯托娃·娜塔莎去看歌剧,她在听一段爱情的二重唱时,忘记了所有“欧洲的”“约定”,只看见两个拙笨的歌手在歌唱。开始轮换着唱,后来一起唱,但他们俩甚至都没相互看一眼。那个男的穿着一条可笑的秋裤站在一些被画得乱七八糟、粘得到处都是硬纸板子中间的一个小亭子旁。后来歌手们的视线集中到厅上,他们周期性地沉默,沉默的时候正巧乐队就轰轰地响。最后当观众鼓掌与吵嚷时,这对“情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鞠躬。太荒谬了!
在这一事件中遭遇解构的不仅是音乐语言,还有歌剧的文化制度与欧洲的艺术概念本身。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一个事实:俄罗斯艺术家的眼光总是双重的,从欧洲内部审视的同时也从外部观察。俄罗斯艺术家的复杂情况还在于:如果以“纯粹的欧洲人”来看待,只算是派生性的;但如果过分强调“俄罗斯地方性”,那就屈于一隅了。这也是使得整个俄罗斯文化内部充满戏剧性的同时保证了丰富性的矛盾之一。
如前面的题目所言,我们音乐的民族化到何等程度?我想再次谈到个人的体验。我的曲子《切文古尔》(Чевенгур)中有一个片段建立在弦乐器的摩擦声上。当“现代乐团”(Ensemble Modern)演奏这首曲子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每一个击弦声;而在俄罗斯“新音乐工作室”(Студияновоймузыки)室内乐团的阐释中这一摩擦声用了全弓演奏,而且奏出来几乎就像柴科夫斯基的作品。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不仅德国人与俄罗斯人的艺术手段不同,甚至也不仅是音不同,而是连他们的“摩擦”都不一样。
前面已经谈到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对术语“民族性”有不同理解。用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波恩贝多芬艺术节的总监妮可·瓦格纳(Nike Wagner)女士的对话做一下补充。瓦格纳决然反对使用术语“民族的”,她以不同民族的作曲家联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新探索的达姆施塔特为例,认为达姆施塔特是一首真正的作曲家的《国际歌》。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完全赞同这一判断,但我想提一提另一个同样非常著名的现代多民族作曲家学派——巴黎的“音乐与声学协作研究所(IRCAM)”。在那里不同民族的作曲家同样联合起来进行新探索,但这完全是另一种“新”,全然不是“达姆施塔特式”的,而是非常法国的!我们如何命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音乐与声学协作研究所”学派?“《第二国际歌》”吗?假设意大利的政府给自己国家的一个类似机构注入同样的资金,那我们将可能会见证一个意大利作曲家的“《国际歌》”,而如果在俄罗斯有这样的机构,也许会有个俄罗斯作曲家的“《国际歌》”。
达姆施塔特的例子恰好说明,现在看起来非常中性的“全球化”这个词中隐藏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对一种文化来说,出离或高于某民族性的性格现象。这里的危险在于,弱化民族性的全球化在我们的世界里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压制文化多样性的形式之一。与此同时,实际上也遏制了我们每个人的自由。
我们的世界当然必须要全球化。但这并非麦当劳的统一式样化,而是亿万个独特个体的全球主义。回到音乐上面,我记得有大量俄罗斯作曲学生去德国的音乐学院学习,被认为是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重新编码”。他们努力变得“更加德国化,更少本民族化”,但暂时既不能给德国的当代音乐发展带来新潮流,也不能给俄罗斯的新音乐发展带来新气象,而这在今天是极其需要的。全球主义同样需要具有“人的特征”,它不能消灭个性——不论是地域的,民族的,还是个人的。
(本文为塔尔诺博尔斯基教授2017年7月8日在第七届北京国际作曲大师班上的讲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