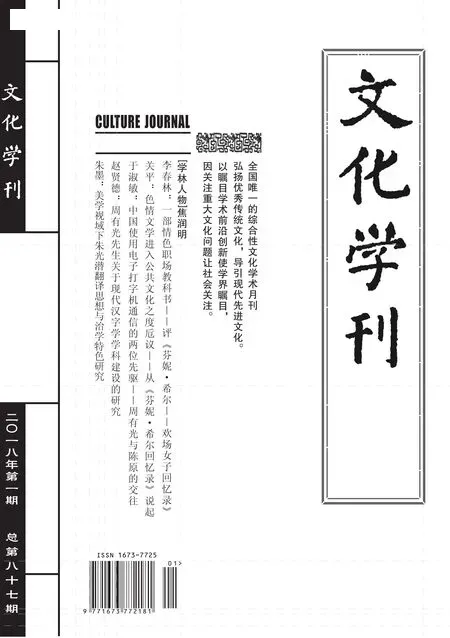“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论意义
2018-03-07王向阳
王向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两个前提
克罗齐认为,“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是在时间之外的。克罗齐面对人们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明显的时间一维性的质疑,提出在时间之外所进行的精神活动才是真历史。这样摆脱了时间的束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可能往下展开了。克罗齐的“当代史”本身也是包含着“当代”这个时间观念的,然而它是在“历史时间中”——过去、现在、未来,如果不是在自然界而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那它更多地表现为相互联结、影响。克罗齐显然明白自己提出的这个乍一看显得武断的论题的逻辑所在,他在《作为思想和作为行动的历史》中明确提出将过去与现在联结,将自己置于决定我们现在的过去之上“只有一条出路,即思想出路,思想既未切断同过去的联系又在它之上,从而在理念上提高它并将它转化为认识”。[1]
历史失去过去的依托似乎已经漂浮在了空中无所适从,克罗齐接着用“凭证”将它定在了当代。这里的凭证指的是史料文献,克罗齐所说的凭证或者史料或者文件所指甚多,可能是“文字的、雕刻的、描绘的、固定在唱片上的,甚至存在于自然物、骨架或化石中的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进入研究者的精神,那它就是死的凭证,而只有活的凭证,即与现在的生活兴趣打成一片的文献与批判才是真正的史料,也就是凭证。在这里,生活与思想显然使“过去”变成当代,使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克罗齐对历史与编年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2]在这里,区分历史和编年史的关键就是历史学家面前的凭证是否引起生活的兴趣,是历史认识中的主体能否通过这些凭证重演历史。可以这样简洁地概括其含义:历史脱离了生活的兴趣就不再是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死的编年史就变成了历史,在这里历史重新被唤醒的原因是“内在动机”,这种内在动机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内在的富有生机的“精神”;当精神或者思想与生活相联系之后,历史得到了它固有的真实性。克罗齐在这里分析的结论是:历史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其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
二、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的可能性
历史研究需要透过史料考证得出历史之真,形成考实性的认识[3],也需要透过史料把握背后的历史联系,也就是史实背后的思想活动,所以历史必定需要探究一切现实和一切可能[4],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又可以假设。克罗齐为了使精神确定历史的完全真实,竟然断然否定探究这种可能性的意义,从而走入了极端,但他对“普遍史”的批判再一次阐释了历史当代性的可能。在克罗齐看来,“普遍史”不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于:认识的有限性不可能穷尽无限的普遍;普遍史只是一种主张、一种愿望,实际上却是“特殊史”,在前一层有限性认识的基础上,如果缺少历史认识的凭借即文献文物时,想确切形成历史认识而不是靠神学的想象补充历史空缺的话,普遍史就成了一种愿望。克罗齐认为不存在纯有限和纯特殊,这明显是哲学概念的讨论,在克罗齐看来,历史与哲学是同一的或者必定要论证其同一,在其哲学体系中历史认识是从直觉开始,由直觉而概念的,由概念而判断,由判断而形成认识。历史认识是从一个具体的判断开始,而判断也是其基本形式,个别和普遍分别作为判断的主词和宾词,通过判断而获得质的统一。例如,现代史中政治史的主词是文化文明,真正的历史是“作为普遍的个别的历史和作为个别的普遍的历史”[5],于是普遍就在个别中得到。
在历史认识中,克罗齐将主体和客体联系在了一起,不仅将作为历史学家的主体与作为史料的客体,也将历史研究所过分追求封闭的脱离历史人物的历史规律与能动的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物联系了起来。克罗齐将历史提高到关于永恒现在的知识(他通过将“逻辑意识”在时间之外展开,脱离物质实在,得到纯粹的思想[6]实现了这一点),然后就与关于永恒现在的哲学实现了同一。它们的同一有以下几层相关含义。第一,在克罗齐的《逻辑学》中,克罗齐通过概念分析的方式,规定哲学对象是关于生活的体验,是精神实在,因为历史即实在,所以两者获得逻辑的同一。[7]第二,对“两眼望天从上天汲取或期待最高真理”式超越(精神)实在的形而上学的批判,确立为历史学方法论阶段的哲学。这种哲学是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是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其显然是有益于历史判断的,历史与哲学通过现实的生活而同一。第三,哲学的历史学家不同于超然物外的哲学家,他们自觉自己既是历史进程的主体也是客体,历史是唯一的真理,是思想的作品,因此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克罗齐通过精神、思想、生活将哲学从封闭体系的关于普遍概念的哲学,变成了内在的即与历史同一的哲学,将哲学变成了历史的方法论阶段,它的意义在于摆脱由于“不可知”却要达成普遍的可知的苦恼,确定变化着的永恒真理的失望。
三、历史当代性的积极意义与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性
克罗齐在历史人性的讨论中确实表现出来了对个体的人的重视,这种重视与其说是缘于西方哲学传统“反思”自我,实现自身进步的人文主义精神[8],不如用克罗齐的话说是具有精神性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显然区别于具有实用主义特征的历史形式——二元论的、非人性的、抽象的历史,同时也是建立在批驳维科和黑格尔的理性和观念基础之上的,以及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史学观点的批判上。它的逻辑是,第一,“实用”面对历史事实时,用抽象的人来寻求原因,它不仅与“思维的人”对立,而且这个“抽象的个人”也与宇宙,甚至和被视为抽象的个人相对立。由于历史事实不同于自然界现象,那么理性的说明也因此失败了。第二,维科和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理性或者天命的作品,为了实现理性的目标,天或者理性就会利用人们特定的目的或者欲望来实现较高的精神境界。[9]克罗齐对黑格尔理性的狡诈做了批驳:在“天命”或者“观念”的立场看来,个人是从属于“理性”之下并且是为实现理性而存在的一个附属物,而这正是历史哲学的超验论,是应该被扬弃的。第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观念”另外的名称,它的缺陷是两者互相对立,成为另外的二元论。实际上,两者都排斥了“整体”概念,这不仅会丢失个人构成的整体,也同样会丢掉整体中的自我。经过层层批驳,“个人”就从实用主义的抽象、黑格尔理性的狡诈、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论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宇宙性的精神性的个人,于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完全获得了思想的主导,成为判断的真正实施者。
不论是历史著作还是我们形成的历史认识,都不能将历史学家的思维排斥在事实之外。首先,我们的认识对象是被主体有意识选定的;其次,史料被收集之后所进行的分析,哪怕是考证工作都无一不渗透着主体的认识;最后,史料中的事实同样包含思想的动因,只要历史学家愿意真正地透过史料追寻背后原因,就必须深入其思想领域,而纯客观的直现史实就不可能了。
历史学家不可避免也必须要进行历史判断,由于深层存在的实际需求使一切历史具有了当代性。历史判断的主体是在其哲学观、价值观指导之下进行判断的[10],价值必定根植在判断之中,这是毋庸置疑的。有疑问的是,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进行历史判断。在克罗齐看来,自由与暴政、慷慨与无私、爱与憎只是情操或者情感,而不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因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是同无价值事物的对立中得到的。克罗齐的有价值与无价值的对立是缘于相信历史判断的积极性,也就是历史是从善到更善发展的,因此,价值判断就必定同现在的事物相联系,而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人物做道德对错上的宣判。因为历史只做判断,追求历史真理,那么历史判断是不是可以一次或者多次完成呢?克罗齐回答说不是,他立足于对黑格尔所预设的理性的实现是最终目的来进行反驳的。反驳的逻辑是:人类精神是不断发展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那么判断的主体意识就是不断发展的,而其所作出的历史判断就是不断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历史时期都需要新历史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确实是一种永恒的超越。而历史目的作为思想与行动的历史是相统一的,所以历史目的就在包含思想的行动中实现了,目的在此就与发展相同一了。由于历史认识主体完全获得了独立判断的地位,历史判断也是积极的,那么“当代性”的历史认识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意义。
[1]贝奈戴托·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M].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6.
[2][5][9]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敢任,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81.77.
[3][10]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32-236.147.
[4]何兆武.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J].史学理论,1988,(1):1.
[6]蒋大椿.析“历史是关于现在的知识”[J].世纪论评,1998,(4):35-40.
[7]彭刚.评克罗齐的历史与哲学同一论[J].哲学研究,1998,(9):72-79.
[8]靳艳,李少浦.也谈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J].社科纵横,2012,(9):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