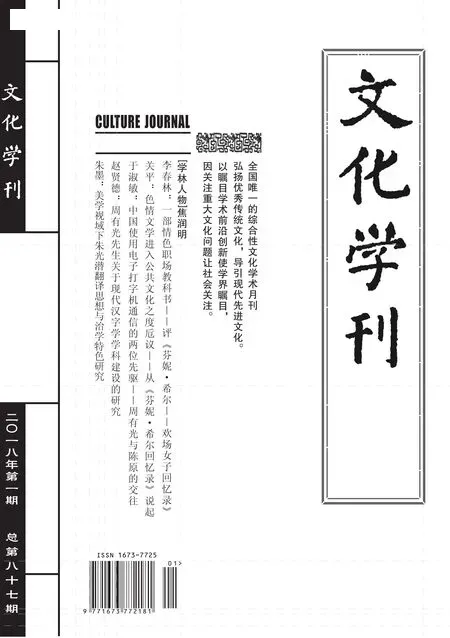用“诗”为乐与唐诗“谐谑”诗类
——从唐人用“诗”为乐的诗文化下寻今人解读唐诗的新途径
2018-03-07李静
李 静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一、“谐谑”之流:正统诗教外的为“乐”之始
《大唐新语》单列“谐谑”类,孟棨《本事诗》“七题”中也列“嘲戏”一题,足见谐谑诗亦是唐诗的一类。中国传统中,诗本正体,自古皆以“温柔敦厚”为准绳和规矩,我们今天又该怎样对待和解读唐诗中的这类“谐谑”诗?
实则在“温柔敦厚”的准绳下,《诗经》中就已经出现类于谐谑的诗作,如《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称赞君子之美,其中一项便是君子的善戏谑。“戏谑”一词,郑玄笺云:“君子之德,有张有驰,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2]朱熹《诗集传》言:“善戏谑不为虐者,言其乐易而有节也。”[3]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释为戏言、开玩笑。[4]从这些不同时代的注解可以看到,戏谑这种不同于传统诗教的东西已经进入诗歌中,虽然历代的解《诗》者用各自的解说或附会、或别出新题,但一种新的诗学功用正滋生蔓延,不言而喻。此还可见于《诗经·溱洧》:“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5]明载上巳节男女相互戏谑的场面,方玉润《诗经原始》言:“每值风日融合,良辰美景,竞相出游,以至兰勺互赠,播为美谈,男女戏谑,恬不知羞……在三百篇中别为一种,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6]方玉润先生的这段话虽以批驳之态解《溱洧》中男女相谑、兰勺互赠之场景,却恰从侧面显露出《诗经》中就已出现类于后世谐谑诗的诗作,可见诗歌的功用从一开始就不止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更是人们抒发情志和记载快乐的方式。
《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孔子讲诗的功用在于“兴”“观”“群”“怨”,其中包括社会功用和个人功用,个人功用中实则已包括诗的娱乐功用。《论语·先进》载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曾点陈说自己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8]可见孔子也是赞同诗歌娱乐功用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单列“谐隐”篇,对“谐隐”进行定义,并对前代涉及“谐隐”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梳理。他言:“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9]这些言辞浅显世俗,使人听了高兴发笑的“谐语”,刘勰认为不可弃。至于不可弃的原因,他明言是因为这些谐辞隐语有讽刺在上者的功用,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编入了《滑稽列传》;同时,刘勰对汉代东方朔、枚皋等人以赋为俳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魏晋之际人们追逐驱扇滑稽之风,他认为此同“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10]。就总体言,刘勰认为谐辞隐语的功用在刺上,沿传统诗教发展而来,其单列一篇进行论述,说明他留意到了“谐”在文学中发挥的功用。但此时的“谐辞”还带有“隐”的特点,即刘勰所言:“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11]唐诗的中的“谐谑”已独立成一类诗,并在士人间公开、大量地吟咏。
二、唐诗中的“谐谑”:唐人生活之“乐”的多方位展现
《大唐新语》单列“谐谑”一类,其中许多故事颇值细读,如“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条[12],载作为帝王的唐玄宗,在大宴群臣的场合主动倡导群臣以嘲谑为乐,可见唐太宗虽为帝王,亦有人情,而谐谑的双方一是身居相位又兼外戚的长孙无忌,一为擅长书法而居高位的文化名流欧阳询,他们以外貌相互嘲讽,欧阳询在对长孙无忌外貌嘲讽的同时,又含沙射影地对其人品进行戏谑,这时太宗收敛笑容站出来说:“汝岂不畏皇后闻耶!”太宗此时的行为表露了什么?当这种“为乐”的谐谑过度之时,他要加以制止,也即“谐谑”是有度的,这个“度”是什么?就是“乐”,不能超出“乐”的限度,长孙无忌毕竟是一朝宰相,又是皇后的弟弟,不能过“礼”对其进行攻击。
又如,“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曰嘲”条[13],故事发生在掌选人资格的吏部侍郎温彦博和被放选人裴略之间,诗所嘲讽的直接对象是“丛竹”和“屏墙”,诗产生的缘由是裴略被放后自赞于温彦博,称解曰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又令嘲屏墙。诗虽以“丛竹”和“屏墙”为嘲讽对象,实则借此戏讽温彦博。如“肚里不能容国土,皮外何劳生枝节?”“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其真的是在说丛竹不能容国土,屏墙遮挡了贤才路吗?显然不是,所以温彦博才会说“此语似伤博”。裴略却明言:“即扳公肋,何止伤博!”径直道出自己作诗就是因内心不平,讥刺温彦博。裴略又是极为有才智的,他不直接写诗攻击温彦博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揭露温彦博作为吏部侍郎在选人上的过失,而是自赞于温彦博,称解曰嘲,让温彦博主动让他嘲“丛竹”和“屏墙”,在嘲“丛竹”和“屏墙”的同时又借以抒不平、刺彦博,嘲的最终结果是温彦博惭而与官。
“则天朝,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条[14],所记故事则颇为有趣,作为在上者的武则天主动问起张元一:“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足见帝王也有娱乐的需要,也好听趣事,而张元一对答的两首以“将名”和“官名”为题的诗,又表现出诗在唐人生活中的广泛性,连姓名、官名都可以用来做诗,可见诗在唐人生活中无处不在。其还可见于另一则“武官学诗”的故事里,即“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条所记[15],言武官出身的枣强尉张怀庆,因好偷名士文章,把李义府赋的一首五言诗,在每句前面加上两字变成了七言诗。形式上看依旧工整,只是诗味全无,句意不通。所以时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作为一个武官,很显然张怀庆的诗作得并不好,甚至是不会作,但他却好偷名士文章,原因何在?
《左传》有“三不朽”之说[16],至魏晋之际,魏文帝曹丕著《典论·论文》更是明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17]况自魏晋起,一个自觉的时代开始到来,文学的自觉,人的觉醒,无一不给生活在其中的士人带来冲击,他们生命、人性、自我个人意识的觉醒,期望借助诗歌实现“托生名于后世”的理想。他们不仅仅着眼于当时有用,更看重个人身后声名不朽,所以武官出身并不懂诗的张怀庆也好偷名士文章。
不仅如此,诗在唐人的生活中还是巧辞的所在,如“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条所记事。[18]武则天初革命之际,恐群心未附,令人自举。自举的结果自然是官员增加、官职增多,但这些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身怀车载斗量之咏。这又表露了什么呢?在上者重视文化,需要文化,在下者又极力迎合,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所以选出来的官员也都有车载斗量之咏,而御史台令史在面对里行大怒,将加杖罚时,说罪过在驴,请求先数驴的罪过,在以诗数驴之罪的过程中,令史把自己的身份也暗藏诗中,诸里行得知令史身份后,皆羞赧而止。御史和里行同属供奉官正员之外所置官职,按理说,这位御史台令史完全可以在面对里行大怒,将加杖罚时,直接告诉里行自己的身份,但他没有,他选择以诗来发声,在嘲驴之过的同时,把这些里行也一并嘲讽了,“技艺可知,精神极钝”,看似说驴,实则针对里行前番行为有意谐谑。可见,在唐人的生活中,对过于物质的东西是鄙薄的,他们追求在文化中展现人性的本真。
此外,诗还经常充当斗具而发挥作用,如“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排斥”条[19],载僧、道各争二教之优劣,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兴善寺为火灾所焚,佛像被火烧尽,故意作诗表达自己所崇奉道教的胜利,对佛教极尽谐谑之言。诗在这里成了僧、道争二教优劣的斗具,但透过诗本身从时人对这件事的态度,“虽称赏荣诗,然其声称却从此遂减”的结局来看,唐人虽称赏一个人的诗才,但更重视人性的善良,并不赞同在他人落难之际对之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足见唐人“情”之真,少伪饰。
即便是在上者亦如此,如“侯思止出自皂隶”条[20],言侯思止因言音不正,在断屠之日对同列语闹出笑话,而遭侍御崔献可戏谑,武则天知崔献可嘲笑侯思止的事后很生气,对崔献可说:“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从武则天的这一行为看,似在为侯思止抱不平,虽有在上者御人之术的谋略含杂其中,但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理解,是不是也能看出即便是在上者,也主张对他人应该施以同情,而不是因人自身的缺陷就对之采取嘲笑讽刺,伤害他人。但当崔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后,武则天亦大笑,终释献可。武则天的这种前后不同的行为,是否矛盾呢?实则并不矛盾,她前责崔氏以为他有意嘲笑侯思止;后释崔献可是因她自己听崔氏以鸡猪之事对后亦大笑,她明白崔献可之笑非出恶意,实发自本能,她以己之感受出发去体会崔氏之行为,释放了崔献可。
当然,唐诗所展现的并不止于人性中的善,还有人性中的恶,如“贺遂涉和赵谦光相互讥讽攀比”之事[21],据《新唐书》载唐代尚书郎分三等:兵部、吏部及左右司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膳部员外郎属礼部,在后行;考功郎属吏部,在前行,且为“员外郎之最望者”[22],贺遂涉戏讽赵谦光不历员外郎而拜高品,赵谦光以自己现下所享受的优厚物质生活相炫耀,同时嘲讽贺遂涉作为房部郎中,不应位列高位,二人各以己之地位相攀比,又彼此嘲谑、不满,尽显人之私心。
在唐朝,人性中的恶又在诗的国度里诗化,不似世俗之鄙俚。如“玄宗初即位,邵景、萧嵩、韦铿,并以殿中升殿行事”条[23],记邵景、萧嵩、韦铿三人因升官不同事而彼此以诗讽刺事。韦铿对邵景、萧嵩二人胡须的嘲讽,实则是他心中不平之气的抒发,他们三人同以殿中升殿行事,后来邵景、萧嵩二人俱加朝散,独自己不沾。他心中一点不平、一点落寞都没有吗?当然不是,但是他没有径直猛烈地发抒其不平,而是在对景、嵩二人胡须的谐谑中,表达自己对官职高位的不在意,“自言身品世间毛”。举朝以为欢笑,又显现出什么呢?他们对韦铿的心迹是理解的,对他抒发感情的方式也是赞同的,所以并没有人责难、讥讽。其后韦铿在睿宗御承吴门、百僚备列之际,因肥短而眩倒,邵景酬其前嘲,亦对他肥短的身躯进行嘲讽,时人无不讽咏,可见唐诗实是真实反映人性,反映唐人生活的所在。邵景酬韦铿前嘲,对他肥短的身躯亦进行嘲讽,实是出于报复他前嘲自己之事,但我们不会觉得邵景为人逼仄,因为他采取了诗歌这样一种典雅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反击。
三、用“诗”为乐下的“情”与“真”:解读唐诗的又一途径
唐诗中的人是真正饱含真情、蕴含人性的生活着。如倡导群臣以嘲谑为乐的唐太宗、主动问张元一近日有何趣事的武则天等,他们都是活生生存在于生活中的人,他们有以诗为乐的需要,也好听趣事,但我们又不可否认他们作为帝王对群臣、对百姓的统治,所以当欧阳询嘲讽长孙无忌过“度”之时,唐太宗提醒他要制约;当武则天听闻崔献可嘲笑侯思止的事后会生气,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上者,他们允许臣子相娱为乐,却不能容忍臣下过礼犯上。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孔子是中国二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创造一个道德体系的人,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即所谓的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的“仁”。[24]
作为在上者,他们也明白礼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以他们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和需要为出发点,时时波及臣下,而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的士阶层,他们是政权运转的具体执行者、代替下层百姓的发声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诗歌的创作者,诗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在不同的场合,诗所发挥的功用也不尽相同,诗可以是欢娱的方式,如“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条,帝王和群臣以诗为乐;诗可以是仕进的手段,如裴略以诗嘲“丛竹”和“屏墙”,进而谐谑选官温彦博,终得官;诗可以是扬名后世的途径,如张怀庆作为一个武官,却好偷名士文章,不过是借诗以期立名后世;诗还可以作为相争的斗具,如李荣以诗向僧徒炫耀自己所崇奉的道教的胜利;诗还经常充当社交手段,文人们以诗相交,以诗相谑,如贺遂涉以诗嘲赵谦光升职的不光彩,赵谦光也以诗回讽贺遂涉所居之位不应列星文。至于诗最常见的作为言志、抒情的方式自不待言,《毛诗序》早已言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5]
即便是杜甫,作为文化人格典范的他也写下了许多戏作诗、谐谑诗,据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所检,杜甫的“戏题诗”共三十六首,如《戏官定后戏赠》《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等,这些诗不论是对时事的讥刺、对亲友的戏言,亦或是作者的自我嘲解,都是作者心路历程的抒发,但杜甫选择以“戏”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足证戏谑已然是杜甫诗歌中的一种类型。李白也曾作诗调侃杜甫,据《本事诗》载:“李白曾作《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26]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诗,也不能欣赏诗。诗和谐都是生气的富裕,不能谐是枯燥贫竭的症候。枯燥贫竭的人和诗没有缘分。”[27]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更是明言“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诗,它一方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子是唐朝,那是一个诗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28]诚如先生所言,诗在我国是全面的生活,尤其是唐诗,其和生活结合得最紧密。
我们今天解读唐诗,不应只限于从美学角度把诗歌当作审美的案头读物,对其进行僵化地赏析。当然,这并不是说审美不重要,审美也重要,但它不能代表一首诗的全部,更不应该成为诗歌解读过程中最主要的东西。艺术手法、写作特点是外在的审美,而文本语境是诗的内在生命力,读诗时,不仅仅因为它的外在美,更因为它的内在感发力,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点,使我们在读古诗感受古人生存状况的时候,也会反思自己现下的生存实际。借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句哲学阐发后所说的一句名言“……人诗意地居住……”[29],也即诗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就要求今天的读者也应该带着诗意来读诗,来理解诗在当时的诗人生活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1][4][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91.158.159.261.
[2][2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9.6.
[3]朱熹注.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5.
[6]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26.
[7][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8.166-167.
[9][10][11]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70.270-271.271.
[12][13][14][15][18][19][20][21][22][23]刘肃.大唐新语[M].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188.188.189.189.189-190.190.190.191.190-191.191-192.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88.
[17]曹丕.魏文帝集全译[M].易健贤,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254.
[2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79.
[26]孟啓.本事诗[M].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99.
[27]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
[28]孙党伯,袁謇.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7.
[29]马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戴晖,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