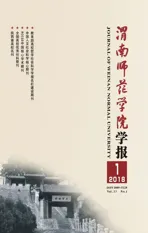王国维之《太史公行年考》立论基石发覆
2018-03-07袁传璋
袁 传 璋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一、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年研究的贡献与缺陷
司马迁自觉承“五百之运”,继周、孔绝业,以续作《春秋》自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撰成的《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史记》),是中华民族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间的文化总汇,是我们民族心灵、民族智慧的伟大载体。要读懂博大精深的《史记》其书,必得读懂司马迁其人。由于史阙有间,史公生平中存在许多疑案。其中与“史记学”中若干基本问题相关联的史公生卒年的定年问题,尤使学者困扰。
司马迁的生年,《史记·太史公自序》未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缺载,因此遂成千古疑案。清代乾嘉以降下迄近世,有数位学者提出司马迁生年的见解。王鸣盛认为当生于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周寿昌认为生于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张惟骧认为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以上诸说大抵出自臆测,并无实据,因而不具深入探讨的价值。直到王国维先生于1916年发表《太史公系年考略》,1923年将此文易题为《太史公行年考》重新发表,方将司马迁生年的探讨引向科学之途。
王国维的第一项贡献是,他首次从今传宋刻以来的《史记》三家注本的《太史公自序》中发现两条有明确司马迁纪年的唐人旧注。一条是《史》文“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注语: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另一条是《史》文“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注语:
按:迁年四十二岁。[1]482-483
在探究司马迁生年时,有了这两条唐人旧注做基础,庶可免除再犯瞎子摸象式的错误。
王国维的第二项贡献是,考出《索隐》与《正义》注语的来源可靠。指出司马贞自西晋张华《博物志》转引的司马迁官历,“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张守节的注语“亦当本《博物志》”。他征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安陵·阪里,公乘,项处”以及敦煌出土的两条完整的汉简履历簿书,归纳出“汉人履历,辄具县里及爵”“或并记其年”的文书格式。《博物志》所录司马迁官历正与此同,故“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
自从王国维先生发现这两条唐人旧注,遂成为王先生本人及此后诸多学者推导司马迁生年的“直接证据”。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岁”。他如此考证:
按《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说见后。”按“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茍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按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1]482-483
王先生先指出《索隐》所引《博物志》“当本先汉记录”,史料可靠;“《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二注同源。然据以推算司马迁生年,却有十年之差。二注必有一误。他根据“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的常理,是《正义》而非《索隐》。他作此判断的大前提是:《索隐》“年二十八”系“年三十八”之讹;小前提是:《正义》“年四十二”绝不可能由“三十二”讹成;由此推出的结论必然是:“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逻辑大、小前提的前提,或曰“立论的基石”,则是数字讹误说。
王国维先生这项著名考证,长期以来被誉为方法正确,逻辑严密,引证可靠,其结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为中外诸多著名学者如梁启超、钱穆、泷川资言、佐藤武敏等所信从。
在王国维发表《太史公系年考略》之后,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据《索隐》立说,发表《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认为司马迁当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桑原骘藏:《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自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附录4转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6-184页。50年代中,郭沫若作《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亦不信王氏的司马迁生年定年,而力主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2]呼应郭说者虽有不少,但由于均未提出足以动摇王国维立论基石的证据,终不成气候。
直到1988年5月,笔者在“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西安)上发表《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另辟蹊径,首创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找到测算司马迁生年的三个标准数据:“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于是仕为郎中”“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和一个基准点——《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以司马迁关于自身行迹的自叙为本证,以唐人古注《索隐》与《正义》为佐证,通过对史公移居茂陵、从学问故、壮游入仕、友朋交往等方面行迹的清理,证实《索隐》所引《博物志》元封三年“年二十八”纪年数字无讹,与史公自叙若合符节,考定司马迁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对于《索隐》与《正义》在史公生年上出现“十年之差”的原因,笔者从书体演变的角度,通过对“廿(二十)”“丗(三十)”“卌(四十)”三个十位数字与“世”字书写形态变化轨迹的考察,广征文物考古成果和多种文献,从中发现确凿的证据,做出有根有据的论证,证明《正义》“年四十二”乃“年丗二”之讹,才第一次真正动摇了七十多年来几成定论的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说(前145年说)。
近来主张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的张大可先生,宣称“王国维‘数字讹误说’的立论基石是不可辩驳的”,他要求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说”“做阶段性定论”。[3-4]拙作征引张氏言论除特别注出外,均出自文献3和文献4,下不再出注。
学术的发展永无止境,世间更不存在终极真理。王国维先生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证既有重大贡献,有如上文所述,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严重缺陷。
第一,在没有证明所引今本《史记》三家注本中的《索隐》与《正义》文字有无讹误的情况下,即以其为直接证据进行司马迁生年的考证作业,存在巨大风险。西晋张华(232—300)编纂《博物志》时,上距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时的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已近四百年;下距张守节完成《史记正义》的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2),更逾四百年。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时的官历经辗转传抄、征引,难免会发生豕亥鲁鱼般的讹误。现存最早的南宋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中《索隐》所引《博物志》“大夫司马”下均夺“迁”字,已通报了这方面的信息,但王先生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第二,王国维“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从一个“疑”字出发进行推论,本来就先天不足。学术研究容许大胆怀疑,但必须小心求证。遗憾的是王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史记》的版本依据,通过翔实的考证作业,以释“疑”为不疑;而是凭主观设想篡改古籍文字以建立己说,有违考据学的通则。王国维建立在猜疑基础之上而无实质性证据的关于司马迁生年的结论意见,当然不能奉作定论。
第三,王国维首创的“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的数字讹误说,用以说明古籍中个位数“二”“三”“四”之间的讹与不讹,是行之有效的。但王氏研究司马迁生年所面对的《索隐》与《正义》,却是十位数的“二十八”与“四十二”。宋代版刻经史以前的经史写本、碑铭玉册中,“二十”“三十”“四十”这三个十位数字,按照功令不以俗体书写,而均以正体合体书“廿”“丗”“卌”的形态出现。王氏的“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的数字讹误说,对唐代与唐代之前的经史写本尤其是《史记》写本中的“廿”“丗”“卌”之间的讹与不讹来说,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王国维作《太史公行年考》,仅仅依据宋以后流传至今的版刻《史记》三家注本,却不曾寓目一份六朝及唐代的《史记》写本以作参证。日本国流传至今的六朝与唐代的《史记》卷子本及其古抄本为数并不少,如宫内厅藏《五帝本纪》《高祖本纪》《范雎蔡泽列传》,高山寺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毛利家藏《吕后本纪》,东北大学藏《孝文本纪》,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孝景本纪》,神田文库藏《河渠书》残本,石山寺藏《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以上除《五帝本纪》为无注本外,其他均为《集解》本),有十多篇。这些写本中“二十”“三十”“四十”三个十位数字,毫无例外的均作合体书“廿”“丗”“卌”。如果首创二重论证法的王国维先生在做《太史公行年考》之前,见读过三五份六朝及唐的《史记》写本,肯定不会做出“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这样的误判,甚至也许不会撰写在司马迁生年与行藏的排比考证上有失考量的《太史公行年考》;如果要写,或许会写出观点、材料和论证与今传《太史公行年考》截然不同的另一篇《太史公行年考》的吧。生前因没有机会见读六朝与唐《史记》卷子本而撰写有严重失误的《太史公行年考》,后生只能惋惜地说这是首创二重论证法的王国维先生的遗憾。在王国维身后,坚执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说的学者,有机会参阅《史记》六朝及唐卷子本的影印本以修正失误,却置之不顾避之不及,继续在王先生划定的“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的范围内兜圈子,不能不说这是更大的遗憾了。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考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这个结论立论的基石是他提出的“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的数字讹误说。这块基石有如上文所述存在诸多严重缺陷,其实并不稳固。建立在这块陷空的基石上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自然不可能牢靠。要把这种毫不牢靠的定年强作“阶段性定论”,谈何容易!
二、宋刻以来的《史记》注本中 “二十”与“三十”罕见互讹
张大可在所作《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中不容置疑地说:“史籍中‘二、三、四’与‘廿、卅、卌’都互相发生讹误,事实俱在,任何举证推翻数字讹误说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可以说王国维‘数字讹误说’的立论基石是不可辩驳的。”
赵宋迄今的三家注本《史记》中果真存在有如张大可所说的“‘廿、卅、卌’都互相发生讹误”的“事实”吗?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以一以贯之的“从字缝中”寻找证据的原始方法,全面检阅三家注本《史记》。张大可坚信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具有“科学的基础”,认为王氏猜疑今本《索隐》“年二十八”是“年三十八”讹成的结论坚不可摧,其前提正是肯定“二十”与“三十”这两个数字“互相发生讹误,事实俱在”。然而笔者全面检阅的结果,却有令张大可及所有持前145年说者非常失望的惊人发现:自宋刻以来的《史记》三家注本中“二十”与“三十”这两个数字罕见相讹!张大可言之凿凿的“事实俱在”的“事实”,笔者竟莫之见。
清儒梁玉绳、王先谦曾先后从《史记》与《汉书》中发现“二十”与“三十”互讹的两条例证,但经笔者实地勘查都不能成立。
梁玉绳撰有学术名著《史记志疑》。他所发现的“三十”误书为“二十”的一例,为《史记·傅靳蒯成列传》阳陵侯傅宽曾孙傅偃的材料:“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史记志疑》卷三二于其下“附按”曰:“立三十一年也。各本皆譌。”[5]1352笔者按:傅偃于景帝前四年(前153)代侯,至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坐诛,实“立三十一年”。梁氏之前的《史记》诸版本,如宋刻《集解》单本、《集解》《索隐》合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史记集解》,《史》文皆作“三十一年”,不误;梁氏谓“各本皆譌”,不确。《史记》刻本作“二十一年”的,只有南宋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彭本体例款式一同黄本,故黄本实为彭本所从出。黄本刻印精美,而校勘草率。黄本误者,彭本亦沿其误。梁玉绳撰《史记志疑》,其《自序》交代了他所据的《史记》底本是当“世盛行的明吴兴凌稚隆《评林》,所谓‘湖本’也,故据以为说”。“湖本”的《史》文及三家注亦出自南宋黄善夫本系统,更重在文章评点,而疏于《史》文校勘,洵非善本。故《史》文作“二十一年”者,实系梁氏所据“湖本”自误,而与宋、元《史记》诸善刻并无版本承袭关系。假如梁玉绳当年有条件多参考一些《史记》宋元善本,相信他不会写出这条有问题的校语。
王先谦撰有学术名著《汉书补注》。他在《汉书》中发现的“二十”误书为“三十”的一例,见于《高帝纪下》:高帝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王氏认为“三十余人”系“二十余人”之讹。《汉书补注》于其下引“周寿昌曰”作证:
“荀《纪》作‘大功臣封者二十余人’,本书《张良传》同。《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韩信二十八人。‘三’是‘二’之误。” 先谦曰:《通鉴》亦作“二十余人”,此积画传写之误。[6]51
笔者按:此说与王国维的“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不谋而合,而早发于王国维,然其误则同。据《汉书·高帝纪下》所载,高帝刘邦剖符分封功臣曹参等人为彻侯,始于六年十二月甲申(二十八日)。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至正月壬子(二十七日)封吕清为新阳侯止,共封二十八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新阳侯吕清之后尚有郭蒙于“六年正月戊午”封东武侯的纪录。按:高祖六年正月丙戌朔,三十日为乙卯,后此三日的“戊午”系二月初三日。《史表》误记为“正月”。《汉书·高帝功臣表》承袭其误。然在此之前,汉王刘邦曾先后封吕后父吕公为临泗侯、项羽故将利几为颍川侯、太尉卢绾为长安侯;为皇帝后,又于六年十二月降封楚王韩信为淮阴侯。由于吕公已于汉王四年先卒,而卢绾则于五年九月晋封燕王,利几于同月因谋反被诛,故《高祖功臣表》除淮阴侯外,均未入载。而《高帝纪下》所称的六年正月前所“已封”的功臣,实含吕公、利几、卢绾、韩信等人在内,与曹参等二十八人相加,则得三十二人。以《汉表》与《史表》对校,发现班固漏抄了《史表》正月丙戌(初一日)所封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释之两侯,这还不包括班固于二百多年后制作《高帝功臣表》时因资料残缺而漏载的侯封。《汉书·高帝纪下》叙作“三十余人”,正得其真。而周寿昌、王先谦一时疏失,未见及此,误从荀悦、司马光之说,遽发《汉书·高帝纪》“三十余人”系“二十余人”“积画传写之误”的按断,从而犯下以不误为误的错误。此外,周寿昌云“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其表述亦有误。史实是高祖于六年十二月甲申先封十侯,正月壬子前再封十八侯,合二十八侯。正确的表述应为“六年二月以前封二十八人”。
张大可为了解释《索隐》与《正义》发生“十年之差”的成因,曾经十分用心地从正史中搜寻“二十”与“三十”互讹的例证,欲为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提供文献的根据。好不容易的从《汉书·霍光传》发现了一例,他指出:“辅佐昭、宣中兴的大臣霍光”,此前曾侍从武帝“三十三年”,但“《汉书·霍光传》却说霍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可见,‘廿余年’乃‘卅余年’之误,即‘卅’误为‘廿’了”。[7]86这下可好,终于为王国维关于《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系由“年三十八”讹变而来的推测提供了一条史料的“铁证”。但是,且慢,还是让张先生与我们一起重温《汉书》的原文吧。《霍光传》“出入禁闼二十余年”的下文,接叙征和二年(前91)卫太子之变后,武帝因为霍光“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决定托孤于霍光。[8]2931-2932霍光于元狩四年(前119)秋后,随其同父异母兄长霍去病由河东平阳至京师长安,“时年十余岁”。不久即因霍去病的官秩权位保荐霍光为郎。稍迁为诸曹侍中,“出入禁闼”,到征和二年,首尾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七八年。《汉书》叙作“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实事求是,并未误书。张先生的这项“发现”,其实是在没有读懂《霍光传》的状况下而做出的错误认定。他用以证明《史记》与《汉书》中“廿”与“卅”易致互讹的唯一孤证,事实上并不存在。如果这也算证据,只能是伪证;如果这也算考证,只能是伪考!当然,这已是张先生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现存的《史记》三家注本中“二十”与“三十”这两个十位数字相讹之例极为罕见,至少笔者从未之见,已如上述。张大可力挺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坚执今本《索隐》“年二十八”是“年三十八”之讹,认为“王国维‘数字讹误说’的立论基石是不可辩驳的”。口说无凭,实难当真。不知张先生如今能否从《史记》三家注本中找到几条经得起推敲的“二十”与“三十”互讹的例证,为王国维说提供文献上的支撑,从而证明王说“是不可辩驳的”?如果找到了,无疑会给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说增添筹码。
三、宋刻以来的《史记》注本中 “三十”与“四十”频繁互讹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考证司马迁的生年、排列一生的行藏,建立在今本《史记》“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绝不会讹为“迁年三十二岁”的基础之上。然而笔者通检《史记》全书的结果,却令王国维及其后继者大失所望——与“二十”“三十”两个十位数之间罕见互讹相反,“三十”与“四十”两个十位数之间互讹的情况却频繁出现。且容笔者举证。
今传《史记》三家注本中“四十”讹为“三十”者有之:
第一,《夏本纪》:“或在许”句下《正义》:“许故城在许州南三十里。”[9]83而《魏世家》“南国必危”句下《正义》释许故城作“南(西)[面]四十里。”[9]1858笔者按:《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志》所引《括地志》均作“四十里”。可证《夏本纪》之《正义》“三十”,乃“四十”之讹。
第二,《周本纪》:“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其下《集解》:“徐广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汉之九十四年也。汉武元鼎四年封周后也。’”[9]170笔者按:日本国高山寺藏《周本纪》古抄本《集解》作“一百丗四年”。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实为一百四十四年。是高山寺古抄本“丗四年”中“丗”乃“卌”之讹。
第三,《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而《六国年表》则作“西北取戎为四十四县。”其下《集解》:“徐广曰:‘一云四十四县’是也。”[9]758笔者按:《匈奴列传》与《六国年表》皆作“四十四县”,可证《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县”,系“四十四县”之讹。
第四,《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徙谪,实之初县”句下《索隐》云:“即上‘自榆中属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是也。”[9]254笔者按:如上条考证所言,今本《索隐》“三十四县”中之“三十”当为“四十”之讹。
第五,《秦始皇本纪》“得齐王建”句下《正义》云:“齐王建之三十四年,齐国亡。”[9]235而据逐年编排的《六国年表》,齐王建被俘国亡,在四十四年。是此条《正义》“四十”讹为“三十”。
第六,《项羽本纪》“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9]311《秦楚之际月表》及荀悦《前汉纪·高祖纪》均作“四十万”。而《汉书·高帝纪》却作“汉元年,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然则《汉书》“三十”乃“四十”之讹。
第七,《项羽本纪》“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句下《正义》:“《括地志》云:‘固陵,县名也。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9]332而《彭越列传》“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句下《正义》:“固陵,地名,在陈州宛丘县西北三十二里。”[9]2593笔者按:“四十二里”与“三十二里”,必有一误。《荆燕世家》“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句下《正义》:“《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9]1994然则《彭越列传》句下《正义》“三十二里”系“四十二里”之讹。
第八,《越王勾践世家》“商、於、析、郦”句下《正义》:“《括地志》又云故郦县在邓州新城县西北三十里。”[9]1748而《齐悼惠王世家》《樊郦滕灌列传》之《正义》引《括地志》皆作“四十里”,然则《勾践世家》句下《正义》“三十里”系“四十里”之讹。
第九,《赵世家》“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赵襄子元年,越围吴。”其下《正义》:“《年表》及《越世家》、《左传》越灭吴在简子三十五年。”[9]1793笔者按:《六国年表》赵简子在位六十年,其四十五年,越灭吴。故《正义》灭吴下文称“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六十减十五,正为四十五。然则今本《正义》“三十五年”系“四十五年”之讹。
第十,《魏世家》襄王“六年,与秦会应”句下《正义》:“《括地志》云:‘故应城,故应乡也,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9]1848而《范雎蔡泽列传》“秦封范雎以应”句下《正义》:“故应城,故应乡,在汝州鲁山县东四十里。”[9]2412及《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文“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句下之《正义》所引《括地志》亦作“四十里”[9]2090。然则《魏世家》之《正义》“三十里”乃“四十里”之讹。
第十一,《仲尼弟子列传》:“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9]2187《论语·雍也篇》孔子答鲁哀公问弟子孰好学,称其弟子“有颜回者,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于“西狩获麟”下,接书“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笔者按:子路死于哀公十五年卫国蒯聩之难。《公羊传》将颜渊、子路之卒连书,则可知二人卒时相距甚近。获麟后一年,孔子年七十二。依今本《史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则死时年四十二,已逾不惑之年,不得谓“短命”。然据萧统《文选》卷五十四刘孝标《辨命论》“颜回败其丛兰”句下李善注引“《家语》曰:颜回年二十九,髪白,三十二而早死。”又《史记索隐》注引《家语》说,与李善注引同。“三十二而早死”,可称“短命”,且与《仲尼弟子列传》所叙“回年二十九,髪尽白,蚤死”吻合。故清儒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谓《史记》“《弟子列传》所云少孔子三十岁者,原是四十之误。”是“四十”讹为“三十”。
第十二,《张仪列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句下《正义》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显王之三十四年也。”[9]2284笔者复按《六国年表》,秦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君为王。”是年为周显王四十四年。《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周显王四十四年,亦书“秦初称王。”可知今本《正义》“三十四年”之“三十”,实为“四十”之讹。
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筑碣石宫”句下《正义》“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9]2345而《乐毅列传》“齐器设于宁台”句下《正义》以及《通鉴地理通释》《太平寰宇记》所引《正义》皆作“四十里”。然则《孟荀列传》之《正义》“三十”乃“四十”之讹。
第十四,《张释之冯唐列传》“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句下《正义》:“云中郡故城在胜州榆林县东北三十里。”[9]2758笔者按:《苏秦列传》“西有云中”、《匈奴列传》“直代、云中”句下《正义》皆作“四十里”,《绛侯周勃世家》“云中守遫”句下《正义》所引《括地志》亦为“四十里”。可证《张释之冯唐列传》之《正义》“三十”乃“四十”之讹。
今本三家注《史记》中“三十”讹为“四十”者为数亦不少:
第十五,《秦本纪》“徐偃王作乱”句下《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9]175而《黥布列传》“楚发兵与战徐、僮间”句下《正义》:“杜预云:‘徐在下邳僮县东。’《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四十里,古徐国也。’”[9]2606若以本纪为正,则《黥布列传》之《正义》“四十里”为“三十里”之讹。
第十六,《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9]203而《六国年表》《商君列传》以及日本高山寺旧藏东洋文库藏古抄本《秦本纪》皆作“三十一县”。显然今本《秦本纪》之“四十”乃“三十”之讹。
第十七,《项羽本纪》“诸项氏支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句下《正义》:“《括地志》云:‘故桃城在滑州胙城县东四十里。’”[9]338而《万石张叔列传》“代桃侯舍为丞相”句下《正义》作“三十里”,《玉海》所引《正义》亦作“三十里”。是《项纪》“桃侯”《正义》“四十”系“三十”之讹。
第十八,《高祖本纪》“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句下《集解》:“徐广曰:‘三十二县。’”[9]365而《汉书·高帝纪》作“四十一县”,《汉纪》同。笔者按:《汉书·地理志》巴郡十一县,蜀郡十五县,汉中郡十二县,一共三十八县。是《汉书·高帝纪》及《汉纪》讹“三十”为“四十”。
第十九,《高祖本纪》叙高祖与项王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9]378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孔聚“以都尉击项羽,属韩信,功侯”句下《索隐》:“即汉五年围羽垓下,淮阴侯将四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是也。费将军即下费侯陈贺也。”[9]899是《索隐》“四十”为“三十”之讹。
第二十,《景帝本纪》“更以弋阳为阳陵”句下《正义》:“汉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9]442而《外戚世家》“合葬阳陵”句下《正义》引《括地志》作“四十里”。[9]1978若以本纪为正,则世家“四十里”为“三十里”之讹。
第二十一,《封禅书》“上郊雍,通回中道。”[9]1400日本泷川资言博士《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佚存》手稿抄录《正义》佚文:“《括地志》云:‘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三十里。’”而今本《秦始皇本纪》“过回中宫”句下《正义》,以及《匈奴列传》“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句下《正义》皆作“四十里”。是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早已误认唐人写本“丗(三十)”作“四十”矣。
第二十二,《河渠书》“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云云。[9]1409笔者按:汉兴之三十九年,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从文帝前元十二年河决酸枣,到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瓠子,实为三十七年。故《河渠书》“四十有余年”乃“三十有余年”之讹。
第二十三,《越王勾践世家》“北破齐于徐州”句下《集解》:“徐广曰:‘周显王之四十六年。’”[9]1751笔者按:《六国年表》周显王三十六年《楚表》“(威王七年)围齐于徐州。”同年《齐表》云“(宣王十年)楚围我徐州。”又《楚世家》“七年……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皆当周显王三十六年。可证《集解》“四十”乃“三十”之讹。
第二十四,《赵世家》“反巠分。”《正义》:“《括地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陉山,在代州雁门县西北四十里。’”[9]1819笔者按:《刘敬叔孙通列传》“是时汉兵已逾句注”句下《正义》《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高帝六年胡三省《注》引《括地志》并作“三十里”,可证《赵世家》“反巠分”句下《正义》“四十里”之“四十”乃“三十”之讹。
第二十五,《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句下《正义》:“平邑故城在魏州昌乐县东北四十里。”[9]1821而《赵世家》悼襄王元年“欲通平邑、中牟之道”句下《正义》:“平邑在魏州昌乐县东北三十里。”[9]1830又《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句下《正义》:“平邑在魏州昌乐县东北三十里。”[9]2444可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之《正义》“四十里”乃“三十里”之讹。
第二十六,《苏秦列传》“乃西南说楚威王曰:‘……北有陉塞、郇阳’”句下《正义》:“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百)[西]四十里。”[9]2259而《张释之冯唐列传》“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句下《正义》:“《括地志》云:‘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及《苏秦传》云“楚北有郇阳”,并谓此也。’”[9]2751《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光武帝·建武四年》“延岑复寇顺阳”胡《注》引《括地志》亦作“西三十里”。可证《苏秦传》之《正义》文“四十”乃“三十”之讹。
第二十七,《季布栾布列传》季布曰:“夫髙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9]2730笔者按:《史记·匈奴列传》作“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三十二万,北逐之。”而《汉书·季布栾布传》作“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又《汉书·匈奴传》叙髙帝自将兵击匈奴,“三十二万,北逐之。”班固《汉书》叙武帝朝以前的汉代史事均取自《史记》旧文,其《季布传》《匈奴传》均与《史记》同。可证《史记·季布列传》高帝所将兵数应与《汉书·季布传》同作“三十余万”,然则《史记·季布列传》之“四十余万”乃“三十余万”之讹。
第二十八,《李将军列传》:李广“为二千石四十余年”[9]2872。笔者按:李广自景帝前三年(前154)始任二千石的上谷太守,至元狩四年(前119)被迫自尽,首尾为三十六年。故《李将军列传》“四十”为“三十”之讹。
张大可曾经在其论文《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中说:“‘丗’与‘廿’仍相近,容易互相讹误,而与‘卌’则不易讹误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7]87-88如果这几个合体文字“历史的演变”真按张大可所设计的那样“演变”,王国维猜疑今本《索隐》“年二十八”原作“年三十八”,而《正义》“四十二岁”绝不会讹成“三十二岁”,定然水到渠成。但不幸的是,笔者通检三家注本《史记》所发现的真实的“历史的演变”,却是“廿”与“丗”罕见相讹,“丗”与“卌”频繁互讹,与张大可的设计完全相反!
四、王国维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不能成立
今存宋刻以下的《史记》三家注本中“二十”与“三十”两个数字罕见互讹,而“三十”与“四十”两个数字频繁互讹的铁的事实,把张大可的如下说辞——“史籍中‘二、三、四’与‘廿、卅、卌’都互相发生讹误,事实俱在,任何举证推翻数字讹误说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可以说王国维‘数字讹误说’的立论基石是不可辩驳的”,砸得粉碎。
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虽经张大可等人用廿、卅、卌之间都是一笔之差,易致互讹的说辞,予以补苴修正,但他们无法解释今本《史记》中何以“二十”与“三十”罕见互讹,而“三十”与“四十”却经常互讹的事实。可见它并不具备论客所坚称的“科学的基础”。至于施丁从日本“南化本”(其实是南宋黄善夫梓行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发现的《索隐》作“年三十八”,则不仅是条孤证,而且是条伪证。清代乾嘉学者衡量一词一事的考据能否成立,要以“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的标准进行验证。这是一项客观公正的学术标准。运用这项标准去衡量王国维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说”的立论基石——“数字讹误说”,用以解说“二十”“三十”“四十”这三个十位数字之间的讹与不讹,结论只有一个:“数字讹误说”根本不具备解说的资质,遑论“科学的基础”!
总括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两点基本认识:
第一,由于王国维立论的基石并不具备“科学的基础”,却据此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其方法自难称正确,逻辑也谈不上严密。《史记》中“二十”与“三十”罕见互讹的事实,使王国维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说”立论的大前提——《索隐》“年二十八”系由“年三十八”讹成的疑测,成为无根之木;而《史记》中“三十”与“四十”频繁互讹的事实,又昭示王国维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说”立论的小前提——《正义》“年四十二岁”绝不与“年三十二岁”相讹的判断,丧失立足的余地。作为立论基石的大小前提皆错,其最终的结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年)说,安能不轰然坍塌?
第二,《索隐》所引《博物志》录载的司马迁就任太史时的履历材料,其文书格式已经王国维、郭沫若分别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敦煌、居延汉简证明“当本先汉记录”,是“完全可靠的”档案资料。今本《史记》中“二十”与“三十”罕见互讹的事实,加之南宋通儒王应麟《玉海》卷四十六征引《正义》所录《博物志》、卷一百二十三征引《索隐》所录《博物志》,皆作元封三年“迁年二十八”,与今本《史记·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所引《博物志》作“年二十八”完全一致,足以证明今本《史记》自南宋版刻以来,《博物志》所引司马迁官历纪年数字“年二十八”从未发生讹变。笔者三十年前在《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中,曾以《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为本证,证实了《索隐》所引《博物志》的纪年,与太史公的自叙若合符契。它应是推算司马迁生年可靠的重要佐证。
关于《索隐》与《正义》在司马迁生年上出现的十年之差,张大可认为是“两说在流传中发生了数字讹误”。“张守节直以按语出之,必有所据。”他说:“据程金造先生的考证,司马贞稍年长于张守节,《索隐》早于《正义》20年问世,后出的《正义》对《索隐》有疏通、修订与补充的关系。张守节按语是依据《索隐》‘年三十八’之文推断出来的,《索隐》是在唐代以后流传中‘三十八’讹为了‘二十八’。”
张大可请出程金造先生为自己背书是大错特错。因为他所引据为证的程金造说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程金造据今本《史记》研究三家注,写了数篇考据文章,其中亦有就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生年者。虽被论客誉为“考释谨严,举证精确”,然经笔者检核,发现程氏考证颇为粗疏,持论往往武断,与“谨严”“精确”南辕北辙。说他粗疏,如程氏称“约计汲古阁《索隐》百三篇总数,为五千八百条。而黄善夫本《正义》,其总数约为四千条。”其实今本《史记》中《索隐》为7053条,《正义》为5315条。汲古阁单本《索隐》条数、南宋黄善夫三家注本《史记》中《正义》条数,与今本三家注《史记》相当。数据误差如此之大,而程氏未曾点核便信口开河,可见其发言的随意。说他武断,如程金造根本不知日本泷川资言《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佚存》手稿的本真面貌,就敢撰《〈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列举二十“证据”,断定泷川资言在日藏《史记》古活字本《史记》栏外标注中发现的一千三四百条《正义》佚文,手抄为《史记正义佚存》二卷,十之八九是日人的伪托。*程金造《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之来源与真伪》,原载《新建设》,1960年第2期。后对内容作重大增补,易题为《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之管见》,代表程氏关于《史记正义佚存》系日人伪托的最后意见,编入程氏著《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将湮没八百余载的一千余条《正义》佚文妄断为日人伪托,此说居然曾被学界长期奉为定论,辗转评、引,实亦一大奇闻。这是张守节的不幸,也是中国《史记》学界的悲哀。在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了不让程金造在《史记》三家注研究领域某些影响甚大的伪证伪考贻误后学,笔者奋起而作《程金造之‘〈史记正义佚存〉伪托说’平议》(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五期,2000年6月),对程氏精心挑选以证《佚存》为伪托的二十证例,逐条平议,彻底推倒程氏的误断,证明《佚存》一千余条《正义》非张守节所作莫属,为此疑案做出总结。本文评审专家指出:“此文拨云见日,发潜德之幽光。幸亏‘伪托说’之错误,由中国人自行订正;若此文由日人写出,则难堪矣。”笔者之所以掲举上例,是为了借此对程金造的考据功力做出评估,以供学者验证。关于《正义》与《索隐》的关系,程金造从清四库馆臣邵晋涵《南江书录》之《史记正义》条“《史记正义》三十卷……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的两句话*清代邵晋涵《南江书录》,清光绪聚学轩丛书第五集第七,《南江书录一卷》第4页,贵池刘世珩校刊。,得到灵感,推衍出《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认为张守节“撰《史记正义》确乎是见到小司马《索隐》之书的”,“《索隐》成书,早于《正义》二十年”,“《正义》在解释正文之外,又时时疏通《集解》和《索隐》”[10]169-188。笔者按:《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御府藏书下限断自开元十年。刘知几卒于开元九年(721),“《刘子玄集》十卷”已经著录。而据程金造说,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早于张守节“《正义》二十年”,则应于开元四年前后杀青。然《索隐》并未入录《旧唐志》的铁的事实,确证开元十年前其书并未完稿。《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本《注》其官衔为“开元润州别驾”,而非宋刻今传《史记》三家注之“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足见其书实杀青于开元九年离京外任润州别驾任內。《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人著作,按入藏御府先后排列。《史记索隐》编录于德宗贞元(785—804)中呈御的“陈伯宣《注史记》一百三十卷”之后,可知司马贞生前实未及将《史记索隐》上呈御府,呈献者或为其后裔,而其时上距开元(713—741)之末已过半个世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其撰著期间根本不存在见读《索隐》其书的现实可能性。程氏称“《索隐》成书早于《正义》二十年”,显然为想当然的无根之谈。程金造也不知道他据以研究的今本三家注本《史记》中附刻的《正义》,是经过宋人合刻者大幅度的整合重编后,以削除、删节、合并、拆分、移置等多种形态呈现于世的,已大失张守节《史记正义》写本旧貌。由于宋人移置了某些《正义》条目,有时误置于《索隐》之下,遂造成《正义》配合、疏解《索隐》的假象。程金造不推寻本末,居然将假象信为本真,从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找出若干似是实非的例证,由此得出“《正义》疏通《索隐》”自认为的独得之见。殊不知张守节根本没有可能见读《索隐》,何来有以《正义》为《索隐》“疏通、修订与补充”其事?然而张大可却把程金造关于“《正义》对《索隐》有疏通、修订与补充关系”的伪证伪考,奉为圭臬,一再引以为据,宣称“《正义》据《索隐》立说”,他先伪造一个“《索隐》‘年三十八’”的虚假数据,然后就按程说推衍:“张守节按语是依据《索隐》‘年三十八’推断出来的,《索隐》是在唐代以后流传中‘三十八’讹为了‘二十八’。”张大可这番“论证”是循环论证。张氏的这番“论证”依然是在重复王国维的老套路:“四十二”不可能讹成“三十二”、“三十八”容易讹为“二十八”。但是,证据呢?司马迁生于前145年说论者能从《史记》的任何一个版本中找出《索隐》所引《博物志》作“年三十八”的版本依据吗?能从宋刻以来的《史记》三家注本中找出两三条经得起查证的“二十”与“三十”两个十位数互讹的例证吗?窃以为前145年说论者都拿不出。在王国维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立论基石的命门上,前145年说论者都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得出确凿的证据来为王氏护法,就无法为毫无文献支撑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作阶段性定论”。
五、《索隐》与《正义》“十年之差”成因探究
西晋张华编纂的《博物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自《元史》起不再入录。足证其书散佚于宋元之际。唐宋两朝自有《博物志》全帙,且非稀见秘籍而为学者案头常备之书。笔者三十年前曾经指出,《博物志》存录的司马迁于武帝元封三年继任太史时的官历档案资料,司马贞作《索隐》时征引了,官拜大唐东宫诸王侍读的张守节作《正义》时也必见读过。张守节按语系据《博物志》而下,原来当作“按迁年三十二岁”。唐代《索隐》单本与《正义》单本之间并无“十年”之差。差讹发生在由唐人写本到宋人刻本的转换期。本文第四部分已证明《博物志》所录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时“年二十八”这个纪年数字,自南宋版刻以来从未发生讹误。二十、三十、四十这三个十位数字,殷周秦汉的正体均书作廿、丗、卌。传世的石鼓、钟鼎、石经、碑铭、敦煌与居延出土的大量汉简、湖北江陵县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湘西龙山里耶故城出土秦简《乘法表》等等,提供了巨量的实物证据。这种合体书写的形态,中经魏晋六朝,一直沿用到隋唐五代。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鸣沙石室佚书》等所收的大量六朝与唐代的经传卷子本的影印件可见,凡十位数字二十、三十、四十均作合体字廿、丗、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国公私所藏十多种六朝与唐的《史记》写本,凡数字二十、三十、四十,皆作合体字廿、丗、卌,毫无例外。
自殷周秦汉下迄李唐,作为正体使用了二千年的廿、丗、卌的合体写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人们从出土的宋人墓志、版印的经史典籍中可以看到,合体书写的形态被取消了,而代之以“二十”“三十”“四十”的书写形态。宋人在将唐人写本摹写版刻时,按照功令规定的书写程式,必须将合体字廿、丗、卌分别改易为二十、三十、四十。唐人将“三十”写成“丗”,而宋人将“世”字刻成“丗”,在誊录上版时,抄胥略有疏忽,就会将“丗(三十)”字误认作“丗(世)”字,而不予分解。校雠者也极难发现。笔者在南宋蔡梦弼《史记集解索隐》二注本与黄善夫《史记》三家注汇刻本刊行千年之后,于“字缝”中首次发现这种因误认而致讹的典型例证。这两部现存最早的《史记》二注本、三注本,都于《五帝本纪第一》前刊刻了司马贞补撰的《三皇本纪》,《纪》中有云:
故《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丗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讫纪。当黄帝时,制九纪之间。
“丗”字是“三十”字的合书,还保存了唐人写本的旧貌。“凡丗七万六百年”,是说每纪为三十七万六百年。满九纪为三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年,满十纪则为三百七十万六千岁。黄帝在位与孔子获麟之年均处于第九纪禅通纪之内。而蔡、黄刻本已将唐写本的上文“凡三百廿七万六千岁”中的合体字“廿”分解为“二十”,却未将下文“凡丗七万六百年”中的合体字“丗(三十)”分解为“三十”,可证蔡梦弼、黄善夫已将“丗(三十)”字误认作“丗(世)”字了。宋以后、清以前,凡从黄本所出的《史记》版本,所刻《三皇本纪》中的“丗”字皆相沿未改。清四库馆臣亦未识出此字,故四库全书《史记》写本遂沿宋本之误,将“丗(三十)”字径改作“世”字,抄写为“凡世七万六百年”。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则以讹传讹,排印作“凡世七万六百年”。这就与“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三十七万六百年”,风马牛不相及了。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修订本,附录了《三皇本纪》,也未予校正,颇为憾事。
宋人不仅将唐人写本《史记》中的“丗(三十)”字误认作“丗(世)”字,而且还因为“丗(世)”字与“卌(四十)”字古时读音相近,在特定的语文环境中,有时还会进而讹作“卌”字,这种阴差阳错导致了宋刻以来的《史记》文本中“三十”与“四十”两个十位数字的多处相讹。张守节《正义》唐写本原来当作:“按迁年丗二岁。”宋人据唐写本汇刻《史记》三家注时,将“丗(三十)”字误认作“丗(世)”字。然而“按迁年世二岁”又于义不通,遂猜度“世(丗)”字或为读音相近的“卌”字之讹,于是径将《正义》臆改为“按迁年卌二岁”,进而按宋时书写程式分解作“按迁年四十二岁”。这样一来,就铸成了今本《史记》的《正义》按语与《索隐》所引《博物志》之间“十年之差”的大错。
南宋王应麟(1223—1295),仕宦三十余年,长期处于朝廷中枢,执掌祕阁,主笔诏诰,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氏除天才绝识、好学精进有大过人者外,又得尽读馆阁祕府所藏天下未见之书,故成有宋一代通儒。所撰《玉海》二百卷,专精力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四库全书总目》称《玉海》“贯穿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玉海》卷四十六引录:“《史记正义》:‘《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玉海》卷一百二十三又引录:“《索隐》曰:‘《博物志》:太史令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王应麟所征引的《正义》与《索隐》,均为南宋馆阁所藏单行唐写本或其抄本,二者引录《博物志》同作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时“年二十八”,从而为笔者往年所做的“写本《博物志》,司马贞作《索隐》时征引了,张守节也会见读过”的判断,提供了可信的文献根据,同时也否定了王国维疑今本《索隐》“年二十八”乃“年三十八”之讹的臆测。
不仅如此。《玉海》引录的这条《正义》佚文,也使笔者关于张守节“据《博物志》所做的按语原作‘迁年丗二岁’,唐代《正义》单本与《索隐》并无‘十年’之差”的推断得以证实。因为《玉海》引录的《正义》《索隐》与今本《史记》的《索隐》,三者所征引的《博物志》,皆作“年二十八”,证明从古到今这个司马迁的纪年数字,从未发生讹变。《正义》据以推算,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所作按语,只能是“按迁年三十二岁”,而今本作“按迁年四十二岁”,必错无疑。
由于上述《玉海》卷四十六引录的《史记正义》佚文的重见天日,《史记·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一节《史》文下,张守节《史记正义》写本旧貌的复原成为可能。《史记正义》仿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摘字列句为注,《史记正义序》述其注释体例有云:“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所称“旧书”,指张氏以其为本的裴骃《集解史记》。张氏注例大意是说,他为《史记》作《正义》时,先编次裴骃注文要旨,然后才是本人为《史》文注音释字、推而广之、扩而充之的注义。试遵张氏注例,为《史》文自“卒三岁”至“太初元年”一节的《正义》复原(原格式为:《史》文大字,注文小字双行夹注):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博物志》云:“迁年廿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集解》李奇曰:“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此时述《史记》。”按:迁年丗二岁。
王应麟征引《史记正义》所录《博物志》时,文字有所节略,但基本数据全部保存,符合裴駰“删其游辞,取其要实”的注释标准。通过以上对单本《正义》的部分复原,可以清晰地看到《正义》于《史》文“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的按语“按迁年丗二岁”,系据《史》文“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条所引《博物志》“迁年廿八”推算而得。这就粉碎了程金造坚执《正义》据《索隐》立说的妄言,而施丁与张大可认为《正义》按语系张守节“自按”说也不攻自破。
笔者于1988年发表《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其观点、材料、论证方法与文字表达,迄今一以贯之,无须做任何修正。根据从《玉海》中发现的《正义》佚文、《玉海》引录的《索隐》、今本《史记》三家注三者征引的《博物志》,皆作武帝元封三年“迁年二十八”,以及修正后的今本《史记》“太初元年”句下张守节按语“迁年丗二岁”推算,司马迁也必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前135)。
本文的最后结论是:王国维先生所撰《太史公行年考》,在司马迁生年的考证方面有重大贡献,但同时存在更多的缺陷。他从猜“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出发,据以推测“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并无任何文献根据,却改字立说,本就先天不足。其立论基石的数字讹误说,更不具备阐释二十、三十、四十这三个十位数字之间讹与不讹的资质。王氏司马迁生年说的后继者虽极力为其补隙弥漏,力挺孝景中五年说“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但其说辞大都牵强附会,其证为伪证,其考为伪考(具见笔者下篇《“司马迁生年前145年论者的考据”虚妄无征论》的发覆),实无力回天。王国维先生于1916年发表《太史公系年考略》,首次提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今人或简称“前145年说”),迄今已达102年。为了将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推向前进,是应该为不能成立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说”画个句号了。
[1]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M]//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J].北京:历史研究,1955(6).
[3] 张大可.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1):5-13.
[4] 张大可.评“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9):5-9.
[5] 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张大可.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M]//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8] 班固.汉书[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本,1962.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