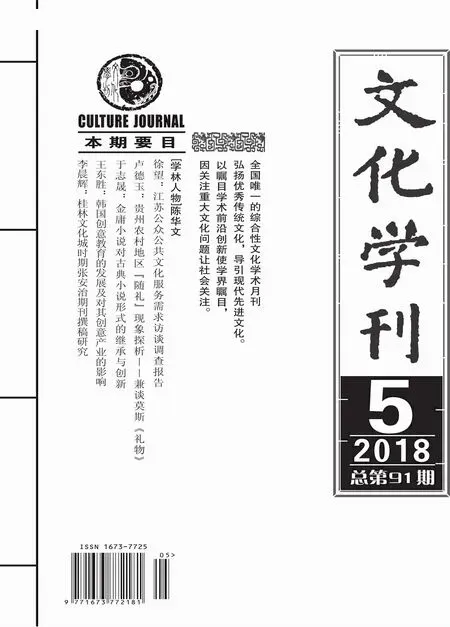汉文训读在东亚语言接触中的地位
2018-03-07刘洪岩
刘洪岩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1004)
一、研究背景
“汉文训读”是一种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文献注解(Glossing)现象,是世界上文献点标(Manuscripts Punctuation)的一个类别。它通常是指古代汉字文化圈中的各国知识阶层在阅读汉文时,用朱笔、墨笔或其他工具在字行间记录下汉字音、字义或语序等注释的阅读方式。带有这类注释记号的文献被运用到各类语言研究中,一般被称为“训点资料”。从流传至今的训点资料来看,存世训点符号形式主要有朝鲜的“悬吐”和“口诀”点、日本常见的“乎己止点”,以及越南的“字喃”等,另外,在回鹘等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有关文献中,也可见到以“小字”标注汉文音训的记载。[1]在这些训点资料中,古代汉语和周边其他语言信息彼此印证,在历史语言研究中受到了广泛重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观点认为东亚各语言在汉文训读过程中受到汉语的影响,从而引发了构词和句法上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本质可认定为一种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导致的语言演变。[2]
作为语言本体研究的前提,“汉文训读”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即在传统的语言接触研究视域下,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演变(language contact induced language change)一般特指发生在“面对面”的语言接触环境中,不同语言在口语层面上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因此,在用语言接触的指标和机制来探究汉文训读对东亚诸语言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解答如下一系列问题:汉文训读作为一种书面形式上的语言交互活动,是否可以被定性为一种语言接触?其在语言接触的研究范畴内,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接触相比,它又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本文将主要针对上述诸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泛语言接触”的观点
在明确语言接触和汉文训读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语言接触的内涵进行讨论。语言接触这一概念虽然被广泛运用在各分野语言研究中,但有学者评论,语言接触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作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存在,用作描述各种语言本体的周边性现象,没有见到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描述。[3]事实上,关于语言接触的概念,我们常以下述几例作为引述的范本。
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语言接触一般被定义为: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在同一社会集团中使用和发生接触。而Thomason更加关注语言接触的时空问题,将语言接触定义为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同一地点同时被使用所引发的语言现象。[4]另一方面,也可着眼于语言接触的结果,将其理解为一种语言直接或间接给另一种语言带来影响,并诱发言语(Parole)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会成为发话者的固有属性,进一步影响语言的历史发展。[5]
上述几种定义虽然视角各异,但它们都是基于多语言并用(multilingualism)的现象得出的描述性概念。但是,仅基于上述定义,我们还无法判定在东亚广泛发生的汉文训读是否可以被定性为一种语言接触现象。一般认为,语言接触的概念对“语言并用”一词的解释最为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对语言接触实际发生的“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社会集团”这些指标应当怎样去理解。在近年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我们发现,除了直接的、口头的接触作为主要媒介外,通过电影、文学作品、互联网等媒介进行的跨语言的一般交流活动也在被逐渐认可为一种语言接触活动,这类“泛语言接触”的观点渐成主流。根据这一观点,语言接触的媒介应该是多样的,只要存在两种以上语言的共存环境,语言接触都是可能发生的。在汉文训读这一历史上的跨语言的文字交流活动中,以古代汉语为中心的多种语言之间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接触是实际存在的。因此,汉文训读不仅可被视作一种语言接触现象,其对于拓宽语言接触的理论内涵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汉文训读的语言接触属性
东亚普遍存在的汉文训读实质上可看作是一种“注解”现象,为了学习中国的汉籍和佛典,东亚各国的知识阶层在以汉字书写的文献的字行间添加上记号,以对汉文进行本土化解读。这一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逐字的直译,在这种不同语言类型的语言交互中,受到汉文的影响,东亚各国书面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构词和句法的变化。因此,从结果上看,汉文训读和其他语言接触一样,都会对语言本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倾向于将汉文训读定性为一种语言接触现象,并从以下三点来考虑。
首先,书面文字也可以视作为语言接触的一种媒介。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接触一般应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下发生的语言交互现象,即特指那些不通过特定媒介的“面对面”的音声语言的直接接触。但这一观点的反例是,通过古代宗教经典等文献的流布,语言间也可以进行一定规模的接触,甚至会对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的演变产生推动作用。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通过对基督教圣典的注解进行本土解读,西欧各地的书面语词汇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拉丁文影响。此外,由于大量佛教典籍的传入,中世纪泰语的书面语言表达受到了古巴利语(Old Pāli)的影响。再则,由于受到宗教典籍诵读的影响,从近代土耳其语和马来语的演变过程中也都能看到古阿拉伯语的影响。上述现象,就结果而论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广义上的语言接触现象。同样,通过汉文训读,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里也发生了类似的语言接触。儒学典籍和汉文佛典作为古代汉语的载体流传整个东亚,东亚各民族在奉读、注释、传播这些汉文著作的同时,本民族语言的历史演变也必然会受到汉语的影响。而这一情况下,语言接触的媒介已不再是单一维度上的音声语言,而是一种书面文字的形式。
其次,翻译行为也可看作语言接触的重要方式。目前,对汉文训读是否属于一种翻译方式还存在一定争论,但由于它是在保留原汉文的基础上将源语言(source language)逐字转化为东亚其他语言后进行解读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把它认定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关于翻译本身的语言学意义,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间接的语言接触,且会给目标语言带来一定程度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汉文训读看作是东亚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的翻译行为,因此,汉文训读也理应符合语言接触的一般特征。
最后,文献的本土化注释是调查语言接触的重要依据。在这一点上,汉文训读并非孤立的现象。文献的本土化注释在中世纪欧洲是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源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的借用(borrowing)研究也往往是以注释文本为例证的。在这一层面上,汉文训读现象具有普世性,它是世界中诸多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接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汉文训读的语言接触类型
(一)语言接触的一般类型
从接触的媒介来看,语言接触可以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前者是指语言的使用者进行面对面的声音语言接触,无需特定媒介;后者是指通过文字等多种物理媒介进行的跨时空的书面语言接触。如Tok Pisin语和Krio语等皮钦语的形成都属于直接接触的范畴,而上述巴利语和泰语、古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及马来语的语言接触都属于间接接触。另外,从影响方向上来看,直接接触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区分,语言接触带来的影响是作用于双方的,而间接接触往往是文化上占有优势的一方会对文化落后一方造成影响,反之则不成立,这和历史上书籍、文献传播的流动方向是一致的。
从接触的时间范畴看,语言接触主要可以分为长期接触和短期接触。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其绝对的时间长度,而主要是取决于语言接触是否具有较长期间的连续性。长期接触是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期间内所发生的连续的语言接触,如Michif语和Chinook Jargon语等皮钦语的形成都是基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接触,它们都是在多民族间形成的简单贸易用语的基础上不断混合和发展而成的。而语言接触只发生在一个特定交流时期,而很快又停止的情况一般属于短期接触,如近代的洋泾浜(Chinese Pidgin),相对短期的多语言并用都是这类短期语言接触发生的舞台。短期语言接触往往与战争、殖民、贸易等相对短期的历史背景有关,是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激烈的语言接触。
(二)作为语言接触的汉文训读的类型
汉文训读可视作一种间接型的语言接触。具体来说,汉文训读是一种由书面文本为媒介发生的语言接触形式,不同于移民、贸易、战争、语言教育等近距离语言接触,而是依托于远距离文献、典籍传播的语言接触形式。中古的汉籍和佛典流入东亚各国,各国文人对这些文献开始进行本土化解读,此后带有本土化注释的文献进一步广泛传播,从而影响了各民族书面语表达的形式。近代以前,东亚各国的书面语大多与口语特点不一致,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汉文训读体”的影响。换言之,汉文训读作为一种语言接触,它给目标语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书面语层面的。汉文训读这类语言接触一般是以文化交流为最终目的,语言接触的方向也与文化传播方向一致。古代汉文的书面语以文化典籍为载体开始和东亚各国语言进行接触,并不断产生影响。而反方向的语言接触,要到近代后汉籍影响势微后才开始出现。
汉文训读对东亚各国影响的历史过程不一,但一般历经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比如从公元6世纪开始,汉籍文献大量流入日本,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汉文输入过程贯穿古代史始终。一般认为,日语中来自汉语的影响始见于奈良时代,最终在近代形成了被广泛应用的成熟的汉文训读文体。从语言接触的频率和强度来看,依据现存的语料,汉文训读的影响一般体现在东亚的知识阶层所使用的书面语中,如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知识阶层的书信、笔记、日记等都是由汉文撰写的。汉字、汉文作为一般知识素养,在古代东亚的士族阶层被广泛学习和使用。而且,东亚各民族的知识阶层所采用的汉文都不同程度显示出了体现其民族语言类型的“变文”特征,这显然是由于“训读文体”的影响。但就一般庶民的情况而言,本国语言一直是其口语语言主体,受到汉文影响的程度难以确认。就这样的影响范畴来看,汉文训读在东亚是以一种低强度的姿态出现的,亘贯东亚文献交流的历史。
五、结论
由上文的讨论可知,在当今语言接触研究视角下,语言接触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因此,汉文训读这一在文献交流背景下发生的书面文字交互过程也属于语言接触,具有普遍性。在世界历史中,由外国典籍的本土化解读而引发的语言接触事例并不鲜见,汉文训读对东亚各国语言的影响也可理解为其中一例。
以语言接触的一般类型来看,东亚历史上所发生的汉文训读现象应属于间接型、长期型、不同族系间的语言接触现象。因此,汉文训读对东亚各国语言带来的影响多集中于书面语层面,属于远距离文化传播形成的单方向的影响。这一影响的过程亘贯上千年历史,周边语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因此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金文京.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2):19-25.
[2]吴福祥.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J].民族语文,2007.(2):3-23.
[3]宮下尚子.言語接触と中国朝鮮語の成立[M].福冈:九州大学出版会,2007.49-50.
[4]托马森.语言接触导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2-3.
[5]方欣欣.语言接触问题三段两合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