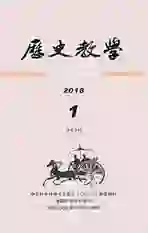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2018-03-06吴宗国
摘 要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要开阔视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囿于前人成说。要善于分别普遍和特殊,从特殊和普遍的结合上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坚持研究生的录取标准,是我们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的前提条件。同时辅导几个研究生,形成一个学术群体,经常在一起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培养他们同学之间学术上的毫不保留,学习和研究上的相互支持,也培养他们为学术发展同舟共济的学术团队精神。
关键词 破除迷信,普遍和特殊,录取标准,学术群体,团队精神
中图分類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2-0003-05
一、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课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先后带了十几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给研究生开设过“隋唐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等课程。
先说一说我开设“中国古代史研究”课程的缘起和情况。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都是按照断代史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因此很多研究生在学习的时候就一心扎到自己选定的一个断代史中去,往往会出现只知先秦、秦汉,或者只知隋唐、宋元、明清,而不知其他。这不仅影响到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也限制了学生视野的开阔、理论思维的发展和历史观点、历史方法的养成。根据这种情况,我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古代史研究”课程。
我给“中国古代史研究”课程定下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中国古代史的专业理论水平,掌握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概貌和发展规律,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性问题,掌握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掌握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概貌和发展规律,就是要开阔视野,从宏观上、总体上、立体地、发展地、全方位地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就是要从发展和联系上,也就是从历史的前后联系和各个时期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上,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把中国古代历史作为一个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整体来进行研究。
我给同学们指出,目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没有搞清的,有待深入的,甚至还没有着手研究的问题也是很多的。而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国历史发展中重大的理论性问题的研究,更是严重滞后。由于材料的限制,有一些问题可能永远搞不清楚。有一些问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障碍。首先是囿于传统和前人之陈说。其次是方法上的错误,理论上的错误。最后还有现实的影响和限制,特别是当今社会思潮的影响,往往会使人迷失方向。
我还给学生指出,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基本的有以下几条:
1.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历史事实出发。要注意,史料不等于历史事实,立论不能从史料出发。同时,不能囿于前人成说。史料和论文专著都不等于历史事实,都有后人的主观因素。不解放思想,也就不能实事求是。
2.要有一个发展的观点,要从历史发展的全局观察历史,要注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每个阶段的转折点及其特点。
3.善于分别普遍和特殊,辩证地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历史事实是具体的,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因此,进行历史研究,首先要注意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实,要进行实证的研究,找出它们特有的本质和特点。但仅仅停留在这种实证的研究上,就变成了一个一个事实的堆砌。那就是故事、典故,而不是历史了。因此,我们还必须把前后左右贯通起来,找出其中相通的东西,共同的东西,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普遍性。所谓前后左右,也包括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不找出共同的普遍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找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看不到具体的特殊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看到历史的发展。例如“田制”,唐以前各个朝代的田令都包含限田、荒地处分等内容,这就是普遍性。而各个田令又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具体到一般,从特殊和普遍的结合上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4.把握好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每一时代都有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的理解。当然这往往是通过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来加以表述的。每一个时期也总是强调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因为历史毕竟不是脱离社会的,特别是在社会激烈变动的时期。温故而知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资治通鉴,经世致用,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传统。例如南朝的史学家,包括他们在唐代的后裔,都强调天命。唐初史学家则注意从前朝的兴亡中吸取教训,注意的是君民关系。而到唐朝对农民的统治稳定以后,又转而强调君臣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甚至又重新提出天命。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50年代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古代史分期问题等“五朵金花”的讨论,80年代以后偏重实证的研究,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当然,80年代以来也开展过不少讨论,如专制主义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停滞问题、文化问题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大多是在历史学圈子以外进行讨论的。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除了少数人,基本上是没有参加的。这些讨论的共同特点是对历史研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却在社会上和青年人中间,把思想搞乱了。首先在学风方面,以论带史,主观臆断,甚至捏造历史。其次是片面强调政治,片面强调文化。在一个时期里,经济问题受到忽视。对经济问题忽视,对政治和文化事实上也没有认真地研究和真切的了解。
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埋头于自己的实证研究,固然有其客观原因,包括对以论带史、儒法斗争、影射史学的反思,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具体问题研究的长期滞后,也使实证研究成为历史学继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进入21世纪后,我们总得对历史的理解更全面一些吧。历史是人的历史。作为个体的人,有他孕育、出生、发育、成长、衰亡的过程,有骨骼,有肌肉,有大脑、有思维。作为人的群体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有它产生发展的历史,有构成历史的骨骼、肌肉和灵魂。这样,历史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的整体。翦老(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说过,经济是历史发展的骨骼,政治是历史发展的肌肉,思想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灵魂。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这也告诉我们,这几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全面地掌握和理解。endprint
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更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问题。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英雄、人民、阶级斗争、生产力、思想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各有其作用。英雄也有帝王将相、圣者贤者和科技家之分。这些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历史学习和研究逐步搞清。
具体到本课程的教学,除了要求对中国历史概貌和重大问题的掌握外,还提出了几点指导性要求。
1.树立通和变的思维方式。通指会通,贯通,要有通识,也就是从发展联系来观察历史。不能只知经济而不知政治,只知中原而不知周边,更不能只知自己研究的断代而不知其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总体来把握历史的发展。不能以点带面,有的研究前面朝代的,写通的文章,按前面的模式一贯到底。研究后面的,往前追溯,按后面的模式一推到顶。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发展似乎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者也是这样。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一点大家似乎都不否认。但是怎么变,分歧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具体到一个王朝,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制度上的变革和革新是经常出现的。每个王朝的中期往往还会出现大的变革,诸如汉武帝,武则天到唐玄宗,唐代宗到唐宪宗,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在这些变革和革新的前后,许多方面也都处在变化之中。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能掌握历史的发展。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可能掌握实际运行中的制度。现在教科书上往往都在王朝初年写上某朝的政治制度。如果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是王朝初年的制度,或者是各个时期制度的混合物。初年的制度只是初年的制度,混合的制度则不存在于任何一个时期。
只有掌握了通和变,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割裂的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历史。
2.学会立足一个断代,或一个王朝,通观中国历史发展的本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深入,更不可能样样精通,但是对于一个断代或一个王朝有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就有了一个典型,一个出发点,并且通过学习和研究,可以掌握基本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对于前后各段,也需要掌握基本的史料和史实,但主要是接受前人的成果。接受成果也不容易,论著越来越多,鱼目混珠,良莠不齐。这就需要鉴别,这就需要功力和眼力。要有能够鉴别好坏的慧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核对史料。
总之,这两点是要求大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点,要把历史学通,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宏观和微观,把理论性的研究和实证性的研究结合起来。
3.学会自己找到问题,找到研究方法,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除了上面所说的理论方面的修养,还要掌握工具和研究方法。邓广铭先生提出的四把钥匙(目录、年代、职官、地理),周一良先生反复强调的五个w(who谁、where那里、when什么时间、what什么、why为什么),是我们时刻应该牢记的。还要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尤其是归纳分析的能力。还要进行讨论,共同研究。
以上是对学生提出的一些概念性问题。要使学生真正领会这些问题,提要求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课程的各个环节使其逐步领会。
我们主要安排了这样几个环节:一是专题讲座,邀请各方面学有专长的学者到课堂讲授其擅长的专题。二是专题讨论,在专题讨论的过程中,要求学生选定一个题目,广泛地搜集材料,写出讨论发言稿,讨论完毕后修改上交。三是安排作业,作业完成后每人进行报告,大家展开讨论,最后修改并结集成册。例如,我们曾安排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作业和讨论,最后编成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资料》并打印成册。我们还围绕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课题安排了几个系列的活动。一是组织专题讲座,主讲的都是校内外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二是组织学生检索与课题有关的论文,编写索引。三是组织讨论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等问题。他们都认真进行了准备,精心写出了发言稿。并有许多研究生在参加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了他们的学位论文。这些都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一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多年后,选修过这个课程,如今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孟彦弘同学回忆道:“吴先生为了让各个断代的研究生对中国古代史能有更直观、更深入的整体认识,而不会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学的那个断代,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吴先生常讲,每门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对这门学科有一个直觉的感受、认识和把握。研究物理,要有物理感;研究历史,也要有历史感)。同时也为了让学生对学术界的情况能有更多的了解,他第一次在系里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主持开设了中国古代史研讨的综论课。大概因为刚留系教書的丁一川、陈苏镇两位青年教师的课时不够,他就请他们两位作这门课的助教。当时主要是选一些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先让同学们熟悉相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核查相关原始史料,然后写成初稿,组织讨论;有时也会请系内外的专家学者作报告(日后大概后一种形式较多,我们那时却是以前一种形式为主的)。我后来发表过的一篇讨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所谓史学理论的文章,最初就是这个课的作业,在这个班上讨论过。”他在1989年3月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到北大上课,该我讲,题目是《中国没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原因》。似乎很得意。……吴宗国先生作了总结。”他还回忆说,自己“几乎是每课必发言、发言必争辩。有一次讨论什么问题,跟瞿剑兄争执了起来,瞪着眼睛,脸红脖子粗。现在想来,实在是够招人烦的”。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课堂气氛是很热烈的。
二、关于培养隋唐史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几点体会
第一,导师的水平、研究的重点和趣味之所在,对学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学生本身的水平。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规定,如果原来规定的招生名额招收不满的话,第二年就会减少招生名额,因此往往会降低水平录取,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的录取上,这种情况更多。在硕士研究生这一块,降低水平录取固然给导师无可奈何的增加了负担,但是经过师生三年共同努力,毕业论文还是可以达到通过的水平。不过这些学生的基本知识、学术视野、学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往往缺乏进一步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而博士生如果降低水平录取,问题就多了。如果不是导师下大力气进行辅导,或者同学竭尽全力的帮助,甚至越俎代庖,他们的毕业论文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的。而严格按照录取标准招收的博士生,导师指导就省事多了。对于他们毕业论文的指导,主要是开题论证,帮他们选好研究方向,平时则只要进行定期检查,解答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讨论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就可以了。从搜集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广泛地阅读文献、搜集资料、考辨相关问题,到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写出论文,基本上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所幸我指导的博士生都具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和科学研究能力,不仅带起来比较顺利,而且在他们工作以后,也都成长为各单位的学术骨干,有些早已开始带博士生了。因此,坚持研究生的录取标准,是我们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的前提条件。那种机械的名额限制实际上是一种破坏人才培养的犯罪行为。始作俑者现在应该都已经退休了,希望后继者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endprint
第二,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时候,最好不要一个时期只带一个研究生,最好是同時辅导三到五个研究生。理想的是一次招收两三个,几年连续招他三五个都可以,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学术群体,他们可以经常在一起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开阔思路。这不仅对他们学术上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学术团队精神,培养他们为学术的发展同舟共济,互相帮助的精神,为了同一个课题各自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名利。
第三,鼓励学生不单单听自己讲的课,还要多听其他老师讲的课,特别是一些学术尖端的和前沿的课程。例如,跟着我学习隋唐史的学生,可以选修魏晋南北朝史、宋史等断代史课程,也可以选修经济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历史地理等专门史课程,甚至可以选修一些世界史的课程。这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都是很有好处的。
第四,注重因材施教。对于原本学习基础不够好的学生,要以鼓励为主,培养起他们的自信心。对于那些见多识广的学生,则提醒他们不能靠聪明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还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和特点进行引导,有些学生比较注重理论,但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把握不好。又有的学生比较注重历史材料,而在分析研究上功力不够。这些都要下大功夫帮助他们。要让他们明白,理论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事实才是研究的出发点,一切要从事实出发;同时,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订,史实的考辨上,还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的、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理论性的结论。
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也要有不同要求,硕士着重在打基础,可以多帮一帮,帮助其搜集资料和修改文章花的功夫较多,而博士生则是要培养其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的能力,因此要多放一放,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摸索。
第五,除了广泛的、系统的、扎实的读书以外,讨论也是研究生学习重要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在扎扎实实读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力,经过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因此一次讨论下来,不仅解决了一些预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一位别的学校来我系进修的老师参加过我们的讨论以后,很有感慨地说,这样,每一次讨论提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个新的论文题目。
第六,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定上,一方面是某个阶段课题要相对集中,另一方面就是在不断地讨论中自主选题。有些重大的问题,经过几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持续努力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例如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三省体制最后完成了到中书门下体制的过渡,这个关系到唐代政治体制和官僚制度的重大课题,从问题的提出到最后完成,那是经过了好几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训练。问题的提出是一位本科生,他在写作毕业论文的时候提出,中书门下的设立与使职差遣的设立有什么关系?当时我也刚刚认识到,中书门下的设立是中枢体制的重大变革,至于这个变革的具体路径和意义,我还没有什么认识,无法给他具体的指导。但我还是鼓励他先摸一摸,看看能否做下去。由于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缺少研究,没有成果可以借鉴,加上他还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这个问题他摸了一下最后还是放弃了。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始终放在心中,并且对后来的研究生加以介绍。最初几年的研究生,由于当时学术界总体研究水平限制,以及他们自己的研究能力,还不可能从总体上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围绕三省所作的研究,却为后来硕士生和博士生冲击这个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80年代开始,在我隋唐史研究的课程中,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十几年间,由我指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是以唐代政治制度为中心的。而到90年代,我们更把《唐六典》作为读书课学习的重点。在阅读和讨论的过程中,对照其他有关史籍,不断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引导同学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写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其中一部分当时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其他成果也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后不断出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有关唐朝前期制度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由刘后滨、孟宪实、叶炜、雷闻四位博士和我一起撰写了《盛唐政治制度研究》。虽然是由我们几个最后完成的,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傅连英、陈爽、罗永生、陈志坚、张建利、祁德贵、李蓉等在他们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成果,而某些思路甚至是由本科学生在课堂讨论和毕业论文中提出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教学相长的集体创造,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在研究过程中,读书讨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方式。结合对各种文献材料的认真比较和反复钻研,讨论时大家提出自己碰到的和发现的问题,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心得体会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主动给别人的研究提供材料和观点。通过讨论,大家受到很大启发,积累了不少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更有意义的是,在这样反复讨论互相切磋的过程中,大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在理论水平上也得到了提高。正如胡戟教授所云,“这种学术上毫不保守,彼此可以无条件运用对方观点材料的朋友圈,是能支持共同成功的一层保障”。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同学之间这种学术上的毫不保留,在学习和研究上的相互支持,在研究生的培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牵涉学生学术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由于长期的坚持,我的这些学生慢慢地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这些学生尽管毕业已经十几或二十几年了,他们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学术上也频繁交流,相互帮助。
以上体会主要讲的是成绩,回想起来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是教学内容不够全面,对于科学技术、生产和经济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论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日常的讨论和指导中都还不到位。这对于帮助他们深刻理解历史发展,特别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原因,都是严重的缺陷。其次是过多地关注他们的毕业论文,而忽略了基础知识的扩大,特别是在古典文献、古典文学、经济史、文化史和世界史等方面。第三是对于中西历史,也就是中国和欧洲历史的对比研究没有展开。没有引导他们阅读与研究相关的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
这些都是20年以前的事了,有些很可能已经过时了,写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作者简介】吴宗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王湉湉】
Abstract: As graduate students who major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y would be better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to seek the truth from the fact and reality and catch the law of histo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culiarity and generality. The graduate admission criter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educating talents equipped with research ability. Professors would be better to guide several graduate students simultaneously,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group, within which they can have discussion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With these supports, the graduate students can form their own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have community spirit as well.
Key Words: Broaden Horizons, Peculiarity and Generality, Admission Criteria, Academic Group, Community Spiri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