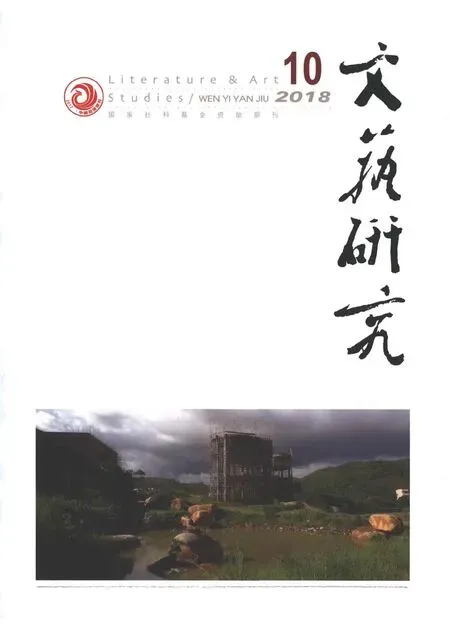袁枚的咏史诗创作与性情人生
2018-03-04马昕
马 昕
袁枚作为清代中期杰出的诗坛领袖,既有大量诗歌作品传世,又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性灵”理论,主张抒发率真性情,坚持书写平凡生活。但在其《小仓山房诗集》所收的4461首诗中却有236首属于咏史题材,占比约为5.3%。这个比例比同属性灵诗派而又是著名史学家的赵翼还要高一点①,足见袁枚对咏史诗有相当浓厚的兴趣。但问题是,咏史题材与袁枚的整体诗学追求构成一定的“矛盾性”,这是其他题材所不具备的。一方面,写作咏史诗要立足于一定的史学修养,素材也源于书本,难免要以典故敷衍成篇,这种“以学问为诗”的做法容易禁锢人之性情,也正是袁枚所一再反对的。另一方面,咏史诗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多属帝王将相主题,又与袁枚的性灵诗学所崇尚的对平凡生活的书写习性相差太远。换句话说,咏史题材最不应该是性灵派诗人的专长,在袁枚身上却恰恰相反,这当然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认为,必须将袁枚一生所作的二百多首咏史诗,与其潇洒率性的人生经历对应起来,才能体察其内在联系,看到其咏史诗如何突破学问和书本的隔膜与阻碍,直达诗人的性情内核。
袁枚的一生,经历了纵横南北的漫游、在翰林院的学习、基层官场的历练以及在随园的隐居生活,生活状态并不相同,其咏史诗的创作风格也有所变化。在34—36岁这三年,也就是初次归隐期间,袁枚只写了一首咏史诗,是其咏史诗创作历程中的一段空白。在这段空白期的前与后,袁枚的人生遭遇和咏史诗创作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以34—36岁初次归隐为界,将其咏史诗创作历程分为前、后两期,分别讨论。
一、袁枚咏史诗创作的前半期(21—33岁)
(一)漫游南北与流落京城时期
《小仓山房诗集》的收诗起点是乾隆元年(1736),袁枚21岁。这年正月,他受父命,到广西桂林投奔当时身处金幕下的叔父袁鸿,希望借金之力谋得进身之阶。这是袁枚第一次出门远行,人生阅历得到极大扩充。他路经浙江、江西、湖南等省,途中参访了不少历史遗迹,写下10首咏史诗,集中表现了青年才子对功名的期许。例如他行经浙江桐庐严子陵钓台时,写下《钓台》一诗,诗中充盈着“为念故人重,转觉天子轻”②的豪气;又在《书子陵祠堂》一诗中写下“何况赤伏符,可无王者师”③二句,似乎在想象着自己也能有睥睨帝王的能力。可见,袁枚从严子陵的事迹中,撷取的并非隐士的恬淡与孤独,而是能与君王同榻而眠的优越感,甚至是可为帝王师的荣遇,我们从中能感受到一个年轻才俊那颗正在蓬勃跃动的雄心。到长沙,他参观孙策庙,作《吴桓王庙》一诗④,只写孙策的英雄意气,却无一字提及其英年早逝的悲剧结局。到贾谊祠,又作一首《长沙谒贾谊祠》。他写贾谊,重点不是悲其“不遇”而是羡其“怀才”,用“屈子堪同调,相如敢比肩”⑤这样的话来追捧贾谊。这些都可看作少年才子的心性表达。
袁枚在这年九月试于保和殿,却不幸落选,不得不暂滞京城,狼狈地过了一年多。这段时光里,他只写出两首咏史诗,都与京城附近的遗迹有关。其中一首是《黄金台》,袁枚并不依寻常意见去歌颂燕昭王之礼贤下士,而是作起翻案文章。他说:“回问当年豪举心,果然值得黄金否?”甚至质疑燕昭王“不报仇时台不筑”⑦。这样的翻案立场,很难不被人怀疑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总结袁枚在这一时期的经历与咏史诗作品,可以发现:袁枚的性情变化几乎纤悉无遗地表露在其咏史作品中。对英雄先辈的崇拜,对功名之念的执著,对书生价值的自信,都是他应试之前的正常心态;可一旦首战失利,自暴自弃与愤世嫉俗的思想就以咏史翻案的方式暴露出来,也使我们看到这位青年才子脆弱和敏感的一面。不过所幸,他这段低谷期并不是很久。乾隆三年(1738),袁枚中进士,以庶吉士身份开始了三年的翰林院生活。他的咏史诗创作也出现了新的主题与风格。
(二)翰林院时期
袁枚在翰林院师从史贻直学习满文,却并不专心,而是对史学议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常与友人蒋和宁谈史论古,“两人不饮而好论古,折堲相对,凡三千年国家治乱,人才臧否,有所见解,动辄相合,拍几叫呼,以故益相得”(《诰授奉政大夫湖广道监察御史蒋公墓志铭》)⑧。“国家治乱、人才臧否”,可作清谈之资,也可为咏史诗提供素材,但他对史学的兴趣显然是肤浅的,并不能像赵翼那样埋首史籍、沉潜考据,而不过是一副坐而论道式的清谈做派而已。他在此时所写的《意有所得辄书数句》之二中说:“形为万卷累,亦非达士怀。不闻古神仙,识字居蓬莱。书堆三万卷,转使我意乖。束之良可惜,读之不能该。吾欲法祖龙,一举为灰埃。终日仰屋梁,不乐胡为哉!”⑨袁枚将万卷书视作束缚,宁愿一把火烧掉。这种束书不观的习惯发展成一种游谈的气质,使他在乾隆六年(1741)集中写出了16首颇见新意的咏史诗。这些诗都是七言绝句,也都写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在诗集中连续编排,应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女性主题恰好很容易写出新意,而七言绝句的体裁也适合写出杜牧式的翻案议论。只不过不同诗篇的“新意”中包含着思想认识上的矛盾。
矛盾的一头是:袁枚对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报以深沉的同情,认为她们不过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只能受男性权力的摆布,一切对她们的批评和责难都过于苛刻。比如《玉环》之一就说:“缘何四海风尘日,错怪杨家善女人。”⑩袁枚认为杨玉环本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子,为何要将国家动乱归罪于她呢?《西施》之一又云:“吴王亡国为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⑪诗中细致刻画了西施的内心矛盾:她一方面是越人,为越国的复兴承担重大使命;另一方面又是女人,面对夫差这位对自己宠爱备至的男人,又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这样的矛盾与撕裂,是她不能改变的宿命。总之,玉环嫁给玄宗,西施进入吴宫,都不能自己决定命运,显然居于被动地位。因此,对她们二人报以同情,都在情理之中。但像妲己、褒姒、张丽华这样的女子,历来都是一副纯粹的负面形象。袁枚《张丽华》之二却说:“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⑫认为褒姒、妲己之流能受到圣主的陶冶而转变成为贤妃,其实暴露了他思想中的某种“局限”:看似要为女子鸣不平,但仍然以将女子置于弱势地位的妥协方式来为这份同情心寻求依据。如果袁枚一直保持这种态度,我们不过说他终究还是个俗人。问题是,他的思想中还存在另一面。
矛盾的另一头就是:袁枚还时常赋予女人以强势地位,让她们在男权体系中展现女人的力量,甚至具有超越男权的资格。例如《上官婉儿》云:“论定诗人两首诗,簪花人作大宗师。至今头白衡文者,若个聪明似女儿?”⑬后世对上官婉儿的功过是非充满争议,或讥其淫乱宫闱,或批其干乱朝政。但袁枚只推重她的文才,认为即便今日执掌文衡之辈也难以与其比肩。这番议论未必高明,但至少显示出袁枚的立论勇气。而且,袁枚对女性地位的抬升,不仅表现为赞美,还可以表现在批评当中。例如《潘妃》云:“玉钗生自劈《楞伽》,尼子归来步步花。争不荆条加苦手,教人好好作官家。”⑭潘妃对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荒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袁枚却希望她能“荆条加苦手”,教导萧宝卷做个好皇帝。这当然高估了潘妃的情操和能力,但正是这份高估暴露出袁枚对女性承担社会责任的较高期待。
学术界研究袁枚的女性观,多将乾隆六年所作的这批咏史诗视作重要依据⑮,但都忽略了以上所揭示的这重矛盾。袁枚对这些女子的评价中隐藏着他对女性权力自相矛盾的两种认识。但有一点一以贯之:他同情玉环、西施的宿命,为褒姒、妲己、张丽华开脱,是因为前人总在批评她们;他赞美上官婉儿对文学的贡献,是因为前人总在夸大她那些宫闱隐私;他批评潘妃不劝谏君王,是因为前人根本未寄希望于她会为国家带来积极影响。如果因为袁枚对几位女性人物表达了同情或赞美,就说他对女性的尊重是从这一时期已注定,那显然是忘记了他在这批作品中的其他几首诗里也暗示了对女性的贬低。这些咏史诗中并没有袁枚一以贯之的女性观,而只有一以贯之的翻案手法而已。翻案技巧无疑能让年轻的诗人发泄他对历史议论的狂热,显示出他在清谈中高人一筹的所谓“识见”。
(三)南京候任时期
袁枚在翰林院学习满文并不用心,所以散馆时被授以末等,只能出放县令。失落至极的他灰溜溜来到南京,准备接受任命。在此期间,他至少写了24首咏史诗,但《小仓山房诗集》只保留了其中5首。不过,袁枚早年编刻了一部《双柳轩诗集》,暴露了他在此阶段更加真实的创作情况。陈正宏考证,《双柳轩诗集》所收245首诗,创作于乾隆七年至十年(1742—1745)间。中年归隐后,袁枚自悔少作,将书板焚毁,但仍有110首诗出现在《小仓山房诗集》中⑯。就咏史诗而言,《双柳轩诗集》保存了袁枚从北京回南京途中以及在南京候命期间所作的22首咏史诗,其中竟有19首没能编入《小仓山房诗集》,而剩下3首也全都被彻底重写。这样严重的删改简直是专门针对咏史诗的,因为其删和改的比例都大大超过其他题材类型的作品。这使我们怀疑,袁枚晚年编定诗集时对这一阶段的咏史作品有所避忌。那么,他在担心什么呢?
研究的突破口是遭到严重篡改的那三首诗,其中有《金陵怀古》二首⑰,在收入《小仓山房诗集》时将诗题改为《抵金陵》⑱。第一首被完全重写,第二首也只有颔联得以保留,修改幅度之大令人咋舌。修改之后,“山头日已斜”“金城泪落”一类气氛阴郁的景物描写都被删掉;“伤心世世帝王家”变成“一片长江六帝家”,“廷尉山头日已斜”变成“辇毂规模大道斜”,伤心的情绪被替换为壮阔、恢弘的气象。原作末句以庾信流落异国自比,在改作中却替换成“手挥羽扇问年华”,俨然一副释然与淡定的模样。可见,原作与改作的最大区别是情感基调与诗人形象的变化,诗人从一副落魄的模样化身为“手挥羽扇”坐看沧桑变化的智者形象。看来,袁枚并不想让读者知道他被外放之后这段时间里的真实心境,担心那会使自己苦心塑造的孤傲自赏的才子形象和淡泊名利的隐士形象大打折扣。
再将那些被删的作品与收入《小仓山房诗集》的同题作品作比较,更能看清袁枚的这层担忧。比如《双柳轩诗集》中有《孙策》一诗,《小仓山房诗集》未见。该诗专写孙策英年早逝的悲剧结局,与上文所述《吴桓王庙》的情绪基调恰成鲜明对照。再比如袁枚还删掉一首题为《昭君》的七绝,《小仓山房诗集》却保留了袁枚在即将抵达南京时所作的《明妃曲》。《昭君》云:“君王不爱倾城色,贱妾无心怨画工。”⑲这个王昭君完全是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不被君王宠爱也就罢了,竟然对画工都无心怨恨。而《明妃曲》却写得慷慨激昂,末二句说:“寄言侍寝昭阳者:同报君恩若个多?”明妃不但不自伤,反而以能报君恩为无上荣耀。这样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最终被晚年的袁枚精心保留下来。
在南京候任的这段时间,袁枚的内心世界里笼罩着一生中最阴郁的一片愁云,这使他满腹牢骚、满腔怨怒,写下了一些任性而又轻佻的作品。这也可能是他最不想回首的一段岁月,所以他后来一辞官,就开始自悔少作了。
(四)任职江宁时期
乾隆七年至九年间,袁枚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等地担任知县。乾隆十年春,又奉命调任江宁知县。这时他已经适应官场规则,甚至在沭阳任上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政绩,俨然一个标准的循吏。《小仓山房诗集》卷四、卷五有21首咏史诗,都写于袁枚在江宁任职期间。诗中的价值观逐渐向官场所能够接受的方向靠拢,也就是对“臣则”极尽推崇,甚至出现一些过于谄媚的表达,都有点让人难以看清这到底是诗人的真心还是假意了。
例如他在乾隆十二年(1747)写了《咏史》6首,都是五言古体⑳。第一首写汉武帝和汲黯。袁枚先用八句铺陈武帝的文治武功,接下来竟以近乎咒骂的方式指责汲黯是“老匹夫”。汲黯曾认为当县令是一件耻辱的事,还感叹自己过去的部下都如“积薪”一般后来居上。袁枚对此表示不满,甚至说:“当时竟杀汝,如鼠投沸汤。”汉武帝对汲黯异常尊重,甚至当汲黯觐见时,皇帝定会衣冠整齐,“不冠不见”。袁枚却说:“不冠而见之,于帝更何伤。”我们联想一下袁枚在几年前刚刚被外放县令时是何等的牢骚,已经做了六年县令的他,不但不对汲黯以做县令为耻的说法表示出同感,反而横加指责。也不知袁枚这种对皇权的一味维护,是否发自内心?
第二首写东汉初年的桓谭。桓谭擅长弹琴,颇受光武帝刘秀欣赏。但他所演奏的琴乐多是新曲,近于“郑声”。宋宏对此非常不满,便劝说光武帝罢免了桓谭的官职。没过多久,桓谭又因为劝谏刘秀勿信谶纬而被贬为六安郡丞。这两件事,桓谭先是过佞,有如优伶;后是过直,有如莽夫,都违反了臣则。最终,袁枚赞成宋宏那样“自重立臣则”。他虽然批评桓谭弹琴近乎优伶,却又为刘秀开脱,说:“君王爱泛声,一弹奚足责。”单从这两句诗来看,袁枚骨子里也够“佞”了。
其他几首大致也是类似的主题,都蕴含着对臣则的鼓吹和对君权的逢迎。我们不禁会怀疑:这还是那个十年前高吟“为念故人重,转觉天子轻”的袁枚吗?不过,再看他在此阶段写的《严助》㉑,就发现袁枚内心深处的牢骚终究还是掩藏不住。这首诗将张汤小人得志后的丑态生动描绘出来,俨然就是一幅讽刺官场生态的漫画。看来,袁枚对臣则的鼓吹,多半也不是真话,而很可能是长久压抑之下的一种自我开解;也可能是反话正说,跟后人开了个冷幽默的玩笑。
乾隆十二年,尹继善举荐袁枚升任高邮知州,却被吏部阻挠。袁枚已经在知县任上苦守七年,却被这件事激怒,决定辞官归隐。次年冬,他来到随园,开始隐居。但时间不长,由于经济日渐窘迫,入仕的想法再次萌生,他又走上入京的路途。
二、袁枚咏史诗创作的后半期(37—82岁)
(一)二次出仕时期
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袁枚离开隐居了三年的随园,北上入都。他本以为还能在南京做地方官,这样就能做官、归隐两不误,没想到消息传来,却是命他去陕西上任。这一年里,他先是在二月入京候命,三月就离京赴陕,五月到达西安,又在西安周边游览一圈。可是官还没做几天,就在这年的九月,父亲的亡讯传来,袁枚只能南归守孝。所以这所谓的二次出仕,多半时间都在路上,说是出仕,不如说是游览。而他所游览的地方,主要是历史遗迹异常丰富的关中地区,少不了登临怀古,咏史诗自然就没少写。《小仓山房诗集》收录了他在这期间的46首咏史诗,是袁枚咏史诗创作最为鼎盛的一次高潮。这些咏史诗展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以帝王主题集中表现的“英雄气”,二是批判性的回归。
袁枚从南京入都的路上经过了汉高祖歌风台、周世宗庆陵、光武帝原陵、秦始皇陵、武后乾陵和唐太宗昭陵,这些帝王都可谓雄主。袁枚在这些地方所写的咏史诗里,再次澎湃起他在少年时代有过的英雄气。只不过,将帝王写成英雄人物,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人专写帝王的文治武功、煊赫业绩,但这样难免千人一面。袁枚的关注点很独特,多写铁汉柔情,把帝王写出了风流才子的味道。比如写歌风台,就最能写出刘邦率真的一幕。因为这是一代开国帝王衣锦还乡、高唱《大风》的地方,威仪赫赫的君王变成了一位可爱的醉汉。所以袁枚在《歌风台》二首中专写他的醉态,说:“有情果是真天子,无赖依然旧酒徒。”“千秋万岁风云在,似此还乡信丈夫。”㉒
刚盛赞过刘邦没几个月,诗人又来到光武帝原陵,这时他却说:“人道萧王逊高祖,我道萧王较英武。”认为与刘邦相比,刘秀更像个英雄。因为“未必中兴输草创,生来天性胜高皇”,赞刘秀“天性”更好。比如“扫除四海净风沙,遂得初心阴丽华”,他取得天下之后,对阴丽华这位糟糠之妻初心不改,可见是个有情人;不像刘邦,先是辜负吕雉,后是保护不了戚夫人使其受虐而死。又比如“一时冯邓皆师友,殊胜争功半鹰狗”(《光武原陵》)㉓,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冯异和邓禹,最终都和刘秀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得以善终;不像刘邦,胜利之后就开始屠戮功臣。总而言之,袁枚对“英雄”的定义,并不是看那些外在的功过成败,而是特别看重人的心性,看他是不是一个有真情、有血性的男子汉。从中我们发现,此时的袁枚突然褪去了前几年那副令人作呕的官僚气质。虽是称颂君王圣德,却多从真情热血着眼。如果再对帝王做些批判,那么袁枚就真是和官僚做派渐行渐远了。下面就来说一说这一时期袁枚咏史诗批判性的回归。
上文提到过,袁枚在南京候任时期写过一首《明妃曲》和一首《昭君》,前诗说昭君自表有功汉室,后诗则说昭君自怨自艾甚至无心怨恨画工,无论表功还是自伤,都处于心理上的弱势地位,也都没有对君王的昏庸行为展开批评。但袁枚在陕西时又写了一首《昭君》,诗云:“阴山月落夜啼乌,放下琵琶影更孤。知道君王终遣妾,将军不赐赐匈奴。”㉔此诗假借昭君口吻,说汉元帝既然不能宠幸自己,为何不将自己赏赐给将军而要便宜匈奴呢?实则批评元帝对敌国的软弱立场。袁枚此时还写了《马嵬》四首,第二首云:“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㉕袁枚在翰林院期间写了两首《玉环》诗,主要是为杨玉环开脱,但这首诗却认为,与李、杨的爱情悲剧相比,普通百姓的离别苦难要更加深重,直指玄宗误国。《昭君》《马嵬》二诗都对古代君主发出责难,这与他在江宁任职时对臣则的宣扬构成鲜明对比。
(二)随园隐居时期
袁枚37岁时经历了短暂的二次出仕,旋即因为南归丁忧而作罢,此后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归隐生活。他在43岁这年,一口气创作了13首七绝咏史诗。诗人写这些诗的时候,并不处于外出壮游的状态,所以都是书斋写作。虽然缺少江山之助,却并不意味着这些诗缺少灵机,反而在诗酒田园的生活状态下,英雄气质与批判精神都得到进一步发扬。在此之前,袁枚的性灵诗学理论已见雏形㉖。再看这13首咏史诗,多写古人性灵之事,恰是袁枚性灵思想的缩影。
例如《朱买臣》云:“采薪歌罢雪花飘,五十登朝气转豪。杀得张汤刀笔吏,一行功已敌萧曹。”㉗此诗写朱买臣为给朋友严助报仇,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害死张汤。《张禹》云:“羽卫传呼谒太师,九重请训万人知。先生开口君王拜,床上深深托女儿。”㉘此诗写张禹为能经常见到女儿,竟然请皇帝将女婿调任到离京城更近的地方。《陶弘景》云:“楼上三层道气浓,永明求禄枉匆匆。先生绿鬓方瞳意,可在乌纱骨相中?”㉙此诗写陶弘景虽享无上恩宠,却仍坚持归隐山中。这些都是七言绝句,篇幅有限,便只写他们一生中最见性情的事迹,正体现出袁枚对真情热血的青睐与推崇。
(三)晚年时期
乾隆四十三年(1778),袁枚63岁始得一子,自此之后重新开始外出漫游。次年春,携幼子回杭州故里游览。四十七年(1782),约诗弟子刘霞裳同游天台、雁宕。四十九年(1784)又作远游,南下两粤。袁枚在这三次出游中,寻访了不少名胜古迹,共写下四十余首咏史诗。随着年龄的增长,诗中的热血逐渐衰歇,但真情并未泯灭。随着袁枚阅历日丰,对世事看得越来越透,热血战斗的激情转变为冷静反思的力量,从批判别人转变为批判自己,这也使其咏史诗的思想内容老而弥醇。
上文已述,袁枚在21岁去往桂林的路上曾路过严陵钓台,对严子陵表达了少年人常有的歆羡与仰慕。但在乾隆四十七年他67岁时,又一次来到严陵钓台,写下《重登钓台》和《再题子陵庙》三首,却表达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再题子陵庙》之二云:“未必无心助文叔,巢由两个误狂奴。”袁枚认为严子陵本来有意出仕辅佐刘秀,却为巢父、许由所“误”,看来他对严子陵归隐的抉择已经不以为然,与之前迥然有别。如将此认定为“性灵派诗人一大惯技”㉚,恐怕会大大误解随园老人的深意。其实所谓“误”,在袁枚早有所感。《随园诗话》卷九云:“鄂公拈香清凉山,过随园门外,指示人曰:‘风景殊佳,恐此中人,必为山林所误。’有告余者。余不解所谓。后见宋人《题吕仙》一绝曰:‘觅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方悟鄂公‘误’字之意。”㉛袁枚对自己是否真为山林所误,是有过反思与省察的,并非一味以归隐高节自我标榜。他对隐士行为的反思,实际也是对自我人生的反思。他在自己年逾花甲之时,去推翻这样一个曾带给他最多荣耀的身份,该是何等艰难。但他不但做到了,还做得很绝。再看《再题子陵庙》之三:“牛牢高获俱同隐,只有斯人事独彰。惹得邺侯还艳羡,也思一枕共君王。”㉜牛牢和高获跟严子陵一样,都是刘秀的旧友,也都在刘秀取得天下之后归隐,但只有严子陵独享盛名。照此推理下去,严子陵的成名实则包含多种偶然因素。《重登钓台》又说严子陵是“圣世辞官易得名”㉝,这也完全可用来说袁枚自己。他对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名,看来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没有首先归因于自己的才情和智慧。
到嘉庆二年(1797),袁枚82岁,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他的最后一首咏史诗是《读孔子世家》,诗云:“尼山道冠千秋处,妙在平生不著书。”㉞诗人认为孔子的伟大,恰在于“述而不作”。这对于已经留下四千多首诗和几十部著作而且还常常忧虑著述湮没不存的袁枚来说,不啻为生命最后的自我反思。
三、袁枚咏史诗的性情追求
本文开篇提出性灵诗学与咏史题材的两点“矛盾”:一是抒写性情、慎用典故的主张,与咏史题材立足史学、“以学问为诗”并且难免要使用典故的特征相抵牾;二是对平凡生活的关注,与咏史题材常见的帝王将相主题相去甚远。那么,袁枚大量创作咏史诗的行为,是否对他的性情抒发构成障碍,又是否与其性灵理论形成真正的矛盾呢?笔者持否定态度。
首先,虽然袁枚在基本立场上反对以学问填诗和在诗中堆砌典故,但并未将学问、典故与性情抒写完全对立起来。总体来看,他的立场是折衷而开放的,所以,他一边说诗歌“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㉟;一边又说“万卷山积,一篇吟成”,“曰‘不关学’,终非正声”㊱。关于这一矛盾,袁枚解释道:“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㊲可见,袁枚不是在诗中排斥一切学问,而是认为诗中不应注入与诗情、诗性严重不合的考据之学;他对典故也没有一味反对,而是反对典故太生和太多,给读者造成阅读隔膜,不利于性情的传达。如像李商隐那样,既可运用典故,又能驱使才情,岂不两全其美?
袁枚曾经颇为自得地介绍自己创作咏史诗的经验:“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㊳他在作咏史诗前遍搜典籍,当然是限于既有阅读量的不足以及过往阅读记忆的缺失,才要寻求书本的帮助,获取更多创作素材,但却不把书本知识直接化为典故填入诗中,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咏史诗具有特别的自信,这份自信或许正源于他认为自己的咏史诗是富于性情与灵机的。袁枚确实有一些咏史诗不用典故,单凭诗人自身注入的情感取胜。比如他21岁出发去桂林之前所写的《钱唐江怀古》:“江上钱王旧迹多,我来重唱《百年歌》。劝王妙选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㊴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是显赫一时的江南霸主,看到钱塘江潮汹涌而来,竟命三千弓弩手向涌来的潮水万箭齐发。这固然是一种英雄气概,但袁枚却奉劝钱镠不必怒射江潮,而应将矛头对准真正的敌人——那个在汴梁建都称帝、让钱镠也不得不俯首称臣的朱温。这首诗虽有典故,却不依赖典故,单凭他这副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派头,青年才子胸中那股昂扬奋发之气就已跃然纸上。
在袁枚的咏史诗中,典故常能形成绝好的隐喻,只要典故不生僻,就能保证诗人的性情既顺畅又不失隽永地表达出来。例如袁枚在参加博学宏词试途中,经过河南开封,想到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就写了一首《大梁吊信陵君》。这首七言歌行一共32句,袁枚先用大量笔墨书写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始末,末尾却一笔宕开,冷冷抛出这样两句:“张耳灭秦封王声赫赫,原是郎君门下客。”㊵张耳在秦末乱世中重建了赵国,后来又助刘灭项,被封为常山王。这样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早年也只是信陵君门下一个普通的食客而已。这类底层人物逆袭成功的案例,最能搔到袁枚当时的痒处,所以他对信陵君的歌颂虽然长达二百多字,却根本不像这两句才真正道出诗人的心里话。可以说,袁枚正是通过这个典故,使我们了解到他当时羞于明言却又不吐不快的真实心境。总而言之,在咏史诗中,典故不一定是性情的敌人。
其次,帝王将相主题与袁枚的性情抒发也不形成真正的矛盾,因为袁枚掌握到了调节矛盾的良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以帝王将相的事迹为主,后人对他们的评价虽然也会出现个别分歧,但总体来说史书记载俱在,以主流的伦理观念和政治立场评价古人,往往会得出趋同的看法,进而形成写作套路。从积极角度讲,这些咏史套路反映了古人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的思想代表了群体的思想,其中的情感也属于群体的情感,当然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人的思想史和观念史。但袁枚所建立的性灵诗学恰恰不能容忍这种诗人主体性与诗歌个性的退却。袁枚认为诗中不能没有平凡生活的真性情,实际是说诗中不能没有一个“我”。而他偏偏又作了那么多咏史诗,歌咏对象也确实都是些帝王将相,那么他将如何避免诗人主体性的消失呢?笔者发现,他至少有两种办法。
第一,将帝王将相的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平凡化”“生活化”。袁枚只做过最基层的地方官,后来又长期在野,因此和权力中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使他论及帝王将相时,可以在士大夫群体意识之外融入平凡生活的成分,也就是以一介布衣的平凡之心看待帝王将相的内心世界,甚至重构其行为逻辑。比如上文谈到他为二次出仕而游历中原、关中,途中写了很多帝王主题的作品。当他歌咏刘邦时,发现开国雄主竟也有卸下面具的时候。当我们想象到刘邦那副临风高歌的醉态,才猛然发现,原来身为帝王,也有酒后的放纵,也有欲诉的衷肠,也有一时乍现的温情,也有难以排遣的寂寞。而当袁枚将刘邦和刘秀作比较时,再度放弃了传统的政治标准,而是特别看重刘秀对妻子与战友的温情。再比如袁枚晚年所作的《读淮阴侯传》:“灭楚身提百万师,知公含笑了无奇。英雄第一开心事,撒手千金报德时。”㊶袁枚认为,即便是亲率百万雄师亡项灭楚的功绩,对韩信来说,都不过置之一笑而已;真能令韩信快意之事,是他功成之后终于能以千金报答漂母。以帝王将相的政治逻辑来看,“灭楚身提百万师”才是韩信留给历史的深刻印迹,但一个平凡小民,却更容易被“撒手千金报德时”的情节感动。“快意恩仇”从来都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该有的情操,但却满足了平凡小民的性情释放。稍能理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政治的游戏会如何扭曲心灵、摧残人性,不能以寻常百姓的生活情感取代帝王将相的生存法则。但袁枚偏不这样,他偏要把帝王请下龙椅,将英雄看作平民,这何尝不是他对平凡生活观的一种坚持?
第二,将帝王将相化为诗人自我的“隐喻”。平凡的人生也都有喜怒哀乐,帝王将相的情感有时只是将平凡的情绪夸张、放大而已。袁枚表面是在歌咏古人,实则要将古人看作自我的化身。所以,当21岁的袁枚从杭州南下广西之时,写下了那首洋溢着英雄豪情的《吴桓王庙》。当年孙策的南下便如同眼前诗人的南下一样,虽然一位是开拓江东六郡的霸主,一位还只是前途未知的后生,但诗内与诗外的两个人是同样的意气风发,也同样在努力为自己的人生开拓全新的格局。37岁谋求二次出仕时,袁枚刚刚离开随园的诗酒温柔,又一次燃起建功立业的理想之火。这时他写到了谢安这样一位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功勋卓著的英雄人物。英雄有大功,却常有小节之失,谢安就总在游览山水时携妓同行。袁枚自己就很喜欢狎妓,所以对谢安这样放诞的行为也相当宽容。《卮言》之三就说:“奇物取大节,瑕瑜不相蒙。谢安游江左,挟妓东山东。”㊷与谢安相比,杜牧也很擅长军事指挥,不仅给《孙子》作过注,还献计平虏,取得过大胜。同时,杜牧也是个风流情种,所以袁枚在《杜牧墓》一诗中专写他的风流,并且还颇有几分歆羡之意。所谓“高谈泽潞兵三万,论定扬州月二分”㊸,就把杜牧在战场和妓馆中的两番英雄举止概括出来了。其实,袁枚是将杜牧化作自己的“影子”,让杜牧在诗酒与功名这两个舞台上都为自己充当替身。展开这些隐喻的时候,诗人得到了一种角色代入的权力,仿佛穿越到别人的时代里,走了一遍别人的路,但其实隐隐约约走的还是自己的路,也可以说是用别人的人生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以历史人物为替身,这确实使性情的抒发变得曲折而又隐晦,但唯其如此,诗人才更敢于抒写真情,因为以隐喻为伪装,反而比直陈心志的时候更加敢想敢说。
去除了“以学问为诗”和帝王将相主题这两重干扰,也还难以真正理解到袁枚咏史诗与其性情人生的全部关联,因为它们都属于诗歌本身的形式或内容特征,没有触及诗人的性格特质。既然诗写性灵,那么诗中真性情的展开方式必然在根本上为诗人的人格气质所决定。诗人内心真诚,诗才能写出性情;诗人内心虚伪,诗就会遮蔽性情。进一步讲,诗人内心天真,则诗中性情往往简单率直;诗人内心老练,则诗中性情每每复杂隽永。这个道理在袁枚的咏史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上文前两部分的论述,运用了最为常规的“知人论世”之法,将袁枚的咏史诗创作历程与其人生起伏相对应,而人生起伏的背后正是袁枚的一部性情成长史。我们将其人生以初次归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也正是以其性情的成长状态为依据。在前半期,他或是天真幼稚得可爱,或是虚伪诡谲得可怕,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到后半期,生活给了他更多的自信与悠游,其性情才变得富于魅力,可谓壮而益真、老而弥醇。
具体而言,袁枚在参加博学宏词试之前,走在漫游南北的路途上,是那样简单而真诚,在对古代豪杰的歌咏中也寄寓了自己的理想与自负。但年轻人的心志宣泄虽然乐观向上,却又容易千篇一律。因为即便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诗人,通常也都有一个青春无敌的少年时代。这时的性情虽然真诚,但未必令我们欣赏。尤其是当青年才子遭遇博学宏词落榜和外放知县这两轮打击的时候,不论是他流落京城还是在南京候任,诗中性情都迅速蒙上阴影。什么豪情,什么壮志,全都被现实打败,我们才发现他之前的青春激情是何等幼稚。而幼稚,作为真性情的敌人,通常不易觉察,因为它总是伪装成乐观豪迈的样子,使人们误以为那就是他的本真自我,觉得他未来的性情人生都在少年时代埋下了伏笔。不要忘记,青年才子们除了高唱美好未来,还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小聪明,所以袁枚在翰林院期间沾染了清谈的风习,也总爱写一些充满翻案意味的作品。炫耀聪明这件事本身就带点儿虚伪的色彩,因此我们很难说那种为翻案而翻案的咏史诗真正符合性灵诗学的宗旨。他的“灵机”不发端于他的“性情”,就会变成虚伪的抖机灵。但比幼稚乐天和炫耀机智更可怕的,是他对性情诗的彻底背叛。他在任职江宁时期所写的《咏史》六首,对汲黯的咒骂,对桓谭的嘲笑,让我们读过之后,背后隐隐发凉。如果这些观点出于小人之手,我们也还能接受;出于袁枚之手,你才会发现生活的诡异和人心的荒诞。我们不禁会问:当初那个青年才子是如何在官场重压之下变成这副模样?所以,幼稚乐天、炫耀机智和彻底背叛这三者,都属于性情尚未完善的状态。真正使袁枚的性情完善起来的,是他初次归隐的那三年。很多研究者会低估这三年的意义,但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作的分析,二次出仕时的袁枚已经和江宁时期判若两人。
在二次出仕和隐居随园时期,袁枚的咏史诗充满批判性,也唤醒了真性情。批判性使其彻底有别于官场的虚伪做派,而此时的真性情又被自信和自由的心满满地滋润着,因此真有了一种手挥羽扇、气定神闲的样子。唯一令我们失望的,是他在此阶段删改了南京候任时期那些抑郁阴暗的作品。以他一个中年人的心智,当然会对自己当年的幼稚不满。但一个彻底具有真性情的人,不应去遮掩自己的过去。真正令笔者佩服的真性情,应是他老年时期的心态,是那种对自己一生做出反思的勇气。王昶曾评价袁枚的诗,说他“才华既盛,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不必尽遵轨范”,这大概能对应袁枚初次归隐之前的状态;又说袁诗“清灵隽妙,笔舌互用”,意思是袁枚还能摆脱简单的逞才,而达到隽永的高度,这很符合他初次归隐之后的状态;而王昶评语的最后一句则说袁诗“能解人意中蕴结”㊹,这就最符合袁枚老年时的心灵境界了。
袁枚讲诗中要有性情,那么我们读袁枚的诗,怎么能不研究他的性情成长史呢?因为对一个真正的性灵诗人来说,他的人生便是他的性灵,他的性灵便是他的诗。以人生况味来衡量性灵诗作的水准,才是比较符合诗学规则的鉴赏手段,至少从咏史诗这个维度来看是这样。
① 笔者统计《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得知赵翼存诗五千余首,其中咏史诗有240首,占比不足5%。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⑱⑳㉑㉒㉓㉔㉕㉗㉘㉙㉜㉝㉞㊴㊵㊶㊷㊸ 袁 枚 :《小仓山房诗文集》,上 海 古 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第1页,第2页,第4页,第12页,第17页,第1826页,第34页,第33页,第31页,第33页,第34页,第32页,第43页,第80—82页,第86页,第153页,第163页,第168页,第171页,第306页,第306页,第307页,第737页,第736页,第1063页,第1页,第12页,第628页,第172页,第177页。
⑮ 宋致新:《袁枚的思想与人生》,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2页;贾君:《袁枚咏史怀古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17—18页。
⑯陈正宏:《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⑰⑲ 袁枚:《双柳轩诗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新编》第1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第14页。
㉖ 王英志:《袁枚暨性灵派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㉚ 张健:《袁枚诗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㉛㉟㊲㊳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第326、146页,第146页,第20页。
㊱ 刘衍文、刘永翔:《袁枚续诗品详注》,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6页。
㊹ 王昶:《湖海诗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