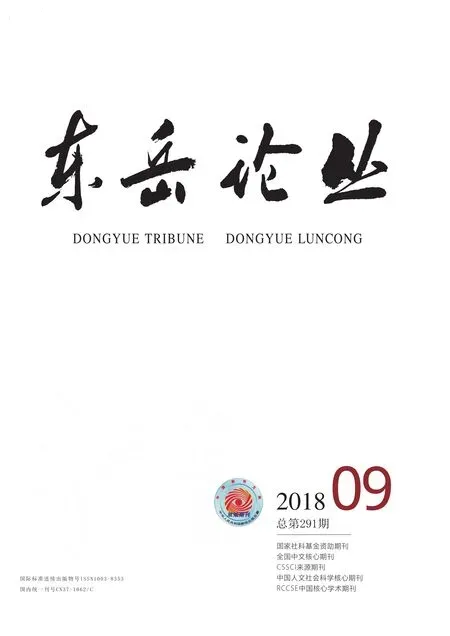荀子姓名再辨正
2018-02-28路德斌
路德斌
(山东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
清代的学问以“考据”而闻名,至今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考据”不仅是一门学问,似乎更意味着事实和真相。但遗憾的是,在荀子姓名问题上,清代考据学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非但没有把问题引向清晰,相反,却使问题愈加变得扑朔迷离,愈加令人无所适从。故在此,本文尝试作出重新梳理和辨正,在努力还原真相的同时,亦可一窥清代考据学之局限和不足。
关于荀子的姓名,过往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第一,刘向改“荀”称“孙”,究属何故?第二,“荀卿”之“卿”,是尊号、官称,还是荀子的字?以下,我们的论述也从这两个方面依次进行。
一、刘向改“荀”称“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司马迁作《史记》,凡有涉荀子者,皆称“荀卿”;刘向校雠荀书,定著三十二篇,名《孙卿新书》,所撰《孙卿新书叙录》曰:“孙卿,赵人,名况。”改“荀”为“孙”,且首谓其名。之后,汉代学者多从刘向,以“况”为名,改“荀”称“孙”,如扬雄《法言》、王充《论衡》、班固《汉书·艺文志》、应劭《风俗通义》等等,或曰“孙卿”,或曰“孙况”,或曰“孙卿子”。但自开唐以来,随着颜师古、司马贞“避讳”之说影响渐广,学者们复纷纷改“孙”称“荀”。至中唐,杨倞首为荀书作注,在刘向校本基础上,“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子》(或作《荀卿子》)”*(唐)杨倞《荀子注序》。。“荀子”“荀卿”之称遂渐成主流并习用至今。不过,需要留意的是,杨倞的改动仅限于书名,本文中依然保留了刘向校本对荀子的称谓——“孙卿”或“孙卿子”*今本《荀子》中,唯《强国篇》“荀卿子说齐相曰”一处,“孙”作“荀”。孙诒让《荀子札迻》曰:“卢云:‘此七字元刻无,从宋本补。’……但以全书文例校之,‘荀’实当为‘孙’耳。”。
毫无疑问,刘向撰《孙卿新书叙录》时,《史记》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孟荀列传》中“荀卿”一节几乎被全文捃摘便是明证*其实并非只《孙卿新书叙录》如此,《管子叙录》、《韩非子叙录》、《列子叙录》亦是如此。。既如此,那么刘向为何不继续沿用《史记》“荀卿”之称谓而改“荀”为“孙”呢?史料中找不到刘向本人任何只言片语的解释。“荀”“孙”之争,由是起焉。
概括言之,围绕“荀”、“孙”之争,自唐迄今,先后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解读和说法。说略如下:
①避讳说。这是对刘向以来由“荀”改“孙”问题作出的最早回应。唐初颜师古注《汉书》,其于《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三篇”下作注:“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其后,司马贞《史记索隐》亦从此说,曰:“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此说一出,悬疑似解,历宋至明,渐成定论。不仅杨倞更名《荀子》系因是之故,即便清代乾隆年间的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以颜、司马之说为正解,曰:“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
要之,依颜师古和司马贞的说法,“荀卿”之“荀”实为本姓,刘向改“荀”为“孙”,是在避汉宣帝刘询之讳;凡今所见古书有谓“孙卿”、“孙子”、“孙卿子”者,亦皆汉人为避宣帝讳而改。
②音转说。这是继“避讳说”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解释。最先提出“音转说”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载曰:“《楚元王传》:‘孙卿。’师古曰:‘荀况,汉以避宣帝讳改之。’按汉人不避嫌名,‘荀’之为‘孙’,如‘孟卯’之为‘芒卯’、‘司徒’之为‘申徒’,语音之转也。”*(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7页。嫌名,《礼记·曲礼上》郑玄注曰:“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汉宣帝名“询”,“询”与“荀”,字异而声同,乃嫌名者也。在顾氏看来,汉人不避嫌名,故颜师古避讳之说不能成立。依其之见,汉人改“荀”称“孙”,实由“语音之转”使然。之后,乾隆朝谢墉亦认同此说,并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和论证,其言曰:“荀卿又称孙卿,自司马贞、颜师古以来,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故改‘荀’为‘孙’。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书本字,讵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改称之?若然,则《左传》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汉书》任敖、公孙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骜’也。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比,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清)谢墉:《荀子笺释序》,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抱经堂丛书》影印版。
音转之说,从者甚众。刘师培《荀子斠补》云:“‘孙’者,‘荀’字之转音也。唐人不察,以为‘荀’字作‘孙’由于讳汉讳,……此大误也。近谢氏墉以为‘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其说近确,惟未得确证。今者《论语·乡党篇》‘恂恂如也’,汉《刘修碑》其作‘于乡党,逊逊如也’,‘孙’即古‘逊’字。此即‘荀’、‘孙’古通之证。故《史记》作‘荀’,本书作‘孙’,是犹‘處子’亦作‘劇子’,‘環淵’亦作‘蜎子’,‘宓子’之‘宓’与‘伏’同,‘筦子’之‘筦’与‘管’同也。”*刘师培:《荀子斠补》,见《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页。
江瑔作《读子卮言》,谓谢墉“音同语易”之论“其说甚通”。曰:“古人于音近、音转之字,均可通用,故古人姓名往往载籍互异。余昔撰古书人名、地名《异文释》二书,蒐罗綦详,而释其异同之故。‘荀’、‘孙’二字,古音同部,故古书多通假。考《论语》‘其于乡党,恂恂如也’,《刘修碑》作‘逊逊如也’。‘荀’之为‘孙’,犹‘恂’之为‘逊’矣。”*江瑔:《读子卮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陈垣《史讳举例》亦作赞助之论,曰:“汉不避嫌名。……《史记·荀卿传》,《索隐》曰:‘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也。’《汉书·艺文志》孙卿子注、《后汉书·荀淑传》注皆谓‘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亦非也,此唐人说耳。《荀子·议兵篇》,自称‘孙卿子’。《后汉书·周燮传序》有:‘太原闵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资财千万。’《刘平传》作‘郇恁’。西汉末人,何尝避‘荀’!‘荀’之称‘孙’,犹‘荆卿’之称‘庆卿’,音同语易耳。……嫌名之讳,实起于汉以后。”*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3页。
要之,“音转说”亦以“荀”字为本姓,但认为汉人由“荀”称“孙”,非为避讳,而乃“荀”、“孙”音同或相近,或同部通假,或方音习久,语遂移易而然。
③荀孙皆氏说。至晚清,胡元仪又提新说,其作《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曰:“谢东墅驳‘郇卿’之称‘孙卿’不因避讳,足破千古之惑。以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则仍非也。郇卿之为郇伯之后,以国为氏,无可疑矣。且郇卿赵人,古郇国在今山西猗氏县境,其地于战国正属赵,故为赵人。又称‘孙’者,盖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也。……由是言之,郇也,孙也,皆氏也。战国之末,宗法废绝,姓氏混一,故人有两姓并称者,实皆古之氏也。如陈完奔齐,《史记》称‘田完’;‘陈恒’见《论语》,《史记》作‘田常’;‘陈仲子’见《孟子》,《郇卿书》‘陈仲’、‘田仲’互见;‘田骈’见《郇卿书》,《吕览》作‘陈骈’。陈、田皆氏,故两称之。推之‘荆卿’之称‘庆卿’,亦是类耳。若以俗语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为言,尚未达其所以然之故也。”*(清)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页。
胡氏本唐人林宝《元和姓纂》所述,认为“荀卿”之“荀”,本字应为“郇”,乃周文王十七子郇伯之后。但后来作“荀”,则非《姓纂》所云“去邑为荀”之故,而是“传写相承,久而不改”使然。至于“郇”、“孙”之争,胡氏既不赞成“避讳说”,也不认同“音转说”,而是主张荀孙皆氏、两姓并称。但胡氏又认为,因各国公孙之后皆有孙氏,若以“孙”称之,则有“不明所出”之惑,故“后人宜称郇,以著所出。”
较之“避讳说”和“音转说”,胡氏的“荀孙皆氏说”可谓应者寥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即持“以‘孙’为氏”说,曰:“荀书《议兵篇》称‘孙卿子’,此自著其氏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然招来的批评却是接二连三,既多且猛。如刘师培即曰:“近胡元仪作《孙卿别传》,以为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则说较唐人为尤谬矣。”*刘师培:《荀子斠补》,见《刘申叔遗书》,第939页。江瑔亦认为胡氏之说“殊悖于理”,曰:“古者姓之外有氏,氏所以别子孙所从出,然未有一人同时而有二氏者。而载籍传述之不同,则由于音近、音转之字而移易,‘陈’‘田’、‘荆’‘庆’亦皆古音同部者也。若谓人有二氏,奚为二氏必为音近之字耶?‘荀卿’之为‘孙卿’,犹如‘管子’之为‘筦子’,‘孟子’之为‘黽子’。‘管’‘筦’、‘孟’‘黽’音皆相近,若如胡氏说,将谓管子别氏为‘筦’,孟子更氏为‘黽’耶?胡氏知‘浮丘伯’之为‘包丘伯’,‘浮’、‘包’音同,而于‘荀’、‘孙’则强分之,亦可谓好于立异者矣。”*江瑔:《读子卮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蒋伯潜作《荀子略考》,于谢氏说和胡氏说兼有取舍。其言曰:“荀氏,古郇伯之后,字本作‘郇’,其又作‘荀’或‘孙’者,一音之转尔。”*蒋伯潜:《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④“孙”为本姓说。这是基于“音转说”之上衍生而出的一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是对“音转说”的修正或补充。与“音转说”一样,此说亦不认同唐人颜师古、司马贞的“避讳”之论,而认为“荀”、“孙”之间是一种音转、通假关系。但与之前的“音转说”有所区别的是,此说认为荀子的本姓并不是“荀”而是“孙”。如梁启雄《荀子简释》即曰:“古书均作‘孙’,独《史记》作‘荀’,疑‘孙’为本字,以音同转为‘荀’耳!”*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2页。廖名春也认为:“荀子应该姓孙而不应姓荀。因为从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除《史记》外,其他文献多作‘孙’,鲜作‘荀’。特别是《荀子》一书,都称‘孙’,这即使不全是荀子亲手所写,至少也当是荀子弟子所记,他们的记载较司马迁说应更可靠。韩非为荀子学生,其著作《韩非子》称其师之姓氏也为‘孙’,这与《荀子》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好,还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时代先后、数量的多寡也好,‘孙’都应该为本姓。”*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故在持此说的学者看来,刘向改“荀”称“孙”,并非为避讳,而是在复其本姓而已。
综观四说,皆有所据,各有拥趸,若无确凿新证,恐亦终难定论。但可以预见的是,今后的争论仍将主要在“避讳说”和“音转说”之间展开。不可否认,单就“音转说”本身说,其所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若将之放在真实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则似乎仍有证据不足、说理未融之处。在此,略申两点管见,供权衡和思考。
第一,虽然有清以来,颜师古、司马贞“避讳”之说频遭质疑,且大有被“音转说”取代之势,但若质诸历史,穷究原委,则知其为说同样是言有所依,论有所据,绝非是简单的一句“此唐人说耳”所能打发了的。考之史籍,宣帝刘询曾于元康二年下过一道避讳诏书。诏曰: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3页。
汉宣帝,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因“病”、“已”二字太过常用,百姓不易避讳,故特下此诏,更名讳“询”。毫无疑问,对于“荀”、“孙”之争来说,此一事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不知何故、不可思议的是,在质疑“避讳说”的过程中,此避讳诏书却鲜被提及和考虑。反思说来,此一史实之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若无,由“荀”改“孙”,原因或可两说;既有,那么刘向因避讳而改“荀”称“孙”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观宣帝诏书,在昭告天下“其更讳询”的同时,还传达了两个非常重要、不可忽略的讯息:其一,当时,“触讳犯罪”在律法上显然已有明文规定,且有大量事实发生;其二,只有“上书触讳”才是犯罪,非“上书”者,应可不讳*(清)刘恭冕:《汉人避讳考》曰:“观此,知当时例禁惟上书触讳为犯罪,而民间文字皆不讳,可知矣。”(《宝应刘氏集》,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566页。)。明乎此,则避讳称“孙”之事之于刘向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刘向校书并非私人行为,而是奉诏行事*(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所撰叙录也非寻常临文或民间文字,而是“随竟奏上”*(梁)阮孝绪:《七录序》:“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故于每篇叙录的最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句大致类似的“下言”——“臣向昧死上”。毫无疑问,刘向校书及叙奏正属于臣下“上书”之列。君讳之事,性命攸关。虽说奉诏校书已然是成帝之时,避宣帝讳已属庙讳,但按规制却在必避之列。一如陈垣《史讳举例》所言:“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9页。有避讳诏文在,有律法条文在,作为光禄大夫的刘向,上书奏事安敢有轻慢、不避之理?
诚然,“音转说”用以否定“避讳说”的最重要论据是“汉人不避嫌名”,宣帝的诏书也确实未曾明言嫌名是否在当避之列。但这并不能构成足够的证据,因为“汉人不避嫌名”并非一确定之事实。汉武帝讳“徹”,“徹”字改为“通”,同时并讳“辙”字。清人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认为此乃“避嫌讳之始”*(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其实,如同任一事物的形成皆有一个过程一样,嫌名避讳之初肯定也并非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状态——要么不避、要么尽避。也即是说,汉人到底避不避嫌名,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实际的情形恐怕应该是,有避,但不尽避。所以,就汉代来说,纵有再多不避嫌名的个例存在,也不能证明刘向改“荀”称“孙”一定不是因避讳而为之。更何况从刘向本人的具体处境来看,避之比不避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一切通避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做法,是情理之中,应然,不得不然。
第二,就实而论,“音转说”与“避讳说”之间也并非是非此即彼、互为否定之关系。依“音转说”的理路,汉人由“荀”称“孙”乃是方音、习俗中之自然而然之过程。但事实恐非如此。改“荀”称“孙”起于刘向,唯有不离刘向及其语境而作出的分析和结论才是最接近于事实的。而这个语境并不是“音转说”基于其上并作出判断的方音、习俗,而是作为背景和前提存在的司马迁的《史记》。
毫无疑问,《史记》之于刘向,并非口耳相传。刘向谙熟《史记》,其撰各篇《叙录》,亦几将《史记》中之相关原文全数引录。既如此,问题就来了。面对《史记》“荀卿”列传,刘向在照录本文的同时,又怎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把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荀卿”拼读并抄写成“孙卿”而且在之后不曾作出解释和改正呢?案牍之上,“荀”、“孙”移易而不觉,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那么退一步讲,刘向改“荀”称“孙”会不会是单纯基于方音、习俗的原因而有意作出的改动呢?若此,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的问题:刘向会宁可舍弃《史记》中的规范称谓而去迎合方音习惯、使用一个俗音不正的字吗?其必要性和意义何在?
所以,在刘向改“荀”称“孙”问题上,起码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这不是一个在方音、习俗中的自然而然、习而不觉的过程,刘向改“荀”称“孙”是自觉意识中的刻意而为,而且是不得不为;其二,这个刻意为之而且不得不为的原因一定不是“音转”,而是另有其因。如此而然,那么这个令刘向必须为之而且无须作出任何解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避讳!在刘向的语境之下,除此而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种更加合理的解释。也即是说,刘向改“荀”称“孙”,非为其他,而实如《四库提要》所云,“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若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怎么避?按照什么样的方法避?答案是:“音转。”这,才是“音转说”真正出场并发挥作用的地方。古人避讳所用的方法有多种,并没有一定之规,陈垣《史讳举例》归纳为四类,王新华《避讳研究》梳理出来的方法则有十二种之多。而刘向在这里所依循的方法便是“音转”,也即是用方音习惯中的一个音转之字假借而代之。
由此以见,“音转说”与“避讳说”之间,其实并不必然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二者不仅在理论上有可以相互兼容和会通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可能恰恰就是同一历史事件及其脉络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质言之,“音转”并不是刘向改“荀”称“孙”的原因,而是刘向为避宣帝嫌名之讳所使用之方法*当然,反思说来,“音转”也并非是刘向唯一可以采用的方法,“以氏为姓”同样是一个可能的选项。郑樵《通志·氏族略》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若如胡元仪所考,荀子乃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则刘向为避宣帝讳,亦可能以氏为姓,以“孙”代“荀”。由此以言,“避讳说”与胡元仪的“荀孙皆氏说”之间,亦有可会通之处。。
二、“荀卿”之“卿”到底是何含义
在姓名问题上,除“荀”、“孙”之争而外,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围绕“荀卿”的“卿”字进行的。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或历朝典籍中,对周秦诸子的称谓一般并无二致,要么直呼其“名”,如孔丘、庄周、墨翟、孟轲;要么尊而称“子”,如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等。而荀子的称谓却有些许不同,在呼名称子(如荀况、孙况、荀子、孙子)的同时,汉代又常被称作“孙卿”、“孙卿子”,其他朝代则常被称作“荀卿”、“荀卿子”。因此,在对荀子“名况”向无异议的情况下,“卿”字的涵义如何便时常成为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一个问题。梳理可见,自唐以来,围绕此议题所形成之观点,大致可分成三派,亦述略如下:
①“卿”为尊号说。司马迁作《史记》,孟、荀同传,但称谓有所区别,前者称“子”,后者曰“卿”。“子”乃尊称,塗人皆知,无须解释;那么,“卿”者何谓?司马迁未作说明,后人也不甚了了,但很显然的是,在当时,司马迁眼中的“卿”字和“子”字一样通晓易知,无须作解。至成帝时,刘向校理荀书,作《叙录》,在姓名问题上,较《史记》出现两大变化:一是改“荀”称“孙”;二是首言“名况”。但“卿”字依然袭用,曰:“孙卿,赵人,名况。”既然“况”为其名,那么“卿”字到底何谓呢?刘向同样未作说明。直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卿”字的涵义才终于有了第一个明确的说法。于列传“荀卿”之下,《索隐》曰:“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曰‘卿’也。”“况”为其名,“卿”乃尊号。此说一出,千年间再无异议。不过,从史籍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看,似乎也并不都是或总是将“卿”字视为尊号。在一些学者看来*即持“卿为其字说”的学者们,如江瑔、钱穆等。他们认为,若“卿”为尊美之词,“子”亦为尊美之词,则“既曰‘卿’又曰‘子’,则不词矣。”,最典型的用例就是“孙卿子”和“荀卿子”。在“卿”字后面加“子”,即意味着使用者眼中的“卿”字并非尊称。其实,更无疑义的用例是宋代的二程和朱熹。程、朱扬孟而抑荀,对荀子极尽苛责和诟病,因此从态度上说,实无推尊、敬佩之可言,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于言谈之中,他们经常称荀子为“荀卿”。不消多说,此类情况之存在正是催生新的解读或说法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为新说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解释的空间。

③“卿”为其字说。学术界一向以刘师培、江瑔为此一说法之始作俑者,其实在稍早一些的章太炎那里,此说已经发其肇端。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即有言:“刘子政《荀子序》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按《汉书·儒林传》云:‘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旁注:师古谓时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亦备一说。)此兰陵人喜字为卿之证。”*《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卿为其字”之意已隐约可见,呼之欲出。其后刘师培、江瑔的工作实乃是此一意念或主张之具体论证和正式表达。所以,较之章太炎,二人的观点已然确定而鲜明:“卿”字既非尊号,也非官称,而是荀子的字。如刘师培《荀子斠补》即曰:“‘况’为荀子之名,则‘卿’为其字。……以‘卿’为相尊之称,此大误也。……据本篇(即刘向《孙卿书录》——笔者注)后文云:‘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此即字卿名况之确证。若以称‘卿’由时人相尊,则‘卿’与‘子’同,非孙况所能专,弗应兰陵人竞取为字也。”并作注论证:“《说文》及《广雅·释言》云:‘卿,章也。’况与皇同。《诗·周颂·烈文》毛传云:‘皇,美也。’是卿、况义略相符,故名况字卿。”*刘师培:《荀子斠补》,见《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页。江瑔《读子卮言》则曰:“古人有名必有字,孟、荀之字均不见于古籍,窃谓‘卿’者即荀子之字也。古者名字相因,王引之作《春秋名字解诂》,蒐录甚详,而证其相因之义。‘卿’与‘况’皆同部字,其义均为长为大,故名况字卿。……刘向《叙》曰:‘兰陵人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云云,此为荀子字‘卿’之确证。刘向不言兰陵人‘喜名为卿’,而曰‘喜字为卿’,则‘卿’为荀子之字可知。盖荀子本字‘卿’,兰陵人向往遗风,故争以荀子之字为字,以示不忘典刑之意,如孟卿之流是也。若以‘卿’为卿大夫之称,则‘卿’非荀子所固有,奚为效之?且如其说,必曾为卿而后可称‘卿’,兰陵人未曾为卿,何以侈然而为卿大夫之号?兰陵人素知礼,断不若是之无耻也。况古有荆卿,亦称‘庆卿’,豈亦曾为卿乎?”又曰:“《荀子》书多称曰‘孙卿子’,《汉书·艺文志》及《隋书》《旧唐书》《经籍志》亦皆曰‘孙卿子’,《唐书》《宋史》《艺文志》又皆曰‘荀卿子’。其称‘子’者,尊美之词也。‘卿’为尊美之词,‘子’亦为尊美之词,既曰‘卿’又曰‘子’,则不词矣。是可见‘卿’为荀子之字,而非卿大夫之称,故可曰‘孙卿子’或‘荀卿子’。”*江瑔:《读子卮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61页。
以上即是围绕“荀卿”的“卿”字所形成的三种历史解读。从学术界的反应和所呈现的影响看,第三种解读即“卿为其字说”的解释力无疑是最强的,故今之学者多从此说*如钱穆之持论即全从江瑔,其《孟子不列稷下考》一文即曰:“荀子称卿,自为其字。刘向《叙》曰:‘兰陵人喜字卿,盖法孙卿。’此荀子字卿之确证。燕有荆卿,不闻其为卿。荀子书多称荀卿子,子者尊美之词。若卿已为尊美之词,既曰卿,又曰子,则不词矣。”,著述言谈之间,似乎已成定论。但话又说回来,一种解释力最强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它也是最正确的呢?其实未必。由反思可见,“卿为其字”说也确实不能真正令人心安理得,因为其所使用的证据事实上没有一条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从“名字相因”、“义略相符”论证“名况字卿”,没有事实,仅凭推论,看似有理,实为臆断*参见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3页。。当然,除此而外,“卿为其字说”还有两个引以为切实而充分的证据:一即所谓的“确证”——“兰陵人喜字为卿”;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卿”、“子”连称。但事实上,这两条看似可靠的证据同样有甚可质疑之处。比如前者,就很难说是一个“确证”。“兰陵人喜字为卿”当然与荀子称“卿”有关,但与“卿”字是否是荀子的字却没有确定而必然的关联。对兰陵人来说,“卿”就是一个与其人相关并因其人影响而颇受人们喜爱的一个字,这就足够了,至于它在荀子那里到底是名、是字、是官称还是尊号,其实并不重要,也未必能搞得清楚。即如学者所言,“以‘卿’为字,不一定必须据其字为字”*参见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3页;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至于后者,问题就更大了,把历史上“卿”、“子”连称的情况当作证据来使用,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逻辑上“倒果为因”的错误。因为在司马迁和刘向那里,荀子仅被称作“荀卿”或“孙卿”,称“孙卿子”、“荀卿子”应是后来的事情*《荀子》本文中的“孙卿子”和“荀卿子”,以颜师古、司马贞“避讳”说推之,亦当是刘向之后改窜使然。,也即是说,“卿”、“子”连称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论证并判断对错的问题,又怎么可以拿来当做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来使用呢?更何况,考之史籍,“卿”、“子”连称亦未必不词。近有学者*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卢永凤,王福海:《荀子与兰陵文化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就发现了一个典型用例——“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裴骃《集解》引文颖曰:“卿子,时人相褒尊之辞,犹言公子也。”其实,从司马贞《史记索隐》对“荀卿”姓名的解读中似乎也能证明裴骃所引文颖之言不虚。司马贞的原话是这样:“卿者,时人相尊而号曰‘卿’也;……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如果文本本身不存在讹窜情况的话,那么这段注解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一方面云“卿”为尊号,另一方面对“卿”、“子”连称却丝毫不以为意。这说明什么?说明“卿子”之称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为人们普遍熟悉并接受的概念。若果如江瑔、钱穆等所言,二字连称为“不词”,则司马氏断不会有“卿”为尊号之语,否则,前后抵牾之明显,错误也实在太过低级了。司马贞不至于此!
其实,判断“卿”字本义的最可靠的方法还是要回到最初的语境即司马迁的《史记》中去考察。司马迁对待孟、荀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用清代学者粱玉绳的话说,即叫做“孟荀齐号”。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称前者为“孟子”,称后者曰“荀卿”。那么,以“孟荀同尊”之理推之,“荀卿”的“卿”字与“孟子”的“子”字一样,首先而且肯定是一个尊美之辞。“子”为尊称而“卿”却为其字的情况理应不会出现,这是其一;其二,但如果“卿”字仅仅只是一个与“子”字一样的尊美之辞的话,那么司马迁也大可不必在“子”字以外另择“卿”字而用之,统以“子”称,岂不更加简洁明了,而且符合习惯和常理?所以毫无疑问,在这里,“荀卿”的“卿”字除了具有与“子”字一样的尊美之义外,它一定还有另外的意义。也即是说,在司马迁的眼里,“卿”字之于荀子,一定是一个比“子”字更加贴合其身份、更能表征其个人属性的概念。那么,较孟子或其他诸子而言,荀子到底拥有怎样一种用“子”字无法表征、但用“卿”字却能够表征的身份或独特性呢?说出来其实无人不知,那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稷下学宫,百家荟萃,名士云集,然而在前后约一百五十年间,能享此殊荣者,唯荀子一人而已。如此荣耀而独特的身份及寓意,一般意义上的尊称即“子”字显然是无法涵盖和呈现的,于是便有了唐人司马贞向我们揭示的另一个事实——时人相尊而号曰“卿”。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曰“荀子”而称“荀卿”,缘由即在于此!如此而然,则“卿”字之本义也就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了。首先,“卿”之于荀子,并非其人之字,而是如“子”字一样,是尊美之辞;其次,但它同时确实又与“子”字不同,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官职色彩。因为此尊号之获得,几乎可以肯定是与其“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独有经历相关。而之所以又说是“某种程度”,是因为荀卿之“卿”毕竟与体制之内拥有实际权责的职官不同,虽为学宫之长,但与赐号“列大夫”的稷下诸先生一样,皆属于“不治而议论”之列。
如此说来,汪中、胡元仪的“卿为官称”说也并非全无见地。简单、笼统地说荀卿之“卿”即是官称,固然有失偏颇;谓荀子曾适赵为卿,且法虞卿而称“荀卿”,亦难免有无稽妄断之嫌。但他们推定在“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与荀子称“卿”之间有直接而不可分割之关联,却甚合情理,当为不易之论。故在今天,若想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卿”字的本义,有必要在司马贞“尊号”说的基础上,取汪、胡之说参酌以观。当然,从逻辑上说,汪、胡之所见其实已经在“卿为尊号说”的语义涵括之中,而且在司马贞的眼里,如同在司马迁的眼里一样,应该是被当成了一件不言自明、不必作解的事情。但是,随着时空的推移和转换,“三为祭酒”与荀子称“卿”之间原本还算清晰和明确的关联却逐渐变得似有若无、模糊不清了,乃至于到最后,歧说纷出,莫知所是。所以,重新厘清并确定二者之间的脉络和关系,从而还原荀子称“卿”之事实真相和本义,实属一项必且为之而不能略过的工作,汪、胡之说的意义即在于此。
综上可见,关于荀子的姓名,虽然有清以来,新论迭出,异说纷呈,且不乏复杂而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但比较而言,还是最初的解读即唐人颜师古、司马贞之说最为切实和近理。故在此问题上,甄别取舍,仍当以颜、司之说为主,至于后起诸说,凡能与之兼容、会通者,则可引为参考和补充。准此,荀子姓名约略可知:荀子,名况,字不可考。因于稷下时,“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时人相尊而号曰“卿”,故又称“荀卿”;汉时,刘向奉诏校书,为避宣帝刘询之讳,依“音转”而改“荀”为“孙”,故又称“孙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