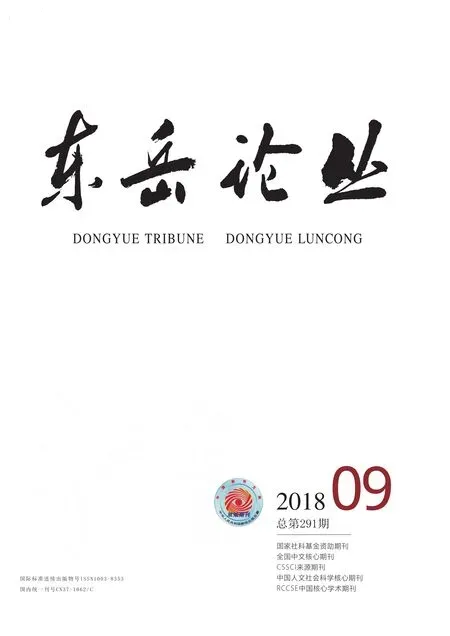贾樟柯的“信息媒介物”:身体的延伸与被围困的人
2018-02-28郎静
郎 静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电影导演贾樟柯自1996年第一部电影短片《小山回家》开始,就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念直面现实,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型中国的巨大变化。与“第五代”导演和其他同时期的导演所拍摄的一个个电影个体不同,贾樟柯通过空间、人、物的重复和互文建构了其独有的影像语言。而与人的重复相比,贾樟柯电影中器物形象及其所构成的空间的重复则成为转型中国之变*贾樟柯电影所重点呈现的转型中国的30年,正是作为消费的“物”逐渐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心的过程,物在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有力证据。贾樟柯在其告别学生时代之后的第一部电影故事长片《小武》“导演的话”中说:“摄影机面对物质却审视精神。在人物无休止的交谈、乏味的歌唱、机械的舞蹈背后,我们发现激情只能短暂存在,良心成了偶然现象。这是一部关于现实的焦灼的电影,一切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在这里,物质与精神、激情与孤独、美好与困境之间的张力,使得作为创作者的贾樟柯对物的选择并不是任意和随机的,而是串联出了转型中国之变的时间线索,并凝聚了深厚的政治寓言。特别是当我们将贾樟柯电影中的“信息媒介物”*在贾樟柯的电影创作中,被赋予了强烈审美意指且承担着电影叙事功能的信息媒介物主要代表是《小武》中的传呼机、《世界》中的手机和《山河故人》中的平板电脑。从其整体电影创作中提取出来共时并置时,在日新月异、更新换代的科技进步的合理性名义之下,其“另一面”逐渐浮出水面。
一、传呼机:被物化为金钱的人际关系
在中国,传呼机*传呼机诞生于1984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又被称为BP机、寻呼机、BB机、Call机等,据《现代汉语新词新语新义词典》的释义,它是“造型轻巧、可以随身携带的无线电报话器,能随时传递信息”。它在整个寻呼系统中,是作为终端的用户接受机,有两种接收方式:人工汇接和自动汇接。由于此两种方式都无法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手机一样自主接受信息,所以其需要靠对应的寻呼台来完成。流行于20世纪的80、90年代。1983年,中国大陆的第一家传呼台在上海出现,自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传呼机逐渐成为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一度最为流行的媒介物。至1998年,全中国传呼机用户突破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高峰时用户总数超过了8000万户*张跃辉:《寻呼往事》,《通信世界》,2008年第48期。。值得注意的是,在传呼机被大多数人接受之前,不菲的价格和服务费用也使得它一度成为“高端商务人士”身份的象征,特别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当传呼机的声音响起时,马上就会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
贾樟柯电影《小武》的故事时间是在1996年汾阳由县改市的前后,正是传呼机逐渐普及为大众日常媒介物的阶段。影片中,在与“成功民营企业家”小勇所拿的“大哥大”*“大哥大”是中国对第一代手提移动电话的俗称。第一代手提移动电话诞生于1973年的美国,是由摩托罗拉公司的一位致力于通信技术研究的工程师马丁·库帊和他的团队发明。作为优越于传呼机单向传呼的“大哥大”,其即时双向的通信技术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通信时代。1987年,“大哥大”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不菲的价格一度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而成为商业人士金钱、财富和地位的身份象征符号。的对比中,小武的传呼机已经失去了话语中的优越性。这一点在小武的传呼机第一次发出声音时得到了印证。在小武的家里,父亲因为二儿子二宝将和城里姑娘办婚礼的事情向大儿子和小武提出了一人拿5000块钱的要求,父亲让大儿子和小武表态。就在大儿子不置可否地岔开话题的间歇,小武的传呼机响了。在这里,贾樟柯以50秒的长镜头呈现了传呼机从小武的手中传到了大哥的手中,从大哥的手中到了母亲的手中,再从母亲的手中传到了父亲和妹妹的手中,最后又交还给小武。在这一传递过程中众人只是“看”,除了大哥和母亲发出了“(拿)来看看”的言语,再没有更多对传呼机的所有者小武言语上的艳羡。就在传呼机传回到小武手里时,父亲的一句“老大,你表表态”立刻使得传呼机在这个家庭空间中造成的意外小插曲消解在了家庭的首要议题——二宝结婚的筹钱事宜中。这一情节与随后家里的二儿子二宝向家人散发“美国万宝路”*20世纪80年代,万宝路香烟以占据美国市场13%的销量,居于美国烟草工业的第二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万宝路作为外贸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比较其作为香烟的使用价值,其本身所携带的符号价值、身份价值则更加受到人们的追捧和青睐。香烟时所获得的言语上的优越感和家人的艳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小武》中,二宝领着城里的女朋友回到县里的家里,二宝随手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在递给父亲、大哥之后又扔给了坐在炕边缘的小武。在这组关于万宝路引发的讨论的长镜头中,影片的主人公小武一言不发,甚至鲜少出现在镜头中。在家人对于万宝路香烟所表征的身份优越性确认的对话中,小武被区隔为家庭空间的边缘人。。
于小武而言,失去了身份标识功能的传呼机成为了等待被“爱情呼叫”的媒介物*在影片《小武》中,小武购买传呼机的动因是由梅梅引发的。在KTV的包房里,小武对梅梅对小武说:“以后我天天来歌厅看你。”梅梅回说:“不用,以后你买个呼机,我有空就呼你,好吗?”小武爽快地答应了。,而恋人梅梅的突然消失则使得他对传呼机的响声充满了强烈的情感渴望。而有趣的是,贾樟柯却让小武强烈的爱情渴望发生在他实施偷窃的过程中,从而使得这种情感渴望被置换为一种危险的信号。小武被抓了,传呼机的第二次响起带来的不是小武想象中的爱情,而仅仅是一则天气预报的推送。正如天气预报的“晴转多云”,小武的心情也经历了双重的失落。当听到传呼机第三次发出声音时,小武急切地问:“上面有什么?”民警郝有亮回答:“一个姓胡的女士祝你万事如意。”至此,小武终于等来了梅梅的“爱情呼叫”,但同时,他的爱情也随之消解了。
在谈到电力媒介的革新所造成的特定文化情景时,麦克卢汉指出:“正是由于电力媒介提供了相互作用的区域,我们才被迫作为一个整体去对世界作出反应。然而,尤为重要的是,电力媒介介入的速度造成了个人知觉和公众知觉结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6页。与此前大众所普遍使用的固定公共电话相比,传呼机更新了大众对于媒介介入速度感和整体感的感知,它之于当时人们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人们之间即时的单向移动呼叫成为可能,打破了此前固定电话对信息传播时间和地点的束缚,配合了人们在空间流动中对信息接收的需求。
当我们回过头再来梳理贾樟柯的镜头中,小武是如何经由“传呼机”来建立和试图维持其爱情关系时,可以看到这种开始和结束的突兀背后的潜在逻辑。小偷小武和歌女梅梅相识于KTV包厢中,这是一个“认人唯钱”的消费空间,小武慷慨地用偷来的钱在梅梅的仰视中获得了在曾经的好兄弟(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小勇那里被践踏的尊严,而梅梅在小武慷慨地消费和细致地关怀下获得了“傍着”的依靠感。两人将金钱-身体的商品关系错认为是“爱情关系”,而根据资本无限度地追求增值的逻辑,当梅梅将其身体“物化”为资本放置在KTV的消费空间时,就已经身不由己地被纳入到不断进行交换的商品逻辑之中,因为“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梅梅换了一个更大的靠山——富有的山西商人,而小武却在传呼机的意外和“情理”的张力中变得一无所有,他不再是靳小勇的兄弟、胡梅梅的靠山,最后也被父亲梁长友赶出了家门。
二、手机:被抽象成符号的人际关系
“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是新千年前后在央视反复播出的一条“商务通”广告。这条广告直白地道出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子信息媒介在中国大众中的接受情况。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和更新换代,传呼机、商务通所起到的媒介功能都被手机所取代。正如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所言,我们不愿意忍受偷窥者汤姆的冲击,所以我们发明了窗帘。我们不甘心让电视屏幕上喜欢的形象飞逝而去却袖手旁观,所以我们发明了录像机。我们不愿意在文字的沉重压迫下洒汗挥毫,让语词从构思的那一刻其就被拴死在纸面上,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文字处理机。拉开距离一看,这些逆转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媒介自动的、必然的突变,是窗户、电视和文字遭遇到功能的外部极限时发生的突变。然而,实际上,它们是人有意为之,是人类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288页。。与传呼机单向的信息接收相比,作为一种新媒介的“手机完全斩断了把人束缚在室内的绳索。就像以前的柯达照相机、圆珠笔、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手机把它的使用者从家宅和办公室里解放出来,送进大千世界的希望之乡里去。”*[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但有趣地是,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手机所表征的这样一种个人独享的文化景观却以动画的形式向观众敞开,既敞开了私密性的文本,也敞开了当事人的身体情绪。而正是这一双重的敞开,我们得以“窥视”手机在全球联通的背后所潜藏的人际困境。
影片中,动画的六次出现均是由现实中来自故乡的打工者小桃和她的男朋友太生的手机接收短信的声音引发的,然后以虚拟动画的形式向观众投射出手机短信的文本内容和内心情绪。第一条手机短信的发收方是太生和小桃,在火车站旁的一家简陋的旅馆里,太生向小桃求爱未果便质疑小桃对他的感情,小桃负气离开,在公共汽车上收到了太生发来的短信——“看你往哪跑!”而与动画里呈现的太生带有狡黠和控制意味的语气相配合的恰恰是现实中正在去往唯一的目的地——世界公园的小桃。贾樟柯以此向我们敞开了现实中小桃所承受的来自太生和“北漂”生活的双重控制力。第二条手机短信的发收方是山西老乡老宋和太生,太生为老宋制作办理“全球通”手机卡所使用的假身份证,老宋付给太生金钱作为报酬。贾樟柯在以动画所承接起来的两个现实空间——世界公园和手机诈骗团伙出租屋的设置中,向我们敞开了漂在城市边缘的故乡人以“不法”对抗社会“不公”的“生存之道”。
第三条和第六条手机短信的发收方均是温州女人廖阿群和太生。第三条短信是因为一次长途路程的陪伴,“北漂”的温州独身女人廖阿群对太生产生了好感。在桃花泛滥的动画氛围的烘托下,一则“有空来坐坐吧,大红门浙江街7排2号2楼”的短信文本给现实中太生庸常的生活带来了意外的悸动。手机联系起了两人的暧昧关系,廖阿群在太生那里获得了长久以来因为生意上的打拼而缺失的男性的精神抚慰,太生在廖阿群那里获得了不同于小桃的新鲜感和男性征服感的自我想象。但这段关系并没有改变两人各自的人生轨迹——太生不打算和小桃分手,因而隐瞒着他和廖阿群来往的事实;廖阿群也不会为了太生放弃去法国的打算,她发给太生的最后一条告别短信是“相遇是缘,相知是福,忘不了你”。而在前后两条短信的对照中,贾樟柯向我们敞开了都市异乡人即时有效的“各取所需”商品交往逻辑。
但有意味的是,最后一条发给太生的短信的读信人却是小桃,第三方身份的出现使得手机文本和动画之间出现了情绪上的错位。动画中一条墨绿色且身体一侧一小部分鱼骨裸露的鱼在充满气泡的暗黑色水里游了一圈后离开。绿色是一种分裂的颜色,它既是新鲜蔬菜的颜色,也是臭肉的颜色。所以绿色既能代表健康与生命力,又能代表危险与衰败。因为绿色模棱两可的特性,电影创作者要谨慎依靠观众的感官反应,来运用特定种类的绿色,想清楚自己要想得到什么效果,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很重要*[美]帕蒂·贝兰托尼:《不懂色彩不看电影:视觉化叙事中色彩的力量》,吴泽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版,第252-253页。。动画中所示显然是当事人小桃心理活动的具象表现。首先就小桃而言,在小桃下定决心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太生之前,她三次向太生提到“不能骗我”,而已经和廖阿群有暧昧关系的太生却告诉小桃:“这年头,谁也靠不住,我也靠不住,你只能靠你自己。”小桃笃定地说:“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然后献出了在她看来“我也就这点资本了”的身体。这也解释了动画中的鱼身体缺失一部分的原因;其次廖阿群和太生充满跳动感的暧昧关系,对小桃而言显然是有着致命“危险”的,因此贾樟柯用墨绿色敞开了现实中小桃精神世界的坍塌。
而小桃之所以在两次拒绝与太生发生关系后做出彻底依靠太生的决定,正是影片中第四条手机短信所间接带来的结果。第四条手机短信的发收方是秋萍和小桃。被围困在世界公园里的小桃神情麻木地撑着一张塑料袋在景观建筑下的一角避雨,看到短信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即在雨中跑了起来,通过动画的插入我们看到了短信的内容——“晚上Party,接你们进城Happy”,然而现实中出现的空间却是灯红酒绿的KTV包厢,Party和Happy的主人公也不是小桃和她的姐妹们,她们“进城”的目的地是另一个把她们当做商品来看和消费的空间。小桃在拒绝了来自有钱老板的性暗示后,来到了KTV的卫生间,在这里她偶遇了安娜*贾樟柯的影片《世界》的发生空间是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世界公园,安娜是在世界公园中作为景观进行表演的俄罗斯籍演员,为了尽早筹措到去乌兰巴托寻找妹妹的费用,她离开了世界公园,到了另一个同样是把自己作为商品但价格更高的空间——KTV。,安娜的装束已然说明了一切,两人相拥而哭。在手机所连接的小桃暂时逃离世界公园的“笑”和在KTV卫生间的“哭”的对比中,贾樟柯向我们敞开了在消费景观遮蔽下小桃和她的姐妹们逃不开的身体困境。
第五条短信的发收方是太生和小桃,正在作为商品景观工作的小桃收到了来自太生的短信。在读信的小桃一脸震惊中,贾樟柯用动画敞开了在灰色冰冷的城市和沉重的资本结构下,外来打工者身体的“轻”。动画中,手机短信文本“昨夜无法回电话,二姑娘死了”的呈现是以一辆逐渐加速的火车为背景的。一方面,这自是为动画之后出现在火车站的二姑娘的父母和三明做了铺垫;而另一方面,二姑娘的死讯在作为“中国速度”象征的疾驰的火车的裹挟下失去了生命的重量。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成为一条手机短信上的痕迹,成为一笔抚恤金,成为亲人孤独而沉默的祭奠。
在当代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手机以其补偿性、私密性和身体延伸性的特质消除了空间界限,形成了一个自由、高效、便捷、亲密的社会认知和共识。而在贾樟柯的镜头中,联通人际的手机带来的却是被抽象成符号的信息和人际的断裂,在看似“全球通”的幻觉中,实则是故乡人在城市冰冷且封闭的生存困境。
三、平板电脑:被剥离了父子伦理的人际关系
莱文森曾预测,“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可以被认为是手机的副手。身体的移动性,再加上与世界的连接性——手机赋予我们的能力——可能会具有更加深远的革命性意义,比如互联网在室内带给我们的一切信息的意义更加重大。”*[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今天,这一革命意义已然得到确认,随着无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界面文本”的依赖更加强烈,而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体验,媒介的补偿性机制再次发挥了其强大的创造力,整合了手机的移动功能和电脑的大屏显示功能的平板电脑应运而生了。而媒介产品“追身”功能的强化,在周志强教授看来,是一种“谋求把自我当做一个神话来叙述”*周志强:《“私人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裂变与转型》,《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策略。在这样的一种策略下,媒介物神奇地被赋予了“人性”,从而出现了“人际关系”逐渐被“人机关系”所取代的现实矛盾。
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将这一矛盾设置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最基本的一对关系——父子之间。在2025年的澳大利亚,作为媒介的平板电脑在父亲张晋生和儿子到乐之间已经不是为远距离的交流提供便利的媒介物,而成为彼此面对面交流时对“本人”的替代。首先,从镜头的视点来看,都是以俯视的角度以代替人眼的方式完成信息发送-接收内容的呈现;其次,从父子俩分别与平板电脑发生关系的状态来看,作为物的平板电脑均居于镜头的正中间,儿子到乐仅显露出手和腿的部分,父亲张晋生则显露出手和肩背的部分。居于镜头正中间且直接作用于观众视点的平板电脑在表现出对人们日常生活全面占有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了父子关系间难以交流的隔阂。特别是当父亲张晋生试图向儿子到乐宣称自己作为父亲(Father)不可冒犯的地位时,儿子到乐的一句话“你是我的父亲,但是谷歌翻译才比较像你的亲生儿子(real son)”使得父亲无言以对的情状,则解构了镜头中张晋生对自己“大父亲”身份的想象。有趣的是,当我们对比《站台》中崔明亮父子面对面的关于“喇叭裤”的对话时,就会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到全球化发展的中国,逐渐被抽空了的“父亲”形象。
在《站台》中,父亲叫住了搬完木头准备和朋友张军、二勇外出的儿子崔明亮,语气严厉地指责儿子的喇叭裤不像样,并以“工人能干活,农民能下地”的标准坚决否决了儿子的穿着。当崔明亮又以“文艺工作者,不用干那些”为借口时,父亲不屑地说:“文艺工作者?刚给你们点自由就想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而崔明亮则以“有沟,代沟”为父子之间不愉快的谈话画下了句点。在这组动态的全景镜头中,首先,崔父占据了景框的黄金分割点上,并以身高的优势俯视着逐渐走进景框的儿子崔明亮;而走进镜头中的儿子崔明亮并没有站在与父亲并置的另一个黄金分割点上,不仅成为被父亲俯视的对象,而且塑造出了观众对父亲权威的认同;面对父亲的指责,崔明亮扭头在父亲的注视下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此时镜头没有跟随着离开的崔明亮,而是继续固定在占据景框黄金分割点的父亲的身上,直到下个场景跳转。
在这里,“父亲”不单单指伦理意义上的父亲,更指向了一个以“父辈传统”为行为逻辑的乡土中国。在《站台》中,贾樟柯通过突出父亲的视点和位置,在象征着权威的父辈传统的缝隙中暴露出逐渐显露出的巨变中国的“异质”;而到了《山河故人》中,随着全球化中国的来临,父亲的权威地位被信息媒介物所取代了,并且更为吊诡的是,贾樟柯镜头中父-子共在画面及全景景别的消失,使得观者对于占据画面中心的平板电脑所表征的科技景观,产生了“自然而然”地合理性认同,景观中国的合理性逻辑也由此完成。
四、去象征化:景观中国的叙事“危机”

就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而言,从传呼机到手机,再到平板电脑,信息媒介物的变化勾勒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变得现代”的时间线索,“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变得现代’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摧毁‘传统的’生活模式,并建立起新的、‘现代的’生活模式。”*[美]詹姆斯·费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张祝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页。而吊诡的是,在这一摧毁-建立的现代化过程中,媒介景观高效、便利、自由联通的“身体的延伸”所塑造的现代生活模式却将人际关系平面化为无限滑动的符号。正如贾樟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有时候我和朋友开玩笑,说等我老了写回忆录,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上半部叫‘互联网之前’,下半部叫‘互联网之后’。互联网之后确实传统的生活方法形态改变得很厉害,它消解了我们情感相处的方式,比如思念带来的想象。我小时候觉得思念这个东西是很浓烈的,你只要隔了50公里,真是就像千山万水,只能通过写信交流了。而现在,交流的简单化却让人的情感反而淡了许多。”*贾樟柯:《漂泊是因为有一个故乡》,http://news.hexun.com/2015-10-30/180226171.html,2015年10月30日。一面是信息爆炸和媒介延伸的现代社会景观,一面却是冷漠的人际隔阂和以“目的合理性”*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区分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在他看来,“目的合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合理性”则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为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目的合理性”是以一种客观的、精确计算地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秩序的最优化;而“价值合理性”则不以功利性的目的为社会行为的动因,而是以精神、情感的满足为行事原则。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为原则的“去象征化”的交往逻辑,贾樟柯在审视与反思中完成了巨变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从熟悉到陌生,从象征到景观的悖论表达。
结 语
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某种程度而言,得益于两种快速移动的“自由”,一种是“行走的自由”,是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人们亲身跨越空间的快速交往和流动成为可能;另一种是“传播的自由”,是由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信息媒介的发展,延伸了人的身体器官和中枢神经系统,使得人们之间非亲身的信息快速传播成为可能。而与“行走的自由”相比,“传播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激发大众对“自由”的想象,从而使人们将自身整合到统一的社会有机体所生产的宏大神话中去。


“去象征化”是法理的秩序和人际情感的矛盾叙事,“景观化”是法理秩序全面胜利的时刻。当社会现实照进艺术的世界,面对日新月异、更新换代的电子媒介物,电影作者贾樟柯用电影语言刺破了信息媒介物所表征的美丽的“自由”幻觉,揭示出“自由”背后吊诡的资本运作逻辑和人的复杂生存境况。当我们将信息媒介物从贾樟柯的整体电影创作中提取出来,仔细审视影片中媒介物在人际关系中的实际作用时,发现媒介物为空间障碍消除后自由移动的人们带来的不是“人的延伸”和一个统一的复合体的融合,而是在资本导向下一次次人际情感的“断裂”和被围困的人。
当曾经怀旧、客观、愤怒的贾樟柯*笔者将贾樟柯学生时代之后的电影创作以“情绪”为标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所标识出的“乡关何处的怀旧”;第二个阶段是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所标识出的“保持距离的冷静”;第三个阶段是以《天注定》标识出的“突如其来的愤怒”;第四个阶段是以《山河故人》标识出的“自反式的焦虑”。在《山河故人》中的2025年未来版块用他鲜少使用的特写镜头对准孤零零的饺子时,强烈的情感凝视如鲠在喉,他满怀情感却无力言说。正如身染尘肺病的梁子问沈涛:“今年过年唱伞头了吗?”沈涛回答:“不唱了,再也写不出那好词儿了。”这是剧中人的心声却也是导演贾樟柯失语的焦虑,更是一个景观时代真正的“危机”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