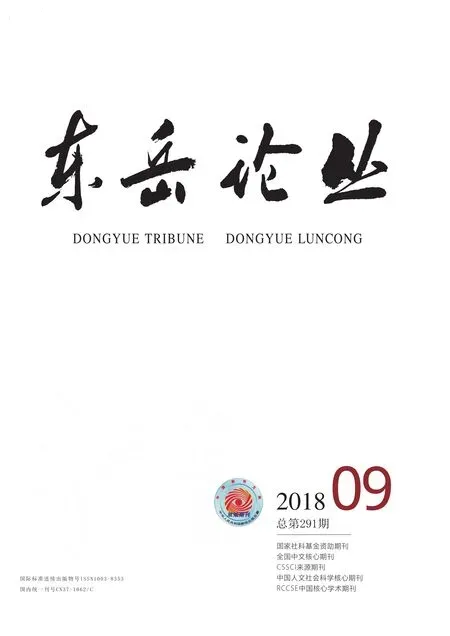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中的“正乐”观念
2018-02-28陈剑
陈 剑
(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教育由传统进入现代之后的音乐教育实践,其教育观念是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一大的历史事件在音乐教育领域的回响和折射,全面整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的发展历程,探讨其中所蕴含的音乐教育问题,对于中国当代音乐教育思想构建有着极大的启发。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对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发展历程的整理已经较为全面,而对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中所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的探讨则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本文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中经常出现的“正乐”观念上,对其基本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渊源等问题进行分析,由此出发而进一步探讨其中所体现出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的理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判其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这一探讨,有助于深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的认识,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的历史面貌和当代价值。
一、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中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
“正乐”是一个古老的音乐美学概念,先秦时代,孔子在其音乐思想中就曾明确地表达过他的“正乐”主张,这种观念在其后世的音乐美学思想(尤其是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普遍地存在着,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一大特色。具体来说,所谓的“正乐”,就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或尺度对音乐艺术进行衡量和筛选,大力发挥优秀音乐作品的正面积极价值,而将低劣音乐作品的消极性影响降到最低,以此来实现音乐艺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功用。“正乐”的观念,不仅在传统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普遍存在,同时也鲜明地贯穿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的发展历程中。当然,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中的“正乐”与传统音乐美学观念中的“正乐”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且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现代“正乐”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中的“正乐”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人本主义立场上的“正乐”,它强调音乐教育在提升个人品德、抒发个人情感以及完善人格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为此必须坚决地反对那些趣味低下、格调低劣、不利于人性完善和品质提升的音乐艺术;另一类则是立足于阶级性立场上的“正乐”,这种“正乐”观念强调的是音乐教育在维护劳动阶级利益、表达阶级诉求、强化阶级团结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为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局限于个体化的小圈子里,不知民众疾苦、缺乏阶级意识、损坏阶级利益的音乐艺术。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主要盛行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而阶级性的“正乐”观念则是盛行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代表着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它们在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通过各自特有的理论构建原则诠释着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提倡用具有极高审美水准的音乐艺术来熏染人的心灵,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完善人的情感世界,进而造就出具有健康审美趣味和高雅审美追求的人。在此前提下,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在大众中传播极广却趣味低下、品味不高的音乐,以防其拉低大众的审美品位,阻碍音乐社会价值的实现。人本主义“正乐”观念中所使用的衡量标准,是超越性的审美主义的标准,它立足于人性本身,大力倡导音乐艺术在陶冶精神、完善人的心理结构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主要的目的是人的整体素质和水准的提升。在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中,存在着明显的精英化意识。在这种“正乐”观念看来,普通民众是迷茫、愚昧的群体,是非理性、蒙昧的代表,其审美趣味是低下的、不完善的,是与生理性的感官欲望联结在一起的,如果任由发展的话,会阻碍人性健康发展甚至引发社会道德堕落和风气败坏,因此必须对普通民众的审美品位加以合理的引导和规范,用高雅且具有高尚审美趣味的音乐艺术来提升其审美修养,完善其心理结构,造就健全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正乐”观念带有一定的启蒙色彩,当然,它所要树立的并非是启蒙理性观念,而是人性所必需的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情感,它最终的导向是个体心理结构的完善,因而它也具有明确的个体化的特点。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音乐审美教育思潮是最典型地体现出了这种“正乐”观念。正是在这种“正乐”观念的引导之下,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才开启了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创作,并由此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创作;同时,也正是出于对这种“正乐”观念的认知和把握,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才真正找到了自身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并且以此为基础开启了自身的制度和体系化建设。
与人本主义“正乐”观念不同,阶级性的“正乐”观念强调的是音乐艺术在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体现阶级情感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正乐”观念中,衡量音乐艺术的标准是无产阶级大众的整体利益,能够鼓舞无产阶级大众的热情、提升民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音乐艺术是优秀的音乐艺术;反之,那些脱离大众审美水准而一味追求高雅,或者站在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大众的审美趣味指指点点,或者缺乏积极的鼓动效应、缺乏明确阶级意识,或者局限于个人的小天地中自怨自艾、不利于阶级团结和巩固的音乐作品必须对其进行坚决地批判和否定,惟其如此,才能维护无产阶级大众的总体利益。可以说,在这种“正乐”观念中,大众不再是蒙昧无知的群体,而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大众的审美标准是唯一正确、合理的标准,任何脱离大众品位的音乐艺术创作都是应该被否定的。这种“正乐”观念,强调的是人的群体性而非个体性,注重的是阶级群体力量的凝聚和鼓舞,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音乐艺术的熏染,使无产阶级大众团结到同一面旗帜之下,为实现共同的利益而努力斗争。可以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在抗战时期乃至建国前后蓬勃发展的左翼音乐大众化潮流,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阶级性的“正乐”特点。在这种“正乐”观念的引导之下,那些表达个体化情感,追求艺术性和审美性的音乐艺术作品,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而遭到彻底否定,如三十年代的聂耳,就曾依据此种观念而将中国早期的都市流行音乐一概斥为“黄色音乐”而痛加批判;同时,也是出于对这种“正乐”观念的理解,中国现代社会音乐教育运动才真正蓬勃开展起来,抗战时期延安合唱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音乐艺术在鼓舞情绪、凝聚群体力量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功效。
由此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在一些具体性的问题上是有着根本分歧的,它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批判和限制对立方的音乐创作和传播,以此来实现各自不同的目的。但即便如此,这两种“正乐”观念依然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对于感官性、娱乐性的音乐艺术的否定和批判,这在这两者来说是共通的。对于立足于人本主义立场上的“正乐”观念来说,对于感官性、娱乐性音乐艺术的批判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以娱乐性艺术的否定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以倡导艺术的通俗化为主要任务的阶级性“正乐”观念来说,对于感官性的、娱乐性的音乐艺术也是极为排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以感官享乐为主要特征的音乐艺术,其主导性的立足点是个体感官,这对于整个阶级力量的凝聚是有消极作用的,因而对于表达感官化娱乐化内容、不利于阶级性强化的音乐艺术也是严厉禁止和否定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虽然是极其复杂和丰富的,在不同的语境和形式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内容,但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对于感官化、娱乐性的音乐艺术的否定和排斥,这是我们在总结中国现代“正乐”观念时所需要明确的一点。
二、中国现代“正乐”观念产生的思想根源
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之所以形成这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具体来说,传统儒家的乐教精神、西方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是中国现代“正乐”观念产生的主要的思想根源,而这三者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领域的碰撞和博弈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张力关系,则是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就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来说,它的产生首先是受到了中国传统乐教精神的影响。传统的乐教观念极为强调音乐在政治生活中的功用,正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和礼结合起来,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为此,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崇“雅颂之乐”,而极力地打击“郑卫之音”,即所谓“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见蔡仲德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从这个方面来看,传统的“正乐”观念中也是带有明显的精英意识的,其中的立足于贵族、精英立场上的“教化”观念极为明显。这种特点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被音乐教育领域所部分地接受,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在最初阶段进行思想建构的理论资源之一。早期的现代音乐教育思想家们常流露对于千年以前乐教隆盛的时代的赞叹与向往,并且自觉地以传统乐教精神的继承人自居:“吾国上世以来,后夔以典乐教胄子,成周以大司乐掌国学政,所谓六代之乐,美矣。三代后,义理之说日盛,乐歌之学日微,音乐之道盖几乎息矣。偶有一二嗜痂癖者,不斥为游荡子弟,则目为世外散人,究其所谓音乐者,亦不过供个人之玩好,于社会上无丝毫裨益也。故今日欲增进群治,必自改良社会始;欲陶融社会,必自振兴音乐始。”*黄子绳,权国垣等:《〈教育唱歌集〉序言》,见俞玉姿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在此情况下,“贵礼乐而贱邪音”的“正乐”精神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正乐”观念产生的理论触发点之一。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领域的一些独特之处。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反传统,但是具体到音乐教育,其中的反传统的意味却并不十分典型。礼乐文化是传统儒家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与礼教不同,中华乐教精神在汉代以后就逐渐衰微,对后世的影响逐渐消减。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世纪反传统的浪潮中,礼教文化被打上“吃人”的烙印而遭到彻底地否定,而与礼教相对应的乐教精神却在现代音乐教育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活和延续,这是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李海鸥:《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乐教精神的继承》,《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传统乐教精神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事实。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传统乐教精神中的“正乐”观对中国现代人本主义“正乐”观念形成的影响又是十分有限的。毕竟二者是产生于两个不同时代的音乐教育观念,在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二者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理论建构的逻辑方式上,而具体到实质性的理论内涵和文化精神,人本主义“正乐”观念吸取的主要还是18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观念,是康德经典美学传统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领域的折射。西方18世纪以来以康德美学为基点而形成的现代美学潮流,强调“天才”“自由”等观念,强调艺术和审美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具有明确的精英化倾向,它对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潮流发展,对于西方现代启蒙精神的演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西方现代学术传统被引进到中国以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领域。在康德美学精神的熏染之下,现代音乐教育者们自觉地强调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强调音乐教育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完善人的心理结构、塑造完善人格方面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音乐教育的超越性意义,突出音乐教育对于人性的改良和提升作用,并由此而衍生对于音乐艺术的批判和取舍问题。可以说,人本主义“正乐”观念的产生,其最初的理论触发点是传统的乐教精神,但真正为其提供明确的理论滋养的,则是西方的康德美学传统,它是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在中国传播和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现代审美主义潮流才是人本主义“正乐”观产生和发展的主导性根源。
而具体到阶级性的“正乐”观念,它首先是以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也就是说,人本主义“正乐”观所大力肯定和推崇的东西,是阶级性“正乐”观念所要大力否定的东西;而人本主义“正乐”观念所大力否定的,对方却部分地予以肯定。这在前文所做的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状况,是其背后所依据的理论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反映出的是整体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潮流逐渐兴盛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群体利益,号召全体受压迫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为获取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压迫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无产者群体的凝聚力量,对于带有贵族化倾向的传统文化,以及表现出明确的个体化倾向的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和批判,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此情况下,以马列主义为基本立足点的左翼文艺思想大行其道,它强调文艺的阶级性与大众化,强调文艺要关注大众,鼓舞大众,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这种观念渗透到音乐教育领域,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阶级性的“正乐”观念。它一方面大力反驳和批判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的精英化和个体化倾向,同时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自身的新的“正乐”思想观念的建构,并由此而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吕骥为代表的左翼音乐理论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就是这种“正乐”精神的基本体现。而这一切,追溯到根源上,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的推动和启发。
可以说,中国现代“正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传统乐教精神、康德经典美学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的合力推动之下完成的。两种不同“正乐”观念的产生及其所发生的碰撞,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透过这一小小的“正乐”之点,我们可以看见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让人感叹的历史命运,可以窥见现代中国人在吸取西方文化资源时所作出的不同尝试,也可以窥见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作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
三、中国现代“正乐”观念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的社会功利性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宏观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
中国现代“正乐”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除了理论机制自身的演化与推动之外,还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现实需求的产物,它从产生的最初时刻就确立了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为自身树立了融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基本准则;在后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风云变幻的现代社会历史状况,它始终结合社会历史情势,把握时代脉搏,自觉地融入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宏阔潮流之中,热烈地响应时代主题观念的变换,并由此而构建起自身多姿多彩的思想演进轨迹。同时,也正是为了使音乐教育更加贴合社会实际,凸显音乐教育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推动性作用,音乐教育者们才要求对音乐艺术进行筛选和限制,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音乐艺术的积极社会效用。可以说,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正是在调整自身以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中生发出不同的“正乐”观念的。透过中国现代“正乐”观念的发展和变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注重音乐教育的功利性,倡导音乐艺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外在性社会价值,大力强化音乐教育的工具性意义。这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说,“正乐”观念的凸显与它对音乐教育社会功利性的看重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正乐”观念发展和变迁的背后,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社会功利性指向发生变化的直接表现。
对于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来说,其功利性的指向和实现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就阶级性的“正乐”观念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方向是“阶级”“革命”等时代观念,而在具体实现这一目的时,它对于音乐的社会功利性的认知和发挥则是较为直接和简单化的,它在全面把握音乐教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功效的基础上,极力凸显其工具性价值,充分发挥它在政治活动中的鼓动效应,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加以弘扬,从而将音乐教育引向“革命”“斗争”等宏大的历史性主题,而对音乐教育本身的问题则没有过多的关注和探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阶级性的“正乐”观念在最终的走向上与政治完全合一,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巩固的有效手段之一,并由此而对音乐教育本身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性的影响。与此不同,对于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来说,其社会功利性实现的逻辑结构方式则要复杂得多。与阶级性的“正乐”观念中社会功利价值实现的直接性相比,人本主义“正乐”观念中实现音乐教育社会功利性的方式则是间接的,即在强化音乐教育自身的审美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将音乐教育引向外在的社会历史领域,发挥其间接改造社会的效果。如前所述,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产生的主导思想根源来自于西方现代的康德经典美学传统,而就纯粹的康德美学精神来说,艺术和审美自律是其根本的理论特征,把艺术和审美从外在的社会政治、道德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强化自身的独立自足性,恢复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是康德美学精神的真谛之所在;为此必须坚决地反对艺术和审美与外在社会之间的关系,还艺术和审美以独立性。但是康德美学传统的这种强调艺术和审美自律的特点在进入中国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音乐教育观念吸取了康德美学中的强调艺术和审美完善人性的内涵,但却并未由此而走向纯粹的西方式的艺术自律,而是在强调音乐自律的前提下为其注入了他律性的内容,这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乃至中国现代美学观念的一大特色。正是由于看重音乐教育的自足独立所带来的间接的社会效应,才有了强调以音乐教育来完善人性、实现民族独立和强大的人本主义“正乐”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正乐”观念所展露出来的是一种“审美功利主义”,它基本的逻辑理路是:用具有极高审美水准的音乐艺术品来熏染人的情感世界,能造就出理性、意志、情感都全面发展的“完善之人物”,即所谓具有完善人格的人,而这种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的形成,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通过大量的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的塑造,能够改变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造就强大的民族,从根本上扭转民族软弱的状况,提升民族的地位。因此,音乐艺术审美水准的高低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为此必须坚决地对于音乐艺术的创作和教育进行限制和审核,以此来实现音乐审美功利性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强调的虽然是音乐艺术的审美性和独立性,但其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民族、国家之类的外在宏大的社会功利性主题。同时,也正是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的音乐审美教育思潮对于西方现代康德美学传统的吸取和改造是有自身的独特性的,它一方面强调音乐教育完善人性、自足独立的特点,同时却又强化康德美学精神所极力避免的音乐艺术的外在社会功利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算是对康德美学的一种“误读”,而正是这种“误读”,才产生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人本主义“正乐”观念,而这一切,都要归结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社会功利性这一总体特征之下。
总之,中国现代“正乐”观念的产生,除了理论自身发展的推动之外,还有着更加具体的社会历史动因,这是现代“正乐”观念生成的现实土壤,这一现实性根由所透露出来的,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根本性特征——社会功利性,“正乐”观念正是这一根本特性的具体展现。当然,在不同的“正乐”观念里,社会功利性的发挥和实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并且其功利性指向也有着巨大差别——阶级性“正乐”观念的重心主要落脚于“革命”,而人本主义的“正乐”观念的重心则主要集中于“民族”;但二者都无一例外地将音乐教育引向了中国现代社会宏大的历史主题,在宏阔时代精神的指引之下来确立自身的理论内涵和发展方向。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宏大叙事精神才是现代“正乐”观念的深层内容。
四、中国现代“正乐”观念的历史评价及其当代意义
“正乐”作为中国传统乐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中的“正乐”观念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观念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发展。在一个以反传统为主导观念形态的时代中,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却通过“正乐”这一概念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地保存和传承,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这对于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是有着非凡的意义的。当然,中国现代“正乐”观念对于传统的接纳是局部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意识的,传统观念更多的是作为宏观的文化背景在间接地起作用,现代“正乐”观念更多的是在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成长与兴盛起来的,它对于传统乐教精神的保留,更多的是与其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结合起来的,它是西方文化观念与中国传统音乐精神相互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现代“正乐”观念固然有着延续传统的特征,是传统音乐观念的现代传承;但与此同时,它更应该是在立足于传统音乐观念基础上的一次新的开创,是中国音乐教育由传统迈向现代的一个新的开始,它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以前的音乐教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这种开创性意义也决定了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思想留给我们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
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音乐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宏观的、带有浓郁的宏大叙事色彩的音乐文化逐渐让位于个体化的音乐潮流,感官化、娱乐化的音乐作品占据了音乐文化领域的主要空间,以人的听觉感官享乐为主要目的的音乐消遣成为当下音乐接受的主导。而本文在前面的分析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现代两种不同的“正乐”观念虽然在基本的理论指向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和分歧,但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对于感官化、娱乐化的音乐艺术的否定,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所“正”之“乐”,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反对这种以“快感”为核心的娱乐化的音乐。从这个方面来说,当下的音乐文化语境与中国现代“正乐”观念所追求的音乐文化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所遗留下来的这项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很多方面都与主流的音乐文化潮流不相容,并且由于大众音乐文化潮流在吸引感官方面的巨大威力,中国现代“正乐”思想所倡导的音乐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显得极为不合时宜。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现代“正乐”精神在当代的音乐教育建构中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现实的影响力,当代音乐教育观念中并没有自觉的“正乐”意识;或许,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当下许多的音乐教育者在面对音乐娱乐化潮流时常显现出一种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之态,态度游移不定,缺乏鲜明的立场。
从根本上说,上述对立状况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对于音乐价值的不同侧面的强调而导致的。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正乐”观念所突出的是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强调音乐艺术的他律性,将音乐教育引向国家、民族、革命等宏大的时代性主题;而以个体的感官享乐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文化,突出的则是音乐艺术的娱乐价值,这是强化音乐自律性特点所间接导致的结果,它将音乐引向个体感官的满足。这两种价值都是音乐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侧重,但二者都共同存在于音乐艺术本身之中,并现实地发挥着各自独特的意义。新世纪感官化、娱乐化音乐潮流的蓬勃兴盛,是商品社会的必然产物,是音乐娱乐价值的大兴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它的过度发展,使音乐艺术流于感官享乐,成为纯粹的商品或消遣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音乐艺术在感性的漩涡中随波逐流;而其过度强调“快感”的地位,进而忽略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和人性改造意义的做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音乐艺术的社会地位,使其丧失了本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而对于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来说,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的坚守和凸显,则是其原生属性之一。之所以如此断定,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作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文化形式而出现的,“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是其基本的着眼点,而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自然也不可能脱离这一特性。因此,在强大的音乐娱乐化潮流面前,音乐教育如果分辨不清自身的目的和任务,而只是一味地认同或否定感官化的音乐文化,则会彻底丧失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正乐”精神中所凸显的音乐教育的社会性及其宏大主题指向,一方面可以为音乐娱乐文化的过度发展提供有效的限制,通过自身的批判性效应,将音乐文化引向一条更能凸显音乐艺术的人文价值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为音乐教育的社会定位和任务确立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实施手段。面对肆意泛滥的音乐娱乐文化,音乐教育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肯定或否定,而是首先应该认清自身的社会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以宏阔的时代主题精神为指引对音乐娱乐文化进行审视,将其纳入到社会时代发展的文化高度上。惟其如此,音乐教育才能凸显其作为一种教育形态的文化意义,才能在娱乐文化的潮流中找到自身的正确位置和努力的方向,进而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只有这样,音乐大众文化才能脱离纯粹的个体化、娱乐化的状态,展现出自身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功效。当然,当下的文化语境与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已经有了本质性的不同,对于音乐进行批判的标准、对于感官娱乐化的音乐艺术的评定和筛选的方式以及对于音乐教育的社会性指向的确立等问题,都需要加以深入探究,惟其如此,才能确立起符合新的时代精神的“正乐”观念;同时,这也是我们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加以拓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