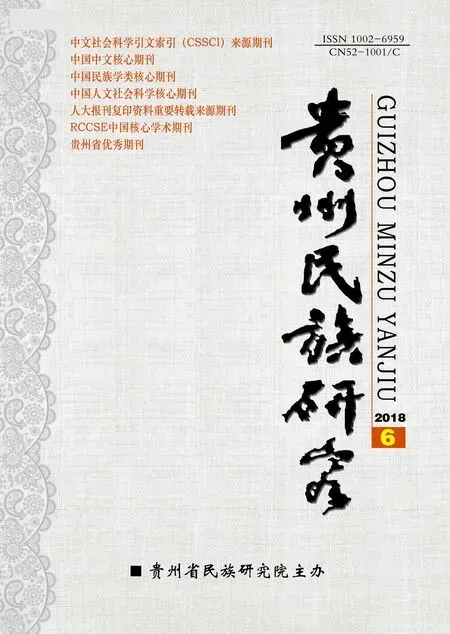苗族《贾理》研究综述
2018-02-22王永伦
王永伦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苗族《贾理》于2008年以“民间文学”类别申报并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P33)是苗族地区最经典的历史文化记忆集成,其内容广博精深,涉及创世神话、族源传说、支系谱牒、知识技艺、宗教信仰、民俗礼仪、伦理道德、诉讼理辞和典型案例等,在各个学科领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文中采用遗产名录中“苗族《贾理》”(以下称《贾理》)这一称谓,并将《贾理》研究文献范围界定为包含与“贾”“佳”“贾理”“理辞”“理词”等同名的文献。
《贾理》文本文献搜集、翻译与整理从1959年开始,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文献共27种。文献工作使人们了解并逐步认识了《贾理》,促进了其保护与传承,也为《贾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贾理》的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于哲学、语言学、文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
一、《贾理》的哲学视角研究
《贾理》的哲学研究,主要表现为《贾理》中蕴含的伦理观、自然观、宇宙观等方面。伦理观方面,曾雪飞认为,《贾理》是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中的一种,体现出“人与人”的“亲缘网络”,如《贾理》的“开路词”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2]杨维文认为苗族理词强调家庭伦理,要求家庭和睦团结。[3]吴大华提到《贾理》中的重婚问题,认为重婚是被人们视为缺德的事。[4](P121)郭凤鸣提到苗族理词中有很多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要求社会要有“体统”。[5](P130)自然观方面,曾祥慧等认为《贾》浓缩了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包含了苗族“以兄弟之情面对自然”的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同源,人与自然是兄弟关系。这种兄弟之情反映了苗族的生态自然观,体现人对自然的态度:因生存而热爱、因害怕而敬畏、因发展而和谐。[6]宇宙观方面,杨茂锐认为《贾理》叙述万事万物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统一,体现了苗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7]《贾理》蕴含着大量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二、《贾理》的语言学视角研究
地理区域、民族文学与语言气质是个文化整体,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学,在语言上有鲜明的文化气质差异。[8]作为民间文学的《贾理》,具备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但这方面研究成果不多,研究主题主要表现为《贾理》的语体特征、《贾理》说理方式的语言学解读等方面。对于《贾理》的语体特征研究,胥奇首先从词语、句式等方面探讨了“苗族理辞”的语言特色。[9]继而其又在硕士论文中,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深入地论述了“理辞”的语体特征,认为其在语音上表现为押韵和押调,在词汇上表现为大量使用口语词、地方词、等义名称词,在语法上表现为以五言句为主、使用同义句式相互重叠呼应等。[10]《贾理》说理方式语言学解读方面的研究,卢凤鹏认为《贾理》说理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语言博弈的过程、言语交际的过程。[11]
三、《贾理》的文学视角研究
苗族理词,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口头韵文朗诵词。[3]苗族理词是少数民族说唱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它是一种说唱文学样式。[12](P223-240)佳既是史诗,又是理词。[13](P206)《贾理》是“民间说理长诗”的一种。[14](P201)贾既是对这类亦诵亦歌的口头诗体作品样式总的专称,也是对这种样式的单篇作品的通称,它在苗族文化体系中是一个独立的文类。[15](P1)这些都是对《贾理》文学性质的有关界定,但都是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具体、深入的论述。
对于《贾理》的文学表现手法研究,陈立浩认为理词的语言运用、修辞手法讲究对偶,表现手法中拟人化的特点较为突出。[16]杨维文认为理词的形式类似古代的“赋”,运用了大量排比句,运用对仗、对偶句等铺陈手法,还采取“比”“兴”手法,拟人化的特点也十分突出。[3]王凤刚认为《贾理》荟萃了苗族民间文学的所有艺术手法,尤其是运用了对仗、对偶、拟人、想象、夸张等修辞手法。[17](P268)徐晓光就《贾理》的比喻、排比、对偶、夸张等文学表现手法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18](P45-53)
在《贾理》的审美意识价值阐释方面,陈立浩和杨维文认为苗族理词渗融了不同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多方面体现了苗族人民的道德、伦理、思想、感情,为研究苗族人民的审美意识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苏晓红、胡晓东等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研究《贾理》,认为在婚姻理辞中存在追求情感和谐型、人格独立型、自我解放型三种女性形象类型,其反映出女性享有和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其女性社会地位形成是受苗族文化思想以及女性在生产劳动、家务处理、教育子女中的重要地位的影响。[19]女性主义视角,丰富了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研究,也为《贾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参考。
四、《贾理》的法学视角研究
对《贾理》习惯法属性的探讨始于杨德,他认为“季节理词是黄平苗族先民的一部生产、生活的‘法典’,纠纷理词是古代社会苗族的一部‘民事诉讼法’,《汤粑理词》和《油汤理词》是苗族先民的一部‘刑事诉讼法’”。[20]后来,周勇又分析了“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认为其具有明显的原始法特质。[21]王凤刚也认为贾是苗族习惯法的“法典”,世代沿袭、自发遵循。[22]徐晓光详细论述了苗族理词体现出的习惯法本质、基本特征,传达出的习惯法历史信息等,认为苗族理词在形式上古朴典雅,含有深刻的法理内容,表现了习惯法的强制性特征,体现出习惯法广泛的社会调整功能、明确的社会规范作用等基本特征。[23](P133-168)后来,胡晓东、胡廷夺继续探讨此问题,认为苗族“理辞”是苗族古代社会的“法典”和“判例”集成。[24]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贾理》是习惯法的主要载体,具有习惯法的属性,体现习惯法的本质、特征和功能。
在《贾理》的法律实践研究方面,关注点集中在《贾理》在司法过程中的实施与运用问题上,具体是探讨《贾理》解决传统纠纷的形式和方法。首先对此进行探讨的是徐晓光,他认为《贾理》中婚姻、家庭纠纷解决一般经过“起诉、辩论、调解、裁定”四个程序,土地纠纷解决一般经过“起因和原委陈述、理师讲理、双方抗辩、判决”等流程。[25]后来,潘海生在徐晓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苗族婚姻纠纷、土地纠纷、借贷纠纷,强奸、故意杀人、偷盗等案件的具体解决流程。[26]胡晓东、胡廷夺通过坟地争夺案、强奸案等个案来阐释“理老司法”“鼓社执法”的流程和形式。[24]学者还探讨了《贾理》通过“歌唱”形式解决纠纷以及在运用中的过错确认等。徐晓光认为理师的调解和裁定、当事人双方的自我辩护都通过唱词“歌唱”出来的。王扬认为《汤粑理词》作为苗族生活化的法律,是通过歌唱的形式展演出来的。徐晓光还认为理师在厘清诉讼双方的具体责任和过错时以“筹”(实际上是芭茅草)作为计算工具,在某个细节上是哪一方的责任,就在对方的簸箕里放一棵芭茅草棍。[28]
关于《贾理》的法治思想、《贾理》纠纷调解原则、理老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龙文勇认为苗族理词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法治思想,具体表现在代际公平、相克相生和心存敬畏等方面。[29]周勇认为“佳”反映了有关程序法的一些原则,如“理老”在调解评判纷争时重视收集和查证证据,纷争歧异较大时形成“对歌审判”场面,纷争聚讼不下时通过神判的方式来解决;[21]吴大华提到了苗族理词注重“以和为贵”的纠纷调解基础原则。[30]李廷贵叙述了理老的资格、产生和职能,认为理老是苗族中的领袖、是习惯法的执行者;[31]潘海生认为理师在解决婚姻纠纷中是仲裁者、代理人,是公平的象征,具有较高威望。[32]
五、《贾理》的社会学视角研究
在《贾理》社会管理思想研究方面,吴晓萍、何彪等认为议榔词、理词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原始法制思想,团结互助和集体观念以及正常的伦理道德观等,但他们还认为进入封建社会后,其思想有一些变化,体现出了私有制、阶级的产生,肯定私有制、反对剥削,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自由等思想内容。[33]王凤刚认为《贾理》促进苗族人创建和完善了鼓社制的社会架构,并通过议榔传统、引经据典解纠纷等方式有效管理社会。[17](P100-116)杨茂锐等对《贾理》社会管理思想研究较为集中,他们将《贾理》社会思想归纳为三个方面:对管理者进行要求和管理,教育为先、预防为主的管理思想以及违反规约及惩处的管理。[34]另外,他们认为《贾理》社会管理思想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及价值;[35]并提出将《贾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结合,从目标、层面、内容和价值等方面提出了研究设想。[36]他们对《贾理》的社会思想观点进行了提炼,认识到了《贾理》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将《贾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合的研究设想,是《贾理》社会管理思想研究新的切入点和视角。随后,宋汉瑞等进一步拓展其研究,认为《贾理》社会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万物和谐共生观”,并由此衍生出“和为贵”“自由恋爱”“热情好客”“一夫一妻”等社会价值观念等。[37]
对于《贾理》教育思想的研究,王凤刚认为《贾理》在做人教育方面价值突出,其教育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崇尚勤劳诚实守信、注重伦理道德修养等。[17](P120-135)杨茂锐认为《贾理》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民族精神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知识技能传承教育等三个方面。[7]2016年,他与陈芳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增加了“方式方法教育”第四个方面,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阐释。[38]此外,李建军提到苗族理词对社会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39]申茂平提到《贾理》具有对族群进行行为规范和道德教育的教化功能。[40](P55)
李建军认为苗族理词的社会控制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39]张斌对《贾理》的社会控制功能论述较为深入,他认为在正式法律产生之前,《贾理》作为一种规范知识和实践理性,在苗族地方社会的秩序构建之中凸显其社会控制的功能,表现为无国家社会的秩序安排、日常生活基本制度与秩序的构建、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民主化社会治理结构、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等四个方面。[41]
六、《贾理》的文化学视角研究
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不同程度发生变化,《贾理》保护和传承面临空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从文化学视角进行研究,主要以“叙”与“议”两种方式对《贾理》文化传承给予了关注。
“叙”为记录与“贾师”们的情缘、“贾师”们的故事等。王凤刚记录了与贾师们的情缘、“贾师”们传承《贾理》的酸甜苦辣的故事。[17](P43-81)吴佺新等通过传略、评传、自述三种形式记录了贾师传承《贾理》的心酸坎坷以及贾师的精彩人生。[42]
“议”主要是传承习俗、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等研究。在传承习俗研究方面,王凤刚说《贾理》传承方式有办班传授、家庭传承、拜师学习三种,传授时间选择吉日,传授地点在室内,传授道具为贾签,传授仪式庄严而独特等;[17](P82-99)余未人提到贾师传贾时有“杀鸡看眼”、“得鸡头者为大徒弟”的习俗等。[43]对传承习俗讨论较多,但对传承习俗成因缺乏分析。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较为详细,罗丹阳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基础上,从提高思想认识、拓展资金来源、壮大传承力量、制定法律法规、整合各方资源等方面提出了《贾理》的保护策略。[44]王凤刚认为懂《贾》的人越来越少、愿学《贾》的人越来越少,传承濒临断代,需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抢救、鼓励专家学者研究。[45]杨茂锐也认为,目前保护好、传承好《贾理》非常重要、紧迫,提出了“依法”“结合苗族特点”“建立民族保护区”等三条保护传承的对策和措施。[46]余学军认为榔规制度是苗族《贾理》文化传承的基石,《贾理》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存在缺乏有效机制、口传文本记录整理缺乏科学性等问题,提出了应从各学科理论出发推动《贾理》研究和传承。[47]
苗族《贾理》30余年的学理研究,哲学视角让我们从《贾理》反映出的自然万物生存规律与法则中体验苗族深邃的哲学思想,语言学视角让我们体会到《贾理》语言上有鲜明的文化气质,文学视角让我们体会作为民间文学的《贾理》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法学视角给我们呈现出《贾理》具有“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条例”的性质、特征、功能及运用,社会学视角让我们了解了《贾理》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功能,文化学视角使我们知道了《贾理》文化独特的传承习俗、传承困境及突围途径。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贾理》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关注度在不断提高。1978年以后,民间文学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呈现欣欣向荣景象。《贾理》的文献搜集、翻译和整理快速发展,在占有“基础文献”的情况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贾理》相关研究逐渐开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有了前面研究基础的积淀,进入21世纪后,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发表的研究成果,相较于前期约增长五倍,研究的深度也得到加强,这有力促进了《贾理》“研究性保护和传承”及特有文化图景的建构。其二,多元化的阐释。起初的研究是综合性的阐释,主要从历史、审美、哲学等方面分析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呈现的是一种“粗线条”的综论,但随着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主要从“哲学、语言学、文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进行多元阐释,这既使《贾理》研究更为“细致”、更广,又极大地丰富了《贾理》思想内涵的解读。其三,法学视角最受重视。各个研究视角孰轻孰重,很难给予说明,但从现有研究来看,从法学视角研究《贾理》最受重视。就数量而言,法学视角的研究成果约占42%,研究学者比其他视角多;就质量而言,法学视角的研究成果深度比其他视角突出。这源于《贾理》内容是典型诉讼理辞,由很多案例组成,是习惯法的载体,是苗族古代社会的“法典”和“判例”集成,在苗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纵观《贾理》的学理研究,表现出了在相关学科的研究价值,但目前研究的学者及成果还不多,专著缺乏,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较少,在理论方法上还需新的突破。为此,我们要秉持“多元论”的观念,不断拓展其研究的理论方法,为《贾理》研究带来新的进展。《贾理》以“民间文学”类入选“非遗”名录,为此我们可紧扣“《贾理》作为民间文学文本”,加强文学视角的研究,对其呈现出来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文体特征、文学地位、文学价值、文学功能以及与苗族文学史的关系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从文艺学、人类学视角拓展其研究,可将其置于审美人类学视域下,阐释《贾理》创造生成美的具体机制、审美传统及其文化变迁、审美制度类型及其成因、“仪式行为”的审美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