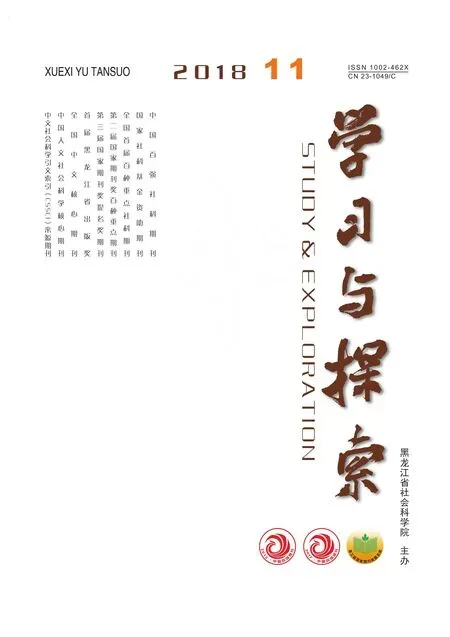《心灵与形式》与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方法论片段
2018-02-20谢尔盖泽姆良诺伊孙叔文
[俄]谢尔盖·泽姆良诺伊孙叔文,刘 博 译
(1.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86;2.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悲剧观”(Трагическоевидение)的语气是深刻铿锵的,这种声音不仅在青年卢卡奇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还反映在他与人的交往中,甚至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音乐与绘画、戏剧、宗教和神学一样,不能与语言相提并论,因为语言是唯一符合卢卡奇内心世界的事物,是他精神探索的写照。卢卡奇在191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需要一个朋友在他的日记中作一个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见证,为的是使自己的精神生活获得黑格尔的那种‘主要的原则’:‘顺便指出,我的品德的‘消极之处’在于面对轻佻时的紧张恐惧和相对于追求精神纯净的过分严格,在挑剔这一问题上,难道还没有显示出我在面对宗教和存在主义时的无能为力吗?或者如果解决问题比较困难的话,那么更应明确的是,我在现有基础上对这一点是否是无能为力的(我在这里也是无能为力的)。于是,需要把伦理学作为一切的标准,这非常接近康德的思想——这是一个新的观点,用来引入宗教的新概念,它大概是一种标准(在这里必须严格地将宗教和美学相互区分,同时,‘生活艺术’这个概念在伦理学、美学、宗教三者间亦存在一个该如何界定各自标准的问题)。而这一切则又回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如何才能成为哲学家?这意味着我只要是作为‘人’而存在,那么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脱离道德的范畴而存在,我如何才能够把道德的形式提升至最高级?”[1]71-72
在此,卢卡奇提出了一个非常高雅的哲学概念——“大写哲学”(о Философии)。 “大写哲学”是带有个性化的直接言语特征的哲学,凸显其位于“一般哲学”之上的地位,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отпервого лица)。 在那几年,“大写哲学”逐渐引入到了青年卢卡奇的思想范畴之中,并在其精神世界中逐渐合法化。“大写哲学”对“现代科学”没有自己特殊的定位,或者说像马堡学派(Марбургская школа)代表人物之一的保罗·纳托普(Пауль Наторп)认为的那样,对“书本”中的既有知识也没有定位。1962年,在《小说理论》(Теорияромана)的前言中,卢卡奇诉说了他在“寻找丢失了的大写哲学”那几年的思想历程,如果套用布鲁斯特小说中的内容来解释的话,就是:“我那时正处于从康德转向黑格尔的过程中,但不管怎样,我对于所谓‘精神科学’(наукао духе)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基本上来自于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西美尔、韦伯著作所留下的种种印象。《小说理论》事实上就是这种精神科学倾向的一个典型产物。1921年,我在维也纳结识了马克斯·德伏夏克,他告诉我,他认为这部作品是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今天,认识到精神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已没有什么困难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正确地评价精神科学的历史相对合理性,不是新康德主义或其他实证主义所显现出来的肤浅平庸,而是在考虑历史形成和相互关系方面,以及在精神学科领域(逻辑学、美学等)的研究发展方面的正确性。例如,我在思考狄尔泰的《体验与诗》一书所展现出来的魅力,他的这本书在当时的许多方面都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和方向。这种新事物在许多方面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在理论和历史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综合的精神世界。”[2]III-IV由此可见, “ 大 规 模 综 合 的 世 界” (мир великих синтезов)是卢卡奇那一时期所憧憬的哲学。
卢卡奇强调了他对耶拿派和海德堡派浪漫主义的执着追求。在《心灵与形式》中有关诺瓦利斯(Новалис)的浪漫派生活哲学(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жизнь)的论说文中,他认清了浪漫主义者所猜想的特征和细节并将其精心地汇总了起来,认为它们来自于宗教和“大写哲学”的神话,并最终成为文化制度形成的重要力量。“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孜孜以求的事物叫作‘文化’,因为在他们眼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救赎的并且是可能的目标,他们因此有了一千种刻画它的诗歌格式,看见了一千条走近它的道路。他们知道:每条路都通向这目标;他们感到为了使‘看不见的教堂’——建造这个教堂正是他们的使命——富足丰饶而无所不包,每个可想象的经历都应该去接受和经历。仿佛一种新的宗教就要诞生,一种泛神论的、一元的、崇尚进步的宗教,一种脱胎于新事实和新科学的发现的宗教。”[2]169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强烈敌视是卢卡奇那时刚刚形成的态度,甚至在新康德主义的外衣下,有关孕育出“新宗教”的科学作用的类似解释看起来都似乎是勇敢的和讨人喜欢的。
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到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天主教教父哲学,再到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这些都是各个时代哲学思想的楷模,它们都是青年卢卡奇所说的“大规模综合的世界”出现之后产生的。简言之,这大概是一个以宗教神秘主义为基础的封闭教条体系。卢卡奇在1913年3 月写给菲利克斯·贝尔多(ФеликсБерто)的信中写道:“对德国来说,幸运的是,无论对当下的迷茫也好,抑或是对打破现状所进行的不充分的尝试也罢,这种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重要的是,在这种不满情绪中,这种对真实存在的同一性的忧虑是德国人较为深刻的情感焦点——这不是艺术的复兴,而是德国哲学与信仰新觉醒的希望。恰恰在这一点上,也只有这一点,才是德国文化的契机(从这里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为了德国的艺术)。德国从未有过类似法国和英国那样的‘文化’,它的‘文化’,恰好是在最好的时代产生的‘无形教会’——它创造了世界观并且成了哲学与宗教包罗万象的力量。德国最后的文化有效力量,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影响要归功于其潜在的宗教和世界观因素,归功于纯主观的世界观,这种力量能够成为深刻的个人经验。”[3]318由此可见,卢卡奇早期的哲学思想体现为“纯主观”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将人们团结在新的整体之中,具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的能力。
卢卡奇最初对 “生命哲学” (Философия жизни)的期望同当时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由著名思想家狄尔泰和西美尔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密切相关,此时的卢卡奇恰好在柏林大学旁听了他们的课程。他主动接近西美尔,并称自己为西美尔的弟子。但是,卢卡奇论说文的主要概念性内容(понятийный аппарат),包括“生命”(жизнь)的范畴、“生命形式”(формажизни)、著名的三段式“体验—反映—理解”(переживание-выражениепонимание)、 “ 世 界 观 的 类 型 ” ( типы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作为哲学的哲学” (философия философии)、“解释学”(герменевтика)等,却是首先在狄尔泰及其学派那里借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与卢卡奇同时代的狄尔泰的学生赫尔曼·诺尔(Герман Ноль)大约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自己的《风格与信念》 (Сmиль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一书,而狄尔泰的另一个学生爱德华·施普兰盖尔(Eduard Spranger)在这时也发表了著名的《生活形式》(Формажизни)一书。 换言之,青年卢卡奇与狄尔泰学派甚至狄尔泰本人,在这个时候都有着相同的思考路径。
然而,狄尔泰及其学生和追随者,此时却遭受了意外的打击,其中也包括了青年卢卡奇——胡塞尔(Гуссерль)的代表作《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сmрогаянаука)在德国杂志《逻各斯》(Логос)第一期发表,胡塞尔毫不留情地批判 了 “ 世 界 观 哲 学 ” (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反转为一种怀疑的历史主义,这种反转本质上规定了新的‘世界观哲学’的兴起,这种哲学如今似乎正在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除此之外,这种哲学本身以其常常是反自然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反历史主义的论战而根本无意成为怀疑哲学。然而,只要它在其整个意图与操作中不再表明自身还受到那种成为一门科学学说——即一门构成近代直至康德的哲学之主要特征的科学学说——之彻底意愿的主宰,那么,关于对哲学的科学本欲之削弱的说法便尤其与这种世界观哲学有关。”[4]6胡塞尔果断地在多个方面分别区分了“世界观哲学”“科学的哲学”且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胡塞尔对狄尔泰历史主义现象学的批判的观点对卢卡奇和他那一代的全部思想家产生了强烈影响。结果是卢卡奇佯装与狄尔泰划清了界限。1911年,这位柏林的哲学家去世了。在卢卡奇撰写的发表在康德学院(Kant-Studien)的悼词中没能隐藏住他对狄尔泰的批判(“经验的心理学概念”等)。尽管这些批评没有了回应,但是哲学的问题却仍旧存在:哲学是否能够追求培养出那种完美的、包罗万象且有责任感的世界观,以击退来自相对主义、唯历史主义和怀疑论的威胁。
通过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方法,那个时期的卢卡奇试图通过将生命历史哲学(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同先验方法相统一的方式来实现培养出上述新世界观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取得海德堡大学的教职资格完全由于当时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讲坛教授的文德尔班(Виндельбанд)以及之后于 1916 年接替他的李凯尔特(Риккерт)的支持。 当时,卢卡奇与胡塞尔几乎同时发表了反对一般“生命哲学”的文章,尤其是批判狄尔泰“生命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汇编成文集,收录进了《生命哲学》(Философияжизни)一书中。 可以大概确定的是,如果说先验主题在《小说理论》中成了主要写作策略的话,那么现象学方法则是卢卡奇在他的海德堡时期的那些著作的主要写作策略,只是这个包括 《 美 学》 (Эсmеmика) 和 《 艺 术 哲 学》(Философияискуссmва)的青年卢卡奇的文本群,在数十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问世。
在这个方面可以适当地强调卢卡奇与马克斯·舍勒(МаксШелер)之间的联系,这是 20 世纪20年代彻底改变了欧洲哲学发展形势的、决定了德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前途命运的从现象学到生命哲学转向的源头,只有卢卡奇是以生命哲学为出发点退回了现象学。此后又过了数年,俄国哲学家古斯塔夫·施佩特(Густав Шпет) 试图将现象学方法同基于“生命哲学”的狄尔泰解释学方法结合起来。 海德格尔(Хайдеггер)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在《存在与时间》(Быmиеи время)中占据了诸多篇幅。这部作品一经《现象学年鉴》发表,这本刊物的知识面貌便瞬间发生了改变。在之后的几卷中又陆续发表了路德维格·兰德格伯(ЛюдвигЛандгребе) 和考夫曼(Кауфманн)的打上了海德格尔和约克·冯·瓦顿堡伯爵印记的狄尔泰式的作品。根据乔治·米什在纪念胡塞尔诞辰七十周年时发表的《生命哲学和现象学:与海 德 格 尔 的 论 争 》 ( Философия жизни и 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я.РазмежеваниесХай∂еггером) 一文,狄尔泰学派对这种现象学扩张的回应是把“生命哲学”重新归入了其学派的研究领域中。而伽达默尔(Гадамер)在《真理与方法》(Исmинаи меmо∂)的思想语境中,通过发表在《逻各斯》上的名为《审美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文章分析了卢卡奇《艺术哲学》文本的特点,进而转向了现象学。
“方法问题”在卢卡奇对“哲学”和“系统”非常集中的思考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时的卢卡奇致力于将他的论说文从自己所痴迷的心理主义方法中完全净化出来。在1911年8月12日写给列奥波德·齐格勒(Леопольд Циглер) 的信中,卢卡奇对此做出了总体性的评价:“如果我在悲剧的定义中突出强调了‘心智’的作用,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切来自经验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悲剧。在‘生命’和‘生命本质’之间形成的紧张和失落在美学层面却被过分地低估,并且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都是模糊的。在我看来,在‘心理学’时代,强调审美范畴的超心理学,在‘心理学’意义上突出其中全部的‘非生命’要素,这是十分重要的。”[3]241
卢卡奇不仅在通信中进行了这种反对心理描写的论述,这些论证的出发点还来自于《心灵与形式》中的一篇关于克尔凯郭尔(Кьеркегор)的论说文。卢卡奇在文章中写道:“心理学开始之处也就是纪念碑终结之地:完全清晰只是对为了纪念碑而奋斗的一种适度表达。在心理学开始之处,除了行动的动机外没有更多的行动,需要解释的东西,能够承受解释的东西,已然不再坚固和清晰。……被动机主导的生活是小人国和大人国的连续转换;所有王国中之最无实体性的和最深不可测的是心灵的理性的王国、心理学的王国。一旦心理学进入生活,那么它就会完全拥护不含混的真诚和纪念碑。当心理学开始统治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能够包容生活和它的全部际遇于自身中的姿态了。只有当心理学依旧是习俗的,那姿态才能不是含混的。和成为悲剧性的确定截然不同的是,在这里,诗和生活结伴离开。诗的心理学是不含混的,因为它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心理学;即使它似乎在一些方向上分岔,但它的多样性依旧是不含混的;它仅仅将更加复杂的形式给了最终统一的平衡。在生活中,虚无是不含混的;在生活中不存在特别的心理学。在生活中,不但动机扮演了一个为了最终的统一而被接受的角色,而且每一个已然被抓住的注释都必然在结束时沉默了。在生活中,心理学不能是习俗的,而在诗中它总是习俗的——不管它有多么精致和复杂。”
由于卢卡奇的缘故,“有限的适用性”(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применимость)在 20 世纪初期变得非常时髦,心理学问题中的艺术和生活因素在这个阶段立刻得到了清楚的解释。“移情”(вчувствование,Einfuehlung)这一心理学概念被应用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它仿佛可以使人充分地理解艺术作品。这一观点改变了吕西安·戈德曼(Люсьен Гольдман)对《心灵与形式》的态度。戈德曼有意曲解了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使用“移情”这个概念的初衷:“卢卡奇文学创作的形式是一种心理内容的表达。甚至连批判也成了作家最重要的任务,以便使每一种形式都能重新与其相应的心理内容相联系,反之亦然。”然而,在基于“移情”为主要创作策略的《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却提出了一个其对任何古典文化都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精神先验类型的完全转变,类型的本质和后果当然都是可以描述的,其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也是可以被解读和领会的,但是,对它而言,哪怕移情心理或仅仅是理解的心理都是不可能被发现的。”[2]6卢卡奇的创作经历是意向性的,他的任务不是“投入”到作品中模仿作者的“心理世界”,而是要借助语言对意向性对象感觉倾向的修复。由于作品的形式,作者可以接触到这个意向性对象,而形式源于作品的客体化。因此,青年卢卡奇在自己的论说文中通过对“固定的生活经历”和“客体化(物化)”(объективация)的理解,把狄尔泰的“迂回策略”和现象学主题相结合 ,而卡洛斯、马查多和克鲁兹·菲舍尔对这种方法都做出了真实评价。
正如马查多所指出的那样,文章并没有直接与事实相关,当它们已经由形式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它们之间才产生联系。文章的主题——形式,已经事先提出。作为解释这些形式的具体学说,文章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生命哲学的解释学。“文章讲述了关于图画、书籍和思想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东西。它在与诗人的对立中表达出了事物的真相,其材料与任何事实均没有关联。对诗歌而言是来自生活中的动机,那么对于论说文而言就是生活中的模型。卢卡奇完全是在狄尔泰的理论框架下解释这种由于抽象而存在的形式。就像《体验与诗》的作者狄尔泰那样,卢卡奇所建构的解释学指向的是‘生活’。为了寻求真理,文章最终超越了最初的目标。”同时马查多引用了卢卡奇的文章:“如同扫罗出来寻找他父亲的母驴,却发现了一个王国,所以,真正有能力寻找真理的论说文作家是会在他的路的尽头发现他所搜寻的目标即生活的。”[2]134换言之,卢卡奇实现了从形式的解释学向存在主义分析的转向。
为了理解青年卢卡奇无论如何探索却都没能够建构出“大写哲学”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哲学化的文学流派对于他而言如此重要,在哲学的现代模式中解释哲学概念是十分必要的,而这必然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观点作为起点。如果采取亚里士多德之前的研究方法,哲学正在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力求达到真理(与作为科学的真理相区别的是,哲学意义上的真理就像小说中的词句一样),那么,哲学最有可能在“技术”领域被发现。这就是说,哲学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具体科学”无关,即哲学是必然的、永恒的和不变的。这些概念陷入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正确的数学论据和自然法则组成的框架之中。这个情况在哲学中无论何时都不会存在。因此,哲学从未享有过特权,它是以自主的、认识论的途径来认识世界,这就要允许哲学认识逻辑学、数学和自然规律,同时它们也要协助哲学以某种方法引导和指示科学认识的过程。因此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науканаук),甚至不是科学之母。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习惯”,并且是一种“紧跟在真实理性之后的创造性的习惯”。
同时,无论合理与否,哲学也许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存在。对此,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是这样的:“理性灵魂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我们需要着重剖析其中不可变的存在原则;其次,还要着重分析哪些是可变的。”理性灵魂的第一部分是利用柏拉图的思想进行分析,它是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即形而上学。卢卡奇所期望的哲学,恰恰就是与形而上学有关的。但是,这一部分的理性灵魂却早已在现代人的思想中死去了。至于理性灵魂中的第二部分——“理性”,它同给定的但反复无常的“生活世界”接触,因此,这个“世界”,也是我们人类自身生活的世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于“生活世界”而言,理性以 “动机权衡”的方式存在着。因此,哲学在其运作模式(modus operandi)上更加接近于道德而非科学。哲学与“推理”或者审查类似,哪些能发生、哪些可能发生但不会成为现实。因此,哲学与“生活世界”中的可实现的部分有关,对于人类活动的实现是必要的。
因此,哲学并不是置身于世界之中,而是置身于“认识世界的人的视角之中”。哲学不是现实的镜像,亦不是现实中的摹写,而是稍纵即逝的一瞥。在哲学中,“技术”不是以其自身存在的原则来运作的,而是根据“他者”(Другой)的属性,来确定原则的属性。就是说,在“哲学化了的人”那里,“生活世界”虽然是主体间的,但是,这个世界的前景和视野,包括其隐去了的真实性部分,都是围绕着“人的存在”这一命题而建构起来的。因此,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回答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处在“生活世界”中的“智慧之地”完全能够用下列方式来回答:“生活世界”是在自然存在的、有“母语”的地方产生。我们的“生活世界”,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用话语来命名和标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话语在“生活世界”中不存在:简言之,‘生活世界’的本体是由人类语言(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构建的。 它处于语言的框架之外,游离于“生活世界”之外,不知其名。我再次重申,这种控制世界的力量借助于人类对自然母语的习得。语言依附于哲学,但又不了解哲学。
青年卢卡奇围绕着自己的哲学主题建构了类似的思想形态:如果“大写哲学”这个概念仍然有建构成功的可能,如果卢卡奇能够成为哲学家,那么他将属于哪个流派?卢卡奇的思想活动表现在他陷入了一个自我选择的两难境地:也许是文学创作(эссе),也许是形而上学(метафизика)或系统论 ( система)。 爱 玛 · 利 奥 托 克 ( Эмма Риоток)非常了解卢卡奇,她猜出了卢卡奇对系统论的着迷态度,在1913年1月17日写给卢卡奇的信中,爱玛这样写道:“你的作品中的思想需要建立一个体系,而非像现在的论说文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3]308库齐乌斯在1912年11月11日给卢卡奇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你的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既不属于艺术范畴,也不属于科学范畴。艺术和科学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形成了同样独特和复杂的关系。如果说柏拉图是最伟大的论说文作家(这是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确立的结论——作者注),那么问题的实质在于形而上学既未从柏拉图的话语体系中公开化,也非处于核心位置(神秘主义者大概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论说文的不完善也在于此,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应该是形而上学的,但在现实中几乎总是表现为一种不完善的、低级的形而上学。例如,确切地说,我想从你这里知道,‘形式’到底是什么;它并非是你对‘形式’的理解,而是形式存在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如何能够想到这种‘心灵与形式’的这场神会。我在这里指的是这不是一场‘偶遇’,而是必然的联系。当您只是把这部论说文集看作先知的话,那它也只是通向终点的倒数第二步,显然还缺少一篇通向终点的结论性文章……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部论说文集的确只是形而上学的初始形态。”[3]301-302对于卢卡奇的论说文写作方式,韦伯曾经也表达了不以为然的态度。
由于卢卡奇“不信奉宗教”(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религии)、对神学缺乏热情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仍然就自己“如何成为哲学家”这一问题作出了虚拟的但确定的回答。在《心灵与形式》的第一篇文章的最后,卢卡奇将论说文作家和哲学家进行了比较:“论说文作家叔本华就是那样的人,他一边写自己的那些次要作品(парерга),一边等待自己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到来,论说文作家是到旷野中为即将来到的那个人传教的施洗约翰,他认为自己就是给那个人提鞋都不配。如果另一方不来呢——论说文作家不就不用辩解了吗?如果另一方来了,他不就因此变得多余了吗?他如果尝试为自己辩解,是不是就变得完全成问题了?他是纯粹的先行者,但如果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也就是说,不受制于另一个牧羊人的命运,他可以向任何价值或合法性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这似乎就很成问题了。与那些在宏大的救赎体系中否定他的成就的人紧紧地站在一起,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一个真实的渴望总是能战胜那些缺乏超越给定事实和经验的粗俗水准的能量的人;渴望的存在足以决定结果。”[2]141-142
卢卡奇在致利奥波德·齐格勒的一封信中,把论说文的本质认作是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论说文(特指我的论说文)包含讽刺性的教条主义,是利用‘补充说明’来表达必然的真理(аподиктичность)。 从黑格尔的角度来讲,论说文大概只是一个‘方面’(момент),因为论说文研究的只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先验的,最初的基础只是直观主义的。而这在系统的框架内却是不可能存在的。”[3]268青年卢卡奇也从未将这个系统建立起来。
顺便说一句,对于“为何是论说文”这个毫无争议的问题,阿尔贝特·阿佐尔·罗莎(Альберто Азор Роза)给出了最为简短但却讳莫如深的答案:“有关尚未证实的‘人的真实状况’,大概只有是人在照镜子的时候才能看到真相,但这也只是刚刚在镜子中看到人的模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