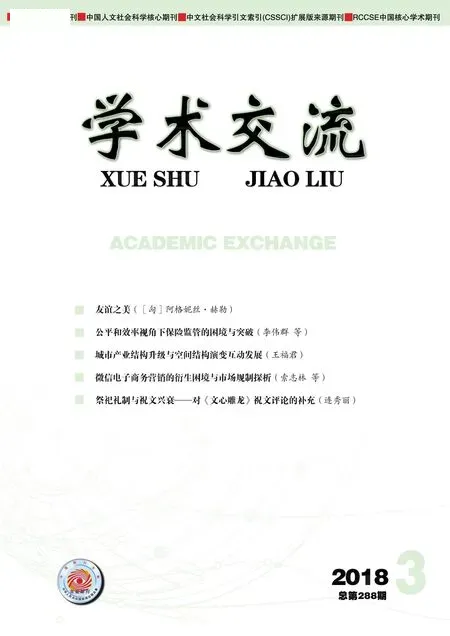友 谊 之 美
2018-02-20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
[匈]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唐文燕 译,傅其林 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44)
柏拉图在《会饮篇》《裴德罗》中讲述的关于厄洛斯(eros,爱欲)的代表性故事和一些其他的主题,以及他在其他对话中所展开的一些主题,成为关于美的叙事基础。我们的欲望被美所吸引——正因为美,所以我们想拥有。柏拉图,特别是在《吕西斯篇》中,论述了友爱(philia,作为友谊的爱)和爱(philein,去爱,与之为友),但在这里,像在柏拉图其他的代表性论述中一样,友爱仍然和爱欲紧紧联系在一起。哲学(对智慧的爱或者作为智慧的朋友)仍然是我们欲求的对象。我们热爱智慧,向往智慧,因为我们并不拥有它。我们爱的是完美,然而作为智慧的爱慕者,我们并不完美,所以我们才想要完美。
友爱中蕴含着的强烈的性的吸引让经历者体验到一种悲剧性的人生经验。柏拉图拒绝把悲剧作为一种政治上危险的文类,但他仍然坚信悲剧性经历的存在及其蕴含的能量。我们整个人生就只是费力地去找寻我们欲望的对象,去拥有我们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去达成自给自足(autarky)的状态——自我满足——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才能最终平和下来。虽然柏拉图对爱欲的洞见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看法,但它使我想起被尼采引用过的埃斯库罗斯讲述的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讽刺性评价:对人类来说,最好的事就是从未出生,其次是年轻时便死去。自给自足的状态如同死亡的状态,但并不必定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个自给自足的人为所有人的情感而献身。在死之前人无法摆脱欲望的束缚,也不能获得快乐。由于这一观点既是古典的又是悲剧性的,柏拉图对爱欲并不赞赏,而是贬低它。准确来说,爱欲本身并没有价值,它只是媒介物、中介者,是一种超越其本身并且为其他事物牵线搭桥的力量源泉。
从这个故事呈现出的美的概念可以发展为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可以从极致的升华角度来考量:我们所欲求的美被认为是完全属于精神上或心灵上的,不是一种视听之美,也不能激动人心(因为它没有情感体验在内,不包括肉体上的痛感或愉悦)。其二,故事讲述者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考察美,在保有上述主题的同时进行重组:由此菲利亚(友爱)取代厄洛斯(爱欲)出现了。
友爱或爱的主要叙述并不是由柏拉图而是由亚里士多德作出的。这是一种次要的,但不同种类的“开始”。如果有人对之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那么他一定会得出结论:关于爱的现代概念从亚里士多德的菲利亚的故事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正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菲利亚的故事从柏拉图的厄洛斯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一样。这是有案可查的,并且很容易查证。难以弄明确的是我所关切的主题:古希腊人称为友爱的这一类爱——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友谊,它以各种形式再现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与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正如柏拉图的爱欲一样。
但是你不必从我这里确证关于友谊的主要叙述是由亚里士多德作出的。你可以和我一样仰赖德里达的《友谊的政治学》(PoliticsofFriendship)[1]。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德里达把伪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友谊的一句夸张的说辞当作其代表观点,这句话被第欧根尼归之于或误归之于亚里士多德名下:“我亲爱的朋友们,世间没有朋友”;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亲爱的朋友们,世间没有一个朋友。”事实上,德里达在包括西塞罗、蒙田、康德、尼采、卡尔·施密特等人的著作中追循这句话在哲理解释上的历史变迁,其含义几经扭曲与转变。然而这些精彩绝伦的分析和解释甚至连关于美的问题都没有触及。正如其著作的标题所示,德里达的主要兴趣在于友谊的政治性含义,因而他选取了这一主旨句作为标题。而我的兴趣在于友谊与美之间的关系,因而我的主旨句便是另外一句——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另一出名的声明——“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是我更好的朋友。”用另一更使人乐于接受的说法便是“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I love Plato,but I love Truth more)。即,如果必须在我的朋友和真理之间作出选择,我将选择真理而抛弃我的朋友。这并不只是表态个人优先选择的问题,也不只是在冲突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偶一为之的个人选择。这被视为行事的准则。如果在友情与真理之间存有冲突,那么哲人应该如亚里士多德这般选择真理。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但在这包含情感色彩的选项之间存有冲突时毫无疑问会选择真理。如果你是一个哲人,如果你热爱智慧,对智慧的爱——真理(the truth)——那么你对智慧的爱会超越其他所有的爱。“行正确之事”视同于(identified)选择真理,而选择你的朋友——谬误(untruth)——意味着抛弃哲理,使你无法符合哲学家的身份(这种观念使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或者至少是克尔恺郭尔)。哲学家在守护神(guiding daemon)的引导下,从原初选择出发,选择真理而抛弃朋友,这是他作为哲学家的纯粹的责任。
依着这条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准则,真理不能被正义所取代。如果能取代,那么前述命题将会完美适配很多传统的以及大多数现代的伦理准则。然后便可以说,如果在正义与忠诚这两种美德之间起了冲突,通常来说(如果不是总是这样)正义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作为正义的美德(相较于其他所有的美德)比忠诚之美德更为重要。更进一步说,即便是在这样的选择中,我仍处于伦理的范围之中,并且所有人(或者至少是所有男人)只要处于类似的境地都不可避免。但是当我要在朋友和真理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便不在“所有人”的范围之内。我能发现真理,即使再无其他人能发现;我知道真理是什么,即使再无第二个人知道真理是什么。忠诚对我的朋友来说只是伦理上的——人人知道忠诚是什么。然而,我为此,或者我应该为此牺牲,将忠诚献给知识、洞见——我的真理,真理(my truth,the truth)——献给这个幽灵。当然,亚里士多德是从不会说“我的真理”这样的话的。他的真理是大写的真理(Truth)——是关于宇宙、人类、存在与思维,关于终结、美德和真理本身;用另一句话说就是,囊括万物。有鉴于此,关于真理与友爱之间的选择并不是两种美德之间的选择,而是关于绝对事实和个人情感或忠诚之间的选择。照此说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对绝对本身(the Absolute)的爱是绝对的爱(love for the Absolute is the absolute love)。
现在让我暂时沿用柏拉图的视角。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挑战,柏拉图会怎样回应呢?他会指责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双重背叛者。他可能会说,亚里士多德对我不忠,更糟糕的是,他为了谬误而抛弃真理,他不仅背弃了友谊,也背弃了真理。他追求幻象,以错误的真理概念为珍。因为我是那个掌握着通往大写真理的关键的人,并且我所有忠诚的学生都表示认同。
这一伪亚里士多德派式的论述只有被某些人表述出来才有信服力,他被其朋友所抛弃(如柏拉图被亚里士多德抛弃)并以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方式抛弃其朋友(亚里士多德)。所有传统学派的哲学家认为,你应该爱真理甚于你的朋友,如果你们都认同同样的真理,那么他将是并一直是你的朋友。认同同一真理是一种美妙的关系吗?对真理的选择是一种美妙的选择吗?这一选择是美的选择吗?柏拉图认为,我们无法欲求我们已有的东西。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说“我更爱真理”意味着他知道大写的真理是什么。如果我说“我热爱真理”,那么我拥有真理,这就是我无法与真理为友的原因。柏拉图会说虽然我不拥有真理,但我有关于大写真理的先见。通过厄洛斯之指引和我对智慧(哲学)的热爱之导向,我能靠近大写真理。但对柏拉图来说,就只有一部代表作,它包罗万象,是纯粹的哲学。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因为在同一学派、同一城市,甚至在朋友们间,多元化的形而上学哲学造成的分裂似乎不可避免。这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论述传达着戏剧的信息。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处的转向和斯宾诺莎从笛卡尔处的转向并不类似。这一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论述作出了在面临纯粹但又非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个人的)的大写真理和个人的反传统的朋友时的优先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暂且别过戏剧,考虑这句话的哲学性的“核心”,我们便又回到“只有我们拥有我们的所爱(大写真理)之后我们才能热爱它(真理)”这一看法中。哲学的历史就是不忠实的历史,是为了哲人拥有的真理而进行背叛的历史。
到了现代,特别是后现代,哲人或哲学思想家再度声称拥有“真理”。他能如实揭露所有哲学性事实的真伪,即我所拥有的是“我的真理”。无论他是如郭尔恺郭尔般认为真理是主观的,或者追随尼采对真理持一种视角主义(perspectivist)的观点,抑或认同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解蔽(aletheia)的看法,这些实际上都是同一回事:我信仰我的真理,认同它,并对它负责,因为我热爱真理(无论我是否相信这一真理,我仍然拥有它)。同时,我承认,人各有所爱,也可能拥有其他的真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声称其拥有真理,更因为他们对其真理负责。为了战胜我们形而上学式的孤独,我们仍然有为了某事或某人献身的意愿,有为了某种事业或者任务而奉献自己的意愿,但不管我们是否无条件地听从内心意愿的召唤,关于伦理的争议仍不可避免。很难判定我们为此无条件献身的真理是否符合伦理规范。它依赖于我们真理的特性、我们的处境和其他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述为“我的真理”(my truth)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真理(the truth),那么超出伦理规范之外的危险将会得到有效降低。不管怎么样,如果以上所有言论为真,那么(后)现代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家则不会背弃哲学或哲理性思考——如果他爱朋友甚于爱他的真理。此外,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这一选择本身不能呈现其自身。这个思考者有朋友,同时拥有真理;他的朋友也能拥有其他真理。如果这两种真理都符合道德规范,那么为什么要在友情和真理之间作出选择呢?或者假设某人有一个挚友,同时渴望真理,但并不拥有真理,那么他为什么要抛弃他拥有的挚友而去追求他渴慕的但并不拥有的东西(真理)呢?
形而上学的终结导致哲学流派的终结。真正的友谊,即便是在坚定信奉他们的个人哲学的哲学家之间的友谊,正变得和共享同一哲学的联盟越来越不一样,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主观化。思想上的友谊使我们想起旧时光,虽然他们通常存活时间不长;一个思想上的联盟就如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之间一样,只有在必要的或者想要的时候才能存在。在城市战争中,这样的联盟代表着一种同志之情——除非个人情感能比公共事业更长久。
目前所论旨在指出亚里士多德学派废弃,至少是消除柏拉图主义对拥有和欲求所作的严格区分的重要性。友爱和性爱之间的区别远没有下面的事实重要,即拥有和欲求谁才是造成友谊和男女之爱区别的根本原因。在友谊中,存在的是欲求;而性爱不仅欲求而且占有其欲求的对象(人或事,抑或思想)——至少它们能做到这样。友谊之美是拥有和欲求的统一体。因为这样的并只有这样的爱才是自由之爱、相互之爱。这样能在各种美中自由穿梭——想象的无拘无束,艺术材料的自由运用,等等。友谊是最具美感的情感体验,因为它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培养;在相互爱慕、相互拥有和相互的自我舍弃中友谊之花更为繁盛。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令人信服地论述道,一个人只有在为了他人而舍弃自我时才是自由的。自由在自我疏离中成为现实。对萨特来说,这是人生中的一个悲剧性因素,因为他坚信互惠互爱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现实主义者——对人类的关系并不持较高的期望。但是他的两本伦理学著作——都成为之后的道德哲学家的模范——却是规范性的著作,虽然里面并不包含极端的感情。亚里士多德把美德呈现给我们——规范是可以习得的,虽然经常不被习得。其正确性在关于亚里士多德式的首份友谊中是显而易见的。很久之后,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中进行了类似的论述。在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纯粹友谊的论述后,他评论道,这极为珍稀,但可能并不存在。纯粹的友谊使人类情感的道德升华和根据责任制定的选择标准得以区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把道德规则作为其选择的准则,并且很可能这道德规则只是大致的要求。但是《保卫友爱》,虽然其并不多见,却是可能的和可见的;在这里能正中靶心,因为友谊是感官的,是人类善和美德可感知的实现。
完美的友情在道德上是善的,同时它是美的;它包含并传达着快乐的希望。在这里,美德和优雅,拥有和欲求结合在一起。友爱(而不是性爱)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典型因其《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德米安伦理学》(Eudemian Ethics)和《大伦理学》(MagnaMoralia)——虽然这三本书可能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最具天才的著作——而广为人知。友谊属于伦理的范畴;它是一种美德。从这三本伦理学著作被广为引用的大师级的论述中,我们都没有找到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显著姿态。他的著作主要是针对普通市民和哲学家之外的对象,除了可能的例外——《尼各马可伦理学》。这些普通的市民就像今天的我们,很少有面对友谊和真理这样的戏剧性选择。朋友是由我们自由选择的。虽然我们经常称朋友为兄弟,但他们并不是兄弟。自由选择的关系比血缘关系更为亲密。众所周知,友谊总是相互的。它是互惠的,因为它是一种关系。处于朋友关系中的双方为了他们的朋友会完全舍弃自己。我的朋友从我这里得到自由,正如我得到他的自由。
自由是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因为选择的自由性,自由也是一个道德问题。确实,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在任何事关伦理的选择上,选择者为其选择负责。为了承担起这一责任,作为选择者,我们有时,也可能是经常不能做一些我们最想做的事,或者我们必须克制内心的冲动,由此带来痛苦并引发自我冲突。在友谊中,对他人的爱是值得褒奖的——这是个仅存在于友谊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但是,对自我的舍弃是我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为了我的朋友而舍弃自我,而我的朋友为了我也会舍弃他的自我。我们之间不存在冲突,也不存在第三者。为了行使我对他的责任,正如他行使对我的责任,需要我们都作出精神上的痛苦牺牲。而行使这样的责任是使人愉悦的,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也是我们都最想要的。无论我对他人做什么都是出于我的意愿而不是我的责任。责任本身是令人愉悦的,它从不是义务。在友谊中,拥有和欲求合二为一——在《保卫友爱》(友爱即特别的友情,第一份友情,最好的友情)中——理性和激情合二为一。而我们称为美的东西正是理性和激情的结合体:友谊是多么美。
亚里士多德的《保卫友爱》类似于阿里斯多芬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描述了一对相互分开的男女)的神话般的遭遇。虽然它们本质上并不一样,但正是这差异成就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纯粹友爱之美。在阿里斯多芬的神话中,偶然相遇和永恒拥有就像命运——它是命中注定的。分开或者相聚,并不是自我选择造成的;而其相聚却是由不可抗拒的想要永恒拥有的欲求达成的。但是在《保卫友爱》中,自由选择排在首位,因为友情是一种建基在相互选择基础上的关系。受不可抗拒的内驱力或欲求的驱使,两个人想要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经常相见并永不分离——一句话,亚里士多德在《保卫友爱》中列举的所有情形——都是自由和相互选择的结果。欲望进入了世界和通过自由而展开的友谊的运作之中。不可抗拒的冲动仍然存在。但因为这样的欲求从自由中生发出来,朋友双方都不想克制这样的冲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压抑的。
一方面是和谐与对称,另一方面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体,二者是美的事物最典型的组成部分。《保卫友爱》是所有美中最璀璨的明珠。虽然友谊事关伦理问题,但它仍超出道德领域——优美的雕塑和诗歌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范围也是如此。因为这里不存在戏剧性遭遇,没有痛苦的冲突使灵魂分裂;也没有为保有负责的能力而要求的道德践行。在友情的范围内,朋友之间所行之事在伦理上可称为“道德的”或“善的”;然而首份友谊仍超脱于伦理之外,因为激励朋友的不是道德而是情感。最后,首份友谊不能违背道德,因为只有正直勇敢的人才有资质成为这样的朋友——从而使美和道德相结合。
柏拉图极度推崇自给自足(自我完善)。一个人如果无欲无求那么他便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因为他拥有一切。亚里士多德也持此观点,《保卫友爱》描述的确实是两个自给自足的人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两个人,两个自足的、自我完善的个体,仍然需要朋友?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确实需要。他们名为一,实为二,一个灵魂分处两具肉体。合二为一时,他们是自给自足、自我完善的。一分为二时,他们互为各自的美德与自足,也是他们的自由。这听起来很有尼采的风格,像亲密的友谊。这不是出于需要、缺乏或不足等原因才导致某人寻求朋友。最好的朋友总是生活在富足之中,人生充实丰富,他们富足而不贫乏。友谊是锦上添花,是对整体的额外补充;友谊是已经拥有远超其所需的人之间互相赠予和收获的礼物。友谊之爱不是由不足与缺陷所触发,而是被另一个人的品格所激起。
在循着这样的思路深入之前,必须考虑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概念的一些其他因素,因为它们在纯粹关系的美学问题上有一定影响。亚里士多德从量、质,时间和空间范畴来分析友谊。我已经提到过质和空间。即友谊是相互自由的选择,是互惠的,朋友拥有他所欲求的,对友谊的质来说亦是如此;善和自足是《保卫友爱》中的质。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友谊:利益之交、声色之交、品德之交(friendships of utility,of pleasure,and those based on the good)。但为什么纯粹的友谊必须基于善?为什么纯粹的朋友必须是好的?这样的论调听着矫揉造作。我们很容易举出两个互为好友的人在道德上摇摆不定,有时甚至道德败坏的反例——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是基于利益,也不是声色之交,就是因为友谊本身,并且他们之间的友情至死不渝。基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条件——善——是虚假的,只为使他的理论假说具有说服力。
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和道德败坏之人并不能为了友谊的目的维持其友谊,尽管这是事实,但并不能以此证明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或许这样的友谊只类似于《保卫友谊》中的友谊,实际上是柏拉图式传统类型的男女情爱;或者,这样模棱两可的品性能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使彻底的道德或伦理友谊成为美德的“神龛”(niche)。莎士比亚了解关于友谊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听从他的智慧。例如,我们可以参照莎士比亚对布鲁特斯和卡瑟斯之间友谊的描绘。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完全互惠的,但布鲁特斯是一个完全追求道德的人——“自我完善”,在亚里士多德派的意义上——而卡瑟斯远不是一个完人。卡瑟斯享受个人的野心,他充满忿恨,猜忌多疑。但是这些性格缺陷使得他的政治直觉更为敏锐,而德行高尚的布鲁特斯在政治上却是天真幼稚的。他们之间的相异处导致这对最好的朋友经常性的冲突,而在政治上每次都是卡瑟斯正确。正如在莎士比亚描述的出色的争执场景中,卡瑟斯深深地知道,如果他屈服于布鲁特斯,他们的共同事业将会一败涂地。但是对卡瑟斯来说,友谊比胜利更重要,即使是他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布鲁特斯和卡瑟斯之间的友情不是《保卫友谊》的原型,而仅仅是一种接近于这种原型的感情——只有他们其中之一(布鲁特斯)成为一个完全有道德的人——在所有冲突性情形下卡瑟斯所作的决定都是基于纯道德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对得失的谨慎考虑。“高尚”的布鲁特斯的友谊——布鲁特斯的拥有——是卡瑟斯最想要的,即卡瑟斯的欲求;为了这样的友谊,为了布鲁特斯的赞许,卡瑟斯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他的事业甚至他的生命。至少这是比“爱智之人”更为睿智的莎士比亚对他们友谊的看法。
朋友间完美的善是亚里士多德《保卫友爱》中模型的主要质性。但是如果每一个朋友都拥有完美的善,借由他们对对方的感情,在需要基于道德的选择时则不会引起任何冲突。在布鲁特斯和卡瑟斯的例子中,他们的友谊被可能的和现实的善的选择所检验和再确认。在现代语境中,亚里士多德派的原型相当于尼采的亲密友谊。每一个部分使他是其所是——在其他事物中,他最好朋友的最好的朋友——借由追随他自己的命运。*尼采也以另外的眼光,更准确地说以其他眼光看待友谊,这是不同的情况。我希望澄清的是要解释友谊的“质性”。或许,克尔恺郭尔是亚里士多德唯一的真正追随者。
现在让我进入到关于量的考量中。一个人不能拥有很多朋友,《保卫友爱》便以两个朋友为典型例证。一个人可能同时或相继拥有三四个亲密朋友。一个人拥有越多的亲密朋友,他越不可能拥有“首份友谊”。这样的纯粹友谊不是由广度而是由深度来界定的——不是由很多“第一个”或“最好的”朋友组成。黑格尔论述了艺术作品的无限深度,这也是适用于首份友谊,即不可耗尽的资源的表述。而无限广度,则激起人们对更多新知识的追求,经历更多的不同的人和事。某事结束后便接着体验下一事。(唐·乔瓦尼是体验无限广度的英雄。)在无限深度方面,人持续不断地在选择同样的对象,在选择同样的关系。他愈重复这一选择,其他不可耗尽的资源愈可供他选择。我不厌其烦再次重复我的观点:在首份友谊中,某人的欲求便是其所拥有的。在朋友关系中,耗尽某人拥有的人或事是不可能的,就如不能拥有他不拥有的所有人或所有事。无限深度意味着一是万物,无限广度意味着全部才是万物。
拥有和欲求的结合体是美的。当你惊叹“这里的风景好美啊”或当你享受一首旋律优美的乐曲时,你拥有了你所欲求的。拥有和欲求的结合体使得无限深度成为关于美的无限。因为在首份友谊中一个人绝对地和同时地拥有和欲求另一人,这是最卓越的美的关系。在爱人的欲求中,想要了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想要互相了解或许是我们所有欲求中最重要的部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爱人强烈想要了解对方。在拥有和欲求的结合体中,拥有建基于自由的互惠,欲求包括渴望了解对方,了解朋友;这个结合体是友谊的真理——这个真理包含了善和美。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第一个朋友(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将是可救赎的;如果我彻底了解我的朋友(这同样是不可能的),我将了解所有的人性。精彩刺激地进入彼此灵魂之迷宫的旅程,犹如伟大的完全可穷尽的艺术作品,是最伟大的冒险,并且是一种没有工具理性在场的行为。微观世界显露宏观世界。这个很大部分或者至少要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第二个方面——数量来论述。
至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第三方面,空间,我已经讨论过:首份友谊意味着亲密的友谊——这是直接的意思而不是比喻的说法——意味着亲密。最好的朋友想要一直在一起,或至少经常见面。当其中一人缺席时他们会互相想念,他们乐于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保卫友爱》很了解人类的苦难和需求。一方缺席,另一方则会为此难受,如果一方远去那么另一方则会陷入不可遏止的想念中。这些苦难不是来自内部,不是由友谊关系本身(美和快乐的结合)造成的,而是来自外部世界。如果好友中一方比另一方先逝,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损失。德里达在他一本书的开头提到,蒙田唯一的、最好的、亲密的朋友的逝世给其造成的痛苦,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弥补蒙田的损失。其他的朋友无法取代最好的朋友,新的爱人也无法取代,即使是最好的爱人。哀痛属于亲密的友谊。身陷首份友谊也包括可能使自己陷入承受难以释怀的悲伤之境地。这就是《保卫友爱》中柏拉图式的寻求不朽的主题。
友谊总有消逝的时候,不是永生的,因为凡人终有一死。但是最好的朋友并不会随其好友一同死去;首份友谊要求其死去的朋友继续存活于暂存者的灵魂中,成为其灵魂的一部分或其灵魂中更好的部分。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最好的朋友便会一直存活于心中,这样仍是凡人的,但却延长了其生命。但是朋友并不满足于这种延长了的凡人世界——他们希望他们的友谊能够永生。讲故事是永生的。朋友为其逝去的好友哀悼,陷入被弗洛伊德称为的“哀悼工作”(the work of mourning)中。在回忆、描述、叙述友谊的故事中,暂存者哀悼其友人,甚至永生化他们的友谊。在讲述这个友谊故事中的幸福时,带着无法治愈的伤痛提到曾经的幸福时,灵魂中的剩余部分使整体得以保存。阿里斯多芬或柏拉图会这样认为吗?在一定程度上会。但这样新的论述已无法追溯到柏拉图的叙述了。
对这个创见来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亚里士多德《保卫友爱》的规范性描述不再作为本质部分显现于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宇宙图景或形而上学理论中。每一个朋友都存在于哀悼他的朋友的记忆中。回忆意味着平凡无奇——一个人回忆平常生活。生活是并将继续是普遍存在的,就如纯粹友谊存在于形单影只之人的回忆中,他失去了朋友,成为幸存的、半个受苦的灵魂。一个人回忆两个人。
友谊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不断重叠,互相影响。因为友情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关系,在朋友各自的生命中,在他们重要的首次相遇的时候,在他们奇迹般地互相倾心的时候,时间便早已存在,而在这过程中空间毫不相干。在朋友相见之前,他们在哪居住,是同一屋檐还是相距千里,这并不重要。在尼采关于友谊的比喻中,两艘船相遇于大洋深处,前者对等于后者。虽然这一形象把握住了友谊的一些特点(例如尼采和瓦格纳之间),但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保卫友爱》,其中前者和后者是不对等的。对朋友间的两个人来说,都有“以前”存在,但只有他们中的一个有“以后”——朋友逝去之后便只有“后者”在“以后”悼念其亡友,此时空间再度不相干系。暂存者可在与其亡友初次相见的地方悼念,也可把他的悲伤带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他的亡友仍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记忆和灵魂里,成为他灵魂中更好的一部分。在空间上,朋友仍在一起。“以后”是回忆和讲述的时候,是过往,因为在朋友死后,友谊便没有将来了。过往的时间意味着讲述的时间。
《保卫友爱》在此再度焕发生机。关于友谊的所有代表性故事都是美的,这不是因为它们由优美的文章写成,而是因为它们是关于真正友谊的故事和回忆,不管它们是由散文、诗歌、私人书信写就,还是存在于一个孤独的人的记忆中。怀旧是友谊之美的其中一种名称。逝去的是美好的,而友谊——显现为悼念,为故事,为敞开的伤口——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美。
关于友谊的“以前”亚里士多德说了很多。性爱的吸引往往瞬间发生,但友情需要时间去培养。友情如佳酿,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更纯更浓。然而,一般来说(遵照亚里士多德派的传统,即使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朋友间也会由“一见钟情”促成。这很有点像陷入爱河,不再是友情的了。但这爱终究会发展成友情。爱或许不能成为友情,但首份友情总是由爱而来。要不然它如何成为“欲求”呢?不掺杂两性吸引力的友情(但不是在性欲的意义上)只是同志情谊,这样的感情对首份友情无所助益。
在亚里士多德的叙述中,《保卫友爱》的纯粹美由此被发现,其再现了关于首份友情的所有叙述。但是如果亚里士多德是说出“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人,那么他同样是不把友谊置于至高地位的人。他随时准备抛弃他的朋友——但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写的真理。但是当他提到非哲学者、他的市民伙伴们,甚至是精神强大的人和最优秀的人时,他并没有把他们置于这一选择的选项中。是的,他把理论生活置于实际生活之上,并且友谊被他置于实际生活的框架中讨论。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过着理论生活的人不能寻求产生友谊的纽带。他实际说过的是,朋友间必须是相似的,至少首份友谊极有可能从两个相似之间的人发展出来,比如两个人具有相似的精神爱好。但他们不必对同样的事作出相似的思考。如果他们对事物的态度特别接近,他们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假设他们都是正直的,没有情绪上或精神上的缺陷),但他们同样也该享受各抒己见的快乐。如果朋友之间对所有事都持同样观点,那么他们还能有什么有趣的对话呢?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话在朋友间的见面和交流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在这里,在友情和真理之间,没有什么是义不容辞的选择。并且,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亚里士多德的真理?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是基于两种美之间的选择。他坚信,被称作游戏之美的哲学——这是他的游戏,他称它为真正的游戏——相较于另一美的事物,即友谊,是更美的、更具价值的。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选择基于两种不同的友谊:对智慧(wisdom)的友谊和对睿智之人(wise man)的友谊。由于首份友谊是一种纯粹关系,我们只能有一个首位朋友——我们不能同时拥有两个纯粹关系。(真理和柏拉图两者不能同时是亚里士多德最好的朋友。)真理的纯粹关系需要拥有和欲求的结合,并且它有可能达到无限深度,但它也可能成为纯粹友谊关系而不用承担风险——因为我(或亚里士多德)可能会先死,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在真理和柏拉图之间,亚里士多德选择了真理,被选定的友谊并不能比亚里士多德长寿,对美的选择才是能得到深度阐释的,但这需要它不可回忆。难道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无论我们是否赞成这一选择)不是对柏拉图的巨大挑战吗?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实际做了什么呢?难道他没有回忆关于其老师兼好友的苏格拉底的个性和著作吗?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不都是因悼念朋友而写吗?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讲述其故事——也是故事之所以美的所在。难道不是亚里士多德,成为真理的首位朋友而不再是柏拉图的首位朋友(而柏拉图仍是苏格拉底的首位朋友),选择另一哲学的种类使得他能赞赏他深爱的在真理和真知面具下的美?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结束了友谊和知识、虚构和确定、生活和真理、描述和回忆的混合状态。亚里士多德开始讨论世界、宇宙、存在、表现、理性、语言,以及朋友之外的所有事物。(我亲爱的朋友,世间没有其他的朋友。我亲爱的真理,世间没有其他的真理。)可能就是在解开这些纠结缠绕的过程中让亚里士多德得以论述友谊。
我确信,在友谊和真理这两种美之间作出选择已不再必要。在现代由柏拉图安排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的姻亲,在很大程度上被亚里士多德取消,早已过了它们分离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再被传统论调逼迫着在“真理或友谊”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现在有人声称他更乐于选择真理,并选择了它,而背弃他的朋友,我们有正当理由质疑他的真实性。我们也可确定他的友谊不是《保卫友爱》中的类型。
而现代生活越多的呈现,越可能展现出其区别,有时候即使是最好的朋友间也会在观点和判断上出现重大的分歧。真诚需要我们自由地说出这些分歧,友谊需要一如既往的相互间绝对的信任。我们不必在正义和友谊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友谊不仅容许正义更鼓励正义。然而朋友般的爱(菲利亚philia)本身并不知道正义。作为纯粹情绪化倾向的首份友谊,与正义无涉,这正是(也是)友谊美之所在。
现在让我再次请出我的主要证人——莎士比亚,不是写作《凯撒大帝》的莎士比亚,而是写作《哈姆雷特》的莎士比亚。尽管在伦理或道德的概念上《哈姆雷特》可视为关于友谊、忠诚和背叛的剧作,但它对我的话题没有直接影响。事实上,《哈姆雷特》中描写友谊的戏属于德里达的故事,不是我的。我选择的焦点是伪亚里士多德派论及和真理之间的友谊与和柏拉图之间的友谊相冲突时的论述,而德里达选择追随伪亚里士多德派关于“我亲爱的朋友们,世间没有朋友”这一险途。但是,正如尼采关于友谊之船只的比喻,这些精警的论断穿过我们传统的大洋而相遇。德里达还讨论了蒙田关于友谊的感人散文。*德里达第一章,《寡头政治:命名、列举与算计》,见《友谊政治学》,第1-25页,尤其是第2页。莎士比亚作为蒙田的读者是广为人知的;而《哈姆雷特》作为讲述友谊的戏剧,在剧中反复重复蒙田的主题,如此明显以至于无法忽视。虽然我从没研究过关于莎翁的出色评论,但我可以肯定,关于莎士比亚重复蒙田主题这个话题早已被穷尽,至少也是经常涉及。我仅仅是莎士比亚一个单纯的朋友;他是我的首位朋友,而我也是他的首位朋友。他对我保持着真实和亲密,从不会背弃我。他是一位最可靠的朋友,因为他知道人性的一切,也最了解我。并且,我将永远不会停止阅读他的灵魂,阐释他。
朋友(在单数上)和朋友们(在复数上)被蒙田作了严格的区分。我的朋友是我灵魂的另一半,是最好的友谊中的伴侣,是我绝对信任的人。我的朋友们可能会背弃我(他们中有人经常这样);我的朋友们可能会成为(如蒙田所说并经尼采复述)我的敌人,我最亲密的敌人。现在让我们回到《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和霍拉旭之间的友谊是一种纯粹关系——首份友谊。在亚里士多德派传统看来,哈姆雷特对霍拉旭的感情是他唯一的纯粹关系。虽然他爱着奥菲利亚,她也报之以爱,然后又背弃了他,但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并没有绝对的信念;他想要她,但他并没有在朋友互相拥有的意义上拥有她。罗森克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是哈姆雷特的朋友们,他相信他们,但从不绝对信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知道他们背叛他之前,他就能感觉到他们已经背叛了他。哈姆雷特的朋友由此变成他最亲密的敌人,所以他任由朋友被杀而毫不同情。我们知道,拉尔特斯是哈姆雷特传统意义上的朋友,他们之间没有深刻的感情;只是哈姆雷特的同情和正义感促使他恢复这业已消逝了的友谊。只有霍拉旭一人是他绝对的朋友。
哈姆雷特是一个失去了他的世界的年轻男子:再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了,再没有什么能被把握或理解。失去了世界这样毁灭性的经历使得他成为一个现代英雄。如果没有霍拉旭,哈姆雷特将会疯掉,因为霍拉旭是仅有的真实,如岩石般坚实的真实。正因为霍拉旭(全方位[omni])的存在,哈姆雷特得以开始逐步重建他失去的世界。当霍拉旭——即使是为他最好的朋友也不会撒谎或伪装的人——证实了哈姆雷特关于其叔父罪行的猜测时,这两个人共享这一认识,进而共享同一个世界。哈姆雷特仍能区分现实与虚幻,因为他仍有一只手去把握世界;他仍然有一个家。哈姆雷特的世界已所剩无几,之前形而上学的存在——来世、死亡、上帝、湮灭等,以及母亲般的爱、其他女人的爱,都不存在了;但仍有纯粹之物留存于他的世界。首份友谊,这纯粹的友谊战胜一切独自留存下来。而这就是一切,是全部。
《哈姆雷特》是一出美的戏剧吗?是的——如果美代表着伟大、完美、深刻等。但这里的美不是塞尚的画、歌德的诗这样的美。《哈姆雷特》并不是那么美,因为它的神秘可怕(照海德格尔式的说法是可怖的离奇),它使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在戏剧的最后,生活中存在和显现仍互相分离(不像《李尔王》或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的《俄狄浦斯》)。存在在这里不是代表着真理(aletheia)、解蔽(unconcealment),它自始至终是隐蔽的。哈姆雷特濒临死亡。随着他的死去,显现和存在之间的鸿沟将会继续存在,隐蔽将会永续延存,直到永远。但是霍拉旭在这儿。垂死的哈姆雷特转投那唯一真实的人,转投那见证真理的人,并乞求他将解蔽之光照向他,以使其无家可归的存在展示出来,并穿过其外表直达内里。不像俄狄浦斯,只要哈姆雷特还活着,他便一直没法解蔽。我们只有从霍拉旭的描述中方才知道哈姆雷特的故事,是霍拉旭使其永生。在莎士比亚所有其他的剧作中,讲述的故事都是来源于戏剧之外,故事讲述者也是如此。但在这里,并且只有在这里,故事的讲述者是剧中主人公最好的朋友。没有霍拉旭的证词,哈姆雷特的故事和剧作《哈姆雷特》仍将处于遮蔽状态,并被这样的表象所遮蔽:一个快乐的王国被一个叫作哈姆雷特的年轻的疯子、残忍的谋杀者所毁灭。在现代世界,就事关己者而言,存在不能在表象内被揭露,你最好的朋友可能仍是你唯一的相关见证人——一个用爱把你的灵魂置于他的灵魂之中的真诚的见证者。这就是一切;无论谁只要拥有好友他便拥有了一切。
关于我们的真理问题的一个回答是,真理居于我们灵魂中更好的部分。这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霍拉旭在讲述他最好的朋友的故事时认为处于存在中的朋友得以显现真理。哈姆雷特故事中的事实是什么?是霍拉旭呈现的关于哈姆雷特的事实。他爱哈姆雷特,因而他的事实是爱的事实;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的事实也是关于正直的事实。他做了垂死的哈姆雷特要求他的事。哈姆雷特死后,霍拉旭担起巨大的重担——复活他最好的朋友。唯一让霍拉旭担着这一重担短暂的苟延残喘的事,是应哈姆雷特之要求把他的故事真实地讲述出来:“啊,上帝!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实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着怎样的损伤!你倘若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2]105
哈姆雷特不是要霍拉旭帮他洗清污名或代为道歉,而是要求霍拉旭把关于他的实情讲出来,以免此事在他身后也不为人知。哈姆雷特希望霍拉旭把他的故事、他的品性、他的命运大白于天下,在悲剧《哈姆雷特》中,霍拉旭正是这样做的。垂死的哈姆雷特要求霍拉旭真实地讲述他的故事,而这个事实很快便得到确证,是哈姆雷特唯一的但却是绝对的确证。在确证场景之后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说了什么呢?“自从我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以后/你就是我灵魂里选择中的一个人。”[2]52哈姆雷特通过霍拉旭确证了其心智,通过霍拉旭的友谊,哈姆雷特确证自己为一个男人,一个完整的灵魂。这友谊,并且只凭这友谊使得哈姆雷特的品性和悲剧命运具有了美的特质。因为它是一种现代类型的友谊,所以它也是现代种类的美。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关于“同”的纯粹关系,而是关于“异”的纯粹关系,在彼此的相异中穿透这异处,他们是并将继续是最好的朋友。朋友间一个是禁欲主义者,一个是其欲望的奴隶;一个清白端正,一个身犯罪责;一个是穷困的学者,一个是顺帝位的王子。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远不是柏拉图描述的由彼此间性欲的吸引而造成。是友谊,凭着朋友间性格上的矛盾和差异提升了这关系的美。这美的源泉来自纯粹的选择,由在所有的情形中,即使是空前的、无法预见的情形都能维系和珍视其关系的朋友作出的选择。哈姆雷特和霍拉旭之间的友谊是纯粹的美,是在无家可归的世界中一个温暖的港湾(it is heimlich in an inheimlich world)。为在神秘的世界建造一个家,为让这个家和神秘的存在物一齐直达这美,这现代的、绝对的美,便要让真理之光在其中闪耀。
《哈姆雷特》不是一出美的戏剧。或者它是?是否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在朋友间的眼里是美的?但是接受这样的解释将会撤回之前论述的关于友谊的一切。霍拉旭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其毁灭性和丑陋程度无以复加。那里没有美,除了被霍拉旭讲述的故事本身,除了死去的英雄和活着的故事讲述者间的友谊,他通过讲述其故事使英雄再生;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会选择死亡,在结束故事的时候结束其生命。这是美的,这短暂的胜利超越了神秘。美是这一短暂胜利的盛会。余下的只有沉默。
[参 考 文 献]
[1]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M].George Collins,trans.London and New York,1997.
[2] [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