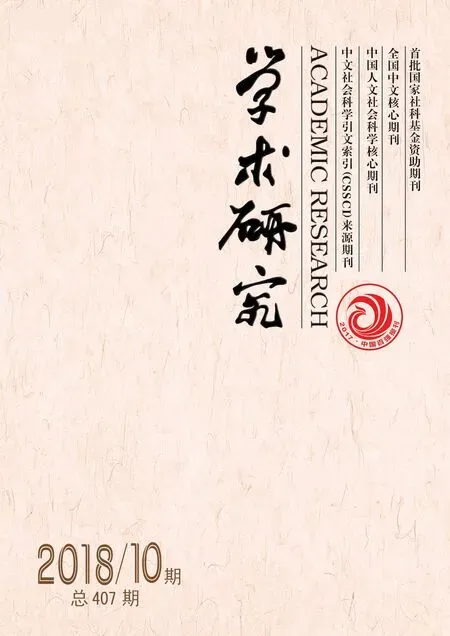论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
2018-02-20余伟
余 伟
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证据。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以历史学为例,近代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查考证据都是以求真为旨趣的历史学的基础工作,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无不以证据详实著称,甚而在历史学中留下了“无征不信”、“如实直书”的论断。然而,在20世纪,尽管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大多依然相信历史是一门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科学,但“如实直书”普遍遭到质疑,并且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历史学那种坚守证据的求真活动被从理论上广泛批驳。a对“如实直书”的客观性思想的批判历程,可参见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批判则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强调历史编纂的虚构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著作尚未出现,而且历史编纂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用着传统的手法,并且在历史研究的程序化工作中并无重大变化。历史学面临重申科学性与捍卫自律性的重大任务,证据概念不可避免地应成为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之一。b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已经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批判的、分析的和叙事的历史哲学。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探究历史为何的宏大叙事已经不再成为主流,取而代之地,是对历史认识与历史表现进行重点研究的史学理论(theory of history)。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二词,目前意义趋同。本文遵从惯例,主要使用史学理论一词。
证据问题在法学领域内被广泛讨论,但自20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绝大多数都未明确涉及这一主题。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国内史学理论的发展和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的较多译介,后现代主义思想进入到史学理论界,这个问题才渐渐引起史学理论家们的重视。c国内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实践的操作与方法层面,有着各种以获得证据、把握真实为目标的方法论(而非本质)意义的操作定义。而在理论认知层面,注重区分史料、史实与证据,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多把材料视作证据的载体,是有着明确意图的历史学家所赋予的,证据成为了论证的产物与要素。参见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新:《态度决定历史: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6期;陈新:《论历史批评》,《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实践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证据与外部实在相联系,专指材料或事实,证据是历史认知的基础。但很多史学理论家却相信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认知主体加工后的产物(信念、陈述或命题)。a参见拙文:《历史证据: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思考与脉络》,《学海》2012年第 6期。理论上的反思似乎并没有改变实践中的做法。在证据这个问题上,证据概念需要兼顾到理论的自洽性与实践的可行性。
在此问题上,柯林武德凸显了他的重要意义。他以历史哲学家和不列颠考古学家的双重身份闻名于世,对他的研究,国内外都比较热,从早期集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命题到近期对其叙事、想象与事实等思想的关注,研究日益深化。b参见袁吉富:《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观点的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张小忠:《从“事实世界”到“思想世界”——柯林武德的历史叙事论》,《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顾晓伟:《试析历史事实、历史推论与历史想象的关联——以布莱德雷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为讨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作为历史哲学家的柯林武德的理论建构,较少涉及到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在笔者看来,柯林武德不仅是史学理论家较早对证据进行深度思考的人,而且他也很强调如何通过证据获取历史真理。证据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界定和指称问题,还是一个程序和方法问题,更重要地是与历史认知紧密结合。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柯林武德的证据思想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哲学分析,以期参与推动相关跨学科研究。
一、证据与历史思维
柯林武德在哲学上是一名观念论者,他并不接受传统历史学中的实在论,反而从认识论角度批评实在论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学说,无益于任何活动。这样,他就不会承认证据是外在事物,相反,他认为外在的认识对象唯有通过人类心灵方可被认识,认识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于精神的统一性,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的关系对于认识活动并非绝对无关,证据只能是在人的思维中。
就历史学而言,尽管柯林武德作为著名的罗马不列颠史专家,从实际工作的角度认可“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变成它现在的样子”,cR.G. Collingwoo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Debbins,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p.124.而且他高度重视证据,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对证据或多或少进行批判性和科学性解释的结果”。dR.G. Collingwood,“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Vol.3, No.10 (April,1928), p.214.但从其观念论出发,他更强调了“一个人不仅应当具有关于历史思维的经验,而且还应当反思那种经验”。e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在此立场上,他把历史学定义为一门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科学,而非单纯获取关于过去真相的科学,而且这种人性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历史的方法。柯林武德也赞同实证史家的看法,认为“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地就叫做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文献是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历史学家加以思维就能够得到对他有关过去事件所询问的问题的答案……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f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11页。似乎这样把证据依然等同于外在事物,但柯林武德在这里附加上了提问的意识,这是不同于实证史家的。证据的主导权实际上在此从外在事物那里转到了历史学家手中。
在这种历史学的定位下,柯林武德认定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由发现一个事件的外部而开始,但绝不能在那里结束;他必须经常牢记事件就是行动,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11页。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也就不再是外在事物,而是认识此事物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在这种历史认知框架下,内在思维中的证据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合法性。证据必然在历史思维中,并且只有在这种历史思维中才能够去谈论证据。
从实践来看,人类过去的活动必然要留下痕迹,否则就无法得以认识,从而外在事物(痕迹)得以在心灵层面激发出证据观念。因此,证据可以外在表现为心灵活动的某种产物,但这种产物却是心灵在进行历史认知时赋予外在事物的一种意义,正是这种意义使得外在事物在心灵中可化身为证据。在不同的历史情势中,被赋予证据意义的外在事物是不同的,但在心灵活动中,它们都可以被称为某点历史的证据。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证据与历史思维的关系,沟通证据的理论与实践,柯林武德构想了一种新的历史认知框架——问答逻辑。他关于历史证据概念的具体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一具体框架下进行的。
问答逻辑总的来说是一种知识论,是出于历史认识的目标创设的。他认为知识是问答的统一体,“知识不仅包括‘命题’(propositions)、‘陈述’(statements)、‘判断’(judgments),或逻辑学家用来指明有关思想陈述规则的任何名称(或通过这些规则被陈述出来的东西,因为‘知识’既指认识活动,又指认识结果),而且还包括陈述、命题等所意欲回答的问题。一种只关心答案却忽视问题的逻辑,只能是错误的逻辑。”a柯林武德:《柯林武德》,陈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0-41页。原书题为《自传》(Autobiography),中译本改题为《柯林武德》。这一定义把认知活动与认知所得密切结合,认为认识的活动就是在问,而认识的结果就是答,认识内容与认识过程同一。从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所认定的证据,仅仅是全部证据的一半,作为证据的事物或观念与使用证据的证明活动是一体的。
更重要的,柯林武德强调了问答的历史性。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我们不断地对具体问题作答,每一次的应答都导致新问题出现并再次作答,直到初始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止。问与答交替循环,前次得出的答案将是下一步提问的基础。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而是随着情境和回答而变化着。柯林武德断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只有应用历史的方法才能给予解决”。b柯林武德:《柯林武德》,第50页。问题本身也具有了历史性,历史渗入进了人的认识中。换言之,一切都是历史,问答逻辑的历史性不仅仅在于对象或所提问的,也在于问答的本身。问答统一体是历史的,显然证据也不可能是永恒的。
这样,在问答的形式下,认知框架从单纯的认知活动扩展到人类的实践生活,人类的历史也视作是心灵的问与答,由之,柯林武德把理论认识与实践工作在某种具有操作性的认知框架中统一了起来,历史思维中的证据不仅在问答框架中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而且可以被应用于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更重要的是,证据因认知框架的历史性变化而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历史学中常说的历史证据,不仅仅指历史学科所需要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证据。
二、历史证据与先验想象
在柯林武德界定了证据与历史思维的关系之后,证据问题就集中在了如何在历史思维中把握证据,或者说,证据如何在思维中具体展开。他的遗稿《史学原理》的第1章专论“历史的证据”,而这一章又被他的学生诺克斯选入1946年版《历史的观念》一书。从文献上来说,我们要考察的这一章,其文本情境应该是《史学原理》,c关于柯林武德写作《史学原理》的过程以及对诺克斯编排的讨论,参见Van Der Dussen,“Collingw ood’s‘Lost’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 Vol.36, No.1 (Feb., 1997), pp.32-62; David Boucher,“The Significance of R. G. Collingwood’s Principles of Hist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58, 1997,pp.150-184.但自1946年以来,人们所接受的柯林武德关于证据的思想,其主要文本情境却是《历史的观念》一书,迄至1994年《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出版,情况依然没有变化。新出的柯林武德原稿《史学原理》“因为它已经被编辑在《历史的观念》第252-82页(以‘历史的证据’为题)。它就从那本书中复制而来了”,dR.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edited by W.H. Dray and W.J. van. Der. Dus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 n.1.那么在证据探究中史料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将主要考察《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中的若干章节。
在柯林武德看来,实证史家们偏爱事件在场者的陈述,把历史真理奠基于历史学家心灵之外的权威,强调思想要符合权威陈述和经验常识。但历史思维的运作不能依赖于记忆与权威,而必须是自律性的。他把历史学家比喻为一位艺术家,认为“对进入画面的东西要负责的,乃是艺术家而不是自然界”,a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34页。从而历史学家本人成为自己的权威,他的历史真理就不可能现成地存在于他所谓的权威的陈述中。历史思维就是“历史学家把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了在他们的原始陈述中所隐瞒了的情报”。b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34页。当获得了这些情报之后,历史学家就可以构造一幅相对完整的历史画卷。柯林武德把历史思维的这种运作称为“构造性的历史学”,c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37页。认为要构造连续性的历史画卷,就必须在我们从权威那里所引陈述之间插入它们所蕴含的陈述,而这种插入,本质上是想象的。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想象的构造不同于小说家的幻想,它仅仅包含了证据所必需的东西,是一种先验的想象。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把权威们的陈述当作构造历史画卷的某些不可变更的基本点,从而把想象奠基于他人处呢?柯林武德的历史认识是在心灵中进行的,那些所谓的基本点就不应该是权威们的陈述,而应该是在心灵中历史思维本身运作所产生的。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思维的对象是不能直接知觉的过去,过去成为对象有赖于历史的想象。通过想象,历史画卷被构造出来,但在构造的时候,权威们的陈述必须经过批判,只有历史批判所得的结果才有资格成为历史想象中的基本点,批判后被接受的权威陈述在历史思维中就不再属于权威,而是属于历史学家的,成为历史学家的证据。正是这种先验的想象所构造的历史画卷才决定了权威们的陈述是否可以被接受。由之,历史思维在“摆脱了他对于外部所提供的那些固定点的依赖之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图画因而在每个细节上就都是一幅想象的图画”。d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42页。这种历史画卷成为历史思维的产物。柯林武德明确说道:“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历史学家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借以判断(哪怕是尝试着)其真理的唯一方式,就是要靠考虑这种关系;实际上,我们问一项历史陈述是否真实,也就是指它能否诉之于证据来加以证明。”e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43-244页。证据在历史思维中被抬升到历史真理评判标准的地位。
在柯林武德看来,证据“不是被历史学家的心灵所吞噬和反刍的现成历史知识。每件事物都是证据,是历史学家能够用来作为证据的”。f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44页。这就把证据的外延做了无限扩大,而从历史思维的角度来看,历史画卷既然是想象的,外在事物只要能进入到历史思维中就能够成为证明某项历史陈述的证据。“历史知识的扩大,主要就是通过寻求如何使用迄今被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是无用的这种或那种可知觉的事实作为证据而实现的。”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44页。证据在历史思维中成为历史知识的源泉之一。进而,最为广阔的完整的历史画卷,或者说总体史,柯林武德也考虑到了,他把现在作为其过去的证据,认为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历史思维把现在的所有可知觉的东西都作为全部过去的证据。不过,他坦承“在实践上,则这个目的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h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44页。因为人是有限的,作为全体的可知觉的事物是永远不可能被个人全部地知觉的,但这种总体画卷是人类的追求。
由之,在历史思维中,证据因这种历史画卷的永不完成性和历史知识边界的变更性,不仅仅是随着历史学家思维能力的变化,而且随着历史学家解释证据的原则而不断变化。柯林武德以问答逻辑的认知框架来思考问题,则不同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不同的历史问题,在不同时期历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变化着的,证据在历史思维中将始终处于历史性状态。
三、历史证据的应用
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在阐释了历史证据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历史证据的应用。“应用乃是理解本身必具的成分……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的统一”a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是必不可少的。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思想兼顾理论与实践,而且其本人多年来从事具体历史研究,历史证据的应用问题已纳入其视野。而且,在实践中,任何事物若是只有在历史思维中才可被当作历史证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单选择某些事物作为关于某一历史画卷的历史证据,而放弃其他事物呢?某些事物的优先权是如何获得的呢?这类问题多是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也必须要予以解决。柯林武德本人以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其历史证据观念的应用。
约翰·道埃案件是他所给出的一个例证。b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63页。在英国某处乡村,一个叫约翰·道埃的恶棍多年来敲诈某位修道院院长并试图侮辱院长妻子,但某日道埃被谋杀了,院长女儿自述是她本人杀死了约翰·道埃,但詹金斯侦探长最终发现实际上院长才是凶手。我们不想讨论是否道埃该死或院长是否要被同情等等伦理问题,要直面的是案件真相为何。乡村警官在办案之初,根据院长女儿的不真实陈述,推断她撒了谎,提问为什么这个姑娘要这样做,判断她要包庇某人,而某人有嫌疑她才需要去包庇。从而,乡村警官回答了“这个姑娘怀疑谁”的问题,但这不是最终的问题。詹金斯侦探长的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了“是谁杀死了约翰·道埃”才是根本问题。
在这个案例中,柯林武德通过问答逻辑的方法来应用历史证据,他“希望使读者熟悉……有关提问题的活动的论点。它们在历史学中乃是主导的因素,正像它在一切科学工作中一样”。c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69页。唯有探究者积极主动地去提问,方可活跃认识。而“论证中的每一步都有赖于提出一个问题……它是每一次活塞冲程的动力。……凡是对方法有所掌握的人,没有人会始终在问同一个问题‘是谁杀死了约翰·道埃’?每一次它都问一个新问题。准备一份包括必须要提问的全部问题的目录,而且或早或迟地要问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包括所有的根据仍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是以正当的秩序来问答。”d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0页。柯林武德明确地把提问视作获得真知的主导因素,“证据只有被充作某些问题的回答时才是证据;历史学家心灵的提问活动使得某些事物成为证据”。eMark. J. Kuhn, A Question of Evidence: A Study of R. G.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97, p.38.更重要的,这种连续提问的方式规范了问答逻辑的技术应用要点,通过案例,以活生生的推理过程来表明具体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严格程序,具体分析,使得作为历史认知框架的问答逻辑被技术化、程序化,从而可以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被广泛应用,而不是一种学理上对认识的解释。传统实在论把证据视作方法或程序的产物,而柯林武德则把程序置于一种情境中,把实在论所认为的证据作为问答逻辑的一部分(答)。
显然,从证据获得角度来看,“科学历史学根本就不包括任何现成的陈述。把一种现成的陈述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整体之中的行动,对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乃是一种不可能的行动。”f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1页。院长女儿的陈述,在未被批判之前,不具有任何意义。由之,在历史学中,对于命题陈述——他人的问与答——就不能简单地考虑为真或假,接受或不接受了,而应探寻其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这些,我们有着我们真正要问的主题这一点是不能忘却的,那么“这个人做出了这种陈述的这一事实,对于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主题投射了什么光明呢?……这可以换一种说法,即科学的历史学家并不把陈述当作陈述而是当作证据:即不是作为对它们所号称是在叙述着的那些事实的或真或假的叙述,而是作为另外的事实,——如果他懂得对它们提问正当的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对这些事实投射一道光明。”a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1页。这样一来,相关叙述的事实就可能是对我们有用的一种事实,只要我们对之提出正确的问题。命题陈述不是我们可接受的正面信息,因为我们在没有确定之前是不接受它们的,它们是第二手的。“一位历史学家所听到的一个陈述,或者说他所读到的一个陈述,却不是一种现成的陈述。如果他向自己说‘我现在正在读或听一个陈述,大意是如此如此’,那么它就是自己正在做出一个陈述;但它并不是一种第二手的陈述,它是自律的。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权威做出这个陈述的。而正是这种自律的陈述,就成为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出发点。”b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2页。因而,在约翰·道埃案件中,警官进行推论的证据,“并不是她的这一陈述‘我杀死了约翰·道埃’,而是他自己的这一陈述,‘院长的女儿告诉我说,她杀死了约翰·道埃’。”c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2页。这种信息,或者说是自律性的陈述,不是依靠他人的陈述(命题)做出的。
柯林武德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靠诉之原则而解决了一种争论……这是坚持历史学最终依赖于‘书面资料’的那些人和坚持历史学也可以从‘非书面的资料’中构造出来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论。”d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3页。“书面资料”是包含现成陈述或命题的东西,而“非书面的资料”是什么呢?他认为是与同一个主题有关的材料,它们不是现成陈述,而是需要我们提问方可得出真知的东西,这在实践中被柯林武德称为“证据”。柯林武德认为,“在科学历史学中,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用来作为证据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在他有机会使用它之前就能知道有什么东西作为证据将会是有用的。”e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6页。那么证据对于历史学的提问意味着什么呢?证据是我们所要问的东西的载体,自律性的陈述使得历史学中真知可以获得,但没有证据,我们将失去问的可能,否则我们将被迫接受现成的陈述这类意见,证据是提问的基石。这样一来,就使得任何人只要严格地按照问答逻辑的指示,都可以获得别无二致完全一样的真知。真知具有普适性。那么在历史研究中,“每一次历史学家问一个问题,他之所以问都是因为他认为他能回答它”,f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7页。换言之,“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对于他将可能使用的证据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和试探性的观念了”,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7页。这样提问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以进行科学的提问。“要提问你看不出有回答指望的问题,乃是科学上的大罪,就像是在政治上下达你认为不会被人服从的命令,或者在宗教上祈求你认为上帝所不会给你的东西。问题和证据,在历史学中是互相关联的。任何事物都是能使你回答你的那个问题的证据,——即你现在正在问的问题的证据。一个明智的问题(即一个有科学能力的人将会问的唯一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你认为你必须有/或者将要有做出回答的证据的问题。”h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77页。
应该说,柯林武德通过问答逻辑有效地把历史证据观念应用于具体实践中。约翰·道埃案例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应用说明,而在真正的实践中,他也做出了不凡的成就。在他长期的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研究实践中,他提出“负责发掘的人必须明确知道他为什么要发掘它,他必须首先确定他想要发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要确定什么样类型的发掘点可能挖出他想要的东西。”i柯林武德:《柯林武德》,第143页。换言之,问答逻辑的认知框架在指引着历史学家去寻找着什么可被认为是证据。1921年,他发表了《哈德良城墙:一部问题的历史》和《罗马墙的目的》两文,充分展示了历史学家如何通过提问,构造出历史认识的证据,从而获得历史知识的。哈德良城墙据说是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下令修筑的,目的在于“防御那些居住在现今苏格兰的‘蛮族’的侵入”。j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柯林武德回顾了相关历史记述与研究概况,并从实际发掘角度批判了以往的种种错误认识,认为他们把前人陈述作为证据却不加分析和实地考察,人云亦云,从而没有获得真知。他认为新的研究结论不仅要解释罗马墙成因,而且要说明人们何以如此错误认识,而他的研究“令人满意地首次应允了所有这类问题”。aR.G. Collingwood:Hadrian’s Wall: A History of Problem,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11 (1921), p.66.在实践中,他要求“发现任何东西都必须问:‘它是用来干什么的?’由之接着发问,‘对于这个目的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其中的目的它是成功地蕴含着的呢?还是不成功地蕴含着的?’。”b柯林武德:《柯林武德》,第150页。通过这种问答,他认为罗马墙是保护士兵防止偷袭的巡逻道,而且,同样的巡逻道一定会延伸,以便监视海港,而海港因不存在偷袭问题则会有相应的具有监视功能的替代物,问题是它们存在吗?柯林武德把确定的外在事物作为证据载体,根据问答逻辑,把罗马墙视作罗马人心中某个问题的回答,推演出了一个新的见解。而要验证他的认识,只要发现相关遗迹即可。确实,在1928年的地面勘查中,人们找到了作为功能替代物的堡垒,并注意到此前已经发现的但被人忽视的堡垒,这种新发现的遗迹反过来又可作为证据,强化人们的新历史认识。不过,正如柯林武德所言,由于一切都可以说是历史,则随着时代的变迁,问答依然会继续,认知框架会不断调整,从而证据也会相应变化,但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历史认知过程中,历史证据才成为可能,历史认识也才得以深化。
总之,在柯林武德看来,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人们采用不同的证据观念,指称不同的外在事物为证据。证据只在内心中,外在事物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有成为证据载体的可能性,而这有赖于历史学家的认知框架。问答逻辑是人们认知的普遍形式,尽管不同的时代、地域和个人所提问的问题与所得的答案是不同的,但人们(在认知中与生活中)始终处于问与答的境地。被当做历史证据的外在事物,其本身首先是以往人类问答的结果之痕迹。正是这一点,使得历史学家能够通过它(外在事物或痕迹),在历史思维中以先验想象构造出一幅统一的历史画卷。他认为只有针对具体的问题,才能有具体的证据,具体的证据是历史中行动者自我提问的结果,以外在事物的形式表现为遗迹。最重要的,这一切本身都是历史性的,从而永久性的确定某事物为证据,或者坚持某某类别的证据观念,很可能会忽视证据概念的历史性,把片面的历史认识当做普适性的。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情境中,才能有效地认识并使用证据及其相关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