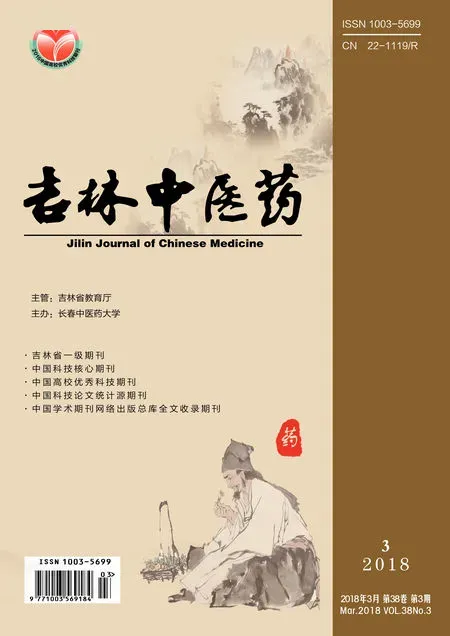慢性荨麻疹辨证论治与辨体论治
2018-02-12闵佳钰秦静波
包 蕾,王 济,闵佳钰,秦静波,王 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体质与生殖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荨麻疹是皮肤科常见疾病,临床上以皮肤黏膜出现 局限性水肿反应、伴瘙痒等为主要表现,若此症状持续6周或者6周以上,即可诊断为慢性荨麻疹[1]。该病病因复杂,易反复发作,缠绵难愈,波及范围广,成人和儿童均可发病,在成人中的发病率为15%左右[2-4]。西医一般给予对症治疗及脱敏治疗,同时规避过敏原,能够有效缓解临床症状,部分患者经脱敏治疗可痊愈。但两种治疗方式均存在不良反应,且治疗周期较长[5]。中医学治疗慢性荨麻疹有独特的优势,从经典的辨证论治到近年来逐渐兴起的辨体论治,在对该病的诊疗上都各具特色,其诊断思路和用药方略值得医家研究探讨。
1 辨证论治
1.1 从外邪论治
1.1.1 风寒束表 寒冷性慢性荨麻疹在临床中十分常见,寒冷季节多发。由于外感风寒,寒邪束于肌表,营卫失调,脉络聚集故而发病。表现为皮疹颜色淡白、淡红,皮疹遇风遇冷骤起,得暖则轻,脉浮紧,舌淡苔薄白。治以疏风散寒,益气固表。赵学义[6]使用玉屏桂枝乌梅汤治疗该型荨麻疹90例,其效果较对照组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液具有明显优势。该药为中药颗粒剂,价位低廉,没有毒副作用,方便服用。周振琴[7]使用针灸配合消风散加减治疗该型荨麻疹患者60例,用药后患者免疫球蛋白E水平显著下降,83%的患者痊愈。张大萍等[8]治疗该型荨麻疹,应用自创经验方麻黄祛风汤,该方是在麻黄汤的基础上再添和血、疏风的药物,临床效果满意。
1.1.2 风热犯表 风热犯表型慢性荨麻疹常因禀赋不耐,风热之邪气侵袭或风寒邪气入里化热而发作。表现丘疹颜色鲜红,有灼热感,痒感明显,遇热、遇风加重,苔薄黄或薄白,脉浮数。治以清热祛风凉血。马林[9]对90例该型荨麻疹患者口服苦柏疏风清热丸的疗效进行统计,痊愈率为72%,总有效率为88%,疗效显著。张敏[10]观察了清热利湿饮配合神阙穴拔罐疗法治疗该型荨麻疹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总有效率达94%,较对照组疗效显著,且不良事件发生率低。文明昌教授[11]自拟清热化湿疏风汤治疗。药物组成:乌梢蛇、牡丹皮、鸡血藤、茯苓、蝉蜕、防风、苍术等。以上诸药合用有宣肺清热、健脾祛湿、凉血活血、祛风止痒之功。
1.2 从血论治
1.2.1 血虚生风 该证常见于先天禀赋不足、年老久病人群,表现为皮疹反复发作,劳累时或夜间加重,体瘦弱,舌红少津,脉细。李晓强等[12]使用自拟归风
汤治疗该证,以口服盐酸西替利嗪片为其对照组。4周后观察示,试验组皮损程度减轻状况优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治疗后血清IL-2、 IL-4的含量降低,认为该方可能具有改善患者免疫状态的功能。邹国明等[13]运用消荨汤配合热敏灸疗法治疗患者40例,以盐酸西替利嗪为对照组。停药后分析得2组均有效,但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周宝宽[14]自拟祛风养血汤(荆芥10 g,蝉蜕10 g,浮萍10 g,当归10 g,胡麻仁10 g,麦冬10 g,天冬10 g,白芍10 g,生地黄10 g,炒酸枣仁10 g,夜交藤10 g,生甘草10 g)治疗此证,全方共奏祛风止痒、养血润燥、滋阴生津之功。
1.2.2 血热生风 该型患者多由外感或内伤等原因引起的心肝火盛或素体阳亢而导致的血分热盛,热极生风引发,内风与外风相合,风血搏结,腠理郁闭,发于肌肤,表现为夜间痒甚、尿黄、心烦、舌红苔少、脉弦滑数、皮肤灼热、红肿等。以清热凉血、疏风止痒为治疗原则,常用清营汤加减治疗。易景媛[15]运用加味凉血消风散治疗,该方具有凉血化斑、祛风止痒的功效。相对于氯雷他定片对照组起效虽慢,但药性持久,服药6周后,78%的患者病情好转,部分痊愈。梁雪松等[16]进行了背俞穴刺络放血拔罐配合神阙穴施雷火灸疗法治疗的临床研究,统计得出其有效率为80%,优于咪唑斯汀缓释片对照组。朱良春教授[17]对于该病证属风热久郁营分、风血搏结者以自拟“顽固荨疹散”治疗。药物组成:乌梅、蝉蜕、生甘草各6 g,赤芍、炙乌梢蛇、荆芥、徐长卿、炙僵蚕各10 g,地肤子、白鲜皮各15 g。
1.2.3 血瘀生风 血瘀型患者多见于慢性荨麻疹疾病后期,旧病气虚不能推动血液运行,旧血不去、新血不生,久病成瘀,血脉不通,瘀血阻于经络腠理之间,丘疹显现。表现为皮疹暗红,多分布于体表受压迫处,舌暗,脉细涩。以活血祛风为原则进行治疗。 徐文静[18]使用化痰祛瘀汤治疗50例,同时以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片为对照组,服8周后停药,随访6个月。2种方法均可降低患者总IgE水平、EOS计数,改善患者病情,降低复发率,且前者优于后者。乔保均[19]使用四逆散合桃核承气汤化裁治疗该证,酌加全蝎、僵蚕疏风通络,祛瘀与疏风并举。
1.3 从脏腑论治 慢性荨麻疹临床表现多为皮肤受损,瘙痒。《内经》素有“肺主皮毛”的说法,但临床上该病病因甚多,肺脏发病只为其一,然五脏六腑皆主皮毛,如功能失调,均可发作。
1.3.1 脾胃失调 如脾虚湿蕴者,主要表现除皮疹显现,皮肤瘙痒外,同时伴有食少、呕恶、腹胀痛、便溏等症状,舌淡胖,苔白腻。治疗应健脾和胃,疏风止痒。临床多用藿香正气散加减。如肠胃湿热者,表现为风团色鲜红,泛发全身,剧烈瘙痒,伴腹泻、腹痛、呕恶,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治以疏风解表,清里泄热,防风通圣散为其代表方药。刘芳等[20]运用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脾虚湿蕴型慢性荨麻疹患者36例,总有效率为94%,痊愈率达到41.7%。李晓霞等[21]根据经络细胞生物场假说,运用经络生物共振技术联合清热除湿、健脾祛风的中药治疗脾虚湿热型慢性荨麻疹患者40例,认为该方法治疗效果优于防风通圣散,且方便安全,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医药的良好结合。陈宏教授[22]认为,虽然慢性荨麻疹是由外感风邪而引起,但是若深入探讨,其病程长,且缠绵难愈,病机之根本为“脾虚湿蕴”,湿性本就重浊黏腻,再与风邪相和,稽留难去,故而病情迁延,临证常在辨证之余加入健脾祛湿之品。
1.3.2 肺脾虚弱 本证多见皮疹淡红,恶风,伴短气乏力、易感冒、纳呆便溏等肺脾气虚的症状,舌淡白苔腻,脉缓,常反复发作。该型患者多先天禀赋不足,脾肺之气虚弱。治以健脾益气,固表祛风,方用玉屏风散加减。曲长春[23]对44例该型荨麻疹患者给予固本消风丸治疗,以阿伐斯汀常规药物为对照组。给药1月,随访3月,结果固本消风丸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复发率低于对照,2组均无药物不良反应。王军等[24]采用加味四君子汤配合穴位埋线治疗脾虚胃弱型荨麻疹50例,有效率为96%,随访6个月无复发。
综上所述,慢性荨麻疹的辨证论治可从外邪、血、脏腑入手,然而临床实际情况复杂,可根据具体疾病进程进行综合应用。闫学文[25]认为该病的治疗应以益气养血祛风为法,临床上使用玉屏风散加益气养血之药,可获良效。姚小平[26]以消风散为基础方,辨其风寒、风热、湿热、血分有热,灵活调整处方,加减用药,可有效止痒,消除风团。此外有医家[27]提出,慢性荨麻疹应责之太阳表虚,治疗时对单纯太阳表虚证、表虚水饮证、表虚血寒证分别施以桂枝汤、五苓散、当归四逆汤加减,临床效果满意。
2 辨体论治
近年来,中医体质学的兴起为慢性荨麻疹的诊疗带来了新的生机,不同于传统的辨证论治思路,关注人的体质状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分析理解慢性荨麻疹的发生、发展及预后。
体质是在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其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表现出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28]。过敏体质是8种偏颇体质中的一种,是指在先天遗传基础和后天外界环境影响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生理机能、自我调适能力低下的特异性体质,表现为对不同变应原的亲和性和反应性增强,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家族聚集性[26]。
过敏体质是诸多过敏性疾病发生的根本,慢性荨麻疹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过敏体质者自身正气不足,免疫功能紊乱,对环境和外界刺激的调节适应能力低下,是过敏性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而变应原作为该病的外在因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并非人人接触后都会诱发过敏症状,其本身并没有致敏作用,只有作用在特定的人身上才会发病。所以应转换思维,治病求本,将过敏性疾病的治疗聚焦在调节人体机能上,而非客观存在的变应原。
王琦教授[27]提倡运用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方式诊治慢性荨麻疹,认为荨麻疹的发生以其禀赋不耐(过敏体质)为根本,以血热风扰、伏邪内潜为主要病机,治疗时以调体扶正为主,配以凉血祛风之法。方药以2组调理过敏体质的药对(乌梅、蝉蜕、何首乌、无柄灵芝)为基础,自拟脱敏消风汤,因该方重在调体,不针对过敏原,所以在服药期间无须忌口。该方用于临床,效果显著。主要药物组成为乌梅、蝉蜕、地骨皮、牡丹皮、旱莲草、紫草、茜草、制何首乌、冬瓜皮、白鲜皮、生甘草。
慢性荨麻疹患者除大部分血分有热,临床以热象为主要表现的人群外,另有因遇寒、遇湿热、五志过极等因素发病的人群。这是因为过敏体质患者亦可兼夹阴虚、阳虚、气郁等体质,各种体质感邪和发病的倾向有所不同。例如阳虚体质者易感寒邪,皮疹多色白,遇寒加重。
3 讨论
作为一种临床常见、顽固难治的过敏性疾病,慢性荨麻疹严重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西医学的脱敏疗法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彻底治愈该病的方法,但变应原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种类复杂,在临床上,仅有少部分常见变应原可做成制剂以供使用。中医学在对该病的治疗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至今已积累了诸多治疗该病的优良经验,在临床实践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在辨证与辨体论治的基石下,现代医家更趋向于使用内治、外治相结合的综合疗法。除注重无不良药物作用的安全用方和针灸推拿等传统外治法外,新兴的穴位自血疗法亦有良效,临床应用广泛。笔者认为,对于该病的诊断与治疗,传统的辨证论治存在依赖过敏症状而忽略过敏患者本身体质的缺陷。随着中医体质学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转换思维,从“过敏的人”的角度出发,纠正患者的过敏体质,调节机体内环境的紊乱,增强机体对外界刺激的适应能力,在根本上阻断过敏反应进程是治愈该病的一个良好思路。由于体质学说提出的时间尚短,目前关于调理过敏体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文献报道不多,缺乏基础研究和临床对照试验。综上所述,治疗慢性荨麻疹应广泛挖掘借鉴传统中医药的经典论著,在辨证和辨体论治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相关微观作用机制研究,科学有效地运用中医理念,找到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靶向通路和药物,以提高疗效,缩短治疗周期,减少复发。
[1] Zuberbier T.Chronic urticaria[J]. Curr Allergy Asthma Rep,2012, 12(4):267-272.
[2]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荨麻疹诊疗指南 [J].中华皮肤科杂志, 2007(10):591-593.
[3]Khan S, Maitra A, Hissaria P,et al. Chronic Urticaria:IndianContext-Challenges and Treatment Options[J].Dermatol ResPract, 2013, 2013:651, 737.
[4] Aguilar-Hinojosa NK, Segura-Mendez NH, Lugo-Reyes SO.Correlation of Severity of Chronic Urticaria and Quality of Life[J]. Rev Alerg Mex, 2012, 59(4):180-186.
[5]赵辨. 临床皮肤病学[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6]赵学义, 朱爱明. 玉屏桂枝乌梅汤治疗风寒型慢性荨麻疹90例临床观察[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10(11):1552-1554.
[7]周振琴. 消风散加减配合针灸治疗对慢性荨麻疹患者IgE水平的影响[J].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5, 26(3):501-502.
[8]张大萍. 张作舟老中医治疗慢性荨麻疹经验介绍[J]. 新中医, 2013, 45(7):200-201.
[9]马林, 武宁波, 孔连委,等. 苦柏疏风清热丸治疗风热型荨麻疹临床研究[J]. 黑龙江中医药, 2014, 43(6):16-17.
[10]张敏. 清热利湿饮配合神阙穴拔罐法治疗风热型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研究[D].山东: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3.
[11] 王琬宁, 王帅印. 文明昌主任医师治疗风热型荨麻疹经验[J].亚太传统医药, 2011, 7(8):44.
[12] 李晓强, 赵晓冬. 归风汤治疗慢性荨麻疹(血虚风燥证)30例临床观察[J]. 内蒙古中医药, 2015, 34(8):40-41.
[13]邹国明. 消荨汤配合热敏灸治疗血虚风燥型荨麻疹50例[J].江西中医药, 2012, 43(2):39-40.
[14]周宝宽, 周探. 辨证论治荨麻疹经验[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14(6):14-16.
[15]易景媛.“凉血化斑、祛风止痒”法治疗血热证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观察[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4.
[16]梁雪松. 刺络拔罐配合雷火灸治疗慢性寒冷性荨麻疹疗效观察[J]. 四川中医, 2015, 33(2):163-165.
[17]杨铭, 付海强. 朱良春教授妙用僵蚕经验[J]. 中医研究,2014, 27(7):46-48.
[18]徐文静. 化痰祛瘀汤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5, 15(3):309-311.
[19]乔艳贞, 孙宏普. 乔保均教授治疗慢性荨麻疹经验[J]. 光明中医, 2010, 25(6):935-936.
[20]刘芳, 王思农. 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慢性荨麻疹36例[J].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1, 27(11):751.
[21]李晓霞. 经络生物共振技术治疗脾胃湿热型慢性荨麻疹的临床观察[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9.
[22]冯爽, 陈宏. 陈宏教授从脾胃论治慢性荨麻疹经验总结[J].中医药信息, 2015, 32(2):86-87.
[23]曲长春. 固本消风丸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体会[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5, 15(82):99-100.
[24]王军,祁原婷,肖云.中药配合穴位埋线治疗寒冷性荨麻疹50例临床观察[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5, 36(2):30-31.
[25]闫学文. 益气养血祛风法治疗慢性荨麻疹探析[J]. 天津中医药, 2012, 29(4):365-366.
[26]姚小平. 消风散治疗慢性荨麻疹80例[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27(1):121-122.
[27]张苍. 桂枝类方治疗慢性荨麻疹26例临床观察[J]. 吉林中医药, 2011, 31(6):527-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