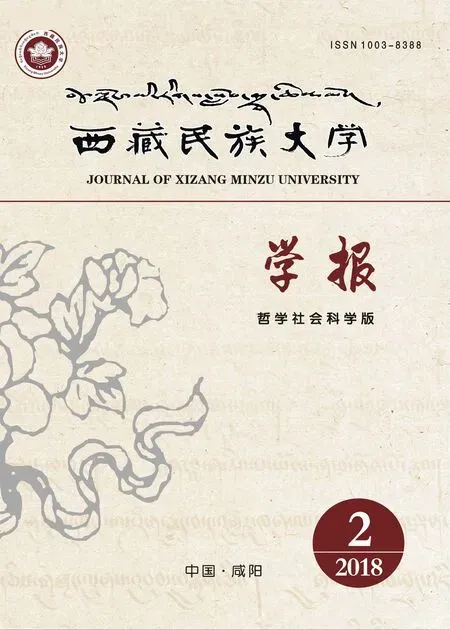儿童、疯子与教育
——以《城南旧事》和《冬冬的假期》为例
2018-02-10康敏
康 敏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以文学作品来谈教育的现实意义在卢梭的著名教育小说《爱弥儿》中已经做了最好的诠释。中外文学作品中涉及儿童或疯子的作品不在少数,仅1985年中国大陆为我们熟知的作品就有《小鲍庄》(王安忆)、《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爸爸爸》(韩少功)、《银庙》(铁凝)等。文学作品对儿童的特别关注,与儿童重回社会中心密切相关,并与弗洛伊德将儿童时期的经历看作未来某种取向的源头是一致的,具有“儿童未来取向”的倾向。文学作品的诸种取向都在阐释或改造传统的儿童观,教育对儿童的关注亦是在继承、改造或颠覆传统儿童观基础上进行着,如儿童新社会学对传统的突破、儿童个案研究的崛起等都开拓了新的领域。自传性文学作品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与近年来教育领域十分关注儿童的健康安全、行为表现等外在问题相比,更能走进儿童鲜活的内心世界、关注其成长的心理历程。
本文涉及两部作品:《城南旧事》(后文简称在《城》),由五篇自传性文章组成;《冬冬的假期》(后文简称《冬》),由自传性文章《安安的假期》改编。作品都关注到了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并涉及一类人:疯子。儿童和疯子这一关注点在两部作品中是巧合还是故意安排,本文不做考证,亦不在以儿童为中心的视角下探讨,而是将儿童置于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与社会中被视为异类的“疯子”关系中来关注儿童的教育问题。
一、儿童与疯子的发现
对于儿童的界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虽有明确的年龄界定,但这一问题在医学界却一直处于讨论之中,这些纷争的焦点在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事实上儿童身份界定并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年龄,更在于社会的地位变化,这在11世纪法国的细密画上得到集中体现:孩子的形象被处理成仅仅身材比成年人矮小,没有丝毫儿童的外形和特征,[1](P51)直到17世纪儿童的单独形象才大量出现。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儿童并非天然的角色,而是通过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的一系列区分逐渐形成,且区分的标准是多样的,其中包括秘密和规则。
(一)通过秘密建构不同的群体
秘密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障碍[2]。当儿童意识到与自己最亲近的成人之间有了秘密,就开始意识到自我与成人的不同。《城》的儿童正是通过“秘密”从成人中被发现的。
英子及妞儿只是被告知,惠安馆里的秀贞是疯子,她们并不清楚秀贞和其他人的区别是什么?秀贞为何成了疯子?而宋妈与其他大人在私下里谈论和确证秀贞是怎样疯的,这些事情是成人才可以知道和谈论的。在英子与宋妈间存在秘密,是关于秀贞成为疯子的“不说的行为”[3](P219-303)。这些秘密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宋妈等成人建构起来,这一建构的秘密将成人划分在了可知范围内,而将英子等划分在了可知范围外,将儿童与成人进行了区分。
通过建构秘密达成了群体的区分,同时通过分享秘密建立密切的关系。也正是通过将自己的身世之秘密与英子分享,英子和妞儿成为儿童阵线上的同盟。同样秀贞也通过与英子分享自己爱人与孩子的秘密站在了一起。在正常情况下爱人和孩子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无可厚非的,但成人却对秀贞的爱人与孩子避而不谈,视他们如洪水猛兽,秀贞的父母也不例外。
此类正常的情感被成人视为异类,真正的原因在于秀贞的性行为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秀贞没有按照习俗被思康娶回去而怀孕。小桂子也没有在允许的时间①和仪式后出生,被认为是不合社会规则,因而小桂子被强行抛弃得到包括秀贞母亲在内的他人的一致认同。时间和仪式在此成为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正是这一点的不合规矩,秀贞的性行为和小桂子不为整个社会文化、道德体系所认可,成了被建构的另一个秘密,秀贞因而被划为异类。而英子不应知道秀贞成为疯子的秘密,同样因为时间(年龄),英子被从成人社会区分出来。
秘密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向一定的人开放的,秀贞没有遵从这一时间和空间的约定,从正常社会中被隔离了出来,秀贞被建构成疯子。而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秀贞问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你看我疯不疯?”秀贞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生理意义上)的疯子,而只是被人认为是疯子。秀贞不遵从成人的约定就被认为是疯子。在道德上不被允许的性行为应该是秘密,而秀贞不愿参与这一秘密的建构,阻隔了秀贞走向社会的正常通道,被宣称是异类。
(二)通过规则区分异类
成人社会通过秘密的构建、持有和分享,发现了疯子与儿童。通过制定规则,区分异类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方面②。分享着同样标准和规则的人被视作是同类人,成人间相互交往的规则由交往的双方协商,通常会在考虑社会资本、利益算计、社会区分或积极应对等方面因素之后而定。而成人与儿童的交往中,占有较多优势资源的成人便在规则制定中占有优势,儿童更多的只能遵从。
在影片《冬》中一开始冬冬和妹妹婷婷被作为累赘送往外婆家。母亲在病床上一直在叮嘱兄妹俩各种规则,要怎样不要怎样等等,兄妹俩只是回答:好。父母并未考虑兄妹俩有什么样的想法,只是一味制定规则。社会的规则同样如此,火车在即将开的时候不能上厕所,而妹妹并未遵从排泄的时间尿湿了裤子。舅舅并未征求妹妹想要哪条裤子随手取出一条裤子给妹妹,妹妹表示不想要之后,舅舅说“你真麻烦!”相比之下,为女友买衣服让冬冬和妹妹在火车站等待,舅舅没有嫌麻烦;等妹妹撒尿之时女友拿着她的新衣服迫不及待想要试穿,舅舅没有嫌不合时宜;女友落下东西,舅舅因给女友送东西误了火车,也没有嫌麻烦,因为女友在舅舅眼中是一个成人。舅舅和女友按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妹妹排泄时间,按自己的方便来为其换取衣物,在方便之余顺带安排冬冬及妹妹,将冬冬和妹妹被置于“顺带”的位置上。在成人的眼中,他们只有按照吩咐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这种约束或控制的标准是由成人决定的,儿童本身需求是被忽略的。妹妹上厕所这一有趣的情节恰到好处地将儿童与成人在规则制定与遵从上不同体现出来,这一添加的影片情节(朱天文原作没有出现)带来明显的对比:规则区分出了儿童。
被称为癫麻的哑巴寒子,打着雨伞游荡在村子周围,不能融入到整个村子的生活规则中,犹如被驱逐在城邦之外的麻风病人③,成了疯子。寒子被视为疯子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她会打人(打人是常人都会的事情),而是因为她生理上已是成人,其行为却不能遵从整个村子成人的规则,因而被宣称为癫麻,即疯子。而宣称这一事实的人便是规则制定者,并宣称寒子会打人。
正是通过规则制定者的分类、排斥、区隔和抑制使儿童和疯子的形象出现,这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现。
二、真儿童、假儿童与“疯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将儿童与青少年、成人等并列解释为生理意义上的概念,仅仅关注到了具有普遍特征的同质化群体,只是看到了一个社会结构化的儿童④,简单地将儿童看成同一个群体,将其解释为与青少年、成人、老人有差异的阶段,而忽略了儿童群体内部在社会中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地通过人与人交往实现,这是儿童走向社会的最重要途径。
英子与妞儿即是很好的解释。两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又很不相同,英子“悬置”了宋妈给她的“先见”,通过自己的眼光来认识秀贞。她看到秀贞“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跟秀贞玩的时候会用其他方式应对父母的查问,以保护自己和秀贞的交往的秘密不被大人察觉。而妞儿被妈妈告知秀贞是疯子的时候,却没有经过思考和判断便认同了成人的看法,仅因为大人说秀贞是“疯子”,并未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接触来认识秀贞,也不知道秀贞和正常人有什么不同,妞儿在与成人的交往中完全接受社会文化的建构,这正是妞儿与英子的不同。英子以一个并未被社会建构的纯粹的人的角度来认识秀贞,她甚至思考: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秀贞是这样可爱可怜,她只想找她的思康跟小桂子,为什么成人眼中那个玩着自己辫子倚在门前的秀贞是疯子?
《冬》中妹妹同样是在交往中认识寒子的。在大人们各自奔忙于自己的世界时,妹妹遇到了游荡在村庄之中的行为怪异并且据说还打人的“疯子”寒子,并未像其他小伙伴一样看到寒子到来就跑开,也在看到寒子并非虔诚地摆祭品时发笑。妹妹摔倒在火车轨道上,寒子不顾一切地救起了妹妹,并背着妹妹将其送回外公家门口,寒子也为自己这一勇敢的行为高兴得手舞足蹈。在被寒子送回家的路上,妹妹很享受在寒子背上的安全感,在不带任何偏见的交往中妹妹把寒子视为同类,并拒绝冬冬让她从寒子背上下来的要求。寒子为帮妹妹把死去的小鸟放回树上而被摔致流产治疗时,妹妹宁愿被外公呵斥也不愿意离开寒子,精神上的相契亦更进一步。治疗后的寒子独自躺在床上,妹妹将自己的宠物拿来放在又脏又乱的、没有蚊帐的寒子床上,自己也很享受地睡在寒子身边,并未遵从婆婆让她离开的要求。妹妹既未叫她姐姐,亦未叫她“疯子”,而是喊她“寒子”,称谓的背后是否意味着寒子与妹妹精神上的相投,正如《城》中英子扯着秀贞的衣服叫秀贞的名字一样。
而冬冬一开始就接受寒子是疯子而且会打人的认知,拒绝疯子靠近,并且在疯子勇敢救起妹妹后会让妹妹从疯子的背上下来。冬冬完全接受了社会建构的结果,与成人社会达成共谋,接受并再次宣称寒子是疯子。这一点从冬冬在火车站与同学极具社会化的交谈(谈话内容为某同学去了日本及相互间留了电话号码)中便可体会。冬冬与妞儿一样,对成人看法不加思考便认同,是社会文化的完全认同者与接受者。
将两部作品中的儿童做以对比会发现:英子和妹妹“悬置”了他人的先见,从纯粹的交往中认识秀贞和寒子,在关系中认识“疯子”,而并未接受社会文化“先在”偏见,英子与妹妹分别和“疯子”成为朋友。
冬冬、妞儿对疯子的认识源于成人。二人并未从交往的角度,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认识疯子,而是接受成人社会的先见,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个疯子,他们并未检验便接受了他人的成见和社会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冬冬和妞儿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儿童,是已经社会化了的儿童,这在冬冬定规则用跑得最快的乌龟交换汽车的方式解决伙伴们的难题中,在妞儿知道唱完曲要钱时大多数人会走的人情领悟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果称英子和妹妹为真儿童,那么可以称冬冬与妞儿为假儿童。
真儿童并非单指生物意义上的儿童,而是自然的,原始的,未接受社会习俗和文化熏染者的儿童。在西方由柯文妮(convenney)作为与邪恶的儿童⑤观点相对立提出的,其真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卢梭的《爱弥儿》。如果从这一意义上看,妞儿和冬冬虽是生理意义上的儿童,却是被社会习俗和文化所熏染、面对种种的现象开始像大人一样无动于衷的假儿童。我国古代对儿童的表述亦更能体现真儿童的内涵:道家用“天”、“真”、“纯”来表达对童子身上自然无伪的天性的认同;儒家则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4](P232)更有“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本心”[5](P368)的说法。
只有真儿童才能够与疯子成为同盟,但这样的儿童如何走向未来的现实生活更引起我们的忧虑。
三、儿童、教育与未来
儿童与疯子在可塑性与发展性上的不同使得他们在教育之途中将面临不同的未来。英子、妹妹与疯子能够交往并成为同盟,而这一同盟内部的根本区分在于:英子和妹妹具有可塑性和发展性,能够通过教育走向未来;秀贞和寒子则在可塑性与发展性极大的受到限制,通向未来的可能性极为渺茫。
冬冬和妞儿已是社会化的儿童,他们只是被告诉那是一个疯子,便认为那是疯子,是一种完全接受社会成见的认识方式,走向未来社会的通道已经铺就。这在他们各自的教育经历中已有表现:冬冬是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儿童,统一穿校服,规定上下课的时间,按时完成作业,这些学校规则是要被无条件接受的;妞儿虽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但她在跟随父母学习唱戏,接受了一种严格的家庭教育,在学习和表演的过程中妞儿被迫接受了社会规则的评判,在家庭教育中完成社会规则的学习。
如果只是一味拒绝社会的文化,一如秀贞和寒子,也一如傻子丙崽(韩少功《爸爸爸》),那样无法融入社会;如果只是接受社会文化,一如冬冬和妞儿,文化只能被复制而无以突破现有的界限得以发展。这一问题在卢梭那里通过自然人的培养来解决,但卢梭的局限在于其教育对象选择和教育实施的限定。福柯则通过向古希腊回溯寻找答案,也未能在实质上找到解决的途径。童年社会学家威廉·A·科萨罗(William A.Corsarro)的阐释性再构理论,以“创新(Innovation)和创造(Creative)”[6](P19)作为儿童社会参与中的特质,并用再构性(Reproductive)替代儿童发展的线性(Linear),在理论上指出另一条路的可能。
如前所言,英子和妹妹在自我的经验中认识疯子,而不是预先在自己的头脑中界定她是一个“疯子”。但她们也并未一味固执于自我世界,拒不接受社会的任何规则。英子明白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妞儿玩,也清楚如果别人看见她和秀贞拉手,自己会被视为异类;妹妹知道那些男孩子脱光了衣服游泳应该知道羞耻,清楚男女之间的界限,但并不仅限于遵循规则。英子告诉宋妈去找妞儿玩,当宋妈不注意时,拐进秀贞的家里玩;妹妹则无声的抵抗外公和阿婆,去关心和温暖受伤的寒子。她们在顺从秩序的同时保有自然的纯粹眼光,即顺从中有反抗。她们既没有纯粹的反抗习俗与文化,也没有被动地顺从社会,而是接受规则的同时不被规则掩盖自我的纯粹,这正是学校和家庭教育可探索的另一条路:社会化的同时以纯粹的自我体验来认知他人和世界,“是积极的,创造性的社会行动者”,“在参与成人社会生产的同时,积极生产特别的儿童文化”[6](P19)。
如果硬生生的把人从过去生活中剥离,结局是很难预料的。英子母亲通过搬家,让英子远离从前的生活,英子从昏迷中醒过来后总是有些事情记不起来,想问大人,妈妈又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英子的现在和过去有了一条沟。妈妈对英子的方式与秀贞母亲对秀贞的方式如出一辙:从过去的生活强行拉开,使现在和过去有一条明显的沟壑。如果英子如秀贞般不能从过去走出来,英子的未来也着实让人担忧。作者林海音通过“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7](P6)的方式走出这一沟壑。秀贞走入社会的契机也并非没有,那便是父母、周围人及秀贞对过去和现在的直接面对,避讳遮盖的方式是很难解决的。敢于正视的涉世也许会使秀贞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某君,最终治愈后赴某地候补去了,而不是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傻子丙崽般永远停留在生命中的某一段。
如果被硬生生地拽入社会当中才算“正常”,那么在进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系统后,是否可以接受社会文化的同时保有童子之心,做一个有童子之心的社会人?这是一个中西方教育实践领域共同的难题。教育系统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从本纳(Dietrich Benner)提出的教育实践不能优先于其他实践,应与社会中其他的实践系统是非目的-非等级关系,为我们在解决这一教育难题上指出一条可行之路:协调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各系统的关系,共同探索解决这一教育难题。
[注 释]
①艾莉·詹姆斯(英)等著,何芳译《童年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版,在文中提出“时间是一个定性而不仅仅是定量测量的手段,……儿童通过年龄维度对自己定位或被作为人在社会中被定位”。
②观点参见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版。
③米歇尔.福柯提出以鼠疫和麻风病两种对待精神病人的模式,分别是通过禁闭的方式和驱逐的方式对待。
④Frones,I.(1994)’Dimensions of Childhood’.In J.Qvortrup et al.(eds),Childhood Matters:Social Theory,Practice and Politics,Aldershot:Avebury.CAASP(Childhood as a Social Phenome⁃non),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童年”项目代表人物之一纽崔普(Qvortrup)为此项目辩护,将童年作为无差别的现象来考察。而艾莉森·詹姆斯(Alison James,1998)在《童年学》认为,CAASP项目的参与者对童年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单一的。
⑤艾莉森·詹姆斯(英)等著,何芳译《童年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版,在文中提出“邪恶儿童模式在16世纪的形成,它假定邪恶,堕落,自私是构成儿童的主要元素。”
[1][法]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著,沈坚等译.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2.
[2]王海英.解读儿童的秘密——基于社会学的分析视野[J].教育研究与试验,2005(1).
[3]吴刚.选择和分配:中国教育知识历史的社会学分析[A].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4](汉)赵岐注,旧题(宋)孙爽疏.《孟子注疏》,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重刊宋版十三经注疏本(卷13)[M].台湾:艺文印书馆,1993.
[5]李贽.焚书·童心说[A].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威廉·A·科萨罗(Willianm.A.Corsaro)著,程福财等译.童年社会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7]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A].城南旧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