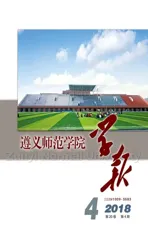《典论·论文》的文体学思想及其文化意蕴
2018-02-10李倩
李 倩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魏晋时代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而《典论·论文》作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更被看作是中国文学自觉的开始,成为曹丕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关于里面涉及的理论内涵,众多批评史著作以及学术论文都有提及,主要从批评方法论、流派论、作家作品论、文体论、文气论和文章价值论等六个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地全面论述。然而很少有人单独以其文体论作为侧重点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究。基于这种现状,笔者拟从文体语体特征、分体归类方法以及体类顺序与文化观念等方面对这篇专论所蕴涵的文体学思想和传达的文化观念进行深入探析。
一、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观念的滥觞
从先秦开始,人们的文章著书中便有了潜在的文体分辨意识,如《尚书》一书的诸多篇章中根据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使用场合分为谟、诰、誓、命等类;东汉蔡邕在其《独断》一书中将下行的诏令文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戒书四类,将上行的奏议文分为章、奏、表和驳议四类,并且对每一类文体的体制要求都作了详细说明。综观这些著作所涵盖的内容,或是文件汇编,或是公务文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一书中著述扬雄的观点时按照经、传、史篇、箴、赋、辞的顺序进行叙述,字里行间都暗含着作者的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然而也只是以排比的形式将扬雄的各种著述并列排序,而没有作出理论上的说明,因此没有作出文体学意义上的类型区分。
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文体学观念应该真正开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这篇专论中首次提出了文体的分类问题,将各种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P158对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或风格特征作出了大致的规定和概括,“本同”即把这些风格各不相同的文章看成一个整体,从而有了整体的文学观念。此后西晋的陆机在其《文赋》一书中论述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P171把文章分为十体,并且从这十种文体的艺术特征来阐述文章的体制风格,显然是对曹丕文体论的继承和发展。到了南朝刘勰,其《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更是将“文”“笔”分为八种类型三十五种文体,分别是: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和记。全面而又系统地阐述了各种文体的名称、特点、风格特征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之后的文学批评家在划分文体时更加具体,多达一百二十七种。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观念滥觞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很多关于文体学的思想都能够在这篇文章中找到源头,对于构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文体源于五经
曹丕以“夫文本同而末异”一句作为其文体论思想的总论,他的“文”涵盖了“四科八体”的所有文章,而“本同”便是这些文体的共性。简洁明炼地表明了自己的文体观念,即所有文体的本源和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源出于五经。这种观念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源于中国古代早期的哲学观。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这些事物都是由一个本源发展演变而来的。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P46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本体论思想,“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自然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源。儒家最初以“天道”观为其哲学本体论,到汉代发展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思想有所变化但都秉承着世界只有一个本源的根本宗旨。而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种早期的一元论的哲学本体观反映到文学上来便同样坚持着一元的观点,认为所有文体的本质本源都是相同的。
其次是“通古今之变”的文学观念。中国古代著书立说都喜欢追本溯源,因此“文源五经”的说法由来已久,并且得到了很多文人作家的认可和继承。扬雄在《法言》一书中称:“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3]P5班固在其《汉书·扬雄传赞》中认为:“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4]P1176在其之后的挚虞在创作《文章流别论》中更是始终贯穿着“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的思想方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创作中同样坚持“原始以表末”的研究方法。诸此种种,都把“五经”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而认为文章大多来自于“五经”。
最后是源于曹丕个人对儒家五经的精通与重视。这一点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表明,如《与吴质书》中写道:“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5]P8在《典论·自叙》中写道:“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5]P12此外,他命令桓范,刘劭等收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编撰类书《皇览》。凡此种种,皆表明曹丕的思想是继承儒家传统的,因此,他的“本同”一说即所有文体都来自于儒家五经。
三、化繁为简、繁琐细分的分类方法
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四科”指的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根据文体之间的相似性,两两相并来论述。以“四科”来概括各种文体,采用的是以简驭繁,以类相从的分类方法,这种以文体形态为主的的类从分类法,使得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术从散乱走向整一。“八体”分别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而用“八体”来分述各种文体,则采用的是繁琐细分的分类方法。相比之下,后者则更能体现出古代文体的文学性特征。
(一)文体排列顺序
在文体排列顺序方面,曹丕按照文体的语体区别采用“先笔后文”的排序方式,代表了一种汉末魏初人的文学观念。排在首位的是奏议,然后是书论,接着是铭诔,最后是诗赋。这种文体顺序表明在他看来不同文体的地位其高低是不一样的。奏议书论等文体皆为“无韵之笔”,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这类文章的价值和社会功用是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在诸多文体中放置在前面。而诗赋等“有韵之文”,是“纯文学”,更多是表达个人的情感价值,与国家政治相比,是小众的情感,因此将其放置在最后。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曹丕对文体有了初步的探索,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文化典籍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是以一定的秩序性为指导。三国时期魏国的鱼豢在其《典略》中描述繁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6]P449先言书记后说诗赋;宋人真德秀在编撰《文章正宗》一书时同样采用“先笔后文”的文体排列顺序,其《文章正宗纲目》言:“汉世有制,有诏,有册,有玺书,其名虽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为重,故今以为编之首。”[7]P106因此把“辞命”这一类文体置于开篇;元人苏天爵在编写《国潮文类》时将诏敕、册文、制等下行的文体放置在奏议、表、笺等上行的文体之前,同样表明了古人的这种传统的文体观下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政治教化、等级尊卑的宗法观念。
(二)文体风格
语体作为文体的四个结构层次之一,鲜明地反映着特定文体的语言风格特征。因此,中国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有一整套自成系统的语词。[8]P9从《典论·论文》开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便有了辨析各种文体的语言风格的意识。
《典论·论文》中明确以“体”为中心,并表明“文非一体”,从“文体”这一角度出发,认识到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与风格功能的差异性。所提出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用“雅”“理”“实”和“丽”四种不同风格的词语来概括这四种类型八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和风格特征,虽然用词简单,但其把握是十分准确精当的。
奏议类文体作为一种公文类文体,是臣下上呈供统治者阅览的一类文书。最初产生于尧舜时期,当时采用的是言语行为方式上奏而没有书面凭证,到了商代开始出现文书上奏的形式,之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发展,到秦朝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文体的总称,汉代“奏”“议”两种文体并列相称,指代两种略有差异的不同的文体,同时新增了章、表两种文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用“奏议”一词来概括汉代章、表、奏、议这四种本同末异的文体,考虑到这类文体的社会功用加之使用对象的身份的特殊性,选用“雅”字来概括此类文体的语言风格特征,并且在论述时将其置于其他三类文体之前,大大提高了奏议的文体地位。
书论类文体作为一种议论性文体,以“说理”为其主要特征。东汉王充《论衡·对作》云:“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9]P146由此可知这种文体最初盛行于汉代,主要受东汉时期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以及清谈辩论文气的影响,代表作品有扬雄的《太玄》和《法言》。许多文士根据其写作特点和要求对其风格特征进行了说明,如王充曾在《论衡·超奇》论述道“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9]P134;徐干在《中论》篇云:“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10]P135虽然时人多有说明,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书论宜理”一说,是他对当时人们所提出的有关书论类文体创作特征的高度概括。
铭诔类文体属于记叙性质的文体,主要是一些记述死者经历表示哀悼和歌功颂德的文章,同样盛行于汉代。桓范《铭诔》篇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11]P271由此可知汉魏时期送葬风气奢靡,对死者生前的行事作风缺乏真实记录,加之曹魏“尚实”的政风,因此曹丕强调这类创作必须以“尚实”为写作原则。
诗赋类文体属于抒情性质的文体,属于纯文学,虽然曹丕在文体分类的排列顺序上将诗赋二体排在了最后,但他所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将“诗赋”区别于其他文体而单列一类,并且指明其具有“丽”的审美特征,认识到了诗赋这类纯文学作品与其他应用性文章的本质区别,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因此下面将单独论之,以表示其影响重大。
(三)诗赋欲丽
曹丕在其众多文章中对“诗赋”二字多有提及。《典论·论文》论及作家作品论时,首论“王粲长于诗赋”[1]P158;《与吴质书》中称赞刘桢“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5]P8;《与王朗书》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12]将诗赋与《典论》这一文学批评史巨著相提并论,其对诗赋之重视程度足以见之。
曹丕所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发展的一大胜利。以“丽”来概括诗赋的风格特征,将诗赋从政治、功用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是对以往重教化、重功利、重实用目的来评判文章价值的认知方式的一种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地位独立的开始。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3]P491
可见,如果没有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是不可能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如此细致区分的。[14]曹丕在论述这四类八科的文体特征时都考虑到它们的功能特征,在此之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唐宋类书中都有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辨析不同文体的语体特征及其功能,因此这种论说思路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在论及文体时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四、文体分类蕴涵的文化意蕴
文学作为一种人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蕴涵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意义。曹丕所采取的“先笔后文”的文体排序规则体现了魏晋时代浓厚的文化观念,即中国古代士人特殊的精神文化观念。《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5]P640“三不朽”之说是传统儒士所奉行的人生价值观。在他们眼中,立德与立功是首要的,立言虽然也可“不朽”但却置于二者之下处于末流的地位。在与此相似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文学”同样处于最后的地位。曹丕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同时更重要的身份是作为一个政治家,难免会考虑文章的社会功用,把文章提高到与国家大业同等的地位。[16]因此,在曹丕的观念里虽然文章写作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然屈居于立德,立功之下。“诗赋”二体与那些和国家政治功名相关的奏议、书论、铭诔相比,只能放在末位。因此,在这种文体排序背后渗透着一种内在的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观念。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本同末异”和四科八体的分类的观点涉及到文体学的文体语体特征、分体归类方法以及体类顺序等诸多方面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雏形,虽论述简洁且不够完备,但开创了文体论研究的先河,同时其中暗含着魏晋时代文人的宗法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因此是我们研究魏晋时代文体学和文化学的一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