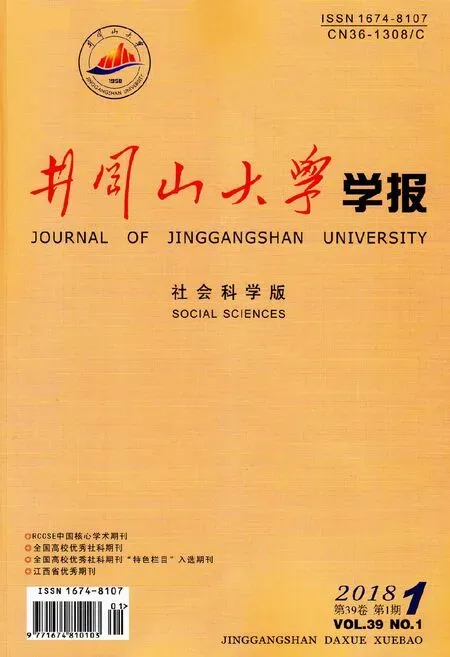论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以庆阳顺风车案为例
2018-02-10温金童王小英
温金童,王小英
(陇东学院政法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1946年6月,陕甘宁边区庆阳县赤城区七乡村民王长发,半道上搭乘村民王兴富赶牛车时,不慎跌落车下,被车轴撞伤后身亡。家属向县府提出控告,认为王长发不明不白地死掉,要求县府从严查处。庆阳县法庭经过仔细访谈、讯问,与双方协商沟通,最后达成了调解协议。这是一起非典型的因“好意同乘”引发的官司,边区法律工作者妥善处理这起诉讼纠纷,彰显了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边区司法原则。
一、案发背景
案子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庆阳县赤城区。庆阳县位于甘肃省东部,泾河上游。东邻合水,南与西峰毗邻,西隔黑河与镇原相望,北与华池接壤。全境为典型的黄土高原残塬沟壑地貌,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具有明显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特征。[1](P125)因地高气寒,自然灾害频繁,素有“三年一旱,五年再旱”之说,有时又多遭水患,且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这些都是造成边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自然因素。革命以前,又受到军阀、地主等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了50%以上必须当做地租交给地主以外,还须以一部分当做各种捐税交给军阀和官僚,有的还要以一部分当作利息支付给高利贷资本家。[2](P138)早在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开始在庆阳传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庆阳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部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从敌占区逃来边区的移难民甚多,而因国民党地区人民受到天灾人祸、压榨,不能生活逃来边区者亦属不少。 ”[3](P400)边区的移民工作,“虽然从1940年起,就开始注意,但是在1943年以前,只是局部地区注意移民,主要还是自流状态。”[4](P643)因此,有些地方的移难民因为拖家带口,加之缺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等,生活还是比较窘迫的,本案中的受害人就属于此种情况。
随着庆阳县成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政府机关所在地,八路军385旅驻防庆阳,承担起保卫边区西大门的重任。庆阳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政令和决策,开展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教育的全面建设,实践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5](P8)特别是大生产运动期间,为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385旅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旅长王维舟组织了15人的生产小组,定名为王维舟生产小组,耕种水地、旱地30余亩,种植棉花、蓝靛等经济作物。此后,旅直部队先后开办了铁工厂、木工厂、饲养场、造纸厂等工厂23处,并与当地军民合办了庆兴纺织厂。到1941年,不仅解决了部队的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供给,还为当地群众解决了许多困难,安置了上千名因贫困而流入边区的移民和难民。中共陇东地委和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主要负责人也都亲自参加劳动,深入农村督促广大干部群众开荒种田,地委和专署机关在庆阳城南席芨沟一带垦荒,种植烟叶、麻、油籽等经济作物和蔬菜。专署机关除兴办一处大型农场外,各部门还各自开辟了一个菜园,配备了富有经验的同志负责经营。[1](P186-187)在陇东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较抗战前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当然,这种提高只是相对而言,认为家家户户都实现丰衣足食的目标未免太不切合实际。
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陇东分区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发源地。“马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刘巧儿”的传奇路人皆知。“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为人民司法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至今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辉。”[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影响下,陇东地区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比较高,人民群众普遍具有了主体意识、平等思想等法律意识,知法、懂法与守法的观念得到增强,维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庆阳县赤城区的这起顺风车案,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本案死者王长发,殁年50岁,原籍河南,因老家灾荒来到庆阳,案发时住赤城区第七乡三村,文盲,家中赤贫。原告李陵主,王长发早年过继给别人的儿子,时年22岁,案发时住合水县一区上庙庄,种地为生,家中没有牲口,租住别人的一处庄子,文盲。被告王兴富,46岁,家住赤城区第七乡曹家渠村,有六十亩原地、四十三亩山地、二牛一驴一马、二处庄、八只窑,家境殷实。王兴富是文盲,案发时任村主任之职。案件所涉另一关联人、牛车的主人王开简家里也很富裕,有一顷地,十口人,六只牲口。[7]交代这些背景,一则因为法律的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人民生活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习俗,[8](P7-8)另一方面案件当事人生活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其生活习俗相仿,政治认识水平差别不大,但家庭经济条件较为悬殊,这是案件发生和最后成功调解的重要依据。
二、一个好意同乘的非典型样态
1946年6月5日,是赤城逢集的日子,远远近近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涌来,买的、卖的、变戏法的、逛大街的……十分热闹。赤城区第七乡的村民王兴富,也坐着王开俭的牛车前往赤城集市卖粮食。牛车上装的粮食计有王兴富的一石八斗麦,王开简的一石麦,刘金海的一斗麦、一斗米,共是三石粮食。车是王开俭家的,拉车的是王兴富的两头牛和王开简的一头牛,赶车的是王兴富和王开俭十五六岁的侄儿王双娃。牛车行至白马铺鸭儿沟的时候,碰到同往赤城赶集的王兴富的亲戚王长发。王长发也是赤城七乡三村的村民,见到熟人赶车,便热情地打招呼说:“姨夫,你去赤城赶集吧?捎我一程吧。”王兴富问道:“你做啥哩?也去赤城赶集吗?”王长发回答他去赤城集上卖了羊毛修锄头。说着,王长发将一捆黑羊毛放到牛车上,自己往牛车前面坐。当时王兴富坐在牛车左面,赶车的王双娃坐在牛车右面。王长发本是打算坐在牛车前面,不成想一下子没坐上去反而掉下车,被牛车轱辘压到脚了,王长发趴在地上,又被车轴撞到了后脊背,大车也坏了。王兴富赶紧喊来旁边锄地的张喜原父子二人,大家一起把王长发抬到路边。王长发叫来了他的女婿范仲,奄奄一息地对女婿说,是他自己去坐人家的牛车,现在出了这事,怪不得王兴富,就算他死了也与王兴富不相干。随后大家就把王长发往家里抬,抬到半路,王兴富回去收拾牛车,顺便买了些治疗跌打损伤的三七药材。等到王兴富晚上回到家时,王长发已经死了。[7]案情本身并不复杂,王兴富、王双娃赶着王开俭的牛车去集上卖粮食,偶遇同样赶集的亲戚王长发,便准备搭上王长发同行,不意仓促间王长发跌落车下,为车轱辘、车轴所伤,不久后死亡。
王长发之死,彼时并无明确的法理认定,以目前的司法实践观之,当属好意同乘致死的范畴。虽然国内学者对好意同乘并无明确的界定,但国际上对于好意同乘则限定得比较清楚:“乘车人在运行供用者好意并无偿地邀请或允许下同乘于运行供用者之车的现象”,同乘人可以是好意人的朋友、 邻居或仅仅是半路上偶遇的陌生人。[9](P100)也就是说,“好意同乘”完全是一种好意施惠行为。对于死者王长发而言,王兴富答应他搭便车仅仅是为了增进双方之间的情感,是其乐于助人等道德情操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提供这种帮助。依据这种逻辑,为了研究方便,就没有必要依照法律行为成立的生效要件来对其作出呆板的规定。
之所以称本案为好意同乘的非典型样态,在于现实意义中的好意同乘指的是机动车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而“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现行法律把好意同乘限定为机动车辆,是因为机动车辆的时速高、质量大,而非机动车时速低、质量小,因此机动车的危险性较高。这种限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做法也是一致的。[10](P14)但是必须考虑的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山高路远沟深,交通十分闭塞,非机动车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机动车,因此,将那个年代的搭便车或搭顺风车行为视为早期的 “好意同乘”,并无不妥。
三、乡村调解
国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第一选择往往是找中人帮忙,打通关节。这种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现象,当然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传统社会生活的维系和社会秩序的控制上,讲求人情、考虑社会关系实际状况的“礼”显然重于客观而不讲人情、寻求消弭差异的“法”。[11](P104)同时,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既能从行动上解决纠纷,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从“心理上”解决纠纷。[12](P347)何况,自“1942 年以后,陇东分区开始普遍实行人民调解制度,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和审理”。[13](P310)这起案子发生以后,由乡村调解自然是首选。问询记录显示,王长发家境贫寒,都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缺乏必要的劳动力。
问:你这次葬埋费了多少钱?
答:我们费了七万多元,我们想卖牲口没牲口,地没地,有些地也荒置了,柴水没柴水,现在不得开交。[7]
乡村调解的主要内容是王兴富给王长发家属补偿一些粮食:
六月十日,村长说合,叫王兴富帮助一石二斗麦,我们也没争论。随后又找到乡长。乡长任宽完全同意村长的意见:既然王长发家庭困难,不得抬埋,就让王兴富帮助粮食一石二斗 (王兴富出八斗,王开简出四斗)。当时双方都同意了乡间的调解意见,还写了具结字据,王长发家是由大兄王常福代表,双方皆划了押,表示同意。初十日下午埋我王父的,是跟前的亲戚四邻帮助抬埋的。[7]
任乡长还对死者家属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两家吵来吵去的也没啥意义,好好让死者入土为安就算了,让王兴富帮助王长发家一石二斗麦子就对了嘛。[7]
既然双方画押同意,这件事情本可就此平息,但出乎意外的是,王长发早年过继到合水县的儿子李陵主不同意乡间的调解意见,要上告到县政府去理论。依照中国传统社会司法实践的惯例,一向重视和推行调处息讼。当事人可以通过有权威的民间途径解决争执,告官成为最后的选择。正如英国学者斯普林克尔所说,乡土社会是“反诉讼的社会”,因为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的冲突。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借贷、田地、婚姻等民事案件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亲戚邻里之间对簿公堂,极易破坏已有的人际关系,并有可能遗祸子孙。[11](P9)难怪主持调解的乡长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李陵主不明事理,胡搅蛮缠,见到李陵主还十分气愤。据李陵主言:乡长对他说,你早就是李家的人了,现在也管不上王家的事。还说如果李陵主继续告状,就叫李陵主把王兴富已经给的八斗麦子退出来。”乡长指斥李陵主“现在管不上王家的事”,貌似合情,实则违法。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案例中,是承认边区存在的“归宗”习惯效力的,而且赋予了当事人依习惯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并将之作为被收养人的一项权利加以保护。[14](P158)汪世荣教授对边区“归宗”习惯的研究表明,在本案中,李陵主有权利提起自己的诉讼请求。
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曾经提出,“调解是更高层次的审判”,对于这种“更高层次”的审判方式,调解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人通常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而不会过多地考虑诉讼本身的道德或价值评价。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调解人必须把握时机,遵循规律,注重场合及主体。[15](P247)考虑到父亲死后家庭实在难以过活,李陵主对区上的调解处理不满意。李陵主提出,其父王长发是帮着王兴富赶粮食车出事的,王兴富家境殷实,不但有马、牛、大车,还有很多良田,现在撞死了人却只赔偿八斗粮食,太不像话。遂以死因不明、需要详查为由到县政府提出申诉:
本月六日赤城逢集,民父为王兴富赶车拉粮同赴赤城赶集。此晚,王回家言民父被车碾毙,民弟即同人去抬,王将民弟隔于门外,同其他人等嘀咕了半夜,将人抬回。经乡里调解后葬埋,而未验尸。葬时王帮粮石余。告到区里,王兴富胡言推托,总言被车碾死。想民父赶集时,自己前往,难道闲来没事睡于车壕待死?民父死因不明,呈县查究。[7]
小小的赤城区七乡与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属于熟人社会,当地人相互之间十分熟悉,就连谁家走失了一只羊这等事几乎全村人都知道,熟人之间为了邻里关系经常会达成某种妥协,乡村舆论约束力对村民的影响力不容低估,违背民间协议的后果很容易受到众乡亲的舆论谴责[16](P119),使当事人很容易在以后的生活中被邻居和村民唾弃。
李陵主不会不知道拒绝乡间调解的风险。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有自己的苦衷。他申诉的要点有二:一是其父是为王兴富赶车出的事;二是其父死因不明,王兴富有害命嫌疑。但从庭审笔录不难看出,李陵主紧盯的这两点其实多半为臆测,并无真凭实据。他咬住王兴富不放,可能缘于其“对诉讼结果的过分关注,对诉讼行为性质的偏颇认识,一场‘官司十年仇’”[14](P159);也可能因李陵主家在合水县,并不在庆阳县赤城区,对邻里亲情的顾忌更少一些;但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为家中骤失顶梁柱的孤儿寡母多讨要一些补偿。
四、县长再审
无论多么完善、多么成熟的法律制度,相对于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必然也存在着漏洞和空白。法官在断案时势必会碰到诸多法无成文规定的情形。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的要求是:“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17](P1)根据边区《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县司法处设处长1人,审判员1人,书记员1人,县司法处处长由县长兼任,负责各类案件的审理,审判员协助处长办理审判事务。[13](P310)接到李陵主的申诉书,庆阳县长兼司法处长杨福祥、审判员金凤岐等正是本着上述规定精神,重新审理了这起案子。为全面了解事情原委,杨福祥县长先是给赤城区区长写了一封信,咨询事故详情:
区长:你区七乡王兴富之车古五月六日将王长发辗死,现在李陵主来控告,该李说他父帮王兴富赶车,同时他家中赤贫,生活艰难,这次又花费抬埋费七万余元。是否确实,请将这次详情来信。及时速将王兴富传来到案,以便审理此案为要。[7]
在赤城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杨福祥重新讯问了相关人员。讯问首先证明案发时李陵主并不在场,他是在事情发生三天以后才知情的,同时也表明死者王长发家生活的确困难。
问:你啥时才知道?
答:我初九日晚才知道。我给土桥区王文秀家做活,王文秀给我说的。
问:你父有几个儿子?他家中过的如何?
答:我弟兄六人,大的保娃十六岁少亡(土窑塌陷砸死),二的就是我,三的叫王富来,四的叫王三娃,五的叫王月子,六的没起个名字。我父亲现年五十岁了,现在我老家共有五口人,四个弟兄,还有亲生母亲。一家人租下邓成玉六十六亩山地,每年庄稼都是我王家父亲耕种。家里只有四个破窑洞,我父亲不识字。这次葬埋父亲费了七万多元,我们想卖牲口没牲口,卖地没地,要柴水没柴水,现在日子完全过不下去了。
问:谁给你证明你王父给王兴富赶车的?
答:没有证明。
问:你父到底给王兴富赶车否?
答:赶车不赶车我也不清楚,反正我父就是王兴富的车撞死了。
问:车是王兴富一人赶的吗,还有谁?
答:王兴富与他侄儿。
问:车上是几个人的麦?
答:王兴富说他拉了三石麦,他与王开俭二人的麦。
问:给你一石二斗麦,是借的还是帮助的?
答:乡长说有良心了以后给,后来没办法就算了。
问:你当人命的告,还是当帮助费的告?
答:就是不得过活没办法告的。
问;你三弟多大了?
答:十五岁了。[7]
这段询问笔录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李陵主的诉求。
其一、李陵主之所以成为“反诉讼乡土社会”的叛逆者,得益于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陇东地区的广泛影响,自身维权意识有了增强。庆阳作为陇东分区的首府,20多年民主革命的思想不可能不对乡村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二、“谎言经不起打击, 而真相却可以。 ”[18](P108)李陵主申诉中所提到的“民父为王兴富赶车拉粮、死因不明”等等,于事实无据,纯属主观臆测,他本人也未必相信这些胡言乱语。
其三、李陵主申诉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究王兴富的命案责任,而是其父死亡之后,家中无有劳动力,生活极其窘迫,迫切需要帮助,希望家庭富裕的王兴富能够对死者家属提供更多的物资支持。
杨福祥们当然读得懂李陵主隐藏在背后的话。为了以理服人,庆阳县司法处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收集到了以下关键证词:
民等是赤城区第七乡三村村民,依实呈报:因有王兴富、王开俭古五月初六日赶车一辆前往赤城卖麦子,行至鸭儿沟路畔,不意来人王长发上车失足滑到,被车撞到硷畔受伤,现时未死,将他女婿范仲叫来,同民等当面说清他的受伤情况,是他自己要将羊毛放在车上,坐车被车撞伤,你们可对我家人说明,与王兴富不相干。民等抬至高户约路五里人业已死了。因家中困难无法埋人,经乡长同民众调解,给王长发他家帮助麦子一石二斗,王兴富出八斗,王开俭出四斗。当时有王长发大哥王长福当面承情领受,再无他说。不意他过继出去的儿子李陵主回来呈报政府,民等只依实证明。证人:刘金海、常正廷、赵玉杰、陈仲福、雷有福、代银(后三人名字不清)[7]
没有完善的法律条文,客观上为审判者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审判者的素质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马锡五曾经深有感触:“三个农民佬,顶一个地方官”。[19]杨县长召集一众“农民佬”,耐心听取大家陈述案发事实,结合调查对象的一致证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使案件得到公正解决。1946年6月14日,彻底查明事情真相后,根据庭审及调查结果,司法处作出判决:
(一)原告李陵主控告人命无理。
(二)被告王兴富等人可帮助已死者王长发抬埋费三石麦子。
事实:缘在本年五月初六日,王兴富、王开俭两家套了一辆车,王兴富载了一石八斗麦,王开俭一石麦,刘金海一斗麦、一斗米,共载了三石粮食去赤城集市出粜。赶车的人是王兴富与王开俭之侄儿双娃二人,后路遇王长发,身背三斤半黑羊毛,手拿一把坏锄头,王长发将他所拿的锄头和羊毛捎在车上,去车前当中坐,不意被车将王长发的脚辗住,后待避脱,又被车轴将脊背顶伤了,王兴富即时叫来杜仲等人抬回,距家一里路,王长发气绝,经当地乡长调解,着王兴富帮助出一石二斗麦子,而李陵主不同意(李陵主是王长发子,卖给李家的)控告本处。言说,他父被王兴富之车辗死,在抬埋当中花了七万元,家子也很赤贫,无劳力、无牲口、地无可卖。所以生活实无办法,经本处审讯属实。
理由:根据以上事实,王长发在王兴富车上捎羊毛,又去车前坐,不幸被车辗伤毙命,这是一件两不幸的事情,但是要怨死者偷懒坐车又不在意,原告李陵主当人命的控告没有道理。不过王长发家中赤贫,又无劳力,这次王长发为坐车死故,可将车上所载的三石粮食帮助给王长发作抬埋等费。故判决如主文。[7]
五、结论
“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不得不依据现有的法律来对这类特殊的侵权案件作出判决。[10](P37)杨福祥、金凤岐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没有现成的法律条令下,尊重事实,尊重民情,作出了当时情境下的最佳选择。
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有序进行。作为一种除了道德之外所存在的最为广泛的社会规则,法律的制定当然应当以人为本,充分考虑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生活、生产活动的需要。[10](P18)案发前的1946年4月,马锡五已赴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髓在这起案子中仍得到了具体灵活的运用。“马锡五审判方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深入调查、合理调解,集中为一点,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司法工作的基本方法:“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据、口供必须经过查对,反对逼供信,禁止肉刑等。 ”[20](P3)在庆阳顺风车案中,王兴富为王长发提供无偿的搭便车机会,展示的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传统道德。在整个过程中,王兴富并没有获得也没想获得任何的物质利益,本身也不以追求金钱报酬为目标,其为王长发提供无偿搭便车机会,纯粹是出于好心而不是歹意。司法处判决理由中提到“两不幸”。意为此次顺风车事件对死者、生者而言都是悲伤的“不幸”,审判人员要做的就是通过调解,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既能坚守立法工作维护良好社会道德的本质,保护好心人的善意,又能给死者家属以必要的生活补偿。
在调解过程中,庆阳县司法处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特有的亲和力,让冷冰冰的法律在普通民众面前显得格外亲切,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法律”。就这个意义说,庆阳县对王兴富车碾死王长发案的审理、调解,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充分尊重民意、体恤民情,调解结果为当事双方共同接受,体现了边区法律以人为本,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值得今天的法律人仔细深思、揣摩、借鉴。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民主司法、司法公正、确保人民参与司法过程”[21](P203)。法治中国建设任重道远,人人有责;法律人责无旁贷,理当谙熟转型社会矛盾发展的多方面特点,努力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凸显法律工作者的中坚力量。
[1] 闫晓辉.红色印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
[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C].西安:档案出版社,1986.
[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C].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5]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M].内部资料,1996.
[6]周强.发扬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N].人民法院报.2014-10-23(1).
[7]关于“王兴富车碾死王长发”案材料[Z].庆阳县政府司法处32-65,庆阳市档案馆藏.
[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0]张宗菲菲.好意同乘民事责任探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2.
[11]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2]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3]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4]汪世荣.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民事习惯的调查、甄别与适用[J].法学研究,2007,(3).
[15]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6]蓝寿荣,武睿彬.论民间调解的乡土逻辑及其政策建议——甘肃天水五个乡村调解个案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6).
[17]马锡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J].政法研究,1954,(12).
[18] 泰戈尔诗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9] 张希坡.党的群众路线与马锡五审判方式[N]. 人民法院报,2013-09-27(4).
[20]马锡五.最深刻的一次教育——记主席在延安杨家岭的谈话[J].人民司法,1960,(7).
[21]陈兵兵.习近平法治中国建设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人民论坛,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