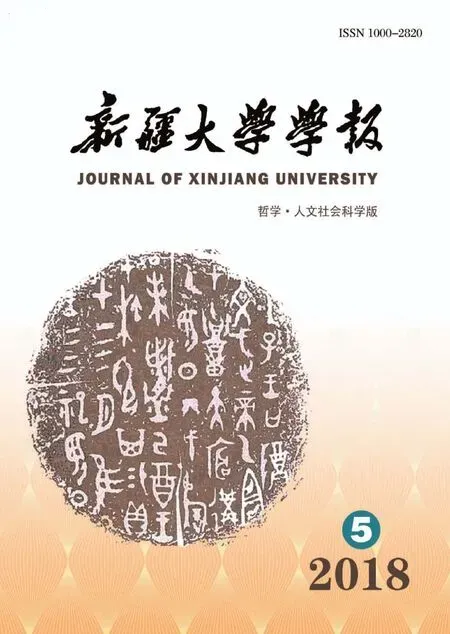全球化下西方社会的国族境遇与国家治理困局*
2018-02-10刘永刚
刘永刚
(1.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2.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由现代“民族”(nation)建构掀起的以主权国家为取向,将特定区域内(领土)的人口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是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路径。在这个国家与民族互相证明、互相塑造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以一个稳定的、全新的忠诚义务联合体的政治形式获得了国家属性与国族(state-nation)地位。以“民族”为中心、以国家的“民族化”为途径克服诸多危机,既是西方早期国家兴起、强大的政治基石,也是认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视角。然而,因全球化带来的跨国流动主义、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治理体系功能的弱化,西方各国的国族无一例外面临着被削弱的现实境遇。同时,因国族的内部聚合力不足与社会秩序供给乏力呈现的国家特性弱化状况,使西方各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国家治理困局。
一、全球化下西方社会趋强的异质性对国族整体特性的削弱
政治、领土的国家与历史、文化的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成员的统一民族身份与国家的整体特征。但全球化下西方国家国族的形式化与国族认同的弱化,已成为西方各国无法回避的客观问题。不断蔓延的多族化现象与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得曾经有效凝聚国民、促进聚合的国族因素处于弱势或不复存在。
1.全球化下国家内部趋强的异质性与成员的多族化,整体国族的聚合性与政治认同的中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从世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领土主权原则成为确认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原则。国家的合法性,除了静态的疆域制度与动态的政治行政绩效外,一体化国族的存在与聚合性功能则是基础性的保障。虽然,民族国家内成员的基础性身份与国族认同内核均是由国家政治体所赋予的国民身份。但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跨国流动主义与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一方面是对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国民身份价值的削弱;另一方面因利益诉求的拥挤性或排他性,族际间的竞争、博弈乃至纷争在西方各国此起彼伏、轮番上演。可知,因全球化带来的国家经济、社会、认同等的系列安全问题,使得西方社会以国民身份为基础的国族中心地位遭到动摇。
全球化推进的过程,在西方社会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多元认同的泛化。这种多元认同状况对国家成员的国族忠诚与国族认同的解构不言而喻。同时,不平衡的国际秩序与国家内部人群间竞争的白热化,“民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突出差异最为廉价、但却最易打动人心的工具。西方社会将基于个体的自由主义应用于族群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①具体内容可参见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2-91页。,就是“民族”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直观体现。就当前西方社会而言,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白人至上”、移民的国民化、难民治理等,使得各国均无一例外的面对所谓的“民族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今的“民族主义朝向两个极端发展,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矛盾与宗教对立互为表里是冷战后世界各地民族问题普遍存在的主要特征”[1]。而所有问题的实质,是与国家高度结合的国族(state nation)认同弱化的境遇。
2.普遍的、全球的人口跨国界流动现象,极大地影响并重塑着西方国家的国族结构
移民及跨国流动主义带来的移民问题全球治理,在突破民族国家传统行政边界的同时,双重国籍、多重认同又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国的治理能力。有研究指出,“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 亿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2],2015年初的欧洲移民危机更使得移民问题治理成为欧洲国家的中心议题。然而,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路径,一方面在抑制“非法移民流入、恐怖主义入侵,维持了本国国民的福利水平,但牺牲了民主原则和个人自由,带来了同质社会的风险,也制造了社会的二元对立和矛盾”[3];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国形成的移民社群很容易形成新的民族群体。当前欧洲国家因移民出现的“伊斯兰化”现象,已成为撼动各国安全基础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国家共同体建构与解构,成为当前世界格局的两个基本趋势。全球化并未如期实现世界一体化,相反,“它是一个始终伴随地方化、充满差异与断裂的过程。”[4]西方社会多元思想的生产与多元价值的供给,使各国成员思想意识和价值认同经历着一定程度的震荡和重塑。而流动中的人群“在内部进行自我建构和证成的各项要素却给它在外部带来了自我解构和证伪”[5]。全球化下,西方各国不同程度的移入人群和原有居民的族体认同强化的现象表明,因国族人口结构的改变,各国国族认同政治的中心地位被动摇。国族对内的凝聚力与对外的特殊性,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世界全球化在强化本土身份意识的同时,激起的流动人口族体价值的再发现现象,表明国家内部异质性增强与国族一体化需要间的内在紧张。
3.异质性强化催动的“自决运动”与“独立公投”,已成为肢解西方国家体系的潜在样式
在20世纪初叶形成的民族自决理论,在20世纪末再次显示其惊人的能量。该理论在肢解苏联、分裂南联盟、南北苏丹的同时,欧美世界的民族分离运动、其它分裂活动在21 世纪也呈强化趋势。除英联邦的北爱和苏格兰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困扰西方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外,近年来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有回潮的迹象。另外,以“公投”为主要形式的民族自决运动,在西方社会几乎没有停止过,并成为西方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无法回避的严峻事件。其典型性事件如先后2次(1980、1995)失败的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投、2014年以失败告终的苏格兰公投独立运动掀起的欧洲大陆“独立”风潮,并以2017年被西班牙政府认定为“非法”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州的独立公投为巅峰。
曾经史密斯笔下的美国被描述成一个虽有族裔冲突,却“没有导致族裔民族主义出现”的成功国家[6]126。但近年美国的种族冲突对社会一体的撕裂呈恶化趋势。自“洛杉矶事件”后持续不断的种族冲突,更是在2016年末进一步升级为持续近一年的以弗吉尼亚州为中心的“夏城暴动”。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高呼纳粹口号,举行被称为“几十年来最大的仇恨聚会”,将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种族斗争伤疤再次揭开。暴乱后,弗州被覆盖的“罗伯特·李将军”雕像仅是美国多个州掀起移除纪念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Confederation)的相关雕像和纪念碑运动的一个缩影。而掩盖的“李将军”塑像成为美国社会被撕裂的表征。
二、族群的“民族化”:族群正义诉求对国族一体的侵蚀
作为现代国家立国之基的“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旗帜,往往掩饰着曾经的血腥掠夺与驱逐。基于对历史时期粗暴的同化主义反思,20 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掀起了西方世界的“族群正义”话题。以少数族裔为对象的平权运动,直接推动了族群的“民族化”。以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族际政治民主”的理论与主张推动的“族群正义”往往指向国家民族的一体问题,并成为肢解国族的汹涌暗流。
1.作为“族群正义”理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试图以文化平等的方式解决国内的族际冲突
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建国历史上的种族压迫、歧视等的反思,以少数族裔为对象的“正义”话题,在西方形成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完整理论体系。在国家政治整合的实践上,多元文化主义是以批评并替代同化主义的形象出现的。如该理论直接将西方国家历史上各种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政策,诸如公民资格、取消少数群体自治、使用多数群体的语言、创立传播多数群体的民族媒体标志假期和博物馆、采取多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教育、以多数群体的语言去服义务兵役制等①具体内容参见Will Kymlicka.Identity Politics in Multination State,Strasbourg: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2005.PP:45-53,视为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剥夺。作为一种国家整合少数族群的政策取向,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对其内部的所有民族的认同(无论多数还是少数)给予平等的公开承认,以推进多元的民族认同(multiple national identities)。
该理论以加拿大为基地逐渐向欧美世界蔓延。到20 世纪90年代,“承认业已存在的民族认同的多样性已成为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方式”[7]49。英国《1976年种族关系法》的颁布和种族平等委员会的成立,表明英国的族群治理开始以多元文化主义价值为导向。法国在1991年发表的《关于融合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表明法国的族群治理从“嵌入”型同化取向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取向②该报告表示:法国并不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融合的政策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从而使不同族群和文化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证每一个人,不论出身都能生活于这个社会中。参见Craw Young.Ethnic Diversity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155.。因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有学者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由各民族融合而成的美国人的熔炉,而是成为一个多元且有种族、民族、国家和宗教术语的国家”[8]。另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其它一些国家,在国内的族际关系上均蕴含着强烈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而“数以千万计来自于不同国度、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移民”[9]被整合进西方国家的成就,使得多元文化主义一度成为西方进行族际治理的标准样式。
2.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对国家潜在的撕裂已在西方各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加拿大试图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解决英、法裔加拿大人、以及“宪章族群”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问题,但魁北克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更加放开手脚来保护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10]的分权挑战,表明“种族马赛克”并未能实现国民一体的目标。在美国“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在某些精英人士中间大行其道”,人种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被抬高的另一面是贬低的国民身份[11]115。这种因多元文化主义加强的西方国家内部“族群正义”话题,其客观结果是族群的“民族化”趋向。正因如此,布热津斯基敏锐指出任由其发展,“美国的社会就会面临解体的威胁”[12]。亨廷顿更是对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破坏与美国“国家特性削弱”的状况发出了严重警告。因多元文化主义激发的“族裔的复兴”,史密斯警告“我们已经在东欧和苏联,以及亚洲、非洲看到了其重绘世界地图的能力”[6]121。
同时,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相配合,近年来随着“族群”概念的传播以及部分学者对族群原生属性的探求,使得西方国家国族的统一性与一体性有被肢解的风险。安德森笔下经政治途径“想象共同体”的“民族”(nation),因被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赋予“建构”特征,而归为非“真实”的族类实体。整体的国族被“族群化”的现象,在解构国族共同体的同时,也侵蚀着西方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在民族主义激荡的第三次浪潮下,族群“民族化”推动的诸多“族群”独立建国的政治诉求,已成为西方社会国家治理最为棘手的问题。
3.多元文化主义推动的族群“民族化”现象,进一步催生的“族际政治民主”主张使西方国家的国族属性与地位受到极大挑战
被长期掩盖下的世界民族问题与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在冷战之后,表现为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基于“市场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富裕,而民主给受挫的多数族群壮大了政治声势”[13]的认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塔利认为文化歧异社会的人民对话与互相承认,需要“达成宪法上的协议。”[14]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supranational identity)”[7]48,来实现国家的稳定。而要求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和建构”使少数民族“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实现“各民族对国家权力的共享”,“保证少数民族进入政治舞台”,在国家重要议程上的“一族一票”的“族际政治民主”诉求[15],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如上理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该理论虽然试图通过族际间的政治民主获得“超民族的认同”,但其认识与行动逻辑仍是族际间区隔与差异。虽然,在一些民主制度和法制体系较为健全的西方民主国家,族际政治民主在短期内未引起较大纷争和动乱。但该理论强调并巩固“异”为认识基础,蕴含着国家认同安全的显见风险。同时,“少数民族对这些旨在定义并推进超民族认同的国家政策的怀疑,正在成为一种共同的趋势”[7]49。亨廷顿早就指出:“文化共性促进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11]10“族际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在模糊国族与族类群体属性的同时,使得与国家相结合的国族地位被极大削弱。
三、国族内核的迷失:领土型主权国家内族际博弈对国民身份价值的背离
从当前西方国家的国族境遇来看,国家成员的“超国民身份/特性”与“身份/特性的狭窄化”两种趋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内核“迷失”现象。在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内公民身份与族群权益的关系,以国家认同问题的形式提出全球化下国族的内核与价值的命题。
1.全球化深入下西方各国内的族性传统与公民政治间的博弈,弱化了统一的国族特性、并侵蚀着国族的内核
“民族”(nation)作为一个有着特殊指向的现代概念与体系,解决了欧洲从普世的教会帝国向地域性的民族国家转型的合法性问题。西方早期现代国家的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过程,大概经历了对“民族精神”的追求、民族集体认同的渴望、民族归属感的强化等过程。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现代性,使得民族走向开放与交流;国民经由民族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认同是西方国家合法性的基石。所以,对这个与国家高度融合的“民族”利益的体认,通过社会人个体价值的确认(公民身份)与实现(公民权益)达到了对国家疆域内暴力的合法垄断。“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其后出现的“美利坚”“德意志”等国家民族均是基于内部聚合与外部特殊的价值建构的。
被西方奉为圭臬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民国家理想与民主制度设计,其初衷在于社会个体凝聚于国族而实现的国家认同内核。然而,全球化下西方国家日益复杂的“多族化”结构下,一方面是当今西方不同程度存在的诸如“种族优劣”“白人至上”等观念以及种族隔离政策的遗存,造成少数族裔群体在就业、薪酬等方面处于全方位的劣势。另一方面,则是非良性族际关系与族际间博弈的蔓延。“大量迅猛增长的不完全的成员身份”“公民身份不断贬值”“赋予公民身份以物质利益时的精确算计导致成员资格不再神圣”“与文化民族成员相分离的完整的国家成员身份的要求和例子日益增多”“持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人口数量的激增”“为数众多的被排斥于选举权之外的长期居民”等现象①具体内容参见Willian Rogers Brubaker.Immigration,Citizenship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rance and German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Sociology,1990,pp.39-407.,表明国家内部成员间的隔阂严重制约着国族的一体化,国族的“国民公民”内核已遭到严重侵蚀。
2.日益普遍的国家认同问题表明,整合国家、凝聚国民的国族在国家的中心地位被削弱,存在空心化的风险
随着族群“民族化”带来的诉求政治特征,西方各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被转换为国族与族群的关系。可期待的族群利益与模糊的国族价值,使得国民对国族认同的疑虑直接表现为国家的认同问题。国家认同安全除了以零星的、从未间断的小范围的利益冲突呈现外,具有国际影响的范例呈增长趋势。除各类“独立公投”掀起的政治纷争外,伊斯兰极端组织与极端势力向欧美各国的渗透,更是引发世人对国家认同安全的高度关注。被誉为成功解决族群问题的美国,也因文化和政治分裂强化的种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冲突,“对美国神话提出了现时挑战”[16]。2015年美国北卡的“3K 党”忠诚白色骑士组织的“白人至上”运动,2017 弗州因罗伯特·李的雕像移除问题而引发的白人与黑人间的种族冲突以及全美反歧视游行等,都是生动写照。
以上事例均进一步验证了塞缪尔·亨廷顿基于国族弱化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警告的正确性。虽然“美国的特性/身份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身份问题的决不只是美国”[11]11。西方国家用于保障国家认同的体系与机制,在全球化下面临制度供给不足、与认同政治效能有限的境遇。伴随着全球化下普遍的跨国流动主义与非均衡的国内外秩序,国家凝聚中心的“迷失”与国族认同中心的动摇,已在西方各国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并有向世界蔓延的势头。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族的空心化与形式化。
3.在全球治理成为普遍需求的背景下,西方各国的国族建设面临着内与外的双重制约
从现代国家建立至今,西方各国的国族不同程度遭到内、外双重挑战。从内部来看,既有国家建设进程中的遗留问题,也有新移民群体进入后带来的文化适应与社会结构调适的问题。从外部来看,既有因治理的全球化取向凸显的部分国民国家认同的削弱,也有因国家拥挤带来的治理创新不足。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的识认,引向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而“民族国家显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17]判断的背后,则是一度喧嚣的民族国家“废弃”论与“终结”论。同时,作为对全球化回应提出的“民族和基于民族模式而被想象的文化认同”的“身份认同与团结”[18],也悄悄解构着国族的政治性和统一性。近年来法国所经历的移民国家认同挑战与频密的恐怖袭击表明,曾经作为欧美精神家园的法国式共和同化政策以及社会整合模式已陷入困境。欧美各国均面临着如何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旗帜下将“穆斯林”塑造成合格国家公民的国家治理问题。
同时,作为政治妥协产物的民族自治,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并可能扩大着少数族体的自我管辖权。意大利南蒂罗尔地区自治、法国的科西嘉地区自治、英国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苏格兰问题以及威尔士问题而设立的各自治体、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区域自治、加拿大的魁北克自治与土著人自治等等,均使得各国因某些民族社会的自治呈现为二元主权结构。在各自治体内以保护少数民族、社会弱势的、语言的或宗教的文化多元政策体系,在建构并巩固少数群体认同的同时,整体的国家认同问题也随之而起。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自治”作为安抚策略的“共同体关系工作”,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病态的国家构造”[19]。近年来西方社会日益兴起的国家认同研究表明,认同安全对于西方国家治理的困扰。
四、国族削弱下的秩序供给不足与社会焦虑
在全球化深入的当下,被预言的民族主义式微、民族问题减少与族际关系缓和的乐观格局并未出现。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推动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注定了西方各国“遭到深刻的国内民族分裂的折磨”[20]。因国族一体性的削弱与凝聚力的不足,社会多元化带来的秩序供给不足,令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普遍的社会焦虑。
1.作为族际差异的扩大与非良性族际关系反弹而兴起的新“同化主义”,力图维护的国族一体化与社会焦虑相伴而生
在“族群正义”议题下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使得同化主义一度式微。与各国不同程度的国民身份价值被贬低的状况相对应,西方国内的族际交往呈指数化增加,族际政治互动变得频繁且日益成为影响西方国家走向的重要因素。族际摩擦和冲突带来的族际关系恶化,显然已经成为21世纪西方国家民族问题形势中最为严重的现象①关于全球化下国家族际关系走向的论述,参见刘永刚《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民族权力析论》,《广西民族研究》,2015第2期,第1-8页。。从现代国家以公民身份为特征进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大量移民的流入与跨国流动主义的客观结果是对民族国家模式的偏离。由于非良性的族际政治互动增多,挑战族际整合和族际合作的因素不断增加,国家的统一、秩序和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随着阿拉伯世界纷乱引起的向欧美的移民潮带来的普遍国家安全问题。要求移民接受移居国文化,学习移居国语言,主动承担起融入移居国社会责任的“新同化主义”逐渐获得了各国的支持。进入21 世纪以来,荷兰对新移民和旧移民采取强制性同化方式,试图化解因融合政策导致的社会凝聚力下降和族群散裂的危险状态。自2010年以来,法国政府政策表现得较为激进,颁布和施行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比较典型的有“罩袍禁令”“控制入境规模”、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等,显示法国政府企图重构原有的共和同化模式。英国政府在“9·11”、特别是“7·7”恐怖袭击事件后,以公民身份认同为中心,通过社区凝聚、伊斯兰事务立法、反恐等措施构成的“管理多元性”移民政策,具备鲜明的“同化主义”色彩。
同时,因“移民危机、多元文化政策、‘申根协定'、民族分裂势力和反恐合作乏力”等原因造成“欧洲成为全球恐怖袭击的核心区域”[21]。各国民众普遍的恐慌抬高的民粹主义与右翼势力的兴起,显然是新“同化主义”政策兴起的社会基础。但从西方各国“新同化主义”的政治实践来看,其一方面加剧了社会动荡与政治失序;另一方面移民群体的“激进化”表明移民心理较为脆弱,新“同化主义”政策一定程度成为移民本族意识强化的政策诱因。
2.全球化下的国家危机与治理悖论,使得西方国家面临着国家价值与国族建设的双重难题
如上文所述,荷兰被率先执行的“新同化主义”,几乎成为当前欧洲各国移民融合的范例。同时,随着全球化、欧共体、以及大量移民带来的经济、社会与认同等安全问题,“法国社会再度兴起了强调民族主权、民族认同和共和传统,乃至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潮。”[22]而近年法国上自总统、下至平民的国家认同全民大讨论,不断地被追问的“什么是法国人”的问题,表明在全球化、欧洲一体化面前所有法国人“为逐渐失去法国之所以成其为法国的特质而担忧”[23]。同样的焦虑,在西方各国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白人属性'与‘非洲中心主义'呈现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对抗”,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于族群矛盾的掩盖、个体主义“强化了少数族群‘自然的'低劣感”,形成了美国“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悖论[24]。这种国家治理的悖论在西方社会并非个案。
另一方面,针对移民的渐进式吸纳进程在不断扩展移民权利的同时,也阻碍了移民完全成员身份的获得。唯一性、神圣性和民族性的三种民族国家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限制移民准入或阻止将移民大规模转变为公民的充分理由。正如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建立在人们的流动之上,建立在他们忠诚或背叛的多元性之上,建立在他们身份的多元性之上”[25]。这种因全球化而出现的普遍“身份认同困境”与“一体化”“差异化”同步的社会结构,对于西方社会国家价值与国族属性提出了深刻地挑战。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与同化主义的争论,引发的关于当代国家治理中“正义”与“权威”孰轻孰重的问题,揭示了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辉煌之后面临的族群“民族化”与国族撕裂的风险。这些均显示着西方社会的国族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并不牢固,在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公共价值供给上国族机制亟待强化。
五、结 语
就全球化而言,依托于民族国家模式整合国民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工程,依然面临着多重“族类”群体异质性的挑战。同时,西方各国均无一例外地面临着政治发展的要求与“巩固和重构民族的国家”重任[6]102-130。所谓的民族国家命运,是基于民族国家的国族及其境遇做出的判断。国族认同弱化带来的民族国家特性削弱的事实,已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面对日益复杂且多元的国族结构以及国家治理的全球取向,须“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11]11。其思路无非国家治理基础性资源的国族建设与国族机制的发挥。但显然,国族治理中心地位的巩固与形成有效社会秩序供给的国族机制,绝非回归传统的“同化主义”,也非新“同化主义”,更非“多元文化主义”。树立新的国家价值与探索新的治理体系,不仅是西方社会国族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克服国家危机、实现国家治理的必答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