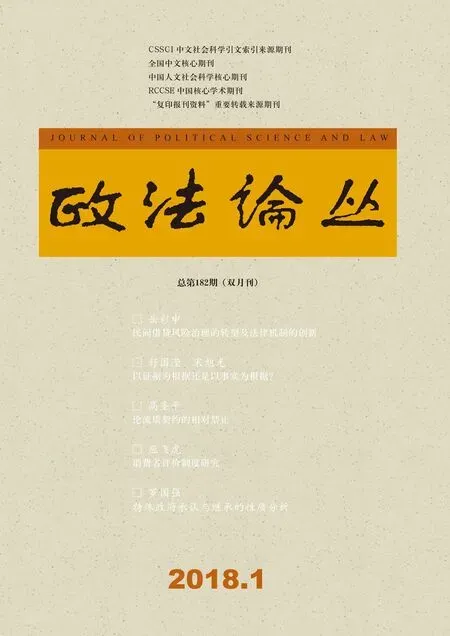以证据为根据还是以事实为根据?*
——与陈波教授商榷
2018-02-07舒国滢宋旭光
舒国滢 宋旭光
(1.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8; 2.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导论:事实认定的意义
一般认为,裁判者做出裁判的过程,伴随着其目光在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往返流转,并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以及原初案件事实的裁剪,最终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对应。这种对应实质上是法律规范的前件(事实范型)与裁判案件事实之间的对应,这种对应的后果便是法律规范的后果被归属于该案件事实,即得出了判决结果。因此,实现这种“对应”与“归属”的前提,便在于对相关法律规范的解释以及相关案件事实的认定。一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成为我国司法审判领域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事实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相互纠葛,关于事实的认定,我国法学界长期有着“客观真实”标准与“法律真实”标准的争论。①有关证明标准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诸多哲学思想之间的对抗,渗透了不同本体论与认识论话语之间的分立。例如,通常认为,客观真实主义背后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而这一概念的反对者则往往选择以实用主义、经验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等带有某种怀疑论倾向的哲学思想为论证基础。令人遗憾的是,在如此重要的法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哲学家却是长期缺席的。不过,陈波最近发表的《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以证据为依据?——科学研究与司法审判中的哲学考量》一文填补了这一空缺,为我们洞察哲学家眼中的“事实”与“证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无疑,作为分析哲学家,陈波对事实与证据概念的细致分析为法学研究者重新审视其内部的有关讨论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考进路。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基于这种分析,最终得出用“以证据为根据”代替司法界长期坚持的“以事实为根据”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粗略来说,主要的反对理由在于:从法律推理的层面上看,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是法律命题与事实命题,这种推理模型与“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其二,事实认定是有价值意涵的,对于客观事实的预设是一切证明活动得以进行的逻辑前提,对于客观真相的追求是引导证明活动不断行进的价值指引,虽然这也隐含着事实认定要“以证据为根据”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却并不必然与“以事实为根据”相冲突。
二、“事实”是什么?事实概念的哲学分析
在没有确切认识“事实”这个概念之前,轻易断言任何一种说法的正确性都是轻率的。但是,对于事实概念的界定却显得尤为困难。
(一)本体论的事实概念
在许多哲学家看来,事实是“外部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态”,是“使得依据或命题为真或为假”的“使真者”。[1]26-7这种观念的背后自然是所谓的真之符合论,即命题或语句的真依赖于其与事实的“符合”或“对应”。但在陈波看来,这种从本体论上界定“事实”概念的做法,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理论难题,例如,事实概念究竟如何界定,事实是否可以个体化,它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等等。[1]P28-31因此,所谓纯粹客观事实的概念,不仅在法学的研究中,而且在哲学的分析中,都会因为这些理论难题而变得难以维系。
我们当然同意陈波的这种分析,符合论背后的客观事实概念确实是难以界定的。不过,如果我们放弃这种严格定义的努力,而尝试寻找事实概念的常规用法,却是可能的。首先,作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事实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事实”指的却是事物的实际情况,即具有什么性质、存在什么关系。例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指出:“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例如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或他娶约瑟芬叫做事实。”[2]P39其次,事实与事情也有区别:第一,语词的搭配有区别。例如,“事情发生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事情的经过一波三折”,“事情终于过去了”,“事实胜于雄辩”,“以事实为根据”;第二,事情是有时态的,但是事实没有时态的变化:事情可以是正在、已经或将要发生的,也可以是可能或者没有发生的,但是唯有尘埃落定,事情摆在那里才有事实;最后,事实是从(已经发生的)的事情中抽取出来用以进行说明、解释、证明的,我们可以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能够以此推论,因此,为推理论证服务的只能是事实,而不能是事情,人们是通过事实来确定某一事情是否存在的。[3]P178-82[4]P13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与事件、事情等相关概念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表达常常是为了论证或说明,当我们为了特定的目的陈述一个事件、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用事实说话。事或者物虽然也常常作为证据在论证中出现,但只有转化为事实的形式才能发挥作用。
(二)认识论的事实概念
于是,陈波转向了认识论视角,开始考察“事实”的认识论概念。从认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事实不是外部世界的对象(事情或事物)本身,这些外在于我们世界的对象未必能够为我们所完全认识,而且也未必会被我们当做“事实”以作为论据或证据使用;另一方面,事实也不是我们所能主观虚构或想象的,“虚构的事实”或者“想象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用法。“事实”都是客观的,虽然我们有时会使用“客观事实”这个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还有“不客观的事实”,毋宁说,这只是对于事实之客观性的一种强调而已。[3]P180可能也正因此,陈波并没有因为上述理论难题就否定事实的客观性,他只是建议,在本体论层面上“不使用‘事实’和‘符合’概念,而只借助‘对象’‘性质’‘关系’‘满足’以及塔斯基的递归方法去定义语句或命题的‘真’或‘假’”。[1]P31
在认识论意义上,陈波将事实看做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混合物。明确来说,事实是“认知主体利用特殊的认知手段,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或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提取和搜集……是人们从世界母体上一片片‘撕扯下来的’”。[1]P31事实是存在于“世界母体”之上的,是依赖于外在对象本身的,这界定了事实的客观性,而“撕扯”的意图、能力与手段则刻画了事实的主观性。因为后者的原因,这些带有主观意图而被“撕扯下来的”事实,就可能会被以多种方式利用,有时候其所刻画的图像就未必是对象的本来面目。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被人们用作论据的“事实”常常会“出错”,但出错的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客观对象的本体论“事实”,而是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和使用。
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种认识论维度上的事实才能进入司法领域,如果法律要求审判者以一种无法或未能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为依据来裁判案件,那无疑是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是不是确如陈波所言,在法律语言游戏中,“事实”应当作为认识论概念而使用呢?
(三)如何理解裁判领域中的事实概念?
前文的分析至少暗示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事实概念: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陈波选择了在后一意义上来讨论法律领域的事实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事实的同时,就必然暗含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事实。
当我们“用事实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论证命题的真。我们说真就是符合事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一旦我们放弃这种客观事实的概念以及其背后的符合论,语句或命题的真似乎是难以保证的。也就是说,虽然从本体论上界定“事实”概念存在种种困难,但这种客观事实的概念却是用来界定真的客观性与可靠性的基础。本体论的事实是一种自然事实,是客观的“自在事实”,它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但这种自在的事实如若进入人类世界,则必须为人类所感知。人类去认知事实,又源于我们相信“客观事实”的存在。“当人感知世界时,他并不知道他所感知的是强加给世界的他自己的思想形式,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或‘真实’)只是因为它在那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5]P3因此,客观事实的预设(或承诺)成为我们认识事实的一个基础。
由于人类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真正有意义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它是人们对某事物存在某种性质或某种关系的一种基于感性经验的断定和把握。作为某种特殊的经验陈述或判断,认识论上的事实,也正如陈波所言,具有一定主观性,因此是可谬的、可废止的,被证谬之后我们就不再称其为事实。再者,“事实可以存而不在。”[6]P744我们所面对的事实都是一种历史事实,一旦发生就不可能重现。因为不能重现,人永远也不能保证事实命题绝对为真。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被认识的自然事实只是一种可能,或者一种猜测或想象,它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认知指引。例如,在科学探究中,在自然规律未被认知或证实之前,科学家提出的是假说;在司法审判中,当事实真相没有被揭示或证明之前,诉讼参与者提出的是事实的主张或叙事。这种假说或叙事必须得在预设客观事实存在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意义,而对于假说或叙事的证实就源于我们寻找客观事实的“兴趣”。因此,认识论上的事实常常表达的是主体的一种确信或信赖,即相信事实命题符合作为参照物的客观事实。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事实不可能回复,发生过的事实就只能以语言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里的语言要做广义的理解,不仅仅包括文字、话语还要包括会意的动作等一切表意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论意义的事实往往都是通过语言来予以表述的,“语言的重要任务是肯定或者否定事实。”[7]P3对于事实的认定,实际上就是对于事实命题的真实性的证明。严格来讲,语言学意义上的事实只是有关事实的命题,往往表达的是主体的一种主观相信,因此有真有假,也可以被推翻或废止。[2]P35
总之,哲学视域往往会区分本体论意义的事实和认识论意义的事实,前者是“外部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态”,而后者认知者从世界母体上“撕扯下来的”的论据。但无论谈论的是何种意义上的事实,在论证实践中,我们首先面临的便是语言意义上的事实,即主体对于事实的陈述,它表现为事实命题的形式,因此有真有假。具体到在裁判中,作为一种应然目标,事实认定所要追求的自然是客观真相,但裁判者首先面对和处理的却是当事人之间的系争事实,这种事实往往是通过语言陈述的事实主张(叙事),哪个叙事版本符合事实必然需要证据的支持。但获得充足证据支持的事实命题通常会被当做是与事实相符合的,它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认定者确信为真的事实。从这一视角来看,在法律领域中,事实认定所应当寻找的是客观事实,但实际被认定的事实却是认识论上被确信为真的事实,两种事实未必总是重合的。
三、“以证据为根据”的主张及其理由
(一)事实的难题
除了上文所述之外,裁判领域中的“事实”还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关键的因素在于事实的认定受到了现行法律秩序的约束,而且有时候我们可能因此要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对于真相的寻求。除了追求真相之外,司法过程还有其他要达致的目标,诸如实现正义、定纷止争等。一方面,作为定案依据的裁判事实会遭到实体法规范的“裁剪”:作为推理小前提的事实并不是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根据相关实体法规范“量体裁衣”所修剪过的事实。[8]P222另一方面,事实的认定受到了法律程序的制约:事实的认定必然是建立在相关证据以及法定的证明标准之上的,这些证据标准常常并不要求事实认定是“绝对确实”的。也正因为这样,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根据法律规范所认定的事实,未必与客观事实相同。
那么,问题就来了,“以事实为根据”这种说法是否还合适呢?陈波在文中倾向于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事实概念的歧义性以及事实认定的法律规制性,所以,与其使用“以事实为依据”这种说法,不如使用“以证据为依据”代替之。[1]P35-7
不得不承认,“以事实为根据”的说法确实困难重重。[9]P662-5首先,虽然看起来好像陈波更青睐于所谓的法律真实说,但实际上他是从根本上就否认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哲学世界中根本不会有法律真实这回事情,因此他所谈论的是认定事实过程中法律的影响,而非法律的真实。但若把这里的事实理解成客观事实,也有着许多难题。第一,裁判者的事实认知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是一个悖论:如若判断裁判者对事实的认知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就必须首先知道客观事实如何,可是既然已经知道事实如何了,又何须对事实再去做认定呢?第二,客观事实是不可能被完全认识的,而且,即使客观事实在理论上可以被完全认识,由于时效、场合、资源的限制,也不可能保证裁判者的事实认知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第三,因为缺少绝对的判定标准,对客观真实的追求,要么会使事实认定陷入无止境的争辩,要么只能断然终止:事实的认定成为一种权力优势的问题,而非理性的论证问题。当有权者断言“客观真实”的不容争辩性时,错案就可能因此失去了补救的理性理由。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陈波文中所提出的理由并没有什么问题,前文已经表明了事实概念在日常话语中用法的复杂性,而且,长期以来,司法实践过于强调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不仅导致了实践难题,也进一步带来了这一原则的虚无化。但对于这个替换建议本身,我们却必须提出审慎的反对意见。
(二)如何理解证据概念?
如果我们将证据理解为“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所有事实”,那么,无疑“以证据为依据”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司法裁判中,对于“证据”概念的界定,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共识:有些人认为,证据是经查证属实并具有关联性的事实;[10]P106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证据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资料);[11]P87更多的人则是在证据事实和证据资料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12]P85
实际上,即使是权威的法律词典,对此也有不同界定。有些词典选择了事实说,例如,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证据是用以证明未知的或有争议的事实或主张的真实性的事实或方法;[13]P499《布鲁姆斯伯里法律词典》则将证据界定为在审判中用来证明或反驳的书面或口头的事实陈述。[14]而更多的英语法律词典还是倾向于材料说,例如,根据《基础法律术语词典》,证据是在法庭中用来证明某一事项之真实性的东西;[15]《牛津法律词典》则规定,证据是用来证明某一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16]也有些词典则更为全面,例如《布莱克法律词典》既给出了作为材料或事物的证据的定义,也说明了证据也可能是事实。[17]更加令人困惑的是《辞海》的解释,首先它将证据界定为“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收集的,能够证明案情真相的事实或材料。是分析和确定案情、辨明是非、区分真伪的根据。”②很显然,这里是采用的是折中说。但接着它又说:“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必须与案件有关,必须经过办案人员依照法定程度搜集和认定属实。”如果说是一种事物的话,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那么,证据更应当是一种材料,而非事实。这种分歧在我国诉讼法的修改中也已经体现出来。例如,依据旧的《刑事诉讼法》(1979、1996)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但新的《刑事诉讼法》(2012)将其改为了“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不过,无论是采用何种观念,我们都不能否认证据的功能是证明事实命题的真实性的根据,而事实说与材料说只是分别强调了证据作为证明根据的两个面向而已。首先,作为材料的证据可能是以物、言词、录音录像等诸多形式存在的,但每一个证据背后都必然支撑着一个事实主张(命题),因为只有在这些材料能够证明事实命题的时候,才能成为证据。将证据看做一种事实就是看到了,最终作为论据的是证据材料背后的事实命题。于是,在这个视角来看,将证据看做是事实命题,还是材料集合,最终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劣的问题。总之,无论是采用事实说还是材料说,毋庸置疑地便是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作为基础,而证据必须是“硬邦邦的”,足以证明相关事实的存在。
(三)为何以证据代替事实?
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陈述主要来源在于诉讼两造,而他们所给出的叙事版本却未必是相同的。哪些是真实的事实陈述,需要有证据的支撑。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撑事实陈述的真实性,也就需要一些可操作的标准来进行认定。正如前述,追求客观真相并非诉讼的唯一目的,对人权的保障、正当程序的遵循都可能会影响这些标准,因而不同法律秩序以及不同领域所确定的标准也可能就不同,这些标准会用来鉴别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等,也会确定裁判事实所需要的证明程度。因为这些程序限制,有时候,即使我们确信案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也不能有所作为。例如,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一旦我们剩余的合法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真相时,裁判的结果就不是基于事实作出的。再例如,诉讼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已经基于既有证据做出了判决,那么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我们也往往不能再就同一问题提出诉讼,事实的最终面目就变得不重要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在司法诉讼中,事实究竟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证据如何,或者可以被认定为证据的那些事实或材料如何。例如,在刑事诉讼中,仅当犯罪嫌疑人被证明从事了犯罪,并且没有被证明其从事犯罪有正当化依据时,程序规则才允许法官确认其有罪,在其中“似乎重要的不是什么是真实的,甚至不是什么是最可能真实的,而是某人能够有理由地述说的东西是真实的。”16这常常是一种受程序限制的理性,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信念或决定是理性的,如果它遵循一个适当的程序而就实际已被纳入考量(或应当已被纳入考量)的那些信息达成了一致。”[18]P5我们所认定的事实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确信或者是基于确信的一种共识。即使在理想条件下通过充分辩论达至的共识,最终也未必是事实本身。强调以证据为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提醒裁判者不能盲目轻信、不能主观臆断,而是要着眼于证据的充分性和相关性。
根据我国传统的司法证明理论,不仅诉讼活动应当追求事实真相,而且这个事实真相是能够被确证的。这就不仅预设了客观事实的存在,而且坚信客观事实是可以被认识的。但前述种种似乎都说明了,司法程序中有的仅仅是一种断言客观事实的语言活动而已,客观事实根本无法确证。我们已经表明,客观事实只是一种预设而已,一旦掺入了人类的认知因素,事实就不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是根据相关标准被当做是客观事实的事实。因此,如果我们将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而将证据理解为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那么,以“以证据为根据”代替“以事实为根据”似乎就没有问题。
四、为什么不宜“以证据为根据”代替“以事实为根据”?
前文已经指出,对于长期受“客观事实”这一概念所困的证明理论与司法实践来说,强调“以证据为根据”的说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用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以证据为根据”代替“以事实为根据”。
(一)“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首先,所谓“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种说法并不妥当。
我们需要看一下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在什么语境中作出规定的。例如,《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很显然,这个原则所强调的是对于法律决策者裁判案件的要求,其所要求的是,在法律审判的过程中必须以事实和法律作为前提,推导出案件的解决方案。而在法律推理中,这里所说的这种作为前提的“事实”和“法律”必然是以事实命题和法律命题的形式出现的:前者是根据证据以及相关规则而认定为真的事实陈述,而后者来自于对法律体系中相关条文的理解或解释。换句话说,司法裁判的逻辑结构就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暂且不论这里的“事实”和“法律”究竟所指为何,一旦上述说法被改成“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种对于法律推理之前提的性质的强调就可能变得没有意义了。
而且,作为一个对照的佐证,和“事实”类似,所谓“以法律为准绳”中的“法律”这个概念也并不是没有难题的。一方面,裁判者所适用的法律前提也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经过了适用主体的理解和解释,即对于意义的带有特定意图的裁剪和修饰。或者说,类似于事实,这里的“法律”是从法律文本的母体中撕扯下来的。另一方面,依法裁判也并非司法活动的唯一目的,甚至有人会认为,司法裁判的本来目的并不是对于法律的适用,而是为了实现正义,“以法律为准绳”只是法律事业赋予裁判者的一种法律手段而已。“我们要求法官不是单纯地解决争议,而是要公平地解决争议——不是单纯地适用法律规则,而是正确地适用这些规则。”[19]P202因此,和“以事实为依据”一样,“以法律为准绳”无疑也并不是一个严密的说法,但因此要对这种说法进行修正的观点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支持者。
(二)事实根据说与证据根据说背后的不同理念
从认识论上来看,事实的认定必然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目标:追求真相与避免错误,按照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理解,这两个目标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分离的两个规则:“我们必须认识真理;而且我们必须避免错误——这就是我们想要成为认知者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命令;但它们并不是同一命令的两种表达方式,它们是两个可分离的规则。”[20]P17那么,在面对这两大目标时,我们就有两种策略的选择:追求真相优先于避免错误;避免错误优先于追求真相。[21]P109那么,在我们看来,强调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无疑是以追求真相为优先目标的,而强调以证据为依据特别是以经法定程序认定为真的证据为实际上就倾向于后一种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过度强调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就可能会出现损害个体权利、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但主张“以证据为依据”代替“以事实为依据”,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也过度强调了证据的作用。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事实认定应当以证据为基础,这不仅有其内在之义,而且也是实在法的强制规定。③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很多裁判语境中,证据之于待认定事实的证明,既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没有程度区别的,事实的认定不仅依赖于证据,也依赖于法律规定与经验法则,在某些法律领域中还要依赖于事实认定者的自由心证。[22]而且,也并不是证据所能证明的所有事实都具有法律意义的,与法律无关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换句话说,以证据为根据认定的事实仅包括根据证据能够且已经证明的事实,但裁判事实还包括法官认知、推定或免证的事实,且这些事实还必须得经过法律规范的塑造。
(三)证据根据说依然需要“事实”的概念
对于为什么需要“事实”这个概念,陈波归纳了四个理由:作为真值载体(语句、命题、判断、思想、信念或理论)的“使真者”;在科学研究作为出发点、校正器和检测点;在证明或反驳中作为论据;在法律诉讼中作为证据。[1]P24-5在我们看来,第一个理由与其他三个理由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前者是“基础”,后三者是“应用”,正是因为我们假设事实是“使真者”,所以,它才能在各种应用环境中起到论据或证据的作用。根据这种界定,在司法中起到“使真者”作用的是“事实”,这种事实是通过作为证据来起到“使真者”作用的。也就是说,最终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陈述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是通过“证据”来达成的。而且,在司法裁判中,避免错误往往比追求真相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裁判应当“以证据为依据”这种说法当然并不为错。
虽然从认识论上来讲,事实的认定应当建立在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证据之外的其他因素不会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认知者求真的欲望和动机在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21]P112裁判者应当追求“客观真相”,它表达的一种理想,一种要求在现实中最大程度得到实现的目标。虽然它可能在与其他理想的冲突中被击败,但却并不能因此被忽视。相反,它将能够反映事实者追求真相的欲望和动机。强调“以事实为根据”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能够以这种目标为基础来对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展开批判。当我们主张某人涉嫌作伪证,或对证据的证明力展开质疑的时候,我们总是预设了 “客观真相”的存在。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证据才会有问题。虽然“以证据为依据”这种说法也并不必然排除“追求真相”这种预设,但与事实据其定义就必然客观为真不同,证据却需要进行真假认定。例如,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从来都不说虚假的事实、伪造的事实,但我们常常会说虚假的证据、伪造的证据。
退一步,即使我们承认证据是一种事实,但当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意图裁剪事实作为证据的时候,也可能正是为了掩盖另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才可能是最终的案件真相。再退一步来说,如果把证据理解成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那么,裁判者也并非是以证据为依据,而是以合法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为依据来裁决案件的。④虽然这种事实可能未必是案件事实的全部真相,但这里同样贯彻的是“以事实为根据”裁决案件,只是因为有时候案件事实无法被证实,所以,我们只能依据合法证明的事实来裁判。例如,在某些情况下,非法证据之所以会被排除,可能是因为它可能存在证明力的瑕疵,为事实的认定蒙上了阴影,这背后无疑有着“以事实为根据”的预设;也可能是为了保障人权,对公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但这并不是对于“以事实为根据”的否认,而是对于追求真相的方式和程序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对于“客观真相”的追求,但却并没有降低“以事实为根据”这一要求本身。换种说法,因为某些比“以事实为根据”本身更为重要的理由(例如保障人权),经过审慎的考量(或者法律的规定),追求真相的理想被迫让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要求本身不再重要了,在不与前述重要理由相冲突的时候,案件的裁决依然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事实为根据”所表达的内容,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用事实说话”或者“这是事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有关事实命题的真实性宣称,与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所言的正确性宣称类似,后者要求“判决在一个可证成的、从而为正确的道德之意义上是正确的”,[23]P120而前者要求判决的基础必须建立在真的事实命题(因此也预设了事实本身)的基础之上。裁判案件“以事实为根据”,是要求裁判者“追求真相”,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自然事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作为一种目标,“以事实为根据”预设了事实的客观性,虽然这种客观的事实真相(绝对的真实性)的认定并不能总是成功地达致,正如绝对的正确性在司法判决中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一样,但即使如此,对于事实认定之真的宣称,对于规范命题的正确性的宣称,却从来都是司法诉讼的必然。
总而言之,“追求真相”是司法裁判的目标之一,即使我们承认裁判者或者诉讼参与者偶然的司法活动或法律程序本身的规定对于事实的认定会产生重要的或者决定性的影响,但如果司法程序不尽其努力地促进对于真相的追求,也难言正义。因此,司法裁判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作为一种真实性宣称,这里的事实可以被预设为“客观事实”,即自然事实。这与正确性宣称一样,正确性宣称中正确性应当被预设为司法判决应当是(道德上)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性是需要理由支持的,而这些理由是否足以支持主张的正确性,需要一些操作性标准,诸如实践商谈的程序和规则,⑤即使依据这些商谈程序和规则,我们未必能够达致最终的正确结论。同理,在司法裁判中,案件一旦发生,便无法还原,实际上作为裁决基础的是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这些事实陈述是否符合事实(即所谓事实的认定),则必须以相关证据作为基础,而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同样也依赖于相关的证明标准。当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命题出现错误的时候,并不是事实本身是虚假的(事实根据定义是不可能出错的),而是事实认定所依赖的证据(或者证明标准)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在应然的层面上,司法裁判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是理想状态下的最佳化要求,而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为依据是在法律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的限制下的次佳要求。
(四)再看裁判领域中的证据概念:事实还是材料?
行将结尾,尚有一问题没有处理,那就是证据意指的是什么。实际上,在主张“以证据为根据”时,陈波明确支持了事实说,证据是经法定程序认定的“事实”。[1]35更明确来说,在他那里,证据主要是作为一种事实命题的形式存在的,“所有证据都是命题性的,‘证物’是潜在的命题集合,在司法审判中必须展开为一组命题,才能进入司法审判环节,这可以通过口述、附加说明来完成。”⑥在这里,我们还要对陈波所使用的“证据”概念进行反驳。
首先我们必须得承认,在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传统中,将证据看做是事实,将事实看做是命题,因而将证据看做是事实的做法很常见。[24]维特根斯坦就断言:“世界是事实而非物的总和”,而“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25]P5,16按照这种关于事实的图像理论,事实便总是通过命题表达的,因此,作为事实的证据也总是一种命题。对此我们并没有异议,而且在前文中,我们也已经指出了,法律论证实践面对的总是事实命题。而且我们也同意,在证明中,常常会拿事实作为证据使用。但这却不能推出证据必然就是一种事实。至少在法律实践中,被当做证据使用的更多是证词、文书以及有形物品等材料。当然,一般来说这些材料所支持的是事实,或事实命题的真。例如,在法庭中,带有被害人血迹的刀子常常被称为证物,但我们却不能把它作为事实,而是将“刀子上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且带有被害人的血迹”以及以此推论得来的“犯罪嫌疑人是拿着这个凶器伤害被害人的”叫做事实。只有后者(事实)才可能称为判决的依据,而非证据(物)。只有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时,这些证据才在裁判中有意义。但证据不足时,证据本身依然是确信为真的,但犯罪事实却无法得到证明。
不过,将物看做是证据,其中最大的难题便在于,孤立的物并不能构成证据,只有处在关系脉络中与所要求证明的事实有关联的物才能成为证物。[10]P107例如,张继成就主张:“能当做证据的只能是事实,物或事件只是证据的载体。”[4]P139严格来说,世界并不存在没有时空限制的材料。不过,在司法证明中,裁判者所关注的是,材料是否曾经作为构成要素出现在有待证明的案件事实的时空界限中。在后一意义上来讲,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作为证据的这些“材料”并不是材料,而是事实,因为当我们使用材料作为证物的时候,材料就必然有了时间、空间的维度,就必然成了事实。
虽然在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中,证据常常被当成是一种事实命题,但在法律领域,将证据当做是事实命题,不仅不符合司法实践,而且会带来理论上的难题。因为作为命题的证据是有真有假的,如果依据证据来裁判的话,那它们也必须是已经被证明的或不证自明的事实,由于除了某些公理或因法律推定而自然为真的事实之外,⑦大部分事实都是有待证明的,因此这些作为证据的“事实”依然需要证据来证明,而这些证据又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为了斩断这种证明的不断递归,我们便需要一些能够被直观感受(听到或看到)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根据常识或程序被认为可以支持一个叙事(事实)的真实性。材料是客观存在于当前时空的,它本身可以直接感知,因此无需进一步的证明。表述事实命题的言语(或支持事实命题的物)作为一种材料,它们就是那里,无需证明,也无所谓真假,只有它所表述的事实命题才是有真有假的。例如,刀子和言语作为物就在那里,我们需要判定的是甲用这把刀子杀人了或者案发时乙不在现场等事实命题是真是假。从这个角度来看,办案人员可以搜集到的“硬邦邦的”证据材料与这些材料所支持的事实命题是两回事,将证据当做材料而非事实可以避免二者的混淆。
使用更为技术性的话语来说,事实认定实际上对事实命题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因此,可以说,“事实命题p是真实的”与“p被证明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拥有着相同的实践效果,即p是真的,如果p被证明了。[26]P4⑧但这种断言却有着三种不同的意义:[27]P294⑨
1.当认定者相信p所指涉的东西时,p为真;
2.当认定者知道p即拥有关于p的充分信息或有充足的证据支持p时,p为真;
3.当事实判断者接受命题p时,p为真。
相信是一个信仰问题,而知道是认知问题,因此某人相信p并不代表有充足的证据支持p,反之亦然。不过,对于法官(或陪审团)来讲,前两种意义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般来说,有充足的证据支持p,就是法官相信p的理由,而法官相信p,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它。而接受是与认知者的信念集合关联在一起的,与相信不同,一般来说,相信p是接受p的初显性理由,反之却不然,因为接受的理由并不必然来源于相信,也可能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例如证据负担和推定)。[27]P302因此,从这种区分就可以看出,虽然事实命题的证明依赖于证据这种说法没错,但仅仅依赖于证据却常常无法做出事实的认定,认定者的心理因素、认知因素以及法律规定等多重原因都可能会影响这种认定,只是强调以证据为根据往往并不能反映事实认定和司法裁判的真实过程。
总之,即使证据的“事实说”与“材料说”都各有支持理由,但与前者相比,后者更能够体现出诉讼证明的目标和过程。
五、结语
在司法裁判中,我们必须要区分三种不同意义的事实概念:第一,作为客观事实的案件事实,事实认定所应当追求的就是还原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即客观真相;第二,作为法律推理前提的裁判事实,即认定者根据实体法规范所裁剪的且遵循法定程序认定为真的事实命题;第三,依据证据所重建的证明事实,这是指能够由证据充分证明或者符合证明标准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裁判事实不仅包括证明事实,还包括免证事实,即某些根据法律规定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
根据上文所述,原初的案件事实是无法自我展现的,它仅仅具有预设或承诺的意义。在实践中,事实总是某种基于特定意图而被特定主体所裁剪过的认识论事实,而裁判中的认识论事实主要以命题或语句的形式表现的,这些被基于求真意图和法律规范所裁剪过的事实陈述未必表达的就是事实,因此需要辨别真假。事实认定就是将虚假的事实陈述剔除出去,而保留真实的事实陈述;根据法律的预设和推定,这些被认定为真的事实陈述所指涉的就被当做是案件真相。虽然事实的认定常常是依据证据做出的,但裁判本身却并不是依据证据做出的,而是以被认定为真的事实命题为前提的,根据相关的证据和证明标准,这个事实命题被当作是与事实相符合的,即依据它就是依据事实。
这三种不同意义的“事实”也表明了,在司法裁判中作为推理小前提的裁判事实,不仅仅应当是认定为真的,而且应当是有用的(即与实体法律规范中的事实范型相符合),而且是能用的(即不违反证据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没有被排除)。[28]P34-7在事实认定中,如果忽略了这些区分,一味强调客观事实的存在与可认识性,就会带来很多实践中的难题,它给实践工作者带来过于苛刻以致无法完成的任务,造成事实认定者的“精神分裂”:一方面法律要求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另一方面认定的事实做不到绝对客观,因此只能“任性断言”,将事实认定变成权力的游戏,或者不得不实施“鸵鸟政策”,而有意回避相关问题。
“以证据为依据”这种说法,虽然可以避免“事实”概念的混淆性,但却也面临着其他的难题。一方面,“证据”这个概念和“事实”一样,也同样存在使用上的混淆,例如,证据究竟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材料,有着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从法律推理的视角来看,司法裁决并不是直接依据证据做出的,而是依据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来做出的,即司法推理的小前提是案件事实,而不是证据;而且,有些事实是不需要证据来证明就因为法律的特别规定而被推定为真的,这些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命题被推定为真,也能成为裁判的依据。
总之,虽然我们并不赞同陈波文中提到的“以证据为依据”替代“以事实为依据”这种做法,但我们却同意,以证据为根据是事实认定的必然要求。甚至我们也同意,案件裁判最终所依据的是证据,更明确的说,是用来证明事实的那些证据。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家的陈波,通过对事实概念进行精致的分析而提出的这个想法,在本质上是可接受的,但出于法律价值上的考量(追求真相)以及推理形式上的要求(案件事实作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我们依然强调事实概念在法律中的重要意义。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司法裁判以事实为依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依据。
注释:
① 这一问题近来被进一步深化为有关证明模式与标准的讨论,例如,王守安、韩成军:“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重塑”,《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第84-91页;徐阳:“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观念之思考”,《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2017年第8期。
② 《辞海》(第六版 彩图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3页。在许多论文中都指明我国《辞海》对证据的定义是“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但并未注明详尽出处。例如,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102页;张中:“法官眼里无事实: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25-26页。
③ 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条第2款:“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司法解释中对此的表述更为清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第104条第2款:“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第2条:“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④ 例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⑤ 阿列克西所提出的有着28个规则和形式的普遍实践商谈体系就是其中最具竞争力的选择之一。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73页。
⑥ 这是陈波私下的回应。
⑦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第93条列出了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六项事实:(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不过,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可以因为相反证据而被反驳或推翻。
⑧ 同样的实践效果不代表逻辑意义相同,例如,有人指出,真是无条件的,但得到验证显然是有条件的。参见陈景辉:“事实的法律意义”,《中外法学》2003年第6期,第666页。
⑨ 需要指出的,虽然这里的区分受益于贝尔特兰(Jordi Ferrer Beltrán)的论述,但是他并没有区分事实命题p与事实命题p所指涉的事实,后一想法来自于拉兹(Joseph Raz)(see 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
[1] 陈波. 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以证据为依据?——科学研究与司法审判中的哲学考量[J]. [澳门]南国学术, 2017, 1.
[2] [英]罗素. 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M],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 陈嘉映. 事物,事实,论证[A],泠风集[C],东方出版社,2001.
[4] 张继成.事实、命题与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5] [英]霍布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翟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 金岳霖. 知识论[M],商务印书馆,1983
[7] [英]罗素. 导论[A].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
[8] 印大双. 如何刻画法律推理中的事实与规范[J],政法论丛,2014,6.
[9] 陈景辉. 事实的法律意义[J],中外法学,2003,6.
[10] 裴苍龄. 彻底清除证据问题上的盲点[J],现代法学,2017,5.
[11] 龙宗智. 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J],法学研究,2005,5.
[12] 李树真. 思考在证据“拿来”之后[J],政法论丛,2008,6.
[13] 薛波主编. 元照英美法词典[Z],法律出版社,2003.
[14] Dictionary of Law[Z], Bloomsbury Reference, 4th ed. 2004.
[15] The Dictionary of Essential Legal Terms[Z], 1st ed. 2008.
[16] Dictionary of Law[Z], Oxford Paperback Reference, 5th ed. 2003.
[17] Black's Law Dictionary[Z], 9th ed. 2008.
[18] Floris J. Bex. Arguments, Stories and Criminal Evidence: A Formal Hybrid Theory[M], Springer, 2011.
[19] Gerald MacCallum, Jr.. On Applying Rules[J], Theoria, 32.3, 1966.
[20] 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M],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21] 舒卓、朱菁. 证据与信念的伦理学[J],哲学研究,2014,4.
[22] 张卫平. 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J],政法论丛,2017,4.
[23] [德]阿列西[阿列克西]. 法概念与法效力[M],王鹏翔译,[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24] 江怡. 分析哲学中作为证据的事实[J],陈常燊译,哲学分析,2017,3.
[25] [奥]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
[26] Michele Taruffo. Towards a Logical Analysis of the Judgment on Facts[A]. Guido Governatori and Giovanni Sartor (ed.). Deontic Logic in Computer Scienc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ON 2010 Fiesole, Italy, July 7-9, 2010, Proceedings[C], Springer, 2010, p. 4.
[27] Jordi Ferrer Beltrán. Legal Proof and Fact Finders’ Beliefs[J], Legal Theory, 12, 2006.
[28] 张继成.真的有效性证明标准[J],政法论丛,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