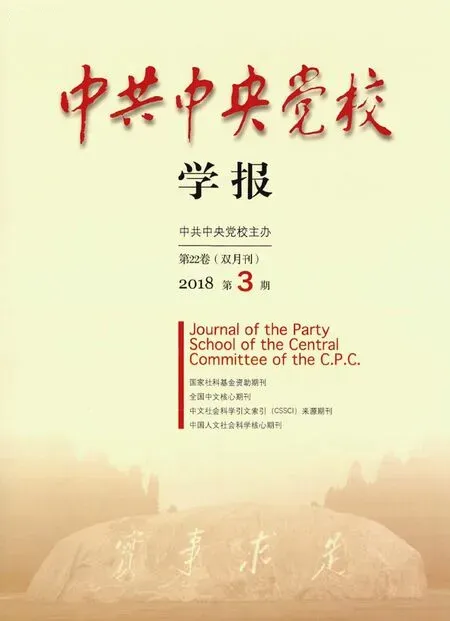重视构建话语体系的路径思考
2018-02-07李德顺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海淀100088)
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经、政、法、社等众多学科,其中每一个学科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学说和话语体系,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而要在整个哲学社科领域里,全面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更是一个“其大无外”的文化工程。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主要是指形成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应的、各个学科自己的学说及其话语体系。就是说,从“横向”上看,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之间,其专业话语可以是不同的,各自有其层次概念体系,唯以实事求是、科学严谨为要。从“纵向”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要努力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基础、理论支撑、观念引导和方法武装。因此各学科之间的专业话语,又是可以方向一致,在不同层次上互相响应、互相配套的。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并通过恰当的中国式话语表达出来,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我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学科专业的。怎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哲学话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财富和话语特色,当然是我的视野所及,也可以提出并考虑的问题。但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可以说是深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过程之艰难。
中央提出构建话语体系的问题已经好几年了。十几年前我在中央党校的刊物上提出,要注意奈斯彼特说的“中国有好故事没有好话语”这个问题,尤其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系统,更应该注意构建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有好故事就要有好话语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到底形成了没有?形成了哪些?形成的怎么样?问一问这些问题,我就觉得我们学界、理论界的状况不太乐观。
总体上看,目前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和科学的步伐,我们的学术思考远离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意识形态的话语也远远落后于党中央的战略意识。这种落后,表现为学术界的分化严重,而凝聚理论共识的动力却不足。
一方面,很多精力都是用来“跟着说”。
一种“跟着说”,是跟着中央说。中央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但只是把中央的提法放大一下,声音喊得响一下,意义强调一下,并不去做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政策不等于理论。每当中央有了重大决策和政策表述以后,怎样给它做理论提升和系统化的工作,怎样在实践中深化和完善,却总是跟不上。因为不能提出什么对实践有所预见、有所启发、有建设性的问题,这叫作“只有宣传,没有研究”。将理论研究等同于宣传教育,其话语表达必然是“口径上下一般粗”“热点一阵又一阵”,形不成深浅梯次、张弛有致、理路一贯的系统化格局和鲜明韵味。
另一种“跟着说”,则是跟着古人或洋人的书本说。一头扎进书斋或故纸堆,唯“经典”是举,“趋史避论”,实际上也起到了作用。“话语异化”,即用古旧的或西式话语,挤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和话语空间。例如马哲界近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热点”:是应该把马克思的哲学“近康德”化还是“近黑格尔”化?人们把马克思的思想和话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以前的,都要划归给康德、黑格尔或别人的体系;另一部分是马克思以后的,则用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来代表。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体系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何在?几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话语空间了,还谈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总体上是落后,理论落后于实践。从话语表达来看,多而杂,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理论、哲学话语等变化很多,但却很难看到成体系的话语表达。我们的新提法很多,但是稳定性、理论的逻辑性差,这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不到位所带来的。
在自觉不自觉地一味“跟着说”的情况下,由于“跟谁”和“跟什么”是比较多样而杂乱的,导致我们有些理论和宣传话语,出现了“五不”现象,使得什么是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是社会主义的新鲜话语,不仅很难出台,即使出台了也特征不明显、内涵不到位、魅力不显著。仅就概念和话语来说,所谓的“五不”是指:有些话语“来历不明”、有些话语“形式不够新”、有些话语“内容不充实”、有些话语“层次不够高”、凝练话语的“公共平台不够牢固”。
一是有些话语“来历不明”。很多被采用的概念和理论表达,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吗?比如,在我们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研究中使用的“价值”和“价值观”概念,是原封不动地使用了西方的传统含义,没有用中国学者自己研制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概念。在西方,价值是value;价值观是values,是个复数。就是说,在西方的语言中,价值和价值观是“一与多”的关系:价值是一般本质,价值观是多样现象。因为在他们那里,无论价值、价值观,首先都是意念的、主观的东西。而在我们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应用到这两个概念上,价值是指客观的社会关系状况,而价值观念是意识形态,是思想观念。它俩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我们从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讲的是“价值体系”,下面说的全是思想观念,并没有与我们改革的本质(改变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结构)这个客观的社会行动结合起来。用价值观代替价值体系,现实的根基和意义就被掩盖了。
二是有些话语“形式不够新”。能够反映新时代新精神的概念是什么?要以新的研究成果为指向,而不是硬要装进旧的框子里去,甚至“以旧代新”。比如自从我们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个原则以后,怎样阐释“主体”和主体性,就有了新的内容。但有人却一味强调说“主体性”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说海德格尔的“此在”才有新意。其实,海德格尔的“此在”才是故弄玄虚并且过时的概念。任何存在都有其“此在”和“彼在”,它与人的“主体性”相比,到底哪个更准确、科学、合理,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试图用“天下”代替“世界”,用“大同”代表共产主义,用国际阶级斗争解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儒家道德解释“为人民服务”,等等,也是并不科学的“以旧代新”。问题在于,他们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旧”的,而别的即使已经说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概念,倒是“新”的。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关于同样指向的概念,他们不首先关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当代中国特色内涵的话语,却满嘴都是西方或古代的现成词句。在这点上缺乏自觉的追求,不仅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也很难跟上人类文明的新发展。
三是有些话语“内容不充实”。我们有一些好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却只有结论和口号,没有理论结构,没有系统论证,也不注意相关的积累。比如我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指导法治中国建设。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是什么?宣布了就等于已经有了吗?我问了一些从事法治研究的人,发现他们也不够有数。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肯定是融汇当代“中、西、马”思想成果和历史经验的产物。但是细想起来,传统的“中华法系”有很成套的东西,西方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很成系统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到底怎么说法和法律的呢?过去的“维辛斯基法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失败,以至于让有些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就是不要法治的。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当下我们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不懈地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究竟怎样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这个问题显然是不能回避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展开已经刻不容缓了。不能设想,没有一个充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体系来指导,怎么可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四是有些话语“层次不够高”。我们现在的新话语其实不少,如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社会、生态等层面,创新的内容很多、很细,但有时拢不到一起,形不成强有力的核心理念和思维逻辑。原因可能是,没有在哲学的高度上把它们用一以贯之的本质表达加以融会贯通,以使它们形成层次鲜明的一体逻辑。相反,有时倒像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既缺少空间覆盖的整体全面性,也缺少时间持续的“一以贯之”清晰线索,体现不出我们应有的高度。比如,究竟如何看待民主与法治?我们能够识别出不适合于我们的西方模式的种种特征,并旗帜鲜明地拒绝体现其导向的话语范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我们自己的正面概念,以阐明自己的思想,并展示其中的话语优势和魅力?不能说了很多“不要怎样”之后,却表达不出“应该怎样”的勇气和智慧。
这里顺便说一下对“民主”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正是立足于最高层次的理解和当代创新的“民主”概念的。“民主”这个概念最初的实际含义,仅是指“多数决定”的原则。但多数人并不一定总是正确。例如古希腊实行民主,就杀死了苏格拉底。一直到二战期间,希特勒搞的“多数人暴政”,更使西方很多人怀疑民主、排斥民主。但是二战以后,人们在共同总结这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给民主增加了一条原则,叫“保护少数”。这样,现代的民主概念,在其最高层次的概念规定中,就是已经具有三条基本原则的完整体系了。第一原则是“多数决定”;第二原则是“保护少数”;第三原则是“程序化”,也就是法制化。含义完整的民主三原则,代表了民主建设的新的高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开始,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的正是符合民主逻辑的一条道路,追求的正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地说到做到,并以鲜明的话语和逻辑把它阐述出来,那就表明,我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
五是凝练话语的“公共平台不够牢固”。这是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体制性问题。有了好故事,要把它讲好,还需要有一套机制,犹如汇集、澄清理论的话语平台,或者展示精彩戏剧的舞台,能够像一个个大的熔炉和锻造车间一样,把我们生活中形成的各个学科、各种各样新鲜的话语汇集起来,展示出来,并在比较中分辨高低优劣美丑,取其精华凝练提升,日积月累,才能构建起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没有这样的一种公共机制,就难以实现相应的构建目标。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和自觉性都还显得不够充分。
例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目前就显得有些乱,甚至乱到了有一些学术研究找不着自己位置的地步。现在时兴设一级学科,但设置的目的似乎不是促进学科融合,而是加深学科分化。由于学科分化严重,彼此没有共同的问题,也就没有共同的话语,就只能是各搞各的,互相之间不往来,彼此隔绝得很厉害。学科壁垒必然造成学科萎缩,人才枯竭。在各个学科内学说学派已经多元多样的前提下,还要加上学科分化带来的话语分工和学术利益的分化,结果必然给构建共同话语体系造成更大的困难。例如这些年来,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单独设立了以后,加进了特别的行政管理和经费支持。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遇到困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算“马克思主义”还是算“哲学”?有些地方把它算“哲学”,不算“马克思主义”;但有的地方要求它归入“马克思主义”,于是把“哲学”都留给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再有马克思主义。这些行政化的体制和机制,造成学科结构的分解和隔绝,非常不利于汇聚多学科的经验和智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有的学科说的话在另一个学科里面就不存在,理论研究成果之间不能相互支持、难以有效关照。
那么我们非常需要的这个机制和平台,怎么样才能形成和建立起来?国家管理部门需要统筹考虑。研究工作,研究者可以个人努力。而从国家社会的全局看来,现在最应该抓的还是公共平台,体制、机制、政策性的融合、熔炼、提升。通过它们,使真正好的话语能够显现出来,传播开来,经过大家反复推敲琢磨,形成真正的时代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