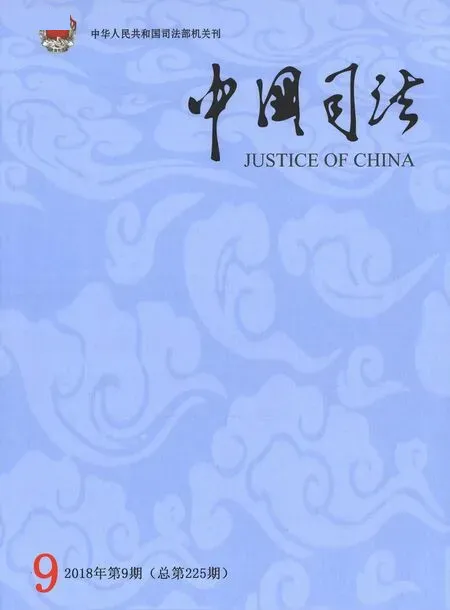新时代加大全民普法力度的思考
2018-02-07陈思明山东行政学院副教授
陈思明(山东行政学院副教授)
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既注重全面推进的过程,又注重依法治国的全面状态,强化了法治建设的整体化思维。同时,通过对公权力监督的监察全覆盖扩大法治治理幅度,通过推进合宪性审查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体现通过扩展广度和增加深度来诠释依法治国的全面性科学思路。
中国特色的普法至今已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从开始注重制度普及,到后来普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再到近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充分体现了普法发展的全面整体化思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如何在法治建设新时代深化普法的整体化思维,是应当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全民普法的价值引领。同时,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传递的法治精神,顺应法治建设新时代的治理思路,通过拓展普法广度和深化普法功能,有效加大新时代全民普法力度。
一、明确新时代全民普法的价值引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全民普法的价值引领,为新时代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供了根本着力点。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法治价值也在人们心中扎根、在人们行为中体现,从而实现新时代全民普法的法治目的。
尽管多年前已然提出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但在普法工作中其多是处于目的层面,现实操作中仍然以制度普及为主,其中以贴近生活的法律规定普及最受欢迎。从实质上讲,这是法律工具主义在普法中的体现,即以与自己相关度为内在尺度审视普法意义。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普法实践,彰显了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①刘建军:《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丰富内涵,为治理主义法律观提供了科学指引。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十分必要②刘风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理据与方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意义及其进路》,《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8期。蒋传光:《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思考》,《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8期。,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民普法发挥引领作用的全部。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多局限于普法内容方面,对于普法行为合理化、普法方式科学化等缺乏应有的关注。换言之,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同时,更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普法行为和普法形式进行必要指引,从而从整体上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普法的价值引领作用。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普法行为科学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囊括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多个层面。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从实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法治的普及提供了一种法社会学视角,即以更加开阔的社会视角看待法治价值,在多种价值比较中科学审视法治价值。相应地,普及法治价值的普法行为,应当注重结合国家、社会等现实发展的多种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与法社会学视角下的普法内容和形式发展相适宜,以现实理性视角对待全民普法,应当对普法行为进行科学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的普法行为,是普及法治价值的重要法治沟通行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建设中,治理理念需要必要的沟通行为作为载体。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必要的法治沟通方式不可或缺。换言之,普法行为不应仅仅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实践的伴生行为,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层面法治沟通交流,普法行为将法律信仰建立在合理商榷过程之中,增进法律的精神文化基础③夏雨:《法治的传播之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从而有效克服法律工具主义的弊端。深言之,作为柔性法治方式,普法行为在国家法治建设、社会法律治理、个人行为规范等多层面具有重要法治发展潜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指导下,普法利于增进国家、社会、个人行为的现代理性程度。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普法活动深入开展
在三十余年的普法成绩基础上,加大新时代全民普法力度,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合理匹配多种普法方式的重要价值根据。一方面,以法治政府理念统合党政主导的普法活动,以行政法治视角合理规制普法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在普法具体形式方面,实现法治宣传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④莫纪宏:《“总体法治宣传教育观”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以各种普法形式的合理结构化为依托来配置多种普法形式。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联系普法活动的主导形式和具体形式的价值纽带。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宽广视角和价值底蕴,是普法活动相关主导方和参与方的重要共识。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普法活动深入开展,普法行为相关方的行为规制和协调是一个重要前提。在缺乏有关普法的制度顶层设计的情况下,以文化认同推进行为规制势在必行。正如喀麦隆思想家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从法治宣传教育角度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普法,普法宣传最终致力于普法教育的目的。借鉴“言传不如身教”“正人先正己”的优秀传统教育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普法活动深入开展,必然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规制普法相关主体行为。
二、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的广度
在法治建设新时代,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并带动社会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常态⑤肖金明:《关于党内法治概念的一般认识》,《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为更好实现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常态,鉴于党内法规的软法性质,为有效引导党内法规的“纪律效应”和“溢出效应”,应当选取党内法规普及作为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广度的重要突破口。进入新时代伊始,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推进了党政合署办公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程。国家监察机构和公权力监督对象的两个全覆盖,将党内法规由制度建设阶段推进到制度运用阶段,相应地党内法治成为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广度的着力点。结合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发展情况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为党内法治实践的重要载体。根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新情况,新时代全民普法应当在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等方面进行必要拓展。
(一)在制定法之外进行必要法治理论普及
随着法制宣传向法治宣传转型、法治国家建设向法治中国建设升级,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科学发展需要充实必要的法治理论。在法治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理论的贡献非常值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将法治从国家法治扩大到政党法治,对中国现代法治进行了全新设计⑥姜明安:《习近平总书记法治理论的重要创新》,《人民论坛》,2017年第9期。。立足法治信仰探究法治价值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特点⑦万高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新贡献》,《学理论》,2015年第32期。。新时代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应当在原有国家法治理论之外,丰富必要的政党法治理论,以更加适应现实需要的法治理论,增进党内法治的信仰基础,从而有效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范围,切实提高新时代全民普法的力度。
从全民普法的发展模式角度讲,我国历来采取党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普法模式,传统普法模式存在政治化、形式化问题。将党内法规纳入普法范围,更加亟需克服传统普法模式的不良影响。在法治建设的新时代,为进一步有效克服传统普法模式运动化、形式化的弊端,应将新时代法治理论纳入普法内容,以新时代法治理论强化党内法规的法治特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细节信息公布后⑧新华社:《新华社首次披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大量细节》. 访问网址: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11_05_433605.shtml,访问时间2017年11月5日。,对于监察机关的政治机关定位,引起各界广泛热议。从全民普法视角看,这是有关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逐渐融合中有关政治与法治的定位之争。这也表明将融合党内法治的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纳入普法范围,成为新时代加大全民普法力度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加强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和政治文化的普及
在党内法规纳入普法范围后,监察体制改革切实推进了由党内法制普及向党内法治普及的转型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党内法治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保障。通过普及党内法治理念,对党政政治文化进行科学指引。新时代法治建设中,法治文化和政治文化存在密切关系。
在新时代全民普法中,需要将优秀政治文化及时导入法治文化。向全民征求意见的《国家监察法》草案,是全民普法融入立法过程的具体体现。该草案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从争议的观点内容看⑨陈瑞华:《〈监察法〉草案存在的七个问题》. 访问网址:http://wemedia.ifeng.com/36271260/wemedia.shtml,访问时间:2017年11月8日。陈光中:《监察法草案应“尊重保障人权”,并增设律师介入制度》. 访问网址:http://tech.ifeng.com/a/20171108/44750684_0.shtml,访问时间:2017年11月8日。沈岿:《提请对〈监察法(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请求》.访问网址:http://www.vccoo.com/v/9ah8lb,访问时间:2017年11月9日。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该如何进行宪法设计?》.访问网址: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12405,访问时间:2017年11月12日。韩大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缺乏宪法依据》.访问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MyO DMwMw==&mid=2247487415&idx=1&sn=4104ccb280a028ed8b669081184a335a&scene=0#wechat_redirect,访问时间:2017年11月12日。,本质分歧是以政治思维,还是以法治思维推进反腐败工作。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后,为巩固这种胜利成果,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为可取。因为在现代政党政治环境下,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制度文化,法治文化是制度文化的最高表现⑩周叶中:《以法治思维的培养为突破口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视野》,2017年第5期。。通过制度规范政治行为和政治运行,以制度力量促进养成良好政治行为习惯,进而生成现代合理政治文化。新时代全民普法应当促进政治文化和法治文化的良性融合传播,充实加大新时代全面普法力度的文化基础。
三、深化新时代全民普法的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党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普法,在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以全民普法作为监督公权力行使的新渠道。
我国普法活动开展的三十余年历程,存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的法治不完善——普法之“体”不足,和法治传播的单向化和形式化——普法之“道”乏力[11]付子堂、肖武:《普法的逻辑展开——基于30年普法活动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和法治传播均采取党政主导模式,所以从实质上讲,公权力缺乏监督是普法之“体”与“道”困境的根本问题。传统法治理论中对于公权力监督主要依靠他律方式,“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出台后通过公权力行使者由传统意义上的普法受体向普法供体转化,盘活了“以吏为师”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法治传播方式增进公权力行使者的自律意识。随着“谁执法谁普法”的推广,促使全民由法治信息的接受者向潜在的公权力监督者转化,从而实现公权力他律与自律有效整合的法治功能。深言之,“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以完善普法之“道”的形式,发挥了促进普法之“体”的功能。为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新时代全民普法功能,应对“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进行必要完善。
(一)确认执法人员的普法供体地位
新时代条件下,随着建设法治国家升级为建设法治中国[12]张文显:《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和突破》,《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3日。,兼顾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治的双重视角,既应当坚持执法人员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传统“硬法”定位,也应当承认执法人员作为权力规制法治信息传播者的新型“软法”定位。这既是立足党内法规软法之治的法治特征,也是与拓展新时代普法广度相适应的客观要求。从实质上讲,这是借鉴三十多年普法经验,以增强主体意识的法治化途径来提高“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现实法治效果。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多年致力于增强法律意识、培育法治理念,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培育具有法律主体意识的公民。在执法过程中开展普法行为,提高行政相对人的法律主体意识,需要以增强执法人员普法主体意识为前提。归根结底,普法作为法治沟通交流的形式,其应当以主体间性为重要理论支撑。传统法治国家理论忽视了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新时代深化全民普法功能,应当以承认执法人员的普法供体地位为必要前提。这既是以普法视角强化执法人员的程序法治意识,也是以主体责任为根据增进执法中普法效果的重要保障。
(二)明确培育公民文化的法治目的
“谁执法谁普法”在刚性执法过程中增加了柔性法治交流内容,柔性法治交流的目的在于培育公民文化。如上文所述,新时代党内法治发展需要将政治文化导入法治文化中,执法过程提供了这种导入的法治流程。执法与普法相结合,将单纯的法治信息沟通转换为以利益为基础的法律关系调整过程,公权力行使的相对方由单纯的法治信息受体转换为利益相关方,法治意识以主体意识增强的形式得以展现。从执法过程讲,执法与普法相结合的过程,为利益相关方发挥主体参与性提供了法治渠道。公民文化是一种具有参与性的政治文化[1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1页。。“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从实质上讲为将政治文化转化为法治文化提供了法定参与渠道。政治文化通过执法与普法相结合的法治渠道,促进全民在法治实践中接受普法教育,进而形成基于有效参与、立足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加大新时代全民普法力度的实质就在于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体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公民主体精神。因为,社会化的个人如果无法通过相互承认关系得到支持,就不可能作为主体而维持自己[14][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7页。。政治文化转化为法治文化,需要以公民主体意识为支撑的公民文化作为必要载体,故深化新时代全民普法功能需要明确培育公民文化的法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