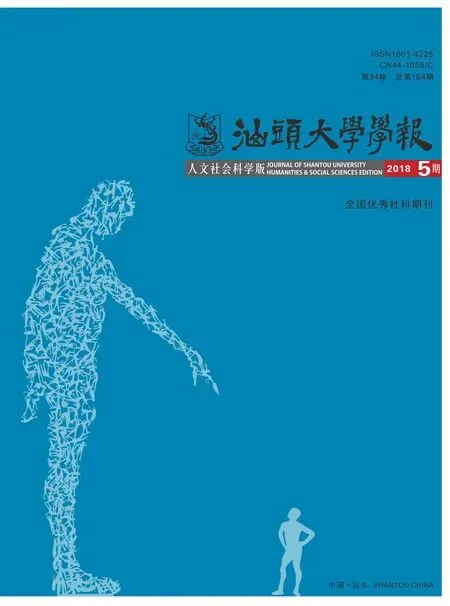汉初郡国并行制的历史必然性探讨
2018-02-01贾军仕
贾军仕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040)
中国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迈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秦并天下尽废封建而行郡县,把中央集权制的功能发挥到空前程度,强大无比不可一世的秦王朝未能千代万世地传下来,反而十多年便土崩瓦解。两千年来,秦亡于制还是亡于政的论争历久不衰,但几乎都以为秦亡于政,与当时推进的进步的郡县制是无关的。笔者以为秦之速亡在于政与制二者并失,人为地强硬地不顾当时历史状况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是其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当时实行单一的郡县制的历史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强硬的手段推行郡县制是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始皇君臣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结果很快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是法家治国纲领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秦王朝政体变革尝试的彻底失败向世人证明: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由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新的制度,其间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期和过渡性制度,而且这种向另一种完全不同制度的过渡,决不能一蹴而就,其间还会伴随着尖锐复杂的殊死斗争,汉初郡国并行制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迪。
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作为历史过渡阶段取得成功,证明郡国并行制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此才真正开创垂两千年而不改的郡县制。但郡国并行制的实行,对于当年羡慕崇拜始皇帝的小小泗水亭长刘邦而言不是自觉意识到的,而是被迫的,所谓迫于势也。
战国后期文化交融军事兼并的快速进展,使统一有了现实可能性,但迄今为止尚见不到一条资料,可以佐证关东六国人民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秦人身上,欢迎秦人来消灭自己的历史悠久的祖国达到天下归一。“事实上,秦代的普通人民并不关心统一不统一,只有争霸天下的帝王才关心这件事。如果说普通人民拥护统一,就请拿出事实来,若没有事实,那只是作者猜想,而作者以猜想为前提就肯定统一这件事对人民有利,这岂不是自欺欺人?”[2]我们从文献中看到的则是各国都有许多志士仁人为反抗秦国的吞并保卫祖国的独立而献出了生命,屈原、项燕、昌平君、李牧、荆轲、高渐离等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其中虽不乏王侯将相,但也有文人墨客下层人士,就连在韩国难展宏图而欲为秦国效力的韩非,也恳求始皇帝网开一面让自己的祖国能多存在些时日。天下归一后,项梁叔侄、范增、陈胜、张良等人还是那样怀念热爱自己的祖国,憎恨秦帝国的殖民统治,这也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失败者的复辟报仇行径。秦的统一是顺应潮流的,也是强加给各国人民的,是用凶残的杀戮血腥的战争实现的,在整个统一战争中绝没有出现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场面,反而遇到各国民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抵抗。虽然,战国以来,人们心中有了华夏夷狄的明确区分,后来逐渐地不再把秦人视为华夏之外的夷狄,但有千年历史的关东六国,有差别较大的政治模式、经济特征和文化背景,尤其风俗民情的差异更大,人们对秦人、楚人、齐人、鲁人的区分之巨,俨然具有亚民族的性质,《淮南子.览冥》中就认为:“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真正统一的主体民族远远没有形成,加之历史的惯性和文化的承继性,六国人民对秦的武力征服充满仇视和反抗是自然的,秦始皇多次对东方的威慑巡视就证明了这一点,秦帝国对关东六国民众的野蛮残忍地奴役和迫害,更激起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各国人民的复仇复国斗争的怒火,早在大泽乡起义爆发前,他们已开始了反秦的舆论和组织准备等前期工作。种种迹象表明,秦实行单一的郡县制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这种政体加速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爆发。并非时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社会危机。关于政体的争论,早在秦刚统一后就展开了。
始皇26年,丞相王绾就建议:“诸侯初败,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3]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王绾在朝廷讨论未来政权组织建设的关乎国家安危的重大决策上,他的提议经过深思熟虑,他清醒地看到了天下初定后潜伏的政治危机,以及秦尚无足够的实力控制所有的新占领区,因而主张在边远地区实行分封制,依赖宗亲血缘为纽带,让诸王国镇抚四方,屏藩中央。王绾是第一个提出实行郡国并行制的卓越政治家,他并不主张全面分封而只是局部分封,应该说他的见解是合乎当时历史需要,是有历史远见的。所以“郡臣皆以为便”[3]唯有廷尉李斯饰词邀宠投始皇所好而坚决反对,最后始皇以“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为由罢其议。始皇帝片面地总结周代分封制的教训,只看到平王东迁后分封制带来的诸侯割据纷争不已的消极一面,而无视周初数百年中央与各地方基本和平共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积极一面,并将西周的全面分封与王绾提议的郡国并行制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完全忽略了关东六国特别是楚、燕、齐等偏远地区的独特情况,把郡县制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体法宝强行推向全国,其实在社会科学范畴内从没有过这种法宝。郡县制风行全国7年后,再次引发了秦中央领导层关于集权与分封的政治大辩论,博士淳于越再次进言,要求封弟子功臣为王,以便“为枝辅”,“以相救”。虽无资料直接记载这次论争的背景,但可以断言论争不是偶然的,小小的博士不敢空穴来风挑起这么严重的争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经过几年单一郡县制的实践暴露出许多重大问题,迫使上层集团再次就国家政治体制做出抉择。李斯当时的反驳恰好证明秦帝国已坐在火山口上,他这次提出的政治纲领无疑把秦帝国推向死亡之途。
大泽乡的怒吼吹响了消灭秦王朝的号角,强大的秦帝国在滚滚的起义大潮面前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人们在消灭强秦的同时,必然会寻找造成如此巨大反差的历史答案。在这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封邦建国几乎成了人们不约而同的共识,义军的蓬勃发展促成这一共识发展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得到各阶级各阶层人士普遍响应和赞成,转化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动力,进而成为支配历史的真正动力,在这个伟大的动力面前,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得不顺从遵行。陈胜率先高举张楚的反秦大旗,三老豪杰建议他“复立楚国之社稷”[3]。
陈胜于二世元年七月首义随即称楚王。六国贵族后裔也借机纷纷称王,赵歇称赵王,韩成称韩王。一时王者多如牛毛,使这次起义迅速演变成六国反秦的军事斗争,清代赵翼把这种历史现象归结为“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剧而易之矣”[4]未免简单化。这些事件宣告了单一郡县制实践的彻底失败,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强大的“裂土分封”的社会动力作用下,项羽只得“假立诸侯后以伐秦”[3]。并且奠定了他以后不得不分封十八王的政治格局,汉代知识分子在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也把不立宗室弟子为王当作重要原因,桓谭说秦“不任人封立诸侯”。司马迁则认为秦“无尺土之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3]。深入研究秦过失的贾谊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观点,说秦王“废王道立私权”,“孤立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他甚至还认为“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只要“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仍可挽救秦王朝的命运[5]。东汉后期的班固也批评始皇帝:“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起白梃,刘、项随而弊之”[5],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探讨中,这些政治家、史学家或学者,一直持此观点,发人深思,简单武断地归之为倒退或人情习见都无法令人信服,只能说尽行郡县确实不适合当时的国情,的确是秦亡的重要原因。
处在滚滚的分封浪潮中的刘邦带领部下投入到与项羽逐鹿中原的楚汉战争中,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外,又增加了军事因素,使裂土分封的形势更为迫切和复杂。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早在进军关中的征战途中就封南阳守 为殷侯[3]。当他要与实力强于自己数倍的项羽一决雌雄时,客观形势迫使他顺应潮流,把封王作为诱饵来刺激拉拢团结各军事实力派首领,结成广泛而脆弱的反楚同盟,最大限度地孤立瓦解主要敌人项楚集团。韩信在刘邦出兵关中前就把能否分封诸侯作为汉王事业成败的重要条件,建议刘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3]。韩信的意见具有广泛性,至少传达了军事实力派的心声,数年后王陵、高起在刘邦称帝后,仍认为刘邦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是刘邦能慷慨地实行分封制[3]。事实也是如此,刘邦以裂土封王为手段壮大了自己,在力量的对比上逐渐超过项羽,最后利用正确的军事、外交、政治策略终于彻底消灭了项楚集团。刘邦所封的诸侯王全是不得不封者,他们有的是独自起家自成体系手握重兵的枭雄,如梁王彭越不王则不会归附;有的是以侯王之尊归汉者,如九江英布、常山王张耳、燕王藏荼,不王就会叛而归楚;有的是本集团中军事首领,如韩信兵多将广用兵如神,在刘邦军事失利时坐山观虎斗,以要挟取得王位,不王则无法满足其欲望从而改变战略上被动挨打的局面。封异姓为王这是刘邦极其无奈不情愿的,他对诸侯王潜在的分裂割据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在无法铲除他们时,已采取各种措施阻止他们势力的过分膨胀。他曾三夺韩信兵权,对其恩威并施牢牢掌握。战争刚结束又以徙封方式削弱诸侯王,阻其坐大。形势稍稍稳定后便制造借口寻找机会有步骤地向异姓王开刀,屠刀首先举向最使他寝食难安的韩信头上,楚王韩信徙封不足一年即被废,不久又被诛杀,韩信无论忠与不忠,都难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下场,剪除韩信表明汉王朝工作重心已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政权的阶段,这一转变不仅及时且非常必要。此后约六年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先后被杀,燕、赵、代诸王相继被废,只剩下无足轻重的长沙王吴芮,因国小力弱地处偏远,吴芮又能力平庸且忠于中央,镇抚南方有功才得以保留。势力强大才干卓越的异姓王的覆灭,使汉政权走出了岌岌可危的险境,但刘邦没有也无法一劳永逸,在这有利时刻全面推行郡县制,汉中央还没有足够力量直接统治全国所有地区,在封王裂土的社会动力推动下元勋功臣渴望分封的狂热不减,其势汹汹甚至有酝酿事变的前兆。实行郡县制的时机尚未到来,刘邦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异姓王甫灭,绝对不可再封;尽行郡县制此路不通,他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就是以封刘氏宗室为王来填补权力空白。在宗法观念浓厚的时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刘氏诸侯王在短期内不仅不会谋逆反叛还能镇抚四方拱卫中央,这一措施也杜绝了异姓功臣争王的念头。从史料分析当时异姓争功封王的威胁是很大的,迫使刘邦不得不与大臣们刑白马为盟,誓约今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3]。无疑欲以此遏制他们觊觎王权的欲望和行动,足以表明刘邦的无奈。分封同姓起到了众建辅弼与异姓抗衡的积极作用,此后数十年国家总体上是太平的,然而不论怎么讲,分封诸侯王潜伏着分裂隐患,刘邦过人之处在于他为势所迫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时已有高度的警惕,刘濞王吴时只有20岁,但仍告诫他“慎无反”[3],临死时仍对诸侯王的割据危险忧心忡忡:“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3]。这里所指背天子起兵者无疑是同姓王,史料说明分封同姓仍是其政体过渡的手段而非目的。可惜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他无力也无时间完成这一使命。基于上述原因,汉初历届中央政权从政策上尽可能地给予诸侯王以限制,他们必须向中央缴纳赋税,无天子诏令及虎符不得动用兵马,王国丞相由中央任命借以控制约束诸侯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破坏性,另一方面王国又拥有很大权力,可以任用百官,有各自纪年等,这又有利调动诸侯王巩固政权建设地方的积极性。汉初实行的郡国并行制,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须的出发点。事实上郡国并行制确实有单一郡县制不可比拟的积极一面,各王国因地制宜,经济恢复社会生产发展较快,尤其以吴、齐为著,“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诸侯各务自附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3]曹参相齐以黄老之术为治,“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3]。
汉初几十年国内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呈两极并立又相安无事态势,以皇帝为一极的中央政府辖中央政府京畿及重要地区共十五郡。司马迁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具其有六。”[3]其人力物力远远强于任何一个诸侯国。郡国并存的严峻形势,也促使中央政府谨慎从事,采取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总方针,中央辖区内的经济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央通过吸纳各诸侯国上缴的钱粮,综合国力有了惊人的发展,“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矩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守闾阎者粱肉;为吏者长子孙。”[5]这与汉初刘邦时“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经济状况相比[5],真有天壤之别。
以同姓王为代表的另一极虽然发展很快,但尚无大规模造反的条件,所以在吴楚叛乱前的四十多年间,中央与诸侯国呈相安共处竞相发展之势,为第一个封建盛世的来临和郡国并行制的最后解决铺平了道路。汉初郡国并行制的尝试是成功的积极的。双方实力增强的同时矛盾也逐渐加剧,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日益关注,而这时中央根基已经牢固,具备解决分裂的经济军事实力。潜在的危险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军事对抗还需一个过程。汉初所封同姓王,以血缘受封,缺乏军政才能,多数年纪轻轻无威望和号召力可言。贾谊也指出:“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5]七国之乱的主要人物,吴王濞立国在位均42年;楚立国48年,楚王戊在位21年。都说明举事需要长期的积聚准备。中年受封的诸侯王或平庸或忠贞,短期内也不可能对抗中央。刘邦的兄长代王刘仲在异族入侵代地时竟致弃国从小道仓惶逃回京城,懦弱无能跃然纸上;荆王刘贾、燕王刘泽虽久习兵革,但忠于皇帝,在击灭英布和平息诸吕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中央无力控制边远之地,诸侯王也无力兴风作浪,客观形势迫使双方致力政权和经济建设,于是出现几十年海内晏如的安定发展时期,其间虽有过济北王刘兴居仓促造反之事,然时间短暂地限一郡,不足为患。汉初中央的正确决断极大地发挥了分封制在发展地方经济保卫中央政权的积极性,把其消极分裂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程度。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少数诸侯王渐行不轨,这时强大的中央政权完全可以解除这一威胁,在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的策划下,采取三部曲策略先发制人消灭分裂势力。文帝据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构想将淮南分而为三,齐分而为六[5]。景帝采纳晁错更强硬的政策,削减诸王封地,这次行动似乎有意使用过激手段,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先后削楚、赵、胶西三地[5]。此举虽是促成吴楚七国叛乱的导火线,但中央掌握战略主动,反叛数月便被平息,变长痛为短痛,为武帝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条件。武帝时颁行推恩令,命诸王在本国内再封众弟子为侯,于是王国被肢解,达到“不削而弱”“藩国自析”的目的。各王国内部国中有国,引发其利害冲突,在内耗中抵消相互力量,这是贾谊众建诸侯理论在实践中的深化和提高。接着颁行“左官律”“附益法”等更是釜底抽薪从官员任用财税收入上使王国陷入困境,终于使诸侯王落到“惟得衣食税租,不得与政事”的境地。成了“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的阔佬,财、政、军三权荡然无存[5]。彼时董仲舒的大一统儒家学说的创立也为政权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汉以来统治集团一直在寻求适合国情的理论纲领,《吕氏春秋》被扼杀,法家学说惨遭失败,黄老之治长于守成但无助于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与巩固。经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大一统理论终于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成为各阶级各阶层都能接受的指导学说。至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汉帝国,终于有了高度集权的物质基础和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郡国并行制才走到历史尽头,垂两千年而不改的郡县制从此才真正巩固起来。
综上可见,秦汉之际近百年间出现的分封思潮及其实践,有着复杂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界思维定势等诸多历史背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人都无法与这股社会动力抗衡,只能屈从它顺应它。汉帝国在夺取天下的斗争中,正是顺应了这股强大的潮流才战胜了对手,建国后若不以之安抚满足诸侯王,立足未稳内忧外患的汉政权极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样不大封同姓屏藩中央就无法与觊觎封王裂土的功臣们抗衡,政权仍有颠覆的危险。刘邦审时度势实行郡县和王国并行制,是一大历史贡献。分封制并非一无是处,在当时条件下短期内仍有其积极作用;郡县制亦非一好百好,也存在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陷。另一方面,分封制确实是孕育分裂的温床。汉代前期始终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集权与分裂的斗争,斗争中最高决策层始终处于主动,较好地利用了分封制的积极面迅速壮大自身,经过六七十年的反复较量,终于彻底消除了危害中央统一的分封势力,为历代封建王朝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汉初的态势是不封则反,剪除过急则众叛亲离,只有中央足够壮大稳固时,才可分阶段地稳妥解决这一问题,逐步过渡到单一郡县制,这才是可行的历史之路。秦亡汉兴的历史,证明郡国并行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封建社会政体演进的过渡阶段。
揆诸史实,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政治体制,都存在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中央权弱则天下离析,地方无权则经济难以发展。没有完美无缺的体制,关键所在是集权和分权的程度是否适宜,中央控制地方的策略是否得当。汉末王莽篡国,班固认为是宗室子弟无政治地位“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是故王莽知中外殚危,本末俱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5],虽不全面,仍是原因之一。足见事物多具双重性,利弊互倚互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