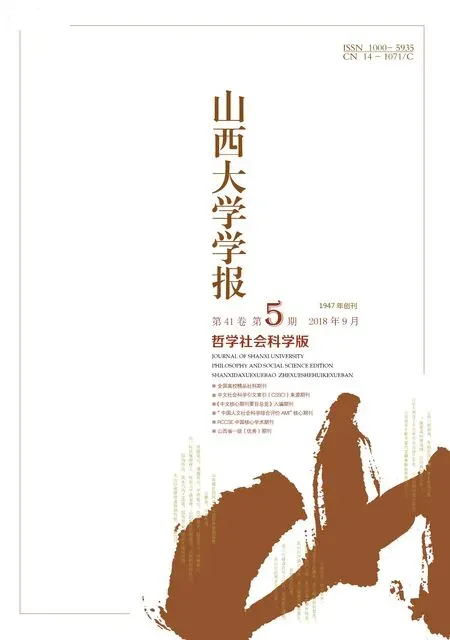“晋抚遣戍案”与道光末年盐务、吏治之困局
2018-02-01张艺维
张艺维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鸦片战争后,“嘉道中衰”之势愈演愈烈。在官民交困的情况下,随着中央财政渐趋窘迫,围绕盐课、盐政问题,清廷、盐商及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各据立场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不断凸显。道光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848-1849)间发生的“晋抚遣戍案”恰为观察其中纷繁景象的窗口,亦可由此窥见道光末年之吏治、盐务与财政困局。然而,就笔者管见所及,学界目前尚未对此案有专题研究。*《山西通志》等中仅对此略加提及。参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0:9.本文拟深入挖掘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并结合《清实录》以及时人日记、文集、年谱等丰富史料,在还原案件史实的基础上,将其放置于道光末年的时代环境中,力图从多方面关照此事,展现河东盐商的疲乏处境及背后制度困局,地方官员竭力迎合道光帝又试图趁机渔利的复杂心理,道光帝彻查案情、整饬吏治的积极行动与掩藏其中的应对统治危机的迁延因循,由此揭示出近代早期的清王朝在财政窘迫与吏治弊病缠绕纠葛中勉力维持的艰难处境。
一 一波三折:河东盐务引发“晋抚遣戍案”
清代盐业实行分区销售。河东盐,又称潞盐,产于山西河东道属地,行销晋、陕、豫三省。河东实行专商制,盐商由山西本地富户组成,每名盐商分配有固定销盐引数*潞盐以240斤为一引,并以引为单位征税。与市场范围,并缴纳相应课税。
道光末年晋抚遣戍案的发生与河东盐务凋敝及充商免商制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盐业经营亏损严重:鸦片战争后愈演愈烈的“银贵钱贱”加重盐课缴纳实际成本;[1]生产食盐的灶户串通私枭“抬价居奇”,提高盐商收盐价格;[2]6089-6090官盐分区售卖体系废弛,私盐充斥令潞盐大量滞销。[3]72在此严峻形势下,即便承领盐数最少的盐商每年亦需赔银四五千两,而规模更大者则“赔累又倍之”。另一方面,盐商身份固定,因经营事务受官府管束,故对官吏需索陋规等行为不得不曲意顺从。尤其是,若因赔累希望告退时需经地方政府批准,且河东实行“举报充商”制度,退出者推举顶替人员,而后者若非官方特准则必须接充盐商。在因盐业亏损导致旧商“只图脱身”、新举富户“多方规避”的情况下,[1]地方政府的盐政权力遂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晋抚遣戍案历经道光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两年,牵涉道光朝后期梁萼涵、吴其濬、王兆琛前后三任山西巡抚,系由“梁萼涵受民人讹索”“御史参奏王兆琛复设陋规”“道光帝褒奖梁萼涵、吴其濬”等多个环节次第演进所构成。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因病开缺回籍的梁萼涵在山东家宅收到民人杨锦说帖,杨声称手中握有梁在晋抚任上收受祁县富户孙陈笏贿赂的证据。梁萼涵莫名被诬,遂向官府控告,山东巡抚复将此事上奏。[4]五月,道光帝谕令将该案人证提集京师审理。由是,一起地方诬告案件迅速升级为钦命要案。经数月审讯,最终查明实情。一是孙陈笏确曾行贿官府。道光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孙陈笏受告退盐商推举,被官府命令接任,但其因恐赔累,向祁县知县、署理河东道等行贿求免。二是梁萼涵并未受贿,系其堂弟借名撞骗。山西巡抚兼管盐政,对免商事务有最终决定权,故梁萼涵成为孙陈笏希图行贿的重点。因在山西“苦无门径”向梁行贿,孙氏遣子进京辗转结识梁之堂弟,后者为“图得谢银”,捏称已与兄长梁萼涵沟通,免商之事将妥。恰巧不久后孙陈笏在充商途中病故,梁萼涵念孙家“情殊可悯”,免孙陈笏之子袭充盐商。梁堂弟的谎言反被“证实”。三是杨锦为借机索诈。杨与参与孙氏请托的一人为友,该人曾向其透露孙陈笏求免充商内幕。杨锦遂误以为梁萼涵受贿,并由此起意“讹诈得钱”。[5]
十月,梁萼涵因失察亲族、下属巨额婪赃,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6] 814然由河东盐务而起的晋抚遣戍案不久便再度升级,二十九年闰四月,曾参与抓捕孙氏行贿官吏的现任晋抚王兆琛复因河东盐务等事被御史参奏。[7]戏剧性的是,梁萼涵的命运却就此发生逆转。
六月,经钦差调查,王兆琛需索盐务陋规情弊浮出水面。先是,尽管陋规久干禁例,但至道光朝,因财政收拨体系不健全及官场奢侈浪费风气蔓延,地方公务经费往往仰给于陋规。山西巡抚亦循例依靠收受河东盐商陋规维持盐政办公开支。然二十六年五月,继梁萼涵任巡抚的吴其濬因盐课短绌,奏报将此项陋规银两“充抵”课银,呈缴中央。同年,吴其濬因病辞官,王兆琛接任巡抚。次年,王因“盐务用项苦于无款垫办”,恢复部分规费。而商众尽管财力竭蹙,亦不得不满足巡抚要求。[8]二十九年七月,道光帝以王兆琛复设陋规将其革职遣戍新疆。[6] 916
与此同时,梁萼涵则被释回原籍,并获六品顶戴。[6] 900原来,除盐规外,御史亦在参折中参奏王兆琛复设“贡余”陋规,即山西某县向内廷进贡特产后呈送巡抚衙门的副贡。此项参款虽为误,但却意外令裁革该规的梁萼涵为道光帝所知。事实上,不仅梁萼涵因革除陋规受到嘉奖,已病故的吴其濬亦因废止盐规被道光帝树为“洁己奉公”的典范,并恩荫子孙。[6] 965至此,关涉三任封疆、诉诸严刑律例、以惩贪倡廉为归旨的“晋抚遣戍案”宣告结束。
二 激浊扬清:道光因“晋抚遣戍案”整饬吏治
诚如道光帝在上谕中所言,因山西案件暴露出官吏受贿、需索陋规等有玷官箴的行径,故“必须彻底根究”[6] 744-745,意即案情本身为严查的直接动因。但若将此事还原于道光末年的时代环境中,则会发现其之所以受到道光帝密切关注,尚有三点因素需纳入视野。
其一,山西个案所反映的吏治弊病具有普遍性。乾隆末年以降,清王朝已显中衰之象,道光帝即位不久,便深忧朝廷上下陋规相沿、察吏不严等“因循疲玩”积习蔓延,并以此作为吏治整饬的重点。
其二,对贪腐案件的重视亦缘于鸦片战争后反思吏治的思想氛围。鸦片战争中清朝官吏骄纵奢侈与懦弱无能的弱点显露殆尽,战败刺激促使朝野内外吁求整肃官方,道光帝亦警觉用人不当的严重后果。故而道光帝一面对于吏治案件尤其事涉大员者,偏于从重处理,以求重整朝纲。一面为应对内政、外交困局所引发的“政治合法性焦虑”,着力于塑造廉洁模范,以维系臣民对清朝政权的认同感。道光帝对梁萼涵由重惩“失察”到褒奖“廉正”的巨大反转,与此不无关联。
其三,财政困境使得整饬与盐务有关的吏治问题显得尤为紧迫。道光朝后期,由于鸦片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额外支出大增,清廷国库常年入不敷出。其时盐税额征银约750万两,为仅次于田赋地丁的中央第二大收入来源,但由于商力疲乏,仅能实征约500万两。[9]241在筹措国库经费的巨大压力下,道光帝遂将注意焦点集中于盐务整顿以求课税充盈。地方浮费陋规被视为导致盐务疲敝的重要原因,道光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道光帝派遣重臣分赴盐课拖欠严重的山东、直隶、浙江等省裁革陋规,其中山东巡抚、盐运使等十数名官员收受盐规,仍分别或被三级调用或遭革职。[6] 840在盐务整顿的风口浪尖,山西巡抚案件又与盐商有关,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以上缘由,随着案情层层推进,道光帝围绕“激浊扬清”的政治目标,交错结合“提京严审”“跨省追捕”“派遣钦差”及“警示宣传”等方式,将“晋抚遣戍案”发展为一场具有示范效应与广泛影响的吏治整饬典型事件。
首先,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山东巡抚张澧中的奏报成为道光帝介入晋抚案件的起点,然其最初对“梁萼涵被民人讹索”一事关注有限。此案虽涉及“受贿免充盐商”这一关乎吏治的重要主题,但道光帝并未真正将之视作贪腐案件而高度重视:这一方面由于山东巡抚对事件的定性,张澧中称经审讯,民人杨锦并未能提供所谓的梁萼涵受贿证据,供词亦情节支离,故认定此人乃“指官撞骗”,梁萼涵系被“诬告”;[4]另一方面则根据梁萼涵在此过程中的表现,其在受到讹索当日即向官府呈诉,主动曝光此事,继而又向道光帝呈递封折,自陈并未受贿,恳请查明真相[10],梁萼涵种种行为所反映出的坦荡态度似表明其确为受诬。
基于此,道光帝虽将案件交由刑部讯办,却仅视之为山东调查的收尾。实际上,其之所以允准山东巡抚奏请,将该案转交刑部,主要出于就近审理的考量。因杨锦指称的行贿者——病故盐商孙陈笏之子孙郅与中间人梁萼涵堂弟等均在京师附近地区,山东巡抚不便究办。并且,由于认可山东巡抚对案情的既有论断,对于讹诈梁萼涵的民人杨锦,道光帝尽管下令将其解交刑部审讯以示慎重,但并未对押解行程速度有所要求。对于案件的重要当事人梁萼涵,甚至未曾命提京质讯。
其次,五月二十日,孙郅供呈行贿账目成为案情演进的转折点。经刑部审讯,不仅梁萼涵堂弟承认以其兄名义撞骗,证明杨锦所言并非全为诬捏,而且据孙郅账目显示,受贿者远比杨锦此前供称之范围广大,包括以署理河东道、祁县知县为首的官员、吏役、幕友等十数人,可谓“节节贪婪”,赃款总额更高达白银五万余两。[6] 744-745
由是,道光帝因案件揭露出其深为关切的吏治问题,应对方式亦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一是要求沿途地方官将杨锦“催趱解京”。[6] 758二是以涉嫌“失察”为由将梁萼涵革职,并派大员将其“迅速押解来京”。三是命多省抓捕人犯,迅速饬提解京,“不准一名漏网”。[6] 744-745由于时隔多年,当日参与行贿受贿的幕友、门丁等早已星散各地,难于访拿,但道光帝仍不断下谕,严令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湖广等地督抚抓捕。道光帝的坚决态度与密切关注加快刑部审理进程,亦促使各督抚积极回应,至八月间,人犯已相继落网。
在官吏犯罪事实渐趋明朗的同时,道光帝进而超越山西个案本身,尝试借此整肃官风。针对失察问题,特颁上谕,以梁萼涵因失察获咎为背景,警告群臣为官“首宜严密”,“如仍不知觉察……必当从严惩处”。[6] 764-765针对受贿问题,一面斥责“得赃甚多”的祁县知县“甚属可恶”,以表明其对受贿行径的极度反感,一面命晋抚王兆琛及直隶总督将该知县寓所、原籍家产查抄,借此惩一儆百,“以为居官贪婪者戒”。[11]
十月二十日,道光帝对案犯进行最终严惩。有失察之罪的梁萼涵,尽管早已因病残废,亦未能博得道光帝同情,仍被按律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借名撞骗的梁萼涵堂弟,被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收受贿赂的祁县知县被判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受贿的典史、差役诸人亦各有处罚。此外,亦曾得赃的署理河东道虽因病故而免于刑宪,但先前在工部任职时将其保举的各堂官则被牵连遭吏部议处。[6] 814
尤为注意的是,道光帝曾在案件审理期间梁萼涵罪名未定时暂时“查封”其家产,但在结案时,则以梁“尚无赃款”而“加恩”赏还。此举实则反映出道光帝在吏治整饬中以道德为评判标准的思想倾向。梁萼涵失察后果严重,必须科以刑责,然其因未曾婪赃,道德无可指摘,故道光帝又以明发上谕宣示朝野的形式“加恩”赏还其家产,以与查抄因受贿而道德有缺的知县家产之做法相区别,彰显出道德维度在律法之上的独特地位。
再次,前任晋抚梁萼涵遣戍未久,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山西巡抚王兆琛又因河东盐务卷入风波,而此事引起道光帝高度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因案情揭露系负有监察百官之责的御史所奏,且为指名揭参。御史杨彤如在奏章中并非泛泛谈论吏治弊病,而是直接指出所参对象为现任晋抚王兆琛,参奏者身份及明确的涉案对象无疑提高了此奏的可信度。二是因所参内容为陋规问题。陋规虽为清代地方官补充公务开支的重要方式,却非合法收入,且其性质“半公半私”,或兼有腐化意味。故自乾隆朝以降,清帝尽管因陋规泛滥而总体持消极放任态度,但对于曝光案件则秉持“既败露则应问”的处理原则。[12]726尤其是据杨彤如所参,王兆琛不仅收受盐务、“贡余”陋规,且为“复设”,这更较官员“相沿收受”陋规情节为重。
故而,闰四月初六日,道光帝在披览杨彤如奏折当日,即派遣深为倚重的刑部侍郎陈孚恩、户部侍郎福济前赴山西调查。并且,道光帝在明发上谕中假称“前往甘肃查办事件”,以免消息泄露。[6] 883可见其对此案十分重视,在处理上又相当谨慎,力求根究彻查。
复次,王兆琛复设盐规被查实后,其境遇急转直下。五月十九日,陈孚恩等上奏道光帝,呈明初步调查情况。钦差根据盐商、巡抚衙门吏役等口供与河东盐务公费账簿等物证,基本认定王兆琛确曾命盐商恢复呈送陋规之旧例。在此基础之上,出于对道光帝重惩贪腐意图的领会,陈孚恩等更奏请将王兆琛革职严审。
面对王兆琛需索陋规情节的显现,道光帝随即展开一系列彻查行动。五月二十三日,道光帝允准钦差奏请,将王兆琛革职拿问,并命钦差严密查封王兆琛任所财产;五月二十四日,复派山东地方官查封王兆琛原籍家产,“不准稍有隐匿寄顿”;[6]896六月初九日,钦差审拟定案,奏报王兆琛复设吴其濬所裁盐规,“贡余”陋规系由梁萼涵裁革但王兆琛未曾复设后,道光帝又命将王兆琛押解来京;六月十八日,王兆琛起解入京后,道光帝严令将其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复审。[6]900
事实上,“提京复审”含有深意。在道光朝,钦差外派审案后,再将人犯提至京师复审的情况甚为少见。道光帝并非质疑陈孚恩等之奏报,从复审结果看亦未有调查突破或拟定罪名变更。可见,“复审”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审理,而在于通过将复设陋规的封疆大吏王兆琛押解至京,并动用处于清廷权力核心的军机大臣审讯以扩大该案影响,进而彰显惩贪决心,给予京师内外官员以警示。此种目的亦为群臣所领悟,在京任职的曾国藩就在家信中慨叹,不论最终如何处置,道光帝的一番举措已令王兆琛“身败名裂”,并由此提醒诸弟为官不可不“自慎”。[13]172
最后,道光帝以激浊扬清姿态,将复设陋规的王兆琛与裁革陋规的吴其濬、梁萼涵置于道德评判之下进行惩奖。虽然王兆琛复设陋规有具体情景:一方面,王兆琛辩称,复设缘由系因盐务办公经费不敷,而所得养廉银中又有“因公坐扣”之项,难以调剂;另一方面,客观而论,王仅恢复7200两规费,实际比历届前任收取1万两陋规为数要少[8],但道光帝却将其行径全然归因于品德低劣,指斥为“恣意贪婪”。六月中旬,道光帝命山西、山东官员查抄王兆琛家产。[6] 900七月二十一日,王兆琛被“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对于吴其濬、梁萼涵,道光帝则不吝褒奖,称前者“洁己奉公,洵不愧为封疆大臣”,子孙5人或遇缺即选、即补或赏给举人,准予会试;赞后者“廉正自爱”,与王兆琛有“霄壤”之别,将之释放回籍,并赏六品顶戴。然道光帝塑造道德高尚的廉臣形象背后,细究之下则可发现刻意掩藏与重新阐释的诸多痕迹。在宣传梁萼涵裁革“贡余”陋规时,道光帝并未言明规费“仅值银一百十余两”[8],且轻易略过梁失察罪名,及其在巡抚任上亦曾收受盐商陋规的事实。在以“洁己奉公”赞誉吴其濬裁革盐规动机时,道光帝却有意消解了最初将吴此举视作普通公务行为的定性。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久病缠身的吴其濬因无力向盐商催科,为应对道光帝责难,不得已奏请裁革作为办公银两的盐规“充抵”短缺课银呈缴中央。道光帝其时仅视之为盐课亏短下的变通手段,更催促吴其濬迅速筹纳剩余课银。[6] 374而吴不久即以病辞官,既未体会过长时间办公银两来源无着的景况,实际为河东盐商所减少的陋规开支亦属有限。
梁萼涵、王兆琛廉洁典范的塑造过程,不仅反映出皇权专制的独断性,道光帝始终以权威者的姿态掌握着对二人行为的解释权,更揭示出在道光末年贪腐、陋规盛行之下,道光帝为求引导官风,“短中取长”树立典型的无奈。当吴其濬最初奏报裁革陋规时,道光帝以陋规本不合法,裁革之举理所当然,对其不作评价,然王兆琛复设陋规案发后,却又在对比中不得不承认吴行为之可贵。而梁萼涵虽亦曾收受盐规,但道光帝为维护其因裁革小额陋规而树立起的廉正形象,则对此置之不问。
通观“晋抚遣戍案”始末,道光帝仅将案件起因简单归结为吏治问题,以“激浊扬清”的方式应对,核心则是对官员行为中所反映出的道德水准的强调。当此番吏治整饬以惩贪倡廉收官时,遮蔽其中的却是如孙家家产丰厚却自称家道不裕不愿充商的矛盾之处,地方官员之所以能够需索陋规的根源所在等更为深刻的问题。
三 各具苦衷:“晋抚遣戍案”中的多元立场
在“晋抚遣戍案”中河东盐商、道光帝与山西地方官举动各异,在案情演进的表象背后,实则反映出道光末年上下交困中,三方基于各自利益考量,秉持不同立场并由此衍生出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
就河东盐商而言,由于盐业经营亏损严重,山西富户逃避充商已为常态,不仅如孙陈笏般行贿现象频发,甚至为此避居外省者亦屡见不鲜。[2]6089同时,浮费陋规遍布地方衙门上下,盐商为此每年支出白银高达28万余两[3] 73,王兆琛需索的7 200两实为冰山一角。由此可见河东盐务的失序乱象。
河东盐务疲敝归根结底在于成本过高导致售价昂贵,百姓“择贱而食”,最终“官不敌私”。盐商眼见官盐滞销无能为力,甚至不得不赔本售卖。究其原因,官盐成本过高与专商制度下的陋规开支及盐课过重紧密相关。一方面,专商制度下,盐商销售区域固定且分配有销量任务,进货、运输、销售等环节皆受严格控制,复杂的监管体系本为防范私盐而设,却由于程序冗杂反令官吏借机需索,出现名目繁多的浮费陋规。另一方面,除人口增长带来市场需求扩大外,清廷亦以弥补军费、河工经费为由增加河东盐引,甚至直接提高盐课,迫使盐商承受巨大经济负担。在这些临时性开支停止后,所增加的盐引与课税却并未随之取消,河东由顺治初年40万引、13万两课银,增至道光年间70.8万引、71.2万两课银。[3]52,69乾嘉时期,在河东盐务“办理裕如”的表象下早已因此而潜藏危机,一是引数过多,潞盐时有滞销之虞,二是盐课涨幅过高致使官盐单位成本大增,一遇盐池产盐不旺、进价上涨或银钱价比波动,商人即无利可图。
由于上述两项内在原因,河东盐务本已脆弱,最终又因遭遇道光朝中期以来的频频打击而难以为继。道光十一年,邻区淮北盐政改革后“盐价大贱”,“倒灌河东”,潞盐销量持续下降。[1]十五至十九年,河东盐池连年水患,灶户产盐成本上升,盐商既要负担部分盐池修理费用,又要承受进价提高的压力。二十二年,随着银贵钱贱、私盐泛滥等不利因素愈演愈烈,官盐壅滞日甚,盐商陷入“难以支持”的处境。二十四年,道光帝不得不允准梁萼涵奏请,此后三年暂停河东4万盐引及相应4万盐课,并于二十八年,在巡抚王兆琛奏请下将之续停三年。[14]然此举仅能暂时掩盖已日趋表面化的盐商蚀本赔累的事实,却难以扭转恶化中的盐务困境。
由此观之,以孙陈笏为代表的山西富户向官府行贿求免充商实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一方面,充商带来的经济损失甚于行贿。盐商受官府管束,有规定的盐引销量任务,即使官盐滞销,盐商仍须按照官方所分配的盐引数额从盐场进货并缴纳相应课银,库存积压造成盐商资金难以回笼,不得不亏本减价售卖。在经营赔累的情况下,富户退商却非易事。因官府知晓富户逃避充商心理,顾虑接充乏人,故直至盐商“家资荡然”始准告退。[15]另一方面,充商会造成巨大的时间成本浪费。充商之后,富户不得不离家远赴潞盐盐场所在地运城处理进货等事务,严重影响原有商业经营活动,构成无形的经济损失。孙陈笏在运城期间即因无法料理家中当铺生意且忧惧充商赔累而“终日愁叹”,最后竟至一病不起。[5]
而“晋抚遣戍案”中商众向王兆琛呈送陋规亦与河东盐务困境不无关联。此举含有迎合王兆琛之意味,因山西巡抚兼管盐政,盐商告退需经王兆琛同意,故为求早日退商、摆脱赔累,商众不得不满足巡抚需索;同时,陋规成为金钱与政治权力交换的途径,由于官盐难销、赔累严重,盐商遂宁愿以呈送7 200两陋规的代价作为对王兆琛奏请朝廷续停4万盐引的“酬谢”。[8]
就道光帝而言,其对“晋抚遣戍案”中的河东盐务情弊并非毫无觉察。早在此案发生前,河东困局已有明显迹象,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因盐商无力销盐不得不暂停4万引额,道光二十六年,复有御史戴孙陈言河东盐商亏累沉重,富户被迫充商“大为闾阎之累”。[16]然而道光帝却并未有改革以扭转河东困局的决心。
首先,河东课税征收现状相对较好,改革并非当务之急。一方面,道光末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为应对财政危机,道光帝甚至不惜施行在其看来弊端明显的“开源”政策,如紊乱正途、有碍官风的捐纳等。在多方筹措国库经费的情况下,对于盐务问题,道光帝最为关心课税征收。另一方面,河东盐商虽然亏累,然由于地方官员强行催科,除暂停征收的4万盐课外,其余课银均可完缴。故从清廷课税收入角度看,相比于两淮盐区、长芦等盐区频年大量积欠的局面,河东盐区现状相对较好。因此,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道光帝集中精力于派遣钦差前赴课税拖欠严重的直隶等省裁革盐务陋规,试图通过此番“恤商”手段减轻盐商成本,以求“减价敌私”,最终达到“裕课”目的。故其并未将改革河东盐政提上日程。
其次,改革专商制度有影响河东及邻区课税收入的风险。在专商制度下,因行政过度干预带来的官吏需索陋规构成盐商经营成本,然若改为“民运民销”,民人不受官府管束,进货多寡听凭自愿,纳课后可在盐区各处自由售盐,则能极大减少采购、运输等环节各种检查所造成的陋规开支。道光十一年淮北票盐改革即以此为宗旨,并取得成功。道光二十六年,御史戴孙亦建议在河东进行此种改革。然而,道光帝却并未采纳,主要原因是在河东盐税收入尚可的情况下,道光帝不愿承担改革可能造成的经济风险。一是近期内将影响河东盐区课税收入。盐政改革是一项牵涉甚广的复杂工程,需要时间过程。在此期间,本已深受盐课之累的河东盐商听闻改革则会心存观望,对于盐课征收“大有妨碍”,在清廷财政窘迫的情况下有“利犹未见,害已先著”之虞。[6] 409二是影响邻区盐课征收。相邻盐区盐价各异,价低一方往往侵灌邻区,导致对方盐引滞销而影响其课税完纳。据此而论,即使河东盐区改革后得以“减价敌私”,然人数众多的民贩难于约束,不免受利益驱使前往邻区长芦、两淮售盐,加剧芦、淮盐政危机。事实上,淮北票盐改革后即引发侵灌山西、山东的后果。
再次,道光帝为政风格偏于保守,缺乏改革魄力。道光帝虽在主政期间有漕粮海运、淮北票盐改革等举措,但实则是在无可回避情况下的小修小补。道光六年,京师粮食因河道受阻无法供应,道光帝不得不实行漕粮海运,然改革虽取得巨大成功,其却未能坚持定见,次年河道畅通后即恢复河运。道光十一年,道光帝允准两淮盐区中淮北实行票盐改革,系因淮北“已全面崩盘,除改革外,别无起死回生之法”,而对于商力亦疲但尚可支持的淮南却未行改革,为两淮盐区留下隐患。[17]65尤其是道光帝晚年对待政事颇有倦怠[18]56,故其对于尚可运行的河东盐务缺乏改革意愿。
可见,在清廷财政窘迫的情况下,道光帝在盐务问题上最为关心课税收入。由于河东盐课征收现状相对较好,而盐政改革则有损害课税的风险,故偏于守成的道光帝在维持清廷财政收入的利益判断下,虽知晓河东盐务运转实系山西富户以“有限之家资”供于盐课“无穷之赔累”,却仍默许了地方官员强征催科、逼令充商等种种损害民生的行径。[1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光帝对“晋抚遣戍案”的处理即是其竭力维系现状的具体体现。道光末年河东盐商举充愈加混乱,“有一年之中,新旧更换至二十余商者,有一县之地,先后提送至一二十户者”,地方官允准富户免商缘由多有“暧昧不可究诘”之处。[2]6091故从某种意义而言,道光帝重惩梁萼涵失察与署理河东道之受贿,即是对行贿免商乱象的惩戒与警告,以遏制山西富户逃避充商风气蔓延,保证盐商数量充足,最终达到维持河东盐课收入的目的。
道光帝对王兆琛施以革职遣戍重惩,表面看系因其在商力疲乏时复设盐规,未能切实“恤商”。更为重要的是,王兆琛以盐商经营困难为由奏请续停4万盐课,却暗自复设陋规,与中央税赋产生直接矛盾,罪在“不顾商课”。在道光帝看来,王兆琛收取的陋规本可作为盐课的一部分呈缴,故道光帝训斥畀以封疆重任的王兆琛“辜恩”不仅在于其收受陋规行径“贪鄙”,更在于其只着眼地方办公经费有无,却罔顾中央财政收入盈虚。[6]900
事实上,由于立场所限,道光帝关注于清廷盐课收入,却未能设身处地对山西富户在充商赔累与行贿免充间进退维谷的处境抱以同情,相反认为“晋抚遣戍案”中行贿与呈送陋规等现象是山西“地方殷富”的表现。[19]215同时,其仅意识到陋规对盐课收入的侵蚀,却无力顾及裁革陋规后地方官从何处获取盐政办公经费的现实问题。在不消除富户逃避充商动机与官吏需索陋规制度诱因的情况下,道光帝只试图借助“晋抚遣戍案”激浊扬清,将维持盐务运转诉诸官员道德自律。
就巡抚为代表的山西地方官而言,透过“晋抚遣戍案”前后关联史事,其表现颇值得玩味。作为兼管盐政的巡抚大员,梁萼涵、吴其濬与王兆琛对于河东盐商困境自然深有感触。然三人却既未主动奏陈“补救”良策,亦不支持盐政改革,致令盐商愈形亏累,富户逃避充商不断,地方普通官吏趁机索贿。造成地方官员在现行制度中迁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山西巡抚以此迎合道光帝对河东盐政的既定态度与对潞盐课税的需求。一方面,因明了道光帝并未有改革河东盐政的决心,故吴其濬虽知晓通过改革降低成本后潞盐可“减价敌私”,于河东盐商有利,却以盐价降低将侵灌淮、芦盐区而奏陈不可“草率”改制。[6] 409另一方面,梁萼涵、王兆琛等深悉清廷中央陷于财政危机,道光帝此际关注于筹措国库经费,故于上任之初呈递谢恩折时即表示将竭力征收河东盐课,并在实践中以“开导”为名,强迫因盐务赔累而不愿充商的富户充商;动用行政手段向盐商追缴短缺课银,盐课“一日不尽则一日不能告退”;屡屡压制商众减引减课恳求,直至盐商“力不能支”方上陈道光帝。[15]可见,在专制皇权体制下,官员基于个人政治利益考量,施政举措以道光帝意志为转移。
其二,地方官员在现行体制下可以渔利。对于山西普通地方官,专商制度中烦琐的行政环节为众多官吏提供职位与陋规收入,盐商亏累造成的富户逃避充商又令其可从中受贿图利,自然不愿改革。对于山西巡抚,维持现行盐制既可索取陋规,同时亦避免了与既得利益者间的矛盾冲突。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北改行票盐时即遭遇来自丧失中饱之利的官吏的强烈抵制,出现“群议沸腾”的局面。[20]11607
其三,为绥靖地方,山西地方官对易激化官民冲突的“课归地丁”改革持反对态度。所谓“课归地丁”即将原本从盐商处征收的盐税摊入地丁银中向百姓征收,如此便可减轻盐商经营成本。然对于此种改革,巡抚吴其濬却力陈不可。在其看来,“课归地丁”看似增加土地所有者税赋,但地主可通过提高地租等方式转嫁压力,故最终承担者仍为底层小农。银价昂贵已令民力不堪重负,百姓能否完缴盐课尚属存疑。[6]409与此同时,山西境内不稳定因素正潜滋暗长,对百姓而言,购买已含盐课之盐与“课归地丁”后直接为盐缴税差异甚大,前者无形且相沿日久,后者有价为新增支出,晋籍官绅徐继畲因此担忧民间易将改革视作“无端加赋”而导致“怨谤群兴”。[21]493尤其是,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吴其濬回禀道光帝不宜“课归地丁”的数月前,江苏常熟等地因官府“浮收”酿成民变巨案,引起清廷君臣极大震动。[注]参见郭燕红.从常熟均赋到昭文民变——清道光晚期江南社会危机透视[J].西南大学学报,2016(3):169-176.可见,赋税征收不当极易激化社会矛盾。故而,在民情不靖的时局下,地方官员出于绥靖考虑,对政治风险高且前景不明朗的改革持回避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梁萼涵等巡抚在上奏道光帝河东盐务情形时皆以清廷财政利益为立言基础,且竭力表现出盐课征收的不易,然作为地方官员,在实践中亦需将筹集地方政府办公经费纳入考量范围。故梁萼涵在向道光帝陈言河东盐商亏损,请求暂停部分盐引的同时,仍收取盐规,吴其濬则是在苦撑病体、无力催科的情况下,不得已将陋规充抵缺课。而当王兆琛顺利完成清廷规定的盐课任务后,并未试图恢复暂停课银,转而令盐商呈送陋规以弥补办公经费不足。由此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配方面的某种分歧。
四 结 语
道光二十八至二十九年“晋抚遣戍案”主要围绕河东盐务,由“梁萼涵失察富户行贿免商”与“王兆琛复设盐务陋规”两部分案情构成。这起吏治整饬典型事件不仅揭露出山西地方官场贪腐乱象,更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盐政积弊之积重难返,道光帝统治方式迁延因循,地方官员对道光帝迎合中存有利益差异的复杂关系,由此展现出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上下交困、危机重重的复杂图景。
山西富户希图通过行贿逃避充商的背后是河东盐商因成本过高、“官不敌私”而导致亏累沉重的现状,此实与全国诸多地区盐务困局有共通性。一方面,清廷增加盐课直接造成官盐成本极大上涨。引课不仅为“潞盐利病之大源”[9]247,事实上,随着乾隆中叶至嘉庆中叶清廷盐课额征银总数“增至四倍”,各地盐商普遍因此陷入困顿。[22]79另一方面,行政过度干预而滋生的陋规泛滥增加了河东等盐区内盐商经营支出。在盐务日疲的情况下,抱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士人如魏源等发出变革呼声,但却并未引起当道者重视。[17]82即使身为疆吏重臣的陶澍力行票盐改革,亦难以拓展范围,突破淮北一隅限制。
道光帝为规避改革风险以保证现有课税收入,未能直面盐务制度转型的时代要求。当收受贿赂、需索陋规等行径暴露时,其仅视之为吏治问题,归咎于官吏个人品行“贪鄙”,希图依靠“晋抚遣戍案”惩一儆百,褒奖梁萼涵、吴其濬裁革陋规之举引导官场风气。然而此种应对方式因未能消除诱发贪腐的制度因素而显得疲软无力。尤其是,道光帝除因御史参奏王兆琛复设陋规而对之进行惩办这一偶发事件外,仅主动派遣钦差裁革缺课严重省份的盐务陋规,却未对其余省份盐规采取实质性整顿措施。可见其扭转盐务疲敝的举措实有本末倒置、外张内弛之嫌。
在专制集权统治下,山西巡抚竭力维持河东盐务运转既是出于维护地方秩序的政治自觉,更是为自身政治前途考量而迎合道光帝的表现。故在明知由盐课沉重引起盐务疲敝的情况下,梁萼涵仅在无法催征课银时方才谨慎奏请“暂缓”少量盐引。在改革有利于本地商民利益却可能因侵灌邻区影响清廷盐课总额的情况下,吴其濬反对河东盐政改革建议,道光二十四年,两江总督璧昌亦曾因此议驳淮南推行票法的奏陈。[17]94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巡抚等地方官为筹措办公经费而收取陋规虽早已常态化,然道光年间清廷中央权力强大,道光帝为打击陋规对盐课收入的影响,在需要整饬时仍可重申禁令,数位山东巡抚即因收受盐规遭降级处分。王兆琛更由于“复设”行径,成为道光朝唯一一位因陋规而被革职遣戍的封疆大吏。反观咸同以降,督抚财权增长,各地开征厘金用于地方支出。
总之,在道光末年这段易被忽视的历史中,虽有君臣民于困局中勉力维持的努力,但更多的却是在现存体制中无法找到合理出路的无奈,预示着风云激荡的剧变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