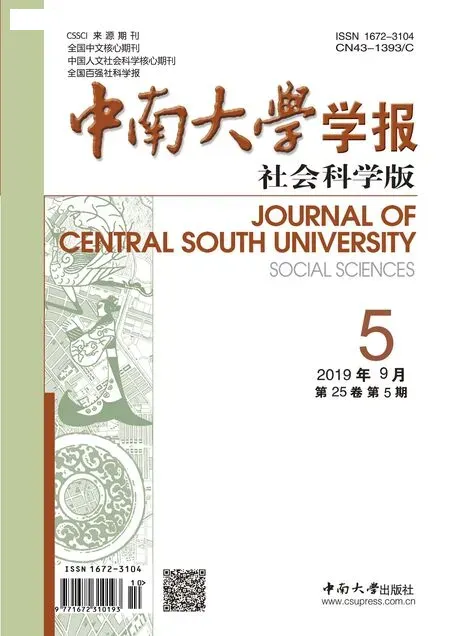道光朝陋规整顿与朝政困局探微
——以道光末年晋抚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为中心
2019-01-04张艺维
张艺维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29)
道光二十六年(1846),山西巡抚吴其濬宣布大幅裁减盐商呈送巡抚衙门的陋规,其后不久,吴其濬卸任,新任巡抚王兆琛因办公经费不敷,恢复被裁陋规。道光二十九年,王兆琛因复设陋规案曝光,被革职遣戍新疆。案件所涉陋规问题实为贯穿有清一代吏治整顿的重要内容。所谓陋规,系指官员所得灰色收入,其性质介于“半公半私”之间。一方面,相沿收受、数额固定的陋规为官员弥补公务开支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陋规既不合法,且存在被蠹吏滥收、滥用等情况。特别是晚清以降,芜杂泛滥的陋规成为吏治日益窳败的显著表征,亦成为清政府丧失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由于陋规对清代地方政治生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陋规问题早为学界关注。然而,在积累了丰富成果的同时,现有研究尚存在三点不足:一是研究时段集中于雍正与光宣时期。因前者发生了曾一度有效遏制陋规蔓延的养廉银改革,后者则在清末新政范畴内出现划定地方办公经费标准,以合理化陋规的尝试[1-2],然而对处于官场风气由清转浊关键期的嘉道两朝陋规实况的考察却相对薄弱[3]。二是侧重于展现州县基层官吏与陋规之间的复杂关系[4-6],对督抚、两司等地方高级官员对待陋规的态度关注较少。三是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对清廷整顿陋规案件的探讨较为欠缺。晏爱红在《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一书中对此虽有细致研究,但论述时段集中于乾隆朝[7]。
论及道光朝的陋规,王兆琛案作为唯一一起封疆大吏因陋规被革职遣戍的重案值得关注,但目前学界对此尚少有研究,仅有《山西通志》等书略加介绍案件审办过程[8-9]。笔者曾从河东盐务与盐政的角度,将此案与道光末年另一起因失察下属收受盐商贿赂而引发的山西巡抚革职遣戍案进行归纳与探讨[10]。然而,王兆琛案所映射出的诸多有关陋规问题的历史面相仍值得深入挖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该案为中心,并结合关联史实,通过观察道光朝尤其是道光朝后期陋规在地方官场中的实际状况,解读由此反映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官场政治生态特征与关乎吏治的结构性问题,进而在分析王兆琛案被揭发与被处理之特殊性的基础上,揭示清廷中枢对待陋规的复杂态度及实质、案件引发的人事变动与背后的官场利益集团势力扩张等内容,以期对清代陋规问题与道光朝政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王兆琛复设陋规案始末
王兆琛(1786—1852),字叔玉,山东福山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道光十年,王兆琛由御史外放知府,历任陕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升任山西巡抚。道光二十九年初,王兆琛复设盐务陋规一事曝光,引发了一起道光末年颇具影响力的吏治大案。该案从发生至结案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为案发阶段。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六日,御史杨彤如参奏山西巡抚王兆琛,内容包括复设前任巡抚吴其濬所裁盐务陋规、失察轿夫寻衅滋事等,其中尤以复设陋规情节最为严重,因所涉金额达白银万余两[11]。随即,闰四月初九日,道光帝遣侍郎陈孚恩、福济前往山西调查此事。此际,道光帝在公开上谕中假称钦差将“驰往甘肃查办事件”[12](卷467),以免消息走漏;同时,为迅速开展严审,还特别允准陈孚恩等率四名司员协同办案,超过钦差随带两到三名司员审案的惯例。这些举措皆透露出道光帝对王兆琛案的高度重视。
第二为调查迅速升级阶段。一是王兆琛被革职严审。五月十九日,尽管御史多项指控经查与事实有出入,但经过对人证的初步审讯,钦差已基本确认王兆琛复设陋规属实[13]。道光帝因此严令将王兆琛革职拿问,王兆琛案进入实质性审理程序。二是王兆琛任所、原籍财产遭查封。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间,道光帝一面谕令陈孚恩等严密查封王兆琛山西任所财产,一面命登州镇总兵官与登州府知府查封王兆琛山东原籍财产,并派遣京官程庭桂驰往山东监督查封事宜。三是对王兆琛之原山西巡抚一职进行人事安排。五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任命仓场侍郎季芝昌为山西巡抚,未到任前由山西布政使兆那苏图署理[12](卷468)。由以上三个步骤可以看出,随着钦差向道光帝奏报初步调查结果,王兆琛之地位已岌岌可危,道光帝显然做好了王兆琛复设陋规罪名成立后对其严惩的充分准备。
第三为案件审理高潮阶段。六月初五日,钦差在严审王兆琛后奏请将其革职遣戍。据查,山西巡抚因兼管盐政,河东盐商每年提供1.2万两陋规作为办公经费。道光二十六年,巡抚吴其濬将其中1万两裁革。道光二十七年,王兆琛复设节规每年7 200两(元旦、端午、中秋每节各2 400两),至道光二十九年案发,王兆琛共收受陋规1.44万两。对于复设陋规情节,王兆琛虽供认不讳,但又力图辩解因“盐务用项苦于无款垫办”才收受盐商陋规[14]。
然而,在案情已真相大白的情况下,六月初九日,道光帝却并未简单允准钦差奏请了结该案,而是做出详细谕令。一方面,道光帝将王兆琛复设陋规行径斥责为“贪鄙营私”“辜恩溺职”,下令查抄其家产,并将其押解至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复审。另一方面,道光帝称赞裁革陋规的已故前任巡抚吴其濬“洁己奉公”“洵不愧为封疆大臣”,要求查明吴其濬子孙情况,给予奖赏[12](卷469)。道光帝采取提京会审之举措,与在告知全国的明发上谕中对王兆琛、吴其濬的贬斥与褒奖,令王兆琛案一时间成为朝野瞩目的重大案件。
第四为案件处理阶段。七月上旬,山西、山东两省相继完成查抄王兆琛资财事宜,道光帝谕令将银钱等物解交内务府。七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刑部会审认定王兆琛罪名属实,道光帝将王兆琛革职遣戍新疆[12](卷470)。十二月初一日,吴其濬之五子及长孙受到道光帝“赏给举人头衔,准予会试”等奖励[12](卷475)。至此,王兆琛案终宣告结束。
综上可知,王兆琛复设陋规案的案情并不复杂。简言之,即前任山西巡抚吴其濬所裁陋规被继任巡抚王兆琛暗自复设,道光帝发觉此事后按律惩办了王兆琛,且表彰了吴其濬的廉洁品行。这似乎是一个惩贪倡廉的典型案例,然而,在看似成功的吏治整饬背后,实则疑窦甚多,而透过对该案深层次的解析,不难发现道光朝陋规与吏治问题的错综复杂,以及清廷整顿陋规的不彻底性。
二、王兆琛案与道光朝中后期地方官场陋规实态
与一般案件“相沿收受”陋规的情节不同,王兆琛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复设”陋规。一方面,裁革陋规的前任山西巡抚吴其濬受到朝廷褒奖,其行为被钦定为“洁己奉公”,然而检视史料则会发现,吴其濬裁革陋规另有隐情,并非仅仅品性廉洁所能解释。而通过王兆琛案亦可更深刻理解其时“不宜轻裁陋规”的官场环境。另一方面,在吴其濬已将陋规裁革的情况下,王兆琛复设陋规缘由值得探究。同时,在官方公布的案情之外,王兆琛一案还牵连着更多关于陋规与地方官场的隐秘内幕。
(一)王兆琛案背景与“不宜轻裁陋规”的官场实态
在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中,吴其濬裁革陋规为此案的重要背景。了解吴其濬此举是出于追求廉洁,还是有复杂原因,关乎怎样认识被裁撤的陋规,也关乎怎样更为全面客观地评判王兆琛案,故有必要对吴裁革陋规动机与当时处境稍作探究。事实上,尽管吴其濬最终决意裁革盐规,但从时间点看,其于道光二十五年八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直至次年四月临近呈缴盐课之期方裁革陋规;从被裁陋规的用途看,这些银两未转归盐商,而是被用作充抵短缺课银上缴朝廷。此外,在奏报裁减陋规时,吴其濬并未否认原有陋规用于公务的必要性,仅以办公经费当“极力撙节”为言[15]。由此可见,陋规裁革过程颇有微妙之处,非仅仅如道光帝评价吴秉性“清节”所能涵盖,个中缘由是多方面的。
其一,以陋规充抵短缺盐课,缓解来自道光帝的压力。山西巡抚兼管河东盐政,该盐区因税收不菲而颇受道光帝重视。吴其濬获知调任晋抚后,即积极向道光帝表态将竭力征收盐课[16],但当道光二十六年呈缴盐课期限临近时,吴却仍面对4万两课银的巨大缺口。由是,裁革1万两陋规充抵盐课,即是其设法减少缺课,改善道光帝对其办事不力印象的一种努力。其二,受身体状况不佳影响。因私盐泛滥、盐商普遍亏损,河东盐课征收早已成为难题,历任山西巡抚不得不为此耗费巨大精力。吴其濬因痼疾缠身,不堪负担如此繁杂的工作,面对盐商纷纷以经营困难为由拖欠课税,其难以辨别情伪,亦无力催科,而在化解缺课危机时仅能以裁革陋规为一时之计,再无心筹划整顿盐务及陋规革除后行政经费来源问题。未几,吴其濬因病重休养、辞官,当年年末不幸逝世[17-18]。其三,与试图暗示道光帝减轻盐商负担不无关联。嘉庆年间,清廷增加河东8万盐引(240斤为1引)及相应8万两白银课税,称“活引”,意即灵活增加的盐引。然而道光朝后期,因官盐滞销,山西巡抚曾试图奏请停征活引,但道光帝虑及鸦片战争后紧张的财政状况,仅允暂停一半。由此看来,吴其濬虽未能足额征收盐课,然所缺4万两恰为未能停征的另一半活引却恐非巧合。其在奏折中称鉴于国库空虚,河东盐课“断难再行议减”,却又借盐商之口道出盐引销售困境。而裁革历来充作办公经费的陋规充抵活引,更有向道光帝暗示活引已不合时宜的意味。只是这番试探未能奏效,道光帝对改善河东盐商处境并未表态,反着力催促吴其濬命盐商迅速筹纳剩余课银[12](卷429)。
吴其濬裁革陋规的行为看似与当时绝大部分官员所秉持的“不宜轻裁陋规”的态度不同,但其举动所兼有的多重用意,因未能完征盐课而设法减轻责任的考量,因身体不适而仅能顾及眼前的权衡,以及向道光帝申明河东盐务困境的潜在目的等,则透露出其最终做出裁革决定的复杂性。而审视吴其濬革除陋规后,继任巡抚王兆琛因复设陋规遭革职遣戍的案例,或可窥见众多官员奉行“不宜轻裁陋规”信条的原因所在。
首先,陋规已成为地方官员维持公务与生活开支的重要来源,裁革陋规并非只涉及当事人,还事关继任者。乾嘉以降,随着物价上涨,公务开支缺口增大,养廉薪资已难以满足地方官员需要,处于灰色地带的陋规成为地方官弥补经费不足的重要途径。现任官员出于各种原因裁革陋规,将导致后任难以为继。如道光初年,家境殷实的昆明知府陈锡熊不需仰赖陋规,一切用度皆由家中负担,遂大刀阔斧裁革陋规,但其去任后,继任者办理公事难为无米之炊,又不得已将陋规复设[19]。与之类似,当吴其濬基于复杂的动机裁革盐规后,王兆琛却因办公经费不敷而复设陋规。
其次,裁革陋规将使后任者收受陋规之行径超过相沿收受的界限,被言官参奏的风险大增。道光朝时期陋规已是“无处不有,无地不然”,道光帝实际亦默许了陋规在“官民相安”情况下的存在[20]。对于负有监察之责的京城言官而言,无端参奏相沿已久的陋规颇显唐突,难以引起道光帝重视,与陋规相伴的其他问题成为言官决意参奏的重要因素。前任官员裁革陋规后继任官员又复设陋规的行径,明显有别于相沿收受陋规的一般情况,易成为言官参奏的目标。是以道光中叶,武昌知府裕谦告诫所辖州县官,即使个人不需陋规,亦应当“为继我者虑之”,不能裁革[21]。在王兆琛案中,正因为吴其濬已将盐规裁革,御史杨彤如才将参奏矛头指向王兆琛“复设”陋规。
需要说明的是,学者多强调舆论对处于灰色地带的陋规的理解与宽容[7](199-210),然而事实上,即使至道光年间陋规已成泛滥之势,时人对陋规的看法仍存有张力,既承认陋规存在的合理性,宣扬“不宜轻裁陋规”,同时又不乏为追求廉洁名声而不愿收受陋规的心理,如前述昆明知府陈锡熊。只不过,养廉银收入与公务支出间存在巨大缺口也是事实,道光末年的浙江按察使黄宗汉为“成个廉名”,不收陋规,却在任仅三月即欠债1千两[22](90)。
(二)王兆琛复设陋规缘由与被掩藏的地方陋规内幕
王兆琛虽有复设陋规罪名,然其并非将吴其濬所裁革的1万两陋规全部复设,而是降为收取7 200两。从清宫档案所记录的抄没家产情况看,对比道光年间同样被抄家的大臣,素有清廉之名的英和拥有白银4.5万两,琦善家产高达12万两,而王兆琛则仅有6千余两白银及一些田地祖产[23],可以想见,其并非刻意敛财的贪黩之人。那么,王兆琛缘何要颇不明智地复设陋规,令毕生名节化为乌有,且沦为世人指摘对象?
其一,侥幸心理是促使王兆琛敢于复设陋规的首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清廷数十年来对收受陋规的宽纵态度,使得如王兆琛之类官员对陋规罪行的严重性缺乏警觉。尽管陋规并非官员合法收入,但道光帝之祖父乾隆帝曾公开表示陋规与婪赃不同,“不败露则苟免”[24](卷341),道光帝之父嘉庆帝对陋规亦未采取强有力的整顿措施。道光帝也基本延续了父、祖对待陋规问题的方式,在其主政的二十余年中,未出现督抚大员因陋规受到严重处分的事例,无疑助长了王兆琛“胆大妄为”之举。另一方面,收受陋规属“暮夜之行”,往往因缺少证据而难以定罪。陋规呈送者与收受者皆知陋规不合法,故行事隐秘。王兆琛案中,王兆琛起意复设陋规时并未亲自出面与盐商沟通,而是由门丁张某向盐商商总暗示巡抚衙门办公经费不敷,商人即心领神会“主动”呈送陋规。而盐商为免暴露,在账簿中并不依据实情将支出登记为陋规,而是借名指代[14]。当然,这些看似掩人耳目的手段终究纸里包不住火,在道光帝谕令严查之下,均被一一揭穿。
其二,芜湖关亏空所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是促使王兆琛复设陋规的直接原因。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下令将芜湖关库银解往江西以备军需,结果却暴露出始自乾隆年间的芜湖关监督挪用库银以充办公经费之事,王兆琛作为前任监督亦位列其中[25]。对王兆琛而言,其升迁之路并未受此影响,仍顺利擢任甘肃按察使。因王兆琛所挪用金额属“额外盈余银”部分,并非“正额”关税,故不同于某些职官遭降级调用的处分,王兆琛仅需赔缴银两即可,可见其所犯为常见的轻微问题。但是,王兆琛自此背负6.2万两高额赔项,并需在8年内完缴。据此推算,王兆琛每年约需赔银8千两,而其所任甘肃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每年养廉银分别仅为7千两、8千两。不难想象,此时的王兆琛经济状况势必窘迫。道光二十七年,王兆琛升任山西巡抚后,养廉银虽达1.5万两,然扣除赔缴款项后,仅剩约7千两。由此观之,王兆琛在审讯中声称养廉银已被“全行坐扣”充抵亏短库银,导致公务经费不敷而收受陋规的说法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其背负沉重经济负担则确为实情。这一状况促使王兆琛不惜铤而走险,违规行事。
已有学者注意到嘉道年间,由挪用、亏空库款等原因造成的养廉银被扣抵,成为州县官不得不依靠陋规维持办公开支的重要原因[3]。而王兆琛的事例或可说明,督抚、两司大员虽然拥有较为丰厚的养廉银,但由于此前职位亏空造成的赔缴具有持续性,故亦可能面临与州县官类似的困境,成为陋规由州县官向地方大员蔓延的原因之一。
从这一角度,亦可见吴其濬与王兆琛对待陋规不同态度的原因所在。吴其濬早年京外履职经历仅有以钦差身份在湖南等省担任学政,道光二十年即由六部侍郎出任巡抚大员,在地方官中享有最高级别的养廉收入。而王兆琛则是从知府、道员等养廉俸银较少的官职逐渐升迁的,刚刚步入巡抚序列不久。更为重要的是,二人虽相继担任山西巡抚,在山西任上所面临的开支需求基本相同,但用于负担这些开支的实际收入却有很大区别,王兆琛由于赔付因公亏空、养廉银被大额抵扣的困境是吴其濬不曾遇到的。吴、王二人因实际收入不同所引发的对陋规依赖程度的差异显而易见。
其三,吴其濬所裁盐规金额可观,是王兆琛决意复设并从中迅速获取公务经费的重要诱因。盐务陋规为道光年间督抚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两江总督由淮南盐务所得陋规金额可与养廉银相埒,构成收入的主体部分[26](59)。而吴其濬将1.2万两盐务陋规裁去1万两的举动,无疑令继任者王兆琛丧失了弥补公务开支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吴其濬所裁盐规金额数目之大,诱发了王兆琛复设陋规的决心。当然,从王兆琛依据需要复设7 200两来看,其显然深知复设陋规是一步无奈的“险棋”,或许还抱有日后即使被核查不至于被严重追究的侥幸心理。
综上可以看出,王兆琛复设陋规行径根源于其对朝廷惩治陋规案件力度的忽视,而促使王兆琛决意复设陋规的直接原因则是此前巨额亏空导致其养廉银被大部分扣抵。一方面,从查抄家产的金额看,王兆琛并非秉性贪黩,其复设陋规初衷亦非为聚敛私财。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王兆琛又系在官场陋习中浮沉之人,其既在任芜湖关道时仿效挪用库款的惯常做法,亦从众将陋规视为转嫁经济压力之道,甚至不惜冒险复设陋规。因此,其时在京任礼部侍郎、尚不谙外官苦衷的曾国藩即在家信中痛诋王兆琛复设陋规,不能自慎[27](172)。
值得注意的是,除复设陋规外,王兆琛案尚掩藏有涉及陋规的地方官场情弊,主要有“以陋规挟制长官”与“履职程度以自身利益为转移”两方面。前者体现在知县借“京控”陋规名义逃避亏空。此事线索来自钦差审讯盐商的供词,其中提及道光二十八年中秋节前,王兆琛因“有赔项急需”,嘱咐盐商将中秋及次年元旦陋规一并致送,然钦差并未追问该“赔项”为何[14]。所幸,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曾在其自编年谱中详细撰述此事原委:道光二十八年年中,四川一县令被查出亏空库银9万余两,这些亏空大多是因其挥霍浪费而造成的,但此人无力弥补,为求自保,扬言要进京控告上司收受陋规之事。由是,曾收受该令陋规的诸位高官为免行径暴露,不得已共同出资帮助其填补亏空,原任四川布政使的王兆琛亦牵涉其中[28](103-104)。王兆琛正是因需8千两白银寄往四川,才拜托盐商提前致送元旦陋规,陷入为掩饰曾收受陋规而收受陋规的恶性循环。而知县遂得以借陋规挟制长官,逃避亏空责任。陋规对地方财政体系的破坏与对官场风气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
后者体现在琦善处理同僚案件中的两歧态度。琦善的第一次表态出现在上述知县以陋规挟制长官时。其时新任四川总督的琦善虽未收受陋规,却仍竭力居中协调,避免该知县进京揭露王兆琛等收受陋规之事。然而与此次袒庇同僚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光三十年六月,身为陕甘总督的琦善第二次遇到牵涉王兆琛的案件时却转而秉公行事,主动参奏前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署理甘肃藩司王兆琛批准兰州道唐树义借用藩司库银1万两,但银两事后并未还库,并奏请勒令三人均摊赔缴。于是,远戍新疆的王兆琛在家产已被查抄后,又有3 300余两的赔项[29]。
关于琦善处理案件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究其原因,与其所处官场政治生态变化有直接关系。知县以陋规挟制长官一事中所涉官员,除山西巡抚王兆琛外,还有曾任成都将军、署理四川总督的廉敬,曾任四川按察使的潘铎等。廉敬在道光朝颇受重用,潘铎亦升迁频频,道光二十八年时已擢任豫抚。可见,身居高位的当朝同僚与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令琦善恐据实以陈造成政治风波于己不利,故选择息事宁人,使一场牵涉甚广的陋规大案消弭于无形,不为道光帝所知[28](103-104)。对于滥借库款一事,琦善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主要出于两点考量:一是涉及人员在官场中缺乏影响力。富呢扬阿业已身故多年,王兆琛已被遣戍新疆,唐树义最高职位仅为布政使,且已因病辞官,这使得琦善在处理案件时少有官场人际关系的顾虑。二是与向新帝展现尽忠职守的姿态不无关联。道光三十年初道光帝驾崩,咸丰帝即位。咸丰帝执政初期秉持对外强硬态度,尤其忿恨鸦片战争中的主和行径,琦善作为主和势力的代表人物,本身又热衷“阴探上旨以揣摩固宠”[26](56),故不免有借机表现以改善新帝印象的意味。可以看出,在琦善处理公务态度变迁的表象之下,所不变者乃是其对个人利害、政治前途的优先权衡。
三、王兆琛案与清廷中枢整顿陋规内情
在道光帝谕令之下,王兆琛复设陋规案终以王兆琛革职遣戍新疆与吴其濬被树立为廉洁大臣典范而落下帷幕。表面看,该案处理结果彰显出道光帝惩贪倡廉的决心,然而,在陋规整顿的背后,道光帝实则另有目的。而案件审理前后的人事更迭,甚至导引出诸多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势力的悄然扩张,值得深入探察。
(一)道光帝惩办王兆琛的缘由与整顿陋规的困境
纵观王兆琛案始末,一方面,道光帝之所以严惩王兆琛,并非澄清吏治的决心使然,很大程度上系出于应对财政危机的考量。另一方面,结合同一时期钦差所查盐务陋规案可发现,在看似如火如荼的整顿背后,道光帝对待陋规防线的进一步后退,反映出清廷整顿陋规中的深层困境。
首先,对王兆琛案的处理,与道光帝在筹措国库经费的压力下,为求盐税完纳而整顿盐务的局势紧密相关。
王兆琛案曝光之时,正值道光帝着手裁革盐务陋规之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颁布上谕,宣布将派遣钦差赴课税积欠严重的盐区进行整顿[12](卷461);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道光帝两次下旨,针对长芦盐区,严令永远裁汰衙门官役之相沿陋规,针对山东盐区,分别惩办了收受盐商程仪、节寿陋规的历任山东巡抚和盐运使,五名巡抚因此被降三级调用,七名盐运使被革职[12](卷462);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道光帝再颁上谕,针对两浙盐区,严行裁革地方官原有盐店陋规[12](卷467)。
道光帝之所以转变此前默许盐务陋规存在的态度,系因国库空虚成为清廷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是由于鸦片战争、道光末年水旱频发等造成巨额的非常规开支;二是由于盐课、地丁银等收入常年短缺,其中盐课额定每年征收750万两,但因商力疲乏,实际仅能征收500万两。故道光帝裁减盐商呈交地方政府的陋规支出,虽以“恤商”为名,却并非基于提高盐商利润的考量,而是意图“裕课”。更为明显的是,道光帝所关注的裁减陋规全部围绕盐规展开,对其余类型陋规如何处理只字未提。由此可见,此次裁革陋规行动并不以荡涤官场习气为使命,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发生了御史杨彤如参奏王兆琛复设盐务陋规一事。河东盐区虽然存在课银征收问题,甚至不得不减征4万两税银,但相较别省盐区动辄每年拖欠数十万两,问题并不严重,并非是道光帝盐务整顿计划中的重点,故道光帝在派遣钦差裁革盐规时未将山西列入。但王兆琛复设陋规情节亦引起道光帝的重视。第一,就山西一省而言,杨彤如参奏王兆琛“不顾商课”,切中要害。在河东盐商经营亏损、财力拮据的情况下,陋规势必占用盐商有限的经费,与盐课形成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前任巡抚吴其濬裁革陋规以充抵缺课,如今王兆琛却复设陋规,以清廷立场论,所复设的陋规理应作为盐课呈缴,故王兆琛因此受到惩戒亦在所难免。第二,就该事件的广泛意义而言,其时钦差赴地方裁革盐规刚刚结束,此案的发生暴露出被裁陋规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可以说,严查王兆琛一案既可起到惩一儆百之功效,又不会对全国范围内盐课征收的推进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同时,道光帝派遣钦差、提京会审及最终将王兆琛革职遣戍的种种举措即有扩大案件影响,警示官吏复设陋规后果严重的作用,而其最终目的仍在于保证盐课收入。
其次,道光帝对王兆琛案及钦差所调查的盐务陋规案的态度,反映出其在对待陋规问题上的无奈与困境。
其一,是对督抚收受陋规现象的承认。即位之初力求有所作为的道光帝曾试图对陋规进行清查,将“应存者存,应革者革”,但因遭到官僚群体近乎一致的反对而不了了之。曾小萍认为此事标志着依附于陋规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再次成为清代官僚体制的特征[1](282),但细察上谕则会发现,彼时的道光帝仅认为陋规问题主要集中在养廉银较少的府厅州县官,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俸廉优厚,“尚敷公用”,收受陋规情况并不严重[12](卷4),故此次陋规清查的失败,仅意味着道光帝对府厅州县官收取陋规的默许。但至迟在道光末年,督抚养廉银不敷、依靠陋规维持公务的普遍现状亦得到道光帝事实上的承认。如道光帝在褒扬吴其濬裁革盐规为廉洁时,并未追问历任巡抚收受陋规之事,可见其已接受山西巡抚收取陋规用于公务的事实。再如,在山东巡抚陋规案件中,道光帝认可了钦差大臣保留巡抚公费陋规的意见[30]。种种迹象皆表明,至道光末年,“非正式经费体系”在地方官府中全面渗透,已由基层州县官蔓延至督抚大员,亦表明道光帝对陋规防线的进一步后退。
其二,是对陋规管控的无效。前文已论及道光帝对地方官员收受陋规的默许态度,但此种默许具体来说仅限于公费类陋规。从道光帝处理王兆琛等陋规案可以发现,道光帝将地方官吏收受的陋规分为两类,一类为津贴类陋规,另一类为公费类陋规,尽管其试图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管控陋规,然而却未能奏效。所谓津贴类陋规,主要包括下属、盐商等给官员的程仪、节寿陋规,给书吏和衙役的朱费、贴差等。这些陋规的特点是均属于官吏个人,尽管其用途可能仍为公务。对此,道光帝秉持明确的禁止态度。在王兆琛案中,虽然王兆琛辩称收取节规系为补充办公经费,但道光帝仍将其遣戍,且辅以“贪鄙营私”等训斥。在山东陋规案中,数位巡抚之所以被定罪,并被道光帝斥责“卑鄙贪婪”,亦因所收程仪陋规“究非公费可比”[12](卷462)。道光帝将官吏收受津贴陋规均定性为贪婪。但其困境却在于,清廷在未能给官吏提供足够薪资的情况下,又将诸多公务开支,如督抚用于幕友之束脩、文报递送之费用等归入个人支出部分,因此对收受津贴陋规的道德贬斥与全盘否定并未能掩盖津贴类陋规存在的某种合理性。
至于公费类陋规,一方面,其款项归入衙门公库,用于公务的账目比较清晰。如山东巡抚的盐务公费陋规用途包括为盐务缉私而雇佣的弁兵盘川口粮,鸦片战争后增添的巡洋弁兵的薪资等,故而道光帝表面上对此表示允准,以展现体谅外官经费支绌的姿态。但另一方面,道光帝通过惩治王兆琛、派遣钦差裁革津贴类陋规等方式向地方官员传达出对盐规影响课税的不满,给予相关官员以行动压力。道光帝的用意得到了与王兆琛案直接相关的山东、山西两省巡抚看似有效的回应。在山东,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巡抚徐泽醇上奏表示,为“顾正课”,裁减全省各处衙门盐务公费陋规5.5万余两[31]。在山西,翌年九月,巡抚兆那苏图奏报整顿河东盐政以求裕课之策,将巡抚衙门中所剩盐规“全裁净尽”,并将山西省内各衙门中的盐务公费陋规大幅裁革,共计10余万两[32]。
尽管地方大员表现出裁减陋规的积极姿态,王兆琛案后亦未出现惊动中枢的复设盐规案件,但事实上,不论是津贴类抑或是公务类陋规,其存在的土壤并未改变,地方官府依旧受困于办公经费来源不足的现状,造成收取陋规的客观需要。盐商受地方官管束,亦难免因受制于人不得不呈送陋规。故而,当咸丰初年新一轮钦差前往山西调查盐务时,发现盐规早已如故[33](353)。从更广泛的层面看,由于窥破道光帝整顿陋规的实质在于获取盐课,地方官并未因王兆琛案产生儆惧之心。甚至就在当年年末,曾见证王兆琛家产被查抄的山东官员还上演了争抢署理一陋规丰厚官缺的丑剧[22](88-89)。咸丰帝践祚,以陋规泛滥等为表征的“吏治日坏”依旧被视作“时弊”,亟待解决[34](卷6)。
(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借王兆琛案的势力扩张
由王兆琛案引发的官场职位变动中有两位受益者,钦差陈孚恩因审案得力,归京后由刑部侍郎升任刑部尚书,山西布政使兆那苏图因王兆琛被遣戍得以补授巡抚空缺。值得注意的是,结合陈孚恩、兆那苏图的官场背景,并联系此间被派往地方整顿盐务的仓场侍郎季芝昌的升迁重用,隐然可见重臣穆彰阿势力的悄然扩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朝政深陷困境之势。
穆彰阿(1783—1856),字子朴,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历任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等,道光八年授军机大臣,十七年擢首席军机大臣,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为道光朝中后期最受道光帝倚重的大臣。穆彰阿之“门生故吏遍于中外”,其喜好培植势力,不吝利用对道光帝决策的影响力与自身权势来给予门生故吏、政治同盟者以仕途上的便利。是以道光朝中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清廷出现一批追随、迎合穆彰阿的官员,并因数量之众、影响之大而被冠以“穆党”之称[35]。
审理王兆琛案的钦差陈孚恩即为“穆党”重要成员。陈孚恩(?—1866),字子鹤,其虽科名不彰,仅为拔贡出身,然却凭借穆彰阿的“宠任”,迅速由军机章京升任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要职,并被援引入军机处[36]。王兆琛被参后,身为刑部侍郎的陈孚恩被派赴山西调查此事,可谓官场一重要机遇,按照道光朝惯例,钦差审案得力,往往能获得升迁。果不其然,陈孚恩因查实王兆琛复设陋规,回京不久即署理刑部尚书,旋实授[37](171)。与穆彰阿声气相通的陈孚恩在官场地位的提升,亦意味着穆彰阿势力的进一步膨胀。
此际,同样因出差获得升迁重用的还有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季芝昌。季芝昌(1791—1861),字云书,道光十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穆彰阿刊刻文集时,季芝昌作为门生代表为该书作跋,盛赞尊师“光辅圣主”之功绩,流露出与穆彰阿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38]。二十八年十一月至次年七月,官职并不十分显赫的仓场侍郎季芝昌作为钦差,先后随同满洲亲贵大臣定郡王载铨和大学士耆英前往直隶、浙江查办盐务等事,获得罕见的政治机遇,并得到道光帝垂青,于二十九年九月入值军机处,随后又被授为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此前,军机老臣潘世恩因不满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态度与排挤林则徐的行径而与之关系不洽,另一位军机大臣王鼎更为此愤而自缢身亡[39]。随着季芝昌的入枢、陈孚恩在军机大臣中排位的上升,深感孤立无援的潘世恩终以年老为由主动乞休,军机大臣中势力对比向更有利于穆彰阿的一方倾斜。在地方,琦善作为与穆彰阿交好的一方大员,其在道光末年得以由被朝廷问以重责的罪臣迅速恢复政治地位,与穆彰阿的“幕后指使、精心策划分不开”[40]。可见,“穆党”利益集团对朝廷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回到王兆琛案,该案获益者除陈孚恩外,还有由山西布政使升任巡抚的兆那苏图。囿于史料有限,兆那苏图的历史形象较为模糊,此前研究亦罕有关注,但经过梳理后,仍可发现其与穆彰阿关系密切的诸多迹象。兆那苏图(1799—1852),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朝名臣阿里衮之后,袭封一等子爵。道光三年,兆那苏图以荫生身份任工部员外郎[41]。六年,穆彰阿出任工部尚书。在此后长达数年的上下级关系中,公务往来为二人频繁接触提供可能。此外,兆那苏图出身勋贵,久居京师,基于人情交际,亦可能与同为满人的穆彰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穆彰阿还曾对兆那苏图有提携之助。清制,部院长官在三年一次的“京察”中评定司官优劣,被保列一等者有机会升迁、外放。道光十一年,穆彰阿将兆那苏图保列一等,成为兆那苏图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其在当年四月升补工部郎中,随后外放知府。在京察一等者概与堂官缔结厚谊的风气下,于兆那苏图而言,其对穆彰阿“心感保举之力”乃人之常情,更或间有“以为攀援上进”的考量[42],于穆彰阿而言,延揽如兆那苏图等后进亦为其所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兆那苏图因丁忧暂停升转三年,然其升迁却远较一般人为速,三年之中连跨三级:二十五年六月实授陕西陕安道,二十六年十月,升直隶按察使,后改任福建按察使,二十八年九月升山西布政使[37](899)。如此顺遂的官场境遇不免令人联想其在中枢内有力奥援的从旁协助。
王兆琛的突然获谴,为兆那苏图提供了晋升的可能,但相比于升任按察使、布政使时的平顺,其升任巡抚的过程则显得一波三折。在王兆琛被革职拿问后,道光帝先命季芝昌为山西巡抚,不久又决定将季留于中枢,改命直隶布政使龚裕担任山西巡抚,近在山西省府的兆那苏图却两次皆未能获得升迁[12](卷471)。由此看来,兆那苏图并非道光帝最为属意的巡抚人选。道光帝升迁地方官时多秉持稳扎稳打原则[28](120),但兆那苏图资历尚浅,其在王兆琛案发时仅担任布政使数月,尚缺乏历练。然而,龚裕抵任不足一月,情况再次出现变化,二十九年十一月,道光帝将龚裕调往湖北,兆那苏图终得晋升巡抚[12](卷474)。
兆那苏图官至山西巡抚是否有穆彰阿的背后运作,依据目前史料还不得而知。但颇为微妙的是,随着咸丰帝即位、穆彰阿失势,陈孚恩、季芝昌与兆那苏图的官场境遇亦急转直下。咸丰帝因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态度,及其借助集团势力打压主战派的行径深为不满,登基未久就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34](卷20)。深感政治风向突变的陈孚恩不安于位,辞官回籍[36]。季芝昌则于咸丰元年被排挤出中枢,远调为闽浙总督,一年后以病为由主动奏请开缺[43]。而兆那苏图先是被咸丰帝借故施以降级留任处分[34](卷28),又被痛斥“朕闻汝好与朝臣交往,甚属卑鄙”[44],复被受命于咸丰帝的钦差大臣暗中调查与地方官“能否和衷”及是否有“徇情容隐”属下之事[33](347)。咸丰帝对兆那苏图的嫌隙,可见一斑。种种后续变故或可从侧面反映出穆彰阿与兆那苏图之间的关联。面对咸丰帝的不断责难,兆那苏图在“深知感懼”的不安状态中很快于咸丰二年因病去世[44]。
王兆琛案所涉的官员升擢仅是诸多与穆彰阿有关的人事变动的一例。平心而论,穆彰阿有为朝廷慧眼识才的功劳,其所赏识的曾国藩、骆秉章等不负所望,成长为一代名臣。但这种围绕重臣形成的利益集团,及其势力的不断扩张,又是造成道光末年朝政陷入困局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穆彰阿亲近的门生故旧拥有顺遂的仕途、更多的立功表现机会,如曾国藩以“十年七迁”的速度超擢晋升[45],何桂清以17岁的少年之龄获任乡试考官[46],而与穆彰阿政治立场相悖的官员多受排挤、压制[47],鸦片战争期间,坚决主战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湖广总督周天爵等人遭革职的背后,皆有穆彰阿的身影参与其中[48-49]。这样的现实无疑给众人以直观刺激,挫辱了官风士气。曾协助林则徐开展禁烟活动的钱宝琛即因见林受重处而无意仕进,托病回籍终老[50]。道光二十五年,一贯抨击对外议和主张的魏源因不愿依附穆彰阿而在压力之下不得已辞别师友,离京外任[51]。
另一方面,穆彰阿善于迎合上意,见道光帝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52],遂指示众多追随者,此类事务“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53],由此更加剧了官场中粉饰太平的不良风气。曾国藩甚至为受制于此种政治氛围,无法奏陈时弊而深感苦闷[27](176)。广西巡抚郑祖琛则因此前受穆彰阿“援引迁擢”而听从其“风示意旨”,屡屡隐瞒地方动乱消息,直至金田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是以咸丰年间,时人反思道光末年社会矛盾之愈演愈烈,即认为此与穆彰阿势力扩张对朝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无关联[53]。
四、结语
作为道光朝仅有的一起封疆大吏因陋规被革职遣戍的重案,王兆琛案沾染着浓厚的时代共性色彩,为管窥道光朝陋规实态的难得案例,而其浮出水面的特殊之处又揭示了道光帝将裁革陋规作为应对财政危机之手段,以维护其统治的本质。
从案情看,王兆琛复设陋规与其养廉银被扣偿此前任职的因公亏空,故难以维持现任官职所需办公费用直接相关。雍正帝创设养廉银以扭转低薪制下地方官员缺少家用、无经费办公的局面,但清廷采用按年分摊养廉银的方式令官员赔缴被查出的因公亏空却极易引发连带效应,影响官员在当前职位中的表现,反映出清王朝在制度设计上顾此失彼、缺乏整体统筹的弊病。如王兆琛挪用库款用于公务、造成亏空已是当时官场的常见现象。乾隆朝后期以降,由于清廷未能依据物价上涨相应提高官员的养廉银标准,甚至还以河工、军需为由扣除官员养廉津贴填补财政缺口,地方官不得不挹彼注兹,挪用库款暂时应付公务开支。弥补所亏库款遂成为陋规死灰复燃、养廉银制度逐渐失效的重要原因。普遍违例的背后是清廷固守陈规、政策调整滞后等制度因素使然。
仰赖陋规维持公务开支的现实演化为对同僚收支困境的同理之心,道光末年地方官员早已普遍秉持“不宜轻裁陋规”的行事规则,形成官僚集团内部一套自我保护机制。如此行事显然有悖于正统定义的廉洁作风,构成道光帝深恶痛绝的所谓“外官习气”。道光帝试图将吴其濬树立为打破陋规潜规则的廉洁榜样,却只能刻意回避吴其濬此举的真实用意与具体情境,足见其在陋规蔓延风气下试图树立典型、引导官风的无奈。退而言之,即便不收陋规的观念仍然吸引着有仕途进取之心的官员以此为目标,但或靠借贷,或靠家中接济勉强维系的廉洁已然失去存在基础与约束、规范官员的普遍意义。
从清廷处理案件的方式看,王兆琛案实则是一场服务于财政目的的吏治整顿。在国库紧张且山西盐课未能足额征收的背景下,王兆琛复设陋规挤占了盐商本已拮据的支付能力中呈缴课税的部分,有损清廷财税利益,因此遭到重惩。经济动机的分析路径也可解释道光帝为何在同期并未对其他类型陋规有所整顿,而即便是裁革盐规,也只是针对盐课拖欠严重地区进行。可见,道光帝晚年开展的整顿陋规运动并没有澄清官场的决心,仅将此作为应对财政危机的权宜之计。道光帝的态度导引着地方官员回应的方式。一方面,经过王兆琛案与钦差裁革盐规的冲击,山西、山东等地巡抚已深深领会道光帝对盐课的重视,表现出积极裁革盐务陋规的姿态,并使盐税收入在账面上没有继续恶化,反映出专制皇权对地方税收攫取能力的刺激效用。另一方面,道光帝外张内弛的举措难以震慑更广泛地区的官员,种类繁多的陋规依然如故。
除此之外,王兆琛案前后所引发的人事变动亦值得深思。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亲信、门生,陈孚恩、兆那苏图与季芝昌的升迁重用,反映出人际网络对官员个体仕途的影响,私人关系或成为赢得政治资源与表现机会的捷径,折射出道光末年官场中缺乏政治信仰、以集团利益为先导的政治生态,更加深了道光末年朝政的困局。咸丰帝上台后对“穆党”势力的打压,则为晚清初期清帝与重臣间权力博弈的真实写照,而二者的分歧焦点在于对外战、和主张的差异,“夷务”与朝局之间的复杂纠葛初露端倪,外交作为影响清廷内部政治走向的新要素逐渐步入历史舞台中央。总之,当道光帝将王兆琛案当作惩贪倡廉成功案例宣扬之时,该案所暴露出的却是迈入近代之际的清王朝所面临的重重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