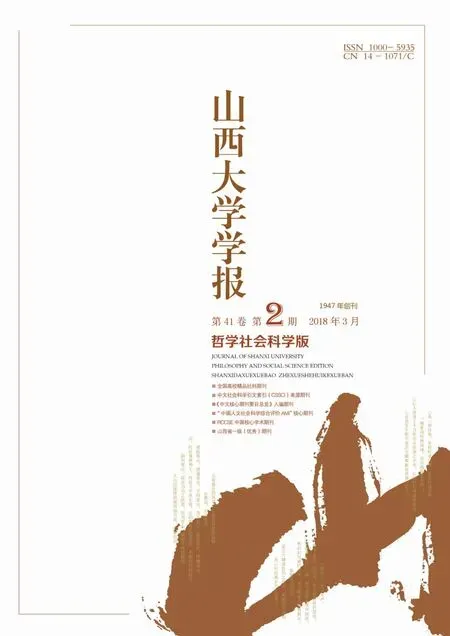古代中国舆论的发生及其内在精神
2018-01-31姜华
姜 华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1910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六),在读了三天前发布的“上谕”后,梁启超撰文议论时政,以相当篇幅论及舆论在立宪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舆论观如下:“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1]在此文中,他还区分了立宪舆论与专制舆论的不同:“专制政体之舆论为消极的服从;立宪政体之舆论为积极的发动”。同年,在一篇报刊叙例中,他再次谈及两种舆论的差异:“专制时代之舆论,不过立于辅助之地位,虽稍庞杂而不为害。立宪时代之舆论,常立于主动之地位,一有不当而影响直波及与国家耳。”[2]“多数人意见”,是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对舆论的界定,这其实是比较“现代”的说法。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舆论并非全然如此,而专制舆论“稍庞杂”且是“消极的服从”并“立于辅助之地位”,恐怕也并不能概括古代中国舆论之全貌。本文关注的问题如下:以谣言面目出现的民间舆论,何以发生,并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进而左右了帝国政治的运作?表现为“公舆论”与“私舆论”的少数人的意见(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舆论)是如何在帝国政治中发挥效力的?明知犯上的“逆龙鳞”之举——谏议,其制度及谏议官的地位在帝国政治中经历了何种变化,为何在地位急转直下且自身安危受到巨大威胁的情况下,谏议官仍能创发并携舆论之力,与最高统治者进行舆论博弈?从民间到庙堂,古代中国政治舆论的发生,其背后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政治精神是什么?本文尝试从辨析“舆论乃多数人的意见”的主流说法入手,从古代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出发,分析探讨越出“多数人之意见”藩篱的古代中国舆论的类型、发生原因及其内在精神。
一 “众寡之争”:何种公众,何种舆论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舆论一定是“多数人意见”,换言之,如果说少数人的观点或意见,即使“公表于众”,也不属舆论之范畴。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界的舆论观有很大影响,诸多学者均持此论。如果我们将舆论置于历史长河和国际视野中,其复杂性恐怕绝非“多数人意见”所能概括。若从“公众”多寡角度看,至少有以下不同的舆论观。
首先是“多数人意见”之舆论观。除任公先生持此种观点外,当代学人大都沿袭此说。学者刘建明在其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著作中就提到:“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3]后来,他对这一观点略有调整:“舆论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概念是指某种舆论而言,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的多数人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共同意见。广义上的概念是指社会上同时存在的多种意见,各种意见的总和或纷争称作舆论。人们多在狭义上使用舆论的概念,因为人们谈论舆论的存在常常是指社会中某种具体意见,剖析某种意见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指向或量化怎么样,以及有何影响,并不过多地分析多种意见的纷争状态。”[4]但大致仍持“多数人意见”之议。也就是说,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必须是“多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舆论观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对舆论的大致看法。
其次是“共同利益者的意见”。从西方学术界看,汉语语境中的舆论,对应的是两个英文词汇,即public和opinion。因此,要理解西方语境中的舆论意涵,首先要厘清public的含义。Vincent Price认为,“Public含义则较为丰富,既可以指‘易于进入的场所’,也可以指 ‘作为整体的公众’或‘有共同利益的一部分人’”[5]。以此观点,舆论即是“整体公众的意见”或“共同利益者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观点倾向于强调“共同利益”,并将其看作是联结公众的内在纽带,至于公众数量上的多寡,则并未言明。由此,我们既可以认为此种舆论观之公众是多数人意见,亦可将之看作是少数人意见。
再次是“共同见解者的意见”。在中国学者陈力丹看来,“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自在的对于外部社会有一定的共同知觉,或者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有相近看法的人群”;那么,相应的,舆论就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这种舆论观与上述第二种舆论观略有不同,即持有共同见解的公众,有表明公众对相关事务认识和看法之意,有可能但并非一定是“共同利益者”,也许仅仅是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评议者。
最后,“社会地位重要者之意见”。有西方学者认为,公众舆论是“一个被随意使用但远非精确或明晰的概念。”“公众舆论可以被定义为:由人口的某些重要部分所持有的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的一系列看法。”[6]“人口中的某些重要部分”,既可以是多数人,亦可以是少数人,只要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这些人居于社会重要地位,对于事态发展、事件走向有重要决定作用,其意见就应当看作舆论。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考察中西方舆论发展史,此种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概括了中外舆论发展的实际状况。
正如最后一种观点所呈现的,公众的含义较为丰富,舆论的意涵更是争议颇多。例如在舆论的性质上,第一和第四种观点就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舆论并非“纷争性”的意见,而后者恰恰认为舆论是关于“争议性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其实,涉及舆论,还存在不少差异性很大的观念。除上述四种不同观点外,沃尔特·李普曼认为,舆论就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7],至于他人是多是寡,他没有做出明确解说。而根据哈贝马斯的考证,追根溯源,在英文的思想语境中,“舆论一词的集体意义十分明显,以至于所有用来指涉其社会性质的定语都可以作为冗词省去不用”[8]。但是昭示公众含义的“集体”究竟何所指,性质如何,规模多大,也并未有详细说明。
具体到古代中国舆论,新闻史家朱传誉认为:“‘舆’是众,‘论’是言论,‘舆论’是‘公众的言论’。”[9]241此种界定简单明了,却也模糊不清。具体而言,公众何所指?言论又是何种言论?均未申明。林语堂先生舆论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新闻舆论史》有关舆论的探究,由于其立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其对于古代中国舆论的探讨,以“专制与反专制”为线索,征引不少案例,纵横古今,联结中外,阐释专制之害与舆论抗争之辉煌篇章。但对于舆论的总体特征,并没有明晰的阐释。[10]23尤为重要的,二者的研究对古代中国舆论的模式、发生及其内在精神均着墨不多,而这恰恰是本文试图努力探讨的。在本文作者看来,因特殊的帝国政治及其政治治理结构,上述四种舆论观在古代中国舆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事实上已经完全突破了“多数人意见”的藩篱,“众寡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尤其突出的是,舆论的“纷争状态”不仅在古代中国的舆论生态中大量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古代中国舆论的本真状态。同时也正是这种“纷争”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彰显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呈现出特有影响。
二 谣言与谏议:关系视野中的古代中国舆论
若从政治关系的角度对古代中国舆论作简要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君—民”、“君—臣”、“臣—臣”几组对应关系。“君—民”关系中的舆论,肇始于社会底层民众对帝国统治者的不满,表达了社会中占人口多数之群体的诉求与心声,可以说是“多数人意见”的呈现;“君—臣”之间的舆论战,则显然是“少数社会地位重要者之意见”的博弈与抗衡,其间体现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也将士大夫身上维护道统的士之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臣—臣”之间“公·私”舆论的争辩,以及介于“公、私”之间或“公、私”不甚分明的舆论争夺,又表现出古代中国士绅阶层的内在弊病。可以说,每一组关系的舆论,均凸显了帝制时代的政治舆论生态特质,“地位显赫者”在纷争舆论中的强势地位及其政治影响,以及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面临“多数人意见”之舆论时的强硬姿态、彷徨与无奈;地位卑微者的大多数,在身处绝境、高压之下的“冲冠之怒”和呐喊;庙堂之上,江湖之间,公卿士大夫于公于私的纵横议论,生动呈现了古代中国舆论的“纷争状态”。
(一) “君—臣”与“臣—臣”:谏议——“公舆论”与“私舆论”
古代中国,从保障政治体系良性运作和延长王朝寿命的愿望出发,历代统治者均设立与言事相关的职位。最早在周代时,已正式设立“保氏”一职,用以“掌谏王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谏大夫”之职,强化谏官的议政监督功能。西汉承秦制,东汉时改称“谏议大夫”。[11]在中国经典文献中,如《国语》《左传》中,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关于谏议的篇目。*如《国语》中的《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范蠡谏句践勿许吴成卒灭吴》,《左传》中的《臧僖伯谏观鱼》《宫之奇谏假道》《伍员谏许越平》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古代中国的谏议制度,对于王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匡正”作用,它之所以有一定成效,与其代表了社会舆论的呼声有一定关系。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谏议制度起起伏伏,官职设置也多有变化,总体而言,秦至宋,专设谏议制度,匹配相应官职,谏议常态化,亦对政治运作影响巨大。元之后,废谏议制度,不再设立专职谏官,但是谏议职能却一直保留下来,继续起到匡正时弊之作用。*赵映诚对古代中国谏议制度的存废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对于历代谏官的设立有详细说明。具体可参考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鉴于谏议制度与监察制度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明清两代,不设专门谏官,而作为监察责任者的御史在一定程度上曾承担谏议职能,宿志丕将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一同给予分析。可参考宿志丕:《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若从政治关系视角出发,古代中国谏官的谏议对象曾经历过一个从“人君”到“臣子”的转化,与之相应,谏议的关系,亦从“君—臣”转化为“臣—臣”。依照钱穆的观点,这种转化发生在宋代。宋之前,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谏官居于重要地位,主要是“补阙”帝王之疏误:“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叫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从这样的关系可以看出,皇帝、宰相、谏官,其实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作用,由于谏官人选由宰相决定,而古代谏官也大都不会因为谏议而遭杀身之祸,这是他们可以凭借或引领社会舆论而谏议朝政,进而影响帝国政治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宋代以前,谏官与御史是决然不同的职位,职责也差异明显:“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务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12]552北宋建立后,谏议制度得以微调,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设立谏院,而谏官也不再由宰相选任和节制,而是直接有皇帝选拔与任命,与之相应,谏官的谏议对象也不再是任命他们的“人君”,而是政府日常运作的“首脑”与“中枢”——宰相。由此往往导致时为同侪的大臣之间的相互攻讦:“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以转为宰相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上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12]554
这种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彰显了古代政治谏议活动中“公舆论”与“私舆论”的分野。依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分析,古代中国公之“古典”含义大致有二:其一,公共场所。如日本学者白川静就认为:“举行仪式的场所的平面图为公。公的初义为公宫。”[13]233这种理解,与欧洲近代早期对public的理解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公平,公正,平分。“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营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知之矣。”(《韩非子·五蠹篇》) “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说文解字》)这种“公”,也“由此产生与众人共同的共,与众人相通的通”[13]5。换句话说,这种“公”因为涉及“公平、公正、平分”,因此也就与国家和社会中共同体成员的所有利益关涉者有了联系。只是“公”的含义在后世不断演化,尤其是到了宋代,“原来归结为君主一己的政治道德性这一概念,一跃横向扩展为更普遍的、与普通人相关的(虽然实质是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内关个人内心世界、外关外界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13]11。尤其更为重要的,公私之关系,到明清之际,又有更为重大的变化,当时的诸多思想家(如李贽、顾炎武、吕坤、戴震等人)认为,“私”,也就是个人的顺应自然的“欲”,应该成为“公”必须要接纳和考虑的要素——“它必须是高一层次的‘公’:这个‘公’要内含‘私’,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私’,还要使民的‘私’,共同得到满足。”[13]23因此,在古代中国的舆论场域中,所谓“公舆论”,就是那些占据重要政治地位的官员士绅阶层,尤其是谏官们,阐发的事关国家、社会与共同体利益的言论;而“私舆论”则是与上述无关,仅仅关涉一己之利或小团体利益的言论。虽然“君—臣”之间的谏议并非全部都是“公”的范畴,而“臣—臣”之间的争论也未必全系“私”的领域,但总体而言,因帝国政治的特殊性,涉及皇帝的谏议与舆论,大多事关政治之“公”域,多与帝国政治及天下百姓相关;而臣子之间的争议,除了有些事务属于“公”域之外,很多的则属“私”域之争。后者恰如前文钱穆所言,当谏议的对象演变为宰相(或同僚)的时候,可以断定,相比以往“逆龙鳞”时的担忧(虽然谏官有“言之无罪”的免罪符,帝国政治中的运作,终究使其对帝王有敬畏之感),谏官在心理上更加放松,加之职责所在即是“言事”,因此,为个人利益或者吹毛求疵的事情屡有发生,而这些“言事”很多时候即属“私”域。无论“公舆论”,还是“私舆论”,虽然话语是从某位或者某些位士大夫口中说出,但是其观点却往往是某种社会观念(如古代伦理观)的反应,而这些观念往往又是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所持有的,只是更多的时候,是经谏官之口说出而已。
“公舆论”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例如明代著名的嘉靖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试图“废长立幼”,屡遭朝廷大臣的“公议”,虽然廷臣接二连三遭到贬斥甚至责罚,但数名大臣前仆后继,屡败屡战,在当时成为有明一代轰动朝野的“舆论”事件。又如同样发生在明代的“梃击案”“移宫案”,也是如此。*所谓“梃击案”,是泰昌帝朱常洛为太子时,有持木棒者闯入东宫,意图不轨,后虽经朝臣再三上疏议处,终草草收场;“移宫案”是指万历皇帝“遗孀”郑贵妃在老皇帝去世后仍不肯搬出乾清宫,而这于明制不符,朝臣再三疏议,闹得不可开交。具体可参阅温功义:《三案始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9月版。至于“私舆论”,在帝国政治中更是屡见不鲜。宋代的谏官从“纠绳天子”转向“纠绳宰相”后,宰相以及其他朝臣往往成为谏官及其利益群体为了达成“私利”“为谏而谏”的目标。王安石变法之际,就有谏官(程颢)攻击他谋一己之私,而事实上,作为“私舆论”代言者的程颢,恐怕也不是为“公”而言。宋代时,还有谏官因为宰相的侧室殴打婢女而上书要求其辞职,这种为言而言的“私议”竟也轰动一时,引人关注,实在是借“舆论”之势、行个人偏私的晦暗之举。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的“公”“私”舆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系“社会地位重要者”之少数人之舆论,但是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常常成为小报传布的重要“政治新闻”,并从帝国上层向社会下层广泛散布,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百姓的议论,又往往进一步演变成自下而上的“舆论压力”和谏官们的“舆论工具”,这种“舆论圈”也因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左右帝国政治的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
(二) “君—民”:作为舆论的谣言
林语堂先生在谈及作为古代中国舆论形态之一的歌谣时,提出因为政府的审查制度,公开的议政与反对政府的声音被压制。口耳相传的歌谣成为民间舆论议论时政、表达民声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此种表达民间舆论的歌谣在中国三千年不绝,先秦两汉之际尤其流行。在他看来,有时候歌谣常常“与中国人的迷信掺杂在一起,民众认为它有预言功能,扮演着神秘的角色”。[10]23这种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歌谣,在古代中国常表现为一种具有隐喻性质的“政治谣言”,它们在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屡屡出现,对于先秦及之后帝国时期的政治产生很大影响。
1.作为社会动员工具与情绪宣泄管道的政治谣言
秦帝国末年,暴政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最终酿成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其中陈胜、吴广的起义,最初即是以政治谣言的形式进行社会动员的,事实上在科学尚未昌明、迷信和民间信仰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政治谣言的筹划、加工与传播,为其起事助力不小。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王。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史记·陈涉世家》)
无论是谎称扶苏、项燕的再生,还是将丹书帛置入鱼腹,抑或是佯装狐仙呜呼,都是陈胜等人精心设计的政治谣言,目的就是借此动员民众群起抵抗暴秦。这种以社会动员为旨归的政治谣言之所以有效,和古代中国长期存在的“民间信仰”是分不开的(将在下文舆论发生之原因中详细分析)。而留意中国史,这样的政治谣言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王朝鼎革之际,更是层出不穷,最终大都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强有力的舆论动员力量。
即使帝国处于安定时期,王朝政治生活中出现重大事项,平民百姓对当政者的处置不满,而又没有政治权力予以干涉,便会制造谣言宣泄情绪,并试图以此匡正时弊。朱传誉在论及宋代小报时,曾征引两则轰动朝野的小报新闻:其一是北宋徽宗时,社会上流传一道“诏书”,内称:原宰相蔡京偏听偏信,行事狡诈,阿谀奉承,引起普天之下百姓议论。尤其是在其任职期间,边疆不宁,百姓失业,忠良臣子受到贬抑,无良小人获得擢升。蔡京恶行,我没有察觉,实在是我的过错。从现在起,凡是发现蔡京及其朋党的,都可将其削除。*朱氏引用的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七原文:“近传伪诏曰‘前宰相蔡京,目不明而疆视,耳不聪而疆听,公行狡诈,行迹谄謏,内外不仁,上下无检,所以起天下之议。四夷凶顽,百姓失业,远窜忠良之臣,外擢暗昧之流,不查所为,朕之过也。今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削除。”可参见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77页。事后证明,这是一则不折不扣的“伪诏”。但“伪诏”通过小报而广为流传,则反映出在帝国政治生活中,民间对皇帝重用奸佞之臣的极大不满,但同时又囿于对帝国政治无能为力,只好通过“伪诏”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而这件事,最终惊动徽宗皇帝,迫使他不得不下诏明示上述所谓“诏书”系伪诏,并表示要抓捕造谣惑众的伪诏制作者。其二是南宋高宗时期,百姓对于朝廷对辽和议极为不满,于是便将具体执行和议事项的秦桧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伪造皇帝贬斥秦桧,征用主战派张浚的诏书。[9]76在帝国政治生活中,言论往往遭遇严密控制,传播渠道亦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因此,古代中国的民间舆论少有宣泄渠道,当对重要政治事件不满且无能为力而皇帝的作为又有负民意时,谣言的一再出现,也就毫不奇怪。
2.“舆论”与“反舆论”:庙堂与民间的“舆论战”
如上述第二点所言,在古代中国的舆论场中,皇帝与民间争抢舆论制高点并借此达至各自政治目标的活动绵延不断,构成了古代中国“舆论”与“反舆论”的奇特图景。事实上,古代中国的皇帝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常常通过诏书、上谕宣示天下,并凭借官僚系统的支持,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舆论生产”与“舆论引导”的核心力量。而此种“皇帝舆论”,恰恰是“寡人舆论”,它之所以能够发酵、扩散,与皇帝的特殊政治地位是紧密相关的。
“皇帝舆论”,印证了前述政治学者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对舆论本质的深刻识见,所谓“社会中重要部分之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中国,这样的舆论纷争,明清之际尤为突出。其中,最为典型同时对当时政治影响最大者,非雍正时期“吕留良、曾静案”莫属。事起湖南人曾静派其门生投书岳钟琪请其反清。待岳钟琪捕获曾静诸人并呈报雍正后,皇帝发现,民间早已盛传其“得位不正”、“弑父杀兄”、“恶迹昭彰”,还有吕留良、曾静这样的读书人进而质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对于此流播甚广的民间舆论,雍正的“反舆论”之策即是他的“出奇料理”——严惩吕留良及其后人,“宽释”曾静。在他看来,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忽号为明之遗民”,质疑清朝统治,污蔑圣祖康熙,实在是“千古悖逆反复之人”,“自是著邪书立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而曾静仅仅是传播谣言的无知小人而已,是“误听流言”。[14]事实上,这未必是雍正的真实想法,留下曾静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争夺舆论场的主导地位,这就引出另一个“出奇料理”——将皇帝本人处理“吕留良、曾静案”时期的多道上谕、审问曾静的案件记录以及曾静的悔过书《归仁说》一并整理成册,定名《大义觉迷录》于1730年刊布全国,令所有读书人人手一册,必须诵读*关于《大义觉迷录》,可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关于《大义觉迷录》成书、刊布、遭禁之经过,可参考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温洽溢、吴家恒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两项“出奇料理”的目的,即是控制政治流言,扭转对自己不利的民间舆论。其实,除此之外,雍正在位还大幅度删改了《古今图书集成》,整理刊印了《康熙实录》,颁布《朋党论》*可参阅房兆楹为《清代名人传略》撰写的“胤禛”词条。房兆楹认为,雍正“是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他极力控制臣民的思想,他重新颁布其父下达的通称‘圣谕’的十六条道德箴言,并加上自己的长篇说明”。参见〔美〕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0页。我们有理由相信,雍正是一位有野心并在政治和文化上均非常自信的帝王,这样的自我期许使得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下帝王之尊,以“出奇料理”的方式,与一个来自湖南乡下籍籍无名的读书人论辩,以期通过论辩并刊布书籍的形式,扭转全国上下对其不利的暗流涌动的舆论风潮。。这些大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试图扭转舆论的重要举措。
其实皇帝与民间的“舆论战”贯穿了帝国时代的始终。早在公元前的秦帝国时代,嬴政执政中后期,即花费大量精力应对来自民间的“舆论攻势”。秦统一六国后,以严刑峻法制御天下,苛政引来不满,民间关于秦朝亡国与始皇驾崩的传闻时有传出。如公元前211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事实上,秦始皇所做的,不仅仅是销石诛人,在他看来,石刻反映的是社会舆论对秦帝国以及始皇本人的不认可,他所要做的也是要扭转这种不利的舆论局面。自公元前219年开始,秦始皇多次出巡,登山封禅,刻石颂德。泰山、芝罘、琅琊、碣石、会稽,一路巡游,留下石刻一路。这些石刻,无不以华美辞藻颂扬秦皇的文治武功与秦帝国传之久远的梦想。例如,登琅琊山的石刻中:“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同文。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又如上会稽的石刻中:“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言论,生动呈现了雄韬大略的秦始皇与民间争夺“舆论制高点”时的种种努力,也反映出古代中国的舆论“众寡之间”为民心所向而竞争的激烈状态。
恰如马基雅维利所言,“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15]这虽然是谈西方君主,但涉及帝国政治,实在是大同小异。雍正对于个人声誉以及个人道德品质的看重,在其处理“吕留良、曾静案”的过程中极为引人注目。他在颁布的多道圣谕中,从儒家经典出发,力争清朝定鼎中原的合天意以及自身的道德感。秦始皇的“石刻引导舆论”之举,也是为了彰显秦帝国的“合法性”、个人对国家、百姓的功业。在古代中国,这些是普天之下从官方到民间都普遍看重的,而这些上谕以及相关书籍的刊布,以及遍布宇内的石刻,都是为了扭转统治者在政治舆论空间的不利地位并试图能够左右舆论进而占领舆论制高点。
三 “天”、“道”,“民间信仰”:古代中国舆论发生之内在精神
古代中国舆论的主体,既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所谓“一人言而天下动”),也有位居政治权力上层的士大夫精英阶层(所谓“居于社会重要地位者之少数”),更有位于社会底层之广大普通民众(所谓“数量庞大的农、工、商阶层”)。三者在帝国政治事务中的言行,很多时候都能引发广泛的社会舆论,进而对帝国政治的运作甚至是王朝的生死存亡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在强大的帝国政治统治秩序面前,士大夫与普通民众的舆论究竟何以产生并发挥作用,这无疑与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密切相关。
(一)知识精英阶层——“天”“道”观念与舆论
1.“少数的舆论”—— “士”阶层的诞生与精英舆论
在帝国政治体系中,精英舆论的发生与“士”阶层的形成密不可分。依照余英时的分析,古代中国士阶层的形成,经历了“学在王官”—“稷下学宫”(“碣石宫”)—“博士制度”的演变。春秋之前,作为一个阶层的“士”,属于贵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低级之贵族”(顾颉刚语),“地位在大夫与庶人之间”,从人员构成上讲,士阶层在春秋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因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居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的总体人数大为增加。[16]9-10从舆论(言论)的角度讲,“学在王官”阶段的“士阶层”,更多的是立足于统治阶层内部,大多数情况下承担的是一种建言献策的角色。恰如余英时所言,当时的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恃以批评政治、抗理王侯”。[16]88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各国国君对知识人尤其是知识领袖的重视、争夺与礼遇则是前所未见,尤其重要的在于身份的变化——这些被各国国君或忠臣“供养”在学宫的知识人,被称为“稷下先生”,虽然饮食源自国家,但却不属于帝国统治阶层,与国君也属“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春秋时期的帝国政治中,“稷下先生”的言论(或反映社会呼声的舆论),常常能够放言无忌,成为先秦政治中一种强有力的制衡机制。而自秦汉时起,统一的帝国,为统治秩序考虑,一改此前士阶层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做法,将士阶层纳入帝国体系,这就是“博士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的设立,将古代中国的知识人纳入到政治系统中,他们如“学在王官”的士阶层,有了职务有了薪资,成为帝国统治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又不像他们的前辈“无职有言”,而是“有职亦有言”。我们知道,在秦汉已降的帝国时代,最高统治者对士大夫的态度起起伏伏,宽待者有,严苛者亦不乏其例。但是士大夫的言责却未受很大影响,这无疑与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知识人的传统密不可分。
2.“天”、“帝”观念与“天”、“人”关系
公元前1046年,西周武王姬发率大军与殷朝军队决战于牧野。两军交战前,西周军队发布一则誓师辞,其中有一句:“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尚书·牧誓》)在殷商及以前的古代中国社会,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大都有对“天”的极笃诚的信仰——在他们的心目中,“天”就像宇宙中存在着的人格之神,俯视着宇宙空间、人间万物,对政治运作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护佑有道之君,贬斥甚至是惩罚无道之王。这也是姬发的誓师辞所力图表明的。清段玉裁认为:“天,巅也。……凡言元始也。……巅者,人之顶也。”(《说文解字注》)也即是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代表万物之始,远远高于人类自身,是万物的主宰。葛兆光认为:“在卜辞中,殷商人不仅已经把神秘力量神格化,而且已经把它们大体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神的系谱。在这个系谱中,第一个重要的当然是殷商时代神灵世界的最高位‘帝’”。“帝的词源意义是生育万物,很可能以‘帝’这个字来表示生育万物的‘天’,是很早就有了的。”[17]钱穆则以为:“根据殷商甲骨文,当时人已有‘上帝’之观念。周人‘他们自认为他们代表着上帝意旨而统治此世’,但认为‘上帝并不始终眷顾一部族,使其常为下界统治人’。”[18]如此看来,在远古时期,“天”与“帝”本是差不多一体的观念,在当事人心目中他们都是万物之主宰。*余英时认为,“上帝”概念的出现要早于“天”:“一般的看法,周代在宗教上的最大特色是‘天’的出现和流行,而殷代则只有‘上帝’,尚无‘天’的概念。”余英时的看法是“‘天’的观念至少在殷代晚期已出现,但‘周因于殷礼’,扩大了‘天’的应用”。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19]178-179也就是说,作为世俗之国的人的命运,是受到万物主宰的“天”或“帝”的统治与控制的。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天”与“人”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上帝与信众之间的关系曾经隔着教士阶层作为中介,后经宗教改革,新教产生,信众与上帝可以直接对话。在古代中国,天人之间的关系似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殷商时期,承接天命或者受到上帝眷顾的是人君、天子。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地天通”,天地间的交通被斩断了,天子成为天与人类社会沟通的唯一渠道,而巫(女)觋(男)则常常受天子委托,代表天子与天交通。在当时的情况下,士阶层并不能与天直接交通,因此其权威性也就不足,而其言其论也不足以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产生足够的影响。余英时认为,重要的转折发生在“轴心突破”的春秋战国时代,此时“‘天’和‘人’的涵义都同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天’已不再是先王先公‘在帝左右’的天庭(换句话说,不再是鬼神的世界),而指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当时各学派都称之为‘道’”。[19]182而在古代中国的士阶层看来,这种“道”即是宇宙万物运作的规律,是他们内在的精神追求,而得道者往往就是把握了宇宙万物与世间社会运转规律的人。古代中国的士阶层也大都以追求“道”、维护“道”为人生的终极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先秦诸子和“稷下先生”们看来如此,即使日后成为“体制内”知识人的士大夫看来亦如此。
紧接着就又引出一个重要论题,即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尤其是秦汉及以后的士大夫阶层,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不少人均将个人荣辱得失置身度外,对于帝国政治往往能够畅所欲言,并常常因此引为一时风尚,其原因究竟何在?这就涉及作为古代舆论主体的士阶层对“道统”的自信与自任的精神。在这些古代士大夫来看,他们的“道统”代表了宇宙人间的运转规律,体现了“天”的意志,相比于历代帝王代表的“政统”,它们更具权威性。恰如余英时所言:“‘士’在危急关头往往表现出一种承担意识,而此意识的后面则必有‘天’的信仰为之支撑”,“君子见‘道’则为‘天’之见证;君子的使命感即是‘天’降的大任;对于统治者必须时予警告,以免他们违逆‘天命’,招致自身的毁灭”。[19]56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敢于发声、乐于倡导引领舆论之言,与这种捍卫道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市井走卒阶层——民间信仰与舆论
虽然孔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他对于殷商时代的鬼神世界已经产生了怀疑(但也未直接否认),而当时以及后世的不少思想家还一度生发出无神无鬼的思想,但对于古代中国的普通下层百姓而言(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鬼神世界离他们并未远去。殷商时代的鬼神信仰,并没有伴随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轴心突破”而中断,相反,这恰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深深根植于古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并成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依靠力量。
在古代的舆论生态中,“征兆”与民间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鲁惟一看来,征兆“是特意用于”某些“怪异事件及其预兆的。它被用来指称那些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隐藏在自然之后的信息”。“对于这些奇怪而又剧烈的事件,人们有着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把它们看成是天的有意识的行为。……有些人把它们用作支持某个政治权威或批评某个国君的手段……某些情况下,自然界所发生的奇异现象则成了某种整治措施的理由”。[20]事实上,在古代中国,诸多情况下,征兆常常成为左右上至朝野下至民间的“舆论利器”——统治者对此极为重视,二十四史中多有记载的天象异动,*如《元史·本纪·顺帝》中,即有大量篇幅,描述相关内容。常常引起统治者的惊慌,以为是统治失当的表现,民间舆论也会因之而动,议论皇帝的无道与失道。而市井走卒对此更是多有信从,这种对征兆的相信,在政治活动中,常常能释放出巨大的舆论动员力量。前述陈胜吴广起义中的人为异象以及秦始皇时代天降巨石,都被认为是代表了上天的某种意志,引发谣言的广泛传播,进而赢得很多普通民众的跟从。
常乃惪曾指出,神权衰落后,“聪明的贵族虽然不敢公开反抗当时普遍的神权政治,但却有人用和平的手段,慢慢改革神权的思想,一步一步引导迷信无礼的神意使之进于有条理的人事规范之内。”[21]通观古代中国民间对抗帝国统治的政治动员,大多采用了通过民间信仰进行舆论造势的方法,而这些民间舆论也恰恰因为有了民间信仰的存在,而迅速扩散。通过对古代中国政治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对神的崇拜与敬畏,在士大夫阶层也并未断绝,它们也会像对平民百姓发生作用一样对精英阶层继续发挥效力。精英阶层的舆论动力,既来自于道统,同时神鬼信仰也在其中起作用。
四 结语
古代中国舆论极为复杂,远远不是“多数人之意见”这样一个对舆论的现代定义所能够涵盖的。在古代中国舆论中,存在“君—民”、“君—臣”、“臣—臣”三组舆论关系。而这三组舆论关系所体现的舆论的发生、形态、社会影响,也不是“多数人之意见”所能涵括的。这其中,既有皇帝携“天子”之尊,对社会舆论的强力压制与严厉管控,也有臣民依照各自诉求,对政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制造”与借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君—民”“君—臣”之间的舆论争夺,常常会涉及“公舆论”“私舆论”的分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古代中国的政治运作。与之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舆论生产者,很多时候,即使是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危险(无论是士大夫阶层的“逆上”,还是民间百姓的“造反”),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誓死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行为,这实在和古代中国的内在精神密不可分:正是有了“天人之际”捍卫“天道”的精神支撑,士大夫精英才能够顺应内心,不畏皇权之威,勇于承担舆论职责;正是有了民间信仰,普通的百姓才发自内心地相信政治谣言,跟从政治运动的筹划者;而作为民众中一员的运动筹划者,很大程度上不仅依靠作为舆论的政治谣言起事,其自身很多情况下也是民间信仰的崇信者。从这个角度讲,古代中国舆论的发生及其表现形态,和古代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政治、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9:145-146.
[2]梁启超.《国风报》叙例[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11.
[3]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1.
[4]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3.
[5]Vincent Price.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M].邵志择,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1.
[6]〔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617-618.
[7]〔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 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08.
[9]朱传誉.宋代新闻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10]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刘小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97-104.
[12]钱 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52.
[13]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M].郑 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4]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905-908.
[1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6-107,85.
[1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91.
[18]钱 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4-45.
[19]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20]鲁惟一.汉代的神话、信仰和理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1.
[21]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