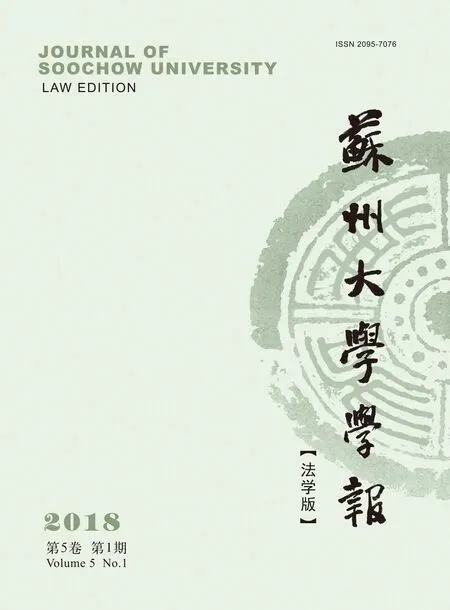法学教授为什么应当学术写作?*
2018-01-31耶鲁卡米萨
[美]耶鲁·卡米萨 著 刘 磊* 译
诚如密歇根大学同事詹姆斯·博伊德·怀特教授的洞见:“当教授们在打字机或电脑前撰写论著时,他们看似只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教授们其实是在做非常迥异之事。而且,我认为意识到这些不同之处以及正确估量其价值非常重要,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同行。”①James Boyd White,Why l Write,53 Washington & Lee Law Review(1996),pp.1021-1022.
我们教授们的论著不仅仅在内容上迥异,在“为谁而写”上也相当不同。我与怀特教授不同②参见前注,第1035页。詹姆斯教授提到:“我不会盲从主流的写法,即专业学者使用专业的写作方法,我的写作方法是从人到人、从心灵到心灵。”,我常常只是作为职业写手专事撰写专业论文而已。③参见前注,第1031页。詹姆斯教授还说:“美国典型法学期刊论文的风格不适合我,我不愿意用他们的方法来写我的论文。”(詹姆斯教授同时还是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教授,故有此论。译者注)我与怀特教授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对美国法学期刊的风格感到相当满意,通常只向法学期刊投稿。
我常常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我非要撰写论文呢?为什么法学教授通常都撰写发表论文呢?”我的家人也常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要给出答案是非常困难的,只要稍作沉思,那些最先闪现在脑海里的答案未必可靠。
一、我脑海里最初的答案
也许,年轻的法学教授如果想要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他们必须发表论文。①事实上,近些年来,一直流传着:年轻的法学院职员必须要“发表”论文才能有机会谋求到理想教职。求职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大多数美国法学院均注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这种趋势非常可以理解。但是,这却也会带来一些不幸的结果。五十年前,当我在法学院当教授时,那时很流行:年轻的法学院毕业生们需要先到知名律师事务公司历练2-3年后,再到大学法学院教书。在法律实务期间,从来不会要求年轻人发表任何学术论文。但是,今天的情况则不同,那些还按照旧制不发表论文的年轻人将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他们要和已经获得法学博士或法律博士的求职者竞争(在发表论文机会上,那些博士们有更多的时间写论文所以占尽先机)。我知道至少有一所法学院的研究生们花六年时间攻读法学博士与法律博士,在他们去教育市场上找教职之前。令人难过的真相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律师而言压力巨大,根本就不可能在工作时间之外再找时间去写论文。这曾经不是问题,但现在成了大问题。我不否认有极少数例外,有少数意气风发的忙碌的律师能挤出2-3星期来写学术论文。但这只会更糟糕,因为2-3个星期写一篇优质学术论文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像我这样够老,并且多多少少在重复着你以前写过的研究内容。而且,你面对你的年轻同行想要出类拔萃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你工作时,那些法学院内攻读学位的年轻人会花上三到五倍的时间从事写作。每一个教职员、每一个学子,都需要一个有着不同研究方向、不同观点、不同学术背景的教授群体。在今天美国的大多数法学院,能够为那些从来没有或只是偶尔从事法务实践经历的人提供足够的研究空间。事实上,我做律师时那些最卓越的同事们,最终都没去法学院教书(对他们而言不去法学院教书是好事一件)。就我的判断而言,今天美国的法学教育正面临严重的窘境,年轻律师们实在太忙碌了,根本不可能发表论文,这等于堵死了那些未曾到大学受训的人的学术研究之路。确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下,对法学院内年轻“青椒”老师而言,发表论文的要求更是令人生畏,也远甚于我开始执教时的20世纪50年代。但是,这个答案仍然不能解释:在已经获取终身教授席位之后,为什么法学院很多教授们仍然在撰写论文,他们的学术创作热情并未因评上教授而中断。
或许有人会因此认为,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法学教授们持续学术写作是为了吸引同行的注意以及在学术圈内保持学术名望。但是,这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全美顶尖的常青藤大学法学院内,一开始就在顶尖法学院任教或后来调任去的教授们仍然在持续学术写作。不可否认,一开始就在顶尖法学院任教的少数职员在论文上往往“并不多产”;但同样不可否认,大多数“论文多产”的法学教授往往也在美国最顶尖的法学院内教书。
这个答案也不能解释:有些退休前已经论著等身的教授们,即使是到了花甲之年,仍然在学术写作(虽然多数人明智地选择退休)。为什么查尔斯·阿兰(Charles Alan)教授的学术写作一直持续到其生命终结时的72岁才结束?②查尔斯·阿兰教授以写作完成多卷本的联邦司法实践及程序法专著的首席作者而出名,其著作多达五十部,他于2000年7月逝世。See Charles Alan,Wright Et Al.,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3d ed. 1999).为什么山姆·达斯(Sam Dash)教授直到他79岁逝世前的几个月里,还仍然完成了一本关于“搜查与扣押”新书的书稿?③萨缪尔·达斯教授2004年5月逝世,他的著作于人故后才出版。See Samuel Dash,The Intrudes:Under 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from King John To John Ashcroft(2004).为什么韦恩·拉法吾(Wayne LaFave)教授在已获得终身教授席位之后,不仅仍在出版他的新扩编版的三卷本巨著,在赢得终身教授职后到退休期间的超过十年期间里,还仍然在撰写新的专著与论文?④韦恩·拉法吾教授1993年后就得到了终身教授职位,在终身教授后的11年间,他发表了新扩编版的刑事法著作。See Wayne R. LaFave Al.,Criminal Procedure(2d ed. 1999);Wayne LaFave,Search and Seizure:A Treatise On The Fourth Amendment(3d ed. 1996);Wayner R. LaFave,Substantive Criminal Law(2d ed. 2003). 此外,拉法吾教授在获得终身教授后,还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三本新的案例教材,例如《当代刑事程序法》。See Wayner R. LaFave Et Al.,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8th ed. 1994,9th ed. 1999,and 10th ed. 2002). 这本书的第11版将于2005年再版。
回忆多年前的一个深夜里,我12岁的儿子在梦中苏醒后发现我书斋里的灯仍然在亮。儿子于是进书房问我深夜不睡究竟在做什么,我告诉爱子我正在为美国法学期刊书写论文。儿子问我:“爸爸这样写论文会得到多少美金?”我坦率告诉儿子,父亲写论文与发表论文的报酬其实为零,我的回答令儿子感到吃惊与不解。既然如此,连儿子亦想知晓其父为何如此?
我很清楚,我这样的回答只会令我的孩子更疑惑甚至因此认为他的父亲有点愚公气。但我后来想要消除儿子的疑惑(从我儿子脸上的不解表情即可看出),我力图为儿子的问题思索出一个好答案。深夜的彼时,面对儿子的问题,我当时能思索到的最佳答案是:深夜伏案写稿,我获得报酬的方式是间接的。由于我很快会发表一篇长文,我或许会比我不勤奋的法学院同事们更快地获得职称升等。升等之后,意味着我的银行账户里每年比以往多了2 000到5 000美金。
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是否会相信我这个略显笨拙的答案,但我知道连我自己也不信这个解释。即使我有论文等身而比同事们更早升等教授,因此每年经济收入增加,但如果我认真权衡一下为法学期刊写大篇幅论文所耗用的额外时间成本,我的时间耗用的回报其实很低。在美国法学期刊上发表一篇高品质的大作,需要作者推敲思考论文的内容与结构,需要几易草稿,需要反复文字校对修正、需要语词润色修饰、需要审校引注……我所投入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我得到的报酬。
我略作估算后,我认为我的写作或许有些低效而且低于多数人的回报,我写论文耗费的时间所得到回报是:每小时赚的还不到25美金。即使我要逐利金钱,我也不会选择通过撰写论文,那只会让自己心力俱竭却不会有好的经济回报。如果真的想要逐利,法学教授有很多回报更好、更快的赚钱方法,比如从事律师或在暑期学校兼职授课。①See Steven D. Smith,Legal Scholarship as Resistance to “Science”,41 SANDIEGO L. Rev.,1775,1777(2004).
二、学术写作乐趣无穷吗?
既然写作不会带来较多的经济回报,法学院写手们能做到以此为乐吗?日复一年,我常听到人们传颂:写作会让作者身心愉悦。事实上,在这场学术会议议程讨论中一度也是这样认为的,将学术写作充满乐趣作为讨论的基础。至少,乔纳森·梅西(Jonathan Macey)教授的观点是如此。
对此,我必须表达相反的观点。我不否认,至少有时,当我不懈努力、数易草稿之后,我可以在法学期刊上向读者成功地诉我所想所愿(我认为任何人均可以如此),论文发表后我能感受到一定的愉悦满足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过程也是充满欢愉的。一名篮球后卫成功防守“鲨鱼”奥尼尔后②即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1972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内瓦克,司职中锋,小名“沙克”(Shaq),绰号“大鲨鱼”。球队四次夺得NBA总冠军,2000年当选NBA常规赛最佳球星,三次当选NBA总决赛最佳球员,十五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防守一流中锋奥尼尔的难度很大。——译者注。,或许感到巨大的满足,但我非常怀疑这个篮球后卫会认为:“防卫中锋奥尼尔的过程也充满了乐趣。”
我的同事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在学术报告中指出,至少有时候,他写作的动机是:“让自己找到好借口不去读其他学者的论文。学术写作有时候非常令自己欢愉,比起被迫阅读其他学者的论文,自己来写论文至少不会那么痛苦不堪。”③See Steven D. Smith,Legal Scholarship as Resistance to “Science”,41 SANDIEGO L. Rev.(2004),p. 1776.我的经验却与此相反。写作之前,只要是与我要研究的论题相关,我经常花时间研读他人之论著,在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前,研读一下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更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也许正是此原因导致我写论文缓慢,迟延写作成了我这个学术写手的弱点之一。④如果是那些尚未在美国法学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学子想要请我给出建议,我想说的首要之事是:尽快开始写作,越快越好。不妨坦率直说,开始写作之时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进行更多的学术钻研,我几乎确定你会进行研究。不要预先假设你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从事研究,然后再另寻时间进行学术写作。你会(也应当)发现你可以两件事同时进行,来来回回地在研究与写作两件事之间往复。争论之中,发现自己不足之处的最佳路径就是开始写作。当你不愿轻易同意他人某些观点时,最佳方法就是开始写作。写作自己的学术思想通常会使你进行更多的研究,即做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而且,学术研究的增加常常会让你修正你最初的一些观点,或者补写一些你研究伊始就应该写的内容。
很多事情都令人心情愉悦,比如带儿孙们去看马戏,或者在凉爽的夏日下午打网球。但是,诸多快乐的事项里却不包括写论文这一选项。论文写作只是一项工作而已,写出一篇好的论文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提起“工作”,我想吐我真言。如果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6-18小时,我不由怀疑: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是用于通电话或是参加、出席会议。我也有能力一天16-18小时说个不停,但写作论文(我是指严肃的学术写作)对我而言却另当别论。学术写作需要相当多的时间集中,需要高强度的体力,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每天能够花5-6小时全身心写作已经相当不易了。
当你向主流的美国法学期刊写作投稿时,我认为奥威尔关于创作的经验分享也适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谈论其写书时的经验。奥威尔或许略微有点夸张,但也并非夸大其词,诚如其言:
“写一本书像是一次令人恐惧、身心俱竭的苦差,就如同要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一般。如果不是被某些不可抗拒的魔鬼欲念驱使或根本未认识到自己已经着魔,不会有人愿意去写书。人们均知:一个婴儿的本能会驱使他通过大声哭闹来引人注意,一个人因着魔而写作的症状正如这种本能。”①George Orwell,Why I Write,in The Orwell Reader(1956),p. 390.
三、乔治·奥威尔②的写作动机
正如我们所知,英国作家奥威尔从来不写法学论文(我也怀疑大多数人会庆幸没有将他们的才华浪费在法学论文的写作上),但他关于写作动机的讨论引发了共鸣。例如,奥威尔曾一度表达了他的“写作初心”是缘于他“对社会不公的直觉”,奥威尔决定开始写书是因为“我想揭穿谎言或者写出令世人注意的事实”③George Orwell,Why I Write,in The Orwell Reader(1956),p. 394.。
虽然很多年之后我才读到奥威尔的随笔,但是,他的述评能够非常好地描述我的写作动机。那时的我,正在写作一篇抨击“前吉迪恩规则”(重罪被告人应于何时被指定律师辩护)的论文。④See Yale Kamisar,The Right to Counsel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A Dialogue on “The Most Pervasive Right” of an Accused,30 U.CHI. L. REV. 1(1963).所谓“前吉迪恩规则”,其实也可称之为“贝茨规则”或者“特定情形规则”(Special Circumstances Rule)。⑤Betts v. Brady,316 U.S. 455(1942),overruled by Gideon v. Wainwright,372 U.S. 335(1963). 1966年的吉迪恩诉温瑞特一案,法院判决在一审审理程序中,不管是各州还是联邦法院,所有重罪的被告人必须有律师辩护,否则程序违法。20世纪70年代的最高法院,在律师权适用的场合问题上,表现出保守后退的倾向,认为上诉审、取保候审听审、假释听证等程序中,政府无义务为被告人请律师。——译者注。当一名贫穷被告人被以死刑以外的重罪罪名起诉时(例如持枪抢劫),除非能够证明案件属于“特定情形”(例如被告人是精神智障人士或者案件被不正常的审理),否则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⑥吉迪恩一案中,一个因盗窃被追诉的被告人申请法庭为其指定律师,法官回应他道:“法官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只有是死刑犯案件,法院才必须为被告人指定律师。”Gideon,372 U.S. p. 337(斜体字为笔者所加)。不幸的是,在州法院审理实践中,极少在非死刑的案件中为被告人指定律师,因为州法院根本没兴趣去发现是否存在所谓的“特定情形”或“特殊情况”。⑦就算那些记录在法庭很好地被读过,又能够证明什么呢?如果被告人有律师在场,这些记录又会如何被宣读呢?那个发展出“满意理论”无律师辩护的被告人是失败的,从来没有证实他受到了“公平审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了“fair trial”内容),或者说就算他这样主张,他也无法证明。对于那些放弃以“不在犯罪现场”为由辩护的被告人而言(被告人贝茨正是以不在犯罪现场为由为自己辩护),对于那些法庭上表现欠佳的其他被告人而言,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无法证明遭受不公正审判),被告人要证明其知晓法律、认定事实的失败原因是由于法庭内外没有律师帮助与律师辩护所导致。作为一个写作生命很长的写手,弗兰西斯·阿兰教授领悟到的可悲的教训之一是:“根本没有所谓最后的胜利者。无论你的成就如何巨大,在世间你其实渺小又微不足道。只要没有更多的努力奋斗,总有一天你会慢慢变得暗淡与消亡。”Francis A. Allen,On Winning and Losing,in Law,Intellect,and Education 11,16(1979). 不幸的是,曾经声名狼藉的“贝茨诉布雷迪”案的幽灵又浮出水面。吉迪恩判决十年之后,最高法院认为,在缓刑与假释程序中没有指定辩护的平权(flat rights)问题。面临撤销缓刑与假释重回监狱时,缓刑者与假释犯如果想要申请获得免费的律师法律援助,必须自己证明:有实质性理由证明收监执行是不恰当的,而且证明理由的成立非常困难复杂,有必要通过律师的法律援助来完成,否则会难以主张与举证。Gagnon v.Scarpelli,411 U.S. 778,790(1973).
借用奥威尔的语言,我写律师权的那篇论文想揭露的“谎言”正是:指望法官、检察官们保护无律师的刑事被告人权利,这就是一个十足的谎言。我指出的另一个“谎言”是:当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时,法庭书面审理记录可以保证无律师的被告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不利。那些法庭记录根本不能实现达成这样的目标。论文中我反复强调,在没有律师出庭的情况下所作的法庭书面记录,根本不能证明:无律师的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奥威尔也告诉我们,他由感而发写作的原因是:“有一些真相,我想要提醒世人注意。”①George Orwell,Why I Write,in The Orwell Reader(1956),p. 394.此言再次为世人敲响了警钟,而我的律师权的那篇论文则再次提供了例证。
我认为论证“贝茨诉布雷迪”一案所设定的“特殊情形”规则非常重要,该案确立的规则是:如果被告人有律师出庭辩护是否会有所不同。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均作出了不当的假设性推论,认为即使是无律师出庭辩护的情形下,对持枪抢劫的贝茨进行审判也未必构成“特殊情形”。②美国最高法院告诉我们:“简单的问题是,是各州与刑事被告人的证据可信度问题。”Betts,316 U.S. p. 472. 在驳回贝茨先生上诉的理由里,州法院的结论也大同小异:“这个案件里,必须说控辩双方的律师辩护问题是都不需要多言的(是否聘请律师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译者注)。”参见州法院对此案的审理记录,第30页。Betts v. Brady,See Yale Kamisar,The Right to Counsel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A Dialogue on “The Most Pervasive Right” of an Accused,30 U. CHI. L. REV. 1(1963),p. 42.但是,当我严格反复地看过贝茨案的法庭记录之后,法庭记录更让我确信该案其实错误百出。
略举一例,在警局“列队辨认”(Lineup Identify)犯罪嫌疑人程序中,该案中被害人最初根本没有认出贝茨。后来,警方将贝茨作为唯一的辨认对象让被害人辨认,警方让贝茨穿上一件黑色外套、戴着黑色眼镜、用围巾围住下巴。黑外套、黑眼镜、围巾究竟是何人的?这些物品根本没有作为法庭证据使用。事实上,检察官从未能够证明:被告人贝茨曾经穿过黑色大衣与戴过黑色眼镜。
我反复地审阅过这些副本并且研究了好几个星期,③比起实务律师们,既然我是一个专业学者,我就能够有时间从事研究。我也不担心,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许这些时间原本可用来逐利。我从事学术研究是建立在我拥有我所有的时间的基础上,后来一直亦是如此。我写论文断定警方进行了诱导性取证:“抢劫案中,被害人叙述了犯罪嫌疑人的各种衣着特征后,警察听完后马上出去寻借了大衣、眼镜与围巾,并且扔在贝茨的面前。正是根据警方让贝茨所穿戴的上述衣物,被害人认出了贝茨。”④See Yale Kamisar,The Right to Counsel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A Dialogue on “The Most Pervasive Right” of an Accused,30 U.CHI. L. REV. 1(1963),p. 40.
借用奥威尔的名言:“作家写作的‘伟大的动机’之一是政治动机,如果将政治这一词汇赋予最宽泛的可能意义。我的愿望是:让这个世界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行,转变别人为这个社会所奋斗时其所持的观念。再说一遍,没有一本书是能够做到真正脱离政治倾向的。”⑤George Orwell,Why I Write,In the Orwell Reader(1956),pp. 392-393.
对奥威尔的言词稍作修改,我必须说我的写作动机与愿望:改变人们对刑事司法制度所持的老旧观念,尤其想要改变那些坐在法官席上的人的观念。⑥我分享这样的观点:“当你在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论证最低收入的权利或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利后,别指望你的论文会有多大影响力,哪怕是让一个法官站在你的立场上。”Steven D. Smith,Legal Scholarship as Resistance to “Science”,41 SANDIEGO L. REV.1775,1777(2004),p. 1778. 但我总是相信,当更多的“增量”(incremental)权利成为审判议题时(译者注:主要指隐私权、沉默权等各种美国宪法暗含的新型权利),法学期刊上发表的权利论证内容会对法院产生重要的影响。当然,对于刑事司法制度的理念内容,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意味着,人们一旦拥有了秉持深信的刑事司法理念之后,将因犯罪议题的讨论而被卷入政治,具体体现为“犯罪问题的政治化”(Politics of crime)与“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化(politics of“law and order”)争论。
在美国注重事实发现导向的文化之下,统计数据因此拥有了某种魔力。正如著名犯罪学家劳埃德·欧林(Lloyd Ohlin)所洞察到的:“当人们对某些问题一知半解时,实证数据能提供所谓的客观现实感(通常是错觉),统计数据的力量将会因此变得异常强大。”①See Yale Kamisar,How to Use,Abuse-and Fight Back with-Crime Statistics,25 Okla. L. Rev. 239,239(1972)(quoting Lloyd Ohlin);see also Lloyd E. Ohlin,The Effect of Social Change on Crime and Law Enforcement,43 Notre Dame Law Review(1967-1968),p.834.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一直以来,对犯罪持强硬立场的政治家们经常用(或许也可说是误用)统计数据证明:犯罪已摧垮了我们的社会,应当严厉谴责那些纵容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法院以及心慈手软的自由派们。②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是否会对犯罪率产生影响的问题,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可以参见:Paul G. Cassell,Miranda's “Negligible” Effect on Law Enforcement:Some Skeptical Observations,20 HARV. J.L. & PUB. POL'Y 327(1997);John J. Donohue III,Did Miranda Diminish Police Effectiveness? 50 STAN. L. REV. 1147(1998);Fred E. Inbau,Public Safety v. Individual Civil Liberties:The Prosecutor's Stand,53 J. CRIM. L. CRIMINOLOGY & POLICE Sci. 85(1962);Kamisar,supra note 24;Stephen J. Schulhofer,Bashing Miranda is Unjustified-and Harmful,20 HARV. J.L. & PUB. POL'Y 347(1997).
如果让我仅举一例,我会想起参议员约翰·迈克莱伦(John McClellan)先生的“战术”。在担任美国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听证会主席时,他强烈主张推翻“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③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36(1966). 反米兰达的法案,即1968年的《犯罪综合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在2000年的“迪克逊诉美国”一案中,被美国最高法院以7∶2多数比例推翻。Dickerson v. United Stp.es,530 U.S. 428(2000). 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美国国会不能通过立法来推翻最高法院对宪法条文的解释与适用。当迈克莱伦参议员极力主张制定新法案来推翻米兰达规则时,他在参议院后厅挂起巨幅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图表。图表的标题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与美国犯罪率峰谷间的关系》,想要证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宽纵刑事被告人的“司法能动行为”(Activity)与犯罪率的升高之间的相伴并行的尴尬关系。④Fred P. Graham,The Self-Inflicted Wound,p.12(1970).他接下来宣布:“犯罪曲线图显示美国犯罪率处在高位阶,犯罪趋势很严峻似乎要冲上峰值。但最高法院却对执法保持低调,我们仿佛已面临着旋风。看看犯罪数据图表吧。好好看看,为你的国家而哭泣吧。犯罪正在盘旋爬升、越升越高!”⑤114 CONG. REC. 14,146(1968).
如果最后再一次借用奥威尔的语言,虽然可以用犯罪统计数据一次又一次地吓唬公众并影响司法与立法机构,很多犯罪统计数据最终被证明仍然只是谎言而已。⑥或者作为他从战术上所使用的误导方法。对犯罪政治化议题感兴趣的人们会有揭穿谎言的冲动。法学教授们或许没有受过统计学方法的专业训练,我当然也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我仍然怀疑,那些写过这些主题的学者们,不管今天在不在会场,也不管讨论主题是否涉及法经济学、法律史、心理学或统计学,好的创作者不会给他们的反对者颁发自由通行证。
为激发所有的潜能,一个美式足球运动员必须坚持不懈地在体育训练房训练。为了达到他们的最大潜能,法学论文写手们必须不间断地自我学习。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犯罪学家,但他们必须进行足够的自我学习以避免被他人误导、困惑或被历史学、犯罪学等其他学科吓傻。优秀的法学论文写作者的自我学习的能力必须足够好,这样才能不被谎言或其他学科的误导性结论所欺骗到,也才能有能力去揭穿谎言。
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合作研究,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用的,但因各种原因,这样的合作常常不可行。多诺霍(Donohue)教授似乎有特殊的其他学科背景对统计学也兴趣盎然,但我一直并不知晓,直到他决定对米兰达判决做实证统计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对于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案件的减少,米兰达规则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而且能够产生长期性的影响。⑦John J. Donohue III,Did Miranda Diminish Police Effectiveness?,50 STAN. L.REV. 1147(1998),pp.1151-1180.多诺霍教授对该参议员论断的回应,我认为在犯罪统计学上的贡献很重要。⑧John J. Donohue III,Did Miranda Diminish Police Effectiveness?,50 STAN. L.REV. 1147(1998),pp. 1151-1156.但是,当我在60年代开始写这方面的论文时,多诺霍教授又在哪呢?⑨See Yale Kamisar,On the Tactics of Police-Prosecution Oriented Critics of the Courts,49 CORNELL L.Q. 436(1963-1964);Yale Kamisar,Public Safety v. Individual Liberties:Some “Facts” and “Theories”,53 J. Crim. L. Criminology & Politics Science(1962),pp.184-193.再说那个时候我真的需要他吗?(何况那时,多诺霍还在上小学呢。)
四、法学教授们为什么应该写作?
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那样,我认为每一个法学院职员群体都应该包含相当数量的曾在司法实务中历练数年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给法学院带来教学与写作方法上的新视角,还因为他们更乐于感激法学院提供非常有利的研究环境,而这些研究环境为一个法学学术写手所需要。
一方面,即使是在美国现在最好的法务公司(我也曾在优秀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工作,一个年轻律师通常会发现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律师事务所历经数年后,我才真正明白这些,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话,我怀疑今天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另一方面,法学院教授们没有必要担心要承担双份工作的问题。在学术前行的路上,法学教授们可以殚精竭虑地深入思考与研究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教授与实务人士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远,不难想到律师们没有学术休假或在暑假里写论文的时间保证。
问题还不止如此。比起律师们,法学教授有更好的机会利用法学院图书馆资料。我可以回忆起无数例子:法学院图书馆馆员们帮我搜集到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其中有些资料甚至是我自己难以发现的。而且,法学院教授们可以将他们的论文初稿交给3-4名同事来获得同事们有益的反馈与评论。事实上,法学教授们将论文初稿发给其他讲授同一门课的同事再正常不过了。此外,为了获得有价值的学术批评,越来越多的教授写完初稿后,开始到全美国各个法学院的“学术工作坊”交流初稿内容。
每当我心情不好、工作劳顿之时,就会想起一件让我重新振作的偶然事件,那件事发生在我在“科温顿与伯灵”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的第二年(1956)。当时,公司鼓励年轻的律师为贫穷被告人代理上诉。有一天,我发现我想推翻一个叫沃伦·威廉姆斯被告的毒品犯罪判决。①See Williams v. United States,237 F.2d 789(D.C. Cir. 1956).
威廉姆斯先生在大街上被非法逮捕,警察强令其上警车并且被带到警局大楼。威廉姆斯被领进警局登记室之前,当穿过走廊时身上掉下了一个雪茄烟盒,虽然他想在被搜身前掩盖起来,但还是被身后的警察捡起来并发现里面有可卡因毒品。警察问被告人香烟盒是不是他的,被告人承认烟盒是他掉在地上的,也愿意承认烟盒内藏有毒品。②对该案的讨论,可以参见卡米萨的论文。Yale Kamisar,Illegal Searches or Seizures and Contemporaneous Incriminating Statements:A Dialogue on a Neglected Area of Criminal Procedure,1961 U. ILL. L. F. 78,127 n.224.
当被告人后来申请排除可卡因毒品证据时,地方法院驳回了被告人的动议,法院的判决根据是:可卡因是被告人“丢弃的”,而不是警察非法搜查获得的。我非常确信的是,上诉法院应当排除这个非法逮捕的“毒果”证据,毒品物证的“丢弃”被警察的非法逮捕行为所严重污染。当我准备法庭口头辩论之前,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问题(也可以说是潜在的问题)。假设代表政府追诉犯罪的一方说:“就算警察是通过非法逮捕而取得毒品物证,但根据上诉审中的‘无害错误’(Harmless Error)规则,被告人自愿地承认可卡因是其所携带。”我该如何应对?
我冲进图书馆寻找资料却发现:自1880年“巴尔博诉人民”③Balbo v. People,80 N.Y. 484,498-500(1880).判例以来,主流的观点认为非法逮捕或者“立即先行搜查”(immediately preceding search)不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④即时的先行搜查(immediately preceding search),主要是指警察在拘捕犯罪嫌疑人时,所进行的附带性的预先搜身,由于有些犯罪嫌疑人身上可能有枪支等危及警察安全的物品,为了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警察在拘捕嫌疑人之后,有权对其搜身甚至身边附近的行李、汽车后备箱等。译者注。我只花了一天半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此后做的研究越多,越发现所有的判例均不支持我的观点。
威廉姆斯的有罪陈述是自愿的,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主张“威廉姆斯陈述是因非法逮捕而被迫的”,这种主张看似非常牵强。而且,只要我在法庭上对此主张,法官每次都会驳回。我感到非常无助。
幸运的是,在法庭上,检察官从来也没有提出我所真正担忧的争议点。因此,这个案子只是围绕着“物证的合法性”问题而进行辩论,在这个辩题上我赢了。但是,我从来没忘记巴尔博规则以及这个案子所带给我的心理煎熬感。
我想巴尔博规则是错误的。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我自己感到巴尔博规则是错的。我认为,非法逮捕或非法搜查所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之前非法取证的“毒果”而被排除,物证也应当如此。但我知道: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在法庭上我必输无疑。
五年后,当我成为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一名年轻的教授时,我又研究了老旧的“巴尔博规则”。现在我终于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并作最后一搏,比如追溯巴尔博规则的历史与发展以及更多近来的与巴尔博规则相反的判例。当我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有时间思索到底。我一次又一次地写我论文的初稿,直到我完全满意为止,不管将有多久(实际上我花了七个月才写完论文)。①不谦逊地说,我希望并期待我的学术论文将会对巴尔博规则产生最终的影响力,我曾想过或许在十到二十年之后,巴尔博规则将会改变,后来的判例证明了我的期待。See Wong Sun v. United States,371 U.S. 471,485(1963). 在该案中,最高法院陈述道:“至少在一定的情形下,相比警方无令状侵入民宅所获取的实物证据而言,用非法闯入或非法逮捕方法所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过是政府非法行为的果实而已。”我的学术论文在该案判决书中被最高法院法官引用,这是值得很多法学教授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
当我撰写完那篇论文时 ,我也未必比五年前做律师助理时的那个我更聪明。但是,我想我毕竟可以在更有利、更满意的学术环境下进行学术创作,这样的写作环境会令千百个忙碌如蚁、行色匆忙的实务人士所艳羡不已。为什么法学教授应该学术写作?也许是那个案例激发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理由,解释法学教授们为何应当进行学术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