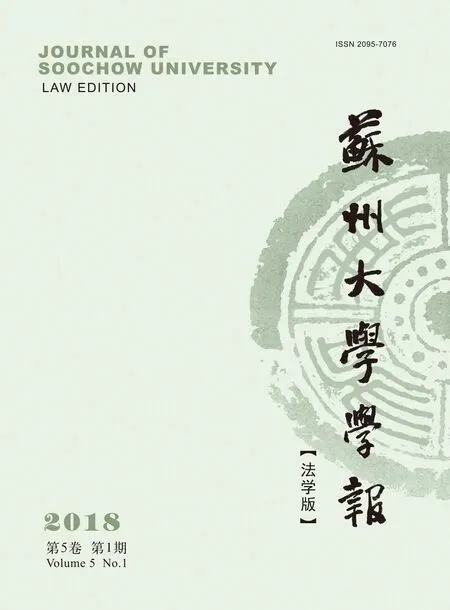有关不作为与共犯的几个问题*
2018-01-31桥爪隆王昭武
[日]桥爪隆 著 王昭武* 译
一、引言
无论是不作为犯理论还是共犯理论,都属于刑法总论中的难点。在所谓“不作为与共犯”的问题中,这两个难点竞合在一起,因而可以说,“不作为与共犯”是刑法总论中的最大难点之一。
对于不作为与共犯的问题,有必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针对作为犯的不作为的加功;(2)针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加功;(3)不作为的共同实行。另外,(4)原本应从何种视角来区分“不作为的加功”与“作为的加功”,这也是一个问题。本文首先探讨第(4)个问题,然后再讨论前三个问题。
二、作为的共犯与不作为的共犯的界限
(一)概述
在作为的正犯实现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际,不予制止而是在现场旁观的,对于持这种消极态度者,能否认定成立不作为的共犯,这一点似乎会成为问题。但是,这种行为在现场显示了声援犯罪行为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将该行为评价为作为的共犯,也不是没有可能。原本来说,我们应该从哪种视角来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呢?这里首先想确认单独正犯中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
如果认为作为是身体的“动”,不作为是身体的“静”,那么,两者的区别就是排他性的。但是,正如学界反复指出的那样,①参见町野朔:《刑法総論講義案Ⅰ(第2版)》,信山社1995年版,第139页以下;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77页;等等。不作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而是指“没有实施被期待实施的作为”。为此,作为硬币的两面,对于某种举动,给予作为的评价与给予不作为的评价,是完全有可能同时并存的。例如,负有给幼儿喂食义务的母亲,怠于履行该义务而一味沉迷于游戏的,在该事实中,在沉迷于游戏这一意义上,属于作为的行为,而在不给自己的幼儿喂食这一意义上,又属于不作为的行为。并且,我们只要就作为、不作为的各个行为,分别探讨其是否该当于构成要件即可。例如,如果该母亲通过在身体上安装感应器而进行非法的弹子赌博游戏的,该作为的行为就该当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②按照判例的观点,在身体上安装禁止使用的感应器而进行弹子赌博游戏的,超出了通常的游戏方法的范围,构成盗窃罪(最决平成19年〔2007年〕4月13日刑集61卷3号340页)。相反,就是否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这一问题而言,并非是由沉迷于游戏这一行为创造了针对生命的危险性,而是由负有保护幼儿生命这一义务的人不给幼儿喂食这一不作为,而扩大、发展了(原本可以避免的)针对生命的危险,进而发展至出现死亡结果,因此,是否成立不作为犯,就会成为这里的问题。③总之,重要的是就各个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对于这一点,参见萩野貴史:《作為犯と不作為犯の区別について》,载《獨協ロー·ジャーナル》第7号(2012年),第69页。
这样,以作为、不作为是有可能两立的概念为前提,原本来说,理应不存在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这种顺序问题。然而,对作为犯来说,(除了身份犯的情形之外)无论是何种主体的作为,都能满足构成要件,而对不真正不作为犯来说,由于只有作为义务者的不作为才该当于构成要件,因此,一般的做法是:首先探讨属于基本类型的作为犯,在不该当于作为犯的构成要件的场合,再探讨是否成立不作为犯。因此,需要探讨是否成立不作为犯的,事实上会逐渐限于那些不成立作为犯的情形。④作为与不作为并非是同一行为的“表里”,例如,出于杀人罪的故意致人重伤之后,即便不采取措施救助被害人,也不再探讨是否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的问题。这与其说是故意的先行行为的场合不产生作为义务,还不如说是,即便能认定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但只要先行行为成立了杀人罪,再探讨不作为的杀人罪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当然能认定作为的实行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行为人因没有注视前方而撞到了被害人,将被害人抬入自己的车内之后,没有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致使被害人(因事故所造成的受伤而)死亡的。在该情形下,行为人将被害人抬入自己的车内,而后实施驾驶汽车的行为,但被害人并非是由此而死亡。为此,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除了驾车过失致死罪之外)是否成立不作为犯就成为问题。不过,对于某些案件,也能设想出作为与不作为均该当于构成要件的情形。例如,在本案中,行为人是出于未必的故意,在大雪之中将被害人放在人烟罕至的地方,被害人最终因车祸导致的伤害而死亡。如果属于因被放在极寒的野外而提前了死期的情形,那么,将被害人放在雪中的行为(作为),以及不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的行为(不作为),就都有可能该当于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该场合下,以作为来处罚行为人,或者以不作为来处罚行为人,都是被允许的。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就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等进行举证的情形,起始就探讨是否成立不作为犯,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二)作为的共犯的界限
这样,针对同一行为样态,作为与不作为是有可能并存的两种评价,只要对作为与不作为分别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即可。对于涉及共犯的处罚情形,这一原则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例如,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情形:与X女同居在一起的Y男,对X女的亲生孩子实施暴力,X在同一房间只是旁观而未加制止。在该情形下,如果X通过“继续打!”“这种小孩,怎么弄都行!”等言语强化了Y的暴力犯意,促进了Y的犯罪行为,那么,X就应承担作为的共犯的罪责。但在该场合下,X究竟是承担(共谋)共同正犯的罪责,还是仅在帮助犯的限度之内承担罪责,这属于应该根据共犯论的一般原则来解决的问题。反之,在不能认定因作为的行为而促进了Y的犯罪行为的场合,就不能作为“作为的共犯”予以处罚,而是仅仅在Y负有保护A之生命的作为义务的限度之内,探讨是否成立不作为的共犯的问题。显然,这种一般论本身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虽说是作为的帮助,也并不是要求存在多么积极的言行。在上述案件中,X是否通过言语形式做了具体的表态,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即便是X数次对Y点头,显示认可、支持Y对A实施暴力的态度的情形,如果由此促进、强化了Y的犯罪行为,想必也能成立作为的帮助。进一步而言,即便是X盯着Y的眼睛,(以默示的方式)传达了“你尽管按你的意思去做”这种意思的,结论也是相同的。最终的归结就是,对于帮助行为的样态并无具体限定,凡能强化正犯的犯意,使其犯罪行为更为容易的一切行为均该当于此,因此,虽说对言行、态度可认定为是作为的方式,但对于作为的程度要求则未必很高。然而,要评价为作为的帮助,就应该以能够被评价为作为的某种“动作”为必要。为此,站在那里、坐在那里这种存在本身,原则上不应该被评价为作为的共犯行为,①参见松原芳博:《共謀共同正犯と行為主義》,载:《鈴木茂嗣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07年版,第539页以下;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1)》,载《立教法学》第64号(2003年),第20页;等等。反之,齊藤彰子虽认为,呆在犯罪现场本身也该当于作为的共犯,但同时要求存在这样的要件:用于将赋予行为人离开犯罪现场这种义务予以正当化的要件(齊藤彰子:《作為正犯者の犯罪行為を阻止しなかった者の刑責》,载《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249号(2013年),第251页以下)。齊藤彰子的这种问题意识是正确的,但在本文看来,其观点最终会发展至,通过要求存在作为义务,而将这种参与定位于不作为的共犯。仅限于那些能将这种存在评价为表明一定意思之态度的情形,才极其例外地能被评价为作为的共犯。②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的情形:能给实行担当者施加强烈的心理影响的人,对于正在犹豫是否实施犯罪的实行担当者,故意背对着他或者故意低着头,通过自己的态度施加压力,让其尽早着手犯罪。还有,被告人的丈夫明知被告人试图抓住幼儿的头撞击(用于取暖的)被炉的盖板,却故意躲开目光,没有制止被告人,对此,大阪高判平成13年〔2001年〕6月21日判タ1085号292页判定其与被告人之间“成立默示的共谋”。而且,即便能够认定存在作为的言行,但在无法认定实行行为者由此被具体地强化了犯意,因而也无法认定,存在针对构成要件之实现的因果性的场合,对此,否定成立作为的共犯,就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在所谓“警卫事件”中(最决平成15年〔2003年〕5月1日刑集57卷5号507页),某暴力团组长确切地知道几名保镖会随身携带枪支进行警卫,仍决定进京游玩,而且,进京之后始终与携带枪支的保镖一起活动,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实质上可以评价为,正是被告人让保镖携带了本案枪支”,进而以此为理由,判定该组长成立共谋共同正犯。本案被告人在确切地认识到保镖会持枪警卫的基础上,仍然决定进京,且指示手下安排进京相关事宜,进京之后认识到有保镖在进行护卫,乘坐汽车在东京市内活动。既然能理解为正是被告人的这些行为让保镖携带了枪支,对于本案就应认定成立作为的共犯。并且,判例正是考虑到被告人与保镖之间存在默示的意思联络(共同性),以及被告人拥有指挥、命令保镖的权限(重要的因果性贡献),才认定被告人成立共谋共同正犯。③本判决是有关共谋共同正犯的最高裁判所的最新判决之一,案情比较特殊,但判决本身对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走向影响巨大。与一直以来的其他案件不同,本案的共犯之间并无明确的共谋,由此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默示能否构成共谋?只有默示的共谋是否可成立共谋共同正犯?对于前者,判例明确予以了肯定;但对后者,判例并未正面回答,但显然同时考虑了被告人的地位、实际作用等其他因素。本案案情大致如下:被告人为某暴力团的组长,属下有3100余名组员,平常出门总是带有保镖。而且,为了在被告人遭到袭击之时能保护其安全,尽管被告人并未要求,但保镖身边总带有枪支,被告人对此也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保镖也一直以为被告人知道他们携有枪支。但是,被告人与保镖之间就是否携带枪支从未有过具体明确的意思联络。被告人每次去东京,总是由5、6台车组成车队,其中既有先导车也有装备车,规模很是壮观。1997年12月下旬,被告人告知其助手准备到东京游玩。因当年8月28日,另一暴力团的组长曾被枪杀,且考虑到东京的警察对枪支管制非常严格,该助手一边命令一名保镖提前到东京准备枪支,一边决定加强保卫,将保镖由平时的3名增加到4名。同年12月25日,被告人到达东京,迎接车队一共5台,其中先导车内携带2支手枪,护卫车里的3名保镖各携带1支手枪。行进途中,被警察截住,查获了枪支。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实质上可以评价为,正是被告人让保镖携带了本案枪支”,而认定被告人构成违反《枪炮刀剑类等持有取缔法》第3条第1项“禁止持有”的共谋共同正犯。主要判决理由为:(1)尽管被告人并未直接命令保镖携带枪支,但确切地知道保镖为了保护其安全而自发带有枪支,并认为这理所当然而坦然接受,保镖们对此也知道,因而共犯之间“存在默示的意思联络”;(2)被告人具有指挥命令保镖的权限,而且处于由他们保护其安全的地位。——译者注。本判决在考虑有无共谋的同时,也考虑到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说是妥当的。
又如,X是A游戏中心的店长,店员Y等人打算在与A店由同一经营者经营的B弹子店将营业款解往公司总部之际实施抢劫,X从Y处得知该计划之后,一度要求Y放弃实施该计划,但Y对X说,“和你没关系!”为此,X回答,“既然和我没关系,那行!”自此就没再关注Y等人的抢劫行为。对于该案,东京高判平成11年〔1999年〕1月29日判时1683号153页认为,不能将“既然和我没关系,那行!”这一表态,也评价为,X表明了对于犯罪行为一概不再多言这种意思,因而否定成立作为的帮助。X的“既然和我没关系,那行!”这一表态,显然属于作为的言行。并且,通过该表态,Y也许多少有些放心了:“X不会妨害自己的行为了”。然而,没有阻止犯罪之作为义务的人没有阻止犯罪,①如后所述,对X而言,既没有保护将B店的销售款解往总公司的义务,也没有阻止同事Y的犯罪行为的义务,因而不成立不作为的共犯。这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情况。这样的话,即便X的“既然和我没关系,那行!”这一表态,表达了不妨害Y等人的行为的意思,但如果该表态不能被评价为属于更加强化了正犯的犯意,积极地促进了犯罪的行为,那么,否定成立作为的共犯这一结果就是妥当的。
另外,最近有这样一个最高裁判所案例(最决平成25年〔2013年〕4月15日刑集67卷4号437页):两名被告人与既是同事也是玩伴的A一起饮酒,A提出酒后驾驶,二人向其点头说,“那就这样吧”,从而给予认可,并乘坐A驾驶的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也没有改变态度,而是持续予以默认。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比照A与两名被告人之间的关系,A就启动本案车辆征得两名被告人的认可的经过与情况,以及两名被告人对此的应答态度等,可以认定:一方面,A就驾驶本案车辆,确认了既属于工作上的前辈同时也是同乘人的被告人的意向,得到两人的认可属于(决定酒后驾驶的)重要的契机;另一方面,两名被告人虽认识到A因受酒精的影响处于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仍对启动本案车辆给予认可,没有制止A的驾驶而是同乘该车,一直予以默认。因此,两名被告人的上述认可与随后的默认这种行为,通过更加强化A的驾驶意思,使得A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更为容易实现,这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判定成立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帮助犯。在本案中,被告人对于启动车辆给予了认可这一行为,显然属于作为形式的参与。相反,对于同乘并默认驾驶的行为,(如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所判定的那样)其实质应该求之于不制止酒后驾驶这一点,因而也完全有可能理解为不作为形式的参与。不过,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没有区分二者,而是将“认可与随后的默认这种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评价为帮助行为。对此,一般理解为,虽说是默认,但该行为同时还具有持续表达此前已经由认可所显示的态度的一面,因此,才可以对全体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认定成立作为的帮助犯。②关于这一点的分析,参见内田浩:《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38号(2013年),第96页;亀井源太郎、濱田新:《判批》,载《法律時報》第86卷第2号(2014年),第126页。为此,诸如乘上汽车之后才察觉驾驶者的醉酒状态,仍就这样默认的情形那样,对于那些不能与先行的认可行为一起进行评价的情形,很多时候很难将默认本身评价为作为。
三、不作为的共犯
(一)概述
有些时候,对于那些不阻止作为犯的行为的态度,并不能将其当作“作为的共犯”予以处罚,在此情形下,是否具有不作为的共犯的可罚性,就会成为问题。这里首先想就不作为的共犯,简单地阐明本文的理解。
要认定成立不作为的共犯,以参与者存在作为义务为必要。③参见林幹人:《不作為による共犯》,载《齊藤誠二先生古稀記念·刑事法学の現実と展開》,信山社2003年版,第318页;等等。并非是所有旁观他人犯罪的人,都要承担共犯的罪责,因此,对于共犯,要处罚不作为,也以存在作为义务为必要,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要将科以作为义务予以正当化,也应该要求能够期待行为人履行该义务(作为可能性、容易性),这一点也与正犯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其他问题,应该与作为的共犯做相同的理解。也就是,对于作为的帮助犯中的因果性要件,不需要与由正犯引起的构成要件的结果之间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只要存在强化正犯的犯意,促进、强化了该构成要件的实现即可。为此,对于不作为的帮助而言,如果存在同样的作用,也就满足了因果性要件。而且,对于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与帮助犯之间的区别,原则上,原样适用作为犯中的共同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别标准即可。下面想具体阐释这种理解。
(二)共犯中的作为义务
1.法益保护义务
对于正犯的作为义务的根据的理解,原则上,同样适用于共犯的作为义务。换言之,基于下述两点,正犯被赋予一定的作为义务就得以正当化:(1)以对于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支配关系为前提;同时,(2)由先行行为创造了危险,或者接受了保护,或者存在特定身份关系,或者处于职务上的特定地位等。①参见橋爪隆:《不作為の成立要件について》,载《法学教室》第421号(2015年),第91页以下(译文参见桥爪隆:《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4期,第131页以下。——译者注)。其中,对于第(1)点即支配性要件,在共犯的场合,想必不得不大幅度地加以缓和。亦即,在作为的帮助的情形下,对于一名实行正犯,数名共犯给予心理上、物理上的促进效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一来,当然不可能要求存在对于结果发生的排他性支配,毋宁说,在采取指向结果防止的一定措施之际,如果存在难以期待行为人(共犯)之外的其他人采取该措施的情况,原则上就应该理解为满足了第(1)点要件。
例如,被告人X女与Y男属于姘居关系,一同与X的小孩A(4岁)、B(3岁)、C(10个月)生活在一起,Y男平素就经常责打A、B。案发当日,在Y男多次殴打B的头部等处,致B摔倒在地,最终致B死亡之际,X女明知Y男正在责打B,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厨房准备晚饭,而没有制止Y男的暴力行为。②对于该案,作为原审(一审)的釧路地方裁判所指出:“要构成不作为的帮助犯,必须是对他人的犯罪行为负有阻止其实施这一作为义务者尽管几乎可以切实地阻止该犯罪的实行,却放任不管”。并基于这一前提,进一步指出:“除被告人之外,别无他人可以使B免受Y之暴力”,进而认定被告人负有阻止犯罪实行的义务,但因“被告人(当时)处于非常难以阻止Y之暴力这一状况之下”,从而宣判X女无罪(釧路地判平成11年〔1999年〕2月12日判时1675号148页)。对此判决,检察官提出抗诉。与原审判决不同,札幌高等裁判所认为:“负有作为义务者本有可能通过一定的作为而防止正犯的犯罪,虽然存在认识,却并不实施这一作为,因而藉此使得正犯容易实施犯罪行为的,即成立(不作为的帮助)”,并以此为前提指出,由于“可以阻止(犯罪行为)而使B免受Y之暴行者,除了被告人之外别无他人”,因而“(被告人的)上述作为义务极其强烈”,如果X监视并制止Y,则本有可能阻止了Y之暴力。因此,“X的不作为无疑使Y对B的暴力更易实现”,从而认定X构成伤害致死罪的帮助犯。——译者注对此,札幌高判平成12年〔2000年〕3月16日判时1711号170页认定:X“深知Y是急性子且有暴力倾向,却在与Y同居期间,总是带着B等,置于Y的掌控之下”,而且,“被告人是仅仅只有3岁6个月的B的唯一的亲权人”,再者,“在Y试图对B实施本案责打之际,……可以阻止(犯罪行为)而使B免受Y之暴力者,除了被告人之外别无他人”,因此,“被告人负有必须阻止Y向B实施暴力的义务”。这里,判例认定X女负有作为义务,列举的是下面几点理由:(1)X女具有的亲权人这一地位;(2)虽深知有遭受Y男之暴力的危险,却仍然将B等小孩置于Y男的掌控之下;(3)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可能由第三者来避免结果。可以说,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当然能认定X女负有作为义务,但如果上述三点中的某一点并不充分,那么,对此情形能在何种范围之内肯定作为义务,就仍有探究的必要。按照本文的理解,首先,在第(1)点与第(2)点之中,即便其中某一点的事实并不充分,仍有基于另一点的事实而认定存在作为义务的余地;其次,就第(3)点而言,即便当时还有X女、Y男的亲属或者朋友,如果当时的情形是,除了X女之外,其他人很难阻止Y男的暴力,那么,仍应该肯定X女负有作为义务。
2.犯罪阻止义务
在上述札幌高等裁判所平成12年〔2000年〕判决中,完全是从被告人X女应该保护自己的小孩B的生命、身体这一视角,而推导出了作为义务。那么,基于X女与Y男处于同居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X女就应该阻止该人的犯罪行为(暴力),我们是否有从这一视角推导出作为义务的余地呢?仅就本案而言,无论从哪一视角均能推导出作为义务,然而,例如,在第三者向B实施暴力之际放任不管的,或者,在Y男对其他毫无关系的幼儿实施暴力之际放任不管的,依据从哪一视角来推导作为义务,对于是否成立不作为,就会得出不同结论。学界一般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别将前者作为法益保护义务,将后者作为犯罪阻止义务,来加以探讨。①有关两种义务的内容,参见神山敏雄:《不作為をめぐる共犯論》,成文堂1994年版,第424页;等等。需要确认的是:这里毕竟只是基于推导出作为义务的根据来区别二者,而非是基于具体内容本身的区别。也就是,虽说是法益保护义务,这里赋予的义务是,通过言语或者行动实际作用于正犯Y,进而通过阻止Y的暴力而保护B的法益,在此意义上,作为义务的具体内容是,基于“阻止犯罪”的“保护法益”。②反之,例如,在Y正要开始对B实施暴力之际,如果X带着B逃离现场是有可能的,那么,构成作为义务(法益保护义务)的内容,就有可能会要求X采取这种措施。这样,作为法益保护义务的具体内容,不是作用于正犯,而是以针对被害法益的直接保护作为问题的情形,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但是,法益保护义务的具体内容并非仅限于这种应对措施,这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总的来说,区别的意义就在于,明确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究竟是求之于X与B之间的关系,还是基于X与Y之间的关系。③也就是,按照桥爪隆教授的观点,之所以要做如此区分,就在于明确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究竟取决于行为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行为人(被告人)与正犯之间的关系。依据前者产生的是法益保护义务,依据后者产生的则是犯罪阻止义务。——译者注
那么,在什么范围之内能认定这种犯罪阻止义务呢?④详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2·完)》,载《立教法学》第65号(2004年),第266页以下。对此,应该这样来理解:人,是一种依据自己的判断自律地、主体地进行活动的生灵,因此,是否存在介入到他人(正犯)的意思决定,为让其不实施犯罪而向其做工作的义务,就应该进行极其限定性的理解。为此,即便犯罪人的同事、朋友偶尔也在犯罪现场,面临犯罪人正要实施犯罪的场景,也不应认定该同事、朋友存在阻止犯罪的义务。进一步而言,即便是夫妻之间,也并不存在相互监视不让对方实施犯罪的义务,因而对于这种情形,也应该否定存在犯罪阻止义务。⑤关于这一点,参见西岡正樹:《不作為による幇助に関する一考察》,载《法学》第75卷第6号(2012年),第158页。当然,在丈夫试图虐待小孩的场合,妻子有时候会被科处阻止该行为的义务,但那是从“法益保护义务”的角度所科处的义务。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2·完)》,载《立教法学》第65号(2004年),第271页。进一步而言,如果虽知晓丈夫的暴力的决意,仍接受这一点并表示支持态度的,妻子是有成立作为的共犯的余地的,但这也与是否存在“犯罪阻止义务”无关。相反,例如,对于处于应保护或者监视无责任能力者这一地位的人,就应该理解为,正如该人自己不侵害第三者的法益那样,负有(阻止该无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的)犯罪阻止义务。在该场合下,作为义务人很多时候被作为“不作为的间接正犯”受到处罚。⑥有关父母是否负有阻止属于刑事未成年人的小孩实施犯罪的义务这一问题,如果小孩处于欠缺识辨能力的年龄阶段,则能认定存在犯罪阻止义务,但如果已经达到了实质上能够充分地进行主体判断的年龄阶段,否定犯罪阻止义务这种理解,也是完全有可能成立的。有关这一点的探讨,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2·完)》,载《立教法学》第65号(2004年),第268页以下。
有关该问题,前述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11年〔1999年〕判决的做法是:首先判断“既然和我没关系,那行!”这一表态不属于作为的帮助,在此基础上,再从法益保护义务、犯罪阻止义务这两点探讨,A游戏中心的店长X是否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的问题。首先,就法益保护义务而言,X参与了A游戏中心的整个业务,作为其中的一环,“承担着将店铺的营业款保管在保险箱内,并每隔一定时间将营业款上交给总部的职责”,但其职责范围仅止于将营业款从A店的保险箱运至(同属于一个经营主体的)B弹子店的保险箱,此后,从B店的保险箱回收营业款运至总部的行为,就已经不属于X的职权范围,因而应否定X负有针对本案营业款的法益保护义务。⑦另外,本判决继续做出了下述旨趣的判断:本案受害钱款完全是B点的营业款,A店的营业款不在其中,因而也应否定X负有针对受害营业款的法益保护义务。但是,如果运送至总部原本就与X的职责无关,那么,即便受害钱款中包含有A店的营业款,仅凭这一点,也不应认定X成立不作为犯。
再者,有关从X作为店长的地位是否负有阻止Y的犯罪行为的义务这一问题,判例也是以下面两点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犯罪阻止义务:(1)X虽说是店长,但负责的是A店的店面业务,“除了这种业务之外,并未承担诸如监督、管理其他工作人员的人事管理上的职责”,为此,本判决以“并未特别负有监督被告人Y的行为、工作态度的职责”为由,否定X负有犯罪阻止义务。并且,(2)即便是基于“作为职员的一般地位”而赋予其作为义务,但那“限于将要实施犯罪是切实且显然的情形”,本判决以不属于这种情形为由而否定存在犯罪阻止义务,进而判定X无罪。如前所述,判决否定X负有阻止同事Y的抢劫行为的义务,这一结论本身是妥当的。不过,如果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11年〔1999年〕判决的旨趣是,倘若X作为店长处于管理职员的行为、工作态度的地位,就应被科以犯罪阻止义务,则并不妥当。上司负有阻止部下的犯罪行为的义务,这应该是限于事关公司业务的情形。并且,在该情形下,原本只要讨论是否存在保护公司财产的义务即可。而且,有关第(2)点,所谓实施犯罪的切实性(即便是虽然没有这种事实,但原本也存在加重所科以的作为义务的程度的余地),对于那些原本就不负有作为义务的人来说,这也并不会成为另外科以作为义务的根据。
反之,对于公务员等在一定状况之下负有阻止犯罪的职务上的义务的场合,就存在基于职务上的地位的作为义务,而赋予其阻止犯罪的义务的余地。其中,最典型的情形就是警察的犯罪防止义务。并且,岛田聪一郎教授是将危险创造行为当作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来理解的,他基于这种立场认为,诸如事前作用于正犯的意思而诱发正犯的犯罪决意的情形那样,对于此类以正犯的意思为中介而间接地创造危险的情形,也应认定存在作为义务(犯罪阻止义务)。①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2·完)》,载《立教法学》第65号(2004年),第262页以下。虽然这种理解是妥当的,但如果连正犯只是偶尔被诱发犯意的情形也要科以作为义务,就显然不妥当了,还是有必要限于那些诱发犯意之盖然性很高的情形。②也就是,作用于正犯意思的行为诱发正犯产生犯意的盖然性很高。——译者注
(三)因果性
对于帮助犯中的因果关系,一般认为,不要求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只要存在通过帮助行为物理地或者心理地促进正犯实现构成要件这一关系即可。③参见大判大正2年〔1990年〕7月9日刑录19辑771页、东京高判平成2年〔1990年〕2月21日判タ733号232页;等等。对于共同正犯来说,基本上也是如此:由于是由数人的参与共同引起了构成要件该当事实,因此,特别是按照广泛承认共谋共同正犯的判例、通说的立场,不要求各个共同正犯的参与均与结果引起之间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而是只要存在通过共谋而强化相互的犯意,进而促进结果的发生这种关系即可。
对于不作为的共犯,也应该原样适用这种一般论。④关于这一点,参见町野朔:《『釧路せっかん死事件』について》,载《三井誠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有斐閣2012年版,第310页以下;濱田新:《不作為による幇助の因果関係について》,载《法学政治学論究》第104号(2015年),第199页以下;等等。作为采取这种理解的判例,参见名古屋高判平成17年〔2005年〕11月7日高检速报716号。也就是,(1)只要对正犯实现构成要件予以了促进或者强化即可,(2)不必达到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的程度。并且,所谓能认定“由不作为促进了构成要件的实现”,是要求存在这种关系:与不存在不作为的参与的情形(即,履行作为义务的情形)相比,因为存在不作为的参与(即,没有阻止正犯行为),正犯实现构成要件变得更为容易。因此,反过来说,也就是要求存在这样的关系:可以谓之为,如果履行了作为义务,会使得正犯实现构成要件更为困难(即,存在正犯行为被阻止的可能性)。相反,既然不要求结果避免可能性,那么,也就不必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履行了作为义务(即,没有采取“不作为”这种行为方式),原本是能够切实地阻止正犯引起结果的。
关于这一点,前述札幌高等裁判所平成12年〔2000年〕判决认为,不需要存在“尽管原本是几乎可以切实地阻止犯罪的实行,却放任不管”这种关系,⑤原判决(釧路地判平成11年〔1999年〕2月12日判时1675号148页)虽要求存在这种关系,但以难以要求行为人采取存在避免结果可能性的措施(挺身而出阻止暴力的行为)为理由,判定被告人无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例如,X“即便只是接近Y的身边予以监视,也可以认为,对Y而言,会从心理上抑制其对B实施暴力,因而该行为原本是有可能阻止Y的暴力的”,而且,即便采取的是通过语言来制止暴力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可能阻止Y的暴力的”,从而以“被告人的上述不作为的结果是,与存在被告人的制止或者监视行为的情形相比,无疑使得Y更为容易实施针对B的暴力”为理由,判定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由此可见,判例的旨趣是:不要求存在原本能够切实地避免结果这种关系,而是只要存在“若履行作为义务,避免结果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盖然性的”这种关系,①“原本是有可能阻止Y的暴力的”这一表述,其旨趣不是指能认定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而是指原本存在阻止暴力的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盖然性)。由于“可能性”这种表述有多种含义,稍微有些难以理解,但区分“结果避免的切实性”与“能够避免结果的盖然性”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参见斎藤信治:《不真正不作為犯と作為義務の統一的根拠その他》,载《法学新報》第112卷11=12号〔2006年〕,第295页以下)。不作为以及过失犯的单独正犯中所要求的结果避免“可能性”,就完全是前者的意思。就能由此认定存在由不作为而促进了结果发生这种关系,进而满足了因果性要件。可以说,这种判断是妥当的。
(四)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的区别
因负有作为义务的人的不作为,使作为的正犯得以更容易地引起结果的,就能够将该人作为“不作为的(广义的)共犯”予以处罚。下面的问题是,如何区别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与帮助犯。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下述三种观点:(1)原则上成立正犯;(2)原则上评价为帮助犯;(3)根据义务的具体内容分别认定。②有关学说的详情,参见神山敏雄:《不作為をめぐる共犯論》,成文堂1994年版,第424页;中義勝:《不作為による共犯》,载中義勝:《刑法上の諸問題》,関西大学出版部1991年版,第330页以下;内海朋子:《不作為の幇助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载《法学政治学論及》第56号(2003年),第1页以下;山中敬一:《不作為犯の正犯と共犯》,载《川端博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成文堂2014年版,第663页以下;等等。如前所述,对此应该这样理解:只要适用作为犯罪中的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的区别标准即可,这里基本上不存在不作为犯本身所特有的问题。
首先,作为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的区别标准,是否存在重要的因果性贡献是很重要的。“原则帮助说”认为,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作为的实行正犯直接引起了结果,不作为的参与者仅仅止于以不阻止这种形式消极地参与,因此,其因果性贡献并不重要(即,并未作出重要的因果性贡献),因而应评价为帮助犯。这种观点也是现在的多数说。③例如,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362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432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433页以下;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1)》,载《立教法学》第64号(2003年),第57页以下;等等。不过,不作为的参与的因果性影响是有限的,这种解释未必有充分的合理性。其一,即便是作为的共犯关系,虽然可以说,例如,准备凶器或者负责望风等的人的参与,与负责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实行行为)的人的参与相比,影响力要小,不过是第二性的参与,但也并非是说,因为如此,所以不承担实行行为的参与者总是被评价为帮助犯。在承认共谋共同正犯的判例、通说的立场之下,即便没有直接引起结果,也仍然有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其二,要判断不作为的参与的因果性贡献的重要性,就有必要考虑到与没有采取不作为这种行为的情形相比,不作为的参与多大程度上使得结果发生更为容易。④持这种理解者,参见齊藤彰子:《作為正犯者による犯罪実現過程への不作為による関与について》,载川端博等编:《理論刑法学の探求⑧》,成文堂2015年版,第56页以下;小林憲太郎:《不作為による関与》,载《判例時報》第2249号(2015年),第8页;等等。为此,对于那些如果履行了作为义务,阻止正犯的犯罪行为原本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情形,就完全有可能评价为,不作为的因果性参与是很重要的。⑤另外,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在原本能够切实地避免结果发生的场合,应认定成立不作为的单独正犯(同时犯),但是,也并非是只要存在重要的因果性贡献,就直接为单独正犯奠定了根据(参见西田典之:《共犯理論の展開》,成文堂2010年版,第154页以下)。勿宁说,这种理解实质上应该被定位于,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的区别标准。
不过,要成立共同正犯,除了因果性贡献的重要性之外,还应该要求参与者之间的一体性或者共同性。⑥详见橋爪隆:《共謀の意義(2)》,载《法学教室》第413号(2015年),第97页以下(译文参见桥爪隆:《共谋的意义》,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第124页以下。——译者注)。判例、多数说主张,要成立共同正犯,参与者之间的意思沟通是必不可少的,进而否定片面的共同正犯,就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共同正犯之间是否总是以意思联络为必要,尽管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仅凭没有制止作为形式的犯罪行为这一点而言,还难以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密切的共同性,因此,对于那些不作为的参与成为问题的情形,原则上还是应该以存在意思联络为必要。但是,当事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由此给予了实行担当者的心理以重要影响的,对不作为的参与者而言,原本就应该是作为通过某种言行或者态度(即,作为)而达成了共谋的情形来看待,因而几乎都是被评价为作为的共同正犯。①西田典之教授将这种理解贯彻到底,主张不作为的共犯仅限于(不能认定存在意思联络的)片面的共犯,参见西田典之:《共犯理論の展開》,成文堂2010年版,第137页。因此,对于那些能认定与实行担当者之间存在意思联络的人,应将其评价为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仅限于极其例外的情形,例如,虽能认定存在意思联络,但不能抽象到某种身体的“动”的情形。作为结论来说,对于不作为的参与,原则上应该是认定成立帮助犯,其理由与其说是因果性影响不够,倒不如说是在满足了一体性或者共同性要件的场合,基本上都会成立作为形式的共谋共同正犯。
(五)单独正犯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负有保护自己的小孩B之生命、身体这种作为义务的X女,没有阻止与自己处于姘居关系的Y男针对B的暴力,对于X女的这一行为(不作为),前述札幌高等裁判所平成12年〔2000年〕判决判定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犯。在本案事实关系中,由于Y男针对A、B的责打行为一直在持续实施,因而对于X女、Y男居住的公寓,并非不可能评价为:对A、B而言,是隐含着针对其生命、身体之危险性的场所。按照这种理解,对于X女,就有认定为负保护责任者犯不保护致死罪的单独正犯的余地。②提出这种可能性的学者,参见平山幹子:《不作為犯と正犯原理》,成文堂2005年版,第185页以下;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74页;等等。例如,在放养有凶猛的大型犬类的居民小区,对幼童放任不管的行为,就正属于将被害人置于危险场所的行为,就有可能该当于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问题在于,能否将受到Y的责打的紧迫的危险,等同视为遭受大型犬类袭击的危险?如后所述,尽管仍有慎重探讨的余地,但本文认为,不应该将两个案件等而视之,难以将X女评价为保护责任者不保护致死罪的单独正犯。这是因为,在存在遭受大型犬类侵害之虞的场合,不存在人的行为介入其中,X女的放任不管的行为会直接产生危险状况;相反,虽说是遭受Y男责打的危险,但那最终仍然属于,经过Y男自由意思决定的,始有可能产生的危险,换言之,不过是所谓间接的危险。如果重视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有这样理解的余地:仅限于前者意义上的直接的危险的实现,才属于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的处罚对象。例如,猛犬就要撕咬自己的小孩之际,对此放任不管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杀人罪的正犯;但在第三者就要杀害自己的小孩之际,对此不予阻止的行为,则只是构成不作为的帮助。换言之,根据是否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有责的行为,对于其背后的不作为,法律评价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因此,在Y男结束针对B的暴力并离开现场之后,如果X女马上将B送往医院让其接受紧急治疗,原本是能够切实地挽救B的生命的,尽管如此,X女却对B放任不管的,如果是这种情形,X女就要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或者不作为的杀人罪的单独正犯。这是因为,在该场合下,X女负有的作为义务的内容就是,避免直接的死亡结果这种危险的发生,而且,在X女的不作为与死亡结果的发生之间,也并没有介入第三者的行为。③参见曽根威彦:《不作為犯と共同正犯》,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1)》,成文堂2006年版,第414页;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1)》,载《立教法学》第64号(2003年),第51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433页;等等。反之,佐伯仁志教授则认为,在“在环视整个因果进程,仅止于第二性的贡献”的场合,对于这种情况,也要认定成立帮助犯,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433页。不过,对于正犯的实行行为结束之后的参与,是否也有认定成立狭义的共犯的余地,就属于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性问题。而且,松尾诚纪基于限制不作为犯处罚的立场,对于作为犯的犯罪结束之后再参与的不作为,主张原则上应否定成立犯罪,参见松尾誠紀:《作為犯に対して介在する不作為犯(6·完)》,载《北大法学論集》第58卷第4号〔2007年〕,第3页以下。
不过,也有个别犯罪将阻止第三者的犯罪行为本身纳入到单独正犯的犯罪构成的内容之中的情形。例如,被告人是弹子店(Pachinko)的职员,按照其职责,有制止顾客的不当游戏行为的必要,但明明看见有顾客身上佩戴体感器实施不当的游戏行为,却有意视而不见的,该行为是否构成针对盗窃行为的不作为的帮助就成为问题。①这里以承认片面的帮助为前提。故意对顾客利用体感器进行游戏的行为视而不见,恰恰属于违背弹子店的职员的任务的行为,如果由此给弹子店造成了财产性损失,对于职员而言,就有成立背信罪的单独正犯的可能性。②在该场合下,背信罪的单独正犯与盗窃罪的帮助犯,是针对同一行为的不同法律评价,因此,处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也就是,作为对背信罪中事务处理者被科以的“任务”的解释,加入了阻止他人的犯罪行为的义务,由此就会将正常情况下作为共犯处理的行为,转而作为独立的正犯行为来评价。③参见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74页。按照这种观点,作为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等中的保护责任的内容,加入了阻止他人的暴力等行为的义务,对于上述问题,毋宁说,会出现成立保护责任者不保护致死罪的余地。④关于这一点,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1)》,载《立教法学》第64号(2003年),第46页以下。这原本属于应该交由具体犯罪的各论性解释的问题,更有必要慎重对待。
(六)近年的判例
在近年的判例中,对于针对作为犯的不作为形式的参与,也有判定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案件,颇引人注目。下面想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判例,简单做些探讨。
1.东京高判平成20年〔2008年〕6月11日判タ1291号306页
本案被告人与其长子A(4岁)、次子B(3岁)一家三口共同生活,在2月的某一天,被告人对B实施暴力,并且,在B的下半身处于赤裸的状态下,将其赶出屋外大约1个小时。其后,当时与被告人处于恋爱关系的X来访,由于X显示了要参与此事的态度,⑤在此之前,对于被告人给小孩做规矩的行为,X经常插嘴,尤其是,还号称是做规矩,而经常对B实施暴力。被告人于是对X说,“不要动手!”在听到X说“不会打脸”之后,就没有再说什么,而走向了同一房间的厨房的水池边。此后,X对B实施了将其后脑勺撞地等暴力行为,结果致B死亡。其间,被告人并未制止X的暴力。对此,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20年〔2008年〕判决认为:“应该说,被告人负有积极地阻止他人实施进一步的暴力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判决:“能够认定,在本案当时,对于X针对B的暴力,被告人没有加以制止而是容忍了这种行为,因此,被告人的责任不是止于帮助犯,而应该是相当于不作为的正犯。并且,还能认定,在被告人谅解了X的‘不会打脸’这一说法的时点,存在X的作为犯与被告人的不作为犯之间的意思联络,亦即,存在共谋”,最终判定被告人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
本案被告人是B的母亲,并且,也是被告人将此前曾对B实施过暴力的X迎入自己家中,因此,被告人显然被赋予了保护B的作为义务。为此,如果是将被告人作为“不作为的帮助”来处罚,想必不会有任何异议。但问题在于,东京高等裁判所将被告人评价为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根据何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⑥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同正犯》,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29号(2011年),第45页。被告人容忍X的暴力这一情况,不过是认定故意的根据,但这并不能成为直接推导出共同正犯性的理由。在这一点上,本判决认定“在被告人谅解了X的‘不会打脸’这一说法的时点”,X与被告人之间就已经成立共谋。这一认定意味着,“不会打脸”这一说法包含着会打脸之外的其他地方这一旨趣,能够说,包括这一旨趣在内,被告人谅解并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在该时点就成立了针对暴力的意思联络。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X向B施加暴力的行为,被告人完全是给予了谅解,并持续显示了默认的态度,毋宁说,是有成立作为形式的共谋共同正犯的余地的。⑦指出这一点者,参见中森喜彦:《不作為による共同正犯》,载《近畿大学法科大学院論集》第7号(2011年),第126页以下。
尽管如此,本判决仍然是判定被告人构成不作为犯的共同正犯。作为一种推测,如果在本案中,认定被告人与X之间存在基于作为的意思联络,由于被告人并非是在现场认同X的犯罪行为,对于X的犯罪行为所给予的心理性因果性未必充分,因而仅凭这一点,也许可以说,其影响力尚未达到足以为正犯性奠定基础的程度。为此,判例也许是试图通过下述两点来认定,存在足以为正犯性奠定基础的重要的因果性贡献:(1)以通过作为形式的参与能认定存在意思联络为前提;(2)不仅仅是作为形式的参与所形成的心理上的影响,还包括作为不作为犯的参与的影响力在内。对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谓之为一定的参与行为的表里两面,因此,在评价作为义务者的参与的因果性影响之际,通过将各个侧面的影响力合算(累加)在一起,就完全有可能以此为基础,认定存在重大的因果性贡献。①持这种理解者,参见西田典之等编:《注釈刑法(1)》,有斐閣2010年版,第930页〔嶋矢貴之〕;村越一浩:《不作為の共同正犯·幇助》,载池田修、杉田宗久编:《新実例刑法(総論)》,青林書院2014年版,第375页。如果采取这种理论,对于本判决认定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结论,就有予以支持的余地。②另外,对于那些综合考虑了作为形式的参与与不作为形式的参与的共同正犯,是否还应该称之为“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也许还有探讨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参见萩野貴史:《判批》,载《獨協ロー·ジャーナル》第7号(2012年),第192页。
2.东京高判平成20年〔2008年〕10月6日判タ1309号292页
X(17岁)与朋友Y一道,向玩伴A等6人说,Z突然向X提出了性要求,为此感到不快的A等人于是将Z叫了出来,由于X还说其已经受到了Z的强奸,A等人更加愤慨,对Z实施了猛烈的暴力,并致Z昏倒。此后,A等人释放了Z,但随后由于担心Z会报警,打算直接杀死Z,遂又将Z叫回来,并命令Z的学长将Z杀害。对此,原判决认为,X、Y在还残留有针对暴力的相互之间的意思联络、协助关系的状态下,参与有关杀害Z的谋议,实施了将Z运至现场等重要的前提行为,进而以此为理由判定成立杀人罪的共谋共同正犯。相反,对于本案,相较于凭借相对稀薄的内容来认定现场共谋,东京高等裁判所基于下述理由,对于通过先行行为而创造了针对Z的暴力并直至杀害Z的原因的X、Y,以存在通过说明真实情况以阻止A等人的犯罪行为的义务为理由,认定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对于同行至现场,没有实施实行行为的人而言,要追究其作为共同正犯的责任,在探讨其是否成立不作为犯,且能够认定其成立不作为犯的场合,应该说,(直接)认定其成立基于与其他作为犯之间的意思联络的共同正犯,有时候要更符合案情。”
对于本案,正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原本就已经在现场达成了有关杀害行为的谋议,因此,有成为“作为的参与”而认定成立共谋共同正犯的余地。③④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第2版)》,弘文堂2010年版,第357页;等等。不过,也许东京高等裁判所考虑的是,在本案中,即便认定存在现场共谋,但那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者跟着集体行事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⑤指出这一点者,参见齊藤彰子:《作為正犯者の犯罪行為を阻止しなかった者の刑責》,载《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249号(2013年),第237页;小林憲太郎:《不作為による関与》,载《判例時報》第2249号(2015年),第12页;等等。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在这种前提之下,该判决实际上探讨的是,是否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问题。正如上一个判例(东京高判平成20年〔2008年〕)也提到的那样,对于能认定由作为形成的意思联络的案件,在作为形式的贡献所形成的影响力未必充分的场合,通过将具有作为义务的人的不作为所形成的影响力“合算(累加)”在一起,进而肯定共同正犯性,按照这种逻辑,也是有可能将本案结论予以正当化的。不过,虽然有点深入到了事实认定的问题,但也有观点指出,具体就本案案情而言,原本来说,即便X在现场讲了真话,由此阻止A等人的杀人计划的可能性也是极低的。①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同正犯》,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29号(2011年),第47页;小林憲太郎:《不作為による関与》,载《判例時報》第2249号(2015年),第12页以下;等等。并且,对于原本是否存在义务这一点,中森喜彦教授也提出了疑问,参见中森喜彦:《不作為による共同正犯》,载《近畿大学法科大学院論集》第7号(2011年),第126页以下。关于这一点,如前所述(正文的三之〔二〕的2“犯罪阻止义务”),重要的是,要判断X、Y的先行行为以及对于暴力的参与,是否足以诱发A等人针对V的杀人犯意。如果本案属于那样的案件,虽说是由X等的不作为的参与所形成的影响,但由于那种影响尚不具有足以为正犯性奠定基础(即便与作为的内容“合算(累加)”在一起),②不过,本判决的判断是:如果X讲了实情,A等人就失去了继续对Z实施暴力乃至杀害的理由,因而不会发展至杀害Z。并且,在本文看来,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对于X、Y,就是作为不作为犯,也能认定其做出了重要的因果性贡献。因此,按照这种前提,对于本案,就会推导出这样的评价:重视参与了现场的谋议这一事实(作为),由该事实本身认定为作为的共同正犯;或者,以X、Y的因果性贡献并不大为理由,仅止于成立作为的帮助犯。
四、不作为的共同正犯
一般认为,负有作为义务的数人在意思联络之下,没有一人履行作为义务,最终发生了结果的,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例如,X男与Y女是夫妻关系,与幼子A等三人一同生活,X男与Y女经过意思沟通,不给A食物,结果致A死亡的,对于X男与Y女,就要认定成立杀人罪的不作为的共同正犯。
在该案的场合,无论是X男还是Y女,不与对方共同实施,自己单独也能够履行保护A的义务。出于这种考虑,有观点主张,该案中的X男、Y女不过是不作为的单独正犯的同时犯,要认定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还必须存在这样的关系:如果全体参与者不共同履行义务,就不能避免结果的发生。③参见神山敏雄:《不作為をめぐる共犯論》,1994年版,第326页以下;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73页;金子博:《不作為犯の共同正犯(2·完)》,载《立命館法学》第347号(2013年),第193页以下;等等。的确,对于该案中的X男、Y女来说,即便不适用共同正犯的相关规定,也完全有可能分别作为单独正犯予以处罚。不过,作为的共同正犯中也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例如,P经过与Q的共谋,由P单独实施了实行行为的场合,尽管P本身具备作为单独正犯予以处罚的实质,但一般的做法仍然是,将P与Q作为共同正犯予以处罚。也就是,即便是也有可能作为单独正犯予以处罚者,如果能认定存在与他人协同引起了结果这种关系,就应该将这种关系反映于法律评价之中,作为共同正犯予以评价。④持这种理解者,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478页;奥村正雄:《犯罪の不阻止と共同正犯》,载《川端博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650页;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同正犯》,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29号(2011年),第38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432页;等等。另外,齊藤彰子认为,在数名作为义务者之中,如果存在能够单独避免结果者,以及只有作用于其他作为义务者才能够避免结果者,那么,只有前者才是正犯,后者仅承担(狭义的)共犯的罪责,参见齊藤彰子:《不作為の共同正犯(2·完)》,载《法学論叢》第149卷5号(2001年),第38页以下。本文以为,如果以这种理解为前提,对于该案中的X、Y,也完全有可能作为“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予以处理。⑤反之,在当事人之间缺少意思联络的场合,就可以作为“不作为的同时犯”来评价。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434页。
相反,例如,在该案中,(在X男长期出差期间)Y女的朋友Z来到Y家,Y女与Z经过意思联络,不给A食物,结果致A死亡的,又该如何处理呢?⑥这里是想以Z并未被科以保护A之生命的作为义务为前提。这样,在负有作为义务者与不负有作为义务者共同实施了所谓不作为的,对于不负有作为义务者,想必不能将其作为“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予以处罚。这是因为,对于不负有作为义务者,我们不能赋予其作为的义务,并以其不作为这种行为作为处罚的对象。⑦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同正犯》,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29号(2011年),第40页。当然,如果Z对Y女说“A死了也没什么”“不必给他食物”等,由此通过给Y做工作而强化了其犯意的,则另当别论。如后所述(“五、针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共犯”),这种情形下的Z,就不是作为不作为犯,而应当作以作为的形式作用于不作为犯的人而受到处罚。
五、针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共犯
在上述案件中,如果Z教唆Y女不要给A食物,或者给Y女做工作,促进、强化了其犯意,那么,如前所述,问题就在于,Z是否成立针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共犯”?对于这种作为形式的共犯,即便该人没有作为义务,也能作为共犯予以处罚。这是因为,参与者毕竟是通过作为的形式参与了犯罪,处罚该人并不一定要求其负有作为义务;而且,不负有作为义务者,也可以通过对负有作为义务者的不作为施加因果性,间接地引起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这种实质性考虑的根据就在于:通过将作为义务理解为违法身份(《刑法》第65条第1款),连带地适用身份,由此认定成立身份犯的共犯。①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361页。
有关针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参与,不管是否存在作为义务,都能够处罚行为人,但如果行为人的参与形态是不作为,原本来说,只要不能认定该参与者个人负有作为义务,就不能将其作为不作为犯予以处罚。这是当然之理,这里再次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