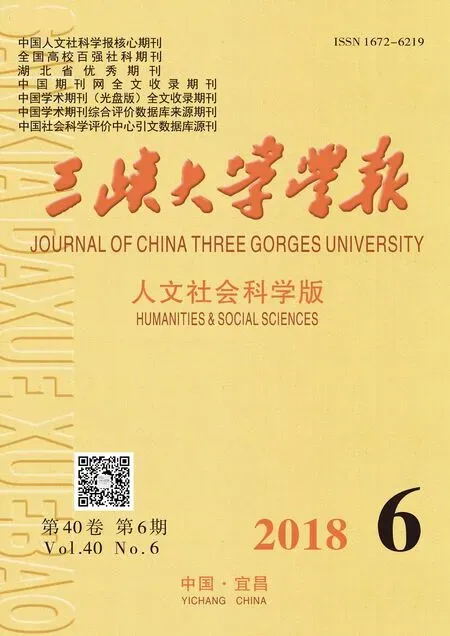是丰碑,不是分水岭
——论韩愈墓志在唐代碑志发展中的地位
2018-01-31高玮
高 玮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一
韩愈是有唐一代著名的文学大家,特别是在古文革新方面功绩卓著,与柳宗元一道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一生志于恢复儒家之道,既从理论上大力倡导古文,又从实践上全力从事古文创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风的转变和文体的改革。北宋学者姚铉对其贡献予以高度评价:“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辚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1]在韩愈的散文创作中,碑志文是其最为重要的类型之一,共有76篇,其中大部分为墓志铭,其成就亦被推为韩文之首。
墓志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学样式,春秋是其发轫期,经过战国至东晋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南北朝时期这一文体渐趋成熟,和其他文体相比,墓志铭最终凝定成自己独立的格式和独特的风格。至唐代,墓志铭的写作便成为文人的一种风尚,杜佑《通典·开元礼纂类·凶六》有“去灵车,后次方相车,次志石车,次大棺车……”[2]的记载,证明李唐王朝已将墓志列入礼制,作为丧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志铭受到朝野的高度重视。从历史上看,墓志铭的写作形式比较固定,钱钟书在评价庾信时就论述道:“按信集中铭幽谀墓,居其太半;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虽按其题,各人自具姓名,而观其文,通套莫分彼此。惟男之与女,扑朔迷离,文之与武,貂蝉兜牟,尚易辨别而已。斯如宋以后科举应酬文字所谓‘活套’,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也。”[3]从整体风貌看,唐代墓志铭和此前的作品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从写作形式上看,呈现出“因循旧制”、“发展缓慢”的总体特征。根据笔者的梳理总结,唐代墓志最基本的要素为:讳、字、籍贯、家族溯源、世系、履历、卒年、卒地、年龄、妻(子)、亲友之悲、葬地等,且书写之次序亦大致如是。而从内容的撰写上,也给人以千人一面、谀墓成风的感觉,虽间或出现如陈子昂、张说等有些创新的墓志,但偶一为之的力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整体创作的“程式化”倾向。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韩愈的墓志创作以其大胆而多方面的改变让当时文坛为之侧目。其墓志铭除了具备一些此类文体必备的内容要素外,完全打破常规,与传统写法相比,韩愈行文结构的重新编排、文风的自如挥洒、题目摆脱对官阶罗列的窠臼、纵情的议论与抒情、形式不拘一格的铭文等等,这些改变,极大地丰富了墓志铭的表现形式,并在艺术上体现巨大的创新。宋人楼昉《崇古文诀评》赞其曰:“退之所作墓志最多,篇篇各有体制,未尝相袭。”[4]充分肯定了其在墓志写作方面的创新成就。
韩愈墓志的创新,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散体写作。韩愈墓志的创作,体现了其“古文运动”的理念,全部采用散体古文写作;即使是露于地面更加重视格式法度的神道碑,韩愈也使用散体进行创作。如《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许国公赠太尉韩公神道碑铭》:
公少依舅氏,读书习骑射,事亲教谨,侃侃自将,不纵为子弟华靡遨放事。出入敬恭,军中皆目之。尝一抵京师,就明经试。退曰:“此不足发名成业。”复去从舅氏学,将兵数百人,悉识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叹奇之。士卒属心,诸老将皆自以为不及。司徒卒,去为宋南城将。比六七岁,汴军连乱不定。贞元十五年,刘逸淮死,军中皆曰:“此军司徒所树,必择其骨肉为士卒所慕赖者付之,今见在人莫如韩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请命于天子。天子以为然。[5]502
整个铭文完全采用散体文方式,对墓主的家世、生平、功绩进行描写,给人以亲切朴实之感。
第二,对固化的创作程式和叙事模式的解构。传统墓志在写法上基本形成一种固化的格式:首先介绍志主的名讳;然后详细叙述其家世出身;之后才开始描述志主的生平事迹。但韩愈的墓志则将重点放在对志主的描写上,且在顺序上灵活而不拘泥。《施先生墓志铭》便是如此:先云“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由四门助教为太学助教,由助教为博士;太学秩满当去,诸生辄拜疏乞留。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等,详述了志主在太学的执教经历;然后介绍家世,“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豪州定远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贸阝县主簿;曰友谅,太庙斋郎。”在作者看来,志主在太学的执教经历才是体现其性格和人生价值的重要事件,故而不惜改变叙述重心和顺序。同样的变化还在《贞曜先生墓志铭》《孔君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作品中表现出来。
第三,以小说家笔法和戏剧化冲突塑造人物。在叙述志主的事迹时,韩愈打破传统墓志平铺直叙的方式,借鉴小说的某些手法,将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融入墓志铭,这样便有效改变了传统墓志的平庸面目,使人读之兴趣盎然,颇有波澜起伏之感。这一手法的运用在韩愈的数墓志铭中频繁出现,形成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如《孔公墓志铭》:
吏部侍郎韩愈常贤其能,谓曰:“公尚壮,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为左丞,不能进退郎官,惟相之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于乡者,将自佚,非自苦:闾井田宅具在,亲戚之不仕与倦而归者,不在东阡在北陌,可杖履来往也。令异于是,公谁与居?且公虽贵而无留资,何恃而归?”曰:“吾负二宜去,尚奚顾子言?”愈面叹曰:“公于是乎贤远于人!”[5]528
通过韩愈与志主对话的描写,凸显志主之贤德,使读者如临其境,亲眼所见,十分亲切。
再如《太原王公神道碑》《柳子厚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多篇墓志铭均体现了这一特色。
第四,铭文格式的创新。韩愈墓志铭中的铭文部分,除传统的三言、四言格式以外,还根据创作的需求采用了许多新的格式。试看《柳子厚墓志铭》的铭文部分:“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居然以一句话的形式平淡地道出柳子厚之墓的特质,而这样的平淡跟墓志铭通篇夹叙夹议精彩绝伦的写法形成对比,却也正好体现出柳宗元绚烂一生终究归于平淡的感觉。再如《郑君墓志铭》:“再鸣以文进涂辟,佐三府治蔼厥迹。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浑朴绝瑕滴。甲子一终返元宅。”以七言古诗的格式铭之;《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后缗窦逃闵腹子,夏以再家窦为氏。圣愕旋河犊引比,相婴拨汉纳孔轨。后去观津,而家平陵。遥遥厥绪,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怀其德。作诗孔哀,质于幽刻。”将七言与四言相结合。由此可以看出,韩愈在创作铭文时完全根据自己的表达需求,选择不同的铭文格式,较少受到传统格式的束缚。
二
韩愈墓志的“新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当时社会就赢得广泛的赞誉和热烈的追捧。同时代的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道出韩愈碑志文当时受欢迎的盛况:“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6]韩愈自己所创作的《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中也描写过这样的场面:“其子逞、迺、巡、遇、述、迁、造与公婿广文博士吴郡张籍,以公之族出、行治、历官、寿年为书,使人自京师南走八千里,至闽南两越之界上请为公铭刻之墓碑于潮州刺史韩愈……”[7]由此可见其文名之盛,实令人叹为观止。
而后世对韩愈墓志铭的赞叹也从未终止过。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文章宗旨》中赞道:“碑文惟韩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决不再行蹈袭。”清人储欣于《唐宋八大家类选》中称“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胡念修《四家纂文叙录汇编序》中言“封墓之文……唐贤既兴,首推昌黎”。直到近年来,学术界多认定韩愈在墓志铭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进一步认为韩愈开创了墓志铭发展的新时代,对后世墓志铭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如有研究者认为“韩愈碑志文作为这一文体的典范,在接受后人顶礼膜拜的同时,也成了新的模式化创作道路的起点,形成了陈陈相因、不思创新、生搬硬套的公式化创作倾向。韩愈在碑志文领域的改革突破了六朝以来的模式化套路,却未能避免新的模式化倾向出现。所不同者,韩愈之前因袭庾信,韩愈之后因袭韩愈也”[8];或明确提出“在韩愈的垂范和影响下,中唐及以后的墓志撰写少用四、六体骈文,多用散文或者直接用古文”[9];或认为“韩愈碑志文则在汉魏六朝初盛唐碑志文基础上新变:变骈为散,变雅为奇。相对于前代碑志文,韩愈碑志文多新变,而相对于后世碑志文,韩愈碑志文被尊为正体。……而自宋元至于明清的墓志碑铭类作品莫不推崇韩愈,视韩愈碑志文为马首是瞻乃是不争的事实”[10]。《韩愈墓志文研究》也提出:“韩愈墓志文彻底突破了旧有的模式化写作,为后世墓志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而此后的墓志文也开始沿着他所开创的方向发展。”[11]这些研究似乎让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作为唐代碑志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韩愈的墓志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墓志铭新旧两种不同写法的分水岭。情况果真如此吗?
三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曾经说过:“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2]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上,这句话阐述的其实就是“文学发展”的理念,即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综合评价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
一般而言,文学的发展应该包括“顺向发展”和“逆向发展”两个层面,所谓“顺向发展”,谈的是文学的历史继承问题,文学的发展是沿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经验一定会对后代文学产生影响,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而所谓“逆向发展”是关于文学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指的是与时间顺序相反方向的发展,以当代视野观照文化传统,在当代作品中不同程度地隐含或凸现文学传统的精神,从而使传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得以重构。根据这种理论,从“逆向发展”的层面上看,前文所述,韩愈所创作的墓志铭被高度评价乃至于推崇,奉为圭臬,贯穿于整个唐宋元明清时代。如元代学者潘昂霄撰《金石例》十卷,独创以“例”研究金石文字的方法,他所采用的结构方式是“类下设例,以例统文”。卷二至卷五对德政碑、神道碑、墓志、碣、墓碑、行状等25种传记文体的缘起加以考订,并辅以例证,所举例子多出自于中唐作家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卷六至卷八则专为韩愈墓志铭括例。明代学者王行在其《墓铭举例》中曰:“由齐至隋唐诸家文集,传者颇多,然词皆骈偶。惟韩愈始以史传作之,后之文士率祖其体。”[13]其中关于论碑志文的例子,同样也以韩愈所作的碑志文为主,同时兼及唐宋其他作家文集中可作范例的碑志文。书中论碑志文的写作技法亦多采用韩愈的说法,如其论“纲”要“目”便是以韩愈《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为范详加叙述:“盖题为纲,文为目。纲既详之而目则略者,嫌于辞之繁也。其纲举其要而目致其详者,如韩文《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之类是也。”清代有大量志于墓铭例一类的著作,其编著原则无一不尊韩愈为墓志之正,如黄宗羲所作《金石要例》一书,其“称呼例”一条列举韩愈碑志文为例;其“碑志文烦简例”一条中则极口称赞韩愈碑志文“烦简得当”[14]。又如鲍振方《金石订例》在潘苍崖《金石例》和黄宗羲《金石要例》基础上,进一步作了严密详审的考订,其书卷二有小序云:“文章贵先合体,体者例也。昌黎文越八代之衰,义正词严,《金石例》一宗其法。但例之缘起可否,有不尽于昌黎者。”[15]对韩愈墓志作法的典范性给予了充分肯定。王振声在序言中亦云:“自昌黎振起八代之衰,其法流传。”[16]在卷四“金石推例”八十条中,首列韩昌黎二十条,占所列十四家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刘宝楠在《汉石例》中将韩愈碑志文与前代碑志文加以比较,得出“昌黎之功,诚以不细”[17]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韩愈所创作的墓志铭堪称墓志铭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结论应该为学界所公认。
然而,从“横向发展”的层面上来看,是否真如近年来学界研究成果所述,自韩愈墓志之后,墓志的发展就朝着这种“新变”的方向发展下去,韩愈墓志俨然成了墓志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了呢?如前所述,韩愈墓志铭具有散体写作、创作程式和叙事结构的改变、以小说家笔法和戏剧化冲突塑造人物、铭文格式的创新等几个特点。其中,创作程式和叙事结构的改变、铭文格式的创新是与作者自身才力紧密相关的,传承性并不强。但散体写作、以小说家笔法和戏剧化冲突塑造人物等特点均属于具体的形式变化,具备可供传承的特点。因此本文考察韩愈所作墓志铭对中晚唐墓志铭创作的影响,重点考察创作体式及铭文样式,兼及考察人物塑造与结构变化。
按其成就地位的不同,可将墓志铭的作者分为知名作家和一般作者两类。从中晚唐墓志铭创作情况来看,以《唐代墓志汇编》整理的墓志铭为考察对象,较为突出的代表性作家有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翱、元稹、白居易、杜牧、穆员等。此处重点考察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杜牧的墓志铭创作。
柳宗元共创作墓志铭63篇。从体式来看,明显表现出偏爱在写作时使用大量整齐的句式,甚至是骈句。章士钊在评价柳宗元所作《安南都护张公志》时提到:“此张舟志也,全体用骈语,而如文单环王怙力背义云云,竟用七句相对为长联,公患浮海之役可济可覆而无恃云云,且用十句相对,其联更长,此最为桐城派所不喜,然子厚似亦好用其所长过甚,因遭到俭腹者疾首蹙额,理有固然。夫七句联共十四句,十句联共二十句,两共为三十四句,以五字或六字平均计之,当在二百字弱或微强,倘志文不长,则两联已占去全副之半矣,亦自于志体非宜。”[18]同样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在创作墓志铭时却仍遵循常法,几乎不存在韩愈皆以散体写作墓志铭的现象。据统计,柳宗元现存作品中有铭文的墓志计28篇,其中四言20篇,三言6篇,其它2篇。在四言铭文中,超过20句的铭文16篇,超过30句的9篇,而三言铭文有的长达30句,由此可见柳宗元在撰写铭文上体现出固守陈法的传统意识。
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创作墓志铭12篇,在结构布局方面较少变化,通篇采用散体的语言程式,可见韩文及古文运动对其具有深刻影响。但在铭文方面,有9篇都采用了四言的传统形式,并且铭文篇幅均较长,如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子刘子自传》,全篇程式俨然,铭文亦为四言,可见刘禹锡的墓志铭创作观也是较为传统的。
白居易创作墓志铭22篇,采用了散体的语言形式;铭文方面,在秉承四言传统的基础上,也能做到因志人对象的身份特点差异而改变铭文的程式。然而,白居易在人物塑造方面就体现出了明显的传统墓志的写作态度,一味对志主颂扬夸赞,特别是对其官职的叙述不厌其烦,而对墓主一生的行事却吝于着墨,从而造成墓主的形象缺乏鲜明特征。
最后看杜牧的墓志铭创作情况。其现存墓志约14篇,明代学者何孟春在《余冬序录》中云:“朱子尝言,牛僧孺何缘去结得个杜牧之,杜为渠作墓志。今《通鉴》所载维州事,有些好底,皆是墓志。”[19]从中可从侧面反映出杜牧墓志写作的成就。首先,杜牧基本采用散体写作,只因晚唐骈体文风的回归,部分墓志铭呈现出骈散结合的文风,如《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中“公始至任,计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钱,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叠亿计。人能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赋,徐责其直,自载酒食,以勉其劳,初若艰勤,日成月就,不二周岁,凡为瓦屋万四千间,楼四千二百间,县市营厩,名为栋宇,无不创为。泒湖入江,节以斗门,以走暴涨。”[20]3466一段就是骈散结合的典型体现。其次,杜牧非常注重细节描写,并也以戏剧化的手法志人,如《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会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庐,路田钱塘。龚轺袖诗以进士名来谒,时剌史赵郡李播曰:‘龚秀才诗人,兼善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听。及饮酒,颇攻章程,谨雅而和。饮罢,某南去,舟中阅其诗,有山水闲淡之思。后四年,守吴兴,因与进士严恽言及鬼神事,严生曰:‘有进士龚轺,去岁来此,昼坐客馆中,若有二人召轺者,轺命驾甚速,始跨鞍,马惊堕地,折左胫,旬日卒。’余始了然。忆钱塘见轺时,徐徐寻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殡於野,乃命军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严生与轺善,亦不知其乡里源流,故不得记。呜呼!胡为而来二鬼,惊马折胫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岁五月二日记。”[20]3468在这段不足三百字的志文中,出现两处细节描写,一写墓主的个性品德,一写其死因,而两处细节描写各有用处,前者能使人对墓主的品性有所了解,后者为志文带来某种神秘气息,造成文章的波折效果。第三,杜牧的铭文创作变化较多,根据志主的身份特点,选择不同的语言程式撰写铭文等,如《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的铭文“铭曰:古之达人,以生为寄为梦,以死为归为觉,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为大空,与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呜呼!胜之今既归而觉矣,其自知矣,何为而然乎?呜呼哀哉。”[20]3472完全以议论手法入铭文,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慨,可谓别出心裁。第四,杜牧作墓志时,根据墓主本身的特点,先对要如何表现墓主生平加以整体考虑,然后再进行写作方式的选择。如《唐故进士龚招墓志》,基于对墓主事迹了解的有限,作者便重点写所熟悉的事和有关传闻;《唐故款州刺史邢君墓志铭并序》主要表现墓主的治理之才以及与作者的友谊,对其他事情便忽略。这种写法说明,杜牧是在韩愈创新墓志写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以上作家的墓志铭创作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则《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宝历年(韩愈逝后)至唐末963篇的墓志铭则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综合这些墓志铭的写作情况,就文体而言,判断是骈体或散体的标准除了对偶句的多少外,还在于文章风格的追求,可明显看到,这些墓志铭中绝大多数仍是采取骈散结合的方式进行写作,完全采取散体写作的只占极少数,而且整篇墓志铭仍然以追求典雅工整、严谨有度为基本风格;铭文部分,虽出现了很多句式的变化,如兮字句、五言、七言等句式的加入,但富有变化的铭文大多数都体现于为女性而作的墓志铭中,大体仍然以传统的四言铭文为主,且铭文的风格仍以谨慎的总结概括为主,少有如韩愈所作铭文的恣意挥洒的议论等风格;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以平铺直叙为主,力求安全、较平面地陈述逝者的品行,用对话、故事等小说家笔法来立体地塑造人物颇为难见;在文章结构方面,则更鲜见随意布排,仍以遵守传统法度为主。其中《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53一篇,全文颇有韩愈碑志之风,录全文如下:
故光禄苗卿家人捧琴。宅内自遭大事,日放从良,所买时契券并焚毁讫。姓吴改名孝恭,年六十七。大中五年四月廿六日染时疾亡于东都恭安坊内。吴孝恭孝顺小心,干谨端直,不欺于人,不诬于上,仆隶之中,殆无伦比。自童稚之岁,伏事尊长,在左右凡五十余年,未尝一日有嚬眉窃语之过。呜呼!斯人也!岂易得哉!以此尤以重焉!亡之明日,殡于东都城北清风乡郭村。呜呼!每念其为人如此,不觉其凄怆久之。是以列其行迹,书其姓名,亦以金石之坚,期于不朽,呜呼!能无念哉!能无悲哉!故具纪之。[21]
此墓志行文虽简短,但对于逝者的性情有了生动的描写,且抒发情感极其顺畅自然。全文在形式上亦未受到一般程式的约束,信笔而行,洋洋洒洒,真情流露,明显看出受韩愈碑志的影响。然而这样的碑志作品极其罕见,完全不成气候。
结合代表性和普遍性两个因素的综合分析,可见韩愈的墓志铭创作作为一座“丰碑”,对于同时期以及后世的墓志铭创作的影响,稍体现在较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如杜牧。但这种影响也似可湮没于杜牧自身的才华与创作理念,不可一概而论地认定为是韩愈的影响。而对于大众的普遍的墓志铭创作而言,虽间或受到代表性作家或当时文风的些许冲击,但总体上仍然是按照自初盛唐以来的墓志铭创作程式缓慢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墓志铭本身首先是作为一种应用文,发挥现实功用是它的首要目的,文学性必须服从于功能性,因此文学的变化只能对它产生“微调”的作用,总体上不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二是一种文体在长期固化的背景下要实现破体变格的改变,必须依赖于大家个人的才情识见与学养。具体到韩愈本人,其独特的个性、出众的才情、丰厚的史识学养,造就了韩愈兼美包容的创作理念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这种理念和意识促使其在碑志文文体的演变过程中,不仅具有舍我其谁的勇气,而且具备担当改革文体的自身条件。但是对于一般文人而言,受能力所限,只能一边仰望着“丰碑”感叹,一边仍在自己所能驾驭的范围内,受着客观文学发展规律的制约,创作合乎常规的程式化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