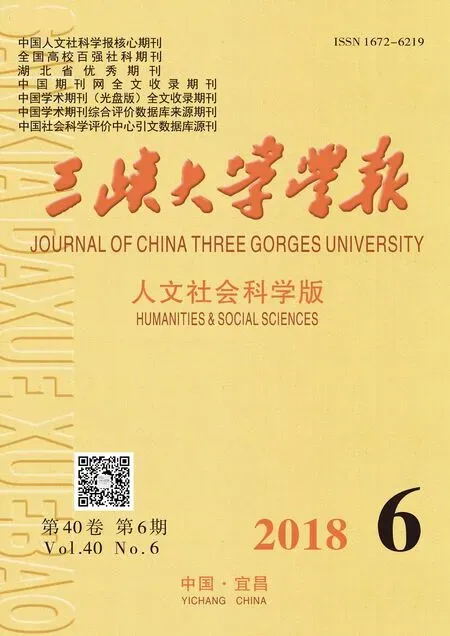明氏大夏国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2018-10-19刘兴亮
刘兴亮
(三峡大学 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宜昌 443002)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徐寿辉部明玉珍据有川蜀之地,建立大夏国,陈友谅占据湖广鱼米之乡,弑杀徐寿辉自立大汉国,其他势力纷纷割据自立。这些割据政权,明氏大夏国的统治时间较长,政权稳定,疆域广阔。其疆土范围,在朱元璋给明昇的书信中有明确提及:“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借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1]3407意即,大夏国疆域南达播州,北抵汉中,东有瞿塘,西有剑门,基本覆盖了今川蜀之地,还包括黔北、鄂西南、陕南、滇东北等地。董其祥《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始末》说:“其疆域四至,最盛时东及夷陵(今湖北宜昌),西迄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南郑);除四川全部外,还有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北部等地区。”[2]108其论述大体较为准确,唯部分疆界仍可加以讨论。
一、南征与北伐:天统年间的疆土扩张(1363—1366)
明玉珍建国后,为“逐元虏以靖中夏”的战略目标,积极扩张疆土。天统元年(1363),“置奉天征北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陈友谅”[3]5。后因陈友谅败亡,“进取陈友谅”并未真正开展。其它军事活动主要有南征云南和北伐兴元。
1.南征中庆
元朝末年云南地区为元梁王孛罗管辖地。天统二年(1364)春,万胜、邹兴、芝麻李领兵11万三路并进,南征云南,万胜从界首(今四川叙南)入[4]19,邹兴从今西昌进兵,芝麻李从今贵阳进入云南。万胜的部队于二月初八日抵达云南,驻扎于金马山。由于邹兴、芝麻李联军未能按计划汇合。三月,孛罗、云南廉访司官逃往威楚,大夏军攻陷中庆城,“遣使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纳降,降者不可枚举”。万胜军获胜后,派侍中杨源向明玉珍进表文,说:“大军即发于三巴,逾月遂平于六诏。穷民交贺,远近同欢。……郡守无恻怛爱民之意,肆为虐政,害彼黔黎。下诏杨庭,出师讨罪。初临乌撤,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马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3]6在《滇载记》中也记载曰:“明玉珍自将红巾三万攻云南。梁王及宪司官皆奔威楚,诸部悉乱。”亦印证了万胜军队攻陷中庆城。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领兵攻城,大败万胜于关滩,并俘虏了招安元帅姬安礼,从中探知大夏国远征军队人数并无三万,于是积极调集兵马,汇合大理段平章兵力大败万胜。明玉珍恐国中有变,令万胜班师,留建水元帅府聂堇领兵八千“拒守同马”。
南征云南持续四月余,占有中庆城仅有月余,大夏并未对昆明城实行有效统治。南征行动客观上削弱了元朝在云南地区的统治,有利于大夏国南部边疆的稳定。南征失败,红巾军主力折损大半,直接影响了大夏的北伐军事活动。此次拓展疆土失败,有战略方面的因素,也和时机不成熟及军队阶级局限性有关。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需假以时日,此时调集人力、物力、财力远征,给新政权带来巨大财政负担,致使边防部署吃紧。此外,攻占中庆城后,万胜上表说军队纪律严明,“一毫不犯”,但也有文献记载万胜军“毁民庐以为寨栅,梵宇神祠亦不免焉”,“官舍民居焚毁殆尽”[5],“所过暴掠,为民患,玉珍不能制”[6]269。事实上,大理段氏的反戈也间接表明了民众对大夏军队的态度。
2.北伐兴元
天统元年,万胜率军攻打汉中,平章普颜达失出走,缴获人马万余口。天统二年,普颜达失又领兵从小路向陕西进发,明玉珍命戴寿追击至秦州,未能成功。天统三年(1365),万胜再次领兵攻取兴元,亦未能克。直至天统四年(1366),才攻下兴元城[7]1333。明玉珍还派遣邹兴攻打巴州尚仓,并留军队驻守[6]269。北伐屡次受挫,巴州(今巴县)等地的残元势力趁机发动叛乱,邹兴领兵平叛。明玉珍病逝后,留下“中原未平,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之遗言[3]8。北伐结束后,基本奠定了大夏国的疆域范围。
南征和北伐,明氏大夏国的政治空间有所拓展,北部的汉中纳入版图,南征云南也占有昆明城数月。天统四年,明玉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邹兴为平章,俾镇成都;吴友仁为平章,俾镇保宁;莫仁寿为平章,俾镇夔关;邓元帅(元亨)为平章,俾镇通江(州);江宝英为参政,俾镇播州;荆玉为宣慰,俾镇永宁;商希孟为宣慰,俾镇黔南。”吴友仁镇守剑门关,“保宁”即广元路保宁府(今阆中县)。“通江”,为广元路通江县(今通江县)。又“永宁”,宣政院辖有永宁府(今四川丹巴县境),丽江路宣抚司领有永宁州(今宁蒗县永宁镇),建昌路有永宁州(今四川西昌市境),四川省亦有永宁路(今四川叙永县),荆玉所镇“永宁”疑为四川之永宁路。商希孟镇守黔南,在今铜仁、镇远地区。保宁、夔关、通江、播州、永宁、黔南等重镇构建了大夏国主体军事防御网,基本奠定了天统年间的疆域范围。
二、内忧与外患:开熙年间的疆界危机(1366—1371)
天统四年(1366),明玉珍病逝,子明昇继位,改年号为开熙。明昇继位时,尚年幼,由太后及明昭等权臣辅佐,国势日渐衰微。明昇继位后,命丞相戴寿领兵攻打乌撒。按乌撒,本乌蛮乌撒部,元至元十三年(1276)置路,二十四年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后分乌撒、乌蒙二路。乌撒治所在今贵州威宁县治,辖境相当于今威宁、赫章二县。明氏政权的动荡,也给边境势力以可乘之机。1366年,保宁镇守吴友仁在统辖州县发表通告:“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者矫旨杀戳功臣,我辈宁能自保乎?”遂割据一方,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相互勾结。开熙二年(1368)四月,戴寿领八万兵前往保宁征讨,吴友仁向戴寿提出条件说:“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1]3704戴寿返回重庆,设计诛杀明昭,叛乱平息。边境危机出现后,“于是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专恣,国柄旁落,遂益不振”[7]。
开熙年间,大夏国地缘政治已发生巨大变化。朱元璋吴政权兴起,攻下元都,扫平两广、关中、陇右等地,兵多将广,势力雄厚。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屡次以“求木植”“借路攻云南”被拒绝为由,遂以汤和为征西将军,以周德兴、廖永忠、杨璟、叶昇等率京卫荆襄舟师,由瞿塘关直趋重庆;又以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由顾时、何文辉等率河南、陕西等地步骑由秦陇直趋成都。两路并发,夹攻大夏国。傅友德一路等从陕西进发,直取汉中。《鸿猷录·夹攻巴蜀》云:“三年庚戌四月,大将徐达等征定西还,将袭兴元。达命傅友德为前锋,李思齐、左君弼、赵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伪平章蔡楙,遂入沔州。又遣金兴旺、张隆由凤翔连云栈入,合兵攻兴元,克之,降其守将刘思忠、刘庆祥等。”洪武四年(1371),大将傅友德“遣使人觇知青州、果阳空虚,阶、文虽有兵垒,而守备单弱,于是引兵趋陈仓。选精兵五千为前锋,攀缘山谷,昼夜兼行,大军继之。直抵阶州,蜀守将平章丁世珍率众来拒,友德击败之”。傅友德旋即“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断白龙江以阻我师,友德督兵修桥以渡,至五里关,世珍复集兵据险,……友德奋兵击破之,世珍以数骑遁去,又拔文州”[8]105。
汤和一路,从瞿塘、归州、湘西、鄂西、渝东南等地突进。《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中山侯汤和师克归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赵庸、宣宁侯曹良臣帅兵取桑植、容美洞,及会江夏侯周德兴合攻茅冈、覃垕寨,庸至中途而还,独良臣会德兴攻诸山寨,平之,和仍驻师归州。”《鸿猷录》详细记载了汤和等人在湘西等地的行动:“汤和、廖永忠等合赵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覃垕、茅冈寨。又攻天门山,擒其将张元帅、小张佥事,降其众千余人,遂克归州。又克夏将李逢春烽火山寨,乃进攻瞿塘关。”慈利《唐氏族谱》云:洪武二年,夏明昇余党为寇,丞相兵屯三江口。公统所隘军属投诚徐达、邓愈二公驾下,纳土归附,仍授原职,助粮佐征,平服十八土司。”与慈利唐氏相同,石柱马氏、平茶杨氏、石耶杨氏以及容美田氏等土司大姓纷纷归降,投诚以表明立场。明氏大夏政权为争取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极尽优渥,以达到守境安民、稳定边防的目的。酉阳冉氏效忠于明氏政权,《冉氏家谱》记载冉应显“负夏人伪敕、舆图、银印,星夜奔驰,谒汤和于白帝城”,“康茂才取酉阳,领兵把守夔关。康茂才恃勇轻进踵关,竟死于冉氏兵卒之手”。在攻克夔关后,明昇等携皇后彭氏“赍符玺诣军门降”,大夏国灭亡。
三、明氏大夏国政治空间范围
大夏国历明玉珍、明昇二代,疆域范围稳定,唯北部局势稍有动荡,疆界略有盈缩。大夏国东、南、西三段疆土相对稳定,疆域东以夔关、瞿塘为界,含恩施大部、宜昌部分地区,南至播州、永宁、建水等地,西抵文州、茂州、黎州、雅州、邛部州,北达文州、阶州、礼店、保宁等地,涵括了今四川和重庆两省大部分地区,还包括鄂西南、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贵州北部、东北部,以及陕西西南部,甘肃陇南、云南东北部部分地区。
1.东部疆界
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尽有湖广之地。明玉珍为稳定政权,极力拉拢湖广地区的土著势力,设置行政机构,提升土司行政级别。
(1)湘西地区。据《鸿猷录》所载,洪武四年(1371)“汤和遣周德兴率周海等进兵取蜀之龙伏隘,又进夺覃屋、温汤关。”“龙伏隘”,即“龙伏关”,在今湖南张家界市境内,《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龙伏关,卫(永定卫)西北百二十里,亦曰龙伏隘。明初伐蜀,别将周德兴取其龙伏隘,是也。”“覃屋”,当为“覃垕”之讹,也即“覃垕寨”,在今湖南慈利县西,“明初,覃垕作乱,命杨璟讨之,进抵覃垕寨。贼下山迎敌,败之,乘胜追至半山。山势险峻,其寨三面岩险,下俯江水,一面仅有一路,才通一人,乃回驻山下,攻围久之,贼遁入溪洞。璟引还,既而大兵取蜀,周德兴克其覃垕寨,即此。”[9]3645“温汤关”,又作“温阳关”,“在(慈利)县西。明洪武三年,蛮酋覃垕连构诸洞为乱,命周德兴讨之,至慈利,垕守险以拒,德兴出奇兵,破其数栅,直捣温阳关,拔之,贼遂溃。既而为伪夏所据。四年,命汤和等伐蜀,周德兴分兵取蜀之龙伏隘,进夺覃垕、温阳关,和克归州,遣赵雄等取桑植、容美洞,会德兴兵攻茅冈、覃垕寨,克之。”“茅冈寨”,“东南去慈利县二百里,亦曰茅冈隘。明初伐蜀,周德兴引兵道此,克其隘”[9]3645,其地在张家界东北。“桑林”,疑为“桑植”之讹。“芙蓉洞”,为“容美洞”之讹,在湖北鹤峰县。天门山,在慈利县西南。永顺土司也属大夏国,洪武七年(1374)五月,“四川散毛宣慰使司都元帅覃野旺、湖广永顺宣慰使顺德汪备、堂厓安抚司月直什用遣人来朝贡方物,上其所授伪夏印”[6]1576-1577。至正十一年,永顺土司由安抚司升为宣抚司,顺德汪备归降明朝时为宣慰使,其官职的提升疑在明玉珍时期。永顺土司领施溶溪长官司(永顺县东)、驴迟洞长官司(永顺县东南)、麦著黄洞长官司(永顺县南)、腊惹峒长官司(永顺县东南)、会溪长官司。
(2)鄂西南地区。大夏国时期,在鄂西南地区设置了散毛沿边军民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以及容美等处军民五路总管府、东乡五路总管府、镇边五路总管府、忠建军民都元帅府、盘顺元帅府、施南宣抚司、镇南宣抚司、沿边溪峒宣抚司、忠路宣抚司、忠孝宣抚司、隆中路宣抚司、大旺宣抚司、龙潭宣抚司、龙渠洞宣抚司、隆奉宣抚司、师壁安抚司、高罗安抚司、唐崖安抚司、又把洞安抚司以及椒山玛瑙长官司、石梁下峒长官司、五峰石宝长官司、水浕源通塔坪长官司、木册长官司[10]。鄂西南地区大部归属大夏国,不少后世土司家谱似对归降明玉珍偏安政权有所忌讳,如明代严首升撰写的《田氏世家》:“独是(田)光宝席祖宗之旧业,识时知命,谨奉正朔,保境息民,可谓贤矣。且明之际,韩山童、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之徒,窃土僭号盗名者不可胜数。况容美疆土,逼处伪夏蚕食之交,自非卓然独见,不为浮名所惑,安能若是长保富贵乎?由此论之,公之不坠先业,克世其家,已无愧于前世。而其识时择主,箕裘重新,则于先代为令嗣于后裔,实又为鼻祖也。”[11]84容美虽非鄂西南大姓土司,但在周边土司都已归附的局势下,所谓的“识时知命,谨奉正朔”应该是其后人编修家谱时刻意修饰家族历史的行为。前引《明太祖实录》、《罪惟录》等史籍记载宣宁侯曹良臣所部军队进攻的目标即是容美。《明史·湖广土司》也记载:“(正德)十五年,容美宣抚司同知田世瑛奏获镇南军民府古印,为始祖田始进开熙二年颁给。”“镇南军民府”当为容美等处军民五路总管府中的一处,与石梁下峒、五峰石宝、椒山玛瑙、水浕源通塔坪构成五路总管府,“开熙”为明昇的年号。
(3)渝东南。重庆市黔江、酉阳、彭水、石柱和秀山等县(区)作为大夏国都重庆的屏障,是明氏重点经营之地。在酉阳设置沿边溪峒军民宣慰使司,领邑梅沿边溪洞军民府(在今秀山梅江镇)、石砫安抚司(在今石柱县境)、石耶军民府(在今秀山县石耶镇)、平茶永化军民府(在今秀山县境)。与容美田氏家谱相同,石柱马氏、平茶杨氏、石耶杨氏三家谱牒都否认其祖曾归降大夏国。如石柱《马氏家乘》曰:“元失其政,天下鼎沸,时明玉珍据蜀,……沿江州县罔不蹂躏,惟我石柱安如磐石,贼兵不敢窥伺。(马克用)当与众民约曰:“今天纲瓦解,贼寇四起,我官民困守弹丸,以待有德,毋得私自附贼,敢有违者杀毋赦。”……及前明定鼎,公率众投诚。”[12]327又如平茶《杨氏家谱》亦云:“再兴当元明鼎革之际,寇盗蜂起,明玉珍据蜀。酉阳宣慰使冉如彪、邑梅土知府杨正天并送款成都,再兴厉兵扞境,深拒伪命。明太祖洪武初,东南大定,再兴纳土归诚。”[13]酉阳《冉氏家谱》则明确记载冉氏派兵助大夏攻打明军。嘉靖《四川总志》记载石柱马氏“为先纳牌印,授石砫安抚使”,被忠路、酉阳、唐崖、沙溪等土司推为司长。酉阳土司率先归附,平茶杨氏、石耶杨氏也不例外。与唐崖土司(在湖北咸丰县)接境的黔江也可能为大夏国所有。
(4)归州与夷陵。归州、夷陵是否为大夏国疆域,历来存有争论。《明氏实录》、嘉靖《归州志》、同治《宜昌府志》等史籍认为夷陵、归州当属大夏。明玉珍《明氏实录》记载,大夏国建立后于夷陵设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作为陈友谅的前哨之地;又天统四年冬,“徐国参政姜珏来朝,仍令守夷陵,就彼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嘉靖《归州志·沿革》云:“归州,至正中升为路,……元末明玉珍僭据其地。”该书还记载汤和、康茂才等与大夏将领龚兴大战于归州城东门,龚兴战败,退守夔州。同治《宜昌府志》与《归州志》均明确说康茂才与龚兴交战地点在城东门头。《明太祖实录》、弘治《夷陵州志》等古籍则认为夷陵、归州先为陈友谅所有,至正二十四年(1364)后为朱元璋所有。《明太祖实录》云:“是年(1364)八月,命达将兵取荆湘湖南北诸郡,达与参政杨璟率战舰至荆州,伪汉守将姜珏以城降,达复遣傅友德将兵取夷陵,守将杨以德、归州将杨兴俱以城降。”弘治《夷陵州志·建置沿革》曰:“元末陈友谅僭据其地,甲辰归附。”嘉靖《归州全志·沿革》亦云:“元末陈氏僭据其地,甲辰归附。”
从已有文献看,大夏国东部疆土未包括夷陵。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弑主自立,明玉珍令莫仁寿领兵镇守夔关,《明史·明玉珍传》作“以兵塞瞿塘”,《明氏实录》所云天统二年“设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应有舛误,在汉中设置的所谓“奉天征北大将军府”同理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兴元城被万胜在天统四年攻克的,姜珏归附大夏也在同一年。《明氏实录》记载姜珏屯种于夷陵的时间为天统四年,而《明太祖实录》记载为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汤和、康茂才等攻克荆州,姜珏投降。
巴东、兴山为大夏国疆土范围。明人文集《东里文集》记载《故怀远将军成都右卫指挥同知陈公神道碑铭》云:“时蜀未附,而归与夔接壤,日渐侵夺。公(陈闻)至归,视其城堕弛,且非可以用武,乃择地,距城二十里楚台故址,建千户所治,高城深隍,缮兵甲,练士卒,实仓廪,悉足用。蜀人以舟师来攻,公预清野待之,而以老弱婴城固守,授之方略,躬率精锐,伏缘江要害处。敌薄城下,守备坚不可攻,又野掠无所得,敛而还舟,伏师突起,斩馘不可胜计。敌兵大败引去,自是无一足犯境。”[14]174“归州”,即归州城。又《明太祖实录》中有“中山侯汤和师克归州李逢春烽火山寨”的记载,按“火峰山寨”,在巴东县西北,“(巴东)县西北三十里。其地有火峰,据险置寨,因名。明初,汤和伐蜀,克归州,取火烽山寨,即此。或作烽火,误也”[9]3694-3695。据嘉靖《归州志·沿革》所载“兴山,先为明玉珍父子所据”可知,归州之兴山县,也属大夏国疆土。
2.北部疆界
天统年间,北部疆域大抵在巴州以南地区。天统三年,明玉珍派兵攻克尚仓,尚仓在今汉中南部米仓山或米仓道中的一段。天统四年,占有兴元城。《明史·徐达传》和《明太祖实录》记载傅友德等从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阳。《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一百八渡河)在(略阳)县城东。自巩昌府徽州界流入境,下流合嘉陵江。明初徐达下秦州,遂南出一百八渡河,由略阳入沔州是也。”按,今成县、徽县境内的洛河、青泥河、西汉水均流入略阳境内,“一百八渡”当为其中一支。又《元史》记载:“(至正)二十五年五月辛酉……侯卜延答失奉威顺王自云南经蜀转战而出,至成州,欲之京师,李思齐俾屯田于成州。”[15]969由此可知,成州为李思齐所控制,今陇南成县境。成州南部之阶州、文州应是大夏国土。洪武四年,傅友德进兵,大败大夏守将丁世珍。傅友德攻克阶州后,“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断白龙江以阻我师,友德督兵修桥以渡,至五里关,世珍复集兵据险,……友德奋兵击破之,世珍以数骑遁去,又拔文州”[8]105。阶州,在今甘肃省陇南市境内。文州,即今文县,大夏时置礼店元帅府,王均谅摄礼店元帅府同知,孙忠谅为礼店副元帅、达鲁花赤。礼店文州,在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境。
3.西部疆界
按元代行政区划设置,四川行省之嘉定路以西为宣政院管辖。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派兵攻打龙州、青州等地,十一月,攻陷青州,置龙州宣慰司[15]959-961。《续通典》云:“龙安府,元代为龙州,属广元路。明玉珍置龙州宣慰司。”[16]薛文胜任宣慰司使,王祥任副使。平武县《薛氏族谱》云:“薛文胜,至正十一年升元帅府元帅,二十一年改授龙州宣慰司使,二十三年授信武将军管军元帅[17]。《奉亲山记碑》云:“王祥,至正二十三年,改龙州宣慰司副使。”另有《三凤堂薛氏族谱》云:“至正二十五年丙午,大夏天统四年,诏授文胜信武将军,管军元帅。”开熙年间,薛文胜又改授明威将军、龙州等处军民宣抚司同知[18]14-15。龙州,在今绵阳市平武县一带。威州,按《明史·地理志》,在今汶川县,“威州,元以州治保宁县省入,明玉珍复置县。”威州治保宁县。另有金州亦属大夏国,“伪夏守金州九龙山寨平章愈思忠率其官属军民二千三百人诣傅友德降,献良马十匹”。雅州,大夏国设雅州宣慰司,《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九月)初,都督何文辉师次雅州,遣千户王祯招降伪宣慰余思聪等,至是,调千户余真领兵镇守。”[6]1283又严道县,大夏国时省入荣经县[1]。雅州领名山、泸山、百丈等县。黎州,明玉珍设黎州招讨司,芍安为黎州招讨使。《明史·四川土司》有云:“黎州,宋属成都路,元属土番等处宣慰司。洪武八年省汉源县,置黎州长官司,以芍德为长官。德,云南人,马姓。祖仕元,世袭邛部州六番招讨使。明氏据蜀,德兄安复为黎州招讨使。明氏亡,蛮民溃散,德奉母还居邛部。至是,四川布政司招之,德遂来朝贡马,请置长官司,诏以德为黎州长官,赐印及衣服、绮帛。”[1]此外,天全、碉门(均在今天全县境)与雅州接壤,可能也为大夏国所有。
4.南部疆界
《明史·明玉珍传》称大夏国疆土“南不过播州,北不及汉中”。天统年间,窦英为参政镇守播州,《明史·地理志》有云:“真安州,明玉珍改真州。”播州以南,部分地区属大夏国。天统年间分三路攻打云南,指挥芝麻李率领的军队经由八番,《黔记·大事记》也记“明玉珍遣指挥李芝麻帅兵由八番分陷云南,是时贵州属伪夏”。八番之一的养龙坑宿征司属大夏国,《黔记》、《明氏实录》徐松注引《宋濂集》称,明洪武四年夏国主明昇投降时曾献良马十匹,其中就有产自养龙坑的良马,在今息烽境内。
又有思州,元代一分为二,田茂安据原思州北部地区,田仁厚占有思州南部,以镇远府(今镇远县)为界。思州北部“镇远军民同知田茂安因不屑堂侄仁厚统辖,遂割思南并镇远地方献蜀(大夏),玉珍授思南宣慰使,其子仁政为龙泉坪宣慰使,仁智领镇远军民同知,仁美授统兵元帅。”田仁厚据有思州南部,后归附朱元璋。思南宣慰司领水德江(今德江县境)、沿河祐溪(今沿河县境)、婺川(今务川县)、龙泉坪、洪安、朗溪司(今沿河务川一带)等地,东与沅州路(今湖南新晃、芷江侗族自治县等)接壤,北与酉阳土司为邻。
在西南缘,明氏三路大军攻打云南时,一路由界首入,“界首”在今叙永县西南。《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九月条有“明昇令叙南宣抚使杨琮领兵守瞿塘”的记载。《明氏实录》云明玉珍设永宁镇边都元帅府,由荆玉镇守,与之接境的筠连州属大夏国。万胜兵败后,令建水元帅府聂堇领兵把守门户。在明昇时期,亦曾派兵攻打乌撒地区,但未成功,故今云南威宁仍为梁王孛罗所有。邛部州为大夏所控制,芍安为黎州招讨使,明玉珍兵败后,“蛮民溃散,德(芍安之兄)奉母还居邛部”,邛部州治今四川省越西县。与邛部州、建昌相邻的马湖当属大夏,“元至元间内附,设为马湖路总管府,分其地置六长官司,明玉珍并而为五。”[19]209又《明史·四川土司》云:“黎雅徼外大小木瓜种分枝,世居河西,初属马湖土官安氏钤辖,自马湖改流,诸官叛入邛部,归岭氏,其地自西河至凉山、雪山诸处,周围蟠据。”马湖土官安氏原领有西河诸土司,在今马边、峨边等县境。叙州南部的珙州,《明史·地理志》云:“明玉珍改为珙州。”珙州领上、下罗计长官司。因此,大夏国南部疆土大致以今越西-雷波-屏山-叙永-大方-织金-贵阳-镇远-玉屏-万山为界。

图1 大夏国疆域、政区全图
四、小结
明氏大夏国政治空间在元代四川行省基础上而成,也有四处明显改变:一是将原属于湖广行省之播州、思州纳入四川省范围,使之成为重庆的天然屏障,明朝的四川布政司辖地也包含了今贵州北部地区;二是占有礼店、阶州、文州等地,使之成为大夏国西北部重要门户,洪武初年,此战略要地成为傅友德进攻大夏的重点,决定了战局的走势;三是占有广元府兴元路,北部疆土扩至汉中;四是明氏大夏国疆域向西扩张,威州、茂州、雅州、黎州、邛部州等地均为大夏所有,明朝在此基础上设松潘卫于阿坝地区的松潘、马尔康、黑水、若尔盖、九寨沟等地,又设四川行都司于凉山地区。
大夏国为有效治理疆土,在主体区设置了具有监察性质的八道,即上川东道、下川东道、上川南道、下川南道、上川西道、下川西道、上川北道、下川北道,以及重庆路刺史府、成都路刺史府、夔州路刺史府、广元路刺史府、嘉定路刺史府、顺庆路刺史府、潼川刺史府,府领州,州领县,由此形成府、州、县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较元代路-府-州-县四级制更为简便[20]74-75。明氏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设宣慰司、安抚司、宣抚司、长官司,以及都元帅府、总管府、军民府、土州、土县,在部分地区两者混杂使用,例如播州宣慰司,即领有播州沿边宣抚司、播州军民都镇府司、草塘安抚司、容山长官司、余庆州、綦江县。明氏政权通过授予土司贵族印章、诰敕、虎符等信物加强管理,受封的土司则需承担屯田守边、征调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