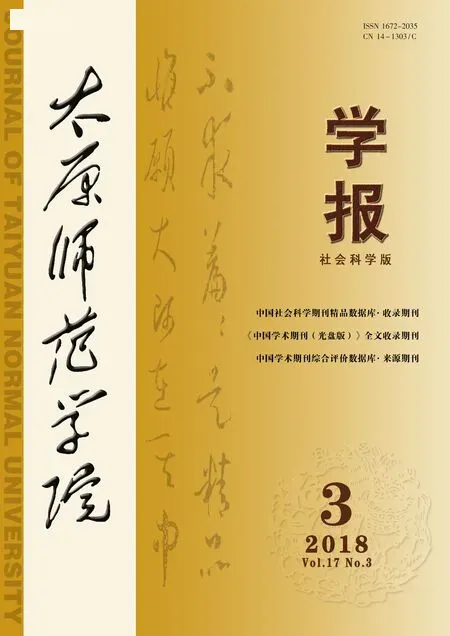晚期维斯康蒂与新现实主义的断裂
——以“德意志三部曲”为中心
2018-01-29符晓
符 晓
(长春理工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鲁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在世界电影史上与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并称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他凭借《沉沦》(Obsession,1943)和《大地在波动》(The Earth Trembles,1948)奠定了他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维斯康蒂的电影主题和电影风格前后两个时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也为对其电影美学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从20世纪50年代的《小美人》(Bellissima,1951)和《战国妖姬》(Senso,1954)开始,维斯康蒂逐渐偏离了新现实主义的轨道,这种倾向在《豹》(The Leopard,1963)中达到高潮,使得这部影片极具个性化。《豹》也成为维斯康蒂前后两个时期影像风格发生重要变化的分水岭。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将一些伟大艺术家生命临近终结时的新风格称为“晚期风格”。在这一框架下,他将《豹》之后的影片看作是维斯康蒂的晚期作品,并认为“他的全部晚期创作都集中在与一种古老的、大体上属于贵族秩序的衰落和消逝、一个新的和粗鲁的中产阶级世界令人不快的出现有关的那些主题之上”[1]94,从主题上概括了维斯康蒂晚期电影的全部内容。“德意志三部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所谓“德意志三部曲”指的是涉及德国历史、文学和艺术的三部影片:《纳粹狂魔》(The Damned,1969)呈现出的是德国钢铁世家祸起萧墙并被纳粹逐渐吞噬的悲剧,是一部家族的衰落史;《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1971)改编自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威尼斯大瘟疫来临前音乐家古斯塔夫对一位美男子的迷恋与行将就木的孤独灵魂;《路德维希》(Ludwig,1972)诉说着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对艺术的毕生追求和隐秘孤傲的内心世界。三部影片已然从对战后意大利社会历史的思考转为对全欧洲政治和文化的叩问,专心致志地分析病态的时代与病态的人,形成一种新视角,同时给这种视角提供了广度。从电影美学上说,维斯康蒂晚期作品是对新现实主义的出离甚至背叛,这种主题和美学转向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潜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秘逻辑,都是需要重新认识并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颓废的生命:“德意志三部曲”的电影主题
维斯康蒂在“德意志三部曲”中着力渲染的是家族或人的末落与衰退。《纳粹狂魔》中庞大家族由盛而衰,其中兼及了人的道德滑坡和自甘堕落;《魂断威尼斯》中古斯塔夫在艺术、美和美男子中间踽踽独行最后孤独死去;《路德维希》刻画了一个国王因为艺术而消耗政治生命,似乎象征着一个王朝逝去的背影。无论是家族的衰落还是人的衰亡,维斯康蒂赋予影片的都是某种颓废主义的倾向。颓废作为美学风格最早出自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对波德莱尔诗歌的评价,马泰·卡林内斯库则认为颓废是欧洲各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腐朽、错乱、衰退、悲观和虚无成为颓废的相近语义群。虽然颓废是一种文学上的批评方式,但是完全适用于维斯康蒂的“德意志三部曲”,所不同的是,在维斯康蒂晚期作品中,颓废既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本质。虽然讲述的都是贵族,但是维斯康蒂习惯将“德意志三部曲”中的故事置于一种萧索凄婉的视域和环境中,无论是光影还是主题都为营造某种颓废感服务。诚如阿兰·巴迪欧谈及《魂断威尼斯》前几个镜头所提到的那样,“这里要表达的理念是爱的感伤、独一无二的地点和死亡这三者之间的关联”[2]105-110,在影片开始就奠定了颓废的基调。《纳粹狂魔》中马丁的第一场戏就是装扮成女性翩翩起舞,畸形而扭捏的动作完成了影片对人物的最初定位。《路德维希》中,国王因为艺术而一点一点沉沦并成为臣子的“阶下囚”,故事本身就掺杂了关于颓废的全部义素。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在维斯康蒂的镜头中都呈现出深深的颓废感。
在“德意志三部曲”中,维斯康蒂对主人公的性取向做了非常隐秘的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从另一个方面呈现出了作为人物的颓废感。《魂断威尼斯》和《路德维希》中,男主角都存在同性恋倾向,古斯塔夫无疑“爱”上了威尼斯的贵族男孩,路德维希则与“罗密欧”“相见甚欢”;《纳粹狂魔》中的马丁则是个“恋童癖”者并且强奸了自己的生母。维斯康蒂在三部曲中呈现出的非正常性心理并非毫无来由:古斯塔夫行将暮年,拖着多病的身躯来到威尼斯,迎接孤独甚至死亡;路德维希愿意为艺术抛开一切,小山顶城堡中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已经暗示着其政治的迷途。两位主人公都处于生命的消解期,本身具有某种“世纪末”情结,在这种背景下加入同性恋要素,无疑加重了这种颓废感,使得他们的人生和前路更加悲凉。其实,这种颓废感与爱和美有关。《魂断威尼斯》中的男孩既是爱的象征,也是美的象征,与其说古斯塔夫对男孩是一种同性之爱,不如说他在男孩的躯体和灵魂中欣赏男孩的美,如维斯康蒂自己所言:“影片中的男孩代表着爱,他是美的象征,而阿申巴赫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理想之美,当他看到这种完美的真实存在之时不免为之着迷”[3]5。路德维希对“罗密欧”的感情或多或少也来自他对艺术之爱,“罗密欧”无疑是艺术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魂断威尼斯》和《路德维希》中同性恋所要表达的颓废感异曲同工。而在《纳粹狂魔》中,马丁本该是家族的继承者,却遭到纳粹的挑唆,绝望感催生了他的变态心理,这也同他的堕落与衰败暗合。可见,“德意志三部曲”隐秘的两性逻辑加强了颓废感的表达,也为影片中的男主角贴上了一个深重的颓废标签。
在“德意志三部曲”中,颓废的终极表达是死亡。颓废的传统本身充满了极度悲观主义倾向,古希腊人认为时间本身具有一种没落性,基督教强调末世论,文艺复兴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大多数是悲观主义者,[4]162-165其最终指向都是死亡,凡此种种也同死亡形成互文。或者说,颓废作为美学传统与死亡必然相关,也同死亡共生共存。所以也就不难理解,颓废与死亡为什么能够在影片中形成互文。在《魂断威尼斯》中,水城威尼斯已经从亚得里亚海的明珠成为弥散着大瘟疫的死亡之城,古斯塔夫在“死亡之城”死亡,无论是因为他对艺术与美的执念还是因为他视线中的那个男孩,都令人叹息。路德维希对艺术的疯狂追求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上的穷途末路,而及至政治和艺术二者都不可得的时候,死亡对于他来说也成为理所当然。《纳粹狂魔》中,马丁虽然还活着,但是灵魂已死,何况影片中的其他人都以死亡告终,索菲运用各种诡计和手段追求家族的最高权力,但是她的生活和处境却使她始终徘徊在边缘,人性的隐没和家族的没落似乎殊途同归。值得注意的是,索菲、古斯塔夫和路德维希赴死之前,脸色惨白,面部涂满了大量白色油彩,仿佛是一张面具,这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他们面部的油彩色度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越靠近死亡,油彩越浓。这说明维斯康蒂刻意考虑了影片在时间上与死亡的关系,油彩浓淡也可以理解成一种“颓废度”。三部曲中的重要人物一直在本我与世界的矛盾中踽踽独行,并萌生出形式上和本质上的颓废感,颓废是矛盾的外在而已,死亡虽然是这种颓废感极端的表现,但却也是唯一的表现。
虽然颓废在一般意义上与没落、衰败、黄昏、衰老甚至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维斯康蒂并不认为他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颓废”是一个贬义词。他认为“颓废”在“德意志三部曲”中烛照出来的就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谈及《魂断威尼斯》,维斯康蒂曾言:“我非常推崇‘颓废’,就像托马斯·曼等人一样的。我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激励:曼就是德国文化的颓废者,而我是意大利结构的颓废者。我始终感兴趣的是,分析病态的社会。”[5]167就维斯康蒂的美学而言,“颓废”既是艺术表现的目的又是艺术表现的方法,在他晚期作品中,他是怀揣着“颓废”完成美学表达的,即使影片中出现的同性恋,维斯康蒂也认为只是一个普通隐喻而已,“既体现了消极品质(《纳粹狂魔》中的权力欲),也有积极的知性艺术奋进(如《魂断威尼斯》和《路德维希》)”[5]169。维斯康蒂追求的是一种以“颓废”为中心主旨的电影美学现代性,他以这种主题风格挣脱某种逝去的范式。马林内斯库在梳理了自柏拉图以来涉及“颓废”的义素和概念后指出:“颓废风格只是一种有利于美学个人主义无拘无束地表现的风格……如此理解的颓废同现代性在拒斥传统的专暴方面不谋而合”。[4]183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斯康蒂与马林内斯库异曲同工,只不过维斯康蒂的内容扮演的是马林内斯库的形式而已,更重要的是,维斯康蒂通过“德意志三部曲”所呈现出来的颓废感更显凄凉。
二、巴洛克电影:维斯康蒂晚期风格论
从电影美学上说,维斯康蒂的电影以矫饰和繁复著称,在晚期电影中他总是习惯于在一个场景中追求精致的、复杂的、重复的布景,并强调场面调度的丰富性,即使从主题上说不重要的物件也要在镜头中发挥其最大值,虽然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这或多或少迎合了17世纪巴洛克建筑的风格,并不是说,维斯康蒂借鉴了这种艺术,而是巴洛克本身的追求与维斯康蒂晚期风格形成互文。最早的巴洛克建筑为了能够走出文艺复兴晚期的范式,不惜矫揉造作,极尽复杂之能事。贡布里希说:“17世纪前半期,意大利仍然在建筑物及其装饰品上打主意,增添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花样,到17世纪中期,我们所说的巴洛克风格就充分发展起来了”。[6]435之后的巴洛克建筑追求个性装饰、多端变化、鲜艳色彩,所谓“眼花缭乱”可以作为巴洛克的美学标签。这些表现也是维斯康蒂在晚期电影中的追求,他在银幕上呈现的是一种电影的“巴洛克”,所以可以从形式上将晚期维斯康蒂的电影称作是“巴洛克电影”。
“德意志三部曲”中的布景非常繁琐,维斯康蒂在三部曲中追求装饰性的华丽布景,将影片布景舞台化、戏剧化,试图达到电影布景形式上的极值。《纳粹狂魔》中生日宴会的场景同《豹》如出一辙,几乎没有一个镜头是纯粹的近景或特写,人物总是出现在餐具和烛台两侧或中间,低垂的吊灯、高大的烛台、华美的餐具和一大束粉玫瑰俨然是钢铁世家贵气的象征,这些装饰的要素也贯穿了整部影片。《路德维希》中的国王加冕礼,维斯康蒂在布景上大做文章,仿佛每一盏烛台、每一套餐具、每一个画框都各司其职并被赋予加冕的意义,加之镜头中的众多人物以及他们华贵的衣饰,将整个场景装饰得繁缛、奢华。导演深知这并不是国王所愿,所以在布景上,王宫的奢华与路德维希所向往的朴实的艺术生活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侧面昭示出国王对权力的不屑一顾。如果说《纳粹狂魔》和《路德维希》的奢华布景是贵族和王室日常生活的形式感使然,那么《魂断威尼斯》中繁复的布景则是维斯康蒂晚期电影的象征,比如塔奇奥第一次进入古斯塔夫视线的那场戏,维斯康蒂连续用了几个摇镜头(与古斯塔夫视线一致)建立二人之间的空间联系,但是在摇镜头中反复强调蓝色花瓶、米黄色沙发、红色或黄色灯饰以及各种颜色的头饰,这些布景增强了画面的复杂性。这种方式贯穿了整部电影,如波德维尔所言,“在《魂断威尼斯》中,摄影机在豪华饭店的柱子、羊齿植物和银质茶盘间搜寻男孩塔奇奥”[7]475。维斯康蒂电影布景中的很多道具甚至布景本身并没有意义,即使是国王的加冕礼,那些华美的烛台、壁纸、衣饰和餐具也不必要发挥至极致,这些布景就像是巴洛克教堂套叠的山花或反曲的涡卷一样没有实际的用途,但是却表现出了维斯康蒂晚期电影中矫饰的奢华。
这种奢华同样表现在维斯康蒂晚期风格中对色彩的设计上。“德意志三部曲”是三部表现颓废与末落的电影,但是维斯康蒂在色彩上却反其道而行,呈现出的不是孤独忧郁的冷色而是鲜明的暖色色块。以《纳粹狂魔》为例,片头就出现红色炼铁高炉的熊熊烈火,既交代出故事的主要背景又成为家族的隐喻,红色成为这部影片的明亮色系,地毯、帷幔、火光、舞台灯光、纳粹臂章和旗帜等都使用大红色,鲜艳的红色与家族的没落形成对比的同时,也暗示着死亡终将来临,所以影片结尾处索菲夫妻在红色的幔帐中自杀身亡,人与家族在血的颜色中双双终结。《魂断威尼斯》中,每一个涉及富丽堂皇的厅堂无不辅之以浓重的色块,花瓶、花束、灯罩、头饰、屏风等都呈现出各种颜色。相反,塔奇奥每次出现都身着素服,维斯康蒂仿佛在用奢华的色彩反衬美少年的清纯,也是古斯塔夫心中“理式”的美和现实的美之区别。比起这两部影片,《路德维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影片中将红色作为背景色发挥到了极致,有几场戏仿佛就拍摄在红色中,镜头中的大部分颜色都是红色,烘托出了王室装饰的繁复和耀眼。而维斯康蒂将路德维希塑造成了蓝色形象,与红色形成了巨大反差,也暗示着路德维希的歧路。在这三部影片中,大面积暖色的铺陈与渲染明显而复杂,在一个画面中常常呈现出色系的交错与叠加,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成为色彩的巴洛克。
在“德意志三部曲”的时间节奏上,维斯康蒂有意识地渲染一种“重复”的“慢”。所谓“重复”指的是“德意志三部曲”中一些场景或镜头的不断呈现,如《纳粹狂魔》中宴会上餐具的镜头,在人物的对话之间频频出现,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配饰充斥着整个画面,使得画面中存在一种膨胀感,也成为家族矛盾的象征。《魂断威尼斯》中不断重复着古斯塔夫在街道上游走和在人群中寻找塔奇奥的镜头,将他怅然所失的颓废感以重复的方式最大化,这种镜头的重复“堆砌”成为巴洛克电影的一个注脚。另外,这些重复镜头都是慢速的而不是频繁剪辑。镜头的慢也是维斯康蒂电影的一个特点,如《魂断威尼斯》中古斯塔夫第一次见塔奇奥的那几个横摇镜头也是慢摇镜头,虽然多个镜头重复组合但是速度放缓,加重了男主角在人群中寻觅的焦虑感。从宏观方面说,“德意志三部曲”中常常出现的慢摇镜头也是家族与人溃塌的渐进式表达。慢还体现在维斯康蒂晚期电影在音乐的运用上,《魂断威尼斯》中,维斯康蒂选择了古斯塔夫·马勒的慢板音乐(《第三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作为影片的主要音乐元素,其缓慢的节奏也和影片的主题暗合,“威尼斯亘古不变的空虚、马勒音乐里柔板的停顿、演员静态和被动的表演”“拜访”的是同一个主题。[2]《路德维希》中虽然大量使用了瓦格纳的音乐,但是却摒弃了带有瓦格纳符号的波涛汹涌且激情澎湃的音乐,而是选择了缓慢抒情的柔板,不停重复的慢板也暗示着路德维希面对周遭一切时隐秘的内心世界。电影音乐上的慢渐渐消解掉影片中主人公的灵魂,颓废的身躯在世纪末的街市游走,仿佛整个世界即将灰飞烟灭。重复和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种叠加,不断申明着属于维斯康蒂自己的主题和美学,这种叠加和布景的繁饰、色彩的明艳一起构成了电影美学的巴洛克,装饰性远大于实际意义,这也成为维斯康蒂走向新现实主义反方向的一个例证。
三、传统的断裂:从新现实主义到反新现实主义
就意大利电影史而言,“新现实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无论是诞生与发展还是起伏与消解都承载着诸多社会、政治、艺术及美学的纠葛,使得概念本身既饱含丰富性又具有不确定性。从主题上说,罗杰·伊伯特认为新现实主义主要指的是“关注劳动阶级的影片”,“它们以贫困条件下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往往暗示着在更好的社会中财富分配会更加平均”;[8]94从形式上说,波德维尔指出新现实主义的美学在于“实景拍摄加上后期配音;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的结合;基于偶然遭遇的情节,省略,开放式结局以及对细微动作的关注;调子的极度混杂”,[7]470他们共同建构了一个新现实主义的叙事内容和艺术逻辑,《沉沦》和《大地在波动》就是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典范。遗憾的是,晚期维斯康蒂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其最具代表性的“德意志三部曲”都将目光投射在贵族、国王与作曲家身上,并且摒弃了朴素的镜头语言,用大量的横摇镜头和变焦镜头进行歌舞剧式的宏大叙事,这些都与《大地在波动》相去甚远,甚至表现出一种反现实主义倾向。一位新现实主义导演在晚期作品中转过身去走向了与初衷相反的方向,其中既有导演自身的创作因素,也与意大利电影的发展史息息相关。
维斯康蒂晚期电影中的新现实主义转向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顺应了20世纪50年代新现实主义电影导演的集体“逆流”。当时,比较重要的新现实主义导演如罗西里尼和德·西卡等都渐次退出了新现实主义的舞台,维斯康蒂的转型也在其中。首先,二战之后意大利电影的审查制度已经不允许新现实主义电影继续以从前的方式存在。意大利具有严格的电影审查传统,1923年电影审查制度的很多条款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即使处于成果最丰硕、实力最雄厚的时期,也无法避免种种尴尬的局面:有些影片因为商业、道德、宗教或政治的原因而被禁止上映,或被摧残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9]15。就新现实主义电影而言,1945年之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电影本身的意义和作用不大,而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表现了意大利的很多瑕疵和晦暗,所以政府开始限制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包括《偷自行车的人》和《大地在波动》等影片陷入被审查的深渊,这种情况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所改观,但是电影审查制度使得新现实主义导演更加中规中矩,围绕“过审”做文章,无形中影响了新现实主义的美学维度和艺术维度。其次,新现实主义导演在电影主题和电影形式上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使得当时的新现实主义形式与之前的形式发生了断裂。即使如罗西里尼、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导演对于新现实主义的态度也比较暧昧,一方面对概念本身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另一方面对概念内涵又存在自己的理解方式。费里尼就曾指出:“我不赞同给事物下定义的做法。在我看来,标签应该贴在行李上,给艺术贴标签没什么意义。”[5]101这并非孤例,而是代表了一些新现实主义导演的心声。所以他们纷纷尝试走出这种电影范式,如罗西里尼的《爱》(Ways of Love,1948)已经开始启用职业演员,他们依靠精湛的演技提升电影的“可赏质”;《游览意大利》(Journey to Italy,1954)则表现出了复杂而深刻的内心情感;安东尼奥尼渐渐从新现实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一些影片充满了新电影的实验特征。这些影片都进行着电影美学新的尝试,从多个方面走出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加之上述电影审查制度,共同加快了新现实主义转向的脚步。
无论是电影审查制度还是电影美学的集体转向,维斯康蒂都在潮流之中。一方面,维斯康蒂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难逃电影审查的命运。《沉沦》虽然在艺术上被看作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是随即遭到意大利当局的禁毁,是维斯康蒂自己保存了影片的拷贝才使得这部作品印刻在电影史上;《小美人》的发行虽然顺利,但是却是制片方意志的反映,维斯康蒂在谈到这部影片时说“主题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导演的个人意志,而是要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3]8,足见内中隐情;《战国妖姬》在威尼斯电影节公映之后就被意大利国防部强制删掉了一些镜头,以削减影片政治性对于观众的影响;《罗科和他的兄弟们》虽然后来得以公映,但是之前同样遭到查禁和剪切。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严酷的电影审查制度对维斯康蒂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像德·西卡等人那样将电影置于审查之外,这成为他背离新现实主义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维斯康蒂与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等人对后新现实主义的态度形成了某种一致性。早在1948年,维斯康蒂谈及“新现实主义”时就指出:“在我看来,它正逐渐变成一张荒诞的标签,像刺青那样贴到我们身上。它成了界限、法则,而不是一种方法,一个时刻。而我们难道已经需要界限了吗?”[9]51显然他对新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美学提出了质疑,所以在他之后的影片中体现出来的是与新现实主义的渐行渐远,以及极具个性的美学风格。及至“德意志三部曲”,呈现出的是一种完全的反新现实主义倾向,与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传统依然发生着深深的断裂。虽然一些美学原则承袭了前期风格,如静止摄影机的缓慢摇摄或长时间拍摄某静止物等,但在整体上存在非常明晰的变化。《战国妖姬》中已经出现了豪华室内的镜头;《罗科和他的兄弟们》侧重的是一种艺术性而不是社会性;《豹》在电影语言上完全是一种转折,影片形式上的奢侈、豪华、矫饰都成为“德意志三部曲”的前在经验,正是这种一步一步的过渡和超越造就了维斯康蒂晚期走向与新现实主义相反的方向。这是维斯康蒂的方向,也是新现实主义一代人的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新现实主义转向存在多种可能,但是维斯康蒂却转向了与新现实主义正相反的方向,这种传统的断裂也与他个人身世和性格有关。维斯康蒂出身贵族,虽然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到了晚年仍然时常关心孕育他的那种贵族文化,并尝试通过末落的贵族生活冷静审视全欧洲的文化和政治,所以《豹》和“德意志三部曲”都将目光集中在上层社会,可以被看作是维斯康蒂多年之后的家族回望。而且,维斯康蒂本身是一位同性恋者,虽然他对此问题一直讳莫如深,但是“德意志三部曲”中同性恋成为颓废的一种表现和美学,这或多或少与他本人的同性恋身份有关。另外,维斯康蒂晚年处于多病之秋,《路德维希》和《家族的肖像》等影片都是在病中完成的。烈士暮年,疾病缠身,直接导致了维斯康蒂电影主题和美学的转型,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死于威尼斯》结尾处“阿辛巴赫徒然剩下一重身份,即成了霍乱的又一个受害者,他的最终的堕落,正表现在屈服于这种危害当时众多威尼斯人的疾病”[10]35,阿辛巴赫可以看作是对维斯康蒂的象征,他对疾病无能为力,这在晚期电影中多有表现,最极端者是对于死亡的反思,所以在“德意志三部曲”中开始讨论颓废和死亡,颓废和死亡都是神经性疾病所致,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了他晚期风格的独特性。
从电影史上说,以“德意志三部曲”为代表的维斯康蒂晚期风格呈现的是内容与形式上的颓废感,并在电影语言中渗透着诸多巴洛克元素,与新现实主义美学愈来愈远。然而维斯康蒂这种对电影传统的反抗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维斯康蒂对早期风格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逆转,事实上是与罗西里尼和德·西卡一道宣布新现实主义的终结。在他晚期作品中,维斯康蒂思考的丝毫不是新现实主义的界限问题,而是在思考如何走出新现实主义去迎接更深广的电影美学空间;另一方面,在晚期电影中,颓废的影像、矫饰的形式和扭曲的人格虽然与传统形成了断裂,却在影像风格上重构了某种新的内容与形式,仅同性恋主题就在20世纪70年代常常被仿效,这说明新的电影传统已经悄然兴起,与之前的影片相比,可以说维斯康蒂晚期电影中隐藏着现代主义的美学逻辑,这远比对他的转型进行指责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维斯康蒂晚期电影中并不存在背叛,存在的只是从传统走向“新的”传统。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M].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 阿兰·巴迪欧.电影的虚假运动[J].谭笑晗,肖熹,译.电影艺术,2012(5).
[3] 伯特·卡杜罗.世界导演对话录[M].龚心怡,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4]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 彼得·邦达内拉.意大利电影——从新现实主义到现在[M].王之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
[7] 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世界电影史[M].范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 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M].殷宴,周博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 洛朗斯·斯基法诺.1945年以来的意大利电影[M].王竹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0]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