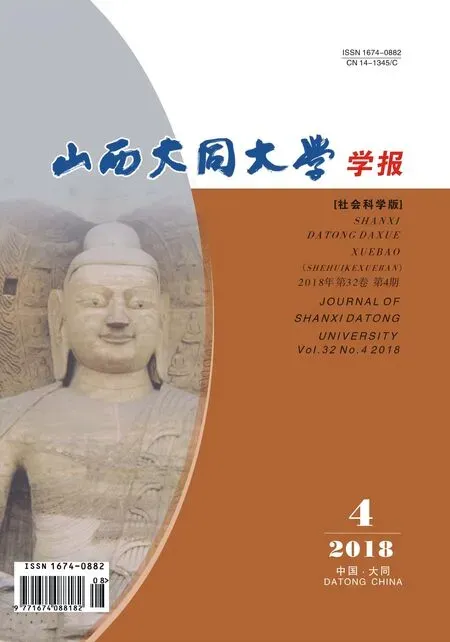张爱玲语言艺术探究
2018-01-29王雁霞
王雁霞
(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 忻州 034000)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作家,由于身处新旧思想交替的大变革时代,为人与为文皆显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张爱玲及其作品就是其中典型。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描写新旧思想激变时期的人伦情感、男女情爱,语言辛辣老道,新鲜活泼。本文从张爱玲的出身、文学素养的形成出发,结合时代赋予她的独特个性,对她的文学语言进行综合解读。
一、文学素养底色
(一)古典小说滋养的深厚功底 仔细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品会发现,她的作品有着端正扎实的古典文学底子,正符合她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出身与学养。尽管她的外在表现、待人接物和中国传统女子有一些不同,但是其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却都是典型的中国女人,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性。品读她的作品,会跳出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形象,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神态风韵,常使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的人物,但却绝不是抄袭,也不是东施效颦。比如在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能够看到每个小姑娘之间,都以“小蹄子”作为称谓,[1](P3)这正是《红楼梦》中众女子口角时的常用语;“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1](P6)出自《红楼梦》第21回,宝玉与袭人赌气时的原话。相似的声气,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张爱玲信手拈来,可见她对《红楼梦》文本非常熟悉。这些化用的语言泼辣辣地将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不由得让人联想那些深宅大院、世宦人家小姑娘的心性模样。
有人说,在《倾城之恋》等后期作品当中,这些古典语言形式的写法被纠正了。但仔细研读、品赏,感觉还是那个着了“红楼梦魇”的张爱玲,只是不再写“摩登红楼梦”,《红楼梦》已化入了她的骨子里。不管是《倾城之恋》还是《小团圆》,张爱玲的文字还是有熟悉的古典小说味道,醇厚自然。不过已经不是曹雪芹的语调,而是张爱玲自己独特的调子。我们能够在小说中“听”到范柳原的声音,而不是贾宝玉的声音。从这一点能够看出古典小说对张爱玲影响非常深刻,是她文学语言的底色,在此基础上,她修炼出了自己的个性。[2]
(二)市井百态呈现俗风俗语 张爱玲从没落封建大家庭中出走,走入市井后,成长为一个独立女性。落入凡间的大家闺秀,感受到了市井实实在在的气息。张爱玲把人生所见,生活感慨,点点滴滴,细细描摹。《倾城之恋》中同样是大户人家的白家,一场相亲展现了热热闹闹的市井。张爱玲不动声色打开了大家庭的门户,让我们看到了家里的明争暗斗,白三爷无奈的胡琴,白流苏幽幽的蚊香……
市井百态,是张爱玲人生磨难之余细细品味的生命气息。日日走过的百十米长的街道,哪家人家吵架,哪些人燃起煤炉做饭,谁家添置些什么,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都进入她的眼底。电车上人们的杂谈,加几句辛辣的点评,就是同一电车上听闲话的路人。坐在乡村戏台下,怀着百般心思看俗到家的民间小戏,观察民间看戏的男女老少,再将这俗世人生的“原生态”铺排在文章中,俗言俗人,真实细致。与没落家庭的脱离,并没有剥离从根底里留给张爱玲的家学教养;堕入凡俗的市井生活,反而给了她由化用到创新的材料与机遇。
二、文学语言的革命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主张书面文字要和口语一致,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终结。经历这个时代洗礼的张爱玲,对文学语言的追求,不仅仅主张用白话写作,更激进地主张用方言写作。她的小说中,延续了古典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更发扬古典白话小说中方言文学的魅力。
(一)方言文学的魅力 从张爱玲和《海上花列传》的纠葛,就能看出张爱玲对方言表现的世情、人物真实性、鲜活性的痴迷。这样的主张,一以贯之表现在她的各种文体中,细节描述、人物形象塑造的关键点,必然应用方言俗语,直说大白话,见心见性。
《海上花列传》被胡适称之为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这部用苏白(苏州方言)写就的古典小说,张爱玲反反复复看,还耗费心血,用国语注释翻译文中的苏白,以至于有“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的说法。苏白是《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语言,文中沈小红和王莲生之间的情感纠葛,用苏白写出来,把沈小红的悲惨遭遇和王莲生的懦弱无情,清楚明白地展现在眼前。
(二)实践方言文学 张爱玲作品中不时跳跃出这样的特色方言。张爱玲后期的小说中,方言写作炉火纯青。如近年面世的《小团圆》,在人物形象塑造、生活描摹中处处可见方言的运用。第三章中“姑姑”与来自合肥乡下的女佣韩妈与之对话:“不做摪(怎样)搞啊?”[5](P70)俏皮风趣。“弟弟”挑三拣四,韩妈用纯粹的合肥方言劝说:“家里没得吃,摪搞呢?去问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给他说了半天,眼泪往下掉。”[5](P89):“快吃,乡下霞(孩)子没得吃呵!”[5](P89)“乡下霞(孩)子可怜喏!实在吵得没办法,舀碗水蒸个鸡蛋骗骗霞(孩)子们。”[5](P89)
张爱玲的小说如《红楼梦》一样,什么人说什么话,人物的身份地位通过方言俗语生动地表现出来。老保姆的方言,合肥人听来,了解张爱玲与合肥的渊源,但并没有减弱整体语言的灵动诙谐、冷峻苍凉。张爱玲回忆起这些过去时光的人与事的片段,仍旧能将隔了几十年的光阴用原话讲出来,可见她对方言情有独钟。
文学的语言,应该就是生活的语言,最原生态的,就是各色人等的方言。张爱玲作品中的上海、苏州白话也不少,各种人的口角当中随时会流露出这种语言的交融来。
张爱玲对各种人感兴趣,对各地方言也非常敏感。她的随笔《“嗄?”?》,考证吴语方言——“嗄”。文中细致详实的考辩和玩味,表现了她对方言的深度了解,也表达了她对方言的保留和应用的主张。她的创作充分吸收民间土语俗语,甚至近乎沉迷,因此成就了她文学语言的生动性、原生态,导致最文艺的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中却并没有“五四”新文学通行的文艺腔,有的只是直白、老辣、形象、传神的文学特征。
三、时代精神的张扬
郁达夫说“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的文学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现象。”“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翻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示在我们的眼前。”[6]他认为体现作家个人生活色彩的文学,才是作家真正的个性化创作,显示了这个作家的个人风采和生命主张。张爱玲在散文中写自己的生活,在小说中描摹类似于自己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展示了自己的文化个性。可以说,张爱玲在小说中演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在散文表现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变革之际的精神特色在她的文字中得以张扬,尤其表现在她的文学语言上。
(一)与旧时代的决裂:从行到言 张爱玲出生在封建社会解体之前,已经支离破碎的封建大家庭中。传统家族伦理中,女性不被重视,但她的妈妈、姑姑,在她之前,率先从大家庭中出走,反抗旧的伦理,带着防身的钱财,谋划独立自强。她们并非实现理想,甚至有更多的不尽人意,但总归开始了谋求女性的独立。张爱玲与旧时代的决裂,是从大家庭中与父亲反目决绝的逃离开始,跟着母亲、姑姑逐渐成长,直到再次的独立。这是她个人成长的历程,也是她的文学创作与旧时代决裂的历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旧时代的终结,从描写旧时代开始。如最经典的《金锁记》,将曹七巧这个鲜活的生命,送入腐朽败落的大家庭,嫁给瘫了的富家儿子。为了金钱的争夺,耗费了自己的一生,无尽的不满足,嫁祸于儿子女儿。曹七巧嫁入大家庭,是走向腐朽;女儿想办法嫁出去,是寻求生命自主的出逃。小说的语言、压抑、灰暗,一如曹七巧被剥夺了生命力的生活。
《半生缘》中主人公看到了新生活的样子,也遇见了爱情,但又被亲情拉回到黑暗中。这篇小说的语言,脱离了些世故,多了单纯的生命气息。
与旧时代的决裂,表现最明显的是,她的文学语言选择了契合时代的白话和更贴近生活的方言。
(二)张扬新时代精神 张爱玲艰难出走后,一个新时代自立自强的女作家成长起来。她的命运和时代同步,她的作品,更是激越着时代女性的风采。她的文学语言,展现这种风采,表现了自己,以及时代风潮下各色人等的命运。这样的文学,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书写,更是时代声音的传达。而张爱玲的女性性别立场,对时代细致深刻的书写,张扬了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自己名与姓的女性的风采,而所谓“出名要趁早!”简直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所有新生力量的口号。
张爱玲的小说是旧时代的总结,她的散文却是新时代的开启。学界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散文成就:“不仅体现在那遍布于作品中让读者惊羡不已的散珠碎玉般的文字和奇语,也不仅仅是让人们捉摸不定、总是充满新鲜感的‘解甲归田式自由散漫’的文章结构。张爱玲的散文,继承了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大胆地进行个性化的追求,毫无避讳的书写着对凡俗而真切的市井生活的好感,在对卑微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寄予同情的同时,也对人性的缺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予以深刻的批判。张爱玲的散文,与五四文学倡导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富于批判精神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7]
张爱玲对古典白话小说的欣赏把玩与摹拟,成就了她文学语言的底色。白话的濡养浸染,让她习得了社风民情最鲜活的语言表达。时代的变革,个人文学创作的成熟,逐渐向个性化的方言尝试。古典文学、民间语言,和她生命的独立、个性的张扬完美融合,形成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