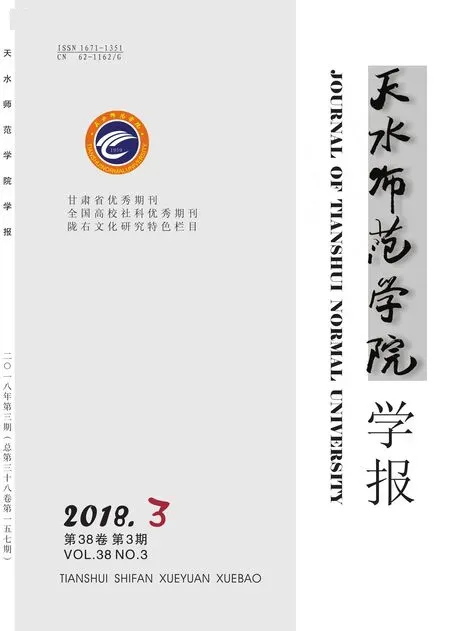陇东南红色歌谣的革命主题演进
2018-01-28李利军李天英
李利军,李天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歌谣作为一种根植于民间的文学样式,通过普通民众的口头创作、口耳相传表达共同的心理诉求和价值取向。其语言浅白、表达直接、形象生动、易于记诵传播等特点往往使歌谣导向激烈而鲜明的政治主题,深度参与社会革命,因此,借口号式的歌谣宣传主张、鼓动民众,成为古代十分普遍的创作改造形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新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以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1]11红色革命歌谣也正是借鉴和发展了这一形式,把革命主题注入歌谣这种民间文艺形式,一方面丰富了歌谣的本体建构;另一方面使“红色印记”深入到根据地和解放区民众的精神领域,成为现代史上革命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
陇东南红色歌谣对时代的反映以及完成推动人民觉醒、团结和斗争的革命任务是通过启蒙性和斗争性这两大主题体现出的。启蒙和斗争的主题渗透并融入歌谣的全过程,从空间分布来看,陇东南地区是指以甘肃省平凉、庆阳、天水、陇南四个地级市为中心的地理空间,这四个彼此相接的地域自伏羲、周、秦始祖文明在此衍生以来,从文化互动、历史沿革、民风民俗、经济形态等方面构成具有一致特色和类型的人文整体。[2]1-27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这一区域的发展,播散了数量众多的红色歌谣,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收录天水陇南红色歌谣41首,陇东红色歌谣78首,高文等编《陇东革命歌谣》收录156首,天水市文化局编《天水民歌集成》收录15首,陇南行署文化处编《陇南地区民歌集成》收录35首,杨克栋编《仇池风》收录陇南红色歌谣14首,郭函殿编《华池歌谣》收录75首,从中可见以陇东地区最为活跃。以时间为序,启蒙性和斗争性的主题沉淀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之前“控诉与揭露”的主题准备期、30年代初“从屈从到挣脱”的启蒙发展期、30年代中期及以后“斗争与歌颂”的革命成熟期三个阶段,革命进程、创作主体等因素影响着各阶段主题的发展趋势。
一、革命前夜的陇东南歌谣:“控诉与揭露”的主题准备
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间,陇东南天灾人祸频仍,民不聊生。旱灾、水灾、雹灾、地震接连相继,1920年海原大地震造成18.5万人死亡,其中陇东南地区5万余人死亡,房屋坍塌无数;[3]2541927~1930年间遍及全省的连年大旱造成寸草不生、颗粒无收、易子而食的难言惨象,甘肃人口从666.5万人锐减了250~300万人,40%的死亡率世界罕见,陇东南作为重灾区,死亡人数远超这一比例。[4]584与极端严重的自然灾害相伴的还有劣绅当道、土匪横行。天水土匪马廷贤、陇南贼匪鲁大昌、陇东陈圭璋、惠彦清等攻袭城镇、烧杀淫掠,称霸一方,为祸百姓。在此背景下,表现仪式、节令、礼俗的高歌远调逐渐被反映时政和苦难生活的歌哭伤乱取代,此时的陇东南歌谣集中反映两方面的情感内涵。
一是底层人民生活的苦不堪言和对压迫的呻吟叹息。如陇东信天游《穷人活受罪》:
天上的星星沙沙稀,地上的穷人穿破衣。
焦头头筷子泥糊糊碗,穷人的日子难上难。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眼泪把心淹。
吃了上顿愁下顿,揭不开祸来难死人。
穿了冬衣没夏衣,六月天翻穿老羊皮。
一没铺来二没盖,又饿又冻实难挨。
五谷里数不过碗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咱可怜。
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人里头数不过咱凄惶。
为人那个不想活,这样的光景实难过。
要穷就穷也安生,财东家要帐如催命。
天气越冷风越紧,人越有钱心越狠。
驴打滚利钱还不完,狗腿子把门槛都踏断。
天下的老鸹一般般黑,天生下受苦人活受罪。
黄连树上吊苦胆,穷人的苦处哟说不完。
青天蓝天紫蓝的天,老天爷杀人不睁眼。
以字字血、句句泪的哭诉反映穷苦人因天人相逼而求生无路、哭告无门的悲苦境地。又如《水冲毛渠井》:
水冲了毛渠井一十三年。老百姓遭大难实实可怜。
一面儿闪上来有钱客官。一面儿土匪生卖人押贩。
一等人驹骡马穿绸挂缎。二等人支牛车好度歉年。
三等人卖妻子家破财散。妻问夫夫问妻泪流满面。
把一岁儿子娃好好照管,咱夫妻重相见鬼门关前。
毛渠井连年洪水,有钱人和土匪又趁火打劫,老百姓家破人亡的惨状和劫掠者富有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长工谣》《长工苦》《脚户调》《蓝桥担水》中凝聚了各类穷苦职业者受罪可怜的命运,《苦蛋蛋》写童养媳七八岁被引到婆家嫁给老汉的苦难和她发出的“不如早死早托生,来世寻个顺心人”的愤激呼声,由于这类歌谣歌哭那个时代百姓的共同命运和苦难生活,在更大域范围内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如《穷人活受罪》、《长工谣》等传遍了陕甘宁、晋冀鲁、鄂豫皖等地区),成为这一时期陇东南歌谣的主体。这类歌谣展现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画面,无疑是典型的“诗史”。
二是朴素坚贞的爱情追求。苦难生活并没有磨灭陇东南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因为歌唱朴素美好的爱情,此时的陇东南歌谣才能在一片黑灰色的基调上点缀了鲜亮的色彩。如唱相思,《眼泪淌的像江河》:
月亮上来一面锣,一夜想郎睡不着。脑壳担在炕沿上,眼泪淌的像江河。”
又如《五哥放羊》: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哟,单等我五哥来上工。
二月里来刮春风,二妹子手拿绣花针。绣上龙凤十样景哟,我问五哥亲不亲。
三月里来是清明,家织户户上新坟。人家上坟成双对哟,五哥上坟独一人。
四月里来四月八,娘娘庙上把香插。人家插香为儿女哟,咱们插香为什么。
五月里来五端阳,糯米棕子包冰糖。雄黄药酒加科香哟,留下给我五哥尝。
六月里来连阴天,五哥放羊寸草滩。身被毡袄打上伞哟,手里又拿放羊铲。
七月里来秋风凉,五哥放羊没衣裳。妹妹有件小夹袄哟,改一改领口你穿上。
八月里来月儿圆,西瓜月饼献当院。人家敬月为团圆哟,咱们敬月缺半边。
九月里来九重阳,妹妹家中细思量。想着想着泪珠淌哟,不见我五哥心发慌。
十月里来天气寒,五哥放羊上高山。天气冷来衣又单哟,五哥放羊实可怜。
十一月里来数上九,五哥放羊进山沟。手扳门槛往外看哟,不见我五哥泪双流。
十二月来整一年,五哥工满回家转。有朝一日天睁眼哟,我和我五哥把婚完。
从女性视角出发,热烈大胆地表达对朴素爱情的渴望和现实处境的不满。如唱爱情立场,《爱的受苦人》:“半边下雨半边晴,斑鸠爱的刺蓬林。鱼儿爱的泉中水,贤妹娃爱的受苦人。”形象地体现了下层女性不慕富贵、不攀高枝的择偶标准,此类表达还有《我就爱个拦羊汉》、《来世还是你和我》、《穷死穷活不变心》等。时代并没有给这些单纯卑微的爱情多少落脚之地,当《走口外》的“妹妹”还在探问“风吹日晒大雨淋,尘世上受不过下苦人。半碗碗黑豆半碗碗米,端起破碗我就想起你。一个东来一个西,什么人逼咱苦分离?”的劳燕分飞时,《哭鼻子》里贪财卖女的“我大我妈”、《媳妇受折磨》里“赛阎罗”的公婆、《傻女婿》里的傻子丈夫以及《小寡妇哭五更》里“杀人的世道瞎眼的天”纷纷浮出了水面。
这些反映农村状况的歌谣表明,面对土豪劣绅对土地的控制和沉重的剥削压迫,农民阶级除了歌哭,缺乏明确的思想意识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唤醒他们改变悲苦命运。这一时期的歌谣把表现生活和反映时政融为一体,歌谣的抒情主体农民阶级压抑地表达着他们与具体或宏观意义上的压迫力量势不两立、怨怒交加的痛苦情绪。然而,宣传自由平等、反抗剥削压迫主题的启蒙歌谣蓄势待发,即将迅速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陇东南大地上以星火燎原之势鼓荡风雷。
二、30年代初的陇东南歌谣:“屈从到挣脱”的红色启蒙
歌谣启蒙性始于五四期间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刘半农、俞平伯等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以歌谣为文学革命大潮下的新诗寻求更多的表达方式,呼应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崇大众易于接受的民间形式,也契合了“平民化”的启蒙需要。与此同时,共产党“一大”发起人兼左翼诗人刘大白、沈玄庐等站在劳动阶级立场创作歌谣,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困苦的心声。[5]76-77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6]的政策;同年鄂西特委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也写道:“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学方面的宣传,多有使用十二月、十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句、六字句的韵文。在许多环境较好的地方,都可以听见农民把这些歌调,提起喉咙高唱。”[7]9当时的红军文艺宣传队专门负责红色歌谣的编写和宣传,在基层部队还有专门的宣传员和山歌队等。这些推行红色歌谣的努力起到了良好效果,据山歌队队员徐光友、徐兴华回忆:“从麻城革命斗争的发动情况来看,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8]306江西赣州兴国地区的山歌,因为影响巨大,还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在政策推动和群众响应的基础上,涌现出不计其数的“红色歌谣”。
除了反抗的呼声和革命歌谣经验的储备,陇东南人民与红军共同奋战形成的鱼水情使歌谣凝练出新的题材和主题,陇东南人民用民歌表情达意的方式及其地貌特征,又成为红色歌谣接受与传播的基础。[9]54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陇东南的崛起和壮大是促成歌谣主题转变的关键条件。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在正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4月,习仲勋、吕建人领导的“两当兵变”建立起陇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在华池和宁县,共产党从对士兵的思想鼓动和宣传走向广大民众,以解脱精神依附和追求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思想启蒙逐渐在陇东南传播开来。针对广大群众和红军战士大多不识字、文化水平低的现状,歌谣作为他们最熟悉、最易被接受的文艺形式,扮演着思想启蒙的重要使命。
陇东南革命歌谣突破反映生活主题和凸显爱情表白的传统内容,启迪民众从受奴役、被压迫的认命屈从的意识中走出来,敢于挑战和否定旧有的统治秩序。如“日头出来端上端,南粱来了刘志丹,志丹练兵又宣传,要把个世事颠倒颠”,迎接红军为老百姓开辟的崭新的生活出路,如:
红旗展,红旗红,红旗下面是红军。红军本是受苦人,受苦人儿要翻身。
红旗飘,红旗绕,红军力量真不小,土豪劣绅都打倒,民团跑了赃官逃。
红旗飞,红旗扬,分了田地分牛羊,分了窑洞又分粮,老百姓来喜洋洋。
红旗来,红旗去,咱们南梁立苏区,穷人当家作了主,不受压迫不受欺。
红色歌谣生动反映出高涨的革命形势给穷苦人带来了翻身解放的光明前景,分地分粮、打土豪、“穷人当家做主”的权利,通过革命歌谣的传播教育,这些潜意识中的愿望诉求被唤醒,民众不再陷入“养下娃娃老蒋的,挣下钱是保长的,下下鸡蛋甲长的”的苦难循环,开始积极挣脱人身枷锁、争取和维护自我权利的意识。人们敢于接受并积极响应革命,如: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后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一面面红旗土佥畔上插,快把咱们的游击队引回咱家。
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好喝。
大红的个犊牛自带耧,游击队来了咱们跟上走。
三号号盒子红绳绳,跟上咱们的游击队闹革命。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跟上咱们的游击队上南梁。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游击队跟的是刘志丹。
山羊绵羊五花子羊,刘志丹跟的是共产党。
红豆豆角角熬冬瓜,跟上咱们的刘志丹打天下。
按照葛兰西推崇的埃莫拉奥·鲁比埃里的划分,此阶段的创作主体既有“人民自己”,也有“为了人民”的人。①在本书《论民歌》一文,葛兰西引述埃莫拉奥·鲁比埃里关于民歌划分的三种类型为:一是由人民自己创作或为人民创作的诗歌;二是为人民所作但并非由人民创作的诗歌;三是既不是由人民创作,又非为人民创作,而是被人民接受,使之适应自己的思想、感受方式的诗歌。[10]169陇东南地区的百姓在红色歌谣的启蒙中获得了他们急需并易接受的知识和文艺作品,提高了有关自由民主等思想的认知,鼓舞起斗争热情,陇东南红军力量在这样的启蒙宣传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坚实。
三、30年代中期以后的陇东南歌谣:“斗争与歌颂”的革命热情
以1934年11月在南梁创建中国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标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陇东南开花结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陕甘红军和人民群众以南梁为核心,在甘肃东部与陕西中、北部交界地区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惩治土豪劣绅、抗击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等红军主力部队相继挺进陇南、天水,突破国民党渭河防线,发动“成徽两康战役”,打土豪、惩污吏,先后在12个县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的发展激起了百姓巨大的革命热忱,红军改编创作的歌谣点燃了他们心底的怒火。在沟道山梁间的无数村落里,“在这些人类学家所谓的‘小传统’社会中,歌谣(山歌)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它不仅是地方特有的传统习俗,也是底层民间社会表达情感、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一文化资源,努力把‘大众’改造为‘先锋’或者说‘新兴’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文化基础中植入了‘红色’印记。”[11]109-110
被红色歌谣开启了新思维和新视野的陇东南民众,从积极接受共产党改天换地的革命成果,发展到主动自觉地投入到革命活动,自己争取解放和平等的前途,实现了从革命的旁观者、接受者到革命的参与者和主力军的身份转变。“跑跑跑,快快跑,豪绅头上是目标,拿起斧,拿起刀,要杀掉呀么要杀掉!工农联合心一条,大家齐心向前跑,地主、豪绅、军阀、官僚,铲除掉呀么铲除掉!”革命的呼声汇成振聋发聩的合唱洪流,显示了觉醒后的民众一致的革命斗志。
红色歌谣充满激情地反映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打开监牢门,罪人放出门,死刑上犯人更是欢迎。思想又思想,思想打武装,打起了武装闹上一场。豪绅要拉完,地主要推翻,革命闹成功好不喜欢。革命要成功,先杀韩俊卿。杀不了韩俊卿,革命就站不稳”,恶霸地主韩俊卿盘踞在华池县,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早已激起群众的仇恨,这首歌谣通过开监牢、杀豪绅,传达了百姓不可遏制的怒火,表达了人民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男人女人都是人,为啥男女不平等?恨爹恨娘不顶用,封建制度是祸根。晴天响起一声雷,组织起妇女联合会。齐心推翻三座山,妇女们才能把身翻”,受封建压迫最重的妇女一旦觉醒,革命热情丝毫不逊于男子;“要解恨,斗豪绅,要太平,打日本;要想永世不受穷,赶快投奔贺老总”,革命歌谣把散布在陇东南人民心间的斗争愿望汇成了强大的革命合力,这种聚成合力的革命意识激励革命力量前赴后继地投入到反剥削、求解放的战斗中去。游击队员和贫苦农民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仅徽县、成县、两当、康县就有三千余人加入了红军,革命力量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12]76
和高扬着革命热情的斗争书写紧密联系的是对革命、对红军、对领袖人物的热情歌颂,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新阶段红色歌谣的斗争性特征。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遍地开花的新政权的创建极大鼓舞了陇东南民众,对这支带领他们推翻旧政权、改变苦难生活命运的红军队伍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和歌颂,并反映在多个层面,如“放羊娃娃揽工汉,争相报名把军参。红军是咱大救星,要想翻身当红军”写积极参军的热情;如“大妈河边洗衣裳,洗了一件又一件。洗下衣裳给谁穿?哎咳哟!子弟兵儿千千万”写后方的积极支援;如“大娘炕头补军装,红军担水装满缸。军爱民来民拥军,咱们军民一家人”写军民鱼水情。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革命领袖刘志丹的歌颂。在百姓的心目中,刘志丹是“精脚片子打裹缠,腰里别的手榴弹”的朴素革命形象,还“不拿架子蛮和善,半月二十常见面”、“打土豪、分田产”、为战士们“连夜打麻鞋”,所以老百姓夸赞“刘志丹真英雄,除害为百姓。穷人都要跟他走,闹呀闹革命”,对刘志丹的赞美“折射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折射了老百姓对自己领袖的一种期待。同时也暗示老百姓的一种心态,由于他们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他们很难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为了坚定自己战胜敌人的信心,他们往往神化自己的首领,实际上也是神化自己,借以提升自己的士气,也是建构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方式。”[13]21
当然,启蒙性和斗争性的双重主题演进不是单向的变化,而是相互渗透中又有侧重。启蒙性唤醒了人民的革命意识,使百姓认识到革命不只是杀富济贫和均贫富,更重要的是要推倒封建制度,建立起多数人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斗争性体现着人民的革命意志,百姓成为革命的一份子,拿起武器和压迫剥削势力展开坚决斗争,热情讴歌和赞美红军以及领袖。启蒙性是斗争性的基础,斗争性是启蒙性的递进,启蒙性没有斗争性的实践行动就成了空中楼阁,斗争性没有启蒙性的思想引领也就会陷入农民起义的悲剧结局。这种相互依存的主题表达,既是陇东南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党发动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既全面反映了陇东南压迫剥削与反压迫剥削的社会历史,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生动记录了轰轰烈烈的陇东南革命斗争,表现出美与丑、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审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