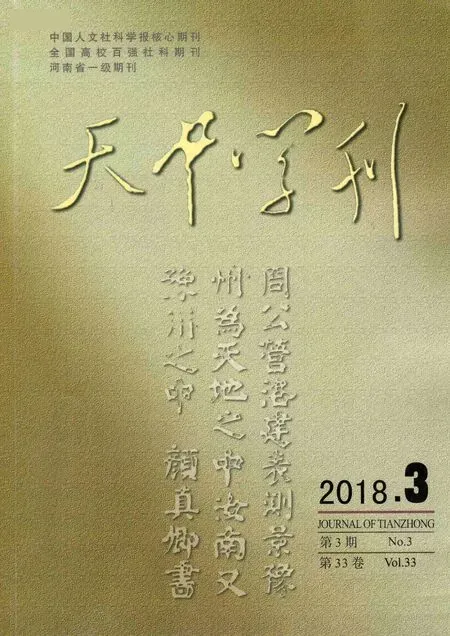近代国人对羽毛球运动的认知探析
2018-01-27尚方超杨水金
尚方超,杨水金
(河南大学 a. 历史文化学院;b. 体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羽毛球是一项深受国人喜爱的体育运动,集竞技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不仅在民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中国的专业运动员在世界各大赛事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林丹、傅海峰、谌龙、李雪芮等为代表的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世锦赛、苏迪曼杯等国际顶级赛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加鼓舞了社会各界的羽毛球风尚。可以说,羽毛球运动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体育强国形象的一个标杆,而且被越来越多的国人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羽毛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一个世纪,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近代中国,国人对羽毛球运动处在认识的阶段。由最初接触、渐有兴趣,到关注增多、尝试摸索,再到创新改进、成立组织,国人对羽毛球运动的认知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在这个长达数十年的认知阶段,国人对羽毛球运动也进行了一些探讨。比如,羽毛球究竟是欧风东渐的产物,还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运动?这个问题即便在今天也存在着不小的争论。要切实了解羽毛球运动的演变历程,就要回归到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场,通过原汁原味的文献史料,挖掘近代国人对羽毛球运动发展的认知。作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最生动形象的见证,以《申报》《现代体育》《中国青年体育》等为代表的报刊关于近代羽毛球的各种新闻消息、评论介绍等内容十分丰富,对这些珍贵史料的勾勒和梳理,可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线索和思路。
一、土生土长:羽毛球运动的创设和探索
近代中国的羽毛球运动,难道完全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恐怕不能轻易地给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它也是中国人民主动探索、积极创设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可谓土生土长。在近代,有不少人对羽毛球运动产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探究,并指明羽毛球运动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
1945年,对羽毛球运动深有研究并大力倡导的陈海涛发表了《我们的发明——板羽球》一文,对羽毛球的产生历程、球拍用具的改进、场地的设置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认为“我们现在所盛行的各种球类运动,只有板羽球一项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当然值得我们研究和注意”[1]186。一位署名为“浪”的作者也认为,板羽球就像三轮车一样,是中国在抗战期间发明的新事物,“战时发明的板羽球亦是轻便合理的游戏之一种……很值得提倡”[2]17。羽毛球的发明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发现认识阶段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自1924年成立以来便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性体育运动的领导组织,宗旨在于“联合全国体育团体,促进体育之进步;主持全国业余运动,既制定运动统一规则及运动标准,并增进运动员仁侠之精神;关于国际运动比赛时,由本会联合各区负责进行”[3]497。1939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干事魏振武、史麟生和李国堂,应驻在贵州都匀的税务总团的邀请前去担任体育教官。他们除了致力于本职工作外,对于附近的苗民生活特别感兴趣,因此留意收集有关苗民风土人情、休闲娱乐的材料。有一次,第三营的医官李天助从团部回去,途中看到苗民用木板拍击类似毽子的游戏,观望了许久。这种游戏所用的毽球是在小竹管上插3到5枚鸡毛,用木板互相拍击,以落地为负。李医官随即要了一副,交给了3位体育教官,并说明所见。魏振武等三人颇感兴趣,立即尝试拍击,并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项具有推广价值、可为更多人所接受的运动。
(二)改进推广阶段
为了更好地改进和推广这项运动,魏振武等三人在运动形式、球拍用具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在运动形式方面,他们认为随意拍击毽球所引起的兴趣不易持久,于是“试验着用比赛的方式二人或四人隔网对垒,就用乒乓球拍在网球场内拍击,以落地为负,由生疏的拍击逐渐产生了高深的技术,由比赛所得到的乐趣益见显著,尤以球在空中旋转前进,是一个绝大的成就,于是定名为‘鸡毛球’,并制定简单规则,择机公开表演,全国官兵,极感满意,遂竞相仿效,盛极一时。但当时条件简陋,经魏君等三人悉心研究,力求改进,此项游戏,遂粗具规模,因鸡毛球系Badminton之译名,为避免混淆,又改称‘羽毛球’。”[1]186–187由随意性拍击,到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隔网对抗,羽毛球逐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由简单的游戏走向正规的运动。
在球拍用具方面,魏振武等三人也进行了多次改进。苗民所用的毽球是在小竹管上插3到5枚鸡毛,用木板互相拍击,在球、球拍、场地等方面均较为粗陋,他们一直在尝试改进。后来,他们去了重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部工作,闲余之暇,对球、球拍等继续加以创新改进,“几经取舍,乃成现今之完全板羽球”[4]105。就这样,球与板均由粗陋逐渐变为精致,最终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标准。
“板羽球运动是由球、板、网、场地配合起来而由二人或四人所造成的比赛游戏,两人谓之单局,四人谓之双局。球之重量为四至六公分,底托则以三至四公分为度;羽翎长度以十至十二公分最佳,翎上齿数以八至十为宜;旋转次数以至二公尺高度自然下落能旋转二次为妙;球拍用〇、九公分至一、一公分之木板做成网球拍之形式,拍子长二十公分,阔十七公分,拍柄长十五公分,柄的直径由三至五公分;网阔至少六十公分,至多七十公分,网孔以二五公分为度;用直径不足〇、四公分之铅丝绳或麻绳穿过,并在其两面中四至六公分阔之白布连网边包缝,网之两端系于球场两边之柱头上。柱高一、六五公尺,树于距边线中点之一公尺处,网之中央应高一、五公尺,球场应为一长方形之平面,单打双打球场均长十二公尺,单打阔四公尺半,双打六公尺半,全场各线应以四公分至六公分显明之白线画成,各线之丈量均以线之外线为准。”①[5]36从这段对羽毛球、球拍、球网、场地等的详细描述可以看出,经过改进后的羽毛球已经成为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体育运动。
(三)完善规则阶段
经过改进后的羽毛球运动,逐渐进入广大民众的视野,在社会上渐渐普及起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著名体育教育家董守义,对羽毛球的发明十分满意,商定后称其为“板羽球”,并郑重地介绍给西北师范学院的体育系。羽毛球作为当时的一项新生事物,社会上对其的称呼一直不统一,大致有毽球、板羽球、鸡毛球、羽毛球等称呼。名称的混乱,代表着国人对这项运动认知的不统一,自然不利于运动的推广与普及。
名称确定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拟定出羽毛球运动的规则和比赛方法,规范球、球拍、球网等比赛用具,正式将其列入各项运动之中,“由此,这项活动也就成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了”[6]7。名称的统一、规则的制定、用具的规范等,使羽毛球由贵州大山深处苗族的简单游戏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正式体育运动,也使其运动价值由单纯的趣味娱乐性变为趣味性与竞技性融为一体,更使社会各界对羽毛球运动有了统一的认知。
最终,羽毛球运动发展成为一项竞技性与趣味性共存的有自身规则的隔网对抗的现代运动。虽然当时名称是板羽球,并未采用羽毛球这一称呼,但这更多的是为了凸显中国自主创造的考虑。从运动的用具、球场的设置、比赛的规则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板羽球和羽毛球只是名字上的一字之别,并无本质差异。可以说,板羽球是一项灵感、发明及创造都来自中国的现代运动。
二、欧风东渐:国际羽毛球运动的介绍和宣传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武力,开始侵略中国,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长期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欧风东渐的历史进程,如西学的输入、西方风俗的移入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现代体育的形式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影响着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此时,国人开始关注和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比赛,以体育的视野诠释着近代国人的精神认知。现代羽毛球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20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主要在上海、天津、北京等一些开埠较早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等地方开展。最初,这项运动主要是一些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军人等在留驻中国期间为了强身和娱乐所开展的一项活动,后来逐渐流传到我国的民间。
(一)西方羽毛球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与传播
天津、上海、北平作为近代中国的重要城市,其羽毛球运动开展十分活跃,引领了全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天津青年会体育部干事李友珍率先在华人会员中开展羽毛球运动,“每星期二、五组织杨锦奎、陶少甫、翟士齐等 10余人在基督教青年会馆进行教学、训练”[7]215。1928年3月,天津华人羽毛球队与外侨队举行了首次羽毛球比赛。由教学训练而竞技比赛,这是近代天津羽毛球发展的重要举措,但这时的比赛仅限于天津。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不同地区球队之间的比赛交往才相应增多。
1932年3月,北平青光羽毛球队一行5人赴天津,在英租界球场分别与天津西商队和青年会队进行了比赛。这次跨地域的比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北平、天津运动界,因此次比赛而对羽毛球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提出举办华北公开单、双打锦标赛的倡议,项目设有男子单打、双打及男女混合双打。
20世纪30年代,最早代表中国参加羽毛球比赛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南洋归国华侨学生,他们组成了一支羽毛球队,取名“飞梭队”。1936年,飞梭队参加了租界的羽毛球乙组联赛并一举获得冠军。1939年,飞梭队打进了上海租界羽毛球甲组联赛,并夺得团体冠军,洪德全、侯树基两位选手还获得双打冠军。1944年,上海羽毛球协会成立,这是现代羽毛球运动传入中国后最早的羽毛球运动组织。1946年,上海青年会举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地点在中国青年基督教会内,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训练班羽毛球的课程内容由世界基督教会派美国人巴克利执教。后来,北京也举办了类似的训练班。1948年,民国第七届全运会首次将羽毛球列为表演项目。
抗战时期,受日本侵华的影响,羽毛球活动仅保留在少数地区的学校里。194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有洪德全、温孔文等六七名华侨学生经常在该校的交谊大厅进行羽毛球活动。后来,体育教师周家骐将交谊大厅内的篮球场改为4块羽毛球场地,参加的人数逐渐增多,并有教职员工的子女参加,电影明星陈云裳也常到学校打球。至1942年,羽毛球运动在圣约翰大学已经非常盛行,许多人将它作为业余体育活动,一到周末,常有外校学生到圣约翰大学进行友谊比赛。
从《外部周刊》保存下来的文献看,“中华民国”驻外领事馆也经常开展羽毛球活动,以丰富职员的业余生活,增强职员的身体素质。1935年,“中华民国”驻棉兰领事馆职员同友人一起练习羽毛球[8]8,该刊记者对此专门进行了拍照。1935年,“中华民国”驻望加锡领事馆领事组织成立羽毛球协会,进行羽毛球运动。“望埠华侨虽数将二万,然平日除教育界中人之外,几皆工作而后,毫无户外运动,以调济其身心。此种情形,尤以商界为最。王领事有鉴于此,乃于上月约同本埠光华学校校长王世保君发起组织一羽毛球会,因羽毛球易学,且所费不多,邀集同志,各捐款项,筑一水泥硬地羽毛球场于光华学校校园中,参加者有本地侨商男女会员十余人”,“日来报名参加该会,已有多人,全城闻风而起,自行组织者亦已十有余起,每日下午四时以后,男女携羽球拍者满街皆是,亦可见羽球在此间已风行一时矣”[9]15。天津、上海、北平的羽毛球活动之所以开展得十分活跃,是因为这些城市较早地与外界进行了交流,受欧风东渐的影响较深。在这一时期,基督教青年会、华侨、学生等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展了国人对羽毛球运动的认知,使现代羽毛球运动在中国更加普及。
(二)国人对国际羽毛球比赛的报道与宣传
对国际羽毛球赛事的报道,可以拓宽国人的视野,有利于中国羽毛球运动与世界接轨。上海《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非常重视体育文化的宣传,经常对一些国际重大羽毛球赛事进行跟踪报道,让国人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到国际羽毛球竞技水平发展情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报道华莱盾国际羽毛球锦标赛。1939年,国人首次参加华莱盾国际羽毛球锦标赛,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申报》进行了跟踪报道。
3月8日,《申报》报道:“1939年华莱盾国际羽毛球锦标赛,报名参加者计葡萄牙、法国、英国、北美洲、丹麦、苏格兰、澳洲及中华等八单位。按中华参加羽毛球尚属创举,其实力如何尚不知,秩序业已排定,第一周中即轮值与英国角逐。”[10]
3月15日,《申报》持续跟踪:“初赛中即遇英国,已于日前在斜桥总会赛毕。结果中华队实力强劲,以十五对八及十五对〇直落二大败英国。双方出席者,中华为王曾两君,而英国则为史笃克与菲洛特。”[11]
3月16日,《申报》继续报道:“华莱盾国际羽毛球赛,自日前中华淘汰英国后,昨又传捷报。男子单打初赛,华将甘氏,以直落三胜名将雪而佛,晋入第二周,此后劲敌已去,设无意外,则必得决赛无疑。闻第二周内,即将与日前胜巴士德之华将王泽鑫对垒,其他方面女子单打及双打,均已开赛,结果寇的斯夫人等告捷。”[12]《申报》还记录了比赛对垒的详细比分。
3月23日、24日,《申报》接连发出“羽毛球单打赛,王林受挫”“国际羽毛球赛,澳洲获决赛权”的报道。
3月30日,《申报》对此次锦标赛的决赛盛况进行了报道:“羽毛球男女双打及混合双打决赛,昨下午五时半在斜桥总会举行。首场混合双打,欧特莱兄妹对勃顿夫人及米西、欧氏兄妹,以十八对十五、十五对八击退勃米,荣膺混合双打锦标。女子双打赛,欧特莱小姐与寇的斯夫人搭档,会战格拉斯莱夫人及霍惠尔小姐,双方实力悬殊,赛成一面倒,结果欧寇组以十五对九、十五对十连取二局,夺得冠军。末场男子双打决赛,桂氏史笃克组与勒特米西组对垒,桂史组以十五对十二,十五对十,吿捷。桂史获得男双打冠军,赛后当场给奖。本届羽毛球于焉告终。”[13]
《申报》对1939年华莱盾国际羽毛球锦标赛的报道,将比赛的盛况客观、全面、详细、真实地展现在于公众,加深了国人对国际羽毛球运动发展的认识。其中,中华选手所表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更是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三、遍地开花:羽毛球运动的价值认知
(一)近代国人热爱羽毛球的原因
囿于价格、设施、场地等限制,羽毛球运动开始流行之际,主要集中于上层社会。虽然如此,但“惟以其亦有特长,自有相当价值”[14]63,羽毛球运动很快就流行起来了。那么,羽毛球的“相当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我国新兴的球类运动——板羽球》一文认为,国人喜爱羽毛球是“由于它本身的极便宜的缘故,它是一种极简便的游戏,而由于它丰富的活动量与引起浓厚的兴趣,它又可以与网球排球等共参与于正式球类比赛的项目中,所以提倡以后,不特普遍各地,而且更普遍到各阶层,正可说他是男女老幼俱宜,四季均合的一种有趣的游戏运动”[5]36。
《三轮车与板羽球》一文指出:“战时发明的板羽球亦轻便合理的游戏之一种,打网球固好,布置场地,购置工具,是相当贵与费事的。而且打网球已偏于剧烈运动以内,球打得不好或对手非敌,往来拾球,常常累得满头是汗,减低兴趣。乒乓球为网球之缩影,购置简易也不费力,只是太嫌机巧,不大过瘾,只有板羽球大小轻重适中,男女老幼随时随地可玩,兼有二者之长,很值得提倡。”[2]17
施养珍在《羽毛球》中认为:“羽毛球是与网球相仿的一种游戏,可是一切都比网球经济。他的场地仅及网球的三分之一,球的价格仅及网球的二十分之一,在这百物都有替代品的环境中,宜乎羽毛球的兴起了。”[15]58这自然有些夸张。文献显示,在当时羽毛球要比网球贵一些,如1939年上海惠康网球拍公司的广告显示,网球每只四角半,网球拍每只五元半,羽毛球每只九角半,羽毛球拍每只四元。其实,这种情况很正常,受战争影响,中国的物价情况每日都会有巨大的变化,更别说1939年至1943年的物价了,而且这些价格也会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公司的进货渠道等因素而有差异。
杨扬在《关于板羽球》中说:“这球很简单,也很有意思,我相信不久可以风行一时的。”[16]16
陈海涛在《我们的发明——板羽球》中总结了羽毛球较之于其他球类运动的几项优势,认为羽毛球有6个方面的“独特的精神”:用具简单,可自制自用;价钱便宜,适合经济原则;场地较小,易于设置,地面只求平坦,无须施工;性质和缓,运动量有伸缩性,不论男女老幼,均很适合;规则简单,容易学习;击球发声,清脆悦耳,球在空中旋转前进,极为美观[1]188。
也有杂志在宣传时,用羽毛球的减肥功效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医药球,骑马,网球,羽毛球,滑冰球,乒乓球及弓箭等游戏亦可退肥”[17]27。
总的来说,国人热爱羽毛球的原因主要如下:第一,运动量可控,适合各个年龄阶段和社会阶层,保证了受众基础;第二,操作简便,规则简单,可随时随地玩,室内室外均可;第三,趣味性强,容易激发参与者的浓厚兴趣,适合娱乐,也适合竞技;第四,经济便宜,购置工具与布置场地都比较容易;第五,能保证合适的活动量,可以减肥和健身。正是这些认知使得国人对羽毛球的热爱逐渐加深。
(二)近代国人热爱羽毛球的盛况
羽毛球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人群方面由上层社会普及到普通民众,在地域方面由沿海大城市推广到一般地区。通过文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羽毛球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真实场景。最终,羽毛球不仅是政府机关、学校团体等机构职员工作之余的娱乐比赛,更走入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通生活中。
1932年,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举办羽毛球比赛,“学生高兴,努力练习,以期胜利”[18]526。
1937年,上海举办羽毛球联赛,“本季进行成绩较好,共有二十五队参加,有一百七十二球员之多”[19]17。
1940年,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体育团体精武体育会成立了羽毛球队。“最近成立之羽毛球队,由李飞云先生担任教导,因勤加练习,进步极速,欢迎各界约期比赛。”[20]16
1942年,中国健美运动的元老曾维祺在上海创建了现代体育馆,发行了《现代体育》杂志,大力倡导“大家玩玩羽毛球”[21]25。
1943年,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公余生活励进会,主办了公开个人羽毛球比赛。比赛“以提倡体育增进健康,及养成正常娱乐之习惯为宗旨”[22]19,参加者极为踊跃。
1944年,西安市银行界同仁进修班体育组主办羽毛球比赛。《雍言》杂志详细记述了这次羽毛球决赛的精彩过程:“本月十七日为板羽球决赛日,我行对亚西,我行选手为刘渐新、杜亚光二君,亚西为吴国华、张明英二君,由亚西银行经理姚伯言任裁判,双方实力均强,战来颇为精彩,刘君发球极妙,着力不多而恰到好处,往往擦网而过落于‘近线’界内最近之处,使对方措手不及,杜君抽球接球迅速,吴君压球亦不弱,激战约三十分钟,终以二比零我行荣获冠军。”[23]110
1946年,广州大学附属小学开始在小学生中开展羽毛球运动,“该部近将售章捐款所得拨购羽球拍网等多套,并于球场上增辟一小型羽球场,小朋友们对此种新玩意,兴致盎然,闻此项设置,在本市各小学中,尚属创举”[24]5。
1947年冬,沈阳大雪,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职员打羽毛球的热情依旧,“塞外早寒,虽时仅初冬,沈市已数度飞雪,十月二十三日初雪,运动场早经冰雪封冻,爱好运动同人,多转移阵地于第二办公厅前空场打板羽球”[25]34。
羽毛球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国人对羽毛球的认知也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中国近代羽毛球的诞生和发展,是土生土长与欧风东渐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近代国人的自主创造,也有西方体育的鲜明影响。板羽球、羽毛球等不同的称谓,反映了近代中西体育交融发展的时代印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向世界学习与接轨,西方现代羽毛球运动最终在中国占据绝对地位,板羽球也完全融合进国际羽毛球运动当中。这些都反映了近代国人对羽毛球运动认知的变迁,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羽毛球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此段文字中的“〇、九公分”应理解为0.9厘米,余同。
[1] 陈海涛.我们的发明:板羽球[J].中国青年体育,1945(3/4):186–193.
[2] 浪.三轮车与板羽球[J].青年生活,1946(创刊号):17.
[3]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章[J].教育与人生,1924(39):497.
[4] 佚名.社教动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制板羽球[J].社会教育,1943(3):105.
[5] 继章.我国新兴的球类运动:板羽球[J].军中娱乐,1947(2/3):36–37.
[6] 谢朝权,魏协生,吴天想等.中国羽毛球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7.
[7] 郭凤岐.天津通志:体育志[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215.
[8] 佚名.驻棉兰馆事馆同人公余与友人练习羽毛球[J].外部周刊,1935(55):8.
[9] 佚名.驻望加锡领馆通讯[J].外部周刊,1935(93):14–15.
[10] 佚名.国际羽毛球锦标赛,中华加入角逐[N].申报,1939-03-08.
[11] 佚名.国际羽毛球锦标赛,中华一鸣惊人[N].申报,1939-03-15.
[12] 佚名.羽毛球男子单打赛,甘氏昨胜雪而佛[N].申报,1939-03-16.
[13] 佚名.羽毛球赛结束[N].申报,1939-03-30.
[14] 赵亚民.济南体育消息:羽毛球运动[J].勤奋体育月报,1934(7):63.
[15] 施养珍.羽毛球[J].现代体育,1943(1):58–61.
[16] 杨扬.关于板羽球[J].新运导报,1943(3):16.
[17] 佚名.消瘦农场种种[J].青年知识画报.1938(11):26–27.
[18] 佚名.各附校分校消息[J].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1932(30):525–527.
[19] 佚名.一周中之精华:本埠羽毛球赛[J].竞乐画报,1937(11):17.
[20] 佚名.会务动态[J].精武丛报,1940(1):15–16.
[21] 佚名.积极推动健身运动的现代体育馆[J].现代体育,1942(创刊号):24–25.
[22] 佚名.新运工作人员公余生活励进会主办卅二年度公开个人板羽球赛[J].新运导报,1943(3):19.
[23] 佚名.无线电:1944年 12月[J].雍言,1945(1):110–113.
[24] 佚名.校友动态[J].广州大学校刊,1946(16):5.
[25] 佚名.会内简讯[J].物调周刊,1947(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