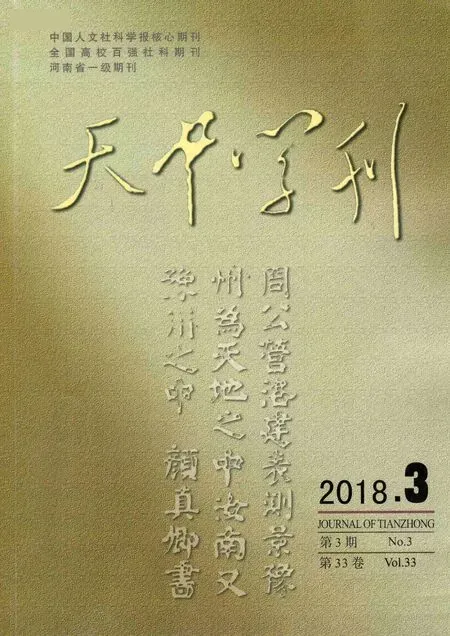扬州学派名家朱彬交游补考
2018-01-27程希
程 希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扬州学派名家朱彬(1753―1834年),字武曹,号郁甫,江苏宝应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举人。朱彬著有《礼记训纂》49卷、《经传考证》8卷、《游道堂集》4卷等。《清史稿》卷481、《清史列传》卷69等均有其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其归为皖派经学家之列,但关于其卒年则误记为 81岁①,实则朱彬享年 82岁。关于朱彬之详细生平,宝应朱氏后人,朱彬六世孙朱庆裴编纂有《朱彬先生年谱》②一书。该书为朱彬首部年谱,其筚路蓝缕、开辟榛莽之功自不容忽视,但作为首创之作,疏误脱漏之处亦为数不少,笔者曾撰文略加更正③。对于朱彬之交游情况,蓝瑶《朱彬交游考述》一文初步予以探讨,得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李惇、汪中、邵晋涵 6人④,后来在其硕士论文第一章第二节“朱彬的交游”中增加汪喜孙 1人⑤,但两者相加不过7人,且基本限于其友朋一辈,未能全面反映朱彬毕生交游之概况,未免有遗珠之憾。有鉴于此,笔者重新梳理相关文献,对朱彬交游情况补苴缺漏,另考得乔亿、朱赛、贾田祖、范鏊、叶世倬、吴瑭、陆继辂等7人,当为考察朱彬诗学观、古文观、理学观乃至医学观之重要材料。今按其年齿先后为次胪列如下,使读者对朱彬之生平学行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对于深化扬州学派个案研究及宝应朱氏家学研究当不无裨益。
一、乔亿
乔亿(1702―1788年),字慕韩,号剑溪,江苏宝应人,乔莱孙、乔崇修子,善谈论,以国学生应棘闱试,不售,辄弃去,专肆力于诗,其五言宗汉魏,其近体亦不屑作大历后语。时沈德潜主东南坛坫,海宁查氏以诗鸣浙西,亿与之游,颇能自树一帜。乔亿著有《元祐党籍传略》《暮齿宜鉴录》《艺林杂录》《小独秀斋诗》《窥园吟稿》2卷附《江上吟》1卷、《三晋游草》1卷《附录》1卷、《夕秀轩吟草》1卷附《惜余存稿》1卷、《剑溪文略》1卷、《时燕石碎编》1卷、《剑溪外集》1卷、《素履堂稿》1卷、《小独秀斋近草》1卷、《集古》1卷、《古诗略》《兰言集》《大历诗略》6卷、《杜诗义法》2卷、《剑溪说诗》2卷《附录》1卷、《杜诗偶评》《诗蒙记》《王孟韦柳诗评》《乔剑溪遗集》等。乾隆六十年(1795年)朱彬曾为
乔亿遗著《兰言集》作序。乔亿乃朱彬祖父一辈,以诗名江淮间,并以此提携后学,邑中人士多以其为师,朱彬伯父宗光、叔父宗大皆终身受业,朱彬父宗贽亦常向其请教诗艺。朱彬少时亦曾以诗向乔亿请教:“忆童稚时以诗请业,翁谬许为可从事于古,或有言于翁者曰:‘朱氏子,其父方教以帖括,将以求科取名。先生顾以诗教,毋乃盭乎?’翁笑不应。越日,余再以诗进,翁正告之曰:‘吾视子之材,方期以大且远者。慎毋以诗自汩。’余于是悚然不敢为诗。”[1]613朱彬本来有很好的诗歌天赋,其晚年曾说:“予束发即好诗。时侍先祖,命题构思,每成一诗,先祖辄色喜。”[1]615但世重科名,朱彬之父希望其攻习时文,邑人亦以此提醒乔亿,乔亿因之不便勉强,本也可以理解,但由此导致朱彬自此不再作诗,至今无一首诗传世,却不免有所遗憾。朱彬后来也曾有悔意:“迄今三十年……因复自悔,假而少即肆力于诗,亲得翁之指授,庶几万一有所成就,厕名篇末,有余慕焉,为慨焉三叹而识之。”[1]613朱彬最终虽未能成为一位诗人,但他对诗歌却自始至终保持着热爱,也从未放弃过对诗艺的钻研。他广泛涉猎大量古今诗作,对先祖中有朱应登、朱曰藩、朱克生等著名诗人引以为傲,称“吾邑本风雅之宗,而吾家实开其先”[1]617–618,并自觉承担起传风续雅、不使断绝的责任,不仅搜集大量清初至清中叶同里诗人诗作汇编而成《白田风雅》24卷,还撰有诗文评类著作《游道堂诗话》,除此之外还为不少亲友及前辈诗人如朱应辰、乔亿、朱赛、叶世倬等人诗集作序、跋⑥。从中不难看出朱彬着意保存乡邦文献、阐扬先贤流风遗韵之良苦用心,亦可见其在诗歌上造诣匪浅,值得重视。究其原因,除受家风家学的熏陶浸染之外,同邑前辈诗人乔亿、朱赛等的关爱提携亦不可忽视。《白田风雅》收乔亿诗61首,为诸人之冠,足见朱彬对其推崇。《游道堂诗话》评其诗曰:“先生诗早宗六朝三唐,晚岁肆力于杜。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与沈尚书德潜、沈光禄起元为忘年交。然诗品清高深稳,不难上掩古人,不因揄扬而重也。”[2]353此外,朱彬还在《剑溪先生墓表》中再次追忆其18岁时以诗向乔亿请教的情景,乔亿勉励他:“以子之材,当务其大且远者,诗非所以涃吾子。”而朱彬也自称“余辍诗不为而求六艺自兹始”[1]634。可见朱彬对此事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乔亿对邑中后学最为喜爱者为朱彬及刘台拱二人,曾对二人嘱托:“吾老矣,身后茫昧不可知,唯赖子与端临尔。”[1]634既有以诗文相托付的信任,又有对二人的殷殷期望。乔亿卒后30年,朱彬犹念念不忘当年重托,亲撰墓表,表彰其嘉言懿行,足见乔亿其人对朱彬影响之深远。
二、朱赛
朱赛,字祈年,号佛景,又号南楼、诸生,居东乡界淘沟,足迹不轻涉城市,闭门课子,以吟咏自适,与苗庄、胡豳、刘玉堂、郭楷等为诗友,著有《屠苏集》《青苔居士集》《蘖树山庄集》《佛影集》《南楼杂咏》《黯然集》等。朱彬在《白田风雅》中将其与乔亿共列第11卷,收其诗17首。《游道堂诗话》评曰:“南楼先生为副使公嘉会之裔,与吾族通谱最久。少时于途次见之。时吾邑称诗者乔剑溪先生外惟先生可肩随。乔孤介,少与先生由由与偕。邑后辈多宗仰之。身后其家秘其稿不以示人,仅从友人斋中所传暨其次孙所记忆钞录者以见一班,后得其全稿,所录无一存者,则散佚者甚多也。”[2]359道光五年(1825年)朱彬为朱赛遗集作序,将其与乔亿并称。而朱赛对朱彬亦颇赏识,对其期许有加,朱彬回忆道:“彬幼年侍先祖,遨游市中,途遇先生,见先祖,正立拱手。先祖命揖,先生执余手曰:‘闻汝颇有志乎古,暇时盖过我。’余逡巡不敢对。”[1]614朱彬祖父泽代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67年),是年朱彬14岁,盖朱赛与朱彬交接当在1767年之前。朱赛与朱彬分属界淘朱氏与朱翁朱氏两支后裔,两家虽非同族,但自明代开始即交往密切,情谊甚笃。明朱嘉会与朱应登同举进士,遂联谱牒,至清初朱赛祖父与朱彬曾祖“以诗投契,情好尤笃,以故两家子弟欢若一族”[1]614。而朱彬后来虽未能以诗名世,但却成为扬州学派经学名家,也算不辜负朱赛对他的一番厚望。
三、贾田祖
贾田祖(1714―1777年),字礼耕,号稻孙,清高邮人,乾隆时廪生,好学,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尝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烂然,著作凡三千余篇,清雄博奥,见者惊为奇才。贾田祖
性耿直,与同邑李惇、王念孙及从弟成祖友,皆善饮,酒酣,辄钩析经疑,间以歌诗,往牒旧闻,泛演旁出,雅噱风生,《清史稿》有传,著有《春秋左氏通解》、《稻孙诗集》4卷、《容瓠轩诗钞》4卷、《礼耕存稿》1卷等。《赠吏部尚书郁甫朱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载朱彬“年十八,补诸生,与高邮贾稻孙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容甫先生中诸先生为友,皆闳洽才而钩贯经史”[3]581–583。蓝瑶《朱彬交游考述》一文对李惇、汪中与朱彬之交往情况有所述及,唯独不及贾田祖。二人定交之年朱彬18岁,该年当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贾田祖长朱彬39岁,是年已经57岁,两人算得上忘年交。汪喜孙撰《容甫先生年谱》中引朱彬语有言及贾田祖者:“贾君以诗名,世人谓容甫之学出于贾稻孙,误也。”[4]可见朱彬比较认可贾田祖的诗歌成就。但贾田祖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即去世,两人相交不过7年,故所存来往资料无多。贾田祖长于《春秋》学,朱彬则于礼学用力较深,其《礼记训纂》及《经传考证》等书亦未见有引贾田祖论说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贾田祖作为扬州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在诸同好中年辈又最长,无疑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及号召力,联系上文朱彬放弃作诗而专力于经学亦在此年,则贾田祖由文学而朴学的学术经历对朱彬无形中的感召作用是无疑的。
四、范鏊
范鏊(1743―1802年),字叔度,号摄生,顺天府大兴人,原籍江苏上元,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湖广司员外郎、陕西司郎中、陕西道监察御史、浙江司郎中、鸿胪寺少卿、通政使司副使、光禄寺少卿监卢沟桥赈务,曾四充会试同考官,典湖北、四川等省乡试。朱彬与范鏊定交当在嘉庆三年(1798年),《墓志铭》载朱彬:“简淡寡交游,尝居京师,足不履贵人门,惟与王观察石臞、邵学士二云、范光禄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义相爱重。”[5]710对王念孙、邵晋涵二人,蓝瑶《朱彬交游考述》已有述及,独于范鏊语焉不详,或因资料不足所致。范鏊于 4年之后的嘉庆七年(1802年)去世,则两人交往时间较贾田祖更短。另据《墓志铭》交代,朱彬长女适大兴廪贡生江西候补府经历范承英,而朱珪所撰范鏊墓志铭载,鏊二子一名准,一名润,字号则未详⑦。承英是否为范鏊子嗣尚不可考,但至少应是范氏族人,宝应朱氏与大兴范氏缔结姻亲之好,则朱、范二人并非泛泛之交。
五、叶世倬
叶世倬(1752―1823年),字子云,号健庵,江苏上元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四十八年(1783年)充《四库全书》馆誊录,五十年(1785年),议叙知县,分发四川,后历任嘉兴乍浦同知、湖北德安府同知、陕西西安府同知、兴安府知府、福建延建邵道、台湾道、江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身后入陕西名宦祠、乡贤祠,著有《健庵日记》《四录汇抄》《退思堂诗文集》等,主修《续兴安府志》8卷。宝应朱氏与上元叶氏乃世交,朱彬之父宗贽与叶世倬之父均官即相友善,均官曾任宝应主簿,并延请宗贽教其二子(即世经、世倬兄弟)。朱彬在《叶健庵六十寿序》中称“余之友未有先于健庵者,年十三四时健庵师事先君子……”[1]623可见二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左右即已结交,后来两家又结为儿女亲家,世倬长女嫁朱彬次子士达,婚姻洽比,情好日笃,两家关系更进一步。朱彬晚年深情回忆二人于嘉庆三年(1798年)的交往情形:“戊午,余赴礼部试,君亦守选北上,驱车并行,至京同寓樱桃斜街。寒夜拥炉,论今道古,漏下三鼓始就寝。平生朋友之乐,无逾斯时者。”[1]623今《游道堂集》卷2尚留存有朱彬致叶世倬书信1通,约略可见二人论学情形。在信中朱彬敞开心胸,纵论古今,臧否人物,抨击陆、王,推崇朱子,甚至对于友人李惇排斥理学的偏颇之举亦直言不讳予以指正,颇能反映朱彬本人的学术宗尚。正是因为将叶世倬视为知己,故而才会无话不谈,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各家各派的真实看法。此外朱彬还为世倬诗集作序,称其诗“深造自得,出入于乐天、子瞻、务观诸家”[1]615。朱彬本来戒诗不做已数十年,及至世倬以诗嘱其点定,“予性到,间一属和,忘其前戒”[1]615,盖因性情投合、不由自主,二人相交之融洽无间可见一斑。至世经、世倬兄弟相继辞世,朱彬又为二人分别撰写碑铭,述其实绩、表其德行。在朱彬所交往的友人当中,其论交之久、往来之频繁、情谊之深笃者无过于叶世倬。
六、吴瑭
吴瑭(1758―1836年),字配珩,号鞠通,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吴瑭年19其父即久病不愈而逝,其遂有志于医学,但家贫,乃弃举子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赴京师,时四库馆开,佣书以自给,得以博览医学名著,自此医道精进。乾隆五十八年(1793)京师瘟疫流行,经误治而死者,不可胜数,瑭以温病法救治,存活者甚众,名声大噪,自此步入医林,长期在京行医。吴瑭对温病研究深刻,创温病三焦辨证理论体系,被后世誉为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著有《温病条辨》6卷首1卷、《医医病书》、《吴鞠通医案》4卷。嘉庆十六年(1811年)朱彬在京师与吴瑭定交,得观其《温病条辨》,大为赞赏,欣然为之作序,称其“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6]1除此之外,朱彬还对全书一一批阅点评,据笔者统计,其评语至少有179条之多,皆简明扼要之语,少者一二字,多者亦不过数十字。朱彬对吴瑭此书颇为推崇,比如卷一中评《辛凉平剂银翘散方》云“妙甚”,评该方之“方论”云“要著”“精能之至”“著眼。止此二语,沾丐后学无穷矣”[6]16–18等,亦可见出朱彬虽不以医学名世,然对医道颇有研究,医学修为亦非同小可。否则以其朴学家的身份,必定不会妄施丹黄,轻易为《温病条辨》作批点。朱彬82岁而卒,在扬州学派诸学人中算得上高寿,应与其本人通医道不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朱、吴二氏的友谊延及后辈,朱彬长子朱士彦与吴瑭亦为知交,士彦曾撰《吴鞠通传》,载吴氏《医医病书》一书,称其“居心仁厚,笃于故旧,与人能尽言,处事悉当……岂独精于医哉?”[7]
七、陆继辂
陆继辂(1772―1834年),字祁孙,别号小元池居士、修平居士,江苏阳湖人。继辂幼孤,生母林严督之,非其人,禁勿与游,甫成童,出应试,得识丁履恒,归告母,母察其贤,始令与结,其后益交庄曾诒、张琦、恽敬、洪饴孙辈,学日进。其乃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选合肥训导,以修《安徽省志》叙劳,迁贵溪令,三年引疾归。继辂仪干秀削,声清如唳鹤,不以尘务经心,惟肆力于诗,其诗清温多风,如其人也。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继辂著有《崇百药斋文集》20卷、《续集》4卷、《三集》12卷、《合肥学舍札记》12卷、传奇《洞庭缘》、《秣陵秋》(与庄逵吉合撰)等。《清史稿》卷486、《(光绪)阳湖武进县志》卷26均有传。朱彬《游道堂集》卷2有《与陆祁孙书》1通,在信中朱彬为陆继辂畅论为文之道,品评各家得失,颇为宏通。信中交代,朱彬13岁时读方苞古文,推崇备至,认为其为北宋诸家之后第一,后来经表兄刘台拱推荐读归有光《震川文集》,又得清初作家宋荦所选《国朝三家文钞》读之,按图索骥,又遍读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魏禧《魏叔子文集》、汪琬《钝翁类稿》三家原著。朱彬认为,“叔子廉悍非常,而少儒者雍容气象;朝宗倜傥,而文气未能调适;钝翁近之矣,而缓弱抑又甚焉”[1]610,皆不甚洽于心。朱彬自言及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赴泰州应试,与汪中定交,其古文得到汪中赞许,治古文自此始。此后朱彬广泛涉猎南宋以后之文,认为“皆懦钝不中法”,40岁之后读姚鼐、刘大櫆之文,以为皆不如归有光及方苞,而在归、方两家之中,认为“震川文似平衍,而宽博有余之气胜;方望溪峭蒨近介甫,而纡余委备实逊震川”[1]610,以为归有光更胜一筹。朱彬对汪中的文章评价很高,谓其“风发泉涌,雄厉凄清。碑铭颇效柳子厚,琅琅可诵,其序事之文亦甚谨严。自孟坚而下逮六朝人,撷其菁英,入其奥窔”[1]610,但对汪中“诋宋人为不足学”及方苞“谓东汉以后之文为衰,必胎息《左》、《史》,具体韩、欧,始可为古文”[1]610的看法却绝不苟同,主张对历代散文博观约取、兼收并蓄,摒弃门户之见。至道光六年(1826年)左右朱彬通过陆继辂友人薛画水得观陆氏所编《七家文钞》⑧,得知陆氏亦治古文,于是读其文集,认为其“与姚、刘诸君子相类似”,将其与姚鼐、刘大櫆等桐城派名家相提并论,并对其寄予厚望,“由是而之焉,归、方不足多也”[1]610,认为其继续努力当可追攀归有光、方苞两家。此外朱彬还对治经学者疏于研习古文的现象颇有微词,信中称“斯道之难成,久矣!刘古塘云:‘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不可以为班、马。’此言至妄,而实有至理。某求友于天下,方今稽经诹古以及六书九数之学,上掩古人者多矣,而成学治古文者实鲜。岂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抑刘君之言信而有征也。”[1]610他感叹朴学家在稽经诹古、钻研六书九数方面固然有超越前人之处,但“成学治古文者实鲜”,继而发出“岂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抑刘君之言信而有征也”的疑问,既一针见血地指出朴学家学术成就的局限与不足,又以身作则,终身研治古文并倡导朴学家重视古文以繁荣创作。无怪乎汪中亦称赞其在古文上的实绩:“治经者固多,文章则无作者,故君于文用力尤深。”[8]后来曾国荃为朱彬《游道堂集》作序,肯定朱彬“工于文”,符合实际,确非谀辞。在信末朱彬还说“某衰老无似,唯好古文之心孜孜弗怠”[1]610,并向继辂索求其《崇百药斋文集》及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可见其研习古文之热情自少至老,始终不减。
注释:
① 详见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② 朱庆裴编纂《朱彬先生年谱》,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③ 详见笔者拙文《〈宝应朱氏世代事略〉〈朱彬先生年谱〉指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66―70页。
④ 详见蓝瑶《朱彬交游考述》(《文教资料》2007年3月号上旬刊)第73―75页。
⑤ 详见蓝瑶《朱彬〈礼记训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07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论文)第6―10页。
⑥ 分别为《跋逍遥馆漫钞》《兰言集序》《宗老南楼先生诗序》《叶子云诗序》,见《游道堂集》卷二。
⑦ 详见朱珪《知足斋文集》卷五《光禄寺卿范君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76册)第710页。
⑧ 七家分别为刘大櫆、张惠言、恽敬、方苞、姚鼐、朱仕伦、彭绩。
[1] 朱彬.游道堂集[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朱彬.白田风雅[G]//扬州文库:第82册.扬州:广陵书社,2015.
[3] 朱为弼.蕉声馆文集[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汪中.新编汪中集[M].田汉云,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5:13.
[5] 朱珪.知足斋文集[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 吴瑭.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7] 李刘坤.吴鞠通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35.
[8]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