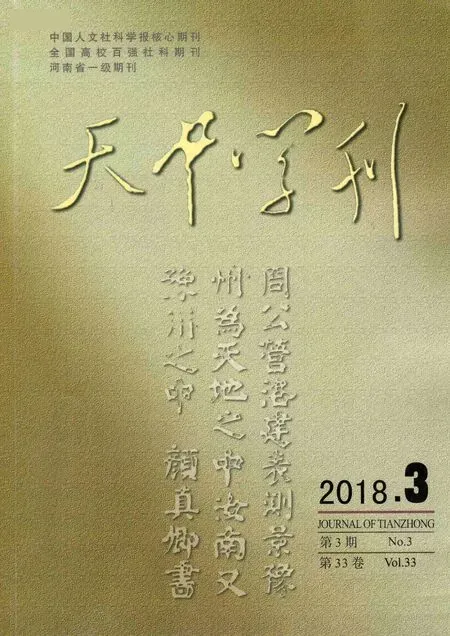宋代节令诗中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化意蕴
2018-01-27李懿
李 懿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中国的传统岁时节令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两宋时期[1]。女性是节令活动中一抹亮丽独特的风景线,“一年之中可谓月月有节,节节关涉妇女”[2]254,因此女性也渐渐成为古代文人关注的对象。自秦汉以来,节令诗里常常活跃着女性美丽欢快的身影。汉代杜笃《京师上巳篇》云:“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3]西晋潘尼《三日洛水作》:“廊庙多豪俊,都邑有艳姿。”[4]唐人郭郧《寒食寄李补阙》:“兰陵士女满晴川,郊外纷纷拜古埏。”①刘言史《七夕歌》:“人间不见因谁知,万家闺艳求此时。碧空露重彩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李山甫《寒食二首》其二:“风烟放荡花披猖,秋千女儿飞短墙。”但整体而言,古代诗歌专门以女性特别是节令女性为描摹对象的篇幅并不多。日本神户大学笕久美子《以“女性学”观点试论李白杜甫寄内忆内诗》一文揭示了女性书写在传统文学中缺失的原因:“一是登上大雅之堂并被正统化的诗文常被作为‘诗言志’的蓝本。二是多数男性本身也极为缺乏将其价值观置于日常生活中的意识。”[5]255啜大鹏在《女性学》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里常见的女性形象分为“奢饰之女”“无权之女”“孝顺之女”“无才之女”“贞烈之女”“七出之女”“奴婢之女”“娼妓之女”[6],也并未见其对节令女性的重视。职是之故,本文以文本细读为主,意在考察宋代节令诗中女性形象的多元塑造,立足于审美嬗变的角度再现多姿多彩的女性节令活动场景,勾勒其超脱于日常的心灵观感与生命情境,进而从文学、女性学、社会学等层面阐明节令女性书写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
宋代诗人主要选择春秋二季节庆中的女性为书写对象,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从单一渐趋立体化、多样化,并且描摹女性形貌愈加精致,这和节令体系在宋代的成熟以及女性节令生活的日益丰富关系密切。上元观灯、寒食清明拜扫郊游、上巳临水、七夕乞巧、秋社归宁、中秋赏月等诸多节俗都和女性密不可分,这些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醉翁谈录》《武林旧事》等民俗笔记的记载即可窥见端倪。
宋前诗人关注的多是城市女性,而宋代节令诗里的女性大致包括村妇、大众化的城市女子、妓女、舞女4类。首先,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是其专门关注的一类。张商英《平阳道中过上元》云:“元夕吾何处,吾行次晋郊。乐棚垂苇席,灯柱缚松梢。俚妇朱双脸,村夫赤两骹。春田夸积雪,酒胆醉仍杪。”②上元日诗人随行郊外,看到村中搭建起乐棚、灯柱,便随手记之,“朱双脸”是对两颊通红的村妇进行的细致写照。张侃《村外寒食》叙述了清明节农村女性划船外出、兴尽晚归之事:“八字桥边春水平,三家村里亦清明。女郎鼓棹归来晚,却被风光赚一生。”有时村妇会趁节庆进城玩乐,《新编醉翁谈录》即云:“自元丰初,每开一池日,许士庶蒱博其中,自后游人益盛。旧俗相传,里谚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盖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7]由于农村和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对待某些节俗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如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云:“朱门巧夕沸欢声,田舍黄昏静掩扃。男解牵牛女能织,不须徼福渡河星。”乞巧是城市女性喜好的七夕节俗,她们期望通过乞巧祭拜让自己的女功更出色,然而“田舍黄昏静掩扃”一句却表明长于织作的农村女性对乞巧等祝拜活动并不热衷。
相对于村妇,城市女性的节令生活要有趣得多。宋诗中的城市女子大都乘车出游且以美丽而欢乐的形象出现。如梅尧臣《又和》云:“康庄咫尺有千山,欲问紫姑应已还。人似常娥来陌上,灯如明月在云间。车头小女双垂髻,帘里新妆一破颜。却下玉梯鸡已唱,谩言齐客解偷关。”诗歌传神点绘出“垂双髻”“着新妆”如嫦娥般美丽的女子观赏繁华灯会的景象。张耒《上元都下二首》点画出京城奢靡浮华、女子盛妆乘车夜游的情景:“淡薄晴云放月华,晚妆新晕脸边霞。管弦楼上争沽酒,巧笑车头旋买花。”也有诗人戏作女子元宵不出门的情形。如王安石《上元夜戏作》:“马头乘兴尚谁先,曲巷横街一一穿。尽道满城无国艳,不知朱户锁婵娟。”古代女子无事不出闺门,这首诗以调侃的口吻,假说城中无绝色美女是由于女子不出游所致。
妓女是宋代社会一个独特的群体,很多妓女才华横溢,和士大夫、文士、商贾都有往来酬答。宁宗一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 · 序》中说:“她们(指娼妓——笔者注)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世界文艺史上,这倒也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异贡献。”[8]李春棠将妓女概括为官妓、声妓、艺妓、商妓4个类型,并列举出《东京梦华录》所记东京城内的8处商妓中心[9]。伊永文通过进一步考证指出:“宋市妓其伎艺精绝,承前启后,其服务对象亦从达官贵人趋向市民大众。”[10]181由于妓女行业的兴盛,宋代各类节令休闲赏玩活动都不乏妓女的身影。唐都长安丹凤街平康坊为妓女聚居之地,故后世多用平康坊或平康里代称妓女居处,如王禹偁《锡宴清明日》云:“宴罢回来日欲斜,平康坊里那人家。几多红袖迎门笑,争乞钗头利市花。”写诗人清明节宴罢归来见到“红袖”之一颦一笑,并描绘了她们争乞利市之物的举止。晏殊《上元》描写元宵节官妓精彩绝伦的绳技表演:“金翠光中宝焰繁,山楼高下鼓声喧。两军伎女轻如鹘,百尺竿头电线翻。”绳技在宋时又称“踏索”或“跳索”,妓女们身轻如鹘,在百尺高的竿头灵巧地翻跟头,给节令增添了不少愉悦的气氛。这些多才多艺的妓女不仅通过公开的艺术表演愉悦大众,诗人的节令宴会或出游更少不了她们的陪衬。韩琦《清明会压山寺》云:“妓歌沈席摧莺舌,花影摇樽衒粉颜。”描述艳丽的妓女当筵佐酒唱歌,歌声纯美直摧莺舌。孔平仲《上元作》曰:“侍觞行食皆官妓,目眙不言语或偷。短长赤白皆莫校,但取一笑余何求。譬如饮酒且为乐,不问甘苦醉即休。”“目眙不言语或偷”细描官妓神貌语态,“短长赤白皆莫校”等句将观妓与饮酒相比,更带着“打油”谐趣的风格。许棐《元夕后湖上作》曰:“自从楼阁罢烧灯,未有今朝一日晴。暖拆葑边冰翼破,寒留山顶雪痕轻。娇骢已印寻芳迹,小妓新翻鬻唱声。每个旗亭商一醉,也应排日到清明。”描绘元夕开筵聚会妓女陪酒助兴的场景。携妓游玩也是宋代诗人的风尚,苏轼《和苏州太守王规父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时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二首》其一曰:“但逐东山携妓女,那知后阁走穷宾。”有时,妓女们会脚穿轻便的鞋子外出游览,吹笙歌唱,享受节庆之乐,王禹偁《寒食》云:“妓女穿轻屐,笙歌泛小舠。”强至《依韵奉和经略司徒侍中清明兴庆池上之作》曰:“烟际飞禽屏上见,水边游妓鉴中行。”虞俦《和王诚之元夕即席之作》:“满城游妓归时节,犹认云间紫玉箫。”
除妓女外,宋诗中亦不乏对舞女的工笔描绘。姜夔《灯词》其一:“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其二:“灯已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此二诗写成群穿着画金刺绣服饰的舞女在元宵月下婆娑起舞,直至深夜才恋恋而归。《武林旧事》载曰:“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11]51舞女形象的出现显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体现了女性在节令里的重要参与性。
宋人笔下的女性棱角分明,极具动态的美感。诗人还善于捕捉女子最动人的形貌特征展开叙述,如张咏《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飖尽似乘烟霞。”写女子之美艳如花,前句写人,后句写花,并以“三三两两”状女子玩赏人数之多,在花光流转、人花交映的氛围中女子之艳丽自然凸显。因而费著《岁华纪丽谱》曰:“公铁心石肠,乃赋此丽词哉!后以为故事。”[12]又王安礼《和踏青》:“侠卿酝藉歌飞雪,游女娉婷脸夺花。”范成大《寒食郊行书事二首》其一:“媪引浓妆女,儿扶烂醉翁。”二诗分别使用“脸夺花”“浓妆女”两个修饰语来描摹游女,使节令郊外游玩中盛装美艳的女子形象豁然挺立。唐诗则没有如此精细的描绘,唐代同类型诗歌常常以“佳人”“士女”“女郎”“闺女”“女儿”等笼统称谓一笔带过。宋人敏锐的视角甚至触及女子的年龄、发型等细节。郭祥正《清明望藏云山怀旧游》云:“红粉佳人十七八,踏青唱歌云鬓颓。”诗中“十七八”“云鬓颓”细描佳人芳龄和踏青歌唱发髻倾颓之貌。又陈与义《清明二绝》其一:“街头女儿双髻鸦,随蜂趁蝶学妖邪。东风也作清明节,开遍来禽一树花。”写寒食街头小女欲作妖邪态,细致地抓住了女子“双髻鸦”这一个性化的发型特征。和宋前相比,宋代节令诗中的女性形象描写整体上更加多元化。
二
宋代节令诗对女性浓墨重彩的刻画打开了认识女性的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诗人从“诗可以观”的角度阐明了众多女性多姿多彩的节令生活状态,同时从“诗可以兴”的角度揭示女性在节庆时的心灵观感以及男性作家的创作心态。梅尧臣《余之亲家有女子能点酥为诗并花果麟凤等物,一皆妙绝。其家持以为岁日辛盘之助。余丧偶,儿女服未除,不作岁,因转赠通判,通判有诗见答,故走笔酬之》云:“翦竹缠金大于掌,红缕龟纹挑作网。琼酥点出探春诗,玉刻小书题在牓。名花杂果能眩真,祥兽珍禽得非广。磊落男儿不足为,女工余思聊可赏。”旧俗农历正月初一用葱韭等五种味道辛辣的菜蔬置盘中供食,以取迎新之意,诗中女子能点抹凝酥为诗句和花果麟凤之状以助辛盘,“琼酥点出探春诗……”是对女子精湛点酥技巧的描摹和称道,结尾说精妙的女工虽可过目,却不是磊落男子的作为,反映了诗人对男女节俗分工不同的明确态度。又如春光明媚的花朝、寒食与清明时节,年轻的女子络绎不绝游春郊外,苏颂《寒食后一日作和林秀才》即云“都人士女趁时节,郡圃山樊乐樽俎”。方回《二月十五晚吴江二亲携酒》云:“喜晴郊外多游女,归暮溪边尽醉人。”端午节年幼的女孩子忙碌着系臂五色缯、百索、双条达,头上争戴缯彩制成的小符儿以逞新巧,如白玉蟾《夏五即事》其一云“藕丝冰水敌时暑,臂彩钗符付女孩”。七夕更是典型的“女儿节”,“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10]781。刘宰《七夕》:“天孙今夕渡银潢,女伴纷纷乞巧忙。乞得巧多成底事,祇堪装点嫁衣裳。”洪咨夔《七夕》:“有齐季女起拜月,绿发一缕蒙金针。眼明志针如志鹄,针发相投如破镞。”女子们焚香乞拜,望月穿针,乐此不疲,即使是很小的女孩子也积极参与其中。宋人的视野还延及一些新颖少见的妇女节俗或禁忌,这种细微的体察拓展了节令女性描写的广度。邓深《观游女次韵》曰:“丽人春游相百十,此风长沙云旧习。绮罗映肌白玉鲜,珠翠压鬓乌云湿。借地持杯递呼唤,笑指花枝时小立。晚风忽遣柳棉飞,竹径梅亭巧穿入。恼乱游人归不去,使我樽中无以给。谁念朝来丘陇间,纸钱吹落无人拾。”小序云:“长沙风俗,每岁二月妇女纷然出城扫墓,谓之上山,率以日午而返。因游帅漕花圃,歌饮尽欢,穷日而后散。时与张庆夫坐观于竹径,张赋诗,乃次韵书所见。”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宋人扫墓一般在寒食、清明,偶有元日或上巳上坟,韩琦《元日祀坟》、杨万里《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可证。长沙女子的扫墓活动又名“上山”,但时间在二月,不同于宋人扫墓的常规时间,并且女子以游乐为主。诗歌开篇“丽人春游相百十”即点明此乃女子游春活动,“绮罗映肌白玉鲜,珠翠压鬓乌云湿”勾画女子美丽的容颜发饰等。全诗展现了长沙地区独有的以游玩为主的女性扫墓民俗。李觏《正月二十日俗号天穿日,以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感而为诗》云:“娲皇没后几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天穿节的诞生和人类始祖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有关,由于文献资料有限,后世对天穿节知之甚少。此诗概述了宋代民间女子的天穿节活动,使读者对不常见的女子用煎饼置屋上以补天的习俗有所获悉。范成大《祭灶词》则描写了女性在节令中的禁忌,诗云:“男儿献酌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祭祀灶神有冬季、夏季之分,宋代祀灶多在腊月二十四日。民间认为灶神是天帝派驻人间的仙官,会定期上天向天帝汇报所驻之家的德行与过失,天帝据以对德行兼备者赐以福财,反之则施加减少寿命等惩罚。《东京梦华录》云:“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10]943宋前文献尚未有“女不祭灶”的记载,虽然此诗并没有详言女子不能祭祀的原因,但“女儿避”却显示出宋代祭灶女子需回避的现象。
其次,诗人们逼真再现了节令时女性穷欢极乐甚至癫狂的形象,尤其展现了都市文化背景下城市女性对外界的向往,表现了她们市民化的世俗情感与欲望诉求。如姜夔《观灯口号》其四描写她们“闹元宵”,常常直至天明:“花帽笼头几岁儿,女儿学着内人衣。灯前月下无归路,不到天明亦不归。”陈世崇《元夕八首》其二云:“苍头喝道烛光微,梅压乌云柳压眉。打块成团娇又颤,闹蛾簇簇翠冠儿。”描写了一群欢快的女子打块成团、欢愉无比的情态。何梦桂《灯夕乐舞》:“玉梅雪柳千家闹,火树银花十里开。”《武林旧事》“元夕”条曰:“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11]55–56宋诗对“拾遗簪”的风俗亦有描写。梅尧臣《和宋中道元夕二首》其二曰:“车马不闲通曙色,康庄时见拾珠钿。”方孝能《福唐元夕三首》其三:“少年心绪如飞絮,争逐遗香拾坠钿。”周紫芝《寒食杂兴》其二:“九陌过香軿,都人拾遗珥。”朱淑真《元夜三首》其一:“争豪竞侈连仙馆,坠翠遗珠满帝城。”诸诗中“珠钿”“坠钿”“遗珥”“坠翠遗珠”等女子遗落的满城珠翠,显示出女子兴尽乃归的欢腾雀跃之态。都人尽拾钗钿,心如飞絮的少年循着遗香竞相寻找遗落的珠钗。遗簪能唤起拾者对于佳人无尽的想象,这是一种委婉而含蓄的精神邂逅。又如梅尧臣《和宋中道元夕二首》其一云:“结山当衢面九门,华灯满国月半昏。春泥踏尽游人繁,鸣跸下天歌吹喧。深坊静曲走车辕,争前斗盛亡卑尊。靓妆丽服何柔温,交观互视各吐吞。磨肩一过难久存,眼尾获笑迷精魂。貂裘比比王侯孙,夜阑鞍马相驰奔。”诗人不避鄙俚,以“目光含情”“一过不遇”“笑眼魂迷”营造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氛围。方回《上元晚晴》曰:“冶妆饰粉黛,豪奏喧丝笙。愚玩夺稚魄,淫窥荡狂情。”“狂情”二字寓诸多含蓄意味于言外。
“帘窥”描写不仅表现了帘外人对帘内佳人的美好想象,还表现出女性对平淡生活的挑战和对帘外世界的向往。梅尧臣《和宋中道元夕十一韵》云:“……端门两廊多结彩,公卿士女争来奔。接板连帘坐珠翠,帘疎不隔夭妍存。”梅尧臣《和王景彝正月十四夜有感》:“隔帘艳色多相照,下马轻豪各竞新。”张耒《上元思京辇旧游三首》其二:“九门灯火夜交光,罗绮风来扑面香。信马恣穿深柳巷,随身偷看隔帘妆。”以上三诗皆以观灯为背景写美艳的帘内女子,从“帘疎不隔夭妍存”“隔帘艳色多相照”等描述可以推想,帘外人大都对帘内的佳人怀有新奇感,“随身偷看隔帘妆”更直言帘外男性对帘内女子的大胆窥视。甚至连方外之人都对“帘”内外的男女、灯景等世俗生活场面进行描绘,如释德洪《京师上元观驾二首》其一曰:“白面郎敲金镫过,红妆人揭绣帘看。”与张耒诗写帘外人的窥视不同,此诗抓住女性揭帘观看敲金镫的白面郎这一瞬间,将帘中女性观看游人的神情娓娓描绘。古代女子一般不轻易和外界接触,现实之“帘”具有一种间隔作用,将出游女性的车内和车外两种空间分开。诗中之意象“帘”极具审美功效,它将女性置于半幽闭空间中,是对女子生存状态的一种暗喻。诗人通过女子“揭帘”或“隔帘”观看外界,将帘内佳人与帘外喧闹活跃的世界组合成奇妙的人生图画,表现了她们对于外界空间的好奇和欲与其沟通的心理。
此外,宋诗还对“交甫解佩”式的男女情遇进行了书写,如苏辙《次韵王巩上元见寄三首》其一:“弃掷良宵君谓何,清天流月鉴初磨。莫辞病眼羞红烛,且试春衫剪薄罗。莲艳参差明绣户,舞腰轻瘦飐惊鼍。少年微服天街阔,何处相逢解佩珂。”杨亿《次韵和集贤李学士寒食即事之什》:“九逵初旭满辎軿,寒食东风二月天。陌上垫巾谁傲睨,江边解佩自婵娟。新妆几处登墙见,沉醉何人藉草眠。豪侠追欢殊未足,归蹄躞蹀夕阳前。”“交甫解佩”详载于旧题刘向《列仙传》卷上“江妃”条,指郑交甫汉江遇游女,游女赠之以佩而佩终不见的典故,一向用来形容遇仙事件,比喻缥缈神秘然终无结果的男女际遇。以上二诗用艺术虚构的手法,将现实男女出游相遇之事巧妙融入郑交甫遇神女的动人传说中,增添了诗歌的传奇色彩,使全诗意蕴更加悠远。
三
罗时进曾对女性投身节令的积极作用进行概述:“女性独特的情感色彩和对节物的欣赏方式能够表现出独特的风情,无疑,适时地释放这种女性美感潜能,有利于丰富社会的审美活动,形成男女双向互补的自然和谐的心理机制。”[2]258在现实中,宋代女性是受拘束的对象,然而节令使她们从封闭的“内闱”走向开放的“深闺之外”,来到街市、郊外、外家,甚至日常明令禁止的关扑赌博一类的活动,她们也获允旁观。对宋代女性来说,节令对她们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即其有机会从“非大故不得出”的夫家归宁,如胡瑗之曾孙胡涤即云:“(先祖)治家甚严,尤谨内外之分。儿妇虽父母在,非节朔不许归宁。”[13]
有关宋代女性的节庆生活情况,仅在少量史料笔记中有零星记录,而节令诗对女性民俗的描摹充分丰富了这方面的记载,承载着丰厚的文化意蕴。
从女性学的层面看,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能等同于男性。司马光《家范》卷八曰:“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14]在男性作家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宋以来的正统文学皆视女性书写为“俗流”而非“主流”范畴,故诗歌对女性的刻画自然较少。宋代节令诗却精致勾画出脱离于“载道”“抒怀”主旨的典型女性形象,再现了她们迥异于日常时间的生活原生态。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宋代城市的繁荣打破了市与坊的界限,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娱游等功能于一体。城市商业经济的急速提升带动了城市节俗活动的发展,城市节庆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区域,表征着“声色、娱乐和情爱的欲望……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诉求与话语方式”[15],生活其中的女子也相应地享有更为繁庶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节令诗所展示的女性形象游离于“女无外事”的模型之外,体现了城市变革背景下新兴市民阶层最普通最真切的情感欲望与精神诉求,形象地表现了以“主中馈惟酒食衣服是议”为主要活动的女子在“内闱”之外的另一面。
从文学的角度看,宋代商业经济的勃兴引起了市民审美观的嬗变。王水照指出,宋代士人的审美追求“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16],因此描写市民世俗情感与现实生活的文学观念日渐萌发。节令诗对女子欢乐至极的节庆生活的描述,不仅客观记录了当时世俗社会崇尚娱游的民俗图景,且清晰反映了宋人日常化、平民化的书写倾向,宏观地显示出由雅尚俗的文学发展趋势。
综上,宋代节令诗对女性的关注,富有丰富的文学意义和时代审美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① 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年版)。以下所引唐诗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② 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全7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以下所引宋诗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1]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7.
[2]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5.
[4]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4.
[5] 笕久美子.以“女性学”观点试论李白杜甫寄内忆内诗[G]//唐代文学研究: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6] 啜大鹏.女性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28–137.
[7] 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13.
[8]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
[9]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247、251.
[10]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 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费著.岁华纪丽谱[M]//杨慎.全蜀艺文志.北京:线装书局,2005:1710.
[13] 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49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0.
[14] 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6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08.
[15] 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91.
[16] 王水照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