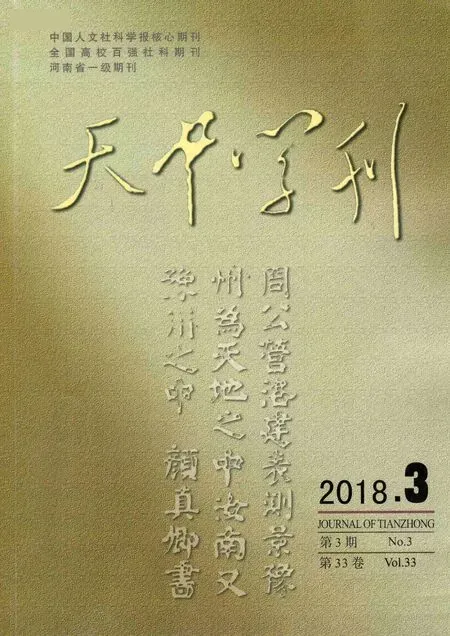先秦诸子视域下的周公形象
——论《墨子》对周公的评论
2018-01-27杨兆贵
杨兆贵
(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澳门 999078)
一、墨子、《墨子》、墨子后学简介
墨子(前480―前390年),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国人[1]100。有关他的生平,历史记载颇少,所以难于详考。有关他的姓名,学者或认为姓墨,名翟,但学界对此有争论[2]51–52。钱穆认为墨不是姓,而是古代刑名、役夫之称,翟为野人冠饰[3]49–51。根据《淮南子 · 大略》篇的说法,墨子曾学过儒家学说,后来对儒家的礼乐学说深感不满,遂背离儒学而另创新说新学——墨学。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曾被并称为“显学”。
墨子的生平、思想基本上记载在《墨子》一书里。墨子的思想主张,主要是提出了“十义”:天志、明鬼、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这些思想观念、言论记录在《墨子》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里。这几篇应是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做的[4]133–134。墨子的言行基本上记录在《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篇里。这几篇是墨子后学辑录的。
墨子提出的“十义”,有些是反对儒学的,如节葬、非乐等。学者因此认为墨子反对儒学,其实此说未必符合史实。众所周知,先秦诸子之间思想互相影响,吸收他家之长,修正、发展自己学说的现象比比皆是。墨子受孔子仁说的影响而提倡兼爱[5],孟子受墨子兼爱说影响而提出仁说;庄子反对仁义,荀子则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见,先秦诸子虽然有自己的立场,但不等于他们不接受其他学派、思想家的观念。陈启云指出: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道家、法家等门派的形成是诸子思想发展到末期的事,至于九流十家的名目更是由后来汉儒所制定。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应该注重的是各个思想家之间思想学说的先后转变及相互影响,从中勾划其发展的线索和关键。[6]16–17
这一说法对研究先秦思想史很重要。现代学者研究先秦思想史,依诸子的思想而把他们分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是受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班固《汉书 · 艺文志》的影响。司马谈在整理先秦思想时,依照诸子的思想内容、特点而把他们分为六家。班固进而把先秦思想分为九家十流,又提出诸子出自王官说。这一分法是汉代人的看法,未必完全合乎先秦的历史真相。这种分法,对研究各家各派的共同思想特点大有益处,但如果忽略诸子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和他们之间相互的问难、影响,单纯地把他们划入某家某派,则未必能说明诸子思想的原貌[3]34–38。
同理,墨子被划入墨家学派,不等于说他没有受到孔子的影响。吕思勉说:“墨子之非儒,仅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他指出孔、墨有不少看法是相同的,如《修身》《亲士》《所染》三篇与《大戴礼记 · 曾子立事》相表里[7]120。顾立雅也指出,墨子激烈批评儒家,是为了强调他离开儒家而自创门派,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他的学说的广阔基础的大部分事实上是他那个时代的儒学”[8]261。所以,墨子受到孔学的影响并加以吸收、发展,应是事实。
墨子将孔学进一步发挥且加以理论化。陈启云指出:“孔子在‘不知、不可知’的‘认识论’怀疑气氛中,提出了人本主义的‘认识论’基点,再由墨子从这个基点上建造出一新的宇宙观、人生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思想系统。”[6]17–22易言之,只有孔子重建认识论的基础,墨子才能开创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思想观念发展而言,墨子将孔子“仁”中的“爱人”观念发展成兼爱思想;把孔子“下学上达”理论发展成法天的一套完整理论,进而认为天有其规范人间的客观规则——义;把孔子重视贤能的观念发展成尚贤的理论[9]。可以说墨子发展了孔学,自创墨学,旨在批评当时贵族种种侈靡生活,指陈当时各国统治的弊病,提倡非礼、非乐、非攻、薄葬[1]88。由于儒家对传统礼乐文化采取温和的保守态度,于是就成为他所批评的对象[10]33。一般学者认为墨学具有功利性,其实墨子重视客观知识,注重逻辑[11]185–193。
墨子死后,墨学分为三派,《韩非子 · 显学》篇:“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12]有关这三派的构成成分、主张,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蒙文通认为这三个学派与地域有密切的关系:东方墨者相里氏重说书权说,南方墨者邓陵氏重辩说,秦墨相夫氏重实事而轻理论[13]。李生龙的看法与此基本相同[14]。
《墨子》一书应是记载墨子及其后学的汇编。《汉志》著录为71篇,今仅存53篇。这53篇,大体可分为三类,一属名辩类,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这6篇,“经”应该产生较早,“说”产生较晚。一属军事类,即《备城门》以下至《杂守》11篇。一属思想类,即除以上两类外的其他36篇。
《墨子》书中论及周公的有《所染》《非儒》《耕柱》《贵义》《公孟》。胡适认为《耕柱》《贵义》是墨子后学辑录墨子一生言行的篇章,其他自《亲士》至《辞过》或与墨家无关,或是根据墨家余论所作[4]133–134。他这一看法没有提出论据。毕沅、孙星衍认为从《亲士》到《辞过》的7篇是墨子自著,宋人潜溪甚至认为这7篇是墨家中的经[15],陈柱、栾调甫、罗根泽等认为这 7篇是“墨学概要”[16]40。可见,学者多认为这 7篇不仅与墨家有关,甚至认为其在《墨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这几篇记为“子墨子”,所以应是墨子后学辑录的。
二、《墨子》篇章对周公的评论
在论述《墨子》对周公的评论前,先简介周公。周公,又称叔旦、周旦,中国古史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中国信史的第一位极重要人物[17]。周公曾辅助武王克殷。武王在克殷两年后逝世,由周公旦和召公奭、太公望辅佐周成王。周公曾摄政称王,出师东征平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将周势力扩展至东海[18]16–62。关于周公摄政的主要事迹,《尚书大传》有简要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主张,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为周王朝统治、中国文化发展奠下基础[19]240–267。现代学者称赞他是“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缔造者和总设计师,中国礼乐文明的创建者和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中国西周前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先师,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文化始祖和道德典范”[20]。此说实不为过。
下文把《墨子》中《所染》《非儒》《耕柱》《贵义》《公孟》篇对周公论述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墨子对周公的评论,一是他的门人弟子或后学的评论。
(一)墨子对周公的评论
1. 《所染》篇:周公是武王极重要的辅佐
《所染》篇以染丝为喻,说明君主要正确选用亲信,士慎择朋友。该篇所反映的思想与墨子相同。因此,本篇可视为对墨子思想的记载。本篇说: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21]12。
这段文字引墨子的话,说明环境对人性、身边人物产生的重要影响。作者称赞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4位王者,说他们分别受到许由、伯阳、皋陶、伯益、伊尹、仲虺、姜太公、周公的“熏染”,最后才能够统一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易言之,周公是上古史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是与许由、伯阳、皋陶、伯益、伊尹、虺、姜太公等量齐观的人物,他对周武王建立功业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武王极重要的辅佐。可见,周公是三代中一位对王者起着重要正面作用的历史人物。
2. 《耕柱》篇:肯定周公驳斥管叔、东征灭奄符合道义
《耕柱》篇记墨子与时人、弟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墨子派他的弟子管黔敖到卫国称扬高石子,卫君就给高石子高官(卿)厚禄。高石子很尽责,“三朝必尽言”,然而卫君听了却不采纳实行,因此高石子就辞职到齐国,告诉墨子,说自己因己言不被卫君采纳而辞去高官厚禄,“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墨子回答他,提出“去之苟道,受狂何伤”“为义非避毁就誉”的看法[21]432,这是墨子对仕的看法,也是墨子为人处世的原则:他认为做正确或正义的事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最重要的是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正义的,就不要把毁誉放在心里,正道直行就好了。墨子主张士之仕当以义为根据,不当争待遇多寡[10]45。先秦儒、墨、道都有如此相同的看法,如孔子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子对仕的看法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藉孔子之言提出三种不同仕的类型,即“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钱穆及笔者对此有阐论[22][23]42–43。庄子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凡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人,都坚信自己的信念,而不被外在的物质、权位等因素所影响。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墨子作为巨子,有崇高的理想、人格,当然不容易被外在物质影响。所以,他称赞高石子的做法,并以周公旦为例:
古者周公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21]432–433。
关叔即管叔,商盖即商奄,乃鲁国之都曲阜。这段是说周公受到管叔等人的毁谤,带兵东征灭奄[21]433。当时人说周公发狂,但后世称誉他的德行,颂扬他的美名。
可见,墨子相当认可周公驳斥管叔、东征灭奄是符合道义之事,称赞周公为人特立独行,高瞻远瞩,不为俗世观念所囿限。墨子这样称颂周公,与《尚书 · 周书》八诰所记周公的事迹相同,而且墨子这样推崇周公,对荀子也产生了影响,荀子称赞周公是大儒(圣人)[24]3–13。
3. 《贵义》篇:周公勤于读书,礼贤下士
这篇文章应写成于战国中晚期,在该篇中墨子这样评周公: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21]445
“关”即“扃”,“漆”即“七”[21]445。墨子弟子弦唐子看到墨子车里装着很多书,但墨子曾教弟子公尚过少读书,说读书不过是用来衡量是非曲直罢了,因此弦唐子不明其故。墨子称赞周公一早就读很多书,用功学习,非常人所能及;一个晚上(当指一天)接见70位名士,为政勤劳,所以周公辅佐天子取得很大成效,他的美善也因此流传至今。可见,墨子认为周公读书与为政是因果关系:周公读书多,知道的事情、道理多,与他在政治上取得大成功有必然的关系。墨子以前之所以叫公尚过少读书,是因为公尚过对事理已能洞察。可见,墨子认为读书是有用的,读书在知古今、明事理。
墨子所说周公“夕见七十士”的形象,与荀子及其后学《尧问》篇、《史记 · 鲁周公世家》所记相同。荀子特别重贤,认为君主若不用贤,就会有亡国之虞。《尧问》记周公求贤若渴,他不是在十人和三十人之中挑选贤士,而是在百人和千人之中才挑选三位贤士,这是他每天接见很多贤士的原因。《史记 · 鲁世家》称赞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周公的这些举动不仅被后人广为称颂,而且为历代执政者树立了礼贤下士的楷模[24]10–12。可见,墨子对周公的好学、重贤的看法与儒家相同。
4. 《公孟》篇:周公是圣人,其地位比孔子高
《公孟》篇也是墨子后学辑录的。墨子推崇周公是圣人: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21]454
公孟子应是儒者,且是习于俗见的陋儒。他提出做仁者的前提是必须说古人的话,穿古代的服装。顾立雅根据《公孟》《耕柱》篇相关的记载,认为墨子时代的一些儒者只着意模仿某种古代风格,以至成为过去的奴性效仿者。他们对于真正的儒家原则不太了解或关心,却渴望政治事业有一个美好未来[8]261–262。墨子举史事为例反驳公孟子的看法,他说箕子、微子与费仲都是商纣时的人,说同时代同样的语言,但是前者为圣人,后者为暴人;周公与管叔是兄弟,穿同时代的服装,一为圣人,一为暴人,可见不能以语言及服装作为仁与不仁的标准。在这里,墨子明确指出周公与箕子、微子一样都是圣人。但在墨子生活的时代,儒家已经把孔子尊为圣人了,公孟子继承了儒家的圣人观,推崇孔子为圣人,甚至认为孔子可以当天子:“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21]454墨子推崇周公为圣人,也即反对孔子为圣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儒、墨两家不同的圣人观。儒家认为圣人是人伦的极致[23]74–75,墨子则认为圣人必须服从天意、顺应鬼神。具体来说,墨子认为圣人有三种:一为善于创作者,一为最聪明者,一为人格最高者。墨子在《节用中》中说古之圣人因时而制作剑、甲、车、船、宫室,因此墨子认为凡能制作发明器具者皆为圣人。墨子在《天志下》中说只有圣人深明天之志,知道“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21]210,并且能向世人宣明此道理,因此认为唯有法天、以天志为依据的人才能是圣人。可见,墨子虽然和《诗》《书》的看法一样,视最聪明的人为圣人,但是他强调的是圣人服从天志,以天为仪。墨子视人格最高者为圣人,是其圣人观中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其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墨子以天志、鬼神观念论此类圣人:首先,圣人要顺从鬼神,因为鬼神可以辅助天而管制天下,握有赏善惩恶之权,其明智尤远甚于圣人;其次,圣人要去“六辟”:“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从事于义,必为圣人。”[21]442–443墨子以为六欲有其流弊,故想透过修养净化六情之僻,具体方法是以外在标准“义”主导内在修养。墨子主张以客观理性克制主观情欲,希望透过外在的种种规范、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所以他不断鼓吹法仪、尚贤、尚同等,注重逻辑,重视客观知识。墨子重视天志、鬼神,而孔子没有顺天志依鬼神,所以孔子不是墨子的圣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偏重现实人生界,推远鬼神界。墨子批评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21]457,毋宁是说他认为孔子不合此条件,故不能当圣人。
总的来说,墨子推崇周公,称赞周公是圣人,而不认同孔子是圣人,这是由儒、墨的圣人观不同造成的。既然墨子推崇周公是圣人,那么在《所染》篇中说周公是三代中一位对王者起着重要正面作用的历史人物,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墨子又肯定周公驳斥管叔以及东征、灭奄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义”的,称赞周公为人特立独行,是后世做事不避誉毁的典范;赞赏周公勤于读书,礼贤下士,在政治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墨子后学《非儒下》篇对周公的评论
据学者考证,《非儒》不是墨子亲著,亦不是其后学记墨子之言而汇编的,而是墨子后学所作[16]41–42。该篇论及周公的文字如下: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就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21]440–441。
这篇文章对孔子的人格、行事进行诬蔑:(1)借晏子之言批评孔子没有仁义,不是贤人。(2) 孔子帮助田氏专政于齐国。(3) 孔子为鲁司寇时,私开城门让季氏逃亡。(4) 孔子亲口诬蔑舜与周公:舜为天子,而其父亲竟然为臣子,有悖常理,将危及天下;周公旦也非仁人,东征在外,“舍其家室而托寓”。(5) 孔子心术之坏所至,影响弟子,使他们也跟着为非作乱。之所以说这是墨子后学诬蔑,是因为《非儒》篇所提的这些事都不符合史事,其目的是希望收到批判孔子是“非贤人之行”“非义之类”之效,而置儒家于死地[25]55。这与墨子分别看待孔子之人与孔子之学的态度显然不同,不仅无助于宣播墨学,也不能一针见血地批评儒学。陈拱很中肯地分析说:“墨子所争的只是道理,不在人身攻击,其后学不免刻薄、诈伪,有失墨子的风度……这只是其后学中一些卑鄙而不够格者的人身攻击,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26]此言有理。
三、结语
周公是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对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制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孔子对周公特别尊崇,但没有说他是圣人。墨子是第一位推崇周公为圣人的思想家。墨子研读《诗》《书》,了解周公的为人、行事,对周公的历史贡献予以极高的评价。墨子对周公的看法,与孔子、孟子、荀子相同。孟子、荀子也推崇周公为圣人。可见,墨子的周公圣人观影响了孟子、荀子。
虽然墨子与儒家都推崇周公为圣人,但是墨家、儒家的圣人观不同,他们从自己学派学说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理想人物进行阐释、评论。不仅学派不同,圣人观不同,即使同一学派里的人对同一理想人物、观念也有殊异,如孟子与荀子的圣人观就有所殊异,墨子与其后学《非儒》作者对周公的评论也不尽相同。
先秦思想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彼此的负面影响。墨子学说受孔子影响,他推崇周公甚于孔子,尊崇周公为圣人。孟子则因墨子推崇孔子甚于周公,且反对孔子为圣人,而提出孔子是圣人,是圣之集大成者,比周公还伟大。
儒、墨思想互相影响,就从墨子对周公的评论已可见一斑。至于学派之间、诸子之间的学说、思想的互动、互相影响,也是研究先秦诸子所当梳理之事。
[1]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M].上海:上海书店,1992.
[2] 潘水根.墨子姓氏及其他:关于墨子研究的几点看法[J].学术界,1993(3):53–58.
[3] 钱穆.国学概论[M]//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1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2[M].台北:东大图书,1980:418.
[6] 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认识论基础[J].学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1996(4):113–142.
[7]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5
[8] 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M].高专诚,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9] 钱穆.庄老通辨[M].北京:三联书店,2002:56–64.
[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 AHERN D M.Is Motzu a Utilitarian?[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76(2).
[1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3:456–457.
[13] 蒙文通.古学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87:212.
[14] 李生龙.新译墨子读本[M].台北:三民书局,2010:1–2.
[15] 张心澄.伪书通考[M].台北:宏业书局,1970:752–753.
[16] 杨俊光.墨子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17]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1[M].台北:东大图书,1976:83–89.
[18] 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G]//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9] 杨兆贵.归属于周公的“德”说内涵新探[C]//首届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大学,2016.
[20] 游唤民,汪承兴,贾再友,等.元圣周公全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21]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2] 钱穆.孔子传[M].台北:东大图书,1991:67.
[23] 杨兆贵.《鹖冠子》新论[M].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2.
[24] 杨兆贵.论荀子及其后学对周公的论述[M]//冯天瑜.人文论丛:2016年第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25] 杨兆贵.先秦古籍关于孔子论、述的分析[D].新竹:清华大学,1999.
[26] 陈拱.儒墨评议[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