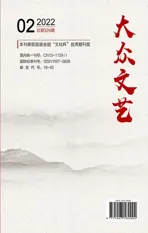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崇王”思想成为沈尹默书学理论核心的内外动因
2018-01-27贝思敏中国美术学院310002
贝思敏(中国美术学院 310002)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沈尹默作为建国后的书坛领袖,为中国传统书法事业做出不懈努力,并著书立说,以相对朴实的理论宣扬其理解下传统书法中技法、价值、审美取向和思想观念。在沈尹默书法生涯的晚期,经过六十余年的书法实践与对历代传统书法理论的研究,沈尹默从书法艺术的求索者,转变为书法知识的传播者。其大量理论开始发表于世,传播“二王”帖学,表达其“崇王”复古思想。
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值得我们探讨,伴随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退居台湾,于右任赴台,这使得原本于右任与沈尹默碑帖双峰对立的局面产生了根本性变化,草书标准化运动销声匿迹,自沈曾植以来的以北碑入行草的清代碑学开始停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传承了上千年的传统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书法作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核心与旧文化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是旧文化的的结晶所在,这一与时代的矛盾开始凸显。另外,毛笔开始逐渐退出生活、学习、办公领域,硬笔的大量普及使得书法渐渐与人民群众产生隔离。社会上开始不断出现“书法并不是艺术”、“书法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用处”、“书法不为人民群众热爱”等等论调。甚至在1949年7月中国文联成立时,没有成立书法家协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尊崇晋唐的沈尹默便挑起了重振中国书法的历史重任。建国后书法的普及和教育重任之所以落在沈尹默身上,一方面是沈尹默社会地位、书艺、威望为世人所敬重,另一方面其与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亦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后经过沈尹默的努力,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出任会长,经过半生的沉淀,由帖转碑复而出碑归帖的书学经历能够使其更全面的关照到帖学的深奥精妙之处,对于二王的崇拜与追求在其后的大量书论中开始正式表露出来。这一时期沈尹默本着实用论与技法论两个核心对“二王”系列问题展开多次研究,沈尹默的理论文献具有相当的普及性质,从初学、临摹与创作等实际问题切入,表述简明扼要,最切实用,这与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对象是有本质区别的,是使当时书法学者最受益的理论。沈尹默通过《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二王书法管窥》、《书法论》等文章介绍自己学习“二王”书法的经验,极力推崇“二王”帖学,从书法史的角度审视和探讨二王帖学的优秀传统,使得世人能够重新看待以“二王”为核心的书法史,对二王进行重新认识、定义和继承。在《谈谈魏晋以来主要的几位书家》中,沈尹默云:“羲献父子,师法钟繇,加以改革,而目一新。褚遂良承接二王之业,兼师史陵,参以己意,乃创立唐规模,传授到了颜真卿,更为书法史开辟了一条崭新大道。故叙述楷行以及草书的书家,必须首先着重二王及褚颜四家,才能使学者明了历代书法演进的轨辙。”1作为当时二王流派的集大成者,其书学理论看似平淡无奇,多与前人所述论调一致,但仔细研读便能发现信息量及其巨大,对于技法层面的表述沈尹默有着时人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广度,沈尹默在《书法论》中说到:“拨镫法是晚唐卢肇依托韩吏部所传授而秘守着,后来才传给林蕴的。它是推,拖,捻,拽四字诀,实是转指法。”2其主张:指是专管执笔的,它须是常静的,腕是专管运笔的,它须是常动的,必须指静而腕动的配合着,才好随时随处将笔锋运用到每一点一画中间去。对于历史上“二王”一脉传承性问题的表述有着极为深刻的穿透力,这是当时中国书坛其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沈尹默以其在文化界的德高望重和坚持不懈的书法创作,用通俗易懂的文章和谈话来阐述“二王”笔法,使得初学者更为明了地了解笔法的重要性,为传统帖学的复兴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建立后客观条件的改变,使得当时书家得见前人难觅的历代帖学法书,书家对帖学及碑学的问题开始重新思考。如沈曾植、高二适走章草书体,于右任晚年发展出融碑帖为一体的行草书风,而沈尹默则提倡晋唐风韵,强调笔法,在创作及理论上,全面回归继承二王书风。
“崇王”思想成为沈尹默书学理论核心代表的是“二王”帖学在近现代的复兴与发展,更代表的是沈尹默等传统文人阶层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觉地回归。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与代表中国传统书法“主脉”的“二王”帖学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造成的。
外部原因上,“二王”帖学的复兴与嬗变离不开近现代复杂、变化、宏观的史学历史文化背景。鸦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改变,对于闭关数百年的晚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漩涡,这对当时的统治阶层和文人阶层的心理震撼是极其巨大的,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中国传统文化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改革派与保守派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产生对立与矛盾。对待民族文化上,改革派敬慕于西方文化的优点,保守派执着于民族文化的继承。而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代表与根基,书法艺术也陷入这场漩涡之中。1926年梁启超作出了《书法指导》的演讲,明确表达了书法是美术的最高点这一观点,将书法艺术放在其它美术艺术之上,指出书法具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艺术家表达出的个性的美等等。此外邓以蛰、朱光潜、白宗华等人把书法美学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不再盲目西化,做到了对中西艺术的兼容并包、客观解读。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一味否定传统文化追求西方文化的趋势。不管当时社会思潮如何复杂多样,不管社会文化如何对立矛盾,文人阶层清晰地认识到民族文化传统是不可能消亡的。也正是在这样复杂艰难的背景下表现出向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势。因此,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书法艺术不仅站住了阵脚,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二王”帖学作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主脉”,不仅没有没落消亡被碑学书法取代,更通过沈尹默等帖学大家得到了复兴与嬗变。沈尹默书学理论的核心是“崇王”思想,这种思想便是以“二王”帖学的回归与发展为主体的,可以说这是晚清至民国期间书坛的一场变革。
内部原因上,晚清以来书家也开始产生对帖学没落原因的反思和对碑学书法的怀疑。清代馆阁体的程式化对传统帖学造成了帖学书法中原本带有的生动、鲜活、痛快等个性趣味被抹杀,帖学末流最后生命力的遗失殆尽使得强调个性,主张创新的碑学书法开始兴起。但是碑学取代打击的是帖学的末流,“二王”体系下的优秀帖学作品的光芒并未被碑学书法掩盖。只不过这一时期的碑学书法被一部分现代书法研究者过于反复凸显焦点化罢了,而“二王”帖学则被无意识的弱化了成为了“背景”,并不能说碑学书法成为当时书法的主流。“二王”帖学的博大精深对于书家的魅力与吸引力并未衰退,反之因为北碑书法的传播途径问题,北碑的石刻文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古人用笔,使得学者往往雾里看花,难以学得笔法要领。对于同一件北碑作品,不同书家临摹必会出现不同的风格与解读,虽然这使得碑学书法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面貌与不同于帖学的审美趣味,但是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不少碑学书家的作品不得笔法要领,点画破败扁涩,使转失灵,线条缺乏厚度与韧性,结构呆板刻意。而碑学书法逞着改革创新的时代浪潮,打压着晚清帖学书法的生存空间。沈尹默出碑归帖后率先打出了复归晋唐的大旗,以“崇王”思想为核心,力主恢复发展“二王”帖学,并在建国后大量发表浅显易懂的文章,使得“二王”帖学进一步得到继承与发扬。
纵观魏晋以来的书法发展史,我们能发现书法发展总是循环往复的,“二王”帖学也总是在螺旋式的发展,每当书法发展稍稍偏离了“二王”帖学,总会通过帖学书家群体和“崇王”思想拉回到“主脉”之上,并发展出不同的时代风貌。例如元代以赵孟頫为首的书法家群体,面对南宋书法流于今人用笔造成笔法大坏的现象,力主学习晋人书法,表现出极强复古倾向。在表面上看这是书法艺术自身的修正与发展,但更深层次的是在元代外族统治的社会对立矛盾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继承,试图通过学习传播二王“主脉”书法来表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肯定。而沈尹默以“崇王”思想为核心的书学理论何尝不是文人阶层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回归。我们不能说沈尹默对“崇王”思想确立与发扬是近现代“帖学”回归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以沈尹默为代表的近现代帖学书家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崇敬与认同。
注释:
1.沈尹默著,朱天曙编.《沈尹默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2.王利翔编.《沈尹默讲授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