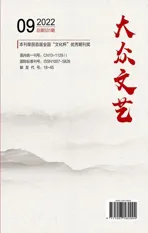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人间词话》之“隔”与“不隔”美学义发微
2018-01-27刘真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100020
刘真睿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100020)
一、引论——略介《人间词话》稿本情况
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年始在上海《国粹学报》发表,直至1926年俞平伯进行标点并序后由北京朴社出版单行本,期间近18年基本是处于消寂状态的。但时轮运转,承袭晚清学术界“遗民之风”蓄积增长,至民国以降便大都推及王国维“担任”国学大师的称号,其早年学术这才逐渐抖落于尘,为世人所关注。王国维对词话文本屡次删减,其理论也在不断地芟薙中趋于其自我认定的完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手稿本、《国粹学报》的发表本(简称学报本)和《盛京时报》的发表本(简称时报本)三种。手稿本撰写于1908年夏秋间,学报本发表于1908年末至1909年初间,时报本发表于1915年1月。这三种版本的《人间词话》,就篇幅上来说,是不断压缩的,从手稿本的125则到学报本的64则,再到时报本的31则,王国维不仅大致以“对半”的篇幅压缩着《人间词话》,同时对词话的内涵,也在不断做着调整。“特别是在时报本中,连为后来学界广泛关注、讨论过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等重要条目,都被王国维悉数删除,但“隔与不隔”一则不仅一直稳居其中,而且其重要性也在不断的整合中被不断强化着。”1而公众长期以来对于“隔与不隔”的理解也多自于《国粹学报》发表本,自然也是有原因的。王国维自我审订而成的学报本必然代表着王国维最终认定的最能体现其词学思想主张的文本内容。故而,我们要探寻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便也自然非以学报本为最上选了。
二、论“隔”与“不隔”之区分
经由王国维亲自编订的六十四则整本定稿本则是最能体现其词论思想成果的,而在六十四则中仅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专谈“隔与不隔”的问题,其他则涉及“境界”,“有我,无我”,具体作家作品,亦不乏有零星之断想,上述所叙不能说与“隔”论思想无关,事实上不仅有关而且是草蛇灰线的,但碍于今文主题,故不加以表述。另,在笔者看来,王国维所提出的“隔”与“不隔”均经悉思,虽在《人间词话》稿本中依然表露出王国维贬隔而尊不隔,但作为《人间词话》中思想精华的体现,其义理远不及表面文章那么直陋,此二论皆有其所优,王国维以单词只句以蜻蜓点水“隔”与“不隔”,在这一点上也却留给后代论家以更多阐发的余地。
(一)如何理解王国维之“隔”?
《人间词话》三十九则: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此则是王国维单论“隔”的,我们现也以此为基准展开。首先,注意则尾处王国维将“隔”概述为“雾里看花”,以云气雾绕之感来刺激读者对于“隔”的理解度。那我们就顺着王国维给我们的思路先来分析何为雾里看花。在一景中我与花表面上看是共场的,但遗憾之处在于我与花之间夹存着雾,而正因有雾的存在,我与花的共场形态被打破而迫使我欲观花则必将先须除雾,雾阻挡了我原有的视觉观感,进而使我产生了“隔”。上述概较易理解,但王国维所提出“隔”论以并非在于为提出而提出,即帮助普罗大众在鉴词赏诗时多点所谓理论思维,这样说来确实把王国维之“隔”说小了。在笔者看来,“隔”的真义不在存显,而在“破隔”——强调其独特的“转场”性。而王国维说其终隔一层,我们不禁要问,这隔的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隔就隔在了词作者没有使读者(王国维)一以贯之,在整体诗句所自然呈现并实时构拟而成的“画面流”中发生了画面折断——产生场域转换,从而导致读者不得不粘连前后方可续品,以维系原初的审美感受。但这种“迫使”并非读者之意,而是作者客观造成,故因务须“转场”而自生其“隔”。如四十则中至“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只王国维用一“至”字,此画面折断以致非“转场”不可之意甚明。
(二)如何理解“不隔”?
《人间词话》四十则:“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
又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又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
笔者将《人间词话》中所引论述“不隔”之词句列于上,即想为阐述笔者之说提供清朗面目。笔者认为,相较于之前的“隔”,王国维在选取上述词句时,着重突出了一个“语在目前”之义。同前段之”雾里看花“对比,其实不难看出”语在目前“之异了。而也如笔者用以前段之”转场性”提法,今亦配之以“在场性”。即所谓“在场”,指读者(我之主体)与作品及其所呈之世界是在同一场域内的,是“我”目之所及的,是“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是“观自在”的。作品(包括作者)将情感给得直接,明朗,让读者“无能者无所求,犹如不系之舟”。
而笔者拙以为将一“朗”字尝试替代王国维给出的“不隔”概念,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究竟何为“不隔”,何为王国维心中的“不隔”。诚如上文所探讨的,王国维之所以给出“不隔”这一概念,概系其取已有之“隔”的反义加以“不”字状语限定。这固然在字面表征上可以速度化的使受众掌握,但与此同时其弊病也如影随行。因为读者是在隔的基础上去理解不隔,是先期对隔的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去把握不隔,如果照此逻辑推演,就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顺序问题:不隔是否就是隔的反面的正反问题?或者说,隔雨不隔到底谁先谁后的先后问题?而之所以会呈现出问题,源头就在于王国维给概念给得比较主观化,个人意志化。一方面,王国维发现了词句中创作者描摹表诉的境界同欣赏者进行审美鉴赏之间存在着某种隔膜感,即产生了“隔”;而重点是王国维虽然提出了,并且是有明确的尊贬态度的,是绝对的尊“不隔”而贬“隔”。但这么一来,由于语义之间的勾连给他阐释个体思想便带来了天然的屏障的同时,他却又对他所极力追求的“不隔”境界无法做到概念涤清,使接受者对于“不隔”这一伟大境界无法做到深刻体味,而仿佛苟以为不隔只不过是隔的简单对立面,而这本身就消解了王国维的“以境界者为最上”的先验用心。而为以明确的辨正“不隔”的哲学意义,故须将“不隔”去动词化,而加以形容词性表达,方可保真而不失真。东汉班固《白雉诗》:“容洁朗兮于纯精。” 魏晋时期潘安有诗《悼亡诗三首》:“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王羲之《兰亭集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而笔者之所以取“朗”字加以代替王国维“不隔”加以形容性表意,乃源于陶潜《桃花源记》中关于武陵捕鱼人初见桃花源顿生“豁然开朗”之所情所感: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每每读至此,笔者似也有豁然开朗之势,桃花源之境自头脑中潜滋暗长,自此便不再有隔了。上述表达亦同前文较为易解,但重点是,王国维之所以如此倾心于捧“不隔”而鄙“隔”。其一,背后可能因为“不隔”之词句的美及思想同王国维个人主观情感上发生了对应关系,即王国维所推崇的叔本华悲剧主义意志论哲学;其二,与其所提倡的境界说直接关联,这其中有很复杂的王国维主观意志的产生外化于词句的左右判断。而这也是《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不隔”说的独特魅力所在——王国维化了的,专属于王国维式的特定悲剧审美概念产物。
《人间词话》四十一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情之不隔则在于要么苦离怨,要么觅他径;而景之不隔则在于要么物我浑然,要么冷眼静观。可无论情无论景,都无处不散发着一股幽幽渺渺,真可谓韩翃之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三、综论“隔”与“不隔”的中间地带——“天涯情味”
(一)二者均明显带有共时的空间性
如王国维所举欧阳公所作《少年游》一词中无论上阙“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之“不隔”,抑或是下阕被王国维论为“隔”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均易发现其共通处:作者创作之时必处在同景色对象的共享时空或平行时空之中,即便是“谢家池上”和“江淹浦畔”,也是由所处的“阑干十二”所勾带而出的“他景致”,抛开其所用典与否,但就言他也不过是“更特地忆王孙”罢了。
如四十九则:“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王国维在表达对于该词句认可的同时,也在表明出“隔”也好,“不隔”也罢,此二者自一降生便带有天然的空间性或空间距离。江的两岸不仅是离人,是哀愁,更是王国维视角下的“美”存在与境界存在。无论承认与否,至少在王国维眼中,隔与不隔是某种空间概念下的视觉映象,而被固化凝结成为了鉴赏美与不美,境界高低的菽麦之辨。因为有了江,不仅客观上增强了词的意境特写,更加大了作为第三者(王国维抑或他读者)的审美感受与审美体验。
(二)何谓“天涯情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四十则中有谈:“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王国维以“稍隔”这一概念作为二者中间地带的论述,在体法上来讲并无大碍,也得其体,但品来总感少有生气,似乎为文造辞。而近来也有学者对此有过说法,如中山大学彭玉平就提出其间有”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二态,所以共同构成了“隔”与“不隔”的四种结构形态。但在笔者看来,彭玉平是站在王国维境界说之“境多于意”与“意余于境”的角度上,将其转嫁于“隔”与“不隔”之中,虽说境界说同“隔”说有共通之处,但并非可以单向的以一而足。境界说所服务的对象角度与“隔”说是在不尽然全一致。更不必说在提法上刻意如出一辙。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说:“没有对于‘隔’的怀念,岂有对于‘不隔’之执着?王国维没有说过一丁点儿‘隔’不好、‘不隔’好这种小家子气的话。……我想,他是把‘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区别了开来。绝不是以卑陋的尺度去蹂躏古典的狩猎者。”2而在笔者看来,说“隔与不隔”同境界说毫无关联显然不妥,如《人间词话》四十一则中所论“...写景如此,方为不隔”以及第六则中“...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通过此二则对比不难看出,王国维的确将隔与不隔的说法与境界在某种角度予以了结合,即写真景物真感情,谓之有境界,亦为不隔。但这并不能就应因此而将二者关系盖棺定论,毕竟王国维在表述上给得并不充分,而多数相互概念间也极为模糊,正如王国维可以说陶谢之诗不隔,而有论者也可以说此二人之诗存在蠡测。而汪师韩曰:“何仲默谓:‘古诗之法亡于谢’,询特识也,独不当先谓诗溺于陶耳。”3如所引四十一则王国维前句举乐府古体为例重点并不在“方为不隔”,而在其前面一句“写情如此”;同样后句王国维将陶诗同北曲(北方民歌)并举,谈“方为不隔”也意在强调其前的“写景如此”。这里隐然存在一种呼之欲显的主客体参照关系:因为王国维个人同“避世逍遥”与“自然运化”的诗中情景发生了思想共颤,故称其为不隔,而并非代表该诗一定就是王国维所谓有境界者。“写情,写景如此”,即当译为“照这样来表现情感,描绘景致,方可不隔”,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弄清此处的不隔提法实是来自于王国维主观意志下对“不隔”说所提供的作为客体的情景两方面的参照标准,很难同其另一“境界说”理论并轨,或者说据现有《人间词话》定稿本,学报本以及时报本中各则表述中没有明了的理据来斧正境界说同“隔与不隔”确是殊途同归的。其实无论是写情还是写景,均是王国维用“隔与不隔”的审美观照角度来呈现出诗句在表现情景上的美学“成就”,而此美学概念并不等同于境界概念。而我们要做的也无非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罢了。
而在四十则中,王国维举姜白石之《翠楼吟》,前之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我们自然生疑,二句既相连接,怎又隔又不隔呢?回看原词方知,原来二句之间竟还夹杂着一句四字之言,即“天涯情味”,奚不知王国维是否有意将其省略抑或其真乃沧海遗珠?不过在笔者看来,此四字用以表述隔与不隔的中间地带实在妙之极也。何为“天涯情味”?江淹有《别赋》开篇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语中的,真只一别字而已矣!多情自古伤离别,在天涯即有所情味也不免带有苦涩,而在隔至不隔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从“因断而寻”的动到“同命相怜”的静,这其中的进化必然牵扯着极其复杂的“天涯情味”,而正是天涯情味才使得“不隔”的美学意蕴发散得如此幽冥。其实细看《人间词话》也会发现王国维对于“隔或不隔”是留有余地的。在第四十九则中,一改此前对于吴梦窗的笞贬,而说“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此一言一出,大有无声胜有声之势。隔江人于雨声中观菰叶飘旋顿生秋肃之怨,虽不知秋肃之怨是否因隔而兴,但肯定的是,江的隔离必然对于人之怨生起到了推进作用,从而也使王国维认同此一句当属吴梦窗难得之妙句,试想如将隔江人替换成“此处人”,算雨意且存,晚怨何佳?李商隐《春雨》:“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此时李商隐之“冷”怕是对姜白石之“天涯情味”抑或江淹之“别”均做出了最真切的描摹。雨纷纷,欲断魂,隔江者同对江人黯然而别,颸风拂鬓,如此恁般,怎能不为之着迷。
(三)“隔与不隔”中间态的产生系于王国维自身的犹疑——“徘徊”
上文已提到有关王国维“稍隔”的说法,如通览《人间词话》全本抑或知晓王国维其人其事,便会更能读清王国维的犹疑。王国维生于清廷大厦将倾之际,长于北洋马踏乱泥之时,时下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北洋割据,又加之列强蹂凌,宣统假变为康德,真不知何为国,谁当家。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王国维的头脑中既保有着家仇国恨的遗民情绪,又目睹了“堕河而死,将奈公何”的身世飘零;既留存着中国古典文化之传统,又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之翦商,所以结果必然会导致其思想既左且右,忽尔激进,忽尔保守。曹植早年风月,后夺位失败,生活越是压迫,心灵就越是趋于追求自由的幻化美,哪怕野田之黄雀终究挣不开悲剧的命绳:“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这种自由的世界,曹植是永远求之不得的。而后由于苦闷转向了老庄清静逍遥之上:“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但就是因为这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意识浇注中,间接促成了一位伟大诗人的诞生。4这样的王国维倒真有八分曹子建之风了,王国维也是求理想于现世无果从而坚定了叔本华式的悲剧主义美学观。南宋蒋捷有词云: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三段论盖表人世沧桑,赅意总万。其中笔者着重想谈的地方在于壮年之时所闻雨语:“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王国维五十知天命之年自沉昆明湖,亦在壮年。而其虽身处中华,然国将不国,山河飘零,犹如身系孤舟无家泊停。恐这只离了群的断雁如真地描画出了王国维当时的状态,找不到归家之路,找不到心灵的寄托,言虽称清臣,可自己的主上又在哪里?此时的王国维除了拼命地啼叫又还能做些什么?可脱离了大雁的群对(时下大势,五四即为主潮),其结局怕只能是徘徊上下,竟也不知这西风是陪伴还是送葬?
又梁简文帝作《东飞伯劳歌》:
翻阶蛱蝶恋花情,容华飞燕相逢迎。谁家总角歧路阴,裁红点翠愁人心。天窗绮井暧徘徊,珠帘玉箧明镜台。可怜年岁十三四,工歌巧舞入人意。白日西落杨柳垂,含情弄态两相知。
该诗描述了从蛱蝶的视角来观察豆蔻少女的模态,画面极其富有动感,也极其令人伤感,其伤感之处并非全在于自蛱蝶眼中所见的少女是可怜的,年岁十三四,工歌又巧舞,却面临着白日将西落。而是少女之美此时也只有蛱蝶这一真正的相知者,别无他人同道以赏,是谓大可悲。“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王国维最大的苦闷症结也处于自我与时代的互讦,从而造就了王国维根本性的悲剧意义。或许王国维真能理解《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前为何得要“徘徊庭树下”了。
四、“隔与不隔”于我见
(一)各美其美
在笔者看来,“隔”更倾向于一种接受者的审美感受及体验,用王国维于四十三折则中所提到的“颉颃”一词概论甚妙。颉颃者,鸟上下翻飞也。《诗·邶风·燕燕》有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而后又引申为相互较量之义,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王成》:“进退颉颃,相持约一伏时。”在这里则突出了读者在接受作者通过作品所传送的思想情感之时所产生的逆向遇挫而“因其有断而粘连”,与作品,与作者相沟通,相磨合。而对于“不隔”则用四十四则之“捧心”一词概论甚妙,是一种审美理想的涂饰。西子捧心,常言美人病态之美,即表明美可以伴有隐痛感,可以让人稍有不适,悲情美也是一种迷人之“大美”,这亦与王国维之美学诉求相符。正所谓是作者与读者的“同命相怜”,进而惺惺相惜,相偎相依。
笔者认为,“隔”一层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虽好,逢君如故,格调虽高,却苦于落花时节,总不免心生惝恍,普有不适。又虽有不适,仍有江南风景,君之如旧作陪,已有稍缓;而“不隔”一层则应为“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因闻莺之啼叫正如我之泣诉,同命相怜,故盼其飞到天高处,为我垂珠于琼顶之花。两者一如颉颃,一作捧心,是有悲而趋近,是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天涯之事,无力回天。
(二)互作轩轾
此处笔者试以“山障”心理说明。客舟行于水中,两岸猿声,和鸟齐飞,湖侧有山,舟中人眼见此山存于此,心中必略有想过山后之风光许是无限,却因山之阻隔使得自己无法直目其全美,这是“山障”心理的逆向遇挫;不过与此同时,已知山水不可平,便在不觉中学会了如何欣赏自然的本来美,审美能力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进而升华了我之于自然的对照关系,不断地在实践中改写着关于“不隔”的定义。斗转星移,原来发现,正是有了“山障”,才增加了自然的错落与可爱,才知晓了山之障亦是水之生的道理,这就是“山障”心理的顺向相应。于是就有了《古诗十九首之冉冉孤生竹》中的“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有了欧阳修《浪淘沙之万恨苦绵绵》的“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阔山高人不见,有泪无言”。隔山亦隔水,山水脉脉,隔即不隔!的确隔与不隔在审美感受上可能会有差许,但在由隔走向不隔的过程开始,不断地向审美理想逼近,意义也就自然流淌出来了,不觉间隔者似也多了几分不隔之神气。而推至“隔或不隔”,这也正是笔者所欲形容之。“隔”与“不隔”实在是难以分半的,其你中有我,我中亦有你。笔者认为“隔”与“不隔”本是同根生,并无本性之优劣,皆因个人之取舍。隔之为隔,在于其有观之人欲观其貌而努力破其隔以至不隔;而不隔的真义则在于其之前延与后余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先隔的基础上。
五、结言
(一)王国维尊“不隔”而贬“隔”是否存在他因?
《人间词话》三十九则: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之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此处王国维已在字面上很明白的将“隔”字实体义了,地理化了,便带有了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似乎“隔”之诞生边口中衔着某种暗含的政治诉求与原型对应。那么王国维是否真的在尊“不隔”而贬“隔”,尊北宋汴京之词家而极贬南宋隔江之词家,其背后也携带了某种政治隐喻?而“隔与不隔”之说的提出是否确实包含着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并天然存在关联?由于王国维《人间词话》全本均为残丛小语,无法统而论之,但从1928年赵万里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录出的刊登于《小说月报》19卷3号的四十四则,以及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之所谓《人间词话》“补遗”之中,可全面了解王国维关于《人间词话》的原有整体思想脉络。尤其在四十四则中多次贬斥南宋词人词作,如二十六则中:“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做百首也得者也。”5等等。但其中并明确未涉及到“隔与不隔”的问题,而只是就词谈词,所以究竟二者是否真正存在特定关联还需进一步加以考证。
(二)且谈托语
其实若究论王国维之隔与不隔实有太多可阐释的话语,但那都是因说而说的,我们自不必拘泥于王氏先天所给,在我们每人对词句有所感悟之时,心中已然成千。不过回到王国维对于此提法的本身上,笔者思考的是,王国维提出隔与不隔的意义价值究竟在何?其优自不必说,这组概念的提出本就是意义,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解读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学遗产;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不足。
其一,如王氏选取之语汇稍有差池,使人难窥齐全,并且其不加细论,只浮光掠影式点点滴滴,实在有些隔靴搔痒。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十九则所引姜白石写景之作“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并批其皆在一“隔”,可殊不知姜白石此词题为《扬州慢》,全词只为表其所感之慢淌,小溪淙淙,情伤淡淡,这份慢流的基调是姜白石写作的初始;而“二十四桥”即便仍在,也并非有“隔”,只是为了配合后面的“波心荡,冷月无声”而写,并未“出画”;而无论上下阙,词的整体节奏都是放慢的,因为作者对于此时此刻的扬州景是慢看的,是不舍匆匆而过的,因而即便有所谓王国维之“雾”,但其存在也正因慢之所需,有雾似乎也正可帮助作者虚封目前的扬州,缭绕作者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绪。而细品白石《扬州慢》所写背景所写原词后,方可更能体会笔者上述所言。
其二,王国维受西方叔本华之类的哲学悲剧影响过剩,直接导致其思想体系犹豫不决,甚至连犹疑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反复踱步而已。终究使得个性小审美虚化了对于文学的大反思。真如其诗:“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注释:
1.彭玉平.《论王国维“隔”与“不隔”说的四种结构形态及周边问题》.《文学评论》.
2.岸阳子.《竹内好之王国维论——以〈人间词话〉为中心》,孙敦恒、钱竞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3.《诗学纂闻》,《清诗话》第四五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第一版。《明史·文苑二·何景明传》:“其持论,谓:‘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撰《列朝诗》,力诋之。”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版
5.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7月第1版,第57页
参考文献:
[1]徐调孚.《人间词话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2]谭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0年版.
[4]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祖保泉.《王国维词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王宗乐.《苕华词与人间词话述评》.(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9]朱光潜.《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
[10]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
[11]刘锋杰,章池.《人间词话百年解评》.黄山书社,2002年版.[12]唐圭璋.《评〈人间词话〉》.《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13]岸阳子.《竹内好之王国维论——以〈人间词话〉为中心》,孙敦恒、钱竞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罗振常.《〈人间词甲稿序〉跋》.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