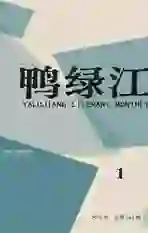上言加餐饭
2018-01-24吴祖丽
吴祖丽
一
我到得比较早,进房间看了会儿电视,又冲了澡,然后到一楼的自助餐厅默默吃了点晚餐,尚见零零落落有人前来报到。他们拖着行李箱停在铺着猩红金丝绒桌布的报到台前,弯腰签到,领房卡和材料。然后又拖着箱子咕噜噜穿过走廊,金色电梯门呼哧打开又呼哧把人一口吞了进去。
我决定去散会儿步,顺便怀个旧。差不多十年前,我在A市短暂工作过。后来的这些年,东飘西荡去过很多城市,却唯独没有回来过这里。主编说有个全省新闻记者高级研修班问我想不想去,我对这类培训向来不抱期望,油腻草率的自助餐,每天端坐七八个小时,听主席台上的老师煞有介事地贩卖连他自己都未必信任的东西。可是想到最近太累了,不妨借这个培训班休息放松一下。
出门右拐,一条颇为修整幽静的人行道,远远看见前面是个街心公园,三三两两有人在散步和遛狗,更多的人在跳广场舞。太阳落下去了,天气却还是很热,风吹在脸上带着溽湿而黏稠的重量。我仿佛嗅到从古运河吹来的一丝丝咸腥气息。想到这里,我被一阵莫名的伤感击中。然后,我看到了他。
他个子很高,腰板笔直,穿着一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白色短袖衬衫束在黑色长裤里,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他正跟一个打太极拳的老人讨论天气,身子前倾,头吃力地够着,几乎把右边耳朵伸到人家脸上了。看着有点面熟,却想不起在哪见过了。他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叶与叶的间隙洒下几点余晖,一缕淡金的光芒恰好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一分而二,一亮一暗,一黄一白。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脸上复又现出一种庄重严肃而又柔和茫然的神气。
我想起他是谁了。对了,就是这种庄重严肃而又柔和茫然的神气,那时候,他天天早上到街道办,比我们上班的还准时。他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我跟朱明背后开玩笑说他是唐国强。因为他长得很像那个演电影的唐国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化不太大,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直固执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连跟人说话的姿势也没有变,身子前倾,头吃力地够着,几乎把右边耳朵伸到人家脸上了。他一直算是讲究的,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眉宇之间很有几分英氣。他说过,他左耳被炮弹震聋了。他怕有五十岁还是五十五岁?现在的人,年龄说不准了。
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他忽然荒腔走板地哼了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转过身去,正对着粗大的梧桐树干啪啪啪地击掌。这是他么,我疑惑着。
二
大学毕业那一年的夏天,很偶然的一日。我下楼去买泡面,被同学拖到校团委,跟着她填了一张表。两个多月后,我作为“苏北计划志愿者”被分到了A市的桃花坞街道办。报到那天,我看到了同班同学朱明,他是A市人。我们俩的相遇,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他的什么。
朱明分在党政科,我在民政科。我还记得,科长见我来时,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把科里事情交代了一番,然后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中年男人,强调说,小乔,我们民政科主要工作是做好服务,要让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走。
他拍了拍中年男人的肩膀说,这是我们科里新来的小乔,以后你有事向她反映。又嘱咐我,小乔,拿本子记下来。科长说着就着急忙慌地推门走了,像被兔子咬了尾巴。
我还没反应过来,靠窗坐着的中年男人忽然走到面前,啪地敬了个礼,大声地说,报——告,脚后跟很响地碰了一下。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什么路数,手里的签字笔没捏牢,滑了出去。我手忙脚乱地捡起笔,又倒了杯水,请坐,请问什么事。他在我桌子对面坐下,笑眯眯地说,我是来开会的。电脑显示屏上映着我一脸的愕然。
大概预料到我的窘境,朱明出现在走廊上。他招手叫我,指了指自己脑袋,耳语说,他这里有问题,你别管他,他来开会,你就让他坐着。他说什么,你听着就是了。
他来做什么的?
不知道,天天来,这里的常客。他们都叫他徐师傅。朱明表示爱莫能助地看了我一眼,摆摆手走了。
徐师傅端正严谨地坐在椅子上,双膝并拢,双手握着一本大红硬塑封面的旧笔记本,好像随时准备往上面记录些什么。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旧军装,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左胸那儿挂了四枚亮闪闪红艳艳的勋章。我按捺不住好奇,徐师傅,你胸口挂的是什么?
我说话的时候,他把右半边身子朝我倾斜过来,然后眼睛很亮声音很骄傲地说,都是我的军功章,你看,你看看。
我凑上前去,仔细辨别着那几枚形状各异的军功章:三等功奖章、自卫反击保卫边疆、作战纪念、献给最可爱的人。有的字勉强可以辨认,有的字已经漫漶不清了。他一直紧紧盯着我,像眼巴巴等待老师表扬的学生。我连忙说,真了不起,徐师傅,你是英雄啊。他摇着头严肃地大声说,我不是,我不是,那些牺牲的人才是英雄。他们有的埋在纪念碑下面呢,有的就这么没了,炮火连天的,连根骨头都没有留下……
他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十分痛苦,像被一股什么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攥住了,声音越来越轻。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自顾自地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不停地喃喃自语。我心惊胆战地看着他,生怕他哭起来或有其他的意外之举。幸而他只是自言自语了一会儿,就客客气气地告辞走了。
朱明告诉我,徐师傅从部队退伍后,分在汽配厂。前几年下了岗,本来好好的人不知怎么就鬼上了身似的,街道给他协调了一个门卫的工作,他也干不下来。
怎么干不下来的?
他们说他听到汽车喇叭响,不去开大门,倒吓得躲到桌肚子里去了。脑子坏了,还以为听到的是枪炮声。也真可怜,现在只能靠点补助金过日子。
家里人也不管他?
不知道。
他结婚了吗?
好像没有。应该没有。朱明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他只有一个老母亲。
可惜了,长得不错啊,年轻时候应该很帅的,像那个电影演员叫啥的?
唐国强。endprint
对,唐国强,你也这么觉得?
街道办的人都这么说。
朱明说的果然不错,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上班都能看到唐国强,噢徐师傅。他有时候来坐一会儿就走,有时候能待半天,看到谁都要立正敬个礼。通常的情况是,我坐在电脑前写材料整理报表核对数字,他就坐在我对面,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我们科长很少在办公室,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外面核对贫困户低保户信息。朱明说科长就要退休了,家里又新添了个孙子,哪有心思上班。朱明跟在大学里一样,是个百事通。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大一就进学生会,大二做了学生会主席,怎么看着都是兴兴头头一心要从政的。志愿者计划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大概只是个历练和跳板,他正在积极准备考公务员。而我,只是因为无处可去。周围人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只有我准备背上背包去流浪,志愿者计划算是流浪的第一站。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的父母迫不及待地离了婚,并且很快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个暑假出席的接二连三的宴会,至今令我难忘,先是我的谢师宴,然后是母亲的婚宴,接着就是父亲的婚宴。一个非常喜庆而诡异的暑假。
刚到桃花坞街道办的那两周,我每一天都想写封辞职信然后抬腿走人,除了民政科的一堆事,我还要打许多杂,准备各种会议和检查,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交通值勤,甚至帮助计生办发放避孕套。最奇葩的是,婆媳吵架,那个女人居然把中风坐轮椅的婆婆往街道办一送,扬长而去。领导没法子,就让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护老人。就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干满了一整年。我其实并不在乎是否履行那纸协议,也不在乎中途毁约,我对体制内的工作毫无兴趣。这些年,我边旅行边工作,也算走了不少地方,干过青年旅舍的前台,酒吧服务员,导游,药房推销员,家庭老师,嗯,然后就是现在这份记者的工作。这是我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大约因为老了,不由得想要安静下来。算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份工作。也许跟徐师傅不无关系,我甚至记得他普通话里芜杂的口音,似乎是A市的,又似乎不是,有点五湖四海的味道。民政科办公室里有个档案柜,我在退伍军人那一格里查过他的资料,他叫徐建军,1983年参军,1984至1985年参战。1988年退伍,2001年下岗。非常简单,没有多余的话。有一阵子,他经常说起一个牺牲的战友叫陶雷的。他们是高中同学,一起当的兵,一起打的仗,一个活着一个死了。他说,陶雷喜欢一个女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她写几封信,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写,外面枪林弹雨也写……
我在电脑上一边弄材料,一边嗯嗯嗯地应着他,女同学回信了吗?
那时候打仗,有回信也不一定收到的。
我逗他,是不是那个女同学也喜欢你。
我不知道,他忽然羞涩地笑了一下,陶雷说谁活着谁就回家娶她。我以为死的肯定是我,谁知道是陶雷啊。他们的卡车轧上了地雷,一车人啊全牺牲了。是我去抬的他。从那以后,我一做梦就是他,到处血肉横飞的……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好像就要哭出来似的。
徐师傅,喝点水,喝点水。我倒了杯水,转移话题说,你回来了,怎么没娶人家?
他呡了一小口水,嗫嚅着,她嫁人了。
民政科人来人往的,大多数是来申请低保以及困难补助的人,个个揣着一本难念的经。可是这些人看到徐师傅还是忍不住打趣他,好像能够从中获得多少快乐似的。徐师傅,又来开会啊。徐师傅,你打过仗,来来,就拿这个当枪使,摆个造型给我看看。老徐,手榴弹什么样子你还知道啊,整天念叨什么山什么洞的,不是编的吧,哈哈。
徐师傅好脾气,谁说话他冲谁竖起右耳,一脸的严肃认真。他说怎么没打过仗呢,千真万确啊,到处是深山老林,天气又坏,潮湿闷热,大雨浓雾,蚊虫乌泱泱的,咬得我们浑身是包,溃烂流脓。有时候他也生气的,怎么是编的呢,你这个人到底讲不讲理的。他的声音逐渐变得无力而哀伤,昨天我还梦见陶雷,梦见他趴在山洞里,一遍遍地放着邓丽君的那支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老茧。他说着,使劲拽了拽自己的耳朵。
他们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了。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自顾自说着,不断引发他们更为大声地笑。他说有时候后勤补给送不上来,我们饿得没办法,只有打野味吃,野鸡野兔野猪,逮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在松毛岭居然撞上一条大蟒蛇,很大,缠在树上。那条蛇少见啊,蛇身碧绿,头赤红,怪哧人的。因为怕招来敌人不敢放枪,大家就手忙脚乱地拿刀去砍,仗着人多也不怕,不知谁一刀削中了蛇尾。蛇断了那么一截尾巴,居然沒死,还逃跑了。我们用尾巴炖了一锅汤,嗬,光一根尾巴足有十来斤重。一个连的人都喝到了,特别鲜美。
我听得直犯恶心,这么大的蛇不怕有毒啊,居然也敢吃,不可能吧。
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呆呆地坐着,一双眼睛定定地大睁着,凝视着空气里的什么。
三
朱明打电话说有时间见个面啊。我心里莫名有点慌张,正思忖他是如何掌握我的行踪的,他笑着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已经到我家门口了,居然不知会主人一声,一点同学情面都不给啊。我也只好笑着说,知道你现在是个大忙人,日理万机的,实在不敢叨扰。
当年我离开A市时,朱明已经通过了公务员招考的笔试,岗位就是桃花坞街道办事员。他想动员我一起报考的,我压根没有这个想法。志愿者工作期满我就收拾行李,去了云南丽江。这些年,我跟所有同学都疏于联系,很少发朋友圈也很少聊微信群。直到去年,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其实这样的聚会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徒增无聊的伤感和回忆。那次聚会,朱明成了令人瞩目的明星,有人爆料他刚提了副区长。从街道办办事员做起,历任副科长、科长以及街道办副主任、主任,三十三岁做到副区长。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人,你大概能想象是怎样一个历程。座中有人低语,还不是走了捷径。我问,什么捷径?他是无党派。我笑笑。
第二天晚上,我们约在一家茶馆见面。茶馆仿明清建筑,四周挂着大红的灯笼。后面有片竹园,是个清幽的所在。坐在雅间,推窗即是运河水,许多红灯笼悉数倒映在水面,水波荡漾,醉红摇曳,倒是颇有几分情趣。朱明指点给我看,那里就是御码头,明清时这里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称。乾隆六次南巡都在此弃舟登陆,曾经写过“便觉景光非北地,行看佳丽到南邦”的诗句。endprint
我笑,你职业病犯了,把我当成招商引资的客人了。你忘了我在这里工作过?
他往椅背上一靠,含笑看住我说,怎么会忘。
气氛有一点微妙,我掩饰地喝了一口普洱茶说,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那个徐师傅,你记得吗,就是当年天天到街道办来报到的。
喔,就是像唐国强那个,怎么不记得。
他现在还到街道办来吗?我指指自己脑袋,这方面怎么样?
自从结了婚就不来了,现在老夫妻俩在小区门口开了个超市,日子过得倒挺不错的。
结婚了?这怎么回事,你说说看?我特别好奇。
他沉吟了一下,右手食指无意识地在桌子上划着那些水渍,他结婚有五六年了吧,我还代表街道去参加婚礼了。新娘叫什么来着,对,淑芬。淑芬和徐师傅,还有他那时候经常念叨的战友陶雷,他们三个人是高中同学。陶雷一直喜欢淑芬,徐师傅其实也喜欢这个淑芬。陶雷死了,徐师傅亲眼看到他被地雷炸得不成样子,当时心理就有点障碍,在部队也治疗过一阵子,好多了。刚退伍回来的时候,淑芬其实还没嫁人,但他一直没有消除心理阴影,想着战友救过他的命,他哪还有勇气追求本来属于战友的幸福。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吧。
命运兜兜转转,居然还能碰上?
是啊,到底是缘分未尽吧。淑芬结过婚,后来离了。跟前夫生的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
真有意思,居然把病也治好了。
心病还需心药医。朱明说着,夸张地捂了捂胸口,听说淑芬当年喜欢的并不是那个战友,而是徐师傅。这么多年了,她还保存着他当年在前线寄给她的一张明信片,我看过,正面是北京天安门,那时候特别流行的那种。明信片上写着一句诗:上言加餐饭,下言常相忆。
上言加餐饭,下言常相忆。想不到徐师傅当年还挺文艺的。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文艺。他笑,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你想不想听?
当然。我看看表,不知不觉已经快十一点了。
朱明起身去洗手间,我看到他信手在桌上涂抹的水渍,竟然写的是筱竹筱竹四个字。明知他大概只是无意识地写了我的名字,看着那水渍渐渐干了,心还是轻轻飘了一下。那年在街道办上班不久,朱明有次酒后跟我坦白,他在团委看到我填的“苏北计划志愿者”表格,就跟着填了一张。后来,他很费了些心思,托熟人把我和他分到了同一个地方。我笑笑,没说什么,我们不是一路人。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约我去看电影《色戒》。那天不知怎么的,电影使我有些莫名其妙的伤感。从电影院出来,我就一直想哭,他拉我去吃宵夜,跑了几条街也没有找到一个大排档。我说我走不动了回去吧,他一把拉住我的手,很自然地吻了我,自然得像是第一百次。我记得,那晚月色溶溶,风有些凉,我告诉自己只是有些伤感。
他回来接着说。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淑芬跟那个战友结过婚,还有了孩子。战友牺牲后,徐师傅一直照顾淑芬母子,还把自己不多的收入和补助金拿出来接济他们。渐渐地,日久生情,也可能徐师傅本来就喜欢淑芬,但始终迈不过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就这样,后来下了岗,脑子就出了问题,整天生活在幻想里。至于天天到街道办去开会,也是幻想所致……
两个版本,不对啊。那时候徐师傅说,陶雷死的第二天,是他二十岁生日,好像是说差一天就二十岁了。二十岁就结过婚有了孩子?
他们那一代的人啊,说不清楚。你说他们文艺吧,他们也愤青,但是他们也有气壮山河的时候,他们甚至有时候可以不为自己活,他们注定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朱明沉思着,他们结婚就办了两桌酒,然后去旅行了,第一站去看的就是明信片上的北京天安门,第二站去看了陶雷。淑芬回来告诉邻居,他们带了卡式录音机和磁带,在陶雷的碑前放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又烧了纸,磕了头,徐师傅当时就脑子清楚了,说起来神奇得不得了。家里都说,早知道应该早点去的。
真好。我前一阵子看过几部电影,像《现代启示录》和《猎鹿人》,还有那个《全金属外壳》。都跟战争有关,很可怕却又很幽微,我说不好,那种感觉。
我知道。我看过你写的影评。
我有些吃惊,想不到朱区长日理万机,居然有时间看我写的那些个鸡零狗碎的东西。
一个穿藏青绣花旗袍的服务员来续水,他停了一下,笑着说,我还看过你写的小说,徐师傅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小说,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你知道的还真多。我喃喃说。
我只要想知道,自然能知道。他笑起来,脸上放着光辉。朱明变了很多,男人就是讨巧,明明历经的是沧桑,到他们身上就成了底气和历练。他倒没怎么胖,但明显结实了许多,举手投足之间有一些圆熟,却也不那么犯嫌。我想他一定经历很多之后,才有这样的安静笃定。大抵他身后有个安稳幸福的家庭,有个贤惠能干的妻子。
时间不早了,你家里?我又一次看看表。
他身子趋前,双肘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指尖,淡淡地说,我离婚了。
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没想到。我隐约记得他找的是个师范学院的老师。
是她要离的。她出国了。
不好意思。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难道跟你有关。他浅笑着看我。
我斜睨了他一眼。
他没有说话,脸上的神色忽又正经起来。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楼下竹林原本黑黝黝的,这会儿不知是谁亮起了灯盏,衬得满林子绿莹莹的,反倒有股子说不出的阴气森森。别人以为我名字里两个字都是竹,不定有多偏爱此物呢。其实名字是父母给的,我倒更喜欢红烧肉。
四
刚洗漱完上床,手机叮咚响了一声,是朱明。没头没脑一行字:你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吗?真是莫名其妙,我怔了一下,发了个问号。
他很快回了一句,你心里明白的。
我叹了口气,颓然把手机反扣到床头柜上,一翻身趴在床上,整張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好一会儿,脑子里一片空白,空调咝咝地吐着冷气,半湿的卷发从毛巾里散开来,几滴水珠滑到脖子里,凉凉的。
我昏昏沉沉地趴在枕头上睡了过去,一夜做了许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不是朱明,而是徐师傅。我梦见他在自家超市里,趴在一张桌子后面写字。本子合起来,是一个大红硬塑封面的旧笔记本。他后面的玻璃展柜里端端正正地陈列着那几枚勋章。勋章上的字有的已经漫漶不清了,要凑上去才勉强可以辨认。超市后面连着一个小披厦,做了简易厨房,女人在灶台上忙来忙去,连名带姓喊了一声,徐建军,吃饭了……
我打开手机,跳出朱明凌晨发来的一段话,再次见到你,我更加确定自己的心意。筱竹,你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是我愿意与之一粥一饭、一菜一蔬过日子的那个人……
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伸出食指摩挲着手机显示屏,一抬头看到梳妆镜里的自己,嘴角上扬,两颊飞红,连眼角都红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婚姻,我看着自己的脸,仿佛感觉有些东西正在被改变,一切都不一样了。
早上的培训班,我去点了个卯就溜出来了。我打个出租,按照朱明说的地址找到清水湾小区。果真挺近的,小区进门右侧就是淑芬超市。超市很小,招牌倒挺大的,看上去是轿车库改建的,卖些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拿着抹布上上下下擦拭玻璃柜台,头发低低地挽了个髻,穿着一件白底碎花连衣裙,她应该是那种会过日子的女人,一举一动里透着某种淡然和安闲。她大概感觉到了我的脚步,转过身来笑了一下,她白皙的杏仁脸上有双含笑的眼睛。她年轻时一定是个讨人喜欢的美人,就是现在也算得上小巧温柔。
小超市跟我梦里的竟然一模一样,一张油漆剥落的写字台。写字台后面的玻璃展柜里端端正正地陈列着那几枚勋章,金色的部分静静放着光辉。不用看也知道是什么。超市的货架尽头还有空间,灰茫茫的光线背后连着一个小披厦,大概是自己搭的。
正在这时,里面有人扬声喊,淑芬,我去买菜了。
我忽然觉得嗓子那儿堵得慌,就低头退了出来。我站在路边给朱明打电话,电话接通了,耳边传来牙痛似的电流声,我怔住了,他也没有说话。好半天,我哑着嗓子说,你昨天说的小说,我想写。他说嗯。写徐师傅和淑芬,我吁了口气,艰难地说,也许还有你和我。他顿了顿,柔声说好。
【责任编辑】 宁珍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