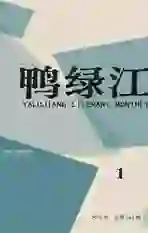短篇长读(之三)
2018-01-24刁斗
刁斗
贡布罗维奇的《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
坦白地说,在这一讲,我选择把維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这个“长篇插曲”介绍给大家,不是特别理直气壮,自己都觉得,它很像一个支应的幌子,而幌子下边我贩卖了私货。当然了,我以这样的口吻论及的私货,也不是什么龌龊的东西,上不得台面见不得人;只是对我们讲座的主旨来说,这私货的存在,会让我这一讲的动机不那么纯粹,其出发点,有欠单一和专一。这么说吧,某种意义上,我将波兰语引入今天的讲座,为的更是音乐家弗雷德里克·肖邦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我是想通过我的方式,向他俩所承载的我心中的寄托请安致敬——哦,我这么一番东拉西扯,有点乱套,像制造混乱,顶好也是在以乱治乱。这不行。那我就还是按部就班地踩着节奏,一句一句地,对我上边的说明做个说明。
不知大家留意过没有,我们这个已进行到第七回的“短篇长读”系列讲座,每一讲的作品以及作家,都出于不同的语种——至于国别,虽然也不一样,但你只要稍加判断,就看得明白,那显然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只能读翻译作品、在任何外语面前都文盲的小说读者,却对语言这一制作小说的基础性材料兴味特殊,所以,每一讲里,我的主角,都会有一个语种的背景:俄语的契诃夫、法语的莫泊桑、英语的霍桑、德语的卡夫卡、日语的芥川龙之介、西班牙语的博尔赫斯……然后,除了今天贡布罗维奇的波兰语,在下一讲和下下一讲,我还将和各位一起聆听莫拉维亚的意大利语和克里玛的捷克语。我意思是,假设我的讲座只做九次,我那粉墨登场的九位同行,所代表的创作语言将没有雷同。事实上,我原来的讲座计划,也的确是九讲,基于某些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原因理由,我一直喜欢九这个数字,此外,对其他奇数,我的喜欢也胜于偶数。听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了,依我前边做的介绍,我这九次讲座里已经出现的卡夫卡和即将出现的克里玛,居住的可是同一座城市,难道,就因为后者小了四十八岁,他们就得成陌路吗?呵呵,这还的确是个问题,还真需要啰唆几句。欧洲历史的沿革演变,与多数情况下中国历史那种单纯的改朝换代是不一样的,即使到了当代,仍然会有麻麻烦烦的分化重组现象间或出现,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国家概念的淡化模糊,比如那个写出了《铁皮鼓》的格拉斯,他那现名格但斯克的出生地但泽,就曾经一会儿归德国一会儿归波兰,一会儿又作为自由邦归国联代管,至于诸多东欧国家,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围绕苏联这一政体所出现的万众归心与众叛亲离就尤其典型。所以,卡夫卡与克里玛虽然都生长在布拉格,又同为犹太人,但还真就不能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之间的刚性分野,不在于他曾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则先后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而在于,他们分别以德语与捷克语写作小说——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好兵帅克”之父哈谢克,与卡夫卡的泾渭之别也是这个。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首先应该服务于语言,唯有语言,或者说唯有母语,对于写作者来说,才最有资格既物质化地标识身份,又精神化地成为存在之家。我不否认,也有些人情况特殊,比如我们以前顺嘴提到过的纳博科夫与贝克特,在漫长的写作历史中,就分别使用过俄语和英语以及英语和法语。对此没必要斤斤计较,应该认同在他们那里,两种语言都算母语,这就好比,光绪皇帝既有生母婉贞,又有慈禧这个著名的养母。
可谈论语言,我却扯出了肖邦和米沃什,这么上挂下连又为什么呢?难道分别作为长住西欧和后来干脆入籍美国的波兰人,他俩的母语很特殊吗?最初,我为九种语言选择作者和作品时,只单纯借助了记忆的提醒,如果也遵循过什么标准,那唯一的标准,便是某篇在我头脑里烙印深刻的小说有可能生成出来的文学话题,除了能勾起我比较强烈的言说兴趣,还应该尽量地少被他人甚至未被他人给予过关注——注意,我说的是“文学话题”,而非某篇具体作品。这样的选择略嫌刁钻,好像也麻烦,但实际上并不困难,虽然在小说欣赏上,我的理性不接受大语种沙文主义,却也没法否认,可圈可点的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作品,的确俯拾即是比比皆是,即使在稍逊一筹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后起之秀捷克语日语里,可评可议者也不难搜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八种语言之外的作品就不值得看,我所说的“可圈可点”和“可评可议”,只是指,它们中恰好纳入我视野的那部分里,有许多都方便我拔茅连茹或顺藤摸瓜;我也愿意相信,很有可能,在马来语孟加拉语斯瓦希里语里,并不缺少能够创造文学话题的小说适合我“圈点”与“评议”,但我没缘分读到它们,自然也就无福把玩。不过我一直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最有价值的文化收获,就是译介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大量世界各国的人文著作,所以,如若哪个小语种的杰出短篇成了汉语翻译的遗珠之憾,我也并不担心,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对整个文学世界的理解与判断。
好啦,至此,算是铺好了轨道架好了阶梯,我们可以登堂入室了,去贡布罗维奇的小说世界里游览观瞻——哦,《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题目太长,以后,我将只以《菲利贝尔特》简略地称它。
在我印象中,波兰语提供过很多好的文学,尽管贡布罗维奇批评它缺少规则和准确性,而米沃什指责它匮乏哲学的表达形式,难以支持智力交流,但近百年来,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它就贡献了四位,并且还出产了像康拉德或辛格这样重要的作家,虽然后来,他们分别成了英国人美国人,又分别只以英语意第绪语写作小说,可由于他们分别在成年以后的近二十岁和三十出头才离开波兰,因而波兰语便不可能不也是他们的重要养分,这样的事实,又足以从文化基因方面,说明某些微妙的问题。但是,当初我草拟讲座名单时,在迅速把其他八个语种敲定以后,并没让波兰语轻易进入九强,其理由是,在我视野里,最理想的波兰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更应该出自上一讲我曾提过一嘴,其经历和小说都话题性很强的布鲁诺·舒尔茨之手。可经过考量我又觉得,舒尔茨小说那种完全彻底的主观化色彩与内趋式表达,似乎更适合一个高度敏感之人暗夜枯灯中的独自感受,而发布时尚新品般地集体围观,恐怕很难尽现其妙。于是,一度,我曾想把九次讲座缩减为八次,毕竟,像我这种不把“八”奉为吉兆的人只是少数,喜欢“八”的则人多势众。但恰在这时,我脑海里,如同有乐音回旋或诗句抑扬那样,连绵接踵地,出现了肖邦与米沃什为他们的母语游说说项的音容笑貌,这么一来……其实,对肖邦我没有太多感觉,想到他也与音乐无关,有关系的,只是我对春心初萌时无比喜爱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切一切都念念不忘,比如,几十年里,我一直坚持把她“休息宜少享受宜简”的生活戒律置于座右,都不介意别人笑话我幼稚病小儿科;同样,我想到米沃什也不为诗歌,而为的是他的散文作品《被禁锢的头脑》,这部致力于思想阐释的独特文本,不论被别人视为随笔长卷还是小说合集,在我看来,都既是超越时空的卜辞谶语,又是灵魂裂变的畸图异像,还是我自童年开始,不管乐意与否,总要心怀恐惧又兼有好奇地反复观看反复揣摩的人性表演,它以一种一剑封喉的准确,真实地写出了我父兄辈的、我这辈的,甚至我子侄辈的已经创造出来的或即将创造出来的人格的卑污与人心的黑暗以及人这一物种的无以救赎,更提前写出了我个人的、需要我不断以余生的理性认知作为涂改液去修订校正的生命自传。endprint
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有一部先定的生命自传,哪怕他对那自传一无所知或并不認同;但同时,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他还没被这世界盖棺论定,他那部貌似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确凿之书,就也有机会有可能得到修订校正,区别只是,那修正它们的涂改液,在每个人那里,又可以原料有别材质不同。前边我说过,为修正米沃什冷酷地揭示出来的我的命运,我愿意以理性的认知为涂改液,通过内省去纠偏我的人生轨迹,争取让米沃什这位通过镜鉴他的同胞而对我做出暗示性估量的先知诗人的预言落空;可我的同行,诞生自贡布罗维奇笔下,也像我一样总心绪茫然满腹困惑的波兰小说家尤瑟夫,所身不由己地被动选择的涂改液,则并非内服而系外敷:他不再以三十多岁的成人年龄立身行事,而是摇身一变,重为十几岁的蒙昧学子,浑浑噩噩却也不屈不挠地,抗争在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惯性之中。当然了,我想说的,并不是所谓“涂改液”的“内服”与“外敷”怎样才有效——我也没资格判断这个——我通过简约地比较我与尤瑟夫迥然不同的“涂改”方式,只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循此线索,对贡布罗维奇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那种离奇荒诞的基本故事气息,对“费尔迪杜凯”这一生造单词所携带的发明者自况的“反传统、反媚俗”的大致价值含义,多少有个轮廓性把握,这样,才比较容易理解我前边提到《菲利贝尔特》时,为什么使用了“长篇插曲”这一说法:在二十二万汉字译文的《费尔迪杜凯》里,有两组四段毫无来由的节外生枝,游离在小说正常的叙述路径之外,而其中的一段,便是《菲利贝尔特》这个不足两千五百汉字的独立篇章。
什么,“小说正常的叙述路径”?这几个字我一说出口,心就虚了,对于行文信马由缰情节荒诞不经的《费尔迪杜凯》来说,又有什么算“正常”呢?若以是否“正常”去衡量它,那出发点先就不正常了。《费尔迪杜凯》昭告世人的核心意思,就是审美的尺度不必刻板,评判的标准允许颠覆,如此,将特立独行的《菲利贝尔特》从本身即没有规矩不守纪律的《费尔迪杜凯》里抽离出来,把它视为与宿主无关的自主生成的寄生者,才更水到渠成并合情合理。记得当年,我匆匆溜过《费尔迪杜凯》,很快就忘了它都说些什么,可它增生出来的四节“插曲”,即彼此遥相呼应的两段“前言”以及《孩子气十足的菲利陀尔》和《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这两段独立的故事,却轻松占据了我的记忆,而且好多年里,还会间或地,让我一想起它们就忍俊不禁。例如这篇画面感很强的《菲利贝尔特》,每次重温,都让我身不由己地就能身临其境于某个晴朗的下午,来到巴黎拉辛俱乐部网球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面对种种似乎没有头绪又意旨隐约的荒唐事件,先惊愕甚至厌烦地溜边观看,然后便“借助别人的酵母膨胀”起来,放肆地参与到那些孩子气或者非孩子气的不乏恶毒恶意的恶作剧中:开枪射击网球、随意扇人嘴巴、作为绅士骑上女人的脖颈、作为淑女驮着男人满场飞奔、为显示血统高贵而把妻子贡献出来任人侮辱、因受到惊吓而在众人脚下早产出哭啼的婴儿……并因为这一切,接受赛场上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的鼓励或嘲弄。
“紧张热烈”的网球赛场何以会失控,乃至于要上演一出把众多观众裹挟进去的荒唐闹剧?而“高贵血统”的菲利贝尔特侯爵又何以会鬼迷心窍,像个没有深浅不识好赖的小屁孩那样,生生把一个“坚定果敢”的自己贬损成一个可笑的丑角?对此贡布罗维奇没有解释,一如卡夫卡不解释格里高尔为什么变成甲虫(《变形记》),霍桑不解释韦克菲尔德为什么离家出走(《韦克菲尔德》),博尔赫斯不解释“我”与“博尔赫斯”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人,而“以上的话”,又究竟出自他俩谁的手笔(《博尔赫斯和我》)……但他们有权“反对阐释”(桑塔格语),我行事的信条,却不应该是“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语),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各司着不同的职责:他们只管创作就行,我的活计则是解释分析——不过,我与他们又终归是同类,所以做解析时,我也依循小说笔法就不能算犯规,况且以前谈芥川时,我这么干过,自以为效果还挺不错。那现在,我就再如法炮制一回。只是,当初为解析“芥川现象”,在我讲述的两则半小故事里,也有我的个人经验掺杂其间,而下面我欲一笔带过的种种信息,除了没什么故事元素,还一丝一毫都与我无涉,它们只是提纲挈领地,撮要一下几位经历特殊的波兰人的特殊经历:著名的肖邦与著名的乔治·桑,共同生活了将近八年,前者的许多重要作品,都创作于那八年中,就此谁都否认不了,是与乔治的恋爱生活,滋养了肖邦的灵感与激情,可有些人,尤其是有些或轻或重的“直男癌”患者,却总拿桑妇人长肖邦六岁且感情经历更为花哨大做文章,甚至荒谬地把两性的欢愉与思乡爱国对立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暗示,是无情无义的法国女文豪的精神折磨,导致了爱祖国爱艺术的波兰病天才的英年早夭;而另一位波兰病天才舒尔茨,即使对恋人精神的或肉体的折磨都持欢迎态度,其爱情生活,也短暂得令人唏嘘,当然他的最大不幸是身为犹太人,只因夜间上街行走,就成了纳粹枪下的冤魂,但这位在绘画上也天赋极高的中学教员,不幸之中也有侥幸,那就是,他喃喃自语出来的那路怪诞小说,从秘不示人的早期到他辞世十年后的广受赞誉,几十年里,总有数量虽少但对他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绝对忠诚的专业人士,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吹,使他仅凭有限的短制,便获得了有资格靠拢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至高荣耀;还有贡布罗维奇和米沃什这对年龄相差了七岁的朋友,不仅都对母语有过批评,面对他国的入侵或本国的暴政,还自1939年和1950年起,就分别选择了漂泊异乡的流亡生活,于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乃至故去以后,即使后者还为波兰语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波兰社会重拾理性后,于耄耋之年又回到了祖国,可还是受到了许多谩骂与诋毁,其实,恰恰是他们,在浪迹天涯时,也没卸除自己的责任,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结合自身的际遇,通过对个体价值与族群想象、国家意志与私人感受、人性欲望与利益驱动等关系的清理省思,在深化个人经验的同时,也充实了波兰经验和丰富了人类经验,使千千万万肤色不一地域不同的人,因为他们,而明敏了眼睛宽阔了心灵。
是的,波兰经验乃至人类经验。乍一看去,以上四位所呈示的,关乎的只是一己的偶然经历,没有因果关系,少见共同特征,无非是一种互不搭界难以复制的芜杂零乱。但正是这种芜杂零乱所传递的“种种信息”,一旦经过语言文字的淘洗淬炼,才更容易超越个别性获得普遍性,才更可以确保“不乏恶毒恶意的恶作剧”《菲利贝尔特》在展演它的破坏秩序嘲弄高雅亵渎神圣时,不至于成为突兀的独角戏自说自话,而可以找到一道恰到好处的精神的背景以为依傍。endprint
所谓经验,并不是一只没有边际的巨大容器,对个体的经历、国族的经历、人类的经历,巨细靡遗地一勺烩一锅煮;经验是在存在的意义上,对经历的反刍倒嚼与提纯抽象,它对形而下事物的形而上认知,能够穿透现象抵达本质。人是经验的动物,保佑着人类大步疾走或跬步缓行时别彻底投进死神怀抱的,唯有直接建立与间接引入的两种经验,而尤其需要以理性能力参与汲取的间接经验,又是更为重要的安全带与保护绳。小说有幸,自诞生起,就成了最不伦不类又最有趣有效的间接经验的汲取工具,或者说,是人类走到了某个拐点,特别需要一种既不伦不类又有趣有效的间接经验的汲取工具,于是,亦庄亦谐又非庄非谐的小说便应运而生了。它的步子迈到今天,尤其是当它从模仿、复制、还原等趋真化表达的禁地有意或无意地回归了象征、变形、超验等寓言式表达的老家之后,它对自己使命的胜任程度也越来越高:聚焦存在现象,探究存在问题。我在我们这一系列讲座的开讲伊始,就表示过,那种欧·亨利式的,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叙事,将不被我重点关注,我更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是小说这个精灵在塑造自身演示自我时,所呈现出来的尽可能多的艺术可能性,通过对这些可能性的理解和接受,来扩大我们感知事物的边界,增多我们发现真相的视角。
具体到《菲利贝尔特》,其实,也可以具体到其他许多内容“怪异”形式“反常”体验难度过大的作品那里,比如《变形记》或《韦克菲尔德》或《博尔赫斯和我》,或许,我们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去理解它们接受它们,相信它们的标新立异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传递更多样的信息,寄托更复杂的意趣,表达更新鲜的观念,实现更深刻的真实。但通常的情形却令人尴尬,我们往往只是被它们文本本身的“怪异”“反常”所迷惑吸引,而对它们传递的信息寄托的意趣以及表达的观念实现的真实,依然还是不明所以。不过,我倒愿意认为,这种尴尬别有妙味,它所证明的,或许正是精神现象之奥妙无穷,艺术行为之耐人寻味,而我们感觉和想象的裂变式解放,也唯有在这些不明所以的困惑疑虑中才能完成。就我个人来说,由于我一向把我反复申说过的“阅读三忌”,即反对提炼中心思想、反对找寻教育意义、反对对号真人真事作为约法三章,我阅读时的“不明所以”,反倒能让我在失去导向的同时也打破禁锢摆脱束缚,确保我的体验能自由无羁。在我眼里,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为写而写,是无目的倾诉,一如有的时候,人的喊叫只为喊叫本身。有的时候,人会生出喊叫的欲望,忍不住想要来一嗓子,可具体原因,又完全可以,与有了快感或受了冤屈或被什么東西刺激到了没有关系。我意思是,作为那喊叫声的倾听者,我只琢磨它高亢或沉郁、浑厚或单薄、有共鸣或没底气、悠扬若长调或短促如哨音……也就行了,而不必让所谓的快感或冤屈或其他什么东西分我的心;倘若那快感或冤屈或其他什么东西也打动了我,那只能算是我的偏得,为了那幸运我得感恩。
莫拉维亚的《梦游症患者》
好多年前,我还年轻,其标志是,一见到能吸引我的女人就会脸红,而一脸红就语无伦次,可问题是,能吸引我的女人到处都有。我不知道,我很早就甘于枯坐一隅,把自己的生活限定为青灯黄卷地读写小说,这是否算理由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十六七岁的我,除了茫然困惑地贬抑自我便再不知道如何是好时,一份未刊的书稿,不仅让我接触到了弗洛伊德,掌握了“精神分析”这个时髦的词汇,还磕磕绊绊地记住了“伊德”“自我”“超我”,以及“力比多”“潜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尤其让我脑洞大开的,是后来,我上大学后,读到了他那本也译作《释梦》的《梦的解析》——岔开一句,为了向弗洛伊德在诸多方面对我的启蒙表示感谢,1997年,我曾以《梦的解析》为题,创作过一个短篇小说,里边一些超现实的情节,现在回味也煞是有趣。另外,直到今天,虽然他的某些理论,越了解越让我不敢信任,可这并不影响对他以及他的志业,我的崇敬始终不渝。
还是好多年前,与年轻比,我已稍稍老了一些,但那时节,报纸仍然有人阅读,方兴未艾的晚报晨报都市报上,除了连篇累牍明星八卦长寿偏方以及外表强悍的时政说辞与内里酥软的心灵鸡汤,也还允许相对地守着几分节操的读书版自得其乐。某一天,在一家报纸的读书版上,我应邀模仿娱乐版上的俊男靓女,回答了编辑的一应问题,约二十个。那是一些诸如哪种血型什么星座处女作何时发表受哪个作家影响最大之类的程式化问题,三分之二系胡诌八扯,但也有三分之一能提醒我,回望一下已然的来路,再展望一下或然的去路。当然了,即使对那需要我收敛戏谑堂皇仪容的三分之一,我的答案,也多半一填上去就给忘了,唯有“业余爱好”一项,我当时的回答,至今想来,也是准确贴切的不二之选:做白日梦。是的,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或者,在“当时”之前我还很小的时候,估计也会是“现在”之后,直到将来我进了棺材,“做白日梦”,都是我最喜欢的、最擅长的,也是从中能得到最多快乐的一件事情。
显然,通过以上回顾,通过那些被弗洛伊德解析过的和我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来的“梦”,我想说的是,在我喜爱文学的早期时段,在我对现代主义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都还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时,我就借助直觉,借助某种不可知力量的刺激和点拨,把梦,看成了一种覆盖在普通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之上的东西,尔后,随着中国百姓从文学阅读的禁忌之中挣脱出来,随着我个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激进理念与生猛探索愈益痴迷,梦作为最经得起解析阐释的象征之物与隐喻之符,很快就被我夯砸成了思想的基石,打造成了美学趣味与艺术追求的形象化代表……呵呵,缅怀一番自己的“梦史”,还真挺让人感慨系之。不过,本次讲座,我选择莫拉维亚和他的《梦游症患者》作为话题,倒并非为了纪念我与梦的千丝万缕,而是相反,我对自己“梦史”的回首,更为有的放矢地呼应《梦游症患者》。这么说吧,若我只想以梦说事,不用远望,只近瞧一下也操意大利语的卡尔维诺,就不难发现,梦也是他笔下的关键意象,而且他在拿捏和摆布梦时,思路和手段还更胜一筹,比如,从我手边他的小说集里,我随便翻到的这篇《弄错了的车站》,渲染的就绝对是一个梦境,只不过,文中并未挑明罢了。其实,与博尔赫斯一样,卡尔维诺的全部小说,整个是一场大梦,当我作为一个喜欢梦游的“寒冬夜行人”徜徉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踟蹰在“命运交叉的城堡”中、徘徊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上时……我每每都会——哦,我就不虚头巴脑地绕圈子了,毋庸讳言,比之于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小说所寄寓的理念运用的技巧,以及营造的气息气氛,都更具有现代意蕴,都更长于巧妙执拗地,把文学阅读引向智力的游戏与审美的狂欢,使那些对所谓“好看故事”或者不以为然或者别有心得的另类读者,不光能吸纳到《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节制和《寒冬夜行人》的睿智,也可以榨取出《看不见的城市》的繁缛和《命运交叉的城堡》的诡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