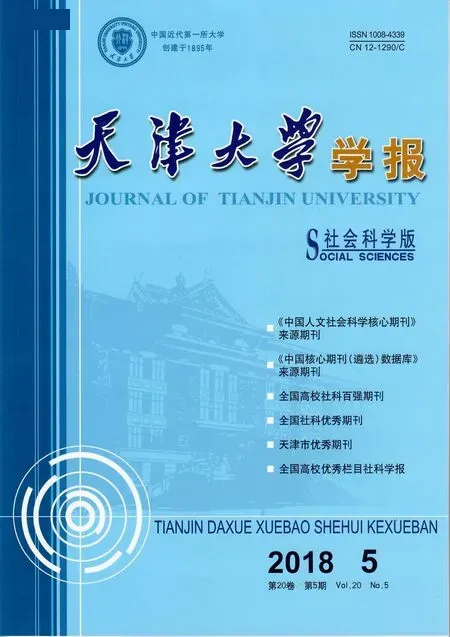张伯苓、张彭春教育理念探析
2018-01-24闫涛,侯杰
闫 涛, 侯 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张伯苓、张彭春是近代天津教育先贤,在南开学校创建及发展的教育实践中,他们努力培养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青年学生,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了完整呈现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本文试图考究张伯苓、张彭春兄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活动在南开学校创建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教育先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从而揭示南开学校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爱国教育的历史,“南开精神”正是中国人爱国精神的凝缩体现。爱国是张伯苓的人生主线,他提倡爱国就要立“为公之志”,爱国就要有“救国之力”,爱国就要强健体魄,爱国就要“知中国,服务中国”,爱国就要团结抗敌,爱国就要刚毅坚卓[1]。
一、 推崇德智体群,培养全面人才
张伯苓为了培育救国济世的人才,消除愚、弱、贫、散、私的弊病,他十分推崇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教育理念,并将其融入南开学校的建设之中,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实现身心均衡发展。
张伯苓在多次发表演讲中同时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1906年11月22日)晚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以学生义务为题,现身说法,谆谆告诫,洵推阅历之谈其果效可卜之于将来也” 。这是《天津青年会报》第5卷第33册中提到的。在《天津青年会报》第7卷第10册中有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在租界会所特别茶会上,“张君伯苓、本社副董仲子凤相继演说,尽欢而散。”在《天津青年会报》第8卷第5册中有记载,在宣统元年二月(1909年3月)《预布下两月星期四智育演说秩序》中,就有“闰二月初四日,私立第一中学堂监督张君伯苓演说”的字样。作为从甲午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张伯苓一直把“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2]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创办南开学校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教育救国之理念,张氏兄弟确立并提出了以下教育方针: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理念,确立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他曾强调:“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3]。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坚强的体魄,健全的精神。作为一所刚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南开的经费常常入不敷出,但在体育教学和设施建设方面,张伯苓总是慷慨解囊,毫不吝惜。南开学校不仅修建了大操场,还修建了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棒球场、冰球场和网球场。张伯苓深知体育教师素质的高低对学校体育教学的质量和竞技运动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为聘请专业体育教师来南开任教而不惜重金。这些体育教师大都毕业于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有的还在国外大学体育专业进修或者留学过。如南开学校有章辑五、董守义、张淑悌等一批优秀体育教员。张彭春更是将体育的作用上升到振奋精神、激励爱国心的高度。他鼓舞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在竞争之时,譬如赛跑,彼一刹那间心专目注,竭全身之力,以冀必得者,为一目的物。是时可谓万念全无,专谋是举。危险祸患,在所不惧。常能操练此种身心,则将来置身社会,敢决必胜”[4]。“运动员比赛时决非个人之荣,实因代表其团体以征赛数,而竭力前争勇气不竭……是心发达之,即可成坚固之爱国心,来日成爱国之事业”[4]357。1927年10月,在南开中学会议厅召开天津体育协进会成立会,张伯苓等5人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并通过了《天津体育协进会章程》,这一事件在1927年10月21日《大公报》有记载。
张伯苓认为,教育是改造个人的工具,但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而应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他常向学生们阐述行已处世之方、求学爱国之道。为此,张氏兄弟特别重视戏剧在道德熏陶方面的作用。张伯苓认为新剧表演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演说和表达能力,能够培养和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必须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随着这一理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张伯苓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戏院不只是娱乐场,更是教堂、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沟通学校生活与现实社会。这正好契合了他长期以来改良社会的理想,而在学校和社会上推广新剧表演,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之一。1909年10月17日是南开学校五周年的庆祝日,在严范孙家的东院,张伯苓亲自主编、导演的新剧《用非所学》正式公演,这部剧成为南开新剧的起点,也是华北范围内新剧的开端。
1914年,为了更好地推动南开新剧的发展,张伯苓组织师生成立了南开新剧团,成为南开学校新剧表演正规化和组织化的开端,这也标志着南开的新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张彭春深厚的西方戏剧理论功底和创作经验得到了张伯苓的赏识,于是张彭春开始推动着南开新剧不断走向辉煌,这在中国现代新剧发展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彭春首先导演了自己在美国创作的写实独幕剧《醒》。《醒》剧演出之后,立即受到了南开师生的一致好评。首演之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在1917年1月校刊《校风》上撰文,称赞该剧“颇多引人入胜之处,佳音佳景,两极妙矣”。1918年10月,张彭春执导了新剧《新村正》。该剧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从编写剧本、选派角色,到排演、邀请校外名家前来指导,无不凝聚着张彭春的大量心血和汗水。该剧一经公演,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曾两度将《新村正》搬上舞台公演。《新村正》标志着南开新剧团从此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南开新剧团的灵魂人物,张彭春从1916年到1936年执导南开新剧团,其间陆续导演过几十个颇有影响的剧目。在这些剧目中,既有他自己编导的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也有翻译和改编自外国名家所创作的经典话剧。张彭春或完全按照原著进行演出,或将原著情节和人物中国化之后再加以表演,将果戈理、王尔德、易卜生、莫里哀等世界著名剧作家及其作品引入中国,为南开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话剧艺术舞台的大门。
张氏兄弟在具体办教育的过程中,还特别重视团体建设和团体活动的开展以及学生爱国意识的培养。张伯苓针对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之弱点,切实倡导并鼓励学生自动建立各种课外组织,开展各种团体活动,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练习做事、参加活动的机会,提高社会活动能力。他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讲解国际形势、世界大事,使学生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救国之力。归纳起来,就是讲求“公能”,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的公德以及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 创办新式学校,培育爱国人才
透过张伯苓、张彭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人生轨迹,深入考究其言行,他们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做出的努力与奋斗,成为其一生的华美篇章。1916年8月初,张彭春怀着“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留美归来,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1916年8月21日,张彭春在南开学校新学年开学典礼上首次公开发表创办南开大学的意见。8月22日,张彭春又邀集了南开学校专门部的师生进行座谈,讨论改办大学的问题。他认为“欲挽社会,非有一般知识高超,道德纯厚之新少年,其眼光、其魄力,均不足以促进其事业。徒志不足有为,识高方见经济”[2]13-15。张彭春的这一提议在南开学校的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反响。也引起了严范孙和张伯苓的高度重视,接受了创办南开大学的建议,并安排由张彭春草拟改组大学的设想和计划。1919年2月4日,成立了南开大学筹备课,张彭春为筹备课主任,主持南开大学的筹备事宜。张伯苓后来称张彭春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此外,在清华学校大学部的筹办过程中,张彭春被聘为清华教务长。张彭春不负众望,对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做出很多实际贡献,极大地推进了清华学校改革的顺利进行。
张伯苓大胆学习、吸收、借鉴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洋货”教育,并亲自前往国外考察。他尝言:“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4]311。张伯苓创办中学有了一定成绩之后,希望自己的学生毕业后能继续读书,便通过私募捐资的形式兴办私立大学。在张伯苓筹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曾到美国进修并多次赴美国各地开展募款活动。《天津青年会报》对张伯苓出访欧美、考察教育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在中美民间文化教育交流过程中,张伯苓扮演了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他一方面为中国的教育发展争取广泛的经济资助和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也向美国各界人士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1909年7月4日,《会员赴东》有则消息记述了张伯苓出访的一些情况:“张君伯苓于前月二十三日,偕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长李君芹香,乘官升轮船,赴申。二十九日,本社接到上海青年会干事骡君来电云:张李二君,已追及天佑丸,开往东京矣。”1908年11月20日,该报相继报道:“本报兹闻张君至华盛顿纽约城,该处官绅商学各界,无不欢迎接待,现闻先生已赴英国游历矣。”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始业式上的演说题目是“培养领袖人才救吾华民族——南开大学成立之动机”,提到“南开大学系由中学部所产生”,3年的发展使学生人数由数十人到三百数十人,得八里台学校用地数百亩来建设新的校舍,得美煤油大王捐款建设科学馆解决经费不足,得知名教授支撑等都是南开大学的幸事[5]。对当时办学之艰辛,张伯苓总结说:“此次大学成立之动机,系第三次之试验,此后将打破艰难,永无止息。至成立之历史,则一由外界之帮助,二由内部之增长——校舍扩充,学生增加,教授得人。而教育之目的无他,在求此解决吾华困难问题之方而已。此问题吾知非一时所能解决者,然百尺高楼从地起,事无大小,全在精神。《圣经》有言:‘对小事忠心者,对大事亦必忠心’。故吾敢语诸生,凡事不在成功,不在失败,只视其如何竞争。今吾辈既生此时艰,万勿轻视自身,须记汝‘责任大’,‘机会好’,志向一定,前途正远。人谓南开今日虽小,后望方长。”[5]14-15由此不难看到张伯苓的自信与创办大学教育救国的笃信。南开大学正如张氏兄弟所设想的一样,成立时约有100名学生,到第一届毕业生只有21人毕业,到1937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才60余人,学生总数才有420余人[5]157。虽然办学规模不大,然而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付出了很多心血。张伯苓赴美学习教育制度、机构设置、学生培养等情况的同时,还与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凯尔鲍德里等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广泛接触了正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了解他们对美国大学的印象以及各自在美国大学求学的经历和体验,以为将来在中国创办高等院校提供某种借鉴。1948年,司徒雷登曾为美国为纪念张伯苓七十岁诞辰出版的ThereIsAnotherChina一书撰写导言《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肯定了张伯苓创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劳与业绩[5]125。
三、 适合中国国情,重视现实需求
“张伯苓从早期仿效日本式教育到南开大学成立后,又推行美国化教育,他这样大刀阔斧、范围广泛地引进西方教育,在当时中国各学校中是比较突出的。”[6]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化的“洋货”教育使南开大学的教育模式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脱离。从南开中学直接免试升入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我跟张伯苓先生说过,我从中学三年级起,耳朵里就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还有一个中国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的教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术语,要我说成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你们看,把一个青年搞成这个样,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呢?”[7]经过反思调整,南开大学对人才培养越来越注重国家的现实需求。1925年11月25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商学会成立会上发表演讲“熏陶人格是根本”,提到:“南开大学教育目的,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做事本就是应用学理,将平日所得来的公律、原则、经验应用出来到实事上去。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5]20
随着不断加深对中国教育当何去何从的理解,张伯苓适时做出转变,制订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该方案对以往的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反对偏重“洋货”的教育倾向,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大学日后发展的根本方针。方案得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的结论。并将“土货化”阐释为“知中国”、“服务中国”。最后,该方案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等具体要求,即“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问题为主”、“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此问题必须适宜南开之地位”[8]。1929年,张伯苓再次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并在回国后的一次欢迎会上明确指出:“此次考察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的考察以前是注意学校的组织、外形,现在的考察不应如此了,因为我看过的学校不知有多少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4]190对于完全效法西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法,张伯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此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已更加成熟,反对“全盘西化”的倾向,不与复古主义为伍。可见,他当时是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南开教育发展道路。
四、 培养爱国情怀,复兴民族大业
众所周知,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是为公育才,育为公之才;“能”是培养能动做事成事之能力,针对旧时中国“愚弱贫散私”之弊,提出体育、科学、团体、道德和爱国的理念;“日新月异”要求每位南开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前列,这是南开精神”。这是1942年张伯苓与重庆南开中学同学谈话时所解释的南开校训,校训饱含着代代南开人刚毅坚卓的爱国情怀。
1935年4月28日,在《南开校友》第6期刊出张伯苓一篇文章,“对于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文中提到:“我个人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南开学校永远是随着时代进展的,以后对于学生之如何训练,课程之如何切实,当然更要与时俱进。可是我们南开的校友,也不能为时代之落伍者。诸位校友或在中学毕业,或在大学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固然都能努力求学,但出了学校置身社会,因职业与环境的关系,恐怕对于求学的志趣没有像在学校那样浓厚,所以想引起校友的读书兴趣,比在校的学生困难。好像我们南开的校友都有一种所谓南开精神,并且诸位在社会上,也全有相当地位,只要不甘安逸,做起来也很容易。”对于南开校友,张伯苓提出4点要求:其一求怎样做人的知识;其二要有团体组织;其三要有求知识的方式;其四努力于有益国家的事业。张伯苓校长对毕业生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即使毕业了也要不断修为做人和做事的本领。
抗战期间,南开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年逾花甲的张伯苓仍不辞辛劳为南开事业操劳。1939年10月9日,在教师节重庆南开中学教职员聚餐会上,张伯苓发表讲话,提醒老师们要“专心致志于教育工作,不仅有乐趣,也不至于冻馁”。重申自己的对“公”理解,提醒老师们要“教学相长”。在发言中,张伯苓还强调“南开以前一贯的是提倡救国教育,抗战以后又提倡建国的教育。英国有牛津、剑桥等校造就人才帮助国家,我们盼望南开大学也能造就人才帮助国家”[5]42-45。可见,张伯苓校长将学校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坚定表达复校的决心。他认为南开大学当时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大学,最大的优点是有优良的中学基础,认为这种以中学帮助大学发展的办法,实在是最好的方法。当时张伯苓校长已63岁,但他说:“我觉得前途真是无限光明的。我的年纪恐怕不会允许我再做什么,但是我决不停止!”1944年10月17日南开40年校庆日,时年68岁的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提到:“兹当南开十周年校庆佳日,吾人回顾以往之奋斗陈述,展望未来之复校工作,既感社会之厚我,倍觉职责之重大。”1945年1月20日,张伯苓发表了“从世界大势说到南开前途”的演说,并提到战后南开的复校计划,“重庆南开继续发展,天津南开首先恢复”,张伯苓提到将南开大学仍设在天津旧址,重在专门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五、 重视现代教育,推崇实践救国
作为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补充和完善,张彭春所阐述的很多重要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对南开学校的教学工作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留学期间,张彭春师从杜威,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杜威就在中国大力宣传“学校即社会,社会即生活”的理念。张彭春的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927年6月21日~7月2日,南开中学召开的暑期“学校改革讨论会”上明确指出:“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现代化。”其时,“教育救国”之说刚刚浮出水面,世人颇多微词。而张彭春则力排众议,大胆提出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见1927年9月6日《南开周刊·临时增刊》第1号)。他的这种教育观,即教育是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支点,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张彭春不仅见解深刻,而且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直接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张彭春除了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立、发展中起到开拓性的作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非凡外,也曾专心致力于中等教育的研究和管理实践。自离开清华重返南开之后,张彭春作为助手协助张伯苓管理学校各项工作,并能独当一面。这一时期,张彭春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特别注重与中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相贯通。张彭春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中国中等教育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或是只知培养一味“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或是脱离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教学模式。他提出,应当让学生摒弃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通过实地观察、动手实验等方式来获取和掌握知识,以达到现代教育培养具有全面能力的现代人才的目的。张彭春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开辟的经验”的概念。所谓“开辟的经验”包括3部分:其一,为个人能力的锻炼;其二,为团体生活能力的锻炼;其三,为生产技能的锻炼[4]388-389。
张彭春所阐述的很多重要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也正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补充和完善,对于以中学为主的南开各学部教学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南开很早就将社会调查课程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对于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27年初,在他的组织下,“社会观察”课列为正式课程。1937年,他还先后发表了《广播在教育上的应用》和《怎样看电影》等讲演或文章,都是他的“使中国现代化”思想在教育上的具体反映,也是较早提倡用现代电化手段进行语文(包括戏剧)、历史和音乐(含用短剧)教学主张的体现。正如张彭春所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个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重庆南开《公能报》,1946年11月)。
张伯苓、张彭春不平凡的生命历程是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曲折之路的凝缩体现。他们作为受近代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教育的先贤,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开学校在张氏兄弟的努力下创建、发展、壮大起来,其教育理念与历史功绩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