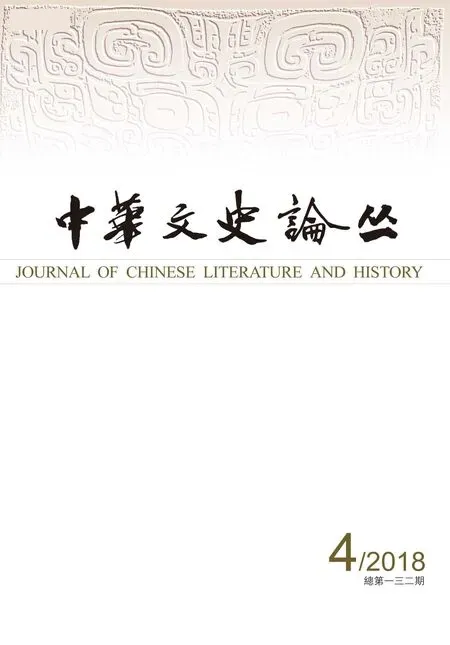對《儒林外史》原貌問題的重新檢討
——對蕭雲仙、湯鎮臺、郭孝子故事出自吴敬梓之手的進一步論證
2018-01-23李鵬飛
李鵬飛
提要: 從《儒林外史》全書主題思想、藝術風格、具體藝術技巧以及藝術思維方式的整體性、連貫性來看,《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同出吴敬梓之手。從對新發現的《儒林外史題辭》的進一步解讀及《儒林外史》跟吴敬梓其他詩文的密切聯繫等旁證來看,《儒林外史》五十六回也應是一個整體,且同出吴敬梓之手。也就是説,被前輩學者懷疑的蕭雲仙、湯鎮臺、郭孝子故事都應出自吴敬梓之手,並非他人竄入。
關鍵詞:《儒林外史》 吴敬梓 主題思想 藝術風格 藝術技巧 思維方式
筆者已經另文論證清人程晉芳所云《儒林外史》爲五十回之説之不可信以及後代學者試圖證明五十回説的論證之難以成立。[注]筆者《〈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爲吴敬梓所作新證》,載《中國文化研究》(轉下頁)對於《儒林外史》原貌問題的研究,外部證據固然重要,但在外部證據缺乏或者不可靠時,小説文本本身便成爲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但前輩學者試圖從文本内部尋找證據來證明五十回説的論證疑點重重,令人難以信服。相反地,筆者認爲: 從文本内部我們可以找到更多、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全書五十六回乃是渾然一體的,而且均出自吴敬梓一人之手。這裏將主要從受到廣泛質疑的郭孝子、蕭雲仙、湯鎮臺等人的故事入手來嘗試作進一步的證明。[注](接上頁)2017年春之卷;以及《論〈儒林外史〉原稿爲五十回説之不能成立》,載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古典學》2018年第1辑。
一
首先,從全書主題的角度來看,郭孝子、蕭雲仙、湯鎮臺等人的故事表達了這部小説豐富複雜主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那就是對禮、樂、兵、農等儒家傳統學問的極大的重視,對能夠研究、踐行這些學問的優秀士人的推崇與頌揚,也表達了作者對這些學問與這些士人所遭遇的現實困境的深深的惋惜和同情。
《儒林外史》的主題絶不是像有些學者所理解的那樣單一——它不只是對科舉制度的反思與批判,不只是對士人人生道路抉擇的觀察與思考,也不只是對世態人情與人性弱點的諷刺與批判,更不只是如同“閑齋老人”序中所説的那樣,表現了人們對富貴功名的不同態度——總之,從任何單一的角度來理解這部小説的主題都將導致我們對小説後半部分郭孝子、蕭雲仙、湯鎮臺等人故事的意義難以準確把握。談鳳梁先生曾指出《儒林外史》的創作意圖存在着階段性的變化,其原因在於作者經歷與思想的變化導致其藝術構思從諷世轉爲匡世,由揭露變成言志,從“文行出處”轉到“禮樂兵農”,由抨擊科舉到進一步抨擊時政。原先他崇拜不從政、不做官的隱士王冕,後來則欽慕應試做官、以德化人、贊助禮樂兵農的賢人君子,從嘲諷醉心功名的儒生轉向給他們更多的憐憫和寬容。[注]談鳳梁《〈儒林外史〉創作時間、過程新探》,《江海學刊》1984年第1期。筆者十分認同這一説法,而且應該説,小説整體上的綴段式結構也爲這種隨着時間而來的構思調整提供了可能,泰伯祠大祭、郭孝子萬里尋親、蕭雲仙與湯鎮臺的文治武功,甚至王玉輝整理“三禮”、王玉輝女兒殉夫這些故事段落的出現應該都是伴隨着這一構思調整而出現的重要内容,而這些内容都跟小説後半部分的核心主題——禮樂兵農——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但提倡“禮樂兵農”這一思想可能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於作者的構思之中的,而是從第三十三回杜少卿搬到南京、遇上遲衡山之後才在小説情節之中逐步出現的:
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着吃飯。遲衡山閒話説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曾製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
此後便緊接着敍述了遲衡山首倡的盛大儀典——泰伯祠大祭,目的正是爲了“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泰伯祠大祭籌備與舉行的整個過程在此很顯然代表着儒家“禮樂”的學問及其實踐。大祭之後,郭孝子登場,萬里尋父,引出蕭雲仙,再引出湯鎮臺——蕭、湯二人代表着儒家“兵農”的學問及其實踐。此後,小説敍及跟余氏兄弟相關的葬禮與宗族之禮、跟王玉輝相關的禮學研究及其實踐,也都是圍繞着“禮”這一議題來安排情節的。從第三十三回開始,作者也反復提到“禮樂兵農”主題,比如第四十四回遲衡山跟余氏兄弟議論葬禮時説道:
更可笑這些俗人,説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
到第四十七回開篇又提到:
話説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到了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道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
可見,對“禮樂兵農”這番學問,作者真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顯然絶非隨意的泛泛之談。商偉先生曾指出吴敬梓在小説後半部着力提倡“禮樂兵農”學問的思想是受到他的好友程廷祚影響,而程廷祚則又是顔(元)李(塨)學派思想的信徒,他曾在給李塨的一封信中概括顔李學説的核心爲“二先生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得漫然虚大者也”。[注]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 儒林外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頁68—75。商偉在此也指出了吴敬梓對禮樂問題的重視還可能受到了他在南京的一些研究禮學並參與禮儀實踐的朋友(如樊明徵、程廷祚)的影響。同時,吴敬梓自己也參加過一些禮儀的實踐,比如參與某人葬禮的設計、參加雨花臺下的倉頡祭禮等。參見該書頁73、74。程廷祚的“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這一表述幾乎可以成爲《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到四十八回的主旨大綱。關於小説對“禮樂兵農”這一番學問的提倡上文已約略述及,這裏且來看一看小説對“孝弟忠信”主題的表達。
泰伯祠大祭所祭祀的泰伯,其事迹彪炳史册,傳諸衆口,這裏無須詳述,總之,他既是孝的楷模,也是悌的典範,更是謙讓美德的象徵(所謂“三以天下讓”的“至德”,讓掉的乃是人世間最大的一場富貴)。郭孝子則是對孝道的絶對的身體力行者,他大半生歷盡勞苦,萬里尋父,甚至爲此荒廢了自己的人生,卻受到衆人的一致推崇。蕭雲仙則既忠且孝,事功、孝道兩不誤,在忠孝之間難能可貴地做到了兩全。余氏兄弟則是既孝且悌的;湯鎮臺、湯知縣兩位也是篤於兄弟情誼的;王玉輝雖然迂腐,不近人情,但也是忠厚誠篤之人。
很顯然,這些人一個個都是儒家傳統美德的“躬行力學”者,而不是如高翰林所説的只將這些名目當作“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第三十四回)的徒托空言的人。
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在除泰伯之外的這些人物中,蕭雲仙乃是一位兼具多種美德的理想型人物,他在青楓城的所作所爲(小説寫了他勸農桑、祭先農、興學堂、與民同樂諸般善政)既是對泰伯祠大祭的遙相呼應,也是對公然視“敦孝弟,勸農桑”爲“呆話”的高翰林之流的强烈諷刺,而他作爲被屈抑人才的代表,更是與第五十六回的主旨遙相呼應——作者將這一人物深深地嵌入了小説的整體敍事肌理之中,成爲“禮樂兵農”理想的重要踐行者,並同時藴含着他對壓抑人才的社會制度的深刻批判,很顯然,這些主題的表達乃是出於作者深思熟慮的精心安排,絶不是其他人所能輕易增入的。在蕭雲仙之後出場的湯鎮臺這一人物,在小説中的主題意義也跟蕭雲仙頗爲相似,他的故事自然也不應該是被人竄入的,對於這一點,這裏就不再詳細討論了。從小説主題的角度看,郭孝子等人的故事,與全書主題聯繫緊密,似非竄入之文。
二
從吴敬梓的慣用結構手段與小説後半部分的結構特徵看,郭、蕭、湯等人的故事也不可能是被人竄入的,因爲這些部分體現出了典型的吴敬梓式的結構風格,而這一典型風格是不大可能如有的學者所認爲的那樣,是爲了掩蓋竄入痕迹而刻意爲之的。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郭孝子故事在小説中是如何安排的——在泰伯祠大祭後,郭孝子才出場,他二十年走遍天下,尋找父親,如今要往四川尋父。虞博士寫信介紹他去拜見陝西同官知縣尤扶徠,尤扶徠卻正好有公事要外出三日(這種刻意爲之的敍事延宕正是吴敬梓的慣技,小説中用過很多次,越是這種細微處越能看出作者的手筆來),便安排郭孝子住到海月禪林,他在這兒認識了第二十、二十一回出現過的慈悲老和尚甘露僧——第二十一回提到他應友人之邀離開蕪湖甘露庵去了京城的報國寺,到第三十八回他又離開京城的報國寺來到了陝西同官縣的海月禪林——老和尚被郭孝子的一番孝行深深感動。等到尤公回來,資助郭孝子上路,又讓他到了成都去找自己的朋友蕭昊軒。老和尚叮囑郭孝子找到父親後寫信告訴他。此後小説即細述郭孝子入川途中之所歷,尤其是他遭遇木耐打劫,勸木耐改過,資助他,教授他武藝等事。此後郭孝子找到父親,寫信告知老和尚。這時,第三十四回蕭昊軒遇到過的山東賊頭趙大也流竄到同官的海月禪林,因被老和尚驅逐而跟他結仇。此後老和尚欲往峨眉,順便去看望郭孝子,入川途中卻落入趙大之手。於是蕭雲仙出場搭救,事後遇到郭孝子,得他指點,打算去從軍。郭孝子和老和尚從此退出小説舞臺,未再出過場。
細細看來,以上這一大段内容的敍事安排着實是頗費匠心的: 從整部小説的空間佈局來看,郭孝子出場之前,大部分故事場景主要集中在從山東到廣東的沿海地帶,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江浙皖地區,隨着郭孝子入川尋父歷程的展開,小説的地理空間背景也向中國的西部地區擴展,小説空間頓時變得非常廣遠闊大——這一地域上從江南向川蜀的延伸擴大,其實在小説的第七回、第三十四回就已經分别埋下了伏筆: 第七回提到,范進門下的少年幕客蘧景玉,曾講過一個擔任四川學差的某老先生搞不清蘇軾是宋朝人的笑話;第三十四回則提到,莊紹光進京途中遇到了從四川押送餉銀入京的蕭昊軒與孫守備。至於爲什麽小説空間背景要從江南往四川延伸轉移,這應該跟蕭雲仙的原型人物李畝曾在四川爲官有關(這一點詳後文)。爲了安排郭孝子入川,並隨後讓郭孝子帶出蕭雲仙,也爲了讓即將發生在四川的蕭雲仙故事跟很久以前發生過的故事、出現過的人物聯繫起來,增强小説的整體感,吴敬梓先是讓第二十、二十一回曾經出現過的甘露僧來到了陝西同官縣的海月禪林,結識了郭孝子,爲他後來入川尋找郭孝子時遭危難、從而引出蕭雲仙搭救做好鋪墊;同時又讓第三十四回出現過的蕭昊軒和强盜頭子趙大也做好重新出場的準備——在郭孝子入川後,賊頭趙大也來到了海月禪林,認識了甘露僧,因趙大攪亂禪林秩序而遭其驅逐,結下仇恨,後來欲害甘露僧,從而引出蕭雲仙。而前文提到,尤扶徠打發郭孝子入川時,曾叮囑他到成都之後去找蕭昊軒,蕭昊軒的重新出場則讓即將登場的蕭雲仙被自然而然地織入了小説既有的人際關係網絡之中。此外,郭孝子入川路上遇到的木耐這一人物的出場則更是爲後文安排蕭雲仙的諸多重要情節做好了鋪墊。
我們看到,第三十八回發生的小説空間的這種大轉移與人物的大流轉之所以並不令人覺得突兀,除了這些精心的敍事鋪墊之外,也跟作者精心選擇的三個流動性很强的人物(郭孝子、甘露僧、趙大)有關,而郭孝子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穿針引線的作用,也正是通過這三個人物合乎情理的流動,小説自然而然地實現了故事空間的重大轉移與人物的轉承交替。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僅僅這一小部分情節的敍事安排,作者就真正做到了前後勾連呼應、聲氣相通、血脈連貫、天然渾成的地步,具備極强的整體性和有機感,若是他人撰寫後竄入,豈能如此諳熟吴敬梓整體創作計畫和結構風格,又豈能通過一時之模仿而做到如此縝密、如此周詳的程度呢!
此後小説即進入對蕭雲仙文治武功的正面敍述,正如前文所述,這一部分既是對提倡“禮樂兵農”等學問及其踐行這一主題思想的具體化,也是對泰伯祠大祭以及高翰林等人的虚僞主張的隱秘呼應與對比,仍然被嵌入了小説的整體主題及結構脈絡之中,絶不是隨意安排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蕭雲仙在青楓城設立學堂,請江南來的沈先生擔任教師這一細節。這明顯是在爲後來沈瓊枝故事的安排做準備,正所謂伏脈於千里之外,吴敬梓十分善於運用這一敍事手法。在蕭雲仙故事的結尾,他被授予應天府江淮衛守備一職,於是繞了一個大圈之後,小説的空間背景又從四川回到了江南——這種處理手段真令我們不得不衷心佩服作者大匠運斤的筆力和才華!蕭雲仙來到江南,遇到了自己當年的老部下、如今已任總兵之職的木耐(這種線索人物的運用吴敬梓可謂得心應手,毫不費力),兩人去廣武山賞雪(賞雪一段藴含無限感慨、無限悲涼,亦非大手筆不能爲也),看到武書題的詩——作者在小説人物之間的溝通聯絡上費盡神思,而每每手筆不凡,蕭雲仙與武書的相識通過一首詩作引子,乃是十分高明的手法。這令人聯想到前文寫虞博士見杜少卿之前,也曾在尤資深案頭看到過杜少卿的詩集,但這兩處情節相似而不相犯。此後敍述雲仙到任後,去拜會武書。次日,武書回拜,送上自己的一卷詩。雲仙則拿出一個自己在青楓城歷年事迹的卷子,請武書題寫,以傳不朽。武書答應了,並表示要請其他大手筆撰文,並介紹他去拜會虞博士、杜少卿、莊紹光諸人。這裏我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吴敬梓慣用的敍事上的“餘波演漾”之法: 蕭雲仙在青楓城的事迹已成爲過去,但作者卻並不讓它一下子就徹底消失,而是會以新的方式不斷地提到它。另外,還需要特别提到在上述蕭雲仙跟武書往還的情節之中被作者插入的一個極其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 在蕭雲仙初次拜會武書之後,虞博士召見武書,告訴他其母旌表的事“部裏因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才准了”,讓武書去領建牌坊的銀子。此後再接着敍述武書回拜蕭雲仙的事。虞博士爲武書母報請旌表事見於第三十六回他剛到南京上任時,至此回,時間已經過去了大約十一年,[注]雖然説是因爲被駁了三回才導致遷延日久,但歷時十一年也未免太久了一點!這也是一個不太合理之處。但作者所考慮的應該主要是通過這麽一個細節來跟前文相呼應,我們也就無需苛責了。其間相隔了如此衆多的其他故事,普通讀者或早已忘記此事,作者卻依然記得,並在這個地方提上這麽一筆,以爲前文之呼應,這足見其結構用心之縝密實在已到了令人歎爲觀止的地步。很顯然,這種地方就絶不可能是他人仿寫竄入所能做到的了!
此後蕭雲仙押運糧船赴淮,在揚州遇到沈先生,從此遞入沈瓊枝,再由沈瓊枝引出湯家兩兄弟並其父湯鎮臺。這其中的敍事安排前文已經約略論及,這裏也不再贅述。筆者重點要討論的是跟兩位湯公子有關的段落中的一些敍事細節: 在第四十二回中,湯家大公子、二公子將往南京參加鄉試,湯六老爺在妓院擺酒給他們餞行——這裏特意强調了他們叫的教門廚子,備的是教門席——如果我們足夠細心的話,將會發現這一細節竟然呼應了第四回寫到過的高要湯知縣是回民這一點,而這是太容易被忽略或被忘記的一個細節了,除了吴敬梓,誰還會記得,誰又還會在意呢?——兩位公子到了南京釣魚巷住下,作進場前的準備工作。入場這天,貢院路邊擺着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公孫等人選的時文——這種對前文的敍事照應也顯得心思極爲細密。考完後,他們請了一班戲子來謝神,請的是鮑廷璽領的班子。在此,作者不僅重新讓鮑廷璽出場,也再一次强調湯家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廚子。戲演完之後,鮑廷璽讓湯大老爺選兩個小孩子留下伺候,但湯大爺不喜歡小孩子,鮑廷璽就向他推薦了對河的葛來官——作者在這裏又順勢提及當年杜慎卿主辦的莫愁湖大會,這又是吴敬梓的慣用筆法。次日,湯大老爺攜重禮去訪葛來官,又一次强調自己是教門,不用大葷。吃揚州大螃蟹時,湯大爺説起“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的,也不得一隻吃吃”——又一筆勾連到高要湯公,雖然湯公年近百歲仍在高要任上這一點很令人起疑。這時,湯府管家尤鬍子前來報告説湯二爺在鷲峰寺旁一個人家喝茶被訛,遭圍困,姚奶奶幫着把住了門——請注意:姚奶奶這個極次要的人物第一次登場是在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婦游清涼山,曾攜她同行;她第二次出現是在第四十一回沈瓊枝拜見杜少卿夫人的場合,她誇過沈的刺繡好;結果此人竟然又在這裏出現了。從上舉故事運用的大量照應前文的敍事手法中,也同樣可以看到十分鮮明的吴敬梓風格,尤其提到湯家是教門以及姚奶奶的重新出現這兩點,[注]第四十四回寫湯鎮臺離職,其同僚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這裏再一次提醒讀者湯家是教門,有自己專門的廚子。最早都曾在無可置疑的吴敬梓原稿中出現過,這種如此芥豆之微的細節,除了對整部小説有着全盤把握並沉浸其中的原作者,誰還會在意它們並能反復利用它們來作爲巧妙的結構因素呢?此後小説進入第四十三回,湯鎮臺來信召兩位公子去貴州鎮署。這時,一個叫王漢策的人前來拜托兩位公子在路上照顧其東家萬雪齋的鹽船——王、萬二人在小説的第二十三回曾出現過,到此回至少隔了三十八年,原本可以不必再出場的人物卻又一次出場了,而且這一段照顧鹽船的故事也完全可以不必寫,但作者出於一貫的敍事匠心,也還是讓他們再一次出場了。這種情節安排似也只有吴敬梓本人才能做到。
湯鎮臺和蕭雲仙的征戰故事後文還要加以討論,這裏先置而不論。在野羊塘大戰之後,湯鎮臺遭降職處分,回返故鄉。蕭柏泉來拜訪他,推薦余大先生爲湯府西賓,由此引出了余家兩兄弟。余大先生到南京訪杜少卿(二人是表兄弟),遲衡山、武書陪坐,余大先生説起湯家請他做館的事,認爲“武夫不過如此”。武書因説起蕭雲仙之事,拿出雲仙手卷請余大先生題詩——以照應前第四十回——敍事能關照到如此細節,可見作者結構上用心之細密,亦此書之慣技也。余大先生返鄉(五河縣),他的一個本家請客,席間他的堂兄弟余殷、余敷説起當地出身的大僚彭老四要舉薦他的同年湯奏(即湯鎮臺)任應天府尹一職——連此等處亦不忘照應湯鎮臺,作者心思實可謂極細。至第四十六回,湯鎮臺到南京來拜杜少卿,適逢余大先生也在,與湯鎮臺攀談,又照應前文所敍湯鎮臺諸故事。湯鎮臺去拜虞博士、莊紹光、莊濯江。在莊濯江家巧遇莊紹光,大家商定給虞博士餞行。湯鎮臺又去拜遲衡山、武書。三日後,衆人在莊濯江家聚會,餞别虞博士,湯鎮臺、蕭雲仙都出席了。言談之間又提及蕭雲仙當年在青楓城的往事來照應前文,尤其是敍及蕭通過工部核算知道青楓城有水草的事,手法十分高明。席間搬演戲文,當年杜慎卿所定梨園榜上戲子都傳到,又跟前文杜慎卿莫愁湖大會一事照應。湯鎮臺又提到杜慎卿已銓選部郎之事。從以上這一大段情節中,我們看到作者頻頻地照應回顧蕭雲仙和湯鎮臺兩人的故事,而且把這些照應回顧的内容跟以杜少卿、虞博士爲核心的南京文人圈子緊密地結合起來,敍事手法細緻而巧妙,呈現出吴敬梓的獨特敍事風格。這種風格,頗不易爲他人所模仿。
從第四十六回開始,小説的主要人物紛紛退場,小説開始進入越來越頻繁的對往事的回顧與重温時期,到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這幾回,回顧與重温漸漸達到高潮,時間的進程也明顯加快了,《儒林外史》終於達到了它的尾聲。看起來,第四十六回正是這一漫長的告别儀式的開始,衆人言談中對蕭雲仙、湯鎮臺、杜慎卿故事的回顧正是這一告别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應該是吴敬梓整體構思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接下來,筆者將從藝術風格一致的角度來探討一下那些被懷疑是竄入的章回。俗話説: 風格即人。風格固然也可以被刻意模仿,但要做到形神畢肖、以假亂真的地步卻並不那麽容易。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將那些没有遭到懷疑的章回跟被懷疑的章回進行對比來作出判斷。這種對比當然不可能是全局性的,而只能從一些特殊的角度來展開。
在中國古代的白話小説中,往往會借助程式化的詩詞歌賦來進行景物描寫,散文化且獨具表現力的寫景文字卻極少。《儒林外史》卻是例外。不少清新優美、富於詩意、且跟小説情境融合無間的景物描寫散佈在全書各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下面讓我們先來看一看没被懷疑的章回中的這一類景物描寫:
第一回: 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給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
第一回: 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佈,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
第二回: 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吃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卻也有幾株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内,望着雨下在河裏,煙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卻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
第八回: 兩公子坐着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撑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内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説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
第九回: 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棵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
第十一回: 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内,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别。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吃到下午,看着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韋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侄告辭老伯下船去。”
第三十六回: 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裏舒暢。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裏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
第四十一回: 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着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
第四十一回: 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鈎,漸漸的照過橋來。
類似的描寫還有不少,在此無需全部摘錄羅列出來。且讓我們再來看一看被認爲是竄入的章回中的一些景物描寫——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奇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個人(此處有黃小田評語云:妙,妙,不是抬頭就見,卻從月影中看出,且令深山夜景如在目前),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
第三十八回: 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的,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别了老和尚又行,找着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棱着,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着,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着。
第四十回: 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黃小田評:寫出太平景象)。蕭雲仙心裏歡喜(天目山樵評:和我也歡喜)。——這一段可跟上引第一回秦老的話作對比。
第四十回: 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個兵,備了幾樣肴饌和一尊酒,一徑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内。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即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黃小田評曰:隨意寫景必妙)。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説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倒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
第四十二回: 説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黃小田評:“煙霧迷離”確是河房暮景,此等細切處,人所易惑,辜負作者用心),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絶。這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裏,擎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
第四十三回: 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
第四十三回: 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裏,扒過牆來,望裏邊,月色微明,照着一個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
我們將上面兩部分寫景文字對讀,不僅能看到二者在文字風格上的高度一致性,更感受到二者都有一種簡潔傳神的韻味,且又彼此皆有對春天、河面和月色的描寫,給人的印象也都頗爲一致。而且,這些景物描寫往往都是通過人物的觀察來呈現,進而跟某個人物的活動、情感與境遇極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比如“虞博士心裏舒暢”與“蕭雲仙心裏歡喜”這樣的描寫何其相似),藝術表現力很强。單純的寫景文字可以模仿,但寫景文字跟人物活動、情感的這種普遍而緊密的結合方式卻不是那麽容易就能模仿的。
一個作家在寫作中往往會表現出特定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上的習慣,别人如果想刻意模仿,則模仿片言隻語的表達習慣相對容易,但要模仿其長篇大論,模仿其思維方式則没那麽容易。我們從《儒林外史》中那些没被懷疑的部分能看出吴敬梓的不少或顯或隱的寫作習慣,而從那些被懷疑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出同樣的習慣——這些習慣有些固然容易被模仿,但有些卻很難被模仿——無論如何,它們的存在都只能進一步加强全書均爲吴敬梓本人所作的可能性。
我們先舉一個吴敬梓運用大體相同的手法刻畫不同人物的例子,來看一看這種寫作習慣的具體表現形式。第三回寫范進中舉之後發瘋的情形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
范進不看便罷,看過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説着,往後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怕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説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
再看第四十八回寫王玉輝女兒絶食而死的消息傳來,王玉輝的表現:
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説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呆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這兩段描寫之間的相似性十分明顯,體現出作者的寫作習慣或寫作套路,但其所刻畫的人物的情感與性格則不盡相同,這正是金聖歎總結《水滸傳》敍事手法時所指出的“略犯法”,吴敬梓成功地做到了同中有異,各擅其美。這種具備自我重複性的“略犯法”在《儒林外史》中普遍存在,下面將列舉若干並存於被懷疑的章回和未被懷疑的章回之中的“略犯法”(有些更近於“正犯法”)來進行分析:
被懷疑的第四十回寫蕭雲仙跟木耐登廣武山賞雪,雲仙看到樓閣牆上的一首《廣武山懷古》的七言古風,“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淒然淚下”——原來這是武書題的一首詩,蕭雲仙因此而得以跟武書結識。
未被懷疑的第五十五回寫荆元爲于老者彈琴的情景與此極爲相似:“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
人物在特定情境下被精微的藝術品所打動而淒然淚下,不僅形似,而且神似。此外,雲仙先讀武書之詩,後識武書之人,這也是吴敬梓連綴人物的重要手法,比較典型的同類例子還有第三十三回寫杜少卿在蕪湖識舟亭牆上看到韋四太爺的識舟亭懷古詩然後跟韋四太爺相見及第三十六回虞博士跟杜少卿相識之前曾先在尤滋案頭看過少卿的詩集。在這三個例子中,表達效果最好的是雲仙這一例: 淒涼,悲酸,情景交融,百感來心,比未被懷疑的章節更具表現力。
在被懷疑的第四十回中寫到蕭昊軒的臨終遺言:
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麽遺言?”蕭昊軒道:“你這話又呆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説畢,瞑目而逝。
再看未被懷疑的第一回王冕母親的遺言:
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看見那些作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作官。我死了,口眼也閉。”
以及第十七回匡超人之父匡太公的遺言:
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你哥是個混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才是!”兄弟兩個哭着聽了,太公瞑目而逝。
以及第三十二回婁焕文臨終囑咐杜少卿的遺言:
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没有飯吃也不妨。……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吃苦。你眼裏又没有官長,又没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着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
將這四處描寫臨終遺言的段落加以對比,可以看出它們在思想上及用語細節的高度一致性。這正體現出吴敬梓本人的用語習慣和敍事習慣,[注]以上兩個方面的證據取自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2015級本科生段安琪的論文《蕭雲仙故事考論》,該文乃筆者所開設的《儒林外史研究》課程的期末作業,未發表。而這種習慣又並未導致内容簡單重複的弊病。
《儒林外史》被懷疑部分與未被懷疑部分出現的一些“略犯法”又折射出思維方式、觀察方式與表現形式的高度一致性。比如如下若干組例子:
1. 對“偷看”場景的描寫
第二十二回,寫牛浦在船上偷窺牛玉圃的場景:
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後船來辦盤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一隻紅蠟燭來。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着四盤菜,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
第三十八回中,郭孝子尋父途中遇虎,老虎將其放入坑中,蓋上樹葉,於是有了郭孝子“偷看”這一場景:
天色全黑,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跳出一隻老虎來……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
這兩個場景雖然具體内容不同,但貫穿其中的人物視角的使用與敍述層次安排卻非常相似,這種内在思維方式的共性顯然不是靠模仿就能輕易做到的。
2. 對“失火”場景的描寫
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將一個異獸的出現誤認爲是失火:
那庵裏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正吃着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
這個場景由一系列動作構成: 第一,人物坐在窗邊;第二,他專注於某事,這裏是吃飯;第三,他透過窗户看到外面一片紅光,頓時慌了;第四,人物驚叫一聲“不好”。
第十六回有個場景和它很像,寫匡超人在家中遇到村裏失火:
他把那鐵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
匡超人也坐在窗邊,專注於讀書,抬頭同樣從窗户看到一片紅光。他懷疑是三房有人要强行拆房,就如同郭孝子以爲失了火一樣。而且匡超人同樣放下手中的事,叫了一聲“不好”,最後就像郭孝子,發現了不同於預料的真相。
真的失火和疑似失火原本可以采用不同的寫法,而這裏卻採取了相同寫法,似表明了吴敬梓有對“失火”場景的描寫套路和思維定勢(第四十五回寫余家對門夜裏失火也跟第十六回相似),所以即使隔了很多章回,寫疑似失火,他也會順手寫出相似的文字。
3. 對人物特定心理的刻畫
第三十八回,郭孝子終於找到父親,但其父親的反應是“嚇了一跳”,之後拒絶相認:
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上慟哭。
作者用“嚇了一跳”表現父親的心虚與錯愕。無獨有偶,未被懷疑的章回中,這種寫法同樣存在。如第二十四回寫牛浦見石老鼠時的反應:
牛浦見是他來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
牛浦在黃家見到石老鼠,“嚇了一跳”,同樣由於心虚和意外,因爲他入贅到黃家是重婚,而黃家人不知道,他怕石老鼠説出來。
第二十八回也出現“嚇了一跳”的場面:
季葦蕭戴着新方巾,穿着銀紅綢直裰,在那裏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揖,請他坐下。
同上例,季葦蕭重婚而親家不知,不巧在婚禮上遇到了前妻的姑爺鮑廷璽。這回鮑廷璽相當於石老鼠的角色,而季葦蕭猛然見到他,又是“嚇了一跳”,又是季葦蕭心虚的表現。這個句子或是吴敬梓不自覺形成的、對某類負面人物特定心理狀態的模式化表達。故這個普普通通的句子在本書中有着獨特的作用和意義。未被懷疑的章回中還有一處用到了該句: 即第三回范進發瘋“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可見作者很喜歡用這種簡潔有力的白描句式來進行人物心理刻畫,以至於形成了難以改變的習慣。
4. 某些特定句式在書中反復出現,具有明顯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這在被懷疑的章回和未被懷疑的章回中都是如此。
比如以“天氣”或“天色”開頭的四字句,第十二回出現了兩次,第十三回和第二十二回各出現了一次:
(1) 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
(2) 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换了單夾衣服,手持紈扇。
(3) 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
(4)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
第三十八回中,這種句式共出現了四次:
(1) 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着一個人。
(2)天色全黑,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
(3) 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
(4) 見天色將晚,自己想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
看起來,這些短句從形式到功能都完全一樣,顯然也是吴敬梓的一種習慣性表達。
未被懷疑的部分中,“第三日”是一個出現頻率頗高的時間跨度敍述。而這一時間跨度敍述也較多地出現在了被懷疑的部分中,如第三十八回就出現了四次“第三日”的時間跨度敍述:
(1)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
(2) 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
(3) 到第三日,雪晴。
(4)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
這幾例中的時間跨度敍述似乎看不出如此安排的明顯的用意,至少很難説明“第三日”和“第二日”究竟有何不同,所以,這一時間設置很可能只是作者的習慣。而在未被懷疑的部分,它們出現的頻率也很高。比如:
(1) 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第四回)
(2)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麻戴孝。(第五回)
(3) 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第十回)
(4)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第十四回)
(5)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第二十三回)
(6)第三日午堂聽審。(第二十四回)
(7)第三日,送婁太爺起身。(第三十二回)
我們找不到很好的理由來解釋這兩種較爲常見的敍事現象出現的必然原因。若爲後人竄入,應該是不太容易注意並模仿這種既不好理解又不太顯眼的敍述特徵。[注]以上四個方面的證據及其分析均取自北京大學中文系2014級本科生張豐楚的論文《從藝術手法試論〈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至四十回的部分非係後人竄入》,該文乃筆者所開設的《儒林外史研究》課程的期末作業,未發表。筆者在征得張豐楚同意後對該文的論據及其論證進行了全面引用,也根據需要作了修改。
我們再來看一看被懷疑的章回跟没被懷疑的章回在諷刺藝術上的聯繫。魯迅先生曾説過《儒林外史》“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無一貶詞,而情僞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注]魯迅《中國小説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189、193。——這一番精闢的論述告訴我們,這部小説的諷刺藝術其實是十分複雜而微妙的: 悲戚、詼諧、辛辣、委婉、含蓄、不動聲色,然而又能看出作者鮮明的態度。在筆者看來,吴敬梓的這些風格有時可以明確區分開來,但有時則雜糅在一起,令人覺得五味雜陳,百感交集,難以截然區分,也難以明確把握,以至招來後代讀者的不少誤解。在小説第三十六回以前的不被懷疑的部分,比較明確的諷刺鋒芒指向了夏總甲、梅三相、王惠、胡屠户、嚴貢生、匡超人、牛浦郎、胡三公子這些人,對范進、周進、嚴監生則既有諷,也有戚,對他們是包含着同情的,尤其是對周進,更是如此。對更多的人則采用“無一貶詞,而情僞畢露”的表現手法,用看似客觀冷靜的文字去呈現這些人物,讓他們用自己的言行來展示自己的性格,而判斷的自由則留給了讀者。這樣一種靈活多變的寫作藝術在那些被懷疑的部分中其實也遍佈各處。其中最令人難忘的例子出現在被懷疑的第四十二回,[注]這一回寫了湯大公子、湯二公子這一對兄弟,吴敬梓很喜歡寫兄弟二人這種成對的人物,比如二嚴、二婁、二杜、二湯(包括湯鎮臺、湯知縣老兄弟兩人)、二余、二胡、二徐。從這一角度來看,二湯的設置也是吴敬梓寫作習慣的一個表現。這回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公子妓院説科場”,竊以爲是可以跟第三回的“范進中舉”這一著名段落相提並論的。
這一回寫南京的下等妓女細姑娘、順姑娘從南京來到儀徵豐家巷,烏龜王義安領着她們拜見湯六老爺。小説描寫湯六老爺的惡賴下流之相與嫖客來嫖妓的惡俗場景均十分真實生動,受到清代評點者黃小田、張文虎等人的一致贊許,説其“神乎技矣”、“畫所不到”、“趣甚”、“真滑稽”,並對作者能做到這一步表示佩服和驚奇。[注]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516,517。其間寫到王義安打聽大老爺(湯鎮臺)邊疆有無消息來,這時湯六老爺一通胡扯,道:
“怎麽没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説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個氈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
針對這一段,黃小田評曰:“末句無情無理,確是此等人談吐。”齊省堂評曰:“真是嚇烏龜、婊子的話。”[注]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517。這一段描寫讓我們聯想到夏總甲、嚴貢生、牛浦郎、匡超人、臧蓼齋這些虚張聲勢、倚仗虚造的官府權威驕人欺人的人物,這裏只需引匡超人的一段故事來作對比,就能見出二者的神似之處:
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麽?”匡超人道:“怎麽不選?象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麽?”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 公座、硃墨、筆、硯,擺的停當。我早上進去,升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床沿上,談了一會出來。”
次日,因湯大公子、湯二公子將往南京鄉試,湯六老爺在妓院擺酒給他們餞行。席間,湯大公子有一大段戲説科場——對這一大段,清代各家評點均備極稱道,如“先生真善滑稽也”、“絶倒”、“絶妙穿插”、“書中人正襟而談,讀者已笑得欲嘔”云云。[注]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519,520。對於科場情形,當時的讀書人凡是觀過場的,應該都十分熟悉,若照直描寫,則容易了無趣味,作者卻在此獨闢蹊徑,描述了一個不學無術、屢試不中的紈絝公子在完全不知科場爲何物的婊子、烏龜面前大肆誇耀的場景,立刻使莊嚴的科舉考場變成了“和尚放焰口一般”熱鬧而詭異的場所,讓人感覺既新鮮,又充滿戲謔嘲諷的意味——對科舉制度的批判也暗含其中。這正和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劉姥姥的眼睛來寫賈府和大觀園、文康在《兒女英雄傳》中借鄧九公的眼睛來寫北京文人的狎優風氣同樣高明(即所謂“陌生化手法”),絶不是一般作者能做到的。如果從寫作風格角度而言,這一段對湯大公子的諷刺性描寫,跟對梅玖、王惠、嚴貢生、匡超人、牛玉圃,還有五河縣那些“非方不心,非彭不口”的勢利者們自吹自擂又出乖露醜的行徑描寫如出一轍,顯然同出於一人之手筆。
如果説,小説在第三十三回以前主要通過有着明顯性格弱點的人物來表達其對科舉制度與世態人情的諷刺和批判的話,那麽從第三十三回到第四十八回則通過對一些比較正面的人物的遭遇的描寫來將諷刺的鋒刃刺向更深的制度層面: 杜少卿、虞博士、莊紹光、遲衡山這些人,或沉淪下僚,或遭逢不偶,或用世之心淡漠而遁世之心深沉,其故安在?從第三十四回高翰林譏諷杜少卿之父不懂爲官之道,以及第三十五回莊紹光被徵辟而又被放還的遭遇開始,官場的陰暗面被掀開了一個小小的角落,科舉制度背後更大的制度弊病露出了其猙獰的面目。被推許爲“書中第一人”的郭孝子在其尋父之旅結束後,[注]“書中第一人”一語是張文虎在第三十七回所寫的回末評語,參見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466。曾苦口婆心地勸説蕭雲仙從軍報國,博一個封妻蔭子、青史留名,蕭雲仙聽從他的勸告,投奔平少保,收復青楓城,築城勸農,興辦學堂,但他有功不獲賞,最終落得個家産賠盡,僅被授區區守備之職的悲慘結局;湯鎮臺的遭遇大體與其類似,立下了赫赫戰功,卻被降職三級任用。這些有才能、有追求的進取型人物在進入仕途之後,卻遭遇了官僚體制這一更頑固堡壘,同樣無法充分施展其用世之抱負。其他衆多不明就裏的讀書人孜孜矻矻,寒窗苦讀,即使能僥倖撞開科舉之門,進入仕途,等待他們的難道就一定是光明的前途嗎?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這些人應該都是真正看透這一點的,於是多少有些不甘地選擇了多餘人與閒散者的命運。跟《儒林外史》完全同時代的《紅樓夢》中也出現了厭惡仕途經濟的“富貴閒人”賈寶玉這一人物典型,這難道只是偶然的巧合嗎?應該説,這一批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讀書人的人生選擇與命運遭遇成爲了小説中最大的反諷與最深的無奈,作品批判的鋒芒大概到此也抵達了它的極限,難以再往前多走一步了。在作爲全書總結的“幽榜”這一回中,作者借御史單颺言的奏疏也委婉地批判了選舉和用人制度的弊端,但也只能無奈地將病根歸結爲“資格困人”,並寄希望于統治者改變這一不合理的用人觀念與用人制度。因此,從批判科舉制度進展到批判用人制度、官僚制度,這至少是貫穿在《儒林外史》中的一條重要主題線索(但不是唯一線索),在這條線索之上,杜少卿、遲衡山、莊紹光、郭孝子、蕭雲仙、湯鎮臺這些人物一個也不能少,而蕭雲仙、湯鎮臺則尤其不可或缺,缺了他們,小説批判的深度顯然就大打折扣了。
四
在導致對蕭雲仙、湯鎮臺故事發生懷疑的諸多理由中,認爲其思想性、藝術性方面存在問題的説法一直有着很大的影響,比如認爲郭孝子在酒店勸説蕭雲仙從軍報國、封妻蔭子的一番話跟全書精神和作者思想完全違背,也跟郭孝子的爲人相違背;認爲蕭雲仙在青楓城開設學堂,與會做八股文的學生分庭抗禮的情節也不符合吴敬梓批判八股文的一貫思想;還有的認爲郭孝子深山遇虎、“羆九”兆雪、蕭雲仙救難明月嶺、收復青楓城、湯鎮臺野羊塘大戰都太具傳奇性,缺乏真實感,是坊間小説老套,跟小説主體部分不相稱;甚至連莊紹光往返北京途中遇到劫匪和詐屍等段落也被有的學者指爲荒誕不經,認爲是被後人竄入的。其實,上述這些段落有的取材於吴敬梓的閲讀所得,有的取材於他朋友們的經歷,還有的取材於社會傳聞,應該説,它們都不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尤其是取材於朋友經歷的那兩次戰事,更不是吴敬梓所能親自經歷的,因此,要説這些段落缺乏實際生活經驗,自然是符合事實的,但如果要説它們在思想上與作者不一致,在藝術上有很大的瑕疵,筆者則無法認同,因此有必要在此爲吴敬梓一辯。
關於蕭雲仙在青楓城禮遇會做八股文的學生這一段是否跟吴敬梓的思想矛盾,拙文《論〈儒林外史〉原稿爲五十回説之不能成立》中已有申辯,此處不再重述。這裏來看一看郭孝子勸説蕭雲仙的那一段話是否有什麽問題。
在開始討論之前,筆者有必要先説明一下: 對待這類爭論的辨析標準主要應該是藝術上的正確與否,而不應該是思想上正確與否,更不應該籠統地以是否符合作者思想作爲判斷的依據。也就是説,判斷郭孝子這一番話是否合理,主要應該看這一番話是否符合小説中的郭孝子這一人物的身份、經歷和處境,而不應看它本身是否正確或符合作者的思想,這一點應該説是毫無疑問的。
那麽,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郭孝子是在什麽情形下跟蕭雲仙説那一番話的——先回顧一下郭孝子的生平經歷: 據蕭雲仙之父蕭昊軒説,郭孝子年輕時武藝精能,與自己齊名。但後來郭父在江西做官時投降了寧王,寧王失敗後,郭父隱姓埋名,遠遁四川做了和尚。郭孝子爲了尋父,二十年走遍天下,奔波辛苦,終於找到父親,但其父卻拒絶跟他相認。郭孝子在廟旁租房傭工,養活父親,等到父親過世,就背着其骸骨準備歸葬故鄉。這時,他在途中酒店遇到了剛救了甘露僧的蕭雲仙,説了如下一番話:
“這冒險借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埸,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説,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
看起來,作爲被書中衆人大力推崇的大孝子,郭孝子不應該説出上面這番話來,他似乎應該説出一番讓蕭雲仙回家侍奉老父,不要以功名爲念的大道理才對啊!然而他卻諄諄勸告雲仙去爲朝廷效力,博個青史留名,封妻蔭子,這豈不是讓雲仙將老父抛在腦後,去追逐個人的功名利祿嗎?這好像既不符合郭孝子的孝子身份,也不符合吴敬梓一貫反對追名逐利的思想吧?如果我們這樣看問題,那就是追求籠統的思想上的正確,而完全忽略藝術上的正確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站在此時的郭孝子的角度來體會他的處境和心緒,其實應該是頗爲複雜的: 他年輕時一身武藝,本可以建功立業,顯親揚名,封妻蔭子,青史留名,但爲了尋找父親——而這位父親背叛了朝廷,按照當時的觀念來説,他自然是不忠不義之人——他耗費了半生精力,找到了父親,父親卻根本不願與之相認,最終這位父親也死去,變成了一抔白骨,背在囊中,準備歸葬故鄉。他自己而今也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這是多麽悲涼而虚無的結局!他這麽做的意義何在呢?他的人生是不是就只是奉獻給了一個虚幻的孝子的名聲?他勸雲仙“萬不可蹉跎自誤”,這話似乎有些隱微的弦外之音,他是在暗示自己被“蹉跎自誤”了嗎?他對他的行爲感到後悔了嗎?作爲讀者,我們感到疑惑的還有: 當初驅使他走上艱辛的尋父之路、並堅持了二十多年的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動力?是發自天然的對於父親的强烈思念呢,還是出於一種道義上的激勵?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這種行爲具備真實的心理動機嗎?[注]商偉對郭孝子故事的複雜内涵也做了深入的分析,請參看《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第二章“郭孝子的懺悔: 幻滅的一刻”。同前,(轉下頁)看來,如果細細地體會一下,就會感到郭孝子這一番話中真是深藏着無法明言的複雜情感——這種情感驅使他苦口婆心地勸説跟年輕時的自己頗爲相似的蕭雲仙去替朝廷效力,建功立業,不要蹉跎自誤——這是在特定情境下的郭孝子的思想流露,不完全代表着吴敬梓的態度。但,這一番話,跟吴敬梓的思想難道會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嗎?他不是在一再地鼓吹禮樂兵農的學問?替朝廷效力,到疆場殺敵不正是符合這一提倡的嗎?看起來,在那樣一個時代,又是在小説所描繪的那樣一種情境之下,在這麽兩個特定身份的人物之間發生的對話,吴敬梓對之做出了藝術上完全正確的描寫,而且也是十分高明的描寫。這一問題正跟《紅樓夢》第十六回結尾寫到的秦鐘對寶玉的臨終遺言一樣(也曾有學者懷疑這不是出自曹雪芹的手筆,因爲這不符合寶玉的思想,也不符合曹雪芹的思想),表現的不是思想上的所謂正確性,而是藝術上的正確性,可以説,這兩處寫法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注](接上頁)頁105—110。不過,筆者並不認爲小説明確地表現了郭孝子的懺悔和幻滅。在這一段故事中,吴敬梓“婉而多諷”的風格表現得頗爲典型,他對郭孝子這一事件的立場隱藏得很深,以至於我們幾乎無法明確地加以把握。或許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該如何來評價這一人物的行爲和結局吧。
關於郭孝子的問題,這裏不妨再就學界所提出的其他質疑再多説幾句: 在全書的主題層面和敍述風格上,這一人物的故事是否跟全書主體部分不相稱,敍述上也乏善可陳呢?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分開來談比較方便一些。
前文已經特别强調,《儒林外史》的主題思想並不是單一的,而是複雜的,多層面的,然而萬水歸於一源,其實多種主題都跟小説第一回所提到的“文行出處”有關,而把“文行出處”具體化之後,則跟人物的言行相關,其中“文”“出”“處”主要跟讀書人相關,“行”則跟所有人都有關,具體表現在一個人如何處理自己跟他人的關係,即如何處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這儒家所極爲重視的五種基本社會關係上——這些内容都在小説中獲得了具體的表現,尤其父子一倫所要求的孝道被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來加以凸顯,甚至超過了君臣一倫所要求的忠誠的原則。對孝道的重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着十分深厚的淵源,這裏無須去追根溯源,只要就小説本身來加以討論就可以了。我們檢點整部小説,從第一回的王冕開始,依次出現了匡超人、杜少卿、武書、郭孝子、蕭雲仙等以孝行著稱的人物,也出現了反面人物——不孝的温州張氏三兄弟(第十五回)。在匡超人這一故事中,作者集中表達了當時社會對孝道的主流看法,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吴敬梓自己的看法。從小説的第十五回開始(這一回回目的後一半是“思父母匡童生盡孝”),匡超人出場了,他首先就受到了馬二先生關於什麽是“孝”的一番教誨:
(馬二先生)向他説道:“賢弟,你聽我説。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説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説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顔如玉。’而今甚麽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没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注]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論語·爲政》)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轉下頁)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的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注](接上頁)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孟子·離婁上》)
馬二先生是十分誠懇的,但吴敬梓則顯然是要通過他這一番話對第一回王冕所説的“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一預言做一番印證。隨後匡超人在返鄉的船上遇到了衙役鄭老爹去温州提三個不孝的張姓秀才,鄭老爹感歎道:“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匡超人聽了在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象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再一次印證王冕的預言。匡超人返鄉後,對生病的父親確實能恪盡孝道,又能一心向學,因此受到樂清縣知縣的提攜。知縣在學道面前誇獎他的孝行,學道説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匡超人中秀才之後不久,其父病重,臨終囑咐他道:
“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
但匡超人後來的人生道路卻漸漸地走向了違背他父親遺言的方向,成爲被作者諷刺批判的不孝不義之人,他的墮落看來正是讀書科舉、追求功名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我們看到: 作者通過王冕、學道,匡父跟馬二先生、匡超人的不同言行展示了人們對於孝道内涵的不太相同的理解。此後陸續出場的幾位孝子型人物杜少卿、武書、郭孝子、蕭雲仙則基本上都是從正面表現的: 杜少卿這個人“但凡説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就願意不遺餘力地資助人家,他對老家人婁焕文無微不至的關懷也頗令人動容,他的孝義乃是發自赤誠之天性,他似乎並不太在意社會輿論對他的道德評價;武書則有個節烈之母,他事母至孝,爲侍母連科舉都不參加,母親去世後才出來應考;蕭雲仙爲了照顧父親蕭昊軒,不願去松潘投軍,蕭昊軒責以大義,説他如果貪圖安逸,依戀妻子,便是不孝之子,他這才去了;後來被處賠補築青楓城費用,罷官回家,蕭昊軒病重,得知其事,反而安慰雲仙,並無任何怪罪之處,臨終囑咐雲仙“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小説這樣描寫蕭昊軒去世後,蕭雲仙的表現:
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卻自己歎息道:“人説‘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爲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
清人黃小田在這裏有一段評語説:“雲仙忠孝二字足以當之,昊軒可以瞑目矣。”
至此,我們可以更爲清楚地看到: 取材於社會事件、並在明清小説戲曲中被予以廣泛表現的孝子千里尋父故事在整個主題系統與人物鏈條中究竟具有何種意義了。可以説,在小説中,吴敬梓始終是把奉行孝道放在跟追求功名的相互關係之中來加以表現和思考的: 他塑造了爲讀書求取功名而最終背棄了孝道的讀書人,也塑造了忠孝兩全、孝道與功名兩不誤的人,還塑造了爲了行孝而願意放棄功名、甚至放棄自己人生的人——而被吴敬梓將人物行爲推向極致的郭孝子就是這後一類人的典型代表,而緊隨其後出場的蕭昊軒、蕭雲仙父子則似乎是作者特意設置的、以跟郭孝子父子形成對比的一組人物——他們之間的對比似乎在提醒人們: 在恪行忠孝與實現個體人生價值之間實際是存在着一些現實矛盾的,如何協調這些矛盾,從而使之達到最理想的平衡狀態呢?
應該説,蕭昊軒、蕭雲仙父子對於忠孝二字的理解與遵行其實跟馬二先生、郭孝子等人之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只不過由於各人胸懷與人生境遇之不同,才導致了不同的行爲和結果。考慮到這些,我們將會更進一步理解郭孝子、蕭雲仙故事在整部小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明白這些故事其實跟作者對“文行出處”這一根本問題的表現與思考是密不可分的。至於郭孝子故事中那些傳奇性的驚險遭遇自然也是作者塑造這一極端人物的必要手段,其敍事風格也跟吴敬梓一貫的風格並無任何不同。
小説中那些傳奇性的段落,我們更没有理由懷疑它們同樣出自吴敬梓之手。有學者認爲一部寫“儒林”的小説,不應當容納俠客、武將與神怪的内容,這未免把小説的題目看得太死,也把小説的内容限制得過於單一了。小説史上,不會有任何一部長篇小説會絶對遵循題目所限定的範圍來寫作而不越雷池一步。試問: 如果寫“儒林”的小説不應當容納俠客和武將,那麽我們是不是也要質問它爲什麽會容納販夫走卒、莊農倡優之流的人物呢?夏總甲、胡屠户、牛老爹、卜老爹、王義安、鮑文卿、聘娘、鳳四老爹、四位市井奇人等非“儒林”人物是不是也要被剔除在外呢?剔除了這些人物之後,這部小説還能表現豐富多樣的人生百態嗎?顯然,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一種懷疑。
《儒林外史》作爲一部素材來源衆多的長篇小説,其取自史傳、筆記、前代文言小説、白話小説、當代傳聞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朱一玄、劉毓忱所編《儒林外史資料彙編》之“素材編”得到十分充分的證明。比如張鐵臂虚設人頭會、洪憨仙燒銀騙錢、施美卿老婆被搶、向知縣斷和尚騙牛、莊紹光遭蠍子蜇噬而無法奏對這些著名的傳奇性段落均來自唐代或明代的文言小説或白話小説,吴敬梓也不大可能有切身的經驗作爲創作基礎,但這些素材經他改寫進入新的語境之後,對塑造人物或者增强小説的趣味性都産生了很好的效果,這些地方没有人認爲不是出自吴敬梓之手,爲什麽偏偏要懷疑莊紹光往返京城途中遇到的兩件奇事,以及郭孝子入川途中的一系列驚險遭遇呢?對於這些遭到後代學者質疑的段落,清代的評點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給出了很高的評價,這一點實在是令人深長思之的。需要申明的一點是,筆者根據自己的閲讀感受,也認爲這些被懷疑的段落恰恰都是十分精彩的。這裏讓我們來看一下清人的評點:
第三十四回莊紹光遇響馬一段之後的“卧評”云:“遇響馬一段,縱橫出没,極文字之奇觀。昔人謂《左傳》最善敍戰功,此書應是不愧。”[注]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430。筆者案: 前文已經論及,這一段乃是要爲後文蕭雲仙的出場做鋪墊的。
第三十五回莊紹光出京後遇老婦詐屍,老翁亦死,出資埋葬二位死者。各位評點者都看出這一段寫得十分符合莊徵君的身份,且有特殊的敍事意義,比如張文虎的評語説:“亦可謂仁至義盡。初出門有趙大一節,歸來又有此一節,便不直率。全書慣用此法。”[注]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437。筆者案: 這一段情節確實寫得十分驚悚離奇,近似於唐代的一些恐怖故事,但這一段對塑造莊紹光的誠篤爲人與學者心性卻有繪影傳神之效果,尤其是他發現老婦詐屍,老翁也死,遂逃到門外,心裏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虚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理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這一段文字對莊紹光作爲儒家學者的特定身份與心性真是做了十分傳神的刻畫!
第三十八回寫郭孝子深山遇到老虎、怪獸和雪道兄,又遇木耐打劫。情節的創意前二者均來自唐代小説,後者來自《水滸傳》,神怪或傳奇色彩頗重,但被分别放在深山月夜和大雪天來寫,顯得情境如畫,生動鮮明,乃是吴敬梓的天才的創造,實在遠勝於原作。“臥評”“黃評”“天二評”均給予這一回以很高的評價,比如“臥評”云“文章至此篇,可謂極盡險怪之致也。長夏攤飯時讀之,可以醒睡,可以愈病。”“黃評”則云:“此篇略仿《水滸傳》,未嘗不驚心駭目,然筆墨閒雅,非若《水滸傳》全是强盜氣息。固知真正才子自與野才子不同。”[注]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480。筆者案: 蜀道之難,自應在行文中有必要之渲染,這麽做,才能進一步讓人感受到郭孝子尋父所歷之無數艱難困苦。“黃評”正確地指出了從素材到作品的根本性變化——“筆墨閒雅,非若《水滸傳》全是强盜氣息”——也就是語言風格的變化,變成了徹底的吴敬梓式的閒雅簡勁風格。後文兩寫戰事,顯然也模仿了《三國》和《水滸》,但也變成了地道吴敬梓式的風格,藝術氣質也就大不一樣了。筆者認爲它們其實是大大超過了《三國》與《水滸》的相關敍述與描寫的。
第三十九回蕭雲仙救難明月嶺一段,“黃評”云:“前寫郭孝子遇虎,一毫不犯《水滸傳》諸書筆路,此段有意與《水滸傳》相較,便筆路相近。然簡潔雅馴,《水滸傳》萬不及也。”其他各家評語對這一段的評價也很高,于筆者之心均頗有戚戚焉。
需要補充説明的一點是: 黃小田、張文虎對《儒林外史》的評點並没有受到任何商業促銷因素的影響,而主要是出於他們個人對此書的真心喜好,[注]李漢秋《〈儒林外史〉的評點及其衍遞》,收入李漢秋輯《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14—21。大體上是比較忠實於他們自己的閲讀感受的。因此,後人對這些部分的不同看法,跟他們相比,頂多只是見仁見智而已,也談不上更爲客觀,或更爲準確。
五
在以上這些論證的基礎上,筆者最後還要特别提到鄭志良教授不久前發現的寧楷的《〈儒林外史〉題辭》與吴敬梓的《後新樂府》組詩。在《〈儒林外史〉題辭》中,寧楷明確地提到了郭孝子和湯鎮臺的故事:
黃金散盡,義重憐寒;白骨馱回,勳高紀柱。考稽典禮,收寶鼎之斑斕;衡鑒名流,挹冰壺之瑩徹。伐苗民而滅醜,華夏爲功;歌蜀道而思親,虎狼不避。[注]原文參見鄭志良《〈儒林外史〉新證——寧楷的〈儒林外史題辭〉及其意義》,載《文學遺産》2015年第3期。
筆者已經另文論及: 《題辭》中“白骨馱回,勳高紀柱”與“非聖賢之滴(嫡)派,即文武之全材”這兩句都是指蕭雲仙,因爲除了他,整部小説中没有人可以當得起這一評價。[注]筆者《〈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爲吴敬梓所作新證》,載《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春之卷。而在《後新樂府》組詩中,則收有《青海戰》(“志邊功也”)一篇,歌詠的正是蕭雲仙的原型人物李畝的事迹,而李畝正是吴敬梓的友人;《後新樂府》中《茸城女》(“傷仳離也”)一篇涉及沈瓊枝的原型茸城女子沈珠樹的故事;《棘闈怨》(“感士習也”)一篇諷刺科場舞弊現象,《儒林外史》中對此也多有描寫;《友系獄》(“刺朋友失義也”)一篇則諷刺某人系獄後其朋友朋皆遠避的情形,這讓我們想起《儒林外史》也寫過類似的情節,比如潘三系獄之後,匡超人拒絶前往探看這一段情節與《友系獄》一詩所詠主題就緊密相關——這些線索綜合起來,都可以説明小説中蕭雲仙故事的作者也應該就是吴敬梓。而經過學者們的進一步考證,蕭雲仙原型李畝的越來越多的事迹都在小説中發現了投影,比如蕭雲仙參與收復青楓城之戰是以李畝參與過的、由年羹堯指揮的青海桌子山之戰爲原型的,蕭雲仙在青楓城興修水利、勸農興學這些事,跟李畝在青海大通衛駐防時的所作所爲也頗爲近似。[注]鄭志良《新見吴敬梓〈後新樂府〉探析》,載《文學遺産》2017年第4期;李遠達《文人“兵”夢的實與虚——〈儒林外史〉蕭雲仙、湯鎮臺本事補證》,載《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春之卷。此外,湯鎮臺的原型早已被學界考證出是指吴敬梓的另一位朋友楊凱,這裏就不必多談了。
其實,在吴敬梓的詩文中,跟李畝和楊凱有關的詩還有三首——《贈李俶南二十四韻》(作於乾隆二年,1737)、《贈楊督府江亭》(作於乾隆四年,1739)、《雨夜楊江亭齋中看菊》(作於乾隆四年,1739)——李漢秋先生早已指出這些詩所描寫的李俶南和楊凱是蕭雲仙和湯鎮臺的原型,也指出了吴敬梓對湯鎮臺故事的著作權,但没有指出他對蕭雲仙故事的著作權。最近李漢秋先生又發表《〈儒林外史〉蕭雲仙故事考論》一文,結合鄭志良新發現的材料,明確論證了吴敬梓對蕭雲仙故事和湯鎮臺故事的著作權。[注]關於這三首詩的箋注可參看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吴敬梓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儒林外史〉蕭雲仙故事考論》一文載《文學遺産》2016年第5期。李先生這篇論文又重新討論了對學界所熟知的程晉芳《哭吴敏軒三首》“其三”中兩句詩“豔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徵(自注: 君好爲稗説,故及之)”[注]全詩爲:“促膝閑窗雨灑燈,重尋歡宴感偏增。豔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徵(自注: 君好爲稗説,故及之)。身後茅堂餘破漏,當年丹篆想飛騰。過江寒浪連天白,忍看靈車指秣陵。”的解釋問題: 認爲上一句暗指湯鎮臺的野羊塘大戰(所謂“歌舞地酋長劫營”),後一句則是指蕭雲仙故事。對於這一説法,筆者認爲還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反復體會原詩,把“豔歌蛺蝶情何遠”一句解釋成湯鎮臺野羊塘大戰終覺有些牽强,還是理解爲指吴敬梓平生的詩詞創作比較穩妥一些,在吴敬梓存世的作品中有《閒情四首》《美女篇》《念奴嬌·枕》這些詩詞,均帶有古樂府或唐宋詞描寫女性與愛情的“豔歌”的特徵,其中正好也出現了“媚蝶”“蝴蝶”這類意象,而且作品中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更深遠的寄托,也符合“情何遠”的特點。如果這一句指他的詩詞,那麽後一句指他的小説《儒林外史》的創作,就顯得頗爲順理成章,也更符合挽詩的基本體例。但後一句究竟是不是在指《儒林外史》中蕭雲仙的故事呢?對這一點,筆者認爲可能還需作進一步論證: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散錄雲仙”這一説法應該是來自五代時期馮贄的小説集《雲仙散錄》這一書名,當然也跟此書内容是記載唐五代一些著名人士的逸聞趣事有關。《儒林外史》講述的也是“儒林”中人的諸多逸聞趣事,這一點二者很相似,但《雲仙散錄》中的故事大都荒誕不經,而《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則大都有事實依據,是“可徵”的,這是二者的不同之處。再結合程晉芳的“自注”來看,這一句是指《儒林外史》的創作,這是完全没有任何疑問的。那麽,程晉芳是僅僅從這一角度來運用“散錄雲仙”一詞呢,還是同時雙關着蕭雲仙的故事呢?筆者反復思考,覺得程晉芳在這裏用《雲仙散錄》這樣一部並不太重要、也並不多麽著名的小説集來暗指吴敬梓的小説創作,[注]當然,筆者需要指出的一點是: 《雲仙散錄》這本書在清代並非偏僻之書,吴敬梓在他的《閑情四首》其一中就使用過該書中的故事入典——“雖無美酒傾三雅,尚有新詩詠九迷”。參見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頁192。還是有些奇怪的,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程晉芳應該是在看到《儒林外史》中的蕭雲仙這一人物之後聯想到《雲仙散錄》一書,於是用這一名詞來同時指《儒林外史》以及其中人物,這一疑惑就焕然冰釋了。更何況,《雲仙散錄》的“序”也提到編撰者是“事科舉,蓋三十年,蔑然無效”,於是“退歸故里”,編成了這本書[注]馮贄《雲仙散錄》,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5。——這跟吴敬梓創作《儒林外史》的處境也頗爲相似。因此,從這些角度來考慮,這句詩極有可能是小説本身與蕭雲仙故事的雙關。而李漢秋先生已經指出: 這首詩作於吴敬梓去世這一年的除夕以前,這時應該還不太可能有人來得及竄入蕭雲仙的故事呢——也就是説,蕭雲仙的故事在吴敬梓的原稿中應該已經存在了。
總之,結合本文(以及另兩篇拙文)所作的全部論證以及新發現的這些證據來進行全面考察之後,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認爲: 《儒林外史》原就是五十六回,跟郭孝子、蕭雲仙、湯鎮臺相關的全部故事,以及第五十六回全回,都出自吴敬梓本人之手,絶非他人竄入。
在反復閲讀小説文本與有關學術論著的過程之中,筆者常常會想起魯迅先生當年説過的那句話——偉大也要有人懂。我們應該把這部五十六回的小説當作一個完整的整體來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以期獲得對其思想主題與藝術成就的更全面、更公允、也更深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