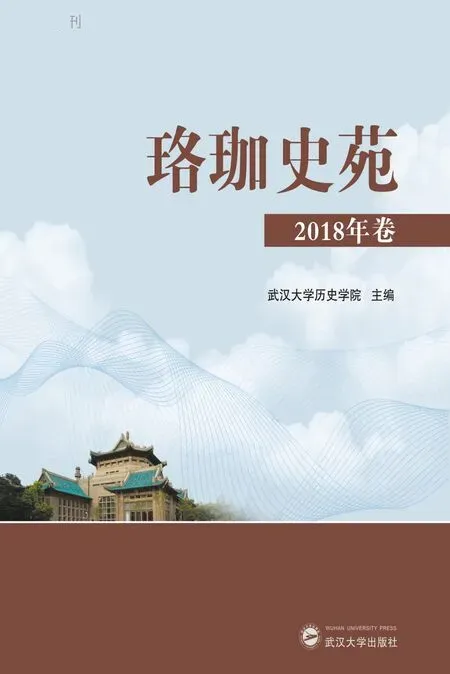中国南方地区佛教遗存研究综述
2018-01-23周静怡
周静怡
一、主要材料介绍
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较能够确定的佛教遗存主要为以下几类。
(一)佛教遗物
本文讨论的佛教遗物,指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以及墓葬本身指示佛教内涵的构件,如石刻、画像砖等。主要指示的是佛教对于丧葬文化的渗透,或说佛教内涵在丧葬文化中的应用与表现。需要指出的是,佛教遗物的出现总体早于佛教遗迹,并且主要存在于东汉末至南朝末期,到隋唐以后,墓葬中的佛教因素几乎消失不见,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也非常值得探究。
本文在此讨论的佛教遗物内容如下。
1.墓葬构件
云南①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以及四川地区早期墓葬中的莲花纹砖②目前相关的莲花纹砖材料有:a.彭山崖墓951-2号墓墓门,罗二虎:《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6页,图三七;b.彭山崖墓莲花石刻,李正晓:《中国内地汉晋佛教图像考析》,《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第118页;c.凉山西昌采集莲花画像砖,刘世旭:《四川凉山早期佛教遗迹考》,《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第38~42页。、佛塔画像砖③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第62~64页。,以及崖墓中的石雕坐佛④目前相关的石雕坐佛材料可见: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69~74页;何志国:《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年代商榷》,《考古》1993年第8期,第760~763页。应当是目前年代最早的材料,非常零星,大多公布状况不佳,图片多数较模糊,且很多是采集所得。依照原报告的观点,这些材料一般能够早到蜀汉甚至东汉晚期,但同时多缺乏确切证据。
到了南朝时期,墓葬中能够明确指示出佛教联系的实例明显增加了。⑤韦正:《试谈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第91~100页。莲花纹、忍冬纹此时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砖室墓中习见的砖雕装饰。瓶花、飞天、供养人等浮雕形象,或许除佛教因素以外,还有更复杂的文化内涵。墓门处常成对雕刻的狮子形象,是佛教文化中的守护形象在墓葬中的应用。而少数墓葬中出现的明显的砖雕佛像以及僧人形象,还有后壁拼砌的砖塔,似乎直接指示出墓主人对佛教的信仰、对僧人的尊崇。然而这样的尊崇,却也有别于真实的宗教信仰,而更类似于将佛教供养方式转借到世俗墓主人的供养方式上来。
而南朝时期墓葬中较突出、较显著的佛教因素却并未在隋唐时期继续发展。莲花、忍冬以及瓶花纹几乎完全成为墓葬中习见的装饰纹,丧失了曾经的佛教文化内涵,其他明确带有佛教色彩的画像纹在此时基本不见。
2.随葬品
随葬品的佛教文化内涵大部分表现为在器物上装饰类似飞天、僧人甚至佛像的纹样。还表现为在一些陶瓷俑额头装饰白毫相。此外,一些陶瓷俑或为胡僧,甚至是佛像,这或许是更明确的佛教内涵指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佛像在这一时期除了出现于某些日常器物,如唾壶、香薰以及青瓷尊等以外,多数选择的载体是较为特殊的器物。长江上游的摇钱树、中游的铜镜,以及下游的魂瓶,或具有天人合一的宗教内涵,或具有辟邪的作用,或象征着死后世界。佛像承托的载体,或许也证明此时佛教信仰是作为丧葬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隋唐时期墓葬中习见的天王俑,也应当是佛教流行的结果①沈睿文:《唐镇墓天王俑与毗沙门信仰推论》,《乾陵文化研究》2010年,第138~152页。,而这类随葬品与佛教信仰是否有更直接的关系,是否可以归为佛教遗物,还需斟酌。
(二)佛教遗迹
中国南方地区的佛教遗迹主要有考古发掘的寺庙、窖藏、僧人墓,以及石窟寺与摩崖造像。
近年来佛教寺庙的研究一般基于配合城市考古而进行的发掘和勘探工作,在都城方面,最主要的是南京建康城②蒋赞初:《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第153~161页;贺云翱:《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第101~113页。。然而除了南京钟山上定林寺①贺云翱:《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瓦当及与南朝上定林寺关系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73~82页。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以外,其余的或仅有简单的文字考证,如建初寺、禅众寺;或仅发现零星的遗物与碑刻,如开善寺②贺云翱:《南京独龙阜东出土南朝石塔构件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第132~135页。、慈恩寺、长干寺③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等。而地方的佛教寺庙大部分经过严格而系统的考古发掘,对寺庙进行了局部甚至整体的揭露。目前的发现有:扬州唐城寺庙遗址④南京博物院:《扬州唐代寺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文物》1980年第3期,第28~37页。及其相关研究⑤罗宗真:《唐代扬州寺庙遗址的初步考析》,《考古》1981年第4期,第359~362页。、边疆军州的邛崃龙兴寺遗址⑥成都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局:《邛崃龙兴寺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6~502页。,县城级别的巴东旧县坪唐宋寺庙遗址⑦武汉大学考古系、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旧县坪》,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以及集镇级别的云阳明月坝唐宋寺庙遗址⑧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管所:《重庆市云阳县明月坝唐宋寺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第30~44页。等。此外,还有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大理巍山龙于图城南诏寺庙遗址。⑨云南省博物馆巍山考古队:《巍山垅圩山南诏遗址1991—1993年度发掘综述》,《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6,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5~2568页。佛教寺庙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要对出土的佛像、陶瓷器以及其他的佛教遗物进行分析研究,更要关注寺庙本身的布局等问题。
佛教窖藏遗迹的发现相当丰富,种类也较多。多数与佛教寺庙相关,位于寺庙遗址附近,或原为寺庙,后来完全废弃。巴东旧县坪、邛崃龙兴寺等寺庙遗址周边均发现了一些残损的佛像残件;南京红土桥出土的一批南朝佛像则被考证为延兴寺旧址10王志高、王光明:《南京红土桥出土南朝泥塑像及相关问题研讨》,《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第48~58页。。同样,也有零星的灰坑遗迹或水井中,出土文物全部为佛像残件与佛教遗物的情况,这部分材料的性质与来源便较难辨别。如成都、茂县、彭州等地出土的一批南朝造像①雷玉华:《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成都考古研究(一)》下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1~648页。,南京德基广场工地出土的铜佛像②贺云翱等:《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3年第1期,第143~153页。等。
目前已公布的僧人墓资料仅有武昌津水路一座五代墓,漆木葬具保存完整,还出土多件随葬品。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考古系:《武汉市武昌区津水路五代墓的发掘》,《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此外,江西瑞昌曾发现一座破坏严重的唐墓,结构已经全部毁坏,仅出土四件器物。④何国良:《江西瑞昌唐代僧人墓》,《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8~10页。
南方地区的石窟寺与摩崖造像仅集中分布于东南、西南两个地区。东南地区规模最大、造像最集中的地点为连云港孔望山与南京栖霞山两地,规模略小,或较零星的材料在江苏、浙江其他地区亦有。西南地区的龛窟造像主要集中于四川、重庆与云南三省。其中云南省的材料应属于当时的南诏大理政权,在相应年代范围的主要为剑川石窟。四川、重庆地区的材料非常丰富,集中于四川盆地,几乎每个县市都有相关发现。而目前在川南山地发现的一些材料更具地方特色,与云南南诏的材料或更接近。川西的材料基本未见公布,或应当与西藏的文化系统更接近。目前将四川地区的材料依照平原内河流的流域分区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在一般情况下,将该地区简单分为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几区,便于指代。目前可见这几个地区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
二、研究现状
佛教考古一直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热点与重点课题,但长久以来,南方佛教考古工作比起北方,却一直是相对落后的,无论是发现情况,还是研究水平。主要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主要依据南方地区零星的佛教遗物的发现情况做一些考证与推测。俞伟超先生曾对东汉末期的佛教图像做过收集与分析,发表了《东汉佛教图像考》①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第68~77页。一文,但其中大部分的材料在年代上都存在争议。阮荣春先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调查工作,将南方地区发现的所有佛教遗物进行了收录与整理,并参与编写了《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②贺云翱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但仅对大部分文物进行了简单的收录,并未配以图片,对发现地点的描述也稍显粗略。同时,对于大部分文物的年代并未做细致的再考证再确认,大部分依旧使用的是发现者判断的年代,也并未给出详细的断代证据,而这批材料大部分在实际的断代上都存在争议。宿白、吴焯、温玉成先生也就相关问题发表过一些文章。
关于佛教的发展程度、表现形式、制度等问题,除了针对特定的一些佛教遗物以外,还有对墓葬中的佛教因素、出土大量佛像的窖藏进行分析研究的,不仅仅是专门进行佛教考古研究的学者,很多传统考古学者也针对自己手中的一手材料,用传统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佛教考古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与探讨。何志国先生曾对大部分的佛教遗物,如佛像柱础、陶瓷器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所收材料最全、最具参考价值的还是其对摇钱树的研究。③何志国:《汉晋佛像研究综述及展望》,《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542页。吴桂兵先生曾对长江中下游的白毫相俑做过系统的研究。④吴桂兵:《白毫相俑与长江流域佛教早期传播》,《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第59~65页。仝涛先生曾对魂瓶做过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其中对于贴塑佛像魂瓶的分析与一些简单探讨很有参考价值。①仝涛:《长江下游地区汉晋五联罐和魂瓶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王仲殊先生对于佛兽镜的研究②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考古》1985年第7期,第636~643页。,以及同日本学者的讨论,虽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技艺的传播,但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一些对当时佛教发展程度、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的简单探讨。徐劲松先生则基于自己在鄂州整理的材料,对鄂州发现的佛教遗物做了梳理和简单考证,大部分涉及的材料都具有详尽清晰的单位、地层证据。③徐劲松:《鄂州塘角头六朝墓地整理收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第61~66页。上文提及的韦正先生亦从传统考古的角度出发,对一些六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并且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对于佛像窖藏以及佛塔地宫的研究则较少,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这一时期的发现不多,目前仅有成都地区发现的一批南朝佛像,以及云南地区零星出土的一些材料,邛崃龙兴寺、巴东旧县坪等发现佛教寺庙的遗址在寺庙周围也发现了类似佛像窖藏的遗迹。然而大量的发现仍然集中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年代上基本在五代以后。不过一些主要研究北方材料的学者对这类窖藏进行的梳理,以及对埋藏原因的分析同样非常值得参考。山东大学高继习博士发表的《宋代埋藏佛教残损石造像群原因考——论“明道寺模式”》④高继习:《宋代埋藏佛教残损石造像群原因考——论“明道寺模式”》,《海岱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0页。一文,对近年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情况做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梳理,并且提出了自己关于埋葬原因的一些观点。张利亚的《北宋舍利崇奉的世俗化趋势——以甘肃泾川龙兴寺出土舍利砖铭为例》⑤张利亚:《北宋舍利崇奉的世俗化趋势——以甘肃泾川龙兴寺出土舍利砖铭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4~79页。一文,则主要就泾川发现的砖铭,结合相关文献进行了讨论和考证。崔峰先生《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①崔峰:《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79~87页。一文中的观点则更像前二者的结合。迄今为止,佛像造像的类型学研究仍未完成,关于瘗埋原因的判断仍未确定,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此外,徐苹芳先生对唐宋塔基地宫②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第59~74页。、舍利瘗埋,以及墓葬中明器神煞的考证和分析③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第87~106页。,虽然并未过多地涉及南方地区六朝至隋唐的材料,但其对礼制,甚至一种“精神制度”的探讨,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配合城市考古进行的佛寺位置、布局的考证与探究。北方的相关工作在较早时期,已有宿白先生对北朝到隋唐的长安佛教寺庙进行的考证④宿白:《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第28~33页;宿白:《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第27~40页。,为以后的工作立下范本。南方地区则主要是针对在南京城中一些零星的发现进行的相关佛寺的考证。蒋赞初先生是相关工作的最早进行者,其《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⑤蒋赞初:《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第153~161页。一文对文献中记载且当时较能够确定的佛寺遗址进行了列举和介绍。贺云翱先生则在将近二十年之后⑥贺云翱:《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第101~113页。,在蒋赞初先生的基础上,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增加了几座能够确定的寺庙,并对之前的一些材料进行了补充说明,及对南京佛寺的布局提出了自己的构想。而清华大学的王贵祥先生⑦王贵祥:《东晋及南朝时期南方佛寺建筑概说》,《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6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则从古建筑学的角度,对六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建筑布局进行了考证。
石窟寺与摩崖造像的考古发掘与调查,主要由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开展相关工作。目前东南地区如南京栖霞山石窟①魏正瑾、白宁:《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石窟寺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203页。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②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7期,第1~7页。的基础调查与发掘工作已完成,相关的研究性文章也已经较为完备,仍有一些零碎的材料未见公布。而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基础调查工作现在依旧在进行,主要由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艺术学院,以及省与地方考古所联合开展,并且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肥田路美、滨田瑞美等学者参与合作。目前材料依旧较零碎,很多未公布,或未经系统的整理,整合得较好的报告有《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④绵阳市文物局等:《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等,较完备的分期分型成果有姚崇新先生对广元石窟的研究⑤姚崇新:《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成都市考古所雷玉华女士对巴中石窟的研究⑥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等。此外,针对四川地区整体的分期分区研究目前仍较少,较早的有1991年胡文和先生根据自己在四川地区的调查工作撰写的《四川摩崖石刻造像调查及分期》⑦胡文和:《四川摩崖石刻造像调查及分期》,《考古学集刊7》,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03页。一文,以及随后发表的《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⑧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胡文和先生的工作非常重要,《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一书中所收集资料非常完整,但很多并无图片和具体龛窟情况的描述,目前最新的针对四川全境的研究成果是雷玉华女士2014年发表的《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①雷玉华:《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219页。,该文在材料的介绍以及分期分区的方法层面很值得借鉴,但因涉及材料较多,只能进行比较粗放、基础的研究,更深入的研究大概还要在更多的材料公布后才能进行。
边疆考古、少数民族,以及中外交流等课题中,也有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如云南地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一些发现。最主要的是针对剑川石窟开展的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但目前考古学方面的材料不多,大部分文章都仅进行了简单的美术层面的鉴赏。原始资料方面,最值得参考的是2000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发表的《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②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剑川石窟考古研究课题组:《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第71~84页。,而宋伯胤先生早在1985年发表的《剑川石窟》一书③宋伯胤:《剑川石窟》,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直至目前仍旧颇具参考价值。研究方面,刘长久先生的《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一书④刘长久:《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云南石窟与摩崖造像艺术》一文是目前相对较值得参考的成果⑤刘长久:《云南石窟与摩崖造像艺术》,《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第112~117页。。时代稍早的还有针对云南地区梁堆墓中佛教因素的一些探讨,但材料公布不多,且多不够清晰。
三、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南方地区佛教遗存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对研究现状做了简单的回顾。自此,我们了解到,几十年来,南方地区的佛教考古领域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起步工作,并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云南地区与内地较割裂。虽然云南在相应年代属于南诏大理国政权,但其仍属于汉传佛教的范畴中,与内地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然而材料公布很少,且多数非常简单、非常粗略。其实从仅有的这些材料中,已能感受到其重要性:无论是早期梁堆墓中出土的莲花石刻、胡僧俑,巍山龙于图城南诏寺庙的相关发现,还是剑川石窟的相关内容,在形态、内涵上都具有特殊性,且年代似乎都偏早,这批材料或许对研究内地的汉传佛教传入与传播路线有很大的帮助。除了资料数量较少以外,大部分资料都仅发表在《云南考古》等省内期刊上,内地的学者较少关注。今后内地的考古工作者若加强与云南工作者的联系与合作,或许能够改变这样的现状,同时加强对中外交流、边疆、少数民族等相关课题的研究。
各地区的研究水平较不平衡,甚至差距较大。贵州、广东、湖南、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的发现与研究仍旧较少,甚至基本为空白。然而其中某些地区在传统历史考古的工作方面同样力量较薄弱,应当首先加强传统考古学的力量,打好基础,并同样加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与合作。
方法论层面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和修正。佛教考古,应当是利用传统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遗存,应当是中国考古学大课题其中的一个课题,不应当完全摒弃传统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而早期的佛教遗物虽然有一些为采集品,但其余材料的相关研究也常常与其发现的地点或出土的单位割裂开来,石窟寺研究中的不少分期与分区工作未建立在对龛窟形制与造像类型严格分型分式分组的基础上。
对不同材料的研究也较不平衡。目前龛窟造像发现较集中的地点,如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大足石刻等,相关研究开始较早,分组分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剑川石窟、夹江千佛岩等地点并未进行系统的分组分期工作,但受到的关注仍旧较多。然而目前四川盆地西部、南部的大量小型龛窟遗迹,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大量的材料缺乏系统的公布与介绍,这或将成为四川地区今后工作的重点。